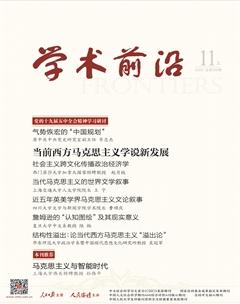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敘事
王寧
【摘要】在一個被認為“宏大敘事”早已解體的時代,“世界文學”可算作21世紀以來一種新崛起的“宏大敘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以及歌德等人對這一敘事作出過奠基性的貢獻。在馬克思主義世界文學理論基礎上,東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和比較文學學者不斷耕耘,逐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敘事。中國的理論家和學者對之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近年來中央領導高度重視世界文學的理念,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之關系的講話精神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觀,對撰寫一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學術史貢獻了中國的智慧和思想。當前,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建構一種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世界文學敘事,已提到了中國學者的議事日程上。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世界文學? 西方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文學敘事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1.003
在一個被認為“宏大敘事”早已解體的時代,我們還能建構怎樣的“宏大敘事”呢?如果我們并不否認,“世界文學”可算作21世紀以來一種新崛起的“宏大敘事”之話題的話,那么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研究則是支撐這一宏大敘事的一種頗有生機和影響力的敘事。盡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研究尚未成為當今國際學界的又一個前沿理論話題,但是東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和比較文學學者卻在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奠基性貢獻,可以說,正是這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學者們的著述不斷地從邊緣向中心運動,進而逐步形成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敘事,中國的理論家和學者無疑對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并且致力于為建構這一敘事提供中國的經驗和中國學者的智慧。但是我們也不應忽視東西方其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貢獻。本文的寫作就是在梳理國際馬克思主義世界文學研究著述之基礎上建構這一敘事的嘗試。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研究之啟示
不可否認,馬克思主義是來自西方的一種理論,世界文學這一術語也最先出于西方作家之手。[1]因此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理論視角來考察研究世界文學就無法排除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貢獻。盡管不少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僅僅將馬克思主義當作西方眾多哲學流派之一來研究,但是近二三十年來,新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已不滿足老一輩理論家僅僅將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哲學理論思潮來研究的傳統做法,他們試圖返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原作。他們認為,研究全球化和世界文學就必須從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開始,這樣才能在一個新時代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觀。這充分說明馬克思主義是在不斷發展的,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也應該在新形勢下不斷發展和創新。在結構主義等專注形式的批評理論思潮風靡西方文學理論界時,正是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高舉馬克思主義的大旗,堅持文學批評的“歷史化”(historicization)和意識形態傾向性(ideological tendency),從而發出了一種異樣的聲音。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的話,我們還應該進一步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于世界文學研究以及其具體作家作品分析時,也作出了一些理論建樹。在這方面,幾位當代杰出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無疑為世界文學話題在新世紀的再度興起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國內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研究成果介紹很少,而且這方面的成果即使在西方學界也十分鮮見。英國學者希·薩·伯拉威爾的《馬克思和世界文學》(1976)一書可算是這方面極少數可見到的著作之一,該書在英語世界出版后備受冷遇,但在中國學界卻受到較高的重視。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來,這部著作的學術性并不很強,加之伯拉威爾并沒有系統、全面地從理論的視角來深入考察世界文學這一個概念及其歷史演變,因而對當下關于世界文學問題的討論基本上未產生任何影響,甚至鮮為今天的世界文學研究者引證或提及。但是該書除了以一種輕松流暢的文學筆觸描述馬克思對文學的興趣和那些即興的有感而發的批評文字外,作者還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出發,對世界文學之于當下的意義作了某種預見:
在我們現在的二十世紀,通過翻譯、紙面書籍普及本、巡回演出、廣播、電影和電視,以那些不會使馬克思感到吃驚的方式改變了我們的文化視野,我們已看到“民族的與地方的”文學的混合和世界范圍的傳播。作為一個龐大想象豐富的博物館,一個偉大的巴貝爾圖書館,“世界文學”猛然到來了。[2]
伯拉威爾在書中指出一個頗有理論前瞻性的觀點,即盡管馬克思本人未能預見現代社會的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及后工業和后現代社會的文學狀況,但是馬克思卻站在一個歷史的高度對當今時代的一些社會和文化癥候作了準確的預示,并在一百多年前就預見了一個即將到來的世界文學時代。因此在他看來,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研究者仍然可以根據今天的特定形勢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理論進行新的闡述。他的這一看法對我們的啟示在于,世界文學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已不再是早先的那種“烏托邦式”的假想,而是成了一個不可回避的文化現實。對于新一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來說,他們所考察和分析的文學作品也應該是全世界范圍內的優秀文學作品,這顯然超越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局限。
英國曾經是馬克思生前從事革命活動的地方,那里有著豐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文化土壤,我們都知道,馬克思的許多著作都是在大英圖書館寫成的,有些著作是他同時用德文和英文撰寫的。在當今的英國大學中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左翼學者也不是少數,他們異常活躍,有著較大的學術和社會影響力。雷蒙德·威廉斯和特理·伊格爾頓這兩位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公開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由于他們專事文學理論批評,因而也是英語世界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和研究者。他們雖然沒有專門對世界文學問題作過較多的思考和研究,但他們對文學理論問題的思考和論述卻為當今的世界文學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威廉斯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一書的第一章“基本概念”中就從考察本民族的文學——英國文學史入手,其中也涉及包括歐洲其他國家文學的世界文學。[3]他認為這些世界文學經典作品的意義和影響并不局限于英語文學,而且對整個世界性的文化語境和世界文學都有一定的影響和啟迪,因此他提出的這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問題也同樣適用于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此外,威廉斯還基于對馬克思原著的仔細深入閱讀,進而發現,“相比之下,馬克思主義在關于語言本身的理論上卻貢獻甚微”。[4]他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文化唯物主義”的重要思想,并將其貫穿全書始終。伊格爾頓則在一開始就宣稱自己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曾經以政治傾向性鮮明的著作《文學理論導論》(1983)而蜚聲英語文學理論界。在世界文學理念興起的新世紀,他還出版了題為《為什么馬克思是對的》(Why Marx Was Right, 2011)這本引發爭議的著作,他在書中選取了當今學界十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偏見和批判性觀點,予以一一批駁,著述文風依然沿襲了早先的機智、譏諷和雄辯,對西方學界行將冷卻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起到了一定的“升溫”作用。[5]可見,對于伊格爾頓這位以文學和文化批評擅長的學者型理論家而言,遠離文學理論批評實踐而對馬克思主義加以抽象的闡釋和辯護并不一定會對人們更有吸引力,至少對當今的世界文學研究未起到應有的影響和啟迪。
作為一個問題導向的世界文學理念在本世紀初率先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關注并從內部予以推進。在這方面,意大利裔美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和比較文學研究者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他所發表的關于世界文學的一系列論文引發人們對之再度關注,因而這些著述已經成為當前所有介入關于世界文學問題討論的學者們無法繞過的經典著述。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這位在中國以其馬克思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研究著稱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近二十多年來尤其關注全球化與文化問題,并針對世界文學和文學史的寫作發表了一些著述。毫無疑問,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關于世界文學和文學經典問題的著述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研究,為我們今天建構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敘事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在最近的十多年里,由于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民族/國別之間的文化和文學交流也日益頻繁。這不禁使人們感到,當年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學”的概念絕不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想象,而是一個存在于當今時代的文化和審美現實。因此它再度浮出歷史的地表并成為國際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界的又一個前沿理論課題就不是空穴來風。在歌德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世界文學理念的影響和啟迪下,一些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針對世界文學問題發表了許多著述,從而促使這一概念在當今語境下逐步成型。他們同時也就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文學現象發表了著述,對之成為一個問題導向的理論概念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尤其是莫瑞提和詹姆遜的著述影響尤為突出。莫瑞提關于世界文學的主要著述包括論文《世界文學的構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2000)、《更多的構想》(More Conjectures, 2003)和《演化,世界體系,世界文學》(Evolution, World-System, Weltliteratur, 2009)等,在這些論文中,莫瑞提從今天的視角賦予世界文學這個老話題以新的意義和內涵。
在《世界文學的構想》一文中,莫瑞提拓展了歌德的“世界文學”構想,他認為,在當今時代,“世界文學不能只是文學,它應該更大……它應該有所不同”,[6]也即“世界文學并不是目標,而是一個問題,一個不斷地吁請新的批評方法的問題”。[7]基于此,他提出了一種“遠讀”(distant reading)的策略,對于我們從一個宏觀的視角來把握世界文學的精神不無啟迪。
詹姆遜的著述涉獵面更廣,但他近二十多年來密切關注全球化在文化上的影響,不僅組織學術會議討論這一問題,還將其與世界文學問題現象相關聯。在他看來,歌德當年提出的世界文學構想之所以在當今時代仍得到人們的不同理解和解釋,是因為人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啟示,才得以從今天的視角重新理解歌德的這一構想。詹姆遜因而指出:
事實上,歌德心目中所設想的世界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信息或交流的概念:在他看來,世界文學顯然不是指拜倫或魯米或沙恭達羅(這三者都是他十分仰慕的),而是《愛丁堡評論》和《兩個世界雜志》或《全球》。當各種民族情境能夠相互間討論它們的世界和文本生產時,世界文學便出現了;它并不是某種可供使用不同語言的所有作家在大學課程中和暢銷書榜上公平競爭的場地,也不是諾貝爾獎或CNN電視名人之間的角逐。[8]
他的這一觀點顯然與他長期以來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對后現代主義文化和文學的考察是一致的,也即在考慮到歷史文化發展的內在邏輯的同時,強調計算機時代信息傳播對各民族文化和文學之間交流的重要作用。這樣,詹姆遜便很自然地將世界文學的興起與全球化時代的信息傳播相聯系了,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體現了歌德當初提出“世界文學”概念的原意。[9]雖然詹姆遜并未對世界文學問題作更多的闡釋,但是我們從他上面的簡略論述不難看出,他試圖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用于描述全球化時代的后現代社會的文學和文化狀況,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蘇聯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世界文學研究
在建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敘事時,我們也不應該忘記蘇聯學者作出的貢獻。不可否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比較文學學者對世界文學研究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觀的形成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但是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占據主導地位時,他們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長期以來卻被有意地遮蔽了。但我們今天在梳理國際學界的馬克思主義世界文學研究成果時肯定要將其納入我們的考察視野,并視作我們建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即使我們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蘇聯學者在理論上的建樹和實踐上的創新也獨樹一幟,因此,我們在建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敘事時也完全應該把他們的研究成果包括進來。作為曾經在國際比較文學界產生過一定影響的“蘇聯學派”的主要研究方法——主題學就貫穿在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主持的《世界文學史》(九卷本)的寫作中。
早在上世紀80年代,蘇聯的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就啟動了大型文學史研究項目《世界文學史》的編撰工作。這部多卷本世界文學史書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陸續分卷在蘇聯以及后來的俄羅斯出版俄文版。這應該被看作是蘇聯-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獻給國際世界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份厚禮,它可以說是迄今為止全世界范圍內最大規模的一部世界文學史學術著作。主持這一項目的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聯合了蘇聯時期各加盟共和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機構的專家和高校教師歷經數十年編撰而成。這部文學史巨著的特色就在于其資料的完整性和理論分析的獨特性,至少突破了傳統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為后來不同國家的世界文學學者繼續深入全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當今的國際學界無論承認與否,都難以否認,九卷本的《世界文學史》之所以得以率先在俄羅斯出版,與前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不無關系。[10]而這在西方國家的人文學術界簡直是不可想象的,自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使與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組織編寫的多卷本《用歐洲語言撰寫的比較文學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s in European Languages)和正在進行中的《劍橋世界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兩卷本)相比,這部大型的文學史書在內容和容量方面也更勝一籌,并且具有內在的連貫性和歷史發展的邏輯性。同時,蘇聯—俄羅斯的研究人員都清醒地意識到,編寫這部《世界文學史》在一定程度上還推進了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11]
這部卷帙浩繁的文學史的編撰者們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和觀點出發,對有著相互聯系的世界各民族文學有著較為全面的整體把握,并且兼顧東西方優秀的文學作品和理論思潮發展的不平衡狀況,提出了相應的對策。當然,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歷史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共同道路上一些民族前進了,另一些民族落后了。這樣的不平衡性是歷史過程的動力之一。”[12]盡管如此,要撰寫一部客觀公正的世界文學史,就要在選擇作品和史料方面不低估所謂的“小民族”文學的歷史作用,也要努力克服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兼顧東方各民族文學的世界性意義和影響。
應該承認,由于特定時期的意識形態傾向性的影響,這部俄文版《世界文學史》仍留下一些冷戰時期的痕跡,編撰者們出于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對一些作家有著不同的偏好,這當然也是在所難免的,但是它對后來的任何民族/國別的世界文學研究者的世界文學史的重新書寫都是一座無法繞過的豐碑。可以說,它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敘事的建構作出的歷史性貢獻對我們今天建構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敘事也有著重要的啟示。
在最近的十多年里,筆者率先再度將國際學界的世界文學新理念引入中國,并在中文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十多篇論文。[13]其中的一些論文以不同的形式用英文改寫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后也引起了國際學界的矚目,從而使西方學者認識到,討論世界文學必須包括中國文學的理論與實踐,包括中國學者的相關著述,具有權威性的世界文學選集也應該收入更多非西方文學的優秀作品。[14]
由于世界文學與中國的密切關系,世界文學的理念于20世紀初進入中國就不是偶然的。這不僅是因為歌德在提出這一構想時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文學,同時也因為自19世紀末以來,世界文學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也和另一些西學理論思潮一樣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因此,我們今天在全球化時代探討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觀,就應當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貢獻也包括進來,因為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觀首先啟迪了中國的文學研究者,然后,中國學者從中國自身的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經驗出發提出的理論建構又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理論寶庫,為當代學者建構一種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敘事貢獻了思想和智慧。
早期的共產黨人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成仿吾、陳望道等人對于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均作出過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雖然沒有在西歐或蘇聯留學的經歷,但是他閱讀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以及列寧的一些理論著作,并通過長期的革命實踐發展了一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他的理論在國內統稱為“毛澤東思想”,而在國際學界則被稱為“毛主義”(Maoism)。毛澤東同志和他的戰友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并不是教條的東西,它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才能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同樣,毛澤東同志也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將其用于指導中國的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批評實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延安講話》)就是他的文藝思想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毛澤東同志始終認為,中國的文學藝術應服務于人民大眾,首先要為工農兵服務,因此它應該“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15]即使如此,毛澤東同志也沒有全然否定文學藝術的審美愉悅性和普及性,認為它應該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
毛澤東同志在強調建設民族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同時,也不否認這種新文化對古代和世界先進文化的傳承作用。他認為:“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對于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16]
但是對于文學創作的題材和源泉,毛澤東同志也有自己的辨證的看法,他認為,文學藝術創作必須反映社會生活,“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文學藝術中對于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17]不可否認,毛澤東同志的外國文學閱讀量無法與馬克思恩格斯對世界文學的涉獵相比,他讀過的世界文學名著數量也遠不及列寧和斯大林,他只能讀到一些外國文學翻譯作品,因此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很少提及外國文學。在整個《延安講話》中,唯一被他引證的一部外國文學作品就是出自蘇聯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說《毀滅》。[18]盡管如此,毛澤東同志在解放后關于文學藝術的所有文章和講話中,都堅持批判地繼承古代和外國的文學藝術,主張以“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原則來對待所有的世界文學遺產。他的這一理論建樹至今仍為中國共產黨的新一代領導集體所傳承和發揚光大。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毛澤東同志的國際聲譽及影響已經得到國內外的廣泛認可。[19]在美籍華裔學者劉康看來,“毛澤東同志的遺產,盡管有著爭議和矛盾,但一直有著持久的影響,因為他不僅為中國革命奠定了政治基礎,同時也提供了一種有著全球意義的理論,至少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是如此,那個時代以全世界范圍內的政治和社會波動而著稱。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尤其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諸國得到響應,正是那些國家和地區共同形成了一個第三世界”。[20]確實,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認為,在整個20世紀,確實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與毛澤東同志的成就和影響相比。毛澤東思想不僅影響了阿爾都塞、薩特等法國理論家,即使對波伏娃這樣的女權主義思想家[21]和阿蘭·巴迪歐這樣的當代毛主義者也有著極大的啟迪和影響。[22]此外,它也吸引了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這位毛澤東同志的崇拜者每次來中國訪問講學,都要尋訪毛澤東同志從事革命活動的足跡,這無疑表達了他對這位偉人的崇高敬意。
改革開放以來,更多的世界文學優秀作品伴隨各種西方現當代文藝理論思潮通過翻譯進入中國,對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產生了較大的啟迪和影響。曾經在中國大地上沉寂多年的比較文學也再度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世界文學這個話題曾在上世紀80年代就吸引了中國學者的關注,[23]但并沒有成為一個前沿理論課題。而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世界文學研究在西方學界的再度興起,更多的中國學者也介入了對之的評介和研究中,并將其與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相關聯。有些學者將世界文學這個概念的演變作一番梳理,有些則對世界文學進入中國的路徑進行述評,有些則結合比較文學研究和教學進行討論,有些結合文學經典的形成與重構問題闡述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思想。此外,由于目前世界文學研究的重鎮仍在西方,或更確切地說在英語世界,因此中國學者用中文發表的關于世界文學的眾多著述都并未引起國際學界的重視。但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世界文學研究也有一些具有普適意義的理論命題和觀點可以供國際同行參考和借鑒。
建構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敘事
如上所述,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思想對中國的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和啟迪,但這只是建構馬克思主義世界文學敘事的一個方面,也即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另一方面,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將其運用于中國的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的過程中又作出了自己的創新和發展,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就是在全球化這個平臺上實現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這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作為一種“旅行的理論”的兩個極致:從西方旅行到中國,經過中國的實踐后又旅行到西方進而影響整個世界。
世界文學的理念進入中國以來,不僅引起了當代文學理論界和比較文學界的高度重視,同時也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工作以來,針對繁榮中國的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批評發表了一系列講話,尤其體現在他于2014年在北京主持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以下簡稱《北京講話》)。國際學界常常將他的這篇講話與毛澤東同志早年的《延安講話》相比較,筆者也作過嘗試。在筆者看來,習近平總書記的這篇講話不僅繼承了毛澤東同志開創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同時還在當今的新形勢下創造性地發展了這一思想。他在講話中著重強調了這樣五個問題:第一,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需要中國文化的繁榮;第二,既然我們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那么就必須創造不負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優秀作品;第三,即使在當今這個新時代,我們仍必須堅持為人民而創作的方向;第四,中華民族的精神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第五,必須加強和改善黨對文學藝術工作的領導。顯然,習近平總書記以及新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繼承了毛澤東同志的文學藝術思想,并將其發展應用于當前的新時代。這一點尤其體現于黨的十九大及其一系列文件中,這次會議標志著我們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毛澤東思想仍然受到高度重視,并被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文學的人民性和世界性的思想貫穿于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始終。在毛澤東同志的《延安講話》中,通篇弘揚了一種民族主義和人民性,對世界文學的引證僅在于簡略地提及了一篇蘇聯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說《毀滅》,而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北京講話》中,則廣泛提及了從古希臘的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悲劇和喜劇,直到俄蘇作家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肖洛霍夫等,甚至還提及了現代西方作家羅曼·羅蘭、薩特、加繆、海明威等文學大師。其中不少作品應該是他在青年時代閱讀過的。這說明了習近平總書記廣闊的世界主義胸襟和面向全人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抱負。當然,這兩篇講話分別出自兩個不同的時代:在上世紀40年代的中國,壓倒一切的主流思想是打敗日本侵略者,使得中國早日成為一個和平獨立的國家。這時的文學藝術就必須服務于當時的形勢,這也許正是為什么同樣進入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及其理論思潮終究未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的原因所在。而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國,不僅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也要時刻為全人類謀利益,從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的智慧和思想。此外,尤其應該強調的是,習近平總書記還號召中國的文學藝術工作者,“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讓外國民眾通過欣賞中國作家藝術家的作品來深化對中國的認識、增進對中國的了解。要向世界宣傳推介我國優秀文化藝術,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理解”。[24]由此可見,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希望中國的文學工作者為中國讀者創作優秀的作品,還希望他們為全世界的讀者提供來自中國的精神文化食糧,從而讓全世界的文學讀者都能夠分享中國文化和文學的豐富精神食糧。
毋庸置疑,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之關系的講話精神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觀,為我們撰寫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學術史貢獻了中國的智慧和思想。他的一些著作經過翻譯也對國際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此外,一些對馬克思主義文學思想有著精深研究且擅長用英語著述的學者也頻頻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向國際學界展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世界文學研究方面的成就,從而打破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長期以來在國際學界“失語”的狀況。可以預見,未來將有更多學者在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資助下,在國際學界發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強勁聲音。這樣看來,建構一種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文學敘事就提到了中國學者的議事日程上。作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世界文學研究者,我們應該勇于承擔自己的歷史使命,不僅為本國的讀者貢獻精神食糧,同時也為國際學界奉獻可為他們參考借鑒的精神財富。就這個意義上說來,本文的寫作則可算作是這方面努力的一個初步嘗試。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與世界文學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14ZDB082)
注釋
[1]盡管學界一般認為歌德是最早提出“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概念的人,但現經西方學者考證,在他之前,德國哲學家赫爾德和詩人魏蘭也使用過這一術語,歌德是最早將其概念化的西方作家和理論家。這方面可參考這兩篇文章:Wolfgang Schamoni, "Weltliteratur — zuerst 1773 bei August Ludwig Schl?zer", arcadia: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43.2, 2008, pp. 288-298; Hans-Joachim Weitz, "Weltliteratur zuerst bei Wieland", arcadia: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22, 1987, pp. 206-208。
[2][英]希·薩·伯拉威爾:《馬克思和世界文學》,梅邵武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第194~195頁。
[3][4][英]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王爾勃、周莉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8、19頁。
[5]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7]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2000, 1 (January-February), p. 55.
[8] Fredric Jameson, "New Literary History after the End of the New", New Literary History, 2008, Vol. 39, No. 3 (summer ), p. 380.
[9]在這方面,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荷蘭學者杜威·佛克馬也有類似的看法。參閱他為《全球化百科全書》撰寫的“世界文學”詞條:Douwe Fokkema, "World Literature", 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290-1291。
[10]這部九卷本的《世界文學史》幾年前已由上海文藝出版社組織翻譯出版,但由于俄羅斯方面認為第九卷尚不成熟,屬于“征求意見稿”,中文版只出版了八卷。
[11][12]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編:《世界文學史》第一卷上冊,陳雪蓮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22、23頁。
[13]這方面可參閱筆者的下列主要相關論文:《馬克思主義與全球化理論建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1期;《“世界文學”與翻譯》,《文藝研究》,2009年第3期;《“世界文學”:從烏托邦想象到審美現實》,《探索與爭鳴》,2010年第7期;《世界文學的雙向旅行》,《文藝研究》,2011年第7期;《世界主義、世界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世界性》,《中國比較文學》,2014年第1期;《馬克思主義與世界文學研究》,《文學理論前沿》第十二輯(2014);《世界詩學的構想》,《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等等。
[14]這方面可參閱筆者的下列英文論文:"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10,? Vol.71, No.1, pp. 1-14;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ARIEL, 2011, Vol.42, No.1, pp. 171-190; "'Weltliteratur': 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Diversified Forms of World Literatures", Neohelicon, 2011, XXXVIII 2, pp. 295-306; "On World Literatur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5.5, 2013, December, Article 4;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16, Vol.62, No.4, pp. 579-589; "Chinese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16, Vol.43, No.3, pp. 380-392; "World Drama and Modern Chinese Drama in Its Broad Context", Neohelicon, 2019, Vol.46, No.1, pp. 7-20.
[15][16][17][18]《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48、855、860、876頁。
[19]Cf. Liu Kang, "Maoism: Revolutionary Globalism for the Third World Revisit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5, Vol.52, No.1, pp. 12-28.
[20]Ibid., p. 12.
[21]Cf. Christina van Houten, "Simone de Beauvoir Abroad: Historicizing Maoism an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5, Vol.52, No.1, pp. 112-129.
[22]Cf. Yiju Huang, "On Transference: Badiou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5, Vol.52, No.1, pp. 29-46.
[23]20世紀80年代中期,比較文學學者曾小逸主編了一本專題研究文集,題為《走向世界文學——中國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
[24]《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責 編/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