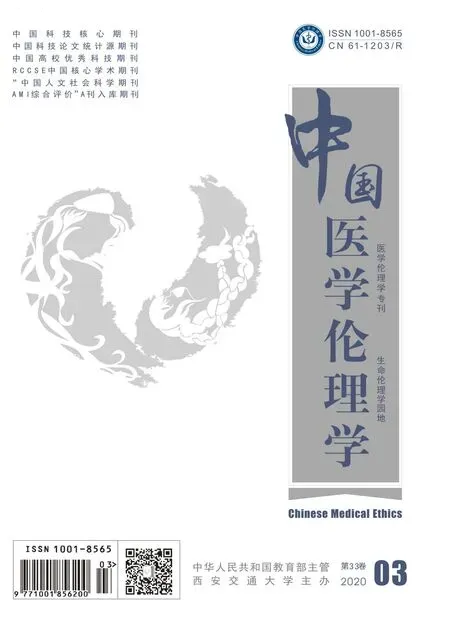論儒家德性倫理對醫學生職業道德教育的啟示
鄭佳琳,張艷清
(1 首都醫科大學燕京醫學院公共教學部,北京 101300,zjl1010519@126.com;2 首都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1300)
德性倫理學作為一種倫理理論,是指把個體的德性作為道德判斷的主要標準。它強調個體的道德行為以其內在的德性品質為基礎,源于個體自身道德意識的內在呼喚。與規范倫理學單純考察人的外在行為是否合乎規范相比,它更加強調從德性這種內在品質出發考察人的道德。儒家德性思想由來已久,它根植于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生活中,其理論形態的產生和形成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發展的需要,并伴隨著歷史的變遷不斷進行演變。在兩千余年的傳承中,儒家德性倫理建構了以“仁愛”為核心精神,以天理良心為價值尺度,以主體“幸福”“修齊治平”為目標要求,以情理交融、“存養擴充”為方法機制的道德教育思想,對整個中華民族產生了持久而強烈的感召力和凝聚力。隨著現代倫理學中心話語從規范倫理學到德性倫理學的轉向,與中華民族個體存在有著更為切近聯系的儒家德性倫理也被重新審視。醫生作為一種強調仁愛、忠誠、尊重等美德的特殊職業[1]。研究儒家德性倫理的合理內核、普及教化的有效經驗,對加強醫學生醫德教育效果有著重要的內在支撐作用。
1 儒家德性倫理的理論內涵
儒家德性倫理認為,人有德性是人與其他動物的本質區別。德性作為人內在的美好道德品質,根植于人的內心,其本質和內涵是情感。鄭玄注:“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周禮注疏—卷十四》)所謂“在心為德”就是指道德已化為人的一種內在品格,而這種美好的道德品質在行為中體現出來就是“施之為行”。在儒家看來,德性轉化為德行的過程,既是將普遍的道德準則、道德規范與主體的情感、認知、信念等相融合的過程,也是將這些道德認知、道德信念轉化為外在行為的過程,個體對道德的認知只有真正轉化為個體的道德意識、道德情感,才可能真正外化為個體的道德行為。德性能夠轉化為德行依靠的是主體的自覺,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這里的“仁”不僅僅是一種德性,是一種美好的道德品質,更是一種終極道德原則,是一切人的道德實踐的最終根據。“仁”的目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仁”要求道德主體以仁愛良知為本心,在道德踐履過程中真誠地與對方進行情感的溝通交流,將內在于心的“善”的德性外化為現實的德行。
在儒家看來,個體德性修養是儒家德性倫理的起點,但是個體道德修養的目的絕非僅僅為了個體本身,而是在“天理良心”主體性價值尺度的規范下,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終極目標。換句話說,個體德性修養的增進是為了建立更加和諧美好的社會。在儒家德性倫理思想的發展史上,不管是孔子的“推己及人”思想、孟子的“仁義禮智”四端學說、朱熹的“天理”學說還是陸王心學的“致良知”之說,雖然各有側重和特點,但通過加強自我道德修養從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圣外王”思路卻是一致的。他們均認為外在的禮制倫理規范僅是作為人性修養的外在標尺,這種約束作用是外在淺層次的。只有主動向善求仁,不斷進行向善復性的修養努力[2],才能夠真正促使個體自覺進行道德踐履。儒家這種極具情感性的德性倫理是單純考察人的外部行為的規范倫理所無法相比的,而這也正是儒家德性倫理的優勢和特征所在。
2 儒家德性倫理的道德教育理路
儒家以人們的德性作為其行為的出發點,主張道德教育應立足于人的情感,以天理良心為價值尺度,以“仁愛”“不忍”為學理基礎,以情理交融、“存養擴充”為方法機制,最終達到主體“幸福”、社會和諧的目標。
2.1 道德教育以天理良心為價值尺度
良心包括良知和良能,是道德理性與情感或意志的統一。良心的確立是道德自我誕生的標志[3]。儒家強調,道德教化要基于人的本性來施教。教化的基礎在于人先天具有的血緣情感和德性萌芽。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他認為人皆具有“仁”這一德性萌芽,“仁”就是一種普遍化的道德情感。孟子更是直接說“仁也者,人也”(《孟子·盡心下》),將“仁”設定為人的本質規定性,將“四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設定為人之良善本性,并且他認為“四心”作為德性的萌芽,要想生長為“仁、義、禮、智”這四種后天的德性,必須通過后天的努力和教化。到了二程、朱熹那里,“仁”則演化為“天理”本體,是天然存在的良知,人與萬物都有“仁”,天地人心皆以仁為根本。而在陸象山、王陽明看來,仁者具有“一體之仁”“生生本性”,人的仁愛之心與自然萬物的生命節奏是同一的,并且他們認為“本心即理”,“天理”就在人的心中。儒家德性倫理的這種以“人性善”為內涵的思維模式奠定了儒家德性倫理主體性價值尺度的哲學基礎和根本特征。仁愛良知既然根植于人的內心,那么道德教育則要以符合“天理良心”為價值尺度,以培育人的情感賦予能力為根本內容。
2.2 道德教育以“仁愛”“不忍”為學理基礎
儒家德性倫理以孔孟學說為基礎,主張“仁愛”“不忍。”儒家認為,仁愛發端于同情心,也就是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和“不忍人之心”。在孟子看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篇上》)“不忍之心”是每個人先天具有的,它潛藏于人的內心深處,是驅動人們關切生命、愛惜萬物的自然情感和道德動因。個體只有能夠設身處地地體驗他人的遭遇、痛苦和困境,才可能對別人表現出關愛、仁愛的情感。這種情感雖是自發的,但確是仁愛的發端,是首善之端。人在實施“仁愛”的時候,內心才變得更加敏感、生動。王陽明強調“仁者渾然與萬物一體”的思想[4],并強調通過“致良知”來實現這一至上境界。可見,“仁愛”“不忍”作為修身的根本和具有普遍價值的倫理原則,是道德實踐的動力和源泉所在。儒家對“仁愛”“不忍”的訴求充分體現了儒家的生命情懷和道德責任,也凸顯了其在整個儒家道德教育中的學理基礎地位。
2.3 道德教育以情理交融、“存養擴充”為方法機制
在儒家看來,德性的本質和內涵是情感。“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意思就是人們的道德認知、道德行為源自人的情感。情感是道德信念的核心力量。道德教育與其說是道德知識灌輸的過程,不如說是人文化成、價值傳遞的過程。要想使人將道德知識、道德信念真正內化于心,道德教育的方法進路就需要立足于情感的學理本位和思維向度,遵循情感之理。同時,儒家還強調“義理”“性理”,強調自我的道德超越,主張情理交融。此外,在儒家道德教育的方法機制中,還要求道德主體要注重擴展自身先驗的道德善性,從道德本心出發,保持道德情感的敏感性。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離婁下》)一方面,道德教育要保證對“赤子之心”或者說道德本心的存養,避免被外界的誘惑和欲望所遮蔽。通過培養自己的浩然之氣來與仁義道德相配,使之真正具有道德力量,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道德修行境界;另一方面,由于修養之道在于從“心”內求,所以“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離婁上》),也就是說在道德實踐上人們要經常“反求諸己”,注重對自我的追問與思考。儒家這種以情理交融,“存養擴充”為內容的道德教育方法,不僅體現了對道德主體的依賴和重視,呈現了強烈的人文關懷,也更加彰顯了德性的力量。
2.4 道德教育以主體“幸福”“修齊治平”為目標要求
蒙培元先生曾經總結:“西方哲學更重視人的知性和知識,而知識就是權力,從中可以得到幸福;中國哲學更重視人的情感,實現人生的價值,從而得到情感的滿足——這就是幸福。”[5]這里的“幸福”更多的是指人作為“情感存在者”對生命存在、發展的感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更傾向于一種情感的滿足,而不僅僅是感官和欲望的滿足。在儒家看來,這種幸福源于人的情感能力,所要解釋的是自我與他人的存在關系,是儒家德性精神的內在目標。它要求人們在進行道德實踐時,是出自情感的純粹目的。人作為情感存在者賦予自己的道德命令就是做道德的事情。人先天的具有“惻隱之心”,這是人能意識到自我與他人作為整體性關系的所在,也是個人發展情感能力、具備幸福人格的充分條件。若要做到對他人、萬物等生命的大愛,最終實現幸福,還要將這種“惻隱之心”進行擴充、完善、發展,并且將這些德性品質自覺貫徹落實到自己的道德行動中,從而達到知行合一。儒家雖然十分強調修身,并希望通過修身來達到道德主體“幸福”目標的實現,但是修身并不是最終目的。儒家德性倫理的終極目的是希望個體通過自我道德修養的“內圣”階段,成長為“大人”,最終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追求。換言之,個體進行人性提升和自我道德修養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實現經世致用、濟世安民、建功立業的價值追求。
3 儒家德性倫理對醫學生職業道德教育的啟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廣大衛生與健康工作者要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化醫德醫風建設和行業自律,為人民提供最好的衛生與健康服務。”[6]醫學的道德屬性和醫務人員職業的崇高性決定了在對醫學生的培養過程中要更加重視對他們道德品質、道德情操的養成。儒家德性倫理關注個體道德自我的培育、精神修養對提升個體生命質量的意義,強調通過內在的情感規約來引導人們踐行道德行為規范,顯示出情感與理性的統一,對人們形成穩定的價值體系支撐及其道德實踐信念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依托優秀傳統文化根基以培育醫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掘其中深厚的文化內涵,仍然是今天加強醫學生醫德建設之所需。
3.1 道德教育要根植于主體的人性基礎、講求向內自省,激發醫學生職業道德自律內驅力
馬克思說:“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7]道德教育要想真正有效,就必須喚起人的道德覺悟,強化人對社會道德規范的認同感,使之真正內化為人的內心自覺,獲得道德自律。而道德內化的關鍵又在于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提升人的道德主體性。儒家德性倫理十分注重個人的自我修養,認為道德教育要根植于主體的人性基礎,強調通過內省、反思和自我教育來達到自我完善。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認為仁、義、禮、智這些善端以萌芽的形式潛藏于人的內心,要想成就道德就需要通過反身內求人的良心本心,把自我內心的良心、善端發掘出來。朱熹則進一步提出“內無妄想”“外無妄動”的思想,認為道德力量根源于主體內在的品質,外在的道德規范必須為道德主體認同才能發揮作用。這要求進行醫學生道德教育時,要重視發揮醫學生道德主體性,注重對醫學生道德自我意識的培養。在實際教育工作中,要理解學生、尊重學生,改變以往單純灌輸的教育方式,積極與學生溝通互動。從醫學生的專業情況、實際身心狀況出發,幫助他們充分認識、理解、吸納與接受社會道德原則、規范,喚醒醫學生的主體意識,激發醫學生職業道德自律內驅力,使之成為個體自覺、自愿的行動,實現“他律”向“自律”的轉化。
3.2 道德教育強調擴充主體的道德善端、完善德性修為,涵養醫學生“救死扶傷、大愛無疆”的情懷
中國傳統醫德歷史源遠流長。在漫長的醫學發展中,形成了以“醫乃仁術,無德不立”為核心的醫德思想。“仁”乃關乎性命之道,是德的表現,亦是醫術的根本。唐代“藥王”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強調:“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認為醫者要秉持仁愛救人的醫德,對待患者要有慈悲心、同情心,即“見彼苦惱,若己有之”[8]。清代儒醫吳鞠通則強調醫德在醫術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醫醫病書》中指出:“天下萬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統于德……有德者,必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油然而出,必力學誠求其所謂才者。”認為學醫當以醫德為中心,醫德至上。傳統醫德的這些思想充分展示了德性的理想和追求。在對醫學生進行醫德教育時,首先要重視提高他們的醫德修養,將道德教育的重點放在醫學生道德善端的擴充和德性行為的完善上。通過“存心養性”“養浩然之氣”的功夫方法,來啟發和滋養醫學生的誠善之心,使愛人之心和同情心充盈于醫學生的內心。同時,醫學院校德育工作者還可以通過開展生命價值觀課堂教育和實踐活動,來引導醫學生認識救人性命、解除病痛是十分高尚而有意義的。作為一名醫學生不僅要探索醫學真理、努力掌握醫術本領,更要涵養自己“救死扶傷、大愛無疆”的情懷,在學習和診療過程中始終抱有仁愛之心,同情之心,端正淳良、一心赴救,全心全意幫助患者解除疾病的威脅與痛苦。
3.3 道德教育需注重解惑傳道與情感關懷相統一,增強醫學生醫患溝通意識和能力
長期以來,我們的道德教育強調對學生道德認知的灌輸,側重于教育的解惑傳道作用,而對學生的道德情感、內心感受卻相對忽視。這就容易造成學生“知、情、意、行”四環節的割裂,學生無法將情感與認知、意志和行為相統一。
情感作為人的一種內心體驗,對個人的行為態度和行為結果具有重要的調節和激勵功能。當前,醫患關系問題備受關注,而醫患關系是否和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醫務工作者的醫德修養和職業精神。醫學生作為未來的醫務工作者,增強他們醫患溝通意識和能力就成為加強醫德修養的重要學習內容。因此,在對醫學生進行道德教育時,一方面,我們要意識到提高道德情感培育的重要性,強調道德教育要浸透情感關懷,從醫學生的個性心理著眼,關注他們的生活、思想、情感、興趣,在診療實習中幫助學生強化對醫學、生命、健康乃至生活的內心體驗,為醫學生提高醫患溝通意識和能力提供情感基礎、心理支持;另一方面,除了傳授學生醫患溝通的理論知識和溝通技巧外,還可以通過開展諸如健康教育志愿者、臨床實踐等活動引導學生設身處地體會患者的處境,在醫患互動中獲得積極的情感體驗。只有喚起醫學生心中的善良感情,才能使他們真正理解和認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職責與誓言,也才能主動自覺去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踐行醫德規范。
3.4 道德教育要重視德育理論與實踐養成相統一,引導醫學生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在儒家看來,道德是一種立身處世、學以為人的學問和藝術。道德的內化認知和外化行為都必須經由個人的實踐歷練方能確證完成。道德的實踐本質決定了道德教育的過程本身就是實踐活動的過程,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務就是育德育人。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切忌純粹空洞的理論說教,要重視德育理論與實踐養成相統一。首先要引導醫學生積極投身到社會實踐中,在現實生活中身體力行,在實踐中培養其良好的道德品質和道德行為。其次,醫學專業“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特殊性,決定了醫學教育中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責任感的特殊訴求。醫學人才質量的內涵以及醫學職業素養的要求,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公民層面所倡導的“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9]。因此,對醫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不僅在醫學教育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也是醫學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現實而緊迫的任務。儒家德性倫理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構方面有很多可資借鑒的資源。如,“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黃帝內經》)指出了生命貴重,告誡我們要有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生命責任意識。“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禮記·中庸》啟發我們在對待醫患關系、師生關系等人情互動時要以誠信為基本原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語·子路》)教導我們要愛崗敬業;“見利思義”“先義后利”的義利觀則啟示我們如何擺脫“物欲”的奴役,不為外在利益左右,做一個具有真正道德自覺的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則有助于醫學生培養社會責任感,增強對國家命運的關心。在對醫學生進行醫德教育時,德育工作者要善于挖掘這些資源,傳承汲取傳統價值的精華,結合醫學生的專業設置、身心發展和實際情況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真正內化于心,外化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