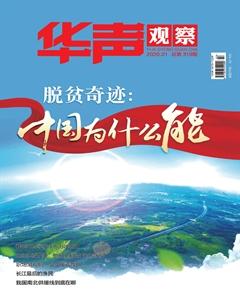當專家錯了

專家犯錯最無辜也是最常見的一種就是我們認為的普通的科學失敗。他們觀察一個現象,或是考察一個地方,想出理論和解決方案,然后進行檢驗。有時候他們做對了,有時候他們弄錯了。整個過程里通常會遇到很多死胡同和失敗的實驗。有時候錯誤沒有被發現,甚至被其他專家進一步加深。這就是為什么美國第一次試射衛星以發射臺的巨大爆炸而告終;這就是為什么外交政策的頂尖專家預測德國的和平統一在未來幾十年都不太可能實現,卻不得不在慶祝的煙火綻放在柏林上空時重新審視自已的觀點。
絕大多數人,包括專家,對這種失靈都是無能為力的,因為這就是科學和學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學就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結論。科學主題本身就是要根據一套細致的規則不斷進行測試,在這個過程中,現有的理論會被更優的理論替代。民眾不能期待專家永遠不犯錯,如果專家能達到這般精準,他們一開始就無需搞研究和作實驗了。如果政策專家能未卜先知或無所不知,那政府就不會陷入赤字,戰爭也只有在瘋子的煽動下才會爆發。專家無法承諾永遠不犯錯,也無法承諾不受人人皆有的缺陷所累,這些缺陷支配著一切人類研究。他們只能承諾,制定規則和方法來減少犯錯的概率,做到遠低于普通人犯錯的頻率。如果我們接受專業人士的工作所帶來的裨益,那也得接受不那么完美的事情,甚至可能是一定程度的風險。
然而,其他形式的專家犯錯就更令人憂心了。比如,當專家試圖把自己的專業從一個領域延伸到另一個領域,他們可能會犯錯。這是專家最常犯的一種錯誤:假設專家在某些事情上比大多數人都聰明,那么他們在一切問題上也比任何人都聰明。這種過度自信不僅使專家偏離自己的軌道,對自己專業相去甚遠的問題發表看法,而且還會“夸大”自己在本專業內的能力和水平。專家和職業人士,就像其他崗位上的人一樣,認為以前的成功和成果就能證明他們學識出眾,他們會把自己的界限往外推,而不是說出每個專家都討厭的那幾個字“我不知道”。
還有些時候界限沒那么清晰,問題就變成了“相對專業”。一個生物學家不是醫生,但總體而言,相較普通人,生物學家能更好地理解醫學問題。當然,這也不是說生命科學領域的任何人對這個領域的任何問題總是比其他人更有見地。一個領域的教育和文憑并不能保證一個人精通所有領域。例如,諾貝爾獎得主化學家萊納斯·鮑林在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相信維生素C是一種特效藥。他提倡服用大劑量的維生素C來擊退感冒和任何其他小病。鮑林的主張沒有任何實際根據,但就因為鮑林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他關于維生素C效用的結論在很多人看來就是將他的專業知識合理延伸到其他領域。后來也沒有一個維生素C實驗能證明鮑林的主張,但鮑林不聽。鮑林在整個70年代一直宣傳自己的主張。他認為維生素能治愈一切疾病,包括癌癥、心臟病、麻風病和心理疾病以及其他各種疾病。他后來還建議大家研究維生素C在對抗艾滋病方面的功效。不過后來證明,服用大劑量維生素其實是危險的,可能會增加患某些痛癥和中風的概率。鮑林最終不僅損害了自己的名聲,也損害了數百萬人潛在的健康狀況。
最后還有就是專家存心不良,徹底地欺騙和瀆職。這是最罕見但最危險的一種。在這種情況中,專家為了自己的目的(通常是野心家妄圖捍衛自已的次品)刻意造假。他們一方面希望民眾不會抓個現行,另一方面則希望同行不會注意到,或是把他們的欺騙歸類到誠實的錯誤。
專家欺詐不難定義,但難以識別。有時候專家不是專家。他們對自己的文憑撒謊,而且做得厚顏無恥。而當真正的專家說謊,他們危害的不僅僅是自己的專業,還有社會的福祉。他們對專業知識的威脅有兩種表現:一種就是欺騙所帶來的直接后果;另一種就是當他們被識破時,這種行為不端對社會信任的腐蝕。這就是為什么(除了對撒謊和欺詐的法律制裁以外)專業組織、學術基金會、智庫、學術期刊和大學保留對這種惡意瀆職行為的一些最嚴厲懲罰。
社會科學和人類學方面的研究尤其難復制,因為它不是基于實驗流程,而是專家對獨立作品和事件的解讀,但還是有一些引人矚目的完完全全的學術詐騙案例。2000年,埃默里大學歷史學家邁克爾·貝里爾因為一本名叫《武裝美國》的書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享有盛名的班克羅夫特獎。貝里爾在書中聲稱揭穿了一個關于擁槍思想的謬論。據他說,美國人擁槍的思想不是植根于早期殖民時代的經歷,而是受近一個世紀后的其他影響形成的。這項研究認為私人擁有武器在早期的美國并不常見,因此立即在讀者中引起兩極分化。這個研究本來不會被人察覺,但因為探討的主題是擁槍,控槍支持者和擁槍團體立刻就貝里爾的觀點選邊站,故而引來細致密切的審查。其他學者試圖找到貝里爾研究所依托的信息來源,但他們的結論是貝里爾要么是誤用了信息,要么是杜撰了信息。哥倫比亞大學撒回了班克羅夫特獎。埃默里大學也展開了調查,發現貝里爾的錯誤有一些可能是因為能力不足,但還有一些是學術誠信的問題,這一點無可回避。此后不久,貝里爾辭去了職位。最初合作的出版商也終止了這本書的出版,不過后來又被一家小型商業出版社重新發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