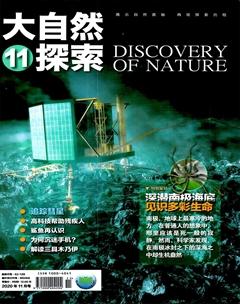追蹤彗星
吳青

彗星攔截器及其釋放的兩顆人造衛星探測彗星(藝術效果圖)。
人們曾經以為,彗星是天空中的幽靈或掃帚星,它們預示著災難或疾病。而今天,科學家已經知道,彗星這種神秘天體是太陽系早期歷史的記錄者,能告訴我們行星形成時期的情況。彗星還能揭示早期地球上存在的一些化學成分,因而有助于我們探索地球生命的起源。
因此,全球多家太空機構熱衷于用飛船(探測器)探測彗星。一項名為“彗星攔截器”的飛船任務正在籌劃中,定于2028年發射的這艘飛船將近觀彗星這種含冰天體。但彗星攔截器并非是造訪彗星的第一艘飛行器。
1986年,歐洲、蘇聯和日本都向經過地球的哈雷彗星發射了探測器。其中,飛得最靠近哈雷彗星的是歐洲空間局(簡稱“歐空局”)的“喬托號”探測器。它拍攝的有史以來第一幅彗核照片顯示,彗星表面的射流把氣體噴射到太空。
歐空局最近的一艘彗星飛行器是“羅塞塔號”,它與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緬科彗星(以下簡稱“67P彗星”)會合,并在2014~2016年追蹤該彗星達兩年之久。“羅塞塔號”首次揭示了彗星在飛近太陽,然后又跳進深空期間的變化情況。有一點因此變得很明確:彗星表面各層發生著許多演化過程。實際上,在“羅塞塔號”觀測67P彗星期間,這顆彗星的表面一直在變化:一些區域被侵蝕掉,另一些區域被墜回彗星表面的物質掩埋。雖然科學家一直知道彗星會遭侵蝕,但通過“羅塞塔號”的探測,他們才明白了彗星在靠近太陽期間被侵蝕的程度如此之大。
空前任務
在探測目標都沒有的情況下設計探測任務,這是第一次。
上述認識對科學家來說既是好事也是壞事。一方面,“羅塞塔號”的發現讓我們對彗星運行機制的認識比之前都多。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了彗星表面并非是對行星初始構建材料的純凈記錄。迄今為止,人類探測器造訪過的所有彗星都是短周期彗星。它們是形成于太陽系外圍比巨行星(木星、土星、海王星和天王星)所在地更遠的地方,然后落入距離太陽更近軌道的古老天體。在這樣的軌道中,彗星被太陽周期性地炙烤、修改,因此今天它們的樣子可能已經與當初完全不同。
幸好,還有另一類彗星——長周期彗星有助于我們理解行星怎樣形成。這類彗星的軌道極其巨大。1997年,海爾-波普彗星出現在地球天空中,連續18個月肉眼可見。基于它目前所處的軌道,科學家推測它在大約4000年前更接近地球。1996年,百武彗星經過地球附近。這顆彗星所處的軌道意味著它要花大約7萬年才能在軌道中轉完一圈。科學家推測,正因為長周期彗星的軌道如此巨大,它們距離太陽比短周期彗星遠得多,受太陽影響小,所以所有長周期彗星現在的表面都很可能很接近原始狀態。
偶爾還有彗星首次墜向太陽。為了破譯早期太陽系之謎,科學家需要調查的正是這種彗星。科學家認為,這種彗星不僅原始,而且當初形成于巨行星之間,因而它們在最初的行星構建材料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它們與新形成的行星之間的引力相互作用導致它們被甩到很遠很遠的距離外,這些地方的極寒讓它們的原始狀態得以保留至今。
如果我們能近距離探測一顆這樣的彗星,那么就有機會檢驗早期太陽系一個至今尚未被探測過的新區域。但科學家并不知道這樣的彗星何時會出現在地球天空中,而探測器的設計和建造一般要花10年時間,因此,就算這樣的彗星出現了,如果我們沒有做好準備,那么等我們造好探測器時它們早就消失無蹤了。如此一來,怎樣才能近觀這樣一顆彗星呢?
這就是彗星攔截器的研發目的。歐空局已經為該任務劃撥了專項資金。如果彗星攔截器在2028年按時發射,那么之后它將在太空中待一段時間,等待目標彗星被發現。該任務的設計和實施都很另類,因為在科學家心目中尚無任何目標彗星。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人在探測目標都沒有的情況下設計過任何探測任務。所以說彗星攔截器的設計開辟了一片新天地。
太空任務通常都有一個具體目標,這樣一來,工程師才能算出探測器的最佳軌道,由此決定需要多少燃料和燃料箱大小,也就能算出探測器能搭載的科學儀器質量。換句話說,探測目標決定探測器。
與目標天體會合的計劃,決定著展開太陽能電池板和打開儀器的最佳位置。而這些因素對彗星攔截器任務設計團隊來說皆未知。他們不知道該讓彗星攔截器從哪個方向、在什么地方——在距離太陽多遠處或在接近地球多遠處接近目標。因此,他們要設計的是一項極度靈活的任務。
系外客人
彗星攔截器的潛在探測目標中,也許有太陽系之外的彗星。
彗星攔截器要拍攝的彗星照片的質量必須與“羅塞塔號”拍攝的67P彗星照片的質量相當,前者還要調查這兩顆彗星之間的不同之處。科學家推測,這兩類彗星的化學組成會有很大差異。這是因為67P彗星之類的彗星形成于距離太陽近得多的地方,彗星表面的有機分子類別和數量無疑會因此大受影響。
長周期彗星不僅能揭示與短周期彗星不同的化學組成,而且能揭示行星的形成過程很暴烈還是很溫和。“羅塞塔號”探測67P彗星的五大結果之一是彗星的形狀。分析表明,67P彗星的啞鈴形態是兩顆獨立彗星融合形成的。這之所以是一大結果,是因為它表明多顆完全成型的彗星會以溫和的方式合并,其碰撞速度和走路一樣慢。與之對比,科學家認為行星的形成過程要狂亂得多。如果行星形成過程與長周期彗星的一樣溫和,那就意味著科學家有關行星形成過程的理論必須重寫。
對彗星攔截器探測目標的找尋將始于2022年。屆時,一部大型望遠鏡——大型巡天望遠鏡將正式運作。這部望遠鏡2020年在智利基本建成。鏡面直徑達8.4米的大型巡天望遠鏡,將能僅花幾個夜晚就掃描完整個天空。預計它能發現比目前已知數量多上千甚至上萬顆的太陽系彗星和小行星。甚至,在彗星攔截器2028年升空之前,大型巡天望遠鏡就能為它找到一個探測目標。
科學家不期望彗星攔截器的可選探測目標太多,這是因為彗星攔截器的設計、建造和運行時間都不長,所以只需為數不多的可選目標供考察就夠了。就算是在這不多的潛在目標里,依然可能存在一個罕見目標——來自另一個恒星系統的一顆彗星(星際彗星)。科學家已經識別了兩顆星際彗星——2017年的奧陌陌彗星和2018年的鮑里索夫彗星。這兩顆彗星的軌道都表明,它們不受太陽的引力束縛,它們只不過是在經過太陽系途中被太陽引力扭偏了方向。

67P彗星的啞鈴形態是兩顆彗星合并的結果。圖為“羅塞塔號”2015年拍攝的67P彗星。
雖然幾乎不可能確定星際彗星形成時環繞的是哪顆恒星,但通過近觀星際彗星,可能會揭示其他恒星周圍的天體形成過程是否與太陽系中的這些過程相似。科學家認為,如果真的能看見來自太陽系以外的天體,看到它與太陽系以內的天體不同或者相似,那將多么有趣。如果其中有一個天體我們能夠前去拜會,科學家就絕對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星際訪客
兩年內就辨識了兩顆星際彗星,但這是常態嗎?
2017年,科學家識別了一顆來自另一個恒星系統、經過太陽系的彗星。該彗星是通過位于美國夏威夷哈萊阿卡拉天文臺的泛斯塔爾斯望遠鏡發現的,科學家依據當地土語“偵察者”的發音把它稱為奧陌陌。開始時,這顆彗星看上去就像是小行星,這是因為它沒有彗尾,也沒有彗發——環繞彗核的氣體。
但后來,奧陌陌開始以無法由太陽或行星引力解釋的方式加速。因此,奧陌陌當時被一些喜歡聳人聽聞的西方媒體說成是外星飛船。而實際上,奧陌陌的“反常”行為恰恰就是彗星的行為——來自太陽的熱量導致彗星表面下的冰釋放氣體,而逃逸的氣體就像是一部火箭發動機。
2018年,另一顆經過太陽系的星際彗星——鮑里索夫彗星被發現。據估計,2019年12月它在最接近太陽時,每秒丟失2千克塵埃和60千克水。
很明顯,對科學家來說,運用彗星攔截器近觀太陽系外的彗星的想法很誘人。但另一方面,科學家對實現這個想法的難度之大也很清楚。有科學家說,這種可能性很低,因為我們對星際彗星經過太陽系的頻率多高根本無法確定。兩年內能辨識兩顆星際彗星也許純屬幸運,以后多年完全有可能碰不到任何星際彗星。不過,當大型巡天望遠鏡2022年升空后,科學家將了解到這方面的更多信息。
彗星取樣
把彗星材料送回地球,是科學家夢寐以求的大事之一。
不管彗星攔截器將前往哪顆目標彗星,科學家都已開始籌劃在那以后要回答的問題了。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彗星在地球生命起源中起了什么作用?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查明彗星表面的化學組成。科學家將重點調查含碳分子。它們也被稱為“有機分子”,原因是它們對地球上的生命來說很重要。正因為有機材料的成分很重要,所以需要查明彗星表面的有機化合物有哪些。要想查明這一點,唯一辦法就是把彗星樣本帶回地球,運用現有的實驗室設備進行全方位檢驗。
正是出于這個目的,一些科學家希望把“雄心”任務納入歐空局2050年長期計劃。如果被選中,“雄心號”探測器將登陸一顆彗星,提取彗星表面含冰物質,裝進液氮囊中送回地球。實際上,把彗星物質送回地球是科學家夢寐以求的大事之一。
但就目前來看,彗星攔截器風頭正勁。畢竟,該任務一旦實施,就意味著我們首次近觀真正第一次進入太陽系的彗星,它的表面將和幾十億年前的一樣。但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改寫現有的太空任務設計和執行方式。雖然這樣做的難度很大,但科學家相信,他們對這一任務前景的期望將激勵他們去克服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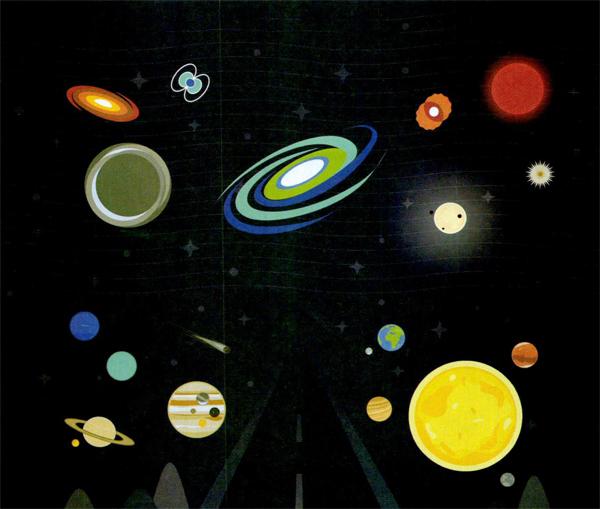
毆空局2050航天計劃海報。
系外彗星奧陌陌的太陽系之旅

一項新的彗星任務
1? 發射
2028年,彗星攔截器升空。這是歐空局阿里爾望遠鏡的次級負載。
2? 等待
彗星攔截器進入引力穩定點L1周圍的一條停泊軌道。
3? 巡航
一旦一顆合適的彗星被辨識,攔截器就提速,進入攔截軌道。
4? 釋放立方衛星
兩顆小型立方衛星(微型衛星)被釋放。其中一顆由歐空局制造,另一顆由其他機構制造。兩顆衛星所搭載的儀器互補。
5? 最近距離
攔截器以10~80千米/秒的速度和大約1000千米的距離經過彗星。立方衛星前往、靠近彗星,并且傳輸數據給攔截器。
6? 數據傳輸
與彗星相遇后,攔截器把數據傳回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