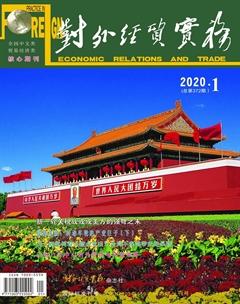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存在的問題及升級路徑
陳勇
摘 要:我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區域集中度高、產業層次較低、市場主體參與度高以及優惠政策豐厚,由此使得合作區的產業升級前景廣闊,多方合作力度較大。然而合作區也存在區位選擇不合理,風險不可控;產業結構單一,發展方式粗放;融資困難及人才匱乏等問題。因此,需要完善合作區內產業鏈布局,強化融資和人才支持,建立風險預防及評估體系,推進合作區本土化經營,如此才能確保合作區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境外經貿合作區;產業結構;“一帶一路”;融資
境外經貿合作區,也稱之為境外產業園區,指的是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企業在境外設立的由中國企業控股的獨立法人機構。境外經貿合作區具有完備的基礎設施、明確的產業主導、健全的公共服務職能等特點。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境外經貿合作區規模在不斷擴大,園區內集中了政策、資源、投資和技術,吸引了眾多的國內外企業的入駐,實現了生產、加工和商貿的一體化。截至到2019年2月,中國企業在境外46個國家建立了113個境外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367億美元,進駐這些園區的國內外企業達到了4665家,創造了近35萬個就業崗位,累計為東道國上繳稅費30億美元。整體看,我國企業在境外設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是中國企業和中國制造“走出去”的重要載體。然而在發展中也存在一定問題,尚有36%的境外經貿合作區未能盈利。因此,分析其發展現狀,明確其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而更好地促進境外經貿合作區的高質量發展。
一、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發展現狀
(一)區域空間聚集度高,集中在“一帶一路”沿線
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企業在境外設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已廣泛覆蓋亞非歐等各大洲。但區域空間分布比較密集,多分布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按照商務部2019年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有82個境外經貿合作區分布于“一帶一路”沿線的24個國家,占到了境外經貿合作區總數的72.7%。“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這82個合作區中國累計投資304億美元,入駐企業達到了4054家,創造就業崗位達到了25萬個,累計上繳東道國政府稅費21.5億美元。從這個數字上看,“一帶一路”沿線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累計投資、入駐企業以及上繳稅費均分布占到了我國境外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總額、入駐企業總數以及上繳稅費總數的82.8%、86.9%和71.6%。我國企業設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集中于“一帶一路”沿線,一方面是因為地域上的臨近,交通相對便利,有助于降低物流交通成本;另一方面是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倡導的結果。沿線各國與我國的經貿合作關系密切,部分國家正處于發展轉型期,不僅有豐富且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而且當地市場對中國商品和技術有巨大的需求。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不斷推進,分布于沿線各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將會為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經貿深度合作創造更多的便利。
(二)合作區產業層次不高,但升級前景廣闊
當前,我國企業在境外設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產業結構層次較低,主導產業類型單一,多數合作區定位為工業園區,以來料加工、資源利用、商貿物流為主。此外,部分合作區規劃面積較小,與周邊城市聯系并不密切。如中海集團2018年在吉布提建立的中國-吉布提自貿區的面積僅為3.2平方公里,主要從事海產加工和貿易。產業層次較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作區的發展,與周邊區域聯系不密切,表明合作區的封閉性較強。然而,從反面看,合作區的產業層次低也就意味著未來產業升級空間大。我國企業設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多是集中于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產業發展水平較低,對中國產品、技術、產業鏈等有較大需求,這對于我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走出去創造了有利條件。由此看,境外經貿合作區是我國當前去產能和實現產業轉移的良好平臺。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在促進投資、貿易便利化的同時,也激發了其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的動力,未來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
(三)市場主體參與度較高,民營企業投資增長較快
境外經貿合作區成為中外企業經貿合作的窗口和平臺,與一般的工業園區相比有自身的獨特優勢。境外經貿合作區是以企業為主導,投資者、參與者、運營者皆是企業,加上擁有中國與東道國政府雙方政策支持,與傳統進出口模式相比,合作區能夠更好地利用東道國的資源、生產資料和市場。一方面,能夠充分利用本地的勞動力和優勢資源,有效降低了生產成本;同時還可以根據當地市場需求的變化及時作出產業結構調整,生產更加符合當地市場需要的產品,能夠獲得較高的經濟利益。與跨國企業投資相比,境外經貿合作區能夠為更多的國內中小企業提供“走出去”的平臺,能夠為中小企業提供“抱團取暖”的機會。正是因為境外經貿合作區具有這些優勢,中國國內的大型企業、中小企業尤其民營中小企業在園區內形成了上下游產業鏈,解決了中國企業“走出去”初期產業鏈難以配套的問題。同時,由于入駐的各類企業能夠形成上下游合作關系,容易在園區內形成一個中國產業轉移的產業群,對當地的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帶動作用。當前境外經貿合作區的投資主體大部分是民營企業,國內的民營企業也能夠借助中國與東道國的政策優勢,在東道國迅速開拓市場。按照商務部統計,2018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45%的貿易額是由民營企業完成的,貿易總額達到了6288億美元,比2017年增加了12.3%。全國工商聯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當中有274家企業入駐了境外經貿合作區,為境外經貿合作區的產業轉型升級注入了活力。
(四)合作區內優惠政策豐厚,多方合作意愿強烈
政策優惠是吸引企業入駐境外經貿合作區的重要推動力。境外經貿合作區能夠同時享有中國政府和東道國政府提供的雙重政策優惠,政策優惠不僅覆蓋面廣,而且優惠力度也比較大。具體而言:第一,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在中央政策方面,為境外合作區提供了貼息貸款、直接補貼、稅收優惠等方面的支持。從2017年起,商務部、財政部對通過評審入選的示范境外經貿合作區每年提供2億元的資金扶持,入駐企業還可以享受5年退稅及100%的貼息貸款支持。對符合《境外經貿合作區考核辦法》的園區,商務部還提供包括前期建設費用、物流運輸費用、科研支持經費、人員培訓費用等方面的支持。另外,在稅收、人員簽證、員工保險等方面也能夠享有一定的優惠政策支持。在地方政策方面,各地政府為了鼓勵本地更多的企業“走出去”,為企業投資設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以及入駐園區的本地企業提供廠房建設、員工培訓、員工保險、貼息貸款等方面的支持。第二,東道國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因我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多是集中于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而境外經貿合作區能夠帶動這些國家的區域經濟增長。因此,東道國政府在土地租賃、企業融資貸款、稅收等方面愿意給合作區及入駐企業提供政策支持。如中國華立集團和泰國安美德集團聯合投資的泰中羅勇工業園區,泰國政府給予了該園區50年的低價土地租賃優惠。湖北聯合發展投資集團在比利時魯汶設立的中國-比利時科技園,園區內的生物制藥、信息通訊、智能制造等企業免收企業所得稅和享有進出口零關稅的優惠。正是因為境外經貿合作區享有的優惠政策力度大,大大激勵了各方合作的需求,也帶動了園區的高質量發展。
二、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合作區區位布局過于集中,風險不可控性較強
境外經貿合作區是我國企業投資設立的,在運營建設中也是以中資企業為主體,本質上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種新形式。然而這些園區80%以上是分布于亞非等發展中國家,東道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風險會對園區發展產生直接影響,加上各國國情差異較大,風險不可控性在增加。具體而言:第一,政治風險在加大。園區所在的東道國很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落后,政府治理能力較弱,法制化程度較低,宗教、部族和民族沖突較多,戰爭、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猖獗,加大了園區經營以及入駐企業投資的風險。第二,經濟風險仍存。部分國家雖然政局較穩,但經濟落后,基礎設施較差,增大了企業的經營成本。如我國在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設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主要是以棉紡加工、服裝生產為主,這些產業對能源要求較高,但因這兩國基礎設施陳舊,斷水斷電情況時常發生,而當地的交通狀況也無法滿足企業的物流需求,加大了企業經營的經濟風險。第三,社會風險難以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問題本身就比較復雜,加上文化、習俗、語言等方面的差異,園區內的中外員工容易發生沖突,勞工問題較為突出。我國盡管規定了入駐境外經貿合作區的中資企業必須50%以上雇傭當地員工,還為他們購買醫療、健康等保險,但由于管理方法和文化差異,罷工鬧事現象時有發生。
(二)合作區主導產業定位欠精準,發展方式較為粗放
具體而言:第一,部分合作區的產業層次低且產業結構單一,降低了其盈利水平。在我國設立的113個境外經貿合作區中,70%以上的合作區是工業園區,主打工業制造和資源利用。入駐企業也多是為歐美企業代工的,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盡管勞動密集型企業可以解決當地人就業問題,但也降低了企業的盈利能力。第二,合作區產業雷同性程度大,容易誘發惡性競爭。在某些資源稟賦相似的地區,我國多個企業在同一國家投資設立境外經貿合作區,誘發合作區之間的惡性競爭。由于埃塞俄比亞的棉花資源較為豐富,我國多個企業在該國投資設立合作區,產業集中于服裝、紡織等領域,園區之間大打價格戰,惡性競爭導致了入駐企業利潤空間不斷縮小。第三,合作區主導產業不突出,發展規劃不明確。合作區作為園區,本應該為入駐企業提供一個保障平臺,而部分合作區沒有明確的主導產業,園區發展欠缺規劃,無法吸引相關企業形成一個產業集群,降低了園區競爭優勢。第四,部分園區主導產業太過超前,采購和銷售較為困難。如中埃蘇伊士經貿合作區主打精細化工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然而,這些產業發展在埃及無法采購原料,市場需求也不大,導致入駐企業采購和銷售成本過高。
(三)合作區融資難度大,缺乏專業的管理及技術人才
具體而言:第一,合作區融資難度較大。盡管中國政府、東道國政府能夠為合作區提供雙重政策優惠,包括貸款優惠。一方面是合作區的前期建設基本上是由投資企業來完成,而大部分投資企業是民營企業。由于建設的園區是在境外,國內金融機構在發放貸款的時候顧慮重重,而民營企業在資產抵押等方面也容易受到限制。而在東道國的金融機構融資,盡管有部分貼息,但融資成本依然很高,加上部分國家通貨膨脹風險大,很多企業只能是靠變賣國內資產來支持合作區的發展。正是因為市場融資困難,合作區的可持續發展較差,同時也為入駐的中小企業提供了風險警示,導致很多中小企業不敢或不愿入駐。第二,合作區缺乏專業的管理與技術人才。一方面,合作區所在的多數國家本身科技、教育水平落后,當地無法為合作區提供人才支撐;另一方面,合作區遠在亞非發展中國家,薪資待遇及工作環境對國內專業的管理與技術人才缺乏吸引力。導致很多合作區只能是在發展中逐步培養自己的人才,制約了合作區的高質量發展。
三、中國境外合作區發展的升級路徑
(一)完善合作區產業鏈布局,提升合作區盈利能力
具體而言:第一,完善合作區產業鏈布局體系。一是要逐步推進其產業層次升級。按照當地的市場需求和合作區產業鏈情況,加快推進合作區內產業從勞動、資源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提升合作區內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打造中國化品牌,提升園區內中國企業競爭力。二是要強化合作區內的產業互補性。合作區內的企業應該打造一個產業集群,明確主導產業,在主導產業之外設立上下游產業并構建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提升入駐企業之間的關聯度,構建一個產業互補性的集群。三要引導合作區內產業鏈的向上延伸,優化產業鏈布局,強化上下游產業之間的整合,在產業集群之外構建縱橫相錯的鏈式發展布局。四是注重培育先導產業,在培育過程中要對企業投資做好引導,糾正先導產業過于超前的問題,確保與當地市場、資源的緊密結合。第二,要切實提升合作區以及入駐企業的盈利能力。境外經貿合作區是中國企業獨資或是與東道國企業共同投資建設的,入駐的企業多是中資企業,企業是合作區運行的主體。因此,作為投資主體和入駐主體,必須要不斷提升自身的盈利能力。對于合作區投資企業而言,要拓寬盈利渠道,提升合作區工業生產收入之外,還應該增加服務收益。對于入駐企業而言,要不斷開拓當地市場,降低生產成本,加大出口力度,提升盈利水平。
(二)完善合作區的融資和人才培養體系,提升合作區服務支持水平
資金、技術和人才是生產要素中最為活躍的因素。境外經貿合作區在境外,要想持續發展,上述生產要素不可或缺。具體而言:第一,不斷完善合作區資金發展保障體系,加強金融機構、合作區和政府三方之間的互動。一是要加大政府資金支持力度,中央和省級政府要設立境外經貿合作區專項扶持資金,或是聯合東道國政府共同設立支持資金,并為合作區融資提供利率補貼。二是要鼓勵國內金融機構創新其服務、產品的力度,通過探索全球授信、外匯債券擔保等形式解決合作區投資企業和入駐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三是要引導和鼓勵多方對合作區進行直接投資。當前絕大部分境外經貿合作區是中國企業獨資建設的,未來要鼓勵中國企業與東道國企業聯合投資境外經貿合作區,不僅能夠降低中資企業風險,還能提升合作區的國際化水平。第二,要不斷完善合作區的人才培養和引進體系,解決其人才匱乏的困境。一是要建立人才交流機制,鼓勵國內優秀的管理、技術人才到合作區工作。二是要加強合作區與東道國的高校、科研機構開展合作,為合作區提供訂單式人才培訓體系,強化合作區的造血能力。三是要加大人才引進力度,在研發、薪資、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吸引全球各國管理、技術人才的聚集。
(三)健全風險評估體系,做好合作區風險預防與控制
具體而言:第一,要加強對風險的研究和預判,將投資和經營風險降至最低。這就要求在合作區建設之前要做好選址布局、明確其功能定位和主導產業,確立其運作模式和招商規則,進而做好風險預判和控制,提升合作區發展的持續性。第二,要完善好與東道國政府的協調機制。境外經貿合作區建在國外,勞工、環境、土地、稅收、匯兌等方面均要與東道國政府打交道。因此,中國政府要加強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溝通,合作區的投資企業要與東道國相關部門建立協調機制,降低其經營、貿易及投資方面的風險。第三,要不斷完善企業海外保險制度。這方面可以借鑒日本的做法,在商務部設立海外投資保險部門,用本國信用作為企業投保及理賠的后盾,從而降低合作區投資企業和入駐企業的經營風險。第四,完善風險應對機制。合作區要利用好國際國內智庫以及專業咨詢機構的信息優勢,圍繞不同的風險預測度來建立風險預警體系和應對方案,打造由合作區、銀行、保險機構、法律服務機構多方參與的合作區投資風險監控平臺,將境外合作區打造成為入駐企業的“安全驛站”。
(四)推進合作區入駐企業加強本土化經營,強化企業與東道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聯系
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內的入駐企業要根據合作區所在國家、地區的產業結構及經濟發展實際水平,不斷調整經營策略與理念,大力發展本土化戰略,確保在經營、產業、勞工、資本、文化等方面與東道國融合。具體而言:第一,合作區以及入駐企業要遵守東道國的法律法規,建立與國際規則相一致的經營管理體系,提升入駐企業的資源整合能力;入駐企業在經營中要主動化解文化沖突風險,提升企業與當地文化的鏈接能力。第二,合作區以及入駐企業要朝低碳化、綠色化轉型。顯然,我國在境外建立經貿合作區的目的并不是要將中國落后的、高污染的產能直接轉移到合作區內,而是要與東道國一起打造一個多元化、本土化的國際產業鏈。因此,合作區及入駐企業要不斷完善環保管理及投資體系,借助于綠色投資工具,嚴格審核入駐企業投資方向和目標,引導入駐企業開展綠色投資,鼓勵企業利用各類清潔能源,提升中國境外合作區及入駐企業的國際形象,打造一條真正的“綠色絲路經濟帶”。第三,加強對當地雇員的培訓,建立穩固的勞資關系。合作區及入駐企業的本土化發展,必須要“就地取材”。
參考文獻:
[1] 丁悅. 我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對策思考[J]. 青海社會科學,2019(4):99-105.
[2] 許培源,王倩. “一帶一路”視角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理論創新與實證檢驗[J]. 經濟學家,2019(7):60-70.
[3] 盧進勇,裴秋蕊. 境外經貿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問題研究[J]. 國際經濟合作,2019(4):43-55.
[4] 武漢大學“一帶一路”研究課題組. “一帶一路”境外經貿合作區可持續發展研究[J]. 社會科學戰線,2019(6):82-88.
[5] 呂秉梅. 當前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發展研究[J]. 價格月刊,2019(8):59-63.
[6] 薄文廣,陳璐琳,胡驛. “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境外經貿合作區可持續發展研究[J]. 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4):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