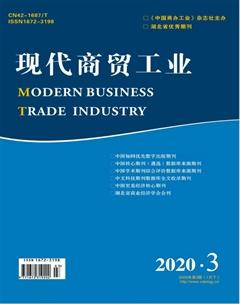族群視角下青藏高原藏回交融現象探析
高思嘉
摘 要:位于青海省化隆縣卡力崗地區的卡力崗人,曾經是信仰喇嘛教的藏族。如今改信伊斯蘭教,自稱“藏回”。卡力崗藏回在生活習俗與宗教符號上趨向回族化,雖然宗教意識的變遷產生了族群邊界,但是在各方面依舊保留了藏族特點。藏回身份建立在藏族與回族的族群邊界之上,藏回與藏族人和諧相處呈現了“我群”和“他群”雜糅交融的卡力崗地方多元文化面貌。在語言作為確定族群成員資格的標準下,因卡力崗藏回和藏族人同樣說著藏語,同為地方文化的攜帶者和傳播者,藏族和藏回的族群便被模糊了。與此同時,在宗教生活中使用阿拉伯語和漢語的互補身份又為卡力崗藏回們提供了自我發展的空間。以既有文化共性存在又允許持續性文化差異遷延的族群關系持續方式,維持著族群間的穩定,并構建出藏文化、伊斯蘭文化、漢文化相互交流的卡力崗族群文化。
關鍵詞:卡力崗;藏回;族群交融;族群邊界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3.042
1 青海化隆卡利崗藏回的形成淵源
我國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縣境內的藏族,多為化隆地區自古就存在的番人土著。化隆境內“吾具”“卜具”等沿用至今的地名,就是藏語名稱。卡力崗藏回的祖先屬于土著藏族,信仰藏傳佛教,后改奉伊斯蘭教,成為青藏高原上的一支使用藏語安多方言的穆斯林。學界普遍將這一現象稱為“昔藏今回”。促使原先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族改信伊斯蘭教的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個原因是當時的政治環境。清乾隆二十年以后,清政府對青海地區藏傳佛教持壓制政策。因為清政府從寺廟經濟、僧人人數等方面對格魯派進行嚴格限制,所以這種來自上層統治者的打擊直接影響了卡力崗地區藏傳佛教信徒的數量。第二個原因是適宜的傳教方式。有這樣一個卡力崗藏回普遍認可的傳說,即十八世紀末乾隆年間一位有學問和威望的蘇非派(Sufism Orders)領袖馬來遲曾在青海當地勸說西番改信伊斯蘭教。馬來遲懂得在傳教過程中做出必要讓步。例如馬來遲在黃吾吉這個地方傳教時,要求當地藏民穿褲子、不吃豬肉、不養豬。但是當地藏民原本的生活習俗為身穿藏袍、不穿褲子、不禁食豬肉。他們向馬來遲坦言不習慣穿褲子,豬也想養著。馬來遲靈活應對:“只要不吃豬肉,豬暫時養著也可以,褲子平時不穿可以,但主麻日一定要穿褲子。”當地藏民聽后大喜,紛紛樂于改信伊斯蘭教。
如果將馬來遲傳播伊斯蘭教的傳說看作卡力崗地區藏回祖先改奉伊斯蘭教的淵源,那么當時清政府壓制藏傳佛教的宗教政策,便為馬來遲在卡力崗地區傳播伊斯蘭教提供了便利條件。不僅如此,馬來遲通過適宜的傳教方式,使得傳播的教義同當地群眾生活習慣相兼容。在這兩個內外因素的作用下,直接促成卡力崗地區部分藏族群眾改信奉伊斯蘭教,成為影響族群身份變遷的根本原因。
2 宗教意識的變遷產生族群邊界
隨著宗教信仰的改變,改奉伊斯蘭教的卡力崗藏回的生活要素形態逐漸變遷。如今,和藏族人相比,卡力崗藏回在形式層面的文化表現上產生了顯著的族群邊界。他們的信仰、服飾、飲食、婚俗等方面日益疏離藏族。在宗教信仰方面,伊斯蘭教的宗教符號使卡力崗藏回族群認同有別于當地信仰喇嘛教的藏族群體,例如清真寺、宗教飲食禁忌等。在服飾方面,改革開放前藏回男女老少一律穿傳統的藏服,現在的男女老少身著漢服,男子頭戴頂帽,女子頭戴蓋頭,與其他地區的回族沒什么區別。在婚俗方面,藏回的婚俗融入了伊斯蘭教的特色。藏回成婚要請阿訇寫“尼卡”(證婚詞)。
基于上述事實,宗教信仰的改變使得卡力崗藏回的生活要素形態上呈現了跨民族的動態表現。在這種分化過程中,雖然直觀的看到相應的生活表現形式層面的族群邊界,但若以廣闊又多元化的族群關系的視角來觀察藏語穆斯林,更應注重藏族與藏回的文化淵源方面的種種因素。卡力崗地區藏回產生的分化是在截然不同的適應性條件下以藏族和藏語穆斯林共享相同文化為基礎。人類學家巴斯認為族群邊界并不取決于形式層面的文化差異表現,而是取決于根本層次的文化淵源。這個觀點同樣適用于卡力崗藏回與藏族人的邊界表現。我們可以將卡力崗信仰伊斯蘭教的藏回身上攜帶的回族元素看作是互補身份的固定化,這種做法將作為一個整體概念的穆斯林族群分化成了各自認可其獨特起源的參照群體,使卡力崗藏回被正視為中國穆斯林群體中獨特的一個分支。因此,這些參照群體得以與非信仰伊斯蘭教的族群相互維持族群關系的理由就必須在其具體條件下族群文化的重構進程中尋找,這些進程可以解釋族群對“他者”的自然相斥力是怎樣在卡力崗藏回與藏族人之間漸漸模糊的。
族群邊界的文化分化反映了人們對不斷變化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的持續適應過程。既然藏語穆斯林和藏族人的族群分化建立在享有共同文化基礎的前提下,那么就為族群的并存適應提供了可能性。筆者認為,族群不僅僅或無須一定建立在排外邊界的空間之上。關于族群關系得以維持下去的方式有必要加以分析。如果毗鄰的不同族群沒有產生非常嚴重的相互適應問題,那么在兩者的社群文化里就包含了一種確定族群成員資格的標準,這種判定標準是下文所要分析的。
3 超民族的卡力崗族群文化重構
民族文化差異常常被輕易攜帶上刻板印象和偏見,大腦系統決定人類在思考問題時,總是本能的習慣于避免完整的、系統的思考。例如提到藏族,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藏袍、長靴、銅壺、龍碗、青稞、糍粑等藏族文化符號;提到回族我們就想到蓋頭、小白帽、清真寺等宗教和民族符號。這些刻板印象,僅僅與具有不同背景和生活方式的群體間有直接的相關性,并不適用于青海化隆的卡力崗藏回,因為他們既不完全屬于藏族也不完全等同于中國其他地區的回族。若以二分法式的宗教性、民族性差異來界定藏族和藏回兩者族群邊界,就很難基于完整的多元化事實呈現“我群”和“他群”雜糅交融的卡力崗地方多元文化面貌。卡力崗地區藏回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卡力崗地區藏回與藏族的文化現象并不是完全二元對立的,而是以交錯雜糅的模式予以展現。雖然卡力崗藏回在許多方面已經趨于回族化,但仍然保留著一些藏族特點。在住房上,藏回居住在藏族傳統建筑風格的莊窠,廚房里鍋臺帶炕、使用推合窗。在衣著上,無論男女到冬天皆喜穿藏式的斜襟皮襖、靴子。在飲食文化上,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食用青稞、小麥、糌粑等藏族傳統主食。如果有遠道而來的客人,他們會用奶茶招待。又比如在生活習俗中,與藏族婦女一樣,卡力崗婦女也采用木桶背水方法。家庭用具仍然使用銅壺、龍碗、木勺等傳統的藏族風格用具。食物的盛法一如藏族傳統,在吃肉時刀尖向里,縫補衣物時針尖向內,這都如同藏族的講究一樣。
不僅如此,卡力崗藏語穆斯林使用的語言在卡利崗藏回族群內部關系,以及對外與藏族、漢族等其他族群關系的維持上,充當了確定族群成員資格標準的功能。這里要說的是兩種影響卡力崗人族群文化構建的語言,一種是卡力崗先祖們世代使用的藏語安多方言;另一種是因歷史變遷、多民族雜居和宗教信仰改變而掌握的阿拉伯語和漢語等語言。長期以來,卡力崗藏回與藏族人和睦相處,藏文化與伊斯蘭文化、漢文化并存適應。藏回婦女一般只會講藏語;卡力崗藏回阿訇說“臥爾茲”時用藏語,有時也夾雜著阿拉伯語和漢語。誦經則用阿拉伯語。年輕的伊瑪目大多到臨夏、蘭州學習過宗教知識,喜歡并擅長用漢語解釋伊斯蘭教經典。年長的伊瑪目喜歡說藏語,但是為了照顧一些年輕的聽眾,他們有時會翻譯成漢語。我們可以看出,在整個卡力崗藏回群體中的藏族族群同質性被保留了下來的同時,卡力崗地區藏回群體在族群邊界互動過程中衍生出了超民族、超族群邊界的伊斯蘭文化、藏文化、漢文化并存的多元化文化形態和族群認同。
這就使卡力崗藏回與其他族群的邊界關系維持的方式得以理解。卡力崗藏語穆斯林在生活形態要素、文化要素上包容并蓄了多民族文化,這表明族群邊界關系的維持既需要同一,又需要差異,即持續性文化差異。族群維持不僅僅意味著認同的標準,也意味著允許持續性文化差異遷延的構建。在有著不同族群文化的人員互動的地方,人們在互動中往往期望差異能夠減少,因為互動的基礎是文化的相似性或文化共性。而語言是族群文化的重要載體,語言的交流是族群關系維持和文化交流的基礎。因為卡力崗地區的藏語穆斯林因和藏族人同樣說著藏語,同為當地藏族地方文化的攜帶者和傳播者,所以在藏語穆斯林和藏族人互動過程中,文化共性使族群分化的邊界被模糊了。與此同時,在宗教生活中使用阿拉伯語和漢語的互補身份又為卡力崗藏回們提供了一個自我發展的空間,使得卡力崗藏回與傳統意義上的藏族產生持續性文化差異,這樣卡力崗族群作為一個獨特的有意義的單位便可以持續下去。并且無須一定建立在排外邊界的空間之上,構建出帶有自身明顯特性的藏文化、伊斯蘭文化、漢文化交流的卡力崗族群文化。這種在多族群地區下起著維持族群關系作用的互動體系,有效避免了族群之間的嚴重排外和文化對抗。了解卡力崗地區藏回交融現象,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我國多民族雜居,民族文化上兼收并蓄、共同進步的多元文化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幫助我們更好的認識世界多元存在、社會規則、民族關聯,乃至形成全面的國家觀和世界觀。
參考文獻
[1]冶清芳.青海化隆卡力崗地區藏回淵源考[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04):70.
[2]冶清芳.青海化隆卡力崗地區藏回淵源考[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04):71.
[3]張中復.歷史記憶、宗教意識與“民族”身份認同——青海卡力崗「藏語穆斯林」的族群溯源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3,(02):37-38.
[4]達娃央宗.青海卡力崗人的族群身份變遷[J].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1):62.
[5]海寶明.藏回 蒙回 托茂人的宗教信仰軌跡[J].中國穆斯林,2009,(04):32.
[6]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與邊界——文化差異下的社會組織[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72.
[7]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與邊界[J].高崇譯.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9,(04):18.
[8]冶清芳.青海化隆卡力崗地區藏回淵源考[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0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