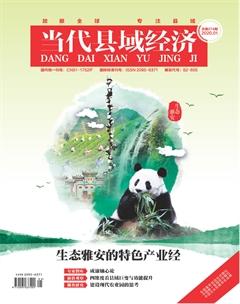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梁平經驗
林冬生
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事關中國未來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發展大局,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但與土地確權頒證、土地流轉、新型經營主體培育等改革相比,難度更大、任務更重。一方面,缺乏改革的基本動力,對地方政府而言增加改革成本,短期內不一定帶來經濟利益,成本高于收益;另一方面,利益矛盾沖突較大,長期以來農村集體資產的模糊化管理,很多利益矛盾本暫時隱藏,改革將使各種矛盾逐漸凸顯,從而增加改革的難度。重慶梁平作為全國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的試驗區,自2015年以來,不僅有系列創新的主動謀劃,實現了改革的總體性突破和全覆蓋,賦予了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拓展了農民增收渠道,更為重要的是形成了顯著的集體經濟改革裂變效應,為全國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提供了具有普適性價值的經驗借鑒。
以農民主動參與化解改革難點
成員界定和股份量化是難點,涉及千家萬戶不同的利益訴求,如果由政府主導就會放大改革矛盾、降低改革成本。以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界定為例,梁平堅持依法依規、民主決策、因地制宜、公平公正、維護穩定五大原則,分成員身份取得、保留、喪失三種情況分別提出指導意見,由各村召開村民大會參照進行民主討論,形成具體的界定方案。比如:部分社區或村組形成了以某一時間為節點,確立了“四認定、八不認定”的界定方案;部分社區或村組則以某一時間為節點,確立了“9類人員界定為成員、11類人員不能界定為成員”的界定方案;還有部分社區或村組則商討出“9符合、9不符合”的界定方案。通過因地制宜的將政府引導與農民參與有機結合起來,既有效弱化了改革矛盾,又大幅降低了改革成本,這雖然不是梁平的獨創,但卻是基礎性的制度設計。
以低成本高效率實現穩妥推進
一是在成員界定上采取“寬進”原則,堅持“法定加討論、不輕易否定”的原則“寬”定成員身份,確保應享盡享。二是股份量化上采取“簡設股權”機制,推行“不設集體股、一人一股、按人平均”的簡易方法設置股權,采取“三合一分”辦法處理建制調整前后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引導每個建制村設立一個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三是在股權管理上實行“固化”管理模式,“增人不增股、減人不減股”。梁平采用“寬簡固”的方式形成了固化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及其集體資產股份、確予成員股份、賦予股份權能,實現農民股民化、集體經濟實體化、成員權益具體化的“兩固兩予促三化”的改革模式,簡便易行、效果良好,為農村集體經濟薄弱地區提供了一條“穩快簡省”的集體資產股權權能改革之路。
以系統性制度設計 提高改革支撐能力
一是梁平的改革路線圖是完整的。既包括清產核資、成員界定、量化確權等基礎性改革,又包括權能賦予、集體經濟發展等拓展性改革。二是梁平的權能賦予是充分的。不僅賦予了占有、收益權,也賦予了退出、繼承、擔保和抵押權能,更為每一項權能的實現提供了相應的制度設計,甚至進行了集體資產股份贈與、轉讓的制度設計,從而構建了整體性的權能實現機制。三是梁平的制度設計是系統的。不僅有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主體制度的設計,也有村級融資擔保基金、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退出周轉金、農業項目財政補助資金股權化改革等配套性制度設計;不僅有改革方案、指導意見,也有重要改革事項的流程和模板,對于增強改革的操作性、簡便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僅有確保推進的組織領導機制、考核督促機制,也有增進動力的引智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可以說,梁平系統性的制度設計有效防止了改革制度的碎片化、零碎化甚至是沖突性,有效提高了改革的支撐能力并促進改革循序深入,這是尤為具有推廣價值的。
以差異化改革模式 增強改革探索價值
梁平在推進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工作中堅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不強行“整齊劃一”,有針對性地采用差異化的改革模式。在集體資產價值認定上,既可采取按資產賬面價值進行定價,也可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代表參照同類資產流轉或交易價格評估作價,還可委托第三方評估作價,但認定后的資產價格經公示后,均要提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大會或成員代表大會討論確認。在集體資產股份量化上,對適合量化確權的集體經營性凈資產,穩妥開展量化確權,資產經營收益按股分配紅利;對集體行政類和公共服務類的非經營性資產,明確歸屬,登記確權,落實管理維護責任,保障功能,發揮作用;對可轉化經營利用的閑置非經營性資產,有效盤活,量化確權,作為按股分配紅利依據;對閑置的集體建設用地等經營性資產,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進行處置。在處理新舊集體經濟組織關系上,根據撤并時各自然村的總資產大小、人均資產是否相等等情況,采取“三合一分”四種改革模式,第一種模式是資產整合、不計以往、股金均算,不考慮撤并時的資產情況,按現有資產和成員設置股權和計算股金,組建一個新的集體經濟組織統一運營;第二種模式是按原建制的資產和成員分開計算現有成員股份及入股股金,用股份、股金上的差別來體現原建制之間資產量的不等,成立一個集體經濟組織統一運營;第三種模式是按原建制分別成立集體經濟組織,再以各自資產入股組建一個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該組織收益通過兩次分紅到成員;第四種模式是按原建制分別組建集體經濟組織,分別運營、獨立核算。通過差異化的改革模式設計,既照顧了村與村之間在資產量、資產結構以及人員流動性等方面的差異,又為探索推廣可資借鑒的經驗提供了更豐富的樣本的模式。
以新型主體協同化培育 加快發展進程
梁平在推進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的同時,還配套出臺了《關于加強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梁平縣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退出周轉金管理辦法》等政策措施,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全縣已發展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10家,入股耕地、林地面積分別達到1.73萬畝和36萬畝,涉及農戶7320戶,六合水產、龍灘柚子、仁賢水稻等28家股份合作社獲評全國及部、市級示范社。梁平將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有機結合,將土地經營交由部分新型主體,既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更為有效的制度支持和要素支撐,又為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的實現提供了更為堅實的承載主體和增收渠道。
以財政投入變革式創新 實現多贏目標
梁平創新性地出臺了《梁平縣農業項目財政補助資金股權化改革方案(試行)》政策文件,將財政資金投入到經營主體補助金額的50%作為項目所在地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涉及土地流轉或提供加工原材料的農民持股,項目財政補助資金由企業持股50%、集體經濟組織持股25%,農民持股25%,農民持股部分按照流轉(提供原材料)實際面積量化到戶。財政資金投入到農民合作社的補助項目,項目所在村集體經濟組織持股25%,合作社持股75%,合作社持股部分按照章程量化到成員。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持有農業經營主體股份,按持有股金額每年5%的標準實行固定分紅。梁平的探索有效促進了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與財政制度優化的深度融化,讓財政投入成為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的重要路徑,尤其是在集體經濟組織薄弱甚至空殼的地方由無到有、由弱到強的重要路徑,這個優化不僅有利于提高財政投入自身的效率,關鍵是把農民與新型經營主體的發展高度綁定,改變了農民與新型經營主體之間的對立和競爭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