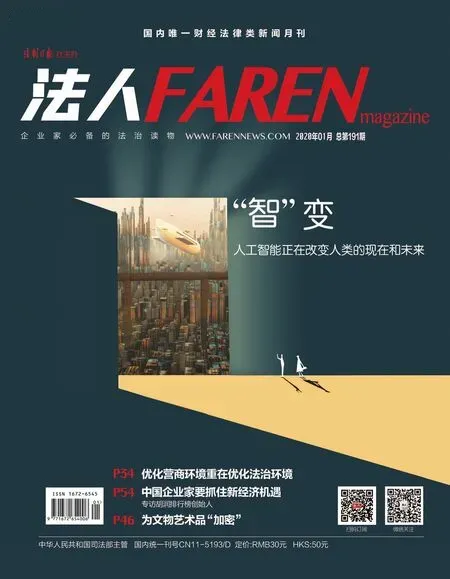一家特色書店的經營謀略空間價值比賣書更重要
◎ 文 《法人》特約撰稿 尚論聰
一家藝術濃度高的書店,如何賺錢?都說“不賺錢的書店各有各的難處,賺錢的書店卻有一個高招”,位于北京和平里北街遠東儀表廠的“碼字人書店”,經過一年多的運營,慢慢走出了自己的特色經營之路。
資深媒體人李蘇皖發起的“碼字人書店”有別于很多其他傳統書店,以戲劇、電影、詩歌三大塊為主題,匯聚了一大群青年創作者,使這家改造于老舊廠房的主題書店,成為藝術領域的策源地。昔日制造精密儀器的車間,在李蘇皖的精心裝飾之下,點亮了一盞盞溫暖的燈,變身成為讀書人的理想場所。在開業后的400天里,先后舉辦了詩歌朗誦會、文學沙龍、電影首映、藝術展覽、音樂秀、先鋒話劇表演等204場活動,在青年藝術家和讀者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
時尚藝術的空間場所搭建
“碼字人書店”創立于2018年9月,那時候的傳統實體書店一片蕭條。
近10年來,隨著中國傳統書店“倒閉潮”愈演愈烈,書店的生存陷入僵局。“傳統書店何去何從”一度引發中國社會的廣泛熱議。2011年,位于深圳華僑城OCT創意園南區的一家書店,直接為自己取名“30天就倒閉”, 是第一家“開業就為關門的書店”,掛在門口的“歡迎光臨,促進倒閉”的標語牌,令人感到悲涼。書店創辦人堅果也曾說,開這家書店,其實是一次為期30天的行為藝術。“30天就倒閉書店”曾經嘗試,每日招募一位新店長,更換一種新的經營模式。這種商業+藝術的創新銷售模式,吸引了不少讀者慕名而來,但是真正的書店老板,試錯的成本可不僅僅是30天,也許需要更大的代價。

書店一樓全景
創立之初,李蘇皖所思考的問題是,把餐飲和書店結合起來,或者一半銷售書,一半銷售咖啡;除了書籍之外,增加文創產品;或者將以上這些全部疊加在一起。但客觀地來說,并沒有改變書店作為圖書零售終端這樣一個事實。書店除了書籍之外,還有廣闊的空間,這個空間還能做些什么?最終,李蘇皖給“碼字人書店”這樣一個定位:聚焦、發展和推動青年創作者。


“碼字人書店”的每個角落都是精心設計的
青年創作者屬于不夠成熟,未能成名,但創作動力最為豐富、強烈、多元化的群體。他們需要和觀眾交流,進行藝術嘗試,一家書店可能就是他們表現自己的舞臺,李蘇皖決定幫助他們搭建這個互通橋梁,“某種意義上,自己的書店也是和這些青年創作者共同成長。”他說。正是在這個理念的驅動下,書店有了四大板塊的活動:其一是“向陌生致敬”,這是一個以詩歌為主題的活動,既有詩歌朗誦會,也有詩歌討論;其二是“映像館”,放映青年導演的紀錄片,并舉行映后談活動;其三是“青年藝術家系列”,主要是一些展覽,包括平面設計展覽、繪畫展、裝置藝術展、材料藝術展等;其四是“演出系列”,包括音樂沙龍、即興戲劇、沉浸式話劇等等。
以“向陌生致敬”為例,書店曾舉行過“青年詩人集結號”的活動,活動每一季有4場。每一次活動,都與讀者們分享了滿滿的詩意,令人印象深刻。在德國詩人保羅·策蘭的誕辰日,書店開展了“冬月與詩”的活動,舉辦了“保羅·策蘭誕辰紀念詩會”。 雖然在寒冷的冬日,但因為詩歌的陪伴,書店里的氣氛異常熱烈。詩人多多從懷里掏出一疊用紅筆做了標注的紙,對現場的讀者說:“策蘭的詩句我每天都讀,你們相信嗎?理解策蘭最好的方式,便是一遍一遍地讀他的詩。”策蘭詩集的中文譯者王家新先生也來到現場與讀者互動,他說:“我反復地讀他的詩,體會他的人生感悟,要求自己進入他內在的起源,知道每一個字詞,每一個細節……這樣才能長時間地與作者在心靈上達到契合。”一場詩會中,最為深情的表白莫過于此。
“映像館”的第一場活動,是青年導演吳杰拍攝的紀錄片《虎頭山》首映。這部電影講述了云南省宣威市一個名叫“虎頭山”的癌癥村的故事,電影以冷靜的鏡頭表達了青年藝術家對現實的關懷,隱忍而沉默,發人深省;獨立導演劉寬所拍攝的以翻譯家、詩人黃燦然的生活為主題的紀錄片《日常的奇跡》,展示的則是知識分子的另外一個世界。黃燦然早先在香港《大公報》擔任國際新聞翻譯,但是2014年辭職,回到了深圳一個名叫洞背村的村莊,開始了隱居生活。對于熱愛西方文學的讀者來說,黃燦然是一個不陌生的名字,他翻譯過蘇珊·桑塔格、布羅茨基、卡瓦菲斯、里爾克、聶魯達、米沃什等世界著名詩人和作家的作品30部,很多讀者都是通過黃燦然,才得以接觸這些偉大的詩歌。其實,這次活動不只是紀錄片放映,更是一場綜合性的活動。在書店入口的位置,用書架設置了一個“走廊”,擺放了黃燦然譯作的各種版本,實際上也是一個“譯本展”。
如上所述,打破詩歌、電影、戲劇界線的綜合性活動,“碼字人書店”已經舉辦過很多次。一位裝置藝術家曾用水晶玻璃設計了一頂王冠,用繩子從屋頂上懸垂下來,剛好落在書店的“主題書車”上,這個設置令人眼前一亮。藝術作品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存在,結合書店的場景,就像為書店裝上了一只“眼睛”。藝術家還在書架上做了一些其他裝置,使得讀者在翻閱書籍的時候,每一次都有一個新的“發現”,這種體驗新鮮而神秘,整個空間仿佛剎那間擁有了靈魂。
正是這些充滿時尚藝術設計的附加,使得書店吸引了大批年輕讀者,年輕人來這里讀書、買書,參與沙龍活動和表演。“碼字人書店”精心打造的場景,使得這里活力四射、獨具魅力,這些都是李蘇皖的經營法寶。
讀書空間比賣書更重要
李蘇皖認為,主題書店真正的價值首先在于空間,一個有溫度的空間對抗虛擬世界是有優勢的。“碼字人書店”分為樓上樓下兩部分,一動一靜分隔開來。樓上的空間布置比較寬敞,可以舉行活動;樓下放置桌椅和書架,便于讀者學習和讀書。
為了滿足讀者的讀書需求,李蘇皖用了一整年的時間來屯書、選書,所選的書不只是當下新出版的書籍,還包含早年出版的、印量很小的一些冷門藝術類書籍,甚至還有一些“絕版書”。在她看來,一本好書可能不是答案,而是一把鑰匙,幫你打開新世界的大門。在“碼字人書店”,買書不是最重要的,看書才是最重要的。和看書同等重要的,還有和“有趣的靈魂”交談,書店其實更像是“讀者的私享書房和文化客廳”。

話劇演出現場
為了讓讀者“舒服地讀書”,“碼字人書店”被李蘇皖打造得文藝范兒十足,但是她卻產生一種擔憂:書店的顏值太高,會不會分散讀者對書籍本身的關注?在并不算寬敞的一個空間里,她硬是塞進去了40個座位,而且每一個座位都帶桌子,她親自坐下去體驗這些“位置”,在每個位置上讀書或碼字,甚至考慮到了不同人的身高需求,桌椅的高矮并不完全相同,這樣讀者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
作為讀書人,李蘇皖還考慮到了光線,書店使用了超過預算兩倍的價格定制了照明燈,確保讓柔和的光打在每一個書架和桌子上,讓每一個愛讀書的人都能夠在溫柔的環境里安靜下來。這樣的設計實在貼心和周到,筆者還記得少年時在校門口的新華書店蹭書看,經常是周日早晨帶一壺水和一塊干面包,站在書架前泡一天,固然是精神上得到了滿足,但是兩腿腫脹,需要一整夜才能緩過來。幸好那時的店員還算和善,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對待我這樣蹭書的家伙們。
李蘇皖認為,對于主題書店來說,空間本身的價值比賣書更重要。書店里的書并不都值得購買,有些書也許看一遍就夠了,如果你在書店里讀完又放回了書架,那么這本書實際上已經屬于你。因此,書店應該是一個讀書的地方,而不僅是一個賣書的地方。很顯然,她的這一想法得到了大部分讀者的認同,很多人辦了會員卡是來店里看書的,看完又將書歸還。他們不但來這里看書,還帶著朋友來這里聚會,把這里變成了除家庭之外的第二活動空間。書店既是一個共享書房,也是社區里的文化客廳。

保羅·策蘭誕辰紀念詩會
此外,在書店找到你想要的書,也很重要。大部分書店所銷售的都是當下出版的熱門書籍,你要找一本早先出版的書很難。曾有一位研究者要找一本書,然而搜遍各家書店包括孔夫子舊書網,都沒有找到,后來打電話給“碼字人書店”,竟然很快找到了。有些書出版很久,在書架上蒙塵,似乎沒有人關注,然而它其實一直在等待一位有緣分的讀者。
人需要書籍,書籍也需要被發現。
留住幸福感就留住了人氣
那么,主題書店對于人或城市,是一種怎樣的存在呢?對于這個問題,李蘇皖給出了這樣一個答案:書店的燈光是一個城市的溫度,書店不應該只是一個打卡拍照的地方,它應該是一個日常的存在,融入到人們的生活中去,成為城市社區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應該關乎記憶,就像老巷子口的冷飲店,承載著少年時夏天的美好光陰。書店不只是單純零售圖書的場所,而是一個能夠讓人停下來、慢下來,并體味生活,進而對生活有更新、更多、更豐富認識的地方。對于社區來說,這里的人會因為一家書店的存在,而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個幸福的地方。
為了說明書店關乎社區人的幸福感,李蘇皖對筆者講了兩個故事:有一天,來了一位中年顧客,他在書店里逗留了很久,一本書一本書地翻看,嘗試去坐書店的每張椅子,最后辦了一張會員卡。他非常愉悅地告訴店員,“我就住在附近,辦了這張卡,仿佛擁有了整座書店的感覺”。這件事讓李蘇皖重新認識到了書店對于城市社區的存在意義——書店不只是一個物理空間,還是一個心靈空間。另外一位顧客則是居住在附近社區的中學生,他把書店當成了溫習功課的“自習室”,幾乎一放學就沖到這里來,帶著書本做作業,立志考清華大學。為此,書店專門給他預留了一個安靜空間,即便是書店正在做活動,也能夠使他安心學習。這樣的中學生會員還有不少——兩個高中男生,一個想當導演,另一個想當演員,他們不但經常來書店借閱影視方面的書籍,而且參加了書店的沉浸式話劇表演,獲得了觀眾們的贊賞。
深入理解讀者的需求,全方位地開拓讀者服務,這樣的經營之道才能讓藝術書店不再“曲高和寡”,努力把書店變成社區里最有藝術氛圍,也最具有人情味的地方,聚攏好口碑和人氣,關于賺錢的部分,自然孕育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