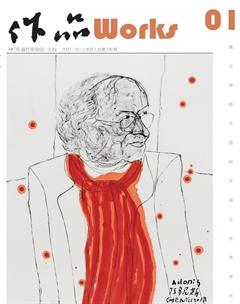隱秘自由
安迪·杜達克 高麒鵬
1
我陷入混沌,恍如夢幻。多倍體熱——“混合你”的代價之一,令我意識模糊。
我看見了你的父親們。還是當年的模樣。再一次地,我呼吸著他們的氣息,觸碰著他們的肌膚:亨利、金碩、哈迪、阿卡迪,每一位都有獨特的美。我再一次與他們相見,與他們墜入愛河,仿佛仍是初次。
然后再一次,我們進入彼此。
……Tau蛋白基因變體,對抗神經退行性疾病……
……載脂蛋白E型基因多態性,提供更長的壽命……
我吐出含混的詞句,仿佛正對著你,我未來的孩子言語。當我混合材料,將你塑造成形時,我發出了歡愉的樂音。但毫無疑問你聽不見我的聲音:此時你還只是一枚被排出的卵子,負載著我從精子中精挑細選后存儲在體內的遺傳基因。
……硬化蛋白突變,更強健的骨骼……
……DEC2基因突變,更短的睡眠時間……
最后的這一項來自阿卡迪。更長的清醒時間,這無疑是一份絕佳的禮物。你被賦有的潛能令人艷羨,猶如美夢中的美夢。你是我親手塑造的魅影,一次重現一位愛侶的身影。
如果我生活在幾個世紀之前,我該早就背上“蕩婦”的罵名,或許早已經被石刑處死;這很可能是你成年之后需要擔心的事情。女性主觀能動的美好時代似乎正一步步滑向終結。很多女性選擇不混合孩子,而儲精囊機能的逐步衰退并非是她們的唯一理由。只是我不能單純因為未來黯淡無光就放棄你。要是每個人都和我的想法相悖,那我們又將走向何方?
再說,混合已經開始了。我肯定得找到一個自己覺得足夠安全的地方再開始,不是嗎?
2
你將擁有一雙藍色的眼睛,其中會閃爍著金色和棕色的光澤。你將擁有一雙像亨利一樣的眼睛。
我和他上床本是為了尋歡。在那時,生育是最后才會浮現在我腦海里的事情;然而在慵懶的賢者時間里,他的美貌讓我改變了初衷。我們在他的被單里云雨時,他注視著我,眼神里帶有一股未經馴化的野性。對于大部分男人而言,這種眼神只會讓他們變得瘆人,可亨利卻因此顯得更富魅力。
這便是我成功受精懷上你的那一刻。“懷”,我指的是這個詞的現代含義,一層在不久的將來或將不復存在的含義。
我下載了一份父系協議,并將我的卷軸遞給了亨利。那時人們還會操心合法性的問題。我依然需要獲得男人的準許才能存儲他們的精子——難以置信,我竟然已經將亨利的精子存在體內七年了。那時“合眾為一”還是一個不值一提的小角色,成日在街頭巷尾嚷嚷著邪道巫術之類的胡話,而末日也還未給他們提供發展崛起的土壤。
亨利驚訝地看著我手中的卷軸。
“你無須承擔父親的責任,”我說,“除非你想承擔。這肯定不是你看過的第一份父系協議。”在他的答案出口之前,我又開始吻他。那時候一切都是那么的簡單。
另外眼睛的顏色并不復雜。我不會被先天后天這樣的問題困擾。一個合適的起點。
我恰巧對于基因型有所了解,因此如果我集中注意力,我能從我的儲精囊中辨認出些許我感興趣的天賦:從亨利那里得到的是“HERC2基因的基因內區86”,但這個名稱不過是無力的能指罷了。卡硼豪斯儲精囊是個神奇的東西。從外形上看它不過是子宮里不起眼的一塊增生,聯系著大腦內一塊豌豆粒大小的新組織——由某種病毒帶給女性的基因型,說起來也挺諷刺的。和很多人所以為的不同,我們女性并不會真真切切地看見基因;至于它們的學名是什么,這對我們而言也不重要。歡愉,快感,高潮,每種基因都會給我們帶來不同的感受,而我們則借此挑揀出最有希望存活的那一些。
約會結束時,亨利簽署了協議。他有心幫我把你養大,但去年“合眾為一”謀殺了他。那群混蛋設法進入了一個存儲有大量父系簽名的數據庫。亨利只是那“長刀之夜”里死去的上千人中的一個。
是我讓他的名字出現在那里的。他因我而死。我無法擺脫這一事實。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有讓他復生的打算。一雙漂亮的眼睛,他能給予的遠不止于此。
或許有一天你會替他報仇。以此為人生目標來塑造你,這樣有可能嗎?如果有,我又該不該這么做?太多問題了,而我卻沒有答案。縱然針對簡·卡硼豪斯的發明我們已經做了這么多研究,它依然包含著太多的秘密。
我只能希望有朝一日你也能體驗到這種神秘感。我希望你有一天也會感受到混合時的燥熱。身處迷醉仿佛置身宇宙,我失去了自己的所在。何處能給我足夠的安全感,讓我著手開始創造你?毫無疑問,不會是麥克摩多……
3
你的面部結構將帶有一夫多妻的烙印。某些特征的高度混合(諸如面部對稱或是免疫系統),會給混合者帶來獨特的歡愉。這并非巧合。在設計儲精囊的時候,簡·卡硼豪斯投入了不少才智。將面部對稱以及平均對稱比率調到最高,這一舉動帶來的感受近乎極樂歡欣。
然而后天因素會影響這些特征。我只能希望我們所在的地方能讓后天因素發揮積極的影響。
一名叫金碩的男人對你的面部以及免疫系統做出了超常的貢獻。我是在某個為女性而設的“父親派對”上遇見他的。說起來相當不光彩,但完美無瑕的一生恐怕也是枉活。
和亨利的約會已經過去了三年。我幾乎將你完全拋到了腦后。分配戰爭席卷了我們,“父親派對”也成了一種地下活動。這類派對一直都非常尷尬,男人間的嫉妒心理總是讓氣氛緊張不安;可如今,這類派對也成了“合眾為一”破壞的目標之一。
那時的我們想象不到事態還會怎樣惡化下去。恐怕你以后是沒機會參加“父親派對”了。
當時我們身處麥克摩多廢棄城區中一間租來的房間里。那確實是個破敗的地方,但“合眾為一”那群暴徒往往不會注意到雜亂城市中這不起眼的一部分。
“敬植入!”其中一個父親說道。
所有人都舉起了酒杯。父親們臉上是冷淡的笑容。呵,男人,如此神秘、如此迷人的造物,卻又總是在瑣事上糾纏不清。要是我為了大腦選擇其中一位,他還要知道他的樣貌為何不能引起我的興趣。我本無意告訴亨利他對你的塑造有什么貢獻,但他不自覺間透露出的些微不滿最終讓我感到疲倦。
“敬西亞蘭。”一位母親說道。
所以弗洛倫斯已經決心要一個男孩了。她一直都是個怪人。弗洛倫斯是我還在卡硼豪斯基金會實驗室任職時的同事。她是一個純粹的研究者,細細推敲著圍繞卡硼豪斯皮質的謎團;我則更像是士兵和工程師的結合體,用我的疫苗與“合眾為一”的病毒不斷地抗爭。所以事實上當時我并不是很理解弗洛倫斯的工作,但我喜歡聽她念叨其中的事情。
然而工作并未在派對時占據我的腦海。剛才祝酒的那個男人,我無法把我的眼睛從他英俊的外表上移開。光是沖著他的外表和他發生關系就已經足夠了,但我隨后認出了他是誰:馮金碩,著名的即興演員、游戲玩家。
而當房門從門框上崩脫時,我正絞盡腦汁想找出一句漂亮的搭訕話。
身著便衣的暴徒占據了客廳,他們戴著綠色的臂章,一面尖叫一面揮動手槍。參加派對的人混亂地逃竄,一群人將我逼進了臥室。不知是誰將我推進了壁櫥,隨后摔上了門。在昏暗的光線中我認出了金碩的身影。他的一根手指放在唇上。
玻璃粉碎。皮肉之苦。隨后一聲槍響,緊接著是失控的混亂。
“看來我們死定了。”我低語道,“既然這樣,要不要死得有型一點?”
微笑從他臉上閃過。正是這一抹微笑讓他賺了個盆滿缽滿,而這般魅力不可能只是因為他面部結構的優勢。我現在想明白了這一點。你無疑也繼承了他的一部分靈魂。
就是這樣,仿佛是一首早被遺忘的歌謠。我們的結合感覺真是太棒了!
我希望自己能活到親眼看到你讓人心碎的那個時候。要是什么地方能實現這一點,那我一定會在那里,不然我又何苦冒這么大的險?
4
批評簡·卡硼豪斯的人說她是一個怪物,指責她將儲精囊強加給人類,剝奪了我們在生育這件事上的選擇權。然而事實是,我們收獲的恰恰是選擇的權利。我并非一定要將你混合出生。這就是一個選擇。我依然可以借傳統方式受孕。
或者我可以縱情肉欲,和每一個漂亮的男性上床而不必擔心懷孕。如果沒有卡硼豪斯皮層深度神經化學質的許可,受孕是完全不可能的。
這便是選擇。
反卡硼豪斯論者說混合帶來的快感會抹殺選擇的權利。他們將混合后代的人描述成傀儡,慘遭已經入土的簡的操控。然而簡給我們帶來的快感只不過是一種指引,一種無言的標識,引導著我們通向廣受歡迎的生物特征以及組合方式。它從不勒令我們服從。有很多事物都讓我們陷入難以抉擇的境地,比如說多種多樣的身體素質,多種才智類型,或者是身體形態等等;而簡帶來的快感則讓選擇變得更為簡單。擁有游泳運動員身板的你,直覺會異常敏銳嗎?緊致結實的身體,再加上非凡的推理能力?或者,你會是一個小巧靈活能適應不同環境的孤獨癥患者?又或者,你會是以上特征有機的融合體?
選擇權在我手上。
如果簡想擁有對人類基因組絕對的控制,那她當初就會設計出能把我們徹底和混合絕緣的儲精囊。
此外有很多混合的選項和簡帶來的快感毫無關系。在我選擇你的眼睛顏色時,我體會到的只有選擇帶來的愉悅;這種愉悅同樣出現在我對你的膚色、發色以及其他和身體素質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關系的表面特征的選擇過程之中。事實上,簡從我們手中奪走的唯一選擇權便是給予后代客觀上不利的特征:我無法選擇讓你患有糖尿病,讓你酗酒,或者患有癌癥。
有一些人質疑簡定義遺傳適應度的標準。他們揣測這其中簡個人的偏見,聲稱她帶來的快感事實上夾帶著她對人類的主觀看法。“她無權這么做!”這些人叫囂道。
也許她確實沒有;但我為她的驕傲和獨斷歡呼。
在身體的燥熱中我感受到有什么正在逐漸成型。是某種特征,如果我選擇了這一特征,它將遍布你的身體。這是個復雜的特征,牽扯到大量的“基因”;但它尚未完全結合,依然無法辨認。撇開它的復雜程度不談,我能感受到這個特征非同尋常,或許從傳統意義上說,它是無法適應的。然而它帶來的快感,千變萬化的快感,正不斷累加。也許簡的主觀臆斷正在產生作用,可或許這并非是一件壞事。歸根結底,她是個天才。
5
我希望你長大之后不會對我強加給你的高智商而心生不滿。
身為一名病毒基因專家和納米工程師,我的智慧絕不落后于人。你會繼承我大部分的聰明才智,但我絕不可能做到哈迪借筆下那些似乎無法避免的文字組合所做到的事情。鑒于他發表的反“合眾為一”的文章,他自然逃不出被逮捕并游街示眾的命運。我不得不用一些實用主義來調和他不顧一切的超然才華,但內心里,我很慶幸哈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人。他的文字不僅推動了反“合眾為一”運動的進步,還將他帶到了我的身邊。
我們戴著傻瓜帽,跌跌撞撞地一起走著。腐爛的食物砸向我們,時不時還飛來幾塊石頭。他的帽子上寫著“母系社會的掃地工”,而我的帽子上寫著“精子銀行”。我們和一群同樣落難的人一起被驅趕著走下街道,每個人的帽子上都寫著難堪的詞語:基因巫婆,卡硼豪斯主義者,妻管嚴,諸如此類。給我們帶來如此苦痛的“合眾為一”成員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與你設想的不同,他們其中大部分男性從基因角度看都能健康存活下去——至少表面上看是這樣的。不過至于智力,我猜這群人就做不出什么貢獻了。毋庸置疑,這群男人中有一些盼望著古老神秘的父系社會能重回我們的世界,有一些則只是單純覺得自己所屬的性別從數量角度看受到了威脅。男性數量正不斷下降,而他們則竭力反抗著現實。
男性減少的問題已經存在有一段時間了。對此我從未覺得驚訝或者憤怒。它的到來是可以預見的,就像總會到來的壞天氣一樣,順其自然就好。只是如今,我自己正身處風暴的中心。
“合眾為一”里的女性才是真正捉摸不透的角色。她們永遠熾熱的自我厭惡,怎樣理解這種情緒究竟為何?我猜想她們之中很多人都在“合眾為一”最近釋放的病毒中失去了自己的儲精囊。也許她們覺得這是上帝的旨意,但這不足以解釋她們行為的暴力粗野。
那天下午我沒有想明白這個問題。而我現在仍然心懷困惑。
“我很欣賞你的作品。”我輕聲說,踉蹌著走到哈迪身邊。
垃圾如流彈般擊中了他。“我也很欣賞你的。”他說。
“你認識我?”
“當然,你以前可走在最前列啊!”
一個“合眾為一”的年輕守衛將我們分開,隨后把我推搡到人行道上。
“以前”,哈迪這個詞用得很準。卡硼豪斯基金會實驗室已經是燒毀的一片廢墟;弗洛倫斯死了,又一簇才智出眾的思想火花湮滅在黑暗的代紀之中。炸彈爆炸的時候,她距離突破性的新發現僅有一步之遙:她發現了卡硼豪斯皮質中一個全新的組織,某個蟄伏許久直至當時才逐漸蘇醒過來的東西。
在我們面前,一個帽子上寫有“基因巫婆”的年老女人被一群暴徒強迫跪在了地上。“供認你犯下的罪行!”一個神經質的男人喝令道。他或許看起來是個男人,但他的行為……不過小孩般幼稚。
“無罪可認。”那個女人說道。
一群人聚集在不遠處,發出噓聲,大聲叫罵著。“優生學的走狗!”有人尖叫道。
一個女孩走上前扇了那個老女人一巴掌。紙帽子摔落在地。“你破壞了自然的基因傳遞,你有罪!招供吧!”
女人的眼神透過額前的灰發直直射向女孩。“‘自然,你以為自己知道這個詞的含義,是不是?”神秘感包裹著她。
他們繼續毆打她,命令她招供。這群暴徒的選擇性失明以及毫無根據的自我正義感讓我幾欲嘔吐,也讓我很想親手結果他們的性命。我猜想哈迪一定是從我的眼神中讀出了這一切,因為他拉住了我,很可能也救了我一命。怒火中燒的我渾身顫抖。我該不該把這種脾氣傳給你?野蠻的怒火是否只會傷害自己和別人?我究竟是誰,憑什么可以替你做出決定?“女性生產,因此女性決定”,我依然相信這句話,否則我也不會在混合產生的燥熱間喃喃自語。
但這絕非易事。
我感受到這股野蠻的怒火正逐漸升騰,而那難解的特征也在燥熱中緩慢成型。這是某個更廣博的特征的一個側面,是一首漸趨激昂的愉悅交響曲中的一個篇章。選擇權依然在我手上。不論這個特征是什么,我依然可以盡情享受,而無須讓它成為你的一部分。很多“合眾為一”的成員并不明白這一點。
只是這逐漸成形的謎題讓我感到困擾。在我們做的所有研究中,沒有任何信息指向它可能的謎底。
那個老女人依然是眾人關注的焦點。此時不采取行動就再無如此良機了。這場游行的終結不是我們的死亡,至少也會是徹底絕育。我抓住哈迪的手,一頭沖進了麥克摩多蜿蜒的小巷。我意識到他在笑,隨后我自己的笑聲讓我吃了一驚。我們還活著,而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律動。在一個靠近無風灣的安靜滴水庭院里,我們稍微暫停腳步喘了口氣,隨后我們又開始奔跑。等到我們進入羅斯島迷宮般的住房群中時,我們減慢腳步,開始快步行走。
我們一直走到夜幕降臨,手牽著手,始終保持沉默。最后我們用了些我的密碼幣,在廢棄城區中開了一間便宜的房。我們精疲力竭,但那一夜我們幾乎沒有入眠。
我從未告訴哈迪我儲藏了他的精子。但正如我說的,他是個聰明人。我愿意相信他自己已經弄明白了我的所作所為。
6
你會享受到的很多天賦都繼承自一個叫阿卡迪的男人,只是我不確定你是否會擁有將我吸引到他身邊的那一個。
我第一次在阿拉斯基福尼亞難民營見到阿卡迪時并沒有覺得他有什么吸引力。他表現得像是一位正派的政治家:抱著難民的小孩,傾聽難民的抱怨,身后跟著一眾自己的媒體代理人和保鏢。我猜想這不過是一場政治作秀。他正在競選州長;而他那憎恨難民且偏袒“合眾為一”的對手則是個令人望而生畏的角色。阿拉斯基福尼亞是地球上最后一片女性還能幻想儲藏精子混合后代的地方。這也是為什么我會來到這里。但我沒想到會踏入這樣一個慘淡的難民營,更沒想到會親歷政治競選。在我眼里,這場競選很有可能會熄滅這個星球上最后一盞自由的明燈。
總的來說,阿卡迪在這場政治斗爭中站在了正確的一邊——可他仍然是個政客。在我和他握手之前,我內心就確定了這一點。
“請問你叫什么名字?”
“尼娜。”我說。
“你吃的東西夠嗎,尼娜?”
實話實說,不夠,因為我還沒餓到會把身體出賣給守衛以換取糧食的地步。靠著半袋配給糧,我勉強活過了一天又一天。我本應該把這些都告訴他的,可那時的我只能盯著他看:他已是中年,身體有些發福,但不可謂沒有魅力。我說不準他是否真的在乎我的回答。不論如何,我什么都說不出口。
“你會落到這種地方,我很抱歉。”他說,“我會讓你離開這里的。”他似乎記起了自己的身份,回頭望向負責新聞報道的媒體代理人,隨后又將視線轉向衣衫襤褸形容悲慘的人群。“你們都會離開這里的!”他說,“我向你們保證!”零零星星的歡呼聲,然而大部分的難民都像我一樣,被疲倦和恐懼剝奪了說話的能力。
然后他離開了,被他的團隊包圍著,推向了下一場電視秀。
那是一個陰暗寒冷的日子。余下的時間我都在丟棄的配給糧袋里尋找面包屑。我在想像阿卡迪一樣,來到這樣一個地方,畫幾個大餅,心里很清楚自己反正也會離開,那些帶刺的鐵網和炮塔也不是沖著自己而設的,這樣肯定非常美好。我已經在這里待了一個月了。我開始懷疑自己還有沒有可能從這里走出去。
至于混合你,那更是癡人說夢。
那晚我走進一個擁擠的電視帳篷,看著阿卡迪和他的對手瑪麗琳·沈辯論。整場辯論就是一出尋常的美式鬧劇,所以我對阿卡迪的印象也沒發生什么改變。他試圖成為獨行的正義斗士,卻給人以自命清高的感覺;而沈則插科打諢,甚至用上了游街示眾時我聽到的誹謗之語。她對事實真相的了解幾乎為零,似乎對卡硼豪斯儲精囊的歷史和作用也一無所知。她的儲精囊早已在某個美國內陸的宗教組織的洗禮中被消除了。她以傳統的方式生養兩個孩子。每當家庭觀成為話題中心時,她總喜歡拿自己的生育史喋喋不休。
阿卡迪為三個混合出的孩子貢獻了精子。他不斷地攻破沈錯漏百出的論點,可這無關緊要;他直接尖銳地回應沈的粗言與一廂情愿的控訴,可他缺乏感召人的魅力。
他換不到任何笑聲。
兩天之后,沈橫掃了所有選區。對于我們這群難民而言,沈的勝利顯得那么不真實,仿佛一場不可能出現的噩夢。這里可是阿拉斯基福尼亞。我們所在的難民營距離新阿斯托利亞并不遠,而那里是我們這個世界最后的山巔之城。
沈上任一周后,一群面色鐵青的雇傭兵出現在難民營大門口,要求進入營內。難民中的孩子已經開始渾身發抖著東躲西藏。我看見一些孩子的身影消失在戶外廁所下。適應難民營的生活沒有花費他們太多的時間。孩子們的直覺總是如此敏銳而強烈。
第一聲槍響響起時,我跑向了難民營的中心。
難民匯集成恐慌的人流。所有人都竭力想擠進人群的中心,期盼著在這場殺戮結束時,自己能從死人堆中幸存下來。我想不到更好的辦法,所以我也加入了這噩夢般的混亂中。驚懼的人群邊緣的難民正接連倒下。沈雇來的殺手將我們團團包圍,在我們接近他們的時候向我們掃射。擠成一團的人群變得愈發稀疏,人們尖叫著,變得越發恐懼而狂亂。死者倒在我們身邊,像是死亡劃出的邊界。
一個奇怪的想法出現在我的腦海里:我希望那時我已經混合了你,生了你。
即便這意味著你不得不藏身于骯臟污穢的避難所,甚至在某個里面死去。我們會在從麥克摩多出發的一艘船上看著大海里躍出的飛魚,而無須理會我們身處的不過是裝滿難民的一艘破漁船,無須理會這艘船只是勉強才在大海上漂浮航行,也無須理會你的一生都會伴隨著羞恥和死亡。
你肯定會被飛魚迷住的。
我現在又在哪里?
槍聲變了,遠處的聲音和槍聲交織在一起。忽然間沈派來的雇傭兵開始倒下,有一些開始進行防御性射擊,有一些干脆轉身逃跑。
突如其來的變化讓剛才還抱成一團的難民開始分散,仿佛是受熱的一團氣體。我看見了幾個新出現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是北美某個雇傭兵集團的人。這些女人身上的裝甲會隨著她們移動而呈現出周邊環境的顏色。我猜想除了我看到的幾個之外,她們還來了更多的人。子彈劃過天空發出的尖嘯。我的猜想得到了佐證。
我肯定活下來了。
在我開始混合你之前,我真的找到合適的避難所了嗎?在臨近死亡的人群中所想到的一切讓我不得不思考這個問題。
燥熱正逼向頂峰。回憶如海潮般翻滾,又迅速消逝。我為什么要回想那該死的難民營里發生的事情?阿卡迪,對,是因為阿卡迪和他給我的東西,其中就有一種后葉催產素受體基因的變體。
7
曾經有一種叫作“婚姻”的東西。他們想要它所給予的安全的幻想回到我們的生活。
曾經只有一個詞——愛,而不是像現在一樣有上百個詞,就像因紐特人描述“雪”一樣。他們想要昔日的簡潔回到我們的生活。“合眾為一”盼望著以一個詞團結一切,以一個過時的幻想來團結一切。
他們的愿望絕不能實現。
我思考著弗洛倫斯·福里德在卡硼豪斯皮質里發現的那個結構:自卡硼豪斯時代的開端就始終處于沉睡狀態,最近十幾年才終于蘇醒——它是在回應“合眾為一”帶來的威脅嗎?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探究的有趣設想。或許弗洛倫斯自己也想到了這一點,只是她從未有機會告訴我罷了。
8
一隊巴士等著我們。難民營北面死氣沉沉的城郊停車場里回蕩著發動機空轉的轟鳴。
將我們搭救出來的雇傭兵趕著我們走向巴士。近三千驚懼惶恐的難民逐一登上了老舊的大巴。軍需糧和救濟藥品在上車之后發到了我們手上。很快車隊便沿著一條滿是彈坑的高速路緩慢向東部駛去,駛向北美內陸不為人知的黑暗。
當我從一陣不適的眩暈中醒來時,我發現阿卡迪正坐在我身邊。
“你感覺怎么樣?”他問。
我在座位上扭動著自己的身子,很認真地思考了一下他的問題:“還活著讓我有些興奮……很害怕……很累……但不管怎樣我吃飽了。我們得救了,我是不是該向你說聲謝謝?”
這個問題似乎讓他很難堪,于是我拋出了另一個問題:“你最后坐到了我身邊……這算是個巧合嗎?”
“我看見你上車了,我記得競選的時候看見過你。”
“你不會是在和我這么一個剛獲得自由的難民調情吧?不然可以說是史上最怪異的浪漫行為了。”
“天啊……不,我……”一時間他陷入迷茫,臉也紅了起來,看起來他已經準備站起身坐到其他地方了。
“別緊張。開個玩笑。”男人和他們的敏感,你能有什么辦法?全世界都知道女人要比男人更風趣。
他望著我的眼睛,似乎受到了驚嚇。他看起來就像我們之中的一員,一個難民,或許他現在就是也說不定。“在競選電視秀的時候,我覺得你似乎想說點什么,但你卻說不出口,或者是不愿說出口。”他的微笑帶著歉意,“對不起。我不該拿這些打擾你的。你需要休息。”他渾身顫抖,似乎下一秒淚水就會奪眶而出。
真是一個典型的男性:為自己的情緒所左右的生物。可這不正是我們喜歡他們的理由嗎?
他的顧問來到身邊時,他設法讓自己振作些。我無意偷聽,但我當時就坐在他們身邊。他們耳語著,凄慘的語調很快告訴了我事情的真相:阿卡迪自己花錢雇人把我們救了出來;這一決定花掉了他絕大部分的家族財產和全部的競選資金;他并不知道該去向何方;營救行動也是在匆忙中施行的。當他們低聲討論著幾個毫無吸引力的目的地(赫特蘭德聯邦,大湖國,努納武特,諸如此類)時,被雇傭兵追殺時產生的頓悟又向我襲來。
一個最適合混合你的時間和地點,其實根本就不存在。
當他的同伴終于離開,他得以喘息之時,他對我說:“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優秀的政客。事實上,我從來都干不好任何事。要不是因為家里給了這么多錢,我早就被學校趕出來了。也是靠著家族的錢,我買通了通向政壇的路。在此之前,我就是個花花公子。我浪費掉了這么多的錢……今天的行為是對我的良心,或者是對我誤認為是良心的東西的一個小小的慰藉。我是個無可救藥的人,尼娜。”
他還記得我的名字。他哭泣的時候我握住了他的手,腦海中則想著你:你會成為什么樣的人,你可能會有怎樣的成就……我還記得在災難降臨麥克摩多前弗洛倫斯給我看過的新數據。或許那個蘇醒過來的結構意識到了對它有威脅的那些想法,還有廣義上對所有儲精囊都會產生威脅的想法。歸根結底,它和大腦間的聯系總是密不可分的。
它知道自己正身處怎樣的危機之中嗎?更確切點說,我身體里的那個結構,它知道嗎?如果它知道,它是否正逐漸蘇醒,直面威脅?
9
旅途。這就是這個世界正逐漸丟掉的東西。
卡硼豪斯儲精囊將受孕變成了一場旅途,一場很可能持續多年,并會塑造準媽媽人生的發現之旅。或許我的旅途會是最后幾場旅途之一。我只得希望你以后也會有你自己的旅途,即便它如我的一般充滿傷悲。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我將把你設置為女性,就像很多在我之前的混合母親所做的一樣。確實,我們該為女性人口數量過多負責;有些人還認為我們也該為蔓延開來的敵意負上責任。
但現在,身處混合的燥熱之中,我將這些煩惱全都拋在了腦后。
這是我應有的權力,我應享的愉悅。而現在我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抉擇。
你該不該獲得使反叛性格呈外在顯型的基因組?你會不會是一個蔑視權威的人?或許等你長大了,你會看不起我,憎恨我,因為我把你變成了一個武器。如果事情變成了這樣,我只得以愛面對你滿腔的恨意。除此之外,我別無他法。
如果我對弗洛倫斯·福里德發現的那個結構的猜測沒有錯,你將會有很多并肩作戰的姐妹。如果我的猜測沒有錯,全世界的女性現在都面臨著這同一個抉擇。簡的個人偏見是如此清晰明確,當我考慮為你注入反叛的基因組時,它以極致的歡愉撼動著我的身軀。
我還記得那個臨近一塊巨大冰磧石的停車場。難民搭起的帳篷仿佛憑空出現的村莊。我們的人數削減了一半。很多人決定前往大湖國或者東部的城邦尋找生活的轉機。阿卡迪沒有阻攔他們,他甚至為這些決意脫離他的人準備了補給。而這一舉動令我下定了決心。
所以,現在我身處曾屬于加拿大的某個地方。我躺在一個帳篷里。阿卡迪從我身后抱著我。我能感受到他的身體。
有一些男人相信,如果在女性混合后代的時候抱著她們,自己就能感受到混合的燥熱,甚至置身其中。愚蠢的生物。但這讓他們感到高興,讓他們有一種參與的感覺。容易遷就男人一直是我的弱點。一個漂亮的男人哭泣,這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不愿看見的事情。
已經沒有時間猶豫不決了。為了簡的夢想能繼續存在下去,你必須戰斗。
但你也會擁有阿卡迪的同理心,這是他身上所有特征里最具男性氣概的那個。你還會擁有他對人的無私。或許這些特征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你反叛的天性將你拖向黑暗的深淵;否則,我覺得我無法將你變成戰斗的武器。
沒錯,這種感覺棒極了。天啊!簡·卡硼豪斯是一個怪物?這種銷魂的感覺可是迄今最強的一波!什么樣的怪物會回報善意的傳播呢?
你已經完整了,我的女兒。我知道我犯下了很多錯誤,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我也會犯下更多。我只能希望你長大之后能原諒我。為人母在犯錯這方面從未改變,一點都沒有。
這已經超過我的極限了。這種愉悅實在是太強烈了。我怎么會有哪怕一絲不混合你的念頭?到時候了,就是現在!
責編: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