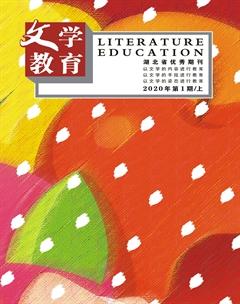中國式愛情觀:《宣室志·英臺》分析
內容摘要:在中國古代所流傳的愛情故事中,梁祝故事家喻戶曉,所描述之情感亦被視為中國古代愛情的經典之作。本文回顧研究《英臺》這梁祝故事最早版本的意義,并注意到《英臺》原型在敘事上的簡明與純粹,減少因戲劇張力及情節考慮的橋段增補所附加形成的干擾,讓人更容易把握《英臺》原本主訴的主題──情感──其特殊性之所在,與我們今日對愛情的看法有本質性的差別。由《英臺》所反映的中國式的愛情觀法與思維,值得我們重新重視并予討論。
關鍵詞:中國式愛情觀 梁祝 故事改寫
英臺,上虞祝氏女,偽為男裝游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為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后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有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張讀《英臺》
在中國古代所流傳的愛情故事中,梁祝的故事乃家喻戶曉,所描述之情感亦被視為中國古代愛情的經典之作。其中,唐代張讀《宣室志·英臺》(以下簡稱《英臺》),為世傳梁祝故事的原型,反映了梁祝故事情節的基本架構,[1]如:英臺易裝游學、兩人同窗共學、山伯求聘而不得、山伯病歿、英臺哭墓、同冢并埋、梁祝墓褒封為義婦冢等。不過,若拿《英臺》這有關梁祝故事最早的版本與后世版本相較,仍可清楚看到《英臺》在故事情節張力上的欠缺與不足。當然,這早已成為后世在進行梁祝故事改編時(尤其改編為戲劇時)所必然列入考慮而力圖解決突破的部分。梁祝故事,也因此在情節的細節交代上更為細膩豐富、引人入勝。若是這樣,那么再次回顧研究《英臺》這梁祝故事最早版本的意義何在?對此,我們其實更應注意到,正因《英臺》這篇短文在敘事上的簡明與純粹,減少了因戲劇張力及情節考慮的橋段增補所附加形成的干擾,才使我們更容易把握住《英臺》原本主訴的主題──情感──其特殊性之所在。這特殊性在于:《英臺》中所描述的梁祝情感,實與我們時代今日對愛情的看法(受西方式愛情觀所影響),有很大、甚至本質性的差別。由《英臺》所反映的中國式的愛情觀與思維,故而值得我們重新重視并予討論。以下,本文便順著前述的思想脈絡,從后世版本與《英臺》的差異比較,先行厘清后來版本因情節增補所可能對《英臺》這原始版本形成的干擾。而后回歸《英臺》文本,探討其中所顯示的男女情誼之實質內涵,同時進行與西方式愛情觀法的對照,闡述中國古代愛情觀法在時代今日的價值意義與啟示作用。
一.情節的增補所產生的問題
若我們以后世梁祝作品與張讀《英臺》進行對照,如本文暫以清·邵金彪《祝英臺小傳》作為對照,[2]茲引原文于下:
祝英臺,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無兄弟,才貌雙絕。父母欲為擇偶,英臺曰:「兒當出外游學,得賢士事之耳。」因易男裝,改稱九官。遇會稽梁山伯亦游學,遂與偕至宜興善權山之碧鮮巖,筑庵讀書。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為女子。臨別梁,約曰:「某月日可相訪,將告父母,以妹妻君。」實則以身許之也。梁自以家貧,羞澀畏行,遂至衍期。父母以英臺字馬氏子。后梁為鄞令,過祝家詢九官,家僮曰,「吾家但有九娘,無九官也。」梁驚悟,以同學之誼乞一見。英臺羅扇遮面出,側身一揖而已。梁悔念成疾卒,遺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臺將歸馬氏,命舟子迂道過其處。至則風濤大作,舟遂停泊。英臺乃造梁墓前,失聲慟哭。地忽裂開,墜入塋中。繡裙綺襦,化蝶飛去。丞相謝安聞其事于朝,請封為「義婦」。此東晉永和時事也。齊和帝時,梁復顯靈異,助戰有功,有司為立廟于鄞,合祀梁祝。[3]
不難看到,除了增加了著名的「化蝶」情節,以作為梁祝二人悲劇命運的反轉之外,最主要的,是在于對人物性格形象的細節刻劃,以及梁、祝二人因身分階級差異所造成的問題,前者如英臺的機伶聰慧自主獨立與山伯質樸木訥至近乎呆板的形象,后者如強調英臺為「富家女」而山伯「家貧」二人在社會階級上的不相稱。這些都是張讀《英臺》所沒有的(至低限度,未多加渲染著墨的)。人物性格實戲劇之主要成分,而由社會階級地位差異所衍生的種種問題及對故事情節發展的影響,則更是引發人心產生不平及回饋共鳴的重要因素。至于由增補化蝶情節所帶來的對世俗大眾心理的慰藉作用,同樣是使得梁祝故事能通行、流傳至今的原因。因梁祝故事在后世逐漸流傳,改編成小說戲曲者不計其數,為增益戲劇或說書橋段的張力,故增加了許多在張讀《英臺》這原初版本中所沒有的劇情及細節。這些做法,確實成功營造出梁祝故事更形豐富的內容,人物刻劃也更為生動鮮明,但同時也衍生了一些問題,甚至可能模糊了故事原本的焦點。舉例來說,在后世版本的改動中,說山伯因家貧而感自卑(「羞澀畏行」),故未敢赴約遂致衍期。直到后來當了縣令有了社會地位才造訪祝氏。山伯之所以錯過了結親英臺的機會,以致懊悔抑郁而終,即導因于此。誠然,梁祝二人身世背景這不由自主的差距、以及各自在生長背景下所形塑的人格差異,都是使得人物形象更為鮮明、故事情節更富張力,且既更為接近世俗一般人日常生存之樣態、同時也因這些遭遇都有其無可自主的原因而使人感其命運的捉弄而為之憐惜。但是,也正是在如此塑造山伯人物性格(受其家世背景所影響)鮮明形象的同時,山伯人格的高度卻也同時降低了:如是刻劃山伯形象,則山伯人格與世俗價值以富貴利達立自己生命之人,實無差異,與中國傳統的「君子」人格形象,距離甚遠。山伯形象既已刻畫為如此,那么更矛盾的是:作為對自己生命有其獨立價值向往、非隨波逐流的英臺:「兒當出外游學,得賢士事之耳」,心目中的賢士實則不過世俗之流,根本并非什么真賢德的君子。如是,連文本本來所欲賦予英臺的人格獨立形象,也同時被瓦解了。而梁祝故事原本所主訴的對于世俗禮教與價值觀念的突破(如英臺的自主及不拘繁文縟節),也同樣在這種階級差異與人物性格刻畫的同時(山伯英臺都只是依循世俗價值之生命型態而已),再次地被曲解。這些都是版本在情節上的增補更動過程中,不可不注意到的問題。
二.由《英臺》所傳達的中國愛情觀
反觀,張讀《英臺》這梁祝故事的原型,反而在少了因增補情節所導致的問題上,變得存有更多的想象空間。同時也使我們更容易將目光焦點單純放在整個故事頗耐人尋味與存疑的一點,此即「帳然若有所失」的問題。
事實上,單純就張讀《英臺》文本而觀,則應有兩大重點:一是對傳統禮教束縛的突破;二是中國特有的愛情觀法的問題。前者我們前段提到過了,少了后世版本對情節的增補改動所可能衍生的矛盾,反觀張讀《英臺》在突破傳統禮教上的敘述上,則顯得單純統一。從文本末句「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可知梁祝故事雖于后世盛行,然其于東晉即已流傳,故其起源理應更早。而魏晉時期,正是中國政治歷史上昏暗之時代,對人文禮樂真實意義的扭曲(禮教殺人),正是造成這個時代晦暗的根本原因,此即梁祝故事之于當時時代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故不應只將作品意義局限于談論兩性之愛而已。至于第二點,即由《英臺》所傳達的中國古代特殊的愛情觀法,則明顯是由「悵然如有所失」在文本敘述中所安排的位置而展現出來。依常理,「悵然如有所失」似應置于「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一句之后始合理,即因求婚不得而感心情失落,如是解釋兩人之間的愛情關系將更形適切。為什么作者將「悵然如有所失」放在「方知其為女子」之后?是一時不察、失誤?還是有其他意義?縱使山伯在得知英臺實為女子后可能備感訝異,并責怪自己之不察,但這種心情始終與「悵然如有所失」有很大的距離,甚至這種驚訝的心情理應更可以是帶著愛慕的喜悅在背后的。山伯在得知英臺為女子后何以「悵然如有所失」,以及由「悵然如有所失」在文本句中的位置所凸顯的問題──究竟兩人之情感是何種情感──因而反而成為本文最重要的關鍵所在。而在后世對梁祝故事的情節改動中,這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隱沒了。
其實,山伯得知英臺為女兒身而感到「悵然」,此恐為失去適道共勉之朋侶而感「如有所失」:在傳統禮教體制中,要維持未婚男女情誼,確是困難重重,故即便英臺得以出游與山伯同窗共學,如此突破禮教藩籬,也仍然只能是透過「易裝」(偽裝)來間接達成的,故于山伯訪英臺而當英臺以真面目示人時,始終也只能是「羅扇遮面出,側身一揖而已」。其中唯一解決之道,就是將朋友之義轉為鶼鰈之情,使這份情感得以延續,故山伯必然告其父母求聘。至于兩人間之情誼究竟單純是朋友之義,抑或參雜男女之情,實難論定、亦不必論定。《英臺》中「義婦」一詞不正兼含此二者,使得這兩種情感仍可并行而不相悖。
從這里已可清楚看到,中國式的愛情觀,實與西方以異性欲望之相互吸引結合之觀點不同。若男女之情感亦屬人倫情感關系的一種,于此我們可問:人倫存在其一切情感關系之鏈接,其最終之價值意義究竟何在?于中國古代思想中,人倫一切之關系交往,不論情感交集如何緊密,始終都是以相互致力并藉以完成自身真實生命為其終極意義,在成就人我相互之致力而一體、與其間各自生命之努力而成就自身主體之真實,而非在種種自我的顯示(不論這自我型態以多高、多超越的方式與價值呈現)。如山伯之為求結親英臺,實為求延續兩人適道共勉相互為他并同時完成自己之可能性而已,故非單純只出于一種對異性(超越者)之熱愛所驅使。在本質上,中國古代所言人倫情感,就其人格生命的相互致力與真實成就這點而言,實可相通而不必局限于男女之情。且言男女之情,亦非只有戀愛之關系,只以婚前戀愛之關系為情感最高價值型態,如西方文學始終所崇尚歌頌的那樣。若能明白人類情感存在的真實意義,其實不外根本于此,亦不應根本偏離了人作為人其人性地真實這一意義,至此我們可以了解、并肯定中國特殊愛情觀法本身的意義與價值。這其實更會是閱讀張讀《英臺》至為深刻的意義之所在。
三.結語
若我們比較中國古代夫婦之道與西方愛情觀的差異,自表面即明顯看到,西方視婚姻為戀愛之墳墓,似只有婚前之戀愛更為人類情感其價值所主;而中國則相反,著重在情定及婚后日常生活中的相互扶持、患難真情。故在西方文學中,在人與人的關系及情感連結中,最易入文人之筆的為男女之關系,而表現男女之情感,則似只有婚前之戀愛,乃為戀愛與人類情感價值高度之所在。其實,中西方文明這兩種面對情感的解釋差異,是根源于雙方文明對價值截然相反之看法的。西方人之所以特重婚前之戀愛,因唯有在婚前,對方對我而言為一超越境中之對象。視對方處一超越價值地位,于是吾人可寄托無盡之理想與美好于對象身上,并加以神圣化。由此可引出吾人無盡的追求意愿與愿力,從而表現其生命精神之向上與對完美價值之向往。此價值型態,充其極,甚至可至于以殉情(全然解消自我于對象上)作為情感最高層次之顯示。故早在古希臘潘多拉神話中,潘多拉(作為人類中第一位女性)便是以神性超越的姿態出現而為人類所期盼欲求者。本質上,這種欲望追求,直是人類對其自身平凡人性之一種異化及否定,而趨向神性。而古希臘神話,正是針對人類超越性價值向往及欲望之一種反省與抵制。至于在中國,則不尚追求婚前之戀愛,不將所愛者過度理想化、神圣化,而推至超越(推崇得越高,便越背離人性平凡之道)。中國人言男女之情,尤重婚后之愛,與其天長地久歷經生活磨難而相互扶持不離不棄之情真。這種情感之真實,在本質上所實現的,實乃人性之「恩義」而非神靈神性超越絕對之欲望。同時也因本于人性之正,故使得中國古代論述男女之情,亦可同時通向其他人倫情感,在情感本質上無所隔閡限制及沖突矛盾,正如《英臺》中山伯欲轉朋友之義轉為鶼鰈之情那樣。故在中國古代愛情文學所好者,非必主于描述男女相求之情,反而更著墨于婚后或情定后的患難扶持之情。西方文人重愛情不重結婚,中國儒者則以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婦:「燕爾新婚,如兄如弟。」其意即在于此。
參考文獻
[1]清·吳景墻:《宜興荊溪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叢書》第9卷(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
[2]黃浩瀚〈信不信由你:梁祝化蝶與傳說信念〉,《中外文學》第16卷(第11期),1988年,p90-107。
[3]劉斐玟〈情義、性別與階級的再現與超越:梁祝敘說與文體之音〉,《戲劇研究》第5期2010年1月,p27-68。
注 釋
[1]有關梁祝的記錄,最早見于初唐·梁載言所撰《十道四藩志》,不過該書對梁祝記述十分簡略,只提及:「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冢。」對梁祝記載較為完整的,首推晚唐張讀的《宣室志·英臺》。張讀的《英臺》,故可算是當前可考的梁祝文獻中年代最為久遠的文本,廣泛流傳,影響極深,同時因反映了梁祝故事情節的基礎架構,故可視之為梁祝故事的原型。
[2]之所以引此段文獻作為參照,是因為邵金彪《祝英臺小傳》文字簡潔地呈現出后世對于梁祝故事在情節內容上所增加的幾個主要部分。
[3]載于清·吳景墻:《宜興荊豁縣新志》,收入《中國地方志叢書》卷9,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
(作者介紹:吳元嘉,文學博士,吳鳳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