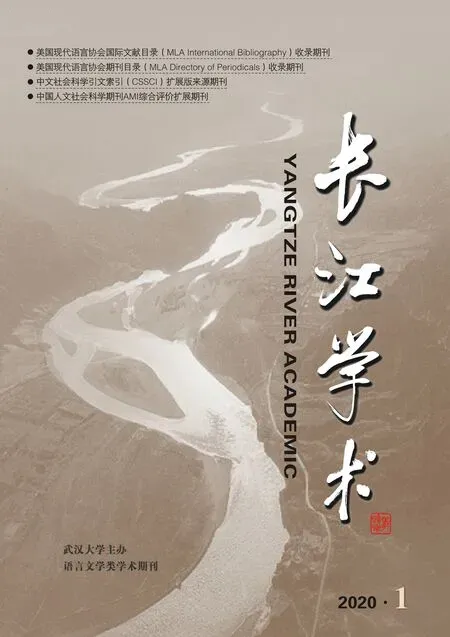三環同心圓:漢英兩種語言波浪式的傳播模式
2020-02-16 07:21:58劉望冬
長江學術
2020年1期
徐 杰 劉望冬
(1.澳門大學 人文學院,澳門999078/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430072;2.華中師范大學 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430079)
引 言
當今中國正處于迅速崛起的關鍵歷史節點,我們的漢民族共同語也處于一個相似的歷史發展階段。得益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漢語在其原有豐沛文化優勢之外獲得了巨大的經濟競爭力,國際地位快速提高。作為一種文化紐帶和交際工具,漢語正逐漸超越國界而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資源。適時有效推動漢語的國際化進程,將有益于華人,有利于中國,造福全世界。
語言沒有優劣之分,但有強弱之別,決定某種語言強弱的主要是語言之外的社會文化經濟等因素,即語言綜合競爭力。如果把世界語言由強到弱劃分為四個層級:頂層語言、高層語言、中層語言和底層語言,那么獨自占據頂層語言位置的毋庸置疑是英語。①所謂“語言綜合競爭力”主要包括五項要素:政治競爭力、文化競爭力、經濟競爭力、人口競爭力、文字競爭力。高層語言包括除英語外其他五種聯合國工作語言和德語、日語;中層語言包括韓語、馬來語、意大利語、荷蘭語等綜合競爭力中等的民族語言;底層語言指數量龐大的弱小民族語言,包括各后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的土著語言,各種地區方言。“語言強弱”概念參見鄒嘉彥、游汝杰:《漢語與華人社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版,第209 頁。憑借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五個核心英語國家的巨大綜合經濟實力,英語牢牢占據頂層語言的位置并成為跨民族的國際共同語。……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城市道橋與防洪(2022年4期)2022-07-01 06:04:12
文苑(2020年4期)2020-05-30 12:35:30
當代陜西(2019年8期)2019-05-09 02:22:48
動漫星空(興趣百科)(2019年3期)2019-03-07 07:23:10
小學生作文(中高年級適用)(2018年3期)2018-04-18 01:24:47
中國科技博覽(2016年2期)2016-04-25 20:32:39
小學生導刊(2016年34期)2016-04-11 00:49:44
專用汽車(2016年4期)2016-03-01 04:13:43
少兒科學周刊·少年版(2015年4期)2015-07-07 21:11:17
電測與儀表(2015年5期)2015-04-09 11:3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