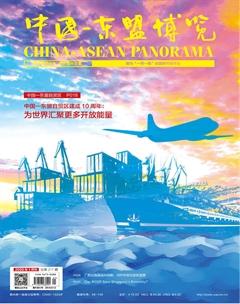中國—東盟的貿易逆順差 我們該怎么看?
黎敏


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里,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的陰云不僅沒有阻隔中國—東盟的經貿合作,反而讓雙方的經貿關系更為升溫。2019年1~11月,東盟超過美國成為了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其中,中國向東盟出口達3230.9億美元,同比增長11.5%;中國從東盟進口達2549.5億美元,同比增長2.8%,中方順差681.4億美元,較2018年同期的425.7億美元增長60.1%。
在為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增長欣喜的同時,細心的人們也注意到了中國對東盟貿易順差的擴大。實際上,關于這種貿易逆順差的討論,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的過程中就從未停止過。
當我們在202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10周年之際,再談中國—東盟的貿易逆順差時,我們該如何來看待;在雙方經貿關系日益緊密的今天,這些數字的背后又意味著什么呢?
中國—東盟自貿區帶來了貿易逆差?
為了更好地明白貿易逆順差是什么,我們可以簡單地把貿易逆差理解為本國進口其他國家的東西,要多過向其他國家出口的東西,買的多、賣的少,就會“入超”;而貿易順差則正好相反,賣的多、買的少,就會“出超”。
近幾年,人們在聚焦中國—東盟自貿區發展時多少會關注到中國對東盟的貿易順差,其間過度解讀,甚至出現了一些“中國—東盟自貿區只有利于中國”“中國建設中國—東盟自貿區是為了貿易順差”的雜音。然而,只要結合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的歷程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來看,便會發現這樣的言論站不住腳。
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之初實施的“早期收獲計劃”,不僅極大地照顧到了東盟新老成員國的舒適度,也將實實在在的關稅紅利惠及了東盟的農戶與企業。
而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中國對東盟的貿易順差是從2012年下半年才開始出現的。在此之前,中國對東盟長期存在大量貿易逆差,逆差額約占雙邊貿易額的15%,個別年份甚至達到20%,致使當時研究中國—東盟貿易逆差對中國經濟發展影響的課題也不在少數。而具體到國別來看,中國對泰國、馬來西亞的貿易逆差依然保持到現在。
這些都意味著,中國對東盟及成員的貿易順差并非由來已久、一成不變的。因為中國與東盟的貿易主要是基于生產的貿易而不是基于消費的貿易,是外部需求派生的貿易而非內部需求拉動的貿易。所以雙方的貿易逆順差更多的是,在雙方資源稟賦、貿易結構、垂直專業化分工、產業轉移等復雜因素的影響下,一種可變化的直觀反映。
盡管表面看上去中國—東盟貿易逆順差轉變的十來年,大抵也是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的十來年,但人們往往容易忽視,這其實亦是國際貿易格局與分工不斷變化的十來年。建設中國—東盟自貿區不是影響這種格局變化的根本原因,其對于貿易逆順差的影響也非常有限。反而,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發展的過程中,它會積極去適應匹配這種變化,探索緩解貿易不平衡的路徑,關切成員對經貿合作的新需求。
當然,我們在思考如何發揮好中國—東盟自貿區的積極作用時,也不會對這種貿易逆順差置若罔聞。
面對順差擴大,不該一葉障目
近幾年,中國對東盟的貿易順差曾一度有縮小的趨勢,但2019年從數據來看,這種貿易順差有所擴大。背后的原因,既有產業結構的長期影響,也有美國揮舞“關稅大棒”的實時影響。
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執行理事長許寧寧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近年來,中國內地、港臺企業,以及西方跨國公司擴大了在東盟的投資,但受東盟有些國家產業配套欠缺所限,因此這些投資企業需要從中國內地進口相應的原料輔料、配套件、機器設備。
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實施的關稅壁壘,也使得原先從東盟進口半成品到中國內地進行最后一道加工再出口到美國的狀況出現了變化,以致中國內地從東盟有些國家進口增速不高或下降。所以,中方的順差擴大,有多方面原因,包括西方跨國公司在中國與東盟貿易中變化的原因。
許寧寧以中國與越南貿易為例。中國與東盟10國貿易中,雖然中國對越南的貿易順差最大,但越南對全球貿易則為順差。正是因為由中國出口到越南的原料輔料、配套件、機器設備增多,在越南加工為成品后出口到其他國家市場。
“這幾年,全球的供應鏈在不斷調整中,不少東盟國家也承接了中國的一些產業轉移。此外,中國對東盟國家出口的增加,有一些也是源于這些國家自身經濟發展的需求。所以我覺得未來的貿易平衡不一定非要追求一種絕對的平衡,因為它實際上還是會根據雙方的資源情況、產業結構等這些條件進行調整的。”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周密在接受東博社采訪時說,“中國不會刻意追求更多的貿易順差,也希望去追求相對的貿易平衡。”
追求貿易平衡還需攜手努力
“中國不刻意追求更多的貿易順差”不僅是專家的觀點,更是中國官方的態度。為了彰顯中國開放市場、擴大進口的誠意,中國采取了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重大舉措。在與東盟商談的升級版中國—東盟自貿區中,雙方也致力于通過削減貿易壁壘、提升貿易便利化、放寬市場準入等方式來進一步激活中國—東盟的經貿合作能量。
據周密介紹,為了推動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落地,中國海關在關稅系統、技術操作上做了相應的調整;商務部則通過宣講推介來積極擴大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影響力,為企業進行相關指導;相關院校也在進一步加強對外經貿人才的培養。
產業結構的調整、專業分工的變化等都是經濟全球化大潮下發生的客觀變化,對于如何在這種變化中盡量緩解貿易的不平衡,周密認為光靠限制是不太可能的,市場的問題最終還是要爭取用市場的方式去解決。
“在貿易層面,我們可以挖掘更多可以滿足對方需求的產品,爭取更為市場化的方式去解決公司之間的對接。當然也可以輔以電商等方式,去強化這種貿易關系。第二,貿易跟投資現在是緊密相連的,通過跨境產業鏈的合作,會帶動一些中間品、原材料的貿易,這對于加強雙方的貿易聯系也是非常有利的。第三,我們應該積極去探討除了美元以外的其他貨幣在雙方貿易和結算中的使用。因為在現有美元主導的貿易體系下,如果東盟國家想從中國購買產品,他們就得通過出口去獲得美元,但是如果使用人民幣等其他貨幣的話,這種需求會變得更容易去解決。”周密說,“這些方法并不是說一定會解決問題,但至少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
·聯系編輯:31346430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