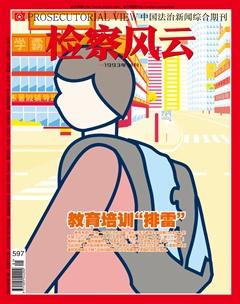海外:校外培訓市場監(jiān)管各不同
劉強
世界各國對于校外培訓機構(gòu)的監(jiān)管,按照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馬克·貝磊(Mark Bray)教授的觀點來看主要有六種:一是完全放開。市場完全可以調(diào)節(jié)校外培訓行為,對校外培訓機構(gòu)完全不加干涉,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二是大力支持。有些國家認為,校外培訓機構(gòu)對學校教育進行了有益補充,因此采取稅收減免、政府補貼、教師培訓等手段大力支持校外培訓機構(gòu)的發(fā)展。三是完全禁止。政府認為校外培訓機構(gòu)嚴重影響了校內(nèi)教育,因此直接完全禁止,歷史上韓國等曾經(jīng)采取過此措施,因為不符合市場實際,均以失敗告終。四是選擇性禁止。五是控制干預。為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和保障培訓行為可控,政府從校外培訓機構(gòu)的準入審批、注冊登記、辦學場地、師資隊伍等各個方面進行直接干預監(jiān)管,采用這種方式的國家較多。六是監(jiān)管而不干預。僅對市場的校外培訓行為進行簡單了解和統(tǒng)計,并不采取任何措施干預培訓行為。
歐盟地區(qū)
歐盟各國對于校外輔導大多抱有不干預態(tài)度,法國甚至出臺政策對校外輔導機構(gòu)進行鼓勵,即對參加校外輔導的家庭給予50%的稅收減免政策。他們認為校外輔導不僅有利于增加就業(yè)、促進消費,而且還具有教育的補充功能以及照看兒童的社會功能。歐盟各國校外輔導的參與率有一定差異,希臘的輔導參與率達到了74.9%,挪威雖然最低,也達到了8.2%。另外,從城鄉(xiāng)之間的差異來看,有些國家如立陶宛差異較大,但是在愛爾蘭,鄉(xiāng)村的學生也可以通過網(wǎng)絡參加輔導。
在歐盟國家中,除了德國對在職教師的兼課行為進行嚴厲禁止外,其他國家如立陶宛、波蘭以及斯洛文尼亞等,其在職教師從事兼課的比率已分別達到了79.4%、35.8%、47.9%。
有些歐盟國家,比如芬蘭,在注重對校外培訓機構(gòu)進行監(jiān)管的同時,注重校內(nèi)教育的升級,為學生興趣愛好方面提供積極支撐,且能夠適應所有學習程度的學生,因此芬蘭的校外培訓機構(gòu)主體地位不突出,學生基本未受培訓機構(gòu)的影響。之所以能夠取得這種成就,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芬蘭十分重視教師隊伍建設(shè),教師素養(yǎng)技能高,能夠很好地照顧到各學習層次的學生,而且能為不同社團提供服務;二是芬蘭注重因材施教,能夠識別學習程度不一的學生并分別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另外,學校設(shè)置專門的培訓干預教師,對學校統(tǒng)一教育的弊端進行彌補。
日本
對于公務員的定位,世界上有一條共同的職業(yè)準則,那就是不得兼職。以德、日為代表的國家,明確把教師的身份定位為公務員。德國的《聯(lián)邦公務員法》規(guī)定:“公務員有責任做好本職工作,將自己的整個人格、能力和全部精力投入到公務員關(guān)系上。”日本的《教育基本法》也規(guī)定:“教師應為全體國民的服務者,自覺行使自己的使命,努力完成自己的職責。”因此,對于公立學校的在職教師而言,要受到國家公務員法的調(diào)整。
在日本,對于校外輔導機構(gòu)的稱呼仍然為“私塾”或“塾”。不同于我國傳統(tǒng)意義上的私塾,日本學生上私塾主要是為了進行補習,以在升小學、初中、高中以及大學考試中取得理想成績。日本的私塾在法律上被明確劃為獨立的服務型產(chǎn)業(yè),根據(jù)《公司法》《法人稅法》以及《特定商交易法》等法律法規(guī)進行調(diào)整,還受到《兒童權(quán)利公約》的約束。另外,還有行業(yè)性組織社團“全國私塾協(xié)會”進行行業(yè)規(guī)范,此社團還制定了行業(yè)的事業(yè)活動基準,并對私塾的經(jīng)營活動進行評價等,還會對私塾的講師進行培訓和能力認證。
講師由私塾進行自主招聘,雖對學歷、資格等無太大硬性要求,但講師依然需要具備全面和深入的學科專業(yè)知識,除此之外還應當有良好的組織和教學能力。另外,全國私塾協(xié)會還設(shè)計了“講師能力評價體系”,即對講師進行個別指導和集團指導的能力認證,既指導了從業(yè)講師的能力開發(fā),也為私塾的研修提供了參考,保證私塾產(chǎn)業(yè)留有優(yōu)秀的講師人才。
日本把公立學校在職教師劃歸公務員體系,并適用公務員法進行調(diào)整,其本職工作之外的兼職是禁止的。他們認為在職教師從事第二職業(yè)是玩忽職守,必須要承擔公務員法和教育法中規(guī)定的后果。

韓國
韓國在職教師享有公務員待遇,不能參加校外兼職,因此稱中小學校外培訓為“私教育”。韓國對于中小學校外輔導行業(yè)的態(tài)度經(jīng)歷了一個從嚴禁到放松又到嚴禁的過程,但正是這種不同的管理經(jīng)歷使得韓國的校外輔導管理體系越來越成熟。
20世紀60~70年代,韓國以教育改革政策來調(diào)整,取消中學入學考試以及高中考試均衡化的政策。取消初中入學考試原本是為了緩解青少年壓力,而取消入學考試增加了中學的人數(shù),把競爭壓力放到了中考階段,為了考入高中精英學校,依然有大多數(shù)的學生參加校外輔導。20世紀80年代,韓國政府對中小學校外輔導行業(yè)實行全面控制的措施,并增加了大學的入學考試次數(shù)來減少考試競爭的激烈程度。20世紀90年代,由于大學入學考試的壓力,禁令開始放松,家長們抱怨課外輔導所帶來的經(jīng)濟負擔,因此韓國教育部又制定措施,緩解課外補習熱,以減少家庭對于此方面的開支。雖然政府政策嚴厲,但是仍然阻擋不了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大趨勢,仍有大量的課外輔導機構(gòu)存在。2000年,韓國最高法院宣布,韓國政府的私教育禁止令違反了憲法和人權(quán),因此規(guī)定除在職教師以外,原則上允許課外輔導和學院教育的存在,此后限制家庭私教育費用成為改革政策的重點。
我們可以看出,韓國政府對于校外輔導的態(tài)度一直采取的是以政策引導的方式進行疏導。根據(jù)社會需要,由政府主辦費用較低的校外輔導機構(gòu),從多方面采取了措施。政府、學校、家庭以及學生的積極參與使得韓國的教育體系越來越成熟。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