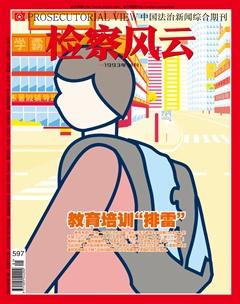保護之名下的強迫無薪休假
林海

“人口出生率下降”是最近的熱點問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敢生孩子,或者說,生了養不起。生育負擔重在西方國家也一樣存在。在美國,至今給孕婦放的也是“無薪休假”,且不保證產后還有職位。在克利夫蘭,這個做法還寫在了州的規定里,成了“強迫休無薪產假”的依據。當然,這一規定后來引發了訴訟,并被裁定因違憲而無效。
懷孕意味著可能離崗一年
卡羅爾·拉弗勒是克利夫蘭一所公立學校初中部的女教師。她懷孕之后,校方要求她在預產期前五個月開始休無薪產假,而且直到孩子出生三個月后,她才能回來工作——而且如果當時是學期的中間,她還要等到下一個學期才能重回勞動崗位。在這個過程中,她拿不到任何工資。對此,拉弗勒十分氣憤,將學校和教育委員會告上了法庭。
事情發生在1971年。拉弗勒向學校報告,她懷孕了,但身體狀況還可以,可以堅持工作。然而,校方根據一項1952年通過的教育委員會規定,要求所有懷孕的教師在預產期前五個月開始無薪休產假。休產假的老師不允許繼續工作,也沒有薪資。校方還通知拉弗勒,孩子出生三個月后,她必須拿到證明其健康的醫生證明,才能返校任教。而且,學校也不保證她能重回原崗位,只是“優先分配”她到適合的職位。
在今天看來,這一決定既蠻橫又不公。但在當時,這是克利夫蘭教育委員會的明確規定。他們提出了許多醫學證據,認為懷孕到第五個月或第六個月的教師,在身體上已經無法勝任長時間站立的教學工作。而且,提前五個月讓她們休產假,是為了尋找和聘用合格的替代人。校方提出,聘請臨時代課老師也是需要花錢的。這筆錢應當從離開崗位、沒有在工作的老師的工資中支付。而且,當她們完成生育后,也不可能立馬讓代課老師走人。另外,為了避免學生們總在學期中間更換老師,教育委員會要求她們在新學期開始后再回來。這也是為了延續學期教育的連續性。
然而,拉弗勒并不這樣認為。她認為,這是學校在敵視生孩子這件事,是在對懷孕的老師決定生育的行為進行懲罰。這不但影響她的收入,還會直接影響“人的基本公民權利”——即生不生孩子、決定何時生孩子的自由。關于學期教育連續性的說法,拉夫勒認為這更是個笑話。因為,她于1970年11月懷孕,要求她離職的時間點是1971年3月——這時正是學期中。如果說重視教育的連續性,那么也應該讓她把這個學期教完,而不是讓懷孕女教師中途離開,去休無薪產假。
盡管對校方的決定十分不滿,拉弗勒有孕在身,也無法與學校抗爭到底。她只能遵守學校的安排,提前五個月離開教職。孩子于1971年7月28日出生。三個月后學期已經開始了,她又要等到1972年的春季才能開始恢復工作。思前想后,拉弗勒發現自己因為一次生育,竟然有接近一年無法獲得薪酬,覺得十分委屈和不甘。同一時期,她的同事納爾遜夫人遇到了更為不公的對待——校方竟然根據“只有連續工作滿一年的教師能享受產假”的規定,要求懷孕的納爾遜夫人辭去教職。這讓她倆氣憤難平,將學校告上了法庭。
女教師的起訴
兩名懷孕老師的訴由是,校方僅從行政管理的便利出發,侵犯了她們基本的憲法權利。無論是持續教學的必要性,或出于對身體狀況不佳女老師的保護,都不能證明克利夫蘭教育委員會強制性休假規定的正當性。另外,這些規定對教師分娩后重返工作的資格進行了限制。無論是體檢要求的限制,還是可能失去職位的威脅,抑或是返回崗位的時間節點,都構成了對女教師就業的不當障礙——在這些舉措的背后,是對生育權這一憲法權利的粗暴干預和無理敵視。
本案一路上訴,經美國聯邦第四巡回上訴法院審判后,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校方在這段時間內重新出臺了有關產假的政策,但并沒有根本性的調整。相反,還規定了有關提前請假的細節:“任何已婚的教師如果懷孕,申請休產假應在兒童正常出生的預期日期之前不少于五個月生效。休假的生效日期:教師至少應提前兩周將此類請假申請發給學校管理部門;校長應當準予其無薪休假,最長不超過兩年……教師如希望返崗,應當在孩子出生三個月后,且在新學期開始前至少六周向校長提交申請。”
和今人的想象不一樣,當時的法官對此規定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例如,菲利普斯大法官就認為,要求在懷孕第五個月初休產假部分符合憲法,因為這能夠保護孕婦更好地待產;但是在分娩后還需等三個月才有資格提起申請重返教學崗位,這個規定是違憲的。之所以認為提前休產假是合憲的,是因為更多的時候孕婦為了多賺些錢,可能會接受雇主的要求,再多干一段時間——這看似自愿的安排,實際上是受困于經濟條件。她們可能不知不覺就損害了自己和胎兒的健康——即使是像教師這樣的文職崗位,也可能會因超時站立而造成傷害。
此外,孕婦的存在會不會影響工作質量呢?校方也就這一點提出了意見。他們認為,妊娠早期的身體不適、后期的并發癥,都可能影響教育質量,甚至可能給同事們造成影響。對此,法庭請到了三位醫學證人。他們分別是代表校方的馬庫斯(Marcus)醫生、納爾遜太太的產科醫生盧騰貝格斯(Rutenbeigs)和上訴人拉弗勒的產科醫生威爾(Weir)博士。三位醫生謹慎地認為,無法就懷孕對教職及同事的影響下定論。他們指出,每個人的每次妊娠情況都各不相同,無法一概而論。但是醫生也提出,今天的時代早就不是將懷孕視為“無勞動能力”或“殘疾”的時代,強制休產假可能不應該是一種常規,而只應該是一種基于醫囑的例外安排。
歧視孕婦本質上是歧視女性
在庭審中,鮑威爾法官提出了一個關鍵觀點:憲法保護生育權,一方面是基于對孕婦及下一代健康的保障,另一方面是基于男女平權的憲法原則。畢竟,男性不會因為懷孕而被迫離開工作崗位。他說,之所以認為“強制性的產假規定損害了生育子女的權利”,是因為這一規定在增加家庭生育成本(丈夫不得不在一年的時間里承擔全家的費用開銷)的同時,還因為這一規定構成了對女性工作人員的排斥和歧視。女教師不得不因為懷孕而離開工作崗位,這是基于繁衍人類、增加新的社會成員的公眾利益所做的努力。這一努力使全社會獲益,而其成本或職業風險,顯然不應該只由女性一方承擔。
鮑威爾法官說,在大多數情況下,懷孕是一種正常的生物學功能。對此進行調整,本身就是充滿爭議的。不過,也不是說,所有增加生育負擔的政策都違反了憲法。有些地方可能會基于鼓勵或限制生育的角度,給予或不給予生育津貼。甚至以收稅的方式,阻止人口過度增長。這都不是一種對生育的“懲罰”,而是地方政府為實現人口與資源之平衡、有權做出的一些調控政策。但是,像本案中這樣針對具體的職業群體(女性教師)設立缺乏充分依據的生育負擔,這樣的規定就可能因為侵犯生育權利、實施了缺乏正當性的“對生育的阻止”,而違反憲法,應予廢除。
法院最終認為,校方過分地強調了教師缺勤、課堂紀律、兒童心理影響這些“行政管理”方面的價值。但是,他們并未能證明,繼續雇傭孕婦教師會真正影響這些方面的價值。此外,由于強制休產假,導致許多有能力繼續教學的孕婦教師在學期中間或接近學期末的時候離崗,這反而會影響教學的連續性——從而也使校方與教育當局的價值訴求看上去不那么站得住腳。“由于上述原因,我們認為,校方與教育當局在目的與手段之間的聯系太弱了,不足以支持其正當性。”法庭裁定克利夫蘭有關法規違憲,以后校方與教育委員會不得強制懷孕教師休假,也不得限制其重返教學的時間。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有前述判決,美國仍然是世界各發達國家中產假最短的。即使是今天,在美國仍然有許多地方給懷孕員工放“無薪產假”。例如,在洛杉磯,孕婦放12周無薪產假。12周內回到崗位,崗位就會被保留。如果員工有年假和事假,或在這12周內正好有圣誕假或新年假,則可以順延(如果是教師還可以用寒暑假)。一些保險公司還推出了短期產假險(并歸類于短期殘疾險,Short term disability),以確保在無薪產假期間為孕婦提供60%的工資補貼。難怪人們說,生育是一場奢侈的戰斗,在世界各地恐怕都是如此。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