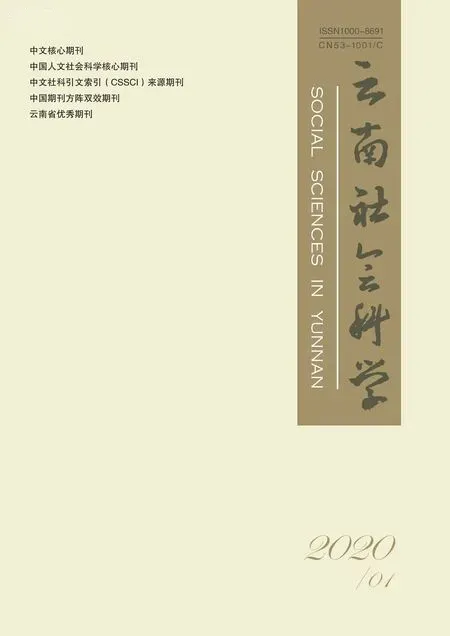祛魅與超越:當(dāng)代青年亞文化的融合發(fā)展
羅紅杰
青年亞文化是中西方文化史中歷久彌新的概念,也是現(xiàn)實生活中不斷更新的文化現(xiàn)象。在戰(zhàn)后英國伯明翰學(xué)派視野中,青年亞文化指“社會階層結(jié)構(gòu)框架中不斷出現(xiàn)的那些帶有一定反常色彩或者挑戰(zhàn)性的新興群或新潮生活方式”①[英]斯圖亞特·霍爾:《通過儀式的抵抗:戰(zhàn)后英國青年亞文化》,孟登迎、胡疆鋒等,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第20頁。。在全媒體時代,青年亞文化是指“青年群體基于共同興趣和價值追求,創(chuàng)造性表達自我的文化實踐”②馬中紅、陳霖:《無法忽視的一種力量:新媒介與青年亞文化研究》,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第1頁。。不同時代、不同視野下的青年亞文化具有不同的涵義和意指。但無可爭議的是青年亞文化是一定社會癥候和精神之域的折射和隱喻,是多元文化中普遍而又特殊的存在。
青年亞文化理論研究歷經(jīng)芝加哥學(xué)派、伯明翰學(xué)派以及后亞文化時代,不同的學(xué)派依據(jù)不同的社會存在,反映不同的社會關(guān)系,站在不同的立場呈現(xiàn)不同的觀點和思想。青年亞文化包羅萬象,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理所當(dāng)然成為不同時代研究的焦點對象。芝加哥學(xué)派最早研究“越軌亞文化”,對青年犯罪、越軌行為的深層邏輯進行深刻剖析,形成了“問題解決”“標(biāo)簽理論”來解釋和界定青年亞文化。伯明翰學(xué)派則是以階級對立的敘事框架將青年亞文化表征為“風(fēng)格化的儀式抵抗”的意義實踐,并認(rèn)為青年亞文化的最終宿命難以逃離“抵抗與收編”的窠臼。后亞文化時代,青年亞文化出現(xiàn)一些不同以往的“場景”和“新部落”,后亞文化理論強烈質(zhì)疑和批判伯明翰學(xué)派階級-結(jié)構(gòu)的研究范式,并試圖用“生活方式”來建構(gòu)“身份認(rèn)同”,賦予后亞文化理論新的闡釋力。新時代,人們正處在一個經(jīng)濟全球化、世界一體化、網(wǎng)絡(luò)信息化的時代,世代賡續(xù)、技術(shù)更迭,青年亞文化呈現(xiàn)出更加復(fù)雜、多樣的文化形態(tài)。無論是經(jīng)典的伯明翰學(xué)派還是后亞文化理論,是否還能完全解釋當(dāng)代的青年亞文化景觀?青年亞文化作為時代變遷和社會癥候的意義實踐,又隱喻著怎樣的青年精神之域,折射出怎樣的社會癥候?新時代,青年亞文化發(fā)生著怎樣的變化?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存在怎樣的關(guān)系,如何處理這種關(guān)系?這些是青年亞文化研究者迫切需要聚焦和闡釋的問題。
一、青年亞文化的理論回顧與樣態(tài)存現(xiàn)
青年亞文化理論發(fā)軔于20世紀(jì)40年代的美國芝加哥學(xué)派,經(jīng)英國伯明翰學(xué)派再到后亞文化時代,歷經(jīng)三個重大的發(fā)展階段。針對不同時期的青年亞文化現(xiàn)象建構(gòu)起不同流派的青年亞文化理論。不同青年亞文化樣態(tài)是青年亞文化理論研究的主要對象,從光頭黨到嬉皮士,從足球迷到追星群;從御宅文化到惡搞文化,從喪文化到佛系文化等一系列青年亞文化景觀。不同的青年亞文化樣態(tài)表征不同的意義實踐,不同的青年亞文化理論具有不同的解釋風(fēng)格和根本立場。
(一)青年亞文化理論的歷史流變
首先,芝加哥學(xué)派:青年亞文化是一種越軌行為。芝加哥學(xué)派是最早開始關(guān)注亞文化現(xiàn)象,并將其理論化的學(xué)派。以羅伯特·帕克、斯莫爾、霍華德·貝克爾等為代表的亞文化研究者開始關(guān)注流浪漢、舞女、吸毒者等特殊群體。他們通過“民族志”“參與考察”等實地研究方法,親身實踐臨摹他們的生活狀態(tài),體悟他們的心理動態(tài),最后形成了“問題解決”“標(biāo)簽理論”等青年亞文化理論。芝加哥學(xué)派注重把青年亞文化現(xiàn)象置于一定社會文化沖突情境中,認(rèn)為越軌行為是為了“解決問題”。“問題解決”是青年拒絕和反抗社會矛盾或困境的文化實踐方案,“貼便簽”則是支配文化對越軌青年進行約束和管控的文化策略。正如貝克爾所說,“越軌者以及越軌行為是強有力的控權(quán)者給少數(shù)弱勢群體貼上的越軌標(biāo)簽,用標(biāo)簽標(biāo)識他們?yōu)榫滞馊恕雹貶oward Becker,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New York and London:the free press,P﹒1﹒。
其次,伯明翰學(xué)派:青年亞文化是一種抵抗儀式。伯明翰學(xué)派是青年亞文化研究影響最大的學(xué)派,以霍加特、霍爾等為主要代表。伯明翰學(xué)派以階級預(yù)設(shè)為前提,將青年亞文化視為戰(zhàn)后工人階級抵抗霸權(quán)的一種方式,并將這種沖突關(guān)系定位在休閑領(lǐng)域,通過拼貼與同構(gòu)形成一種具有獨特風(fēng)格的抵抗儀式,但其最終難逃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商業(yè)的收編。伯明翰學(xué)派對當(dāng)時的泰迪男孩、摩登族、嬉皮士等青年亞文化現(xiàn)象進行了深度的剖析,并形成了“風(fēng)格”“同構(gòu)”“抵抗-收編”等青年亞文化的敘事范式。
最后,后亞文化理論:青年亞文化是一種部落場景。后亞文化時代以班尼特、哈里斯等為代表的學(xué)者認(rèn)為伯明翰學(xué)派的理論已經(jīng)不能完全闡釋新出現(xiàn)的“銳舞”“新部落”“場景”等青年亞文化現(xiàn)象。后亞文化理論更加注重文化實踐的歷時性和混雜性,試圖用“生活方式”“新部族”等建構(gòu)新的青年亞文化敘事框架。后亞文化理論嚴(yán)重質(zhì)疑和批評伯明翰學(xué)派的亞文化理論,他們認(rèn)為青年亞文化是一種具有混雜性風(fēng)格的純娛樂活動,并沒有明顯的階級抵抗風(fēng)格。
(二)當(dāng)代青年亞文化的樣態(tài)存現(xiàn)
新時代,中國正處于經(jīng)濟轉(zhuǎn)型、社會轉(zhuǎn)軌的關(guān)鍵期,加之網(wǎng)絡(luò)信息技術(shù)快速更迭,青年亞文化呈現(xiàn)出多元化樣態(tài)。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粉絲亞文化、惡搞亞文化、御宅文化、佛系文化等。
其一,粉絲亞文化:集體式狂歡。網(wǎng)絡(luò)時代的到來,青年首當(dāng)其沖成為信息技術(shù)的忠實擁躉。網(wǎng)絡(luò)信息技術(shù)的加持改變了傳統(tǒng)追星群體的文化實踐,為青年群體提供了便于情感交流和集體狂歡的時空場域。粉絲亞文化的生成意味著亞文化資本的不斷積累,聚合了“志同道合”趣味群體。粉絲亞文化承載著青年群體的興趣愛好、價值取向以及情感體驗的意義表征,既有如同“烏合之眾”般的狂熱追星,也有勵志向上的奮斗青年。其是資本邏輯和技術(shù)賦權(quán)雙重加持下的必然結(jié)果,蘊含著消費主義下狂熱的物質(zhì)欲望,同時折射出青年群體真實的精神世界和情感渴求。
其二,惡搞亞文化:無厘頭戲謔。不同于伯明翰學(xué)派所關(guān)注的嬉皮士、光頭族,惡搞亞文化采用拼貼、同構(gòu)、挪用、反諷的手段生成風(fēng)格獨特的文化樣態(tài)。惡搞亞文化通過篡改權(quán)威、顛覆經(jīng)典等形式,以無厘頭、夸張式的敘事表達來彰顯青年群體的情感體驗。其既是青年群體張揚個性、批判現(xiàn)實的文化實踐,也可能演化成負(fù)面文化的重要來源。“矮矬窮”“單身狗”等惡搞術(shù)語隱藏著青年群體糾結(jié)焦慮的精神狀態(tài);《大話西游》《一個饅頭引發(fā)的血案》等惡搞電影隱喻著解構(gòu)權(quán)威、抵抗現(xiàn)實的另類表達。惡搞亞文化通過無厘頭和污名化的敘事方式表達對現(xiàn)實境遇的溫柔抵抗,象征性地紓解自我的焦慮。
其三,御宅亞文化:烏托邦想象。御宅文化源自于日本,而后在互聯(lián)網(wǎng)的加持下風(fēng)靡全球。御宅文化總是與商業(yè)產(chǎn)品密切相關(guān),從漫畫、電玩到網(wǎng)絡(luò)游戲、視頻直播等視覺影像構(gòu)建的二次元世界。在封閉的自我世界中,青年群體能夠創(chuàng)設(shè)自由空間,體驗精神快感。御宅族有自身獨特的興趣愛好,且造詣頗深,表面是孤獨的個體,實際擁有龐大的族群。御宅是他們共同的屬性,很少邁出自己創(chuàng)設(shè)烏托邦的世界,卻具有強大的購買能力。“萌文化”“旅行青蛙”就是御宅族典型的文化實踐。御宅文化一方面折射出青年價值虛無、理性祛魅的精神異化之態(tài),另一方面又刺激、促進一定文化和經(jīng)濟的繁榮。
其四,佛系亞文化:有意識無為。佛系亞文化是根據(jù)佛教符號進行話語改寫、意指改造而成,指無欲無求的人生態(tài)度和有意識無為的處世哲學(xué)。并在此基礎(chǔ)上衍生出“佛系青年”“佛系購物”等一系列佛系文化。佛系文化指的是“不爭不搶、凡事都行、認(rèn)命隨緣、無能為力”的心態(tài)特征和形象;其一方面有利于紓解內(nèi)心的精神焦慮和外在的現(xiàn)實壓力,另一方面折射出一定的現(xiàn)實困境和社會癥候,“佛系”成為青年群體無奈的話語表達和真實的情感寫照。青年群體對佛系文化的狂熱和推崇,成為青年亞文化研究不可忽視的文化現(xiàn)象。
二、當(dāng)代青年亞文化隱喻下的精神之域與社會癥候
青年亞文化是青年精神之域的文化映照和社會現(xiàn)實的真實反映。青年亞文化總是以一種具有異化表象和反叛表征的風(fēng)格出現(xiàn),以期區(qū)隔其他的文化實踐,強化自身的內(nèi)部認(rèn)同。新時代存現(xiàn)的青年亞文化景觀隱喻著青年群體的思想觀念和精神世界,也折射出一定的社會癥候和現(xiàn)實寫照。
(一)當(dāng)代青年亞文化隱喻下的精神之域
1.崇尚自我與身份焦慮
新媒體技術(shù)的勃興加持青年群體對視覺圖像的崇拜,使得青年獲得充足釋放個性與情感宣泄的空間和權(quán)力。曬文化、惡搞文化等青年亞文化折射出當(dāng)代青年崇尚自我的精神之域和泛娛樂化的社會心態(tài)。在虛擬的網(wǎng)絡(luò)生活世界中充斥著“曬幸福”“秀恩愛”等行為,這種文化現(xiàn)象逐漸成為青年群體網(wǎng)絡(luò)社交的日常景觀。這種新生的青年亞文化已經(jīng)成為青年群體獲取自我認(rèn)同和情感表達的主要方式。青年群體在自我意識膨脹和崇尚自我的同時也存在著身份焦慮的精神困境,惡搞文化就是青年群體通過無厘頭的敘事方式來紓解身份焦慮的一種文化實踐。“當(dāng)代青年亞文化采用拼貼、戲仿、揶揄、反諷的手段盡情調(diào)侃和諷刺”①馬中紅:《新媒介與青年亞文化轉(zhuǎn)向》,《文藝研究》2010年第12期。,一方面是對傳統(tǒng)權(quán)威和話語霸權(quán)的質(zhì)疑和抵抗,另一方面也是對社會壓力和生活困境的焦慮和無奈。
2.集體狂歡與理性祛魅
集體狂歡是當(dāng)前青年亞文化景觀的鮮明風(fēng)格。惡搞文化、御宅文化等青年亞文化都呈現(xiàn)出青年集體狂歡的精神之域。相比充滿壓力的現(xiàn)實世界,在虛擬化、超現(xiàn)實、匿名化的網(wǎng)絡(luò)空間中青年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他們可以隨意追捧自己喜愛的偶像、扮演任何一個崇拜的網(wǎng)游人物,在彈幕里肆意言說、嬉笑怒罵,在網(wǎng)游中主宰世界、指點江山。青年群體在網(wǎng)絡(luò)空間中逃離了社會的權(quán)威規(guī)制、獲得了情感的宣泄和慰藉,“狂歡讓人們暫時從普遍真理和既定秩序中解放出來;它標(biāo)志著所有等級差別、規(guī)范和禁令的暫時終止”②馬中紅:《新媒介與青年亞文化轉(zhuǎn)向》。。集體狂歡背后同時存在著理性袪魅和價值虛無的精神異化之域。萌文化、網(wǎng)絡(luò)祈愿、佛系文化等青年亞文化折射出青年在審美意識、科學(xué)認(rèn)知、理性思考等層面的價值虛無和理性祛魅。讀圖時代遮蔽了社會生活的真實面相、網(wǎng)絡(luò)祈愿代替了科學(xué)知識的運用邏輯、有意識無為助長了懶惰之風(fēng)、烏托邦想象剝奪了理性思考的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導(dǎo)致青年群體在虛擬性空間和淺表性幻像中疏離社會現(xiàn)實、忽視價值導(dǎo)向、弱化理性思考。
3.戲謔嘲諷與精神抵抗
青年亞文化的意義實踐不是直接彰顯的,而是通過間接的形式表達的。喪文化、惡搞文化等青年亞文化通過文字、圖像、商品等符號經(jīng)過拼貼與同構(gòu)來戲謔嘲諷社會現(xiàn)實和權(quán)威霸權(quán)。“屌絲”“矮矬窮”等青年亞文化景觀就是以一種戲謔性、污名化的敘事方式表達對社會現(xiàn)實的不滿和自我的嘲諷,這種青年亞文化蘊含著去中心化、藐視權(quán)威霸權(quán)的解構(gòu)心態(tài)。當(dāng)然,“更多時候只是用一種象征性的姿態(tài)來展示青年個性的叛逆以及對權(quán)威話語的不屑和嘲弄”①[美]約翰·費斯克:《電視文化》,祁阿紅、張鯤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5年,第349頁。。“抵抗”一直是青年亞文化的風(fēng)格標(biāo)識,當(dāng)代青年亞文化隱喻著青年群體精神抵抗的力量。從“屌絲”到“喪文化”,從污名化到自我矮化無不折射出解構(gòu)權(quán)威和精神抵抗的意味。青年群體試圖通過想象性的解決方案來處理與社會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這種想象性的精神抵抗在一定程度上紓解內(nèi)心的壓力和焦慮,但最終難以逃離被商業(yè)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收編的命運。
(二)當(dāng)代青年亞文化折射出的社會癥候
1.承續(xù)性的階層固化
青年亞文化最能反映社會變化的本質(zhì)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中國發(fā)展新的歷史方位。與此同時,中國也進入改革開放的深水區(qū)和社會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期,在這個時期階層固化現(xiàn)象依然嚴(yán)重,階層流動渠道仍然有待改善。加之在社會急劇變革過程中不確定性因素給予青年巨大的生存壓力,處于社會邊緣的青年群體試圖通過一定的文化實踐來釋放心理壓力、尋求價值認(rèn)同、紓解精神焦慮。惡搞文化、佛系文化等青年亞文化深深根植于一定社會現(xiàn)實的土壤之中,是社會轉(zhuǎn)型和變遷的整體縮影和文化實踐。青年群體通過這樣的文化實踐來逃離巨大的社會壓力,同時也表達出對實現(xiàn)階層躍遷的渴求和對改善現(xiàn)實困境的期待。一定程度的社會結(jié)構(gòu)板結(jié)化和階層流動渠道的不通暢是衍生青年亞文化景觀的重要外在因素,“高富帥”“白富美”成為青年“屌絲逆襲”的美好愿景。
2.技術(shù)性的時空重組
當(dāng)代青年亞文化景觀大多數(shù)是在現(xiàn)代化信息技術(shù)的加持下衍生而成。網(wǎng)絡(luò)正以新的方式重組人們的交往模式,以微博、微信等為代表的社交媒介構(gòu)成了青年娛樂生活的重要場域。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以及信息技術(shù)的賦權(quán)激發(fā)了青年亞文化的意指實踐,信息技術(shù)日新月異,青年亞文化形態(tài)也層出不窮。現(xiàn)代化的信息技術(shù)是孕育和催生青年亞文化的推動力,契合了青年群體文化表達和意義實踐的時空需求。媒介技術(shù)的更新與青年人的反叛具有同構(gòu)性,“新媒介技術(shù)本身天然地包含對權(quán)威的反抗、對集權(quán)的質(zhì)疑、對不確定性的好奇以及對中心的顛覆和瓦解”②馬中紅、陳霖:《無法忽視的一種力量:新媒介與青年亞文化研究》,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第103頁。,彈幕文化、御宅文化等風(fēng)格各異的青年亞文化樣態(tài)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自媒體的技術(shù)賦權(quán)下才得以形成的。熟稔信息技術(shù)邏輯的青年群體在新的時空場域中盡情地展示著自己的獨特個性以及對社會體驗的文化表達。
3.現(xiàn)代性的消費主義
當(dāng)代青年亞文化總是與消費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當(dāng)今社會,青年群體生活在“一個由娛樂、信息和消費組成的新的符號世界。媒體和消費已經(jīng)深刻地影響著青年人的思想和行為”③[美]道格拉斯·凱爾納:《媒體奇觀——當(dāng)代美國社會文化透視》,史安斌譯,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第3頁。。符號的消費成為青年亞文化風(fēng)格形成的必要組成部分。現(xiàn)代性的消費主義為青年提供了一種從惡搞、娛樂、模仿等視角切入社會現(xiàn)實和社會事件的可能,這就契合了青年社會表達和紓解情緒的需求。消費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嚴(yán)肅性的主題,使得娛樂性的自我表達和社會參與隨處可見。粉絲文化、御宅文化、惡搞文化等青年亞文化就是在信息技術(shù)推動和消費主義社會語境中衍生而成的文化新樣態(tài)。粉絲文化中青年通過購買與偶像相關(guān)的商品,強化自己“粉絲”的身份認(rèn)同,他們看中的不是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符號價值;御宅文化中的青年通過購買一系列的裝備模仿鐘愛的虛幻人物試圖尋找自己的存在感;惡搞文化中的青年借助新媒介的技術(shù)賦權(quán),采用娛樂性的消費符號參與到社會事件之中,以“惡搞”的形式表達自身的社會訴求。
三、當(dāng)代青年亞文化的轉(zhuǎn)向與重構(gòu)
回顧青年亞文化理論的發(fā)展歷程,梳理新時代青年亞文化的多元樣態(tài),剖析青年亞文化隱喻的精神之域與社會癥候,可以發(fā)現(xiàn)青年亞文化正發(fā)生著不同程度的變化,也呈現(xiàn)出與以往不盡相同的文化形態(tài)。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經(jīng)典的青年亞文化理論為闡釋當(dāng)代青年亞文化現(xiàn)象提供了思路和借鑒,但是已經(jīng)不能完全解釋新時代呈現(xiàn)的“特殊”亞文化景觀。正如霍爾所說,“伯明翰學(xué)派的亞文化理論可能需要補充和完善,但絕不會在新的時代環(huán)境下完全喪失生命力。”①[英]斯圖亞特·霍爾:《通過儀式的抵抗:戰(zhàn)后英國青年亞文化》,第65頁。
(一)風(fēng)格的改寫:物品-符號到圖像-符號
風(fēng)格是青年亞文化的圖騰和第二皮膚,也是其最醒目的標(biāo)識。伯明翰青年亞文化理論認(rèn)為風(fēng)格由形象、品行和行話三個要素組成②Stuart Hall,eds﹒Culture,Media and Language﹒London:Hutchinson﹒1980﹒P﹒83﹒。形象包括一些服飾、發(fā)型、珠寶飾物等;品行由行為、儀態(tài)等組成;行話則包括言語、詞語等,這就構(gòu)成了青年亞文化風(fēng)格的圖騰。青年亞文化的風(fēng)格包羅萬象,譬如,摩登族的短發(fā)和腳蹬車,光頭族的光頭和街斗靴,以及本土青年亞文化中憤青文化的綠軍裝和五星帽等。物品-符號的青年亞文化風(fēng)格構(gòu)成了他們區(qū)別其他文化形態(tài)的標(biāo)志,也寄托著某種價值觀念和生命體驗的文化表達。新時代信息技術(shù)不斷發(fā)展和現(xiàn)代性的消費主義催生了新的青年亞文化形態(tài),新的青年亞文化風(fēng)格也發(fā)生相應(yīng)的變化。以物品-符號為代表的青年亞文化風(fēng)格逐步轉(zhuǎn)向圖像-符號的風(fēng)格模式。當(dāng)今時代圖像逐漸超越了具有理性思維的文字?jǐn)⑹拢白x圖時代”已然到來。新時代青年亞文化圖像-符號的風(fēng)格圖騰愈加凸顯,青年亞文化對意義實踐的創(chuàng)新也空前活躍。譬如,表情包亞文化的表情加文字,彈幕文化的視覺加文字等,青年亞文化不斷打破傳統(tǒng)物品-符號的模式,將數(shù)字、文字、圖像等雜糅到一起,利用拼貼、挪用、同構(gòu)等方法創(chuàng)制了大量風(fēng)格迥異的青年亞文化景觀。圖像-符號的青年亞文化風(fēng)格對現(xiàn)代新媒介的技術(shù)賦權(quán)有著深度的依賴,加之包容多元的文化氛圍促使青年亞文化蓬勃發(fā)展。
(二)空間的擴展:現(xiàn)實生活到虛擬世界
傳統(tǒng)青年亞文化意義表征和實踐的空間總是在休閑生活的街頭、社區(qū),娛樂活動的部落、場景。“無賴青年”總是奇裝異服地出現(xiàn)在社區(qū)和街頭,“摩登族”總是西裝革履地生活在夜總會和城市中心,“銳舞青年”總是風(fēng)格各異的出現(xiàn)在舞廳場景,他們強調(diào)一種可以確認(rèn)的空間,一種可以被看見和分析的空間③[英]安迪·班尼特、基思·哈恩:《亞文化之后:對于當(dāng)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中國青年政治學(xué)院文化譯介小組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19頁。。信息技術(shù)在遞嬗更迭中總是作用于文化面相的構(gòu)成,同樣,青年亞文化也借助信息技術(shù)不斷擴展自己的發(fā)展空間。新的信息技術(shù)總是激發(fā)青年亞文化的意指實踐,錨定它們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空間,并成為它們反映社會現(xiàn)實以及與主流文化爭奪話語權(quán)的方式和策略。網(wǎng)絡(luò)虛擬空間成為新時代青年亞文化意義實踐的主要空間場域。“我們身處同時性的時代中,處于一個并置的時代,其中由時間發(fā)展出來的世界經(jīng)驗遠少于聯(lián)系著不同點與點之間的混亂網(wǎng)絡(luò)所形成的世界經(jīng)驗。”④包亞明:《后現(xiàn)代性與地理學(xué)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頁。網(wǎng)絡(luò)虛擬空間不僅賦予青年匿名登錄、實時交互、傳遞訊息,而且能夠使其寄寓身份表達和文化實踐。新時代青年亞文化寄生于虛擬空間的同時,也創(chuàng)生和形塑著自身的文化空間。網(wǎng)絡(luò)虛擬空間不僅為青年亞文化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間,也為青年尋找志同道合的“圈內(nèi)人”、尋求身份認(rèn)同構(gòu)筑了一個新的渠道。“網(wǎng)絡(luò)社區(qū)”“貼吧”等成為青年亞文化成員集聚和活動的新空間和“新部落”。
(三)意義的模糊:政治抵抗到混雜認(rèn)同
無論是芝加哥學(xué)派還是伯明翰學(xué)派視野中的青年亞文化都強調(diào)文化實踐的對抗或者抵抗意義。芝加哥學(xué)派認(rèn)為青年亞文化是“對社會秩序具有實際破壞能力的負(fù)文化”,伯明翰學(xué)派則認(rèn)為青年亞文化是“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進行風(fēng)格抵抗的附屬文化”,并始終以階級分析的框架定位青年亞文化的抵抗意義。到了后亞文化時代,青年亞文化則是“無關(guān)政治、遠離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純娛樂文化”,政治抵抗的意義不斷式微,語義的邊界逐漸模糊。新時代青年亞文化政治抵抗意義模糊的同時,混雜認(rèn)同的力量不斷擴大。認(rèn)同問題是青年亞文化實踐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抵抗與認(rèn)同構(gòu)成青年亞文化的內(nèi)在張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jīng)轉(zhuǎn)化,其決定著青年亞文化的政治抵抗意義必然不斷式微,網(wǎng)絡(luò)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加持新媒介的技術(shù)賦權(quán)使得其混雜認(rèn)同的力量不斷擴大。網(wǎng)絡(luò)青年亞文化是新時代青年亞文化的主要形態(tài),網(wǎng)絡(luò)空間文本生產(chǎn)的碎片化、青年群體興趣的跳躍性、文本意義的短暫性,使得青年亞文化身份指向不明、認(rèn)同漂浮不定。粉絲文化中可以分為若干個粉絲群體,青年既可以是一個偶像的粉絲,也可以是若干個偶像的粉絲,同時也可以是御宅文化的主要成員,這不僅證明了青年亞文化身份認(rèn)同的模糊化,也顯示出其不斷與其他青年亞文化進行建構(gòu)和重組的趨勢。
(四)歸途的嬗變:對抗-收編到互動-協(xié)商
青年亞文化對抗-收編的宿命是伯明翰學(xué)派青年亞文化理論的治理邏輯。伯明翰學(xué)派站在戰(zhàn)后工人階級的立場抵抗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秩序,雖然只是符號層面的對抗,但是依然被看成是對神圣秩序的挑戰(zhàn)。對此而言,青年亞文化必然逃離不了被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商業(yè)收編的命運。“收編,是支配文化對體制外的文化進行再次界定和控制的過程”①胡疆鋒:《伯明翰學(xué)派青年亞文化理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2年,第218頁。。伯明翰學(xué)派認(rèn)為,青年亞文化必然被支配文化所收編,一種是意識形態(tài)收編,即支配集團通過重新界定和“貼標(biāo)簽”的方式制造道德恐慌;一種是商業(yè)收編,即把青年亞文化符號轉(zhuǎn)化成商品,直至失去抵抗意義或改弦更張。這種青年亞文化理論不足以解釋新時代的青年亞文化景觀,新時代青年亞文化是青年群體生命體驗和社會表達的一種文化形式,也是反映社會癥候和青年精神之域的觀景窗。當(dāng)今的青年亞文化也發(fā)生了許多變化,政治抵抗意義式微,建構(gòu)功能不斷擴展,并在一定程度可以轉(zhuǎn)化為主流文化。應(yīng)轉(zhuǎn)換對抗-收編的研究范式、轉(zhuǎn)換沖突管理的治理方式、轉(zhuǎn)化社會本位的治療范式,轉(zhuǎn)向互動-協(xié)商的研究范式、轉(zhuǎn)向協(xié)調(diào)管理的治理方式、轉(zhuǎn)向關(guān)系本位的治療范式。青年亞文化既具有溫柔抵抗的意味,也具有批判建構(gòu)的意義。青年亞文化始終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敘事框架內(nèi)反映階層矛盾的社會現(xiàn)實問題,在與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彼此勾連的復(fù)雜關(guān)系中發(fā)揮著批判和建構(gòu)的功能。
四、結(jié) 語
青年亞文化是一種重要而又特殊的文化形態(tài),由青年創(chuàng)設(shè),在青年中傳播,在世代變遷中延續(xù)抵抗意義,又在技術(shù)更迭中模糊認(rèn)同風(fēng)格,它表征著青年群體的身份認(rèn)同、浸潤著青年群體的價值理念,反映著青年群體的社會心態(tài),又映射出一定的社會癥候。它是當(dāng)代文化圖景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理解青年、審思社會的重要途徑。在新時代,應(yīng)以差異的視角和包容的心態(tài)看待、分析和研究青年亞文化。
思維轉(zhuǎn)換:從沖突管理到協(xié)調(diào)治理。沖突管理思維強調(diào)青年亞文化是一種從屬文化,是處于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末端和權(quán)力中心邊緣的文化形態(tài),并具有強烈的抵抗性和沖突性,進而以“管控”為最直接和最必要的手段進行收編與治理。②平章起、魏曉冉:《網(wǎng)絡(luò)青年亞文化的社會沖突、傳播及治理》,《中國青年研究》2018年第11期。沖突管理思維的本質(zhì)是維護支配文化的根本利益。新時代,青年亞文化已經(jīng)發(fā)生了許多變化,特別是新媒介信息技術(shù)的嵌入,青年亞文化的抵抗意義不斷式微,認(rèn)同和建構(gòu)的力量不斷加強。沖突管理的思維方式一定程度上會破壞整體性的文化生態(tài),損害青年亞文化的運行機能。應(yīng)轉(zhuǎn)換思維方式,轉(zhuǎn)變視青年亞文化為“麻煩制造者”的觀念,轉(zhuǎn)向協(xié)調(diào)治理的思維模式。協(xié)調(diào)治理強調(diào)協(xié)商互動、均衡發(fā)展,主張青年亞文化在合理的規(guī)制內(nèi)包容性發(fā)展。對不同的青年亞文化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如分級治理、分類治理、協(xié)商治理等,促使青年亞文化與主流文化和諧共處。
范式變革:從社會本位到關(guān)系本位。社會本位的治療范式是在病癥化、問題性的青年亞文化價值預(yù)設(shè)基礎(chǔ)上,以一種狹隘視野對待青年亞文化的一種引領(lǐng)方式。③閆翠娟:《從社會本位的治療范式到關(guān)系本位的建構(gòu)范式:新時代青年亞文化引領(lǐng)的范式革新》,《新疆社會科學(xué)》2019年第1期。社會本位的治療范式延續(xù)了伯明翰學(xué)派階級對抗的研究范式,強調(diào)社會的主體價值,主張社會利益高于一切,忽視了個體的需求和利益。社會本位的治療范式在文化發(fā)展的一定階段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新時代,特別是網(wǎng)絡(luò)青年亞文化蓬勃發(fā)展的時代已經(jīng)不合時宜了。關(guān)系本位的治療范式是一種調(diào)和、中庸的治理方式,既強調(diào)主流文化的引領(lǐng)作用,又注重邊緣文化的存在價值。應(yīng)轉(zhuǎn)向關(guān)系本位的治療范式,積極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著重發(fā)揮青年亞文化的建構(gòu)功能、凝聚功能和映照功能,探索主流文化與青年亞文化和諧共生之道。
青年亞文化是一種邊緣性、小眾化、短暫性的文化形態(tài),它表達和解決暗藏著或還未解決的父輩文化和社會現(xiàn)實中的矛盾。對待青年亞文化的態(tài)度不能一味抵抗廢弛、抹平封殺,要加以持久的關(guān)注考察、協(xié)商利用,充分發(fā)揮其建構(gòu)、凝聚功能,實現(xiàn)主流文化與青年亞文化和諧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