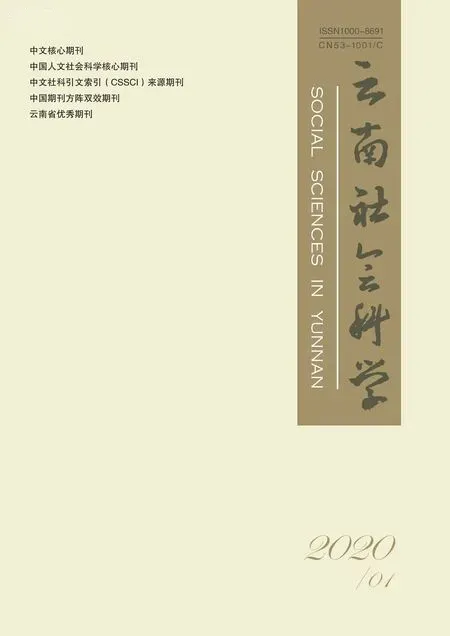國家級承接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示范區(qū)是否推動(dòng)了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
陳 凡 周民良
一、引 言
自2010年中國開始設(shè)立國家級承接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示范區(qū)(以下簡稱“示范區(qū)”)以來,示范區(qū)一直承擔(dān)著推動(dò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和中西部地區(qū)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創(chuàng)造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新動(dòng)能的重任。截至2019年年底,中國先后批復(fù)設(shè)立10個(gè)示范區(qū),范圍涵蓋中西部11個(gè)省區(qū)(直轄市)、38個(gè)市(區(qū))。示范區(qū)在稅收、土地等方面實(shí)行政策優(yōu)惠,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區(qū)域要素配置、優(yōu)化了區(qū)域發(fā)展稟賦狀況,提升了區(qū)域產(chǎn)業(yè)規(guī)模和層次,帶動(dòng)了區(qū)域經(jīng)濟(jì)增長。但示范區(qū)政策究竟是否推動(dòng)了區(qū)域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示范區(qū)內(nèi)不同區(qū)域、不同等級城市之間區(qū)域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效應(yīng)是否一致,還需要通過定量分析才能得出答案。
示范區(qū)實(shí)施的年限不長,目前圍繞示范區(qū)的相關(guān)研究還存在幾點(diǎn)不足:第一,學(xué)者們的研究較多的是聚焦于某一個(gè)示范區(qū)(如皖江城市帶承接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示范區(qū)),缺乏對全國10個(gè)示范區(qū)的整體研究。①高云、王云:《承接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對區(qū)域新型工業(yè)化的影響研究——以皖江城市帶為例》,《經(jīng)濟(jì)論壇》2014年第4期。第二,現(xiàn)有研究中關(guān)注示范區(qū)的經(jīng)濟(jì)增長、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金融發(fā)展、土地利用、政府政策等方面話題,鮮有探討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的作用。第三,已有的文獻(xiàn)多數(shù)以定性化的理論分析為主,缺乏定量化的精準(zhǔn)討論②楊國才:《區(qū)際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的學(xué)術(shù)論爭、實(shí)踐流變與趨勢預(yù)判》﹒《江西社會(huì)科學(xué)》2014年第6期。。有鑒于此,本文擬從全國層面利用定量化手段檢驗(yàn)示范區(qū)的承接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升級效應(yīng),并甄別示范區(qū)對不同區(qū)域、不同等級城市的差別效應(yīng)。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shè)
(一)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的作用
建設(shè)示范區(qū)的目的是在不斷優(yōu)化“存量產(chǎn)業(yè)”、大力發(fā)展“增量產(chǎn)業(yè)”的過程中來帶動(dòng)區(qū)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即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是指產(chǎn)業(yè)由低級向高級狀態(tài)順序演進(jìn)。①袁航、朱承亮:《西部大開發(fā)推動(dò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了嗎》,《中國軟科學(xué)》2018 年第6期。具體來說:第一,按照梯度理論和反梯度理論,低梯度區(qū)域通過引進(jìn)和承接優(yōu)勢企業(yè),形成產(chǎn)業(yè)聚合,推動(dòng)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低梯度地區(qū)可以改善技術(shù)區(qū)位條件,以技術(shù)突破、新興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的方式引導(dǎo)區(qū)域技術(shù)水平提高和創(chuàng)新發(fā)展來帶動(dòng)產(chǎn)業(yè)的高級化。示范區(qū)在承接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過程中,通過重新配置發(fā)展因子、帶動(dòng)新興產(chǎn)業(yè)發(fā)展、推動(dòng)科技創(chuàng)新,能夠顯著推動(dòng)本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向高級化方向邁進(jìn)。第二,現(xiàn)實(shí)經(jīng)濟(jì)中,示范區(qū)產(chǎn)業(yè)升級效應(yīng)顯著。一項(xiàng)好的政策能夠引導(dǎo)產(chǎn)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發(fā)展。示范區(qū)作為一種國家戰(zhàn)略,既能夠體現(xiàn)國家層面的戰(zhàn)略和資源的傾斜,又能夠發(fā)揮區(qū)域比較優(yōu)勢。示范區(qū)政策能夠改善區(qū)域技術(shù)發(fā)展的軟件條件,從而讓示范區(qū)更有條件去吸引高技術(shù)、緊缺型人才聚集,吸引高新技術(shù)公司或產(chǎn)業(yè)安家落戶,從而加快信息、知識的外溢,帶動(dòng)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和主動(dòng)性。同時(shí),當(dāng)區(qū)域持續(xù)改善管理、金融、科技等方面的服務(wù),就有助于示范區(qū)對高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的造血功能的形成,企業(yè)和產(chǎn)業(yè)在發(fā)展中“干中學(xué)”,形成良好的氛圍,從而推動(dòng)區(qū)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發(fā)展。
另一方面,示范區(qū)也存在阻礙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的因素。從理論層面看,“區(qū)域粘性”不可避免。在經(jīng)濟(jì)不景氣或者特殊時(shí)期,原有產(chǎn)業(yè)轉(zhuǎn)出區(qū)域收緊對產(chǎn)業(yè)轉(zhuǎn)出的要求,留住原本那些有轉(zhuǎn)出需求而對示范區(qū)發(fā)展有益的企業(yè),使得示范區(qū)吸收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資源來源被限制,其產(chǎn)業(yè)高級化受到限制。同時(shí),示范區(qū)要推動(dò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發(fā)展,需要發(fā)揮人才和創(chuàng)新的作用。目前示范區(qū)吸引高質(zhì)量的人力資源的各種條件不成熟,對于高質(zhì)量人才的吸引力不強(qiáng),面對日趨激烈的人才競爭,示范區(qū)難以獲得充足的優(yōu)質(zhì)人才資源;即便吸引來了人才資源,相關(guān)軟件和硬件不齊全也限制了人才效用的發(fā)揮。示范區(qū)力圖通過引入創(chuàng)新企業(yè)來帶動(dòng)區(qū)域發(fā)展,而在現(xiàn)有條件下,創(chuàng)新資源有限,示范區(qū)在市場上原本就難以獲得最為優(yōu)勢的創(chuàng)新資源,吸引尖端創(chuàng)新企業(yè)聚集。能夠吸引的創(chuàng)新型企業(yè)大多是東部地區(qū)不那么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企業(yè),在這樣的情況下,吸引來的企業(yè)與示范區(qū)本地企業(yè)的技術(shù)差距不是特別大,對于示范區(qū)產(chǎn)業(yè)的整體改造和帶動(dòng)能力整體有限,加之,有的示范區(qū)存在政策缺失、盲目招商引資、腐敗等問題,也限制了示范區(qū)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發(fā)展。
由此可見,示范區(qū)對區(qū)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存在著拉動(dòng)和抑制兩個(gè)方向的效應(yīng),根據(jù)現(xiàn)實(shí)觀察和已有研究成果②劉瑞明、趙仁杰:《國家高新區(qū)推動(dòng)了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嗎——基于雙重差分方法的驗(yàn)證》,《管理世界》2015年第8期。,示范區(qū)主要設(shè)置在中西部地區(qū),推動(dòng)區(qū)域創(chuàng)新要素聚集的程度不是那么高,創(chuàng)新效應(yīng)難以顯現(xiàn);加之人才和創(chuàng)新資源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中西部地區(qū)難以在人才、技術(shù)上取得優(yōu)勢地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趨勢就會(huì)打折扣,也就是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的抑制效應(yīng)會(huì)比較大,甚至超過拉動(dòng)效應(yīng)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1:示范區(qū)不會(huì)顯著提升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水平,甚至有可能抑制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
(二)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的作用
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是指產(chǎn)業(yè)間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和資源得到有效利用③李虹、鄒慶:《環(huán)境規(guī)制、資源稟賦與城市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型城市與非資源型城市的對比分析》,《經(jīng)濟(jì)研究》2018年第11期。。從理論的視角來看,韋伯的區(qū)位理論認(rèn)為,區(qū)域之間不同因子的地位變化時(shí),區(qū)域可以通過重新配置因子,從而帶動(dòng)區(qū)域優(yōu)勢產(chǎn)業(yè)發(fā)展。邊際產(chǎn)業(yè)擴(kuò)張論和產(chǎn)業(yè)生命周期論認(rèn)為,各區(qū)域可以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優(yōu)化發(fā)展格局。示范區(qū)利用自身優(yōu)勢,改善區(qū)域發(fā)展的要素配置、資源稟賦狀況,吸引本地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產(chǎn)業(yè),豐富本地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類型,推動(dò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從現(xiàn)實(shí)來說,示范區(qū)發(fā)展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因素抑制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根據(jù)粘性理論和發(fā)展陷阱論,示范區(qū)在發(fā)展過程中受到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粘性的影響,使得引入產(chǎn)業(yè)質(zhì)量下降,不利于優(yōu)化配置,難以與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協(xié)同發(fā)展;過度招商,全民招商,容易饑不擇食,盲目引入產(chǎn)業(yè),形成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趨同,阻礙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示范區(qū)盡管是一項(xiàng)國家政策,但國家支持力度不大,前期規(guī)劃設(shè)計(jì)中對于產(chǎn)業(yè)的互補(bǔ)性和協(xié)同性考慮較少,未能夠有效強(qiáng)化產(chǎn)業(yè)之間的專業(yè)化分工,使得產(chǎn)業(yè)之間協(xié)調(diào)力度不強(qiáng),未能夠有效帶動(dò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
盡管示范區(qū)對區(qū)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存在著拉動(dòng)和抑制兩個(gè)方向的效應(yīng),然而相關(guān)的研究表明,①袁航、朱承亮:《國家高新區(qū)推動(dòng)了中國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嗎》,《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jì)》2018年第8期。示范區(qū)政策實(shí)施后,優(yōu)化了資源配置,有效豐富了區(qū)域產(chǎn)業(yè)的層次和水平,使得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的拉動(dòng)效應(yīng)大于抑制效應(yīng)。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結(jié)合產(chǎn)業(yè)發(fā)展實(shí)踐,提出以下假設(shè):
假設(shè)2:示范區(qū)會(huì)顯著帶動(dò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發(fā)展。
三、模型選取與變量甄別
(一)模型選取
近年來,雙重差分法成為經(jīng)濟(jì)學(xué)、管理學(xué)研究中一種重要方法,國內(nèi)外學(xué)者紛紛使用雙重差分法評價(jià)政策效果。②劉瑞明、趙仁杰:《西部大開發(fā):增長驅(qū)動(dòng)還是政策陷阱——基于PSM_DID方法的研究》,《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jì)》2015年第6期。相較于傳統(tǒng)的政策評估手段,其模型設(shè)置簡單,政策識別效果更加精準(zhǔn)。本文主題是評價(jià)示范區(qū)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效應(yīng),屬于政策效應(yīng)研究范圍,故利用雙重差分法來識別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的效應(yīng)。示范區(qū)作為一種探索性政策,為雙重差分法的應(yīng)用提供了天然的“準(zhǔn)自然實(shí)驗(yàn)”。截至2019年年底,中國295個(gè)城市中有38個(gè)城市受到政策的沖擊,自然形成了處理組,另外257個(gè)城市沒有收到政策沖擊,因而形成對照組。設(shè)置示范區(qū)政策trans變量,變量屬于示范區(qū)則trans=1,否則令trans=0,這樣trans變量就能夠識別示范區(qū)政策沖擊的凈效應(yīng)。選用雙向固定效應(yīng)模型檢驗(yàn)示范區(qū)政策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的凈影響,模型設(shè)置如下:

(1)式中i代表地區(qū),t代表時(shí)間,Upgrading-indit是被解釋變量,transit為示范區(qū)政策,Β1正負(fù)值反映示范區(qū)政策對區(qū)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是推動(dòng)還是抑制,大小反映示范區(qū)對于地區(qū)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影響的程度。
(二)變量甄別及數(shù)據(jù)描述
1.被解釋變量
本文主要衡量示范區(qū)政策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的影響。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目前有很多測算方式,早期較多利用第二產(chǎn)業(yè)比重、第三產(chǎn)業(yè)比重、高新技術(shù)比重等單一指標(biāo)衡量,然而使用這些指標(biāo)可能會(huì)造成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泡沫化,即數(shù)據(jù)失真。為了度量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的趨勢,一般利用克拉克定理衡量非農(nóng)化產(chǎn)業(yè)比例,即第二產(chǎn)業(yè)與第三產(chǎn)業(yè)占比之和的變化,其適用于經(jīng)濟(jì)增長的早期和工業(yè)化前期階段,隨著經(jīng)濟(jì)服務(wù)化趨勢增強(qiáng),其難以捕捉服務(wù)化趨勢變化。作為改進(jìn),有學(xué)者使用第三產(chǎn)業(yè)與第二產(chǎn)業(yè)產(chǎn)值之比度量。誠然這一比值度量了服務(wù)化趨勢,卻忽略了非農(nóng)化發(fā)展趨勢。從中國產(chǎn)業(yè)發(fā)展格局來看,中國仍然存在著非農(nóng)化和服務(wù)化雙重發(fā)展的格局,衡量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仍然要體現(xiàn)這種趨勢變化。為此,本文使用的測算公式為“第三產(chǎn)業(yè)產(chǎn)值/(第一產(chǎn)業(yè)產(chǎn)值+第二產(chǎn)業(yè)產(chǎn)值)”。原因在于:相比單純服務(wù)化的指標(biāo)和非農(nóng)化指標(biāo),這種測算方式既兼顧了非農(nóng)化趨勢,也度量了服務(wù)化發(fā)展趨勢,有一定邊際意義。
對于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的測度,學(xué)界未形成統(tǒng)一的意見。本文遵照一些學(xué)者的做法,利用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偏離度度量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③干春暉等:《中國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變遷對經(jīng)濟(jì)增長和波動(dòng)的影響》,《經(jīng)濟(jì)研究》2011年第5期。其公式如下:

這里n=3。考慮到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絕對數(shù)的符號是正號,為了保證后續(xù)分析中回歸符號的統(tǒng)一性和分析的便利性,將公式(2)中加入負(fù)號處理。結(jié)合韓永輝等的分析成果,④韓永輝等:《產(chǎn)業(yè)政策推動(dòng)地方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了嗎——基于發(fā)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論解釋與實(shí)證檢驗(yàn)》,《經(jīng)濟(jì)研究》2017年第8期。穩(wěn)健性分析中采用添加權(quán)重的偏離度替代,其利用公式(2)前面乘以產(chǎn)業(yè)份額得到。
2.解釋變量
本文核心解釋變量是示范區(qū)政策,使用虛擬變量trans,樣本城市受到示范區(qū)政策沖擊的當(dāng)年及以后年度trans=1,否則trans=0,得到每個(gè)城市賦值。
考慮到其他因素對區(qū)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的影響,本文引入控制變量,計(jì)算方式見陳凡、周民良文章。①陳凡、周民良:《國家級承接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示范區(qū)是否加劇了地區(qū)環(huán)境污染》,《山西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9年第10期。

表1 主要變量及測算方式
本文采用2000-2016年全國295個(gè)城市面板數(shù)據(jù)研究國家級承接產(chǎn)業(yè)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的影響。對部分缺失值進(jìn)行插值法處理,采用千分之一縮尾消除極端值。具體看,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指標(biāo)最大值與最小值差別較大,表明指標(biāo)之間分布較廣泛;均值大于中位數(shù),體現(xiàn)整體分布偏右。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指標(biāo)最大值接近于0,說明部分地區(qū)部分年份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偏離小,接近于完全無偏離狀態(tài)。最大值與最小值相差較大,體現(xiàn)了變量分布廣泛;均值小于中位數(shù),說明數(shù)據(jù)整體分布偏左一些。其他變量數(shù)值見表1。
四、實(shí)證檢驗(yàn)與結(jié)果分析
(一)基準(zhǔn)回歸模型檢驗(yàn)
模型(1)和模型(3)分別代表不添加控制變量和添加控制變量情況下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影響回歸結(jié)果。其系數(shù)分別為-8.0223、-5.4586,方向?yàn)樨?fù)且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示范區(qū)未能夠有效聚集創(chuàng)新資源、人才、尖端技術(shù),對區(qū)域管理、發(fā)展環(huán)境的優(yōu)化有限,使得其未能夠帶動(dò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甚至由于區(qū)域發(fā)展粘性、各種體制機(jī)制限制,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產(chǎn)生了抑制作用,從而驗(yàn)證了假設(shè)1。

表2 基準(zhǔn)回歸結(jié)果
模型(2)和模型(4)回歸系數(shù)分別為13.4507、11.9219,方向?yàn)檎揖?%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示范區(qū)作為國家戰(zhàn)略,通過國家層面制定詳細(xì)的發(fā)展目標(biāo)并指明發(fā)展方向,加之配套的各種政策的激勵(lì)作用,改善了要素配置結(jié)構(gòu),有效地優(yōu)化了資源配置,強(qiáng)化了產(chǎn)業(yè)和要素耦合度,從而有效促進(jìn)了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這就驗(yàn)證了假設(shè)2。
控制變量表明:human、sav對Sup-ind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正;fdi、far及l(fā)npgdp對Sup-ind抑制作用顯著;human、gov和lnpgdp顯著提升了Rat-ind水平。
(二)穩(wěn)健性檢驗(yàn)
雙重差分法的使用前提是隨機(jī)性和共同趨勢檢驗(yàn)。本文選取一階差分作為被解釋變量,是否是國家級承接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示范區(qū)變量(treated)作為解釋變量,并選取控制變量,利用2009年數(shù)據(jù)進(jìn)行OLS回歸,回歸系數(shù)不顯著,說明樣本是符合共同趨勢假設(shè)的。采用logit模型以treated作為被解釋變量,選取Sup-ind、Rat-ind為被解釋變量,加入控制變量參與回歸,Sup-ind、Rat-ind系數(shù)都不顯著,說明示范區(qū)政策在選取上是隨機(jī)的。
替換代理變量檢驗(yàn),考慮到原有解釋變量的代理變量可能存在選擇偏向性,因而使用服務(wù)化趨勢指標(biāo)和添加權(quán)重偏離指標(biāo)分別作為替代變量參與回歸,結(jié)論與基準(zhǔn)回歸一致。
匹配檢驗(yàn),針對處理組少、對照組多的現(xiàn)實(shí),采取傾向匹配得分法對處理組和控制組進(jìn)行匹配,然后再利用基準(zhǔn)模型回歸,結(jié)果驗(yàn)證了基準(zhǔn)回歸結(jié)論。
安慰劑檢驗(yàn),為了檢驗(yàn)政策本身存在的一些未識別變量的影響,使用安慰劑檢驗(yàn)。考慮到示范區(qū)批復(fù)設(shè)立前,各地通常推出一些預(yù)備政策,所以將示范區(qū)政策獲批時(shí)間分別向前推移2年、3年,回歸顯示其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均沒有顯著影響,表明政策出臺前處理組和對照組不存在系統(tǒng)性偏差①因篇幅所限,穩(wěn)健性具體回歸結(jié)果備索。。
(三)異質(zhì)性檢驗(yàn)
1. 區(qū)域異質(zhì)性檢驗(yàn)
根據(jù)區(qū)位理論的基本原理,不同地區(qū)發(fā)展區(qū)位因子配置上的不同會(huì)使得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天然形成差別。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qū)的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的影響是否有差異,需要進(jìn)一步檢驗(yàn)區(qū)域異質(zhì)性。按照中國國家統(tǒng)計(jì)局2011年6月公布的區(qū)域劃分標(biāo)準(zhǔn),中國批復(fù)設(shè)立的10個(gè)示范區(qū)均分布在中西部地區(qū)。根據(jù)區(qū)域“是否是中部地區(qū)”,設(shè)置虛擬變量middle;“是否是西部地區(qū)”,設(shè)置虛擬變量west。利用虛擬變量middle、west與trans的交互項(xiàng)來識別不同區(qū)域的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的影響,結(jié)果見表3。

表3 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升級績效區(qū)域差異檢驗(yàn)
模型(1)和(3)中Β1系數(shù)-9.3573、-7.3018且在1%水平下顯著,表明中部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的影響顯著為負(fù);模型(5)和(7)中Β1的系數(shù)不是顯著為負(fù),表明西部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的影響不顯著。從系數(shù)看,西部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的抑制程度要小于中部地區(qū)。可能的原因是,中部地區(qū)和西部地區(qū)發(fā)展基礎(chǔ)不同,地緣不同以及考核壓力不同。第一,從發(fā)展基礎(chǔ)看,中部發(fā)展基礎(chǔ)上相對較好,由于存在體制機(jī)制限制和區(qū)域粘性,通過示范區(qū)政策引入產(chǎn)業(yè)不一定能夠改善區(qū)域技術(shù)水平,帶入新的管理經(jīng)驗(yàn)和人才資源,從而不利于中部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發(fā)揮實(shí)際效用。西部地區(qū)產(chǎn)業(yè)發(fā)展相對滯后,引入的一些產(chǎn)業(yè)與原有產(chǎn)業(yè)沖突不太大,一定程度上還能夠吸引一些創(chuàng)新、人才等資源,因而未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產(chǎn)生顯著抑制作用。第二,從地緣上看,中部示范區(qū)地緣上接近東部,目前集中引入產(chǎn)業(yè)并未帶動(dòng)技術(shù)革新、創(chuàng)新聚集,所以產(chǎn)生顯著抑制作用。西部地區(qū)地緣上遠(yuǎn)于東部,對西部產(chǎn)業(yè)的影響存在著一個(gè)循序漸進(jìn)的過程,因而對西部示范區(qū)影響不那么顯著。第三,從地方官員考核看,中部地區(qū)政府對示范區(qū)GDP考核壓力更大,為了示范區(qū)發(fā)展,更多考慮示范區(qū)體量擴(kuò)展,忽視示范區(qū)質(zhì)量提升,因而實(shí)行全民招商、處處招商,容易忽視創(chuàng)新產(chǎn)業(yè)、技術(shù)改造,使得示范區(qū)反而抑制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相比之下,西部示范區(qū)還未到達(dá)中部地區(qū)那樣的發(fā)展壓力,從而未顯現(xiàn)出顯著的抑制效應(yīng)。
模型(2)和(4)中Β1系數(shù)9.1541、9.0911且在10%水平下顯著,表明中部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的影響顯著為正;(6)和(8)中Β1系數(shù)17.2089、14.4640且在1%水平下顯著,表明西部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的影響顯著為正;且西部示范區(qū)的正向作用要更大。可能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區(qū)發(fā)展資源相對貧乏,引入新的產(chǎn)業(yè)和要素猶如雪中送炭,從而起到更大帶動(dòng)作用。
以上結(jié)果意味著,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的影響存在一定門檻上限,西部示范區(qū)處于成長階段,因而顯現(xiàn)出對高級化的負(fù)向影響小、對合理化的推動(dòng)作用更強(qiáng);中部地區(qū)處于門檻前端,面臨著各種直接的矛盾和沖突,因而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的效應(yīng)不如西部示范區(qū)。
2. 城市等級異質(zhì)性檢驗(yàn)
根據(jù)梯度理論,不同地區(qū)面臨不同的發(fā)展梯度階段。由于各種體制機(jī)制以及歷史的原因,中國的城市在行政等級上存在著差別,行政級別高的城市具有更好的發(fā)展稟賦,故設(shè)立虛擬變量bingfu代表有稟賦城市,其賦值為1; wubingfu代表無稟賦城市,賦值為1,其他賦值0。采用bingfu和wubingfu與trans交乘項(xiàng),衡量不同等級城市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升級的效應(yīng),結(jié)果見表4。

表4 不同等級城市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的凈效應(yīng)差異檢驗(yàn)
模型(1)和(3)、(5)和(7)分別為不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后,有稟賦示范區(qū)和無稟賦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影響的回歸結(jié)果。結(jié)果顯示,無稟賦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呈現(xiàn)出顯著的抑制作用,有稟賦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的抑制作用并不顯著,從系數(shù)來看,有稟賦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的抑制程度要小于無稟賦示范區(qū)。
模型(2)和(4)、(6)和(8)分別為不加入控制變量和加入控制變量后,有稟賦示范區(qū)和無稟賦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影響的回歸結(jié)果。結(jié)果顯示,有稟賦和無稟賦示范區(qū)均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有顯著的促進(jìn)作用,有稟賦示范區(qū)的促進(jìn)作用更大。
上述結(jié)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行政等級城市獲取資源的能力不同。有稟賦的城市相比沒有稟賦城市具有更強(qiáng)的政治資源,能夠獲得更多的政策和資源,從而一方面有助于引入好的發(fā)展技術(shù)、創(chuàng)新資源,另一方面有資源去完善服務(wù)體系,建立良好的制度體系,消除不良影響。相較之下,無稟賦示范區(qū)由于各種資源有限,其效應(yīng)未優(yōu)于有稟賦優(yōu)勢示范區(qū)。這意味著,示范區(qū)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的效應(yīng)因稟賦不同而不同。對于無稟賦示范區(qū),優(yōu)化資源和稟賦支持十分必要。
五、結(jié)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的研究表明:第一,示范區(qū)一方面帶動(dòng)了所在地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合理化,但另一方面顯著抑制了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因此,示范區(qū)并未有效推動(dò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這一結(jié)論在嚴(yán)格的穩(wěn)健性檢驗(yàn)之下依然成立。第二,由于不同地區(qū)發(fā)展基礎(chǔ)、地緣因素、考核壓力等不同,相較于西部示范區(qū),中部示范區(qū)更大程度地抑制了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更少帶動(dò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合理化;第三,由于不同等級的城市獲取資源的能力不同,相較于無稟賦優(yōu)勢示范區(qū),有稟賦優(yōu)勢示范區(qū)更小程度抑制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因而更大程度帶動(dò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高級化發(fā)展。
鑒于總體而言,示范區(qū)并未顯著推動(dòng)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且對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的影響表現(xiàn)出復(fù)雜性,使得其通過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帶動(dòng)高質(zhì)量發(fā)展面臨不確定性。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加大力度培育示范區(qū)創(chuàng)新能力,帶動(dòng)示范區(qū)創(chuàng)新產(chǎn)業(yè)聚集發(fā)展。為此要做到以下幾點(diǎn):一是加大力度引入創(chuàng)新企業(yè)、創(chuàng)新產(chǎn)業(yè)。從發(fā)展的角度認(rèn)識創(chuàng)新的重要意義,將創(chuàng)新產(chǎn)業(yè)作為示范區(qū)的重要考核指標(biāo)來抓。二是兼容并蓄,通過自身投入和開放交流,提升本地技術(shù)水平。要加大技術(shù)投入力度,在中西部形成技術(shù)、品牌為核心的創(chuàng)新產(chǎn)品、創(chuàng)新市場;同時(shí)通過強(qiáng)化國內(nèi)外創(chuàng)新合作,建立包容、開放的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在干中學(xué),在分享開放的氛圍中優(yōu)化自身發(fā)展。
其次,重視人才,大力發(fā)揮人力資源的關(guān)鍵作用。人才在示范區(qū)發(fā)展中的作用十分重要,要利用各種手段將人才引進(jìn)來,擴(kuò)大人才存量。地方政府要利用激勵(lì)政策,鼓勵(lì)和支持示范區(qū)引進(jìn)新的人才;要從留住人才入手,讓人才能夠安心、放心地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形成人才安、創(chuàng)新強(qiáng)的格局。同時(shí),要加大教育投入,培養(yǎng)本土化的人才,特別是通曉本地實(shí)際、掌握發(fā)展前沿的人才,強(qiáng)化本地人才的帶動(dòng)作用。
再次,通過因地制宜、分類指導(dǎo),帶動(dòng)示范區(qū)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更加良性發(fā)展。對于中部示范區(qū),一是要更加明確產(chǎn)業(yè)轉(zhuǎn)型方向和目標(biāo),產(chǎn)業(yè)引入要嚴(yán)格按照轉(zhuǎn)型方向發(fā)展,避免出現(xiàn)饑不擇食、盲目引入。二是要改進(jìn)考核機(jī)制,將創(chuàng)新發(fā)展納入考核當(dāng)中。不以GDP和示范區(qū)規(guī)模作為唯一指標(biāo),而要以示范區(qū)產(chǎn)業(yè)發(fā)展質(zhì)量作為主要考核指標(biāo),從而優(yōu)化示范區(qū)產(chǎn)業(yè)發(fā)展質(zhì)量。對于西部示范區(qū),要強(qiáng)化政策支持,將示范區(qū)做大和優(yōu)化,推動(dòng)示范區(qū)向更高的門檻邁進(jìn)。
最后,要給予更多的資源和稟賦支持。示范區(qū)的發(fā)展更多還是有賴于優(yōu)化整體稟賦。一方面應(yīng)給予政策支持,改善硬件稟賦條件;另一方面應(yīng)改善軟件稟賦條件。要在示范區(qū)打造有助于創(chuàng)新的氛圍,優(yōu)化管理手段、管理制度;構(gòu)建有助于創(chuàng)新的服務(wù)體系,形成良好的發(fā)展格局;從體制機(jī)制上,做到服務(wù)一條龍、人性化,真正服務(wù)于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