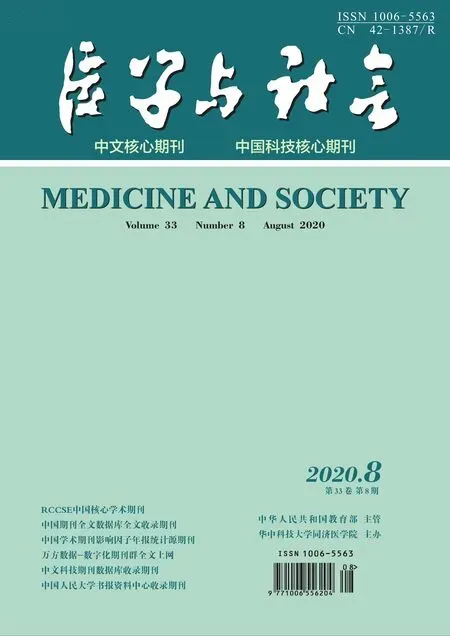“高鐵急救”事件的法律解析
霍 婷 王 岳
1中國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院,北京,100088;2北京大學(xué)醫(yī)學(xué)人文學(xué)院,北京,100191
2019年3月,一則題為《女醫(yī)生高鐵上救人,結(jié)果卻被索要醫(yī)師證》的文章在社會上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1]。一時間,“刀不見血,卻能誅心”、“甩鍋多米諾”等評論紛至沓來。事實上,自當(dāng)年“執(zhí)業(yè)醫(yī)生火車急救產(chǎn)婦,南京法院判非法行醫(yī)”假新聞曝光以來,醫(yī)生路遇急患是否應(yīng)當(dāng)伸出援手就成為了社會關(guān)注的熱點話題[2]。后一事件雖因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北京大學(xué)第三醫(yī)院的澄清而告一段落,但其中所暗含的醫(yī)務(wù)人員院外緊急救治是否屬于非法行醫(yī)、見義勇為是否需要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等問題卻始終未在醫(yī)務(wù)人員中形成統(tǒng)一認(rèn)識,以至于仍有部分醫(yī)務(wù)人員拒絕施救以規(guī)避民事賠償和行政處罰風(fēng)險。此外,若跳出保護醫(yī)務(wù)人員的視角,“高鐵急救”事件則指向了另一關(guān)鍵問題,即當(dāng)前我國公眾急救水平仍需提升。在人流量較大的運輸交通工具上,病人突發(fā)疾病的情況頻繁發(fā)生,此時最有可能提高其生存幾率的方式就是讓現(xiàn)場第一目擊人及時施救。不幸的是,若囿于急救技能的欠缺,目擊者只能寄希望于偶遇好醫(yī)生或等待救護車到來,患者的康復(fù)或存活的幾率將因此大大降低。有鑒于此,我們不禁要問:在沒有醫(yī)務(wù)人員在場的情況下,承運人應(yīng)當(dāng)履行何種救助義務(wù)?社會公眾的自救互救能力又該如何提升?
對上述問題的解答有賴于基本社會共識的形成,而法律就是形成此種共識的基石。本文所要做的就是掃清醫(yī)務(wù)人員對院外緊急救治的認(rèn)知障礙,厘清承運人的救助義務(wù)內(nèi)容。同時,本文強烈呼吁普及急救知識,推廣心肺復(fù)蘇(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自動體外除顫儀(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AED)的操作培訓(xùn)以期提升公眾的自救互救能力,防止悲劇發(fā)生。
1 醫(yī)務(wù)人員的院外緊急救治
1.1 醫(yī)務(wù)人員院外緊急救治不構(gòu)成非法行醫(yī)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zhí)業(yè)醫(yī)師法》(以下簡稱《執(zhí)業(yè)醫(yī)師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雖均未對“非法行醫(yī)”概念給出明確的界定,但實踐中對該情形進行判定并不困難——既然《執(zhí)業(yè)醫(yī)師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明確規(guī)定醫(yī)師應(yīng)當(dāng)取得醫(yī)師執(zhí)業(yè)證書并按照注冊的執(zhí)業(yè)地點、執(zhí)業(yè)類別、執(zhí)業(yè)范圍執(zhí)業(yè),那么任何逾越上述界限的行為都可能構(gòu)成非法行醫(yī)。換言之,非法行醫(yī)有且只有兩種典型情形即非醫(yī)師執(zhí)業(yè)與醫(yī)師超越法定執(zhí)業(yè)注冊事項執(zhí)業(yè)。結(jié)合“高鐵急救”事件之具體情形,涉案醫(yī)生顯然不符合情形一,因此,若想認(rèn)定非法行醫(yī)屬實,則必須證明該涉案醫(yī)生超越了法定執(zhí)業(yè)注冊事項執(zhí)業(yè)。相應(yīng)地,若想為該名涉案醫(yī)生辯護,也應(yīng)當(dāng)從實施執(zhí)業(yè)行為和超越法定執(zhí)業(yè)注冊事項兩大構(gòu)成要件入手。一方面,筆者認(rèn)為,院外緊急救治和執(zhí)業(yè)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醫(yī)生乘客在緊急情況下實施的救治行為不滿足要件一。國家禁止非法行醫(yī)在于確保醫(yī)師對醫(yī)療行業(yè)的獨占地位。因此,非法行醫(yī)語境下的醫(yī)療行為首先應(yīng)該是一種‘職業(yè)行為’,要求從事醫(yī)療的人具有‘反復(fù)繼續(xù)’實施的意思[3]。由此可知,具有反復(fù)實施的意思、以實施某行為為職業(yè)是判定要件一是否滿足的關(guān)鍵。舉例來說,在醫(yī)療機構(gòu)中坐診、隨急救車出診甚至隨采血車出車采血等行為都可因?qū)儆谌粘9ぷ鞯囊徊糠智裔t(yī)務(wù)人員具有反復(fù)實施的意圖而被歸類為職業(yè)活動。相反,偶然發(fā)生的路遇急患情境不具備可控性與可復(fù)制性,施救與否全憑醫(yī)師道德觀念支配,乘客醫(yī)生更不會把無償?shù)氖┚犬?dāng)作職業(yè)行為來對待,因而從根本上排除了認(rèn)定為非法行醫(yī)的可能。
事實上,即使上文對執(zhí)業(yè)行為的解釋遭受其他學(xué)術(shù)觀點的反駁,我們也可借助要件二達成論證目的。雖然“高鐵急救”事件的當(dāng)事醫(yī)生在采訪中曾提到“那不是我的執(zhí)業(yè)地點,那個病也不是我的執(zhí)業(yè)范圍”,但實際上在高鐵上對突發(fā)危險的乘客進行急救不足以對該醫(yī)生造成任何不利影響。因為就執(zhí)業(yè)范圍而言,原衛(wèi)生部、中醫(yī)藥局早在2001年就下發(fā)了《關(guān)于醫(yī)師執(zhí)業(yè)注冊中執(zhí)業(yè)范圍的暫行規(guī)定》的通知,并于其中明確提出:“醫(yī)師注冊后有下列情況之一的,不屬于超范圍執(zhí)業(yè):(一)對病人實施緊急醫(yī)療救護的……”。換言之,緊急情況下的院外救治屬于醫(yī)師超范圍執(zhí)業(yè)的法定例外情形。至于超地點執(zhí)業(yè),也同樣具有類似規(guī)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曾于同年8月公布《關(guān)于非法行醫(yī)罪犯罪主體條件征詢意見函》這一司法解釋性質(zhì)文件,其中所附的原衛(wèi)生部《關(guān)于對非法行醫(yī)罪犯罪條件征詢意見函的復(fù)函》就對超地點執(zhí)業(yè)問題進行了細致解釋:“具有醫(yī)生執(zhí)業(yè)資格的人在‘未被批準(zhǔn)行醫(yī)的場所’行醫(yī)屬非法行醫(yī)……但是,下列情況不屬于非法行醫(yī):(一)隨急救車出診或隨采血車出車采血的;(二)對病人實施現(xiàn)場急救的……”出于現(xiàn)場急救需要而超范圍執(zhí)業(yè)的行為屬于值得鼓勵的善意之舉,其顯然不會侵害醫(yī)師對醫(yī)療行業(yè)的壟斷地位,更不會對社會的公共管理秩序造成沖擊,因而不納入非法行醫(yī)的保護目的范圍[4]。綜上,在“高鐵急救”事件中,構(gòu)成非法行醫(yī)的兩大要件均不成就,醫(yī)務(wù)人員的院外緊急救治行為不會面臨行政處罰風(fēng)險。
1.2 醫(yī)務(wù)人員院外緊急救治應(yīng)受“好人條款”庇護
既然行政法律本身并未設(shè)定障礙,那么導(dǎo)致部分醫(yī)師拒絕院外施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某網(wǎng)站曾于2017年2月16日針對“你會在院外救治突發(fā)疾病者嗎?”這個話題開展網(wǎng)絡(luò)調(diào)查[5]。其中,眾多不愿意主動參與救治的醫(yī)師都反復(fù)提到一個理由——一旦搶救失敗則容易引火燒身,將自己陷入醫(yī)療糾紛的不利境地。院外緊急救治行為的性質(zhì)是什么?類似情況出現(xiàn)后該如何適用法律?這是化解醫(yī)師上述擔(dān)憂、克服當(dāng)前社會道德冷漠的重中之重,更是我們在具體研究中必須準(zhǔn)確回答的兩大問題。
對于前一個問題,如上文所述,醫(yī)師路遇急患緊急施治的行為并不屬于“職業(yè)行為”,醫(yī)、患間具有訂立醫(yī)療服務(wù)合同的合意更是無從談起。若將其中的生活事實識別為法律事實,我們會發(fā)現(xiàn),醫(yī)師在非工作時間、非工作地點自愿無償實施的緊急救治行為實則已符合民法上無因管理制度的各項構(gòu)成要件:①主觀上具有為本人管理的意思;②客觀上實施管理本人事務(wù)之行為且不違反本人明知或可推知的意思;③管理行為無法定或約定義務(wù)要求[6]。換言之,醫(yī)師的院外緊急施治行為應(yīng)歸屬于民法上的事實行為,進而構(gòu)成了醫(yī)、患間無因管理之債的發(fā)生原因[7]。對此,司法實踐中的有關(guān)判例也持相同觀點,如在(2016)京02民終5576號民事裁定書中,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就認(rèn)可了醫(yī)務(wù)工作者何芬在l102次列車上實施救助患病旅客的行為構(gòu)成無因管理,同時釋明該無因管理之債的受益人乃被受助旅客而非豐臺車輛段。
對于第二個問題,鑒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九十三條未對緊急情況下無因管理人的賠償問題作明確規(guī)定,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以下簡稱《民法總則》)出臺之前,基于適當(dāng)管理之義務(wù),理論界通常認(rèn)為無因管理人因任何過失行為致使被管理人受到損害的,均負有債務(wù)不履行下的賠償責(zé)任[8]。雖有部分學(xué)者提出反對意見,主張當(dāng)管理人為避免本人生命、身體或者財產(chǎn)上的急迫危險而管理事務(wù)時,僅對惡意或者重大過失行為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9],但鑒于成文法層面缺乏緊急情況下減輕救助者注意義務(wù)的特殊設(shè)計,因而實踐中的處理非常混亂,緊急救助風(fēng)險較高,一定程度上束縛了緊急情況下救助者的行善之心。事實上,即使是在奉行“禁止多管閑事”規(guī)則的英美法系國家[10],制定《好撒瑪利亞人法》(Good Samaritan Law)以實現(xiàn)對緊急狀態(tài)下救助者的特殊保護也是通行做法。如美國保護采取“合適的措施”的救助者,“通常會免除在緊急事故現(xiàn)場 (而非在醫(yī)院里) 提供救助的醫(yī)師的所有責(zé)任, 或者免除重大過失之外的責(zé)任”[11]。吸取域外的有益經(jīng)驗并基于當(dāng)前我國社會的緊急救助水平,《民法總則》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條明確規(guī)定救助人在自愿實施緊急救助時無須承擔(dān)任何民事責(zé)任,以求消除顧慮、塑造互幫互助的良好社會風(fēng)氣。醫(yī)師院外自愿施救的行為滿足援引“好人條款”的各項要件,自然會被納入該條款的庇護范圍。這意味著即使醫(yī)師在緊急救助中過失地造成了病患損害,亦無需承擔(dān)任何民事責(zé)任。綜上,《民法總則》及《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條之規(guī)定足以構(gòu)成醫(yī)務(wù)人員院外急救的“免責(zé)金牌”,相關(guān)民事法律風(fēng)險同樣得以排除。
2 承運人的緊急救治
2.1 注意義務(wù)內(nèi)容探究
對公共交通運輸工具上突發(fā)疾病的乘客進行施救,不能僅依靠“好醫(yī)生”,明確承運人的救助義務(wù)內(nèi)容、規(guī)范其救助措施同樣值得關(guān)注。雙方當(dāng)事人一旦因此產(chǎn)生糾紛,往往容易在“履行何種程度的救助義務(wù)才算是合乎情理?”問題上爭執(zhí)不下:原告方傾向于設(shè)定一個較高的救治標(biāo)準(zhǔn),而被告方則通常以已經(jīng)盡力救治為由否認(rèn)存在過錯。有鑒于此,在合同法、侵權(quán)法的視域下厘清承運人的救治注意義務(wù)內(nèi)容并指導(dǎo)承運人采取適當(dāng)救治措施已成為了我們必須面對的現(xiàn)實難題。分析相關(guān)司法裁判案件后,筆者認(rèn)為,在討論承運人的救助義務(wù)內(nèi)容前,我們首先應(yīng)明確以下兩點:
第一,從事公共交通運輸業(yè)的公司應(yīng)當(dāng)配備基本的醫(yī)療急救設(shè)備,同時對工作人員進行必要的急救培訓(xùn)。《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條明確規(guī)定“承運人在運輸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盡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險的旅客”,該條款要求承運人應(yīng)當(dāng)具備基本的急救條件。《旅客列車急救藥箱管理辦法》(暫行)和《大型飛機公共航空運輸承運人運行合格審定規(guī)則》對上述急救條件進行了更為細化的規(guī)定,如前者要求從事公共運輸?shù)穆每土熊?包括混合列車)設(shè)置“旅客意外傷害救急藥箱”,每趟旅客列車上要有兩名以上經(jīng)過紅十字會救護員培訓(xùn)合格的乘務(wù)員(即紅十字救護員)。因此,在未滿足上述要求致使患者無法得到及時的救護和簡易治療時,法院可直接認(rèn)定被告救助義務(wù)的履行存在瑕疵。
第二,承運人雖具有救治義務(wù),但無需達到專業(yè)醫(yī)務(wù)人員的救治水平。客運公司并非專業(yè)醫(yī)療機構(gòu),運輸合同附隨的救助義務(wù)更不能與醫(yī)療機構(gòu)的救治義務(wù)相提并論。《合同法》第三百零一條使用的“盡力”表述以及《大型飛機公共航空運輸承運人運行合格審定規(guī)則》第 121.745 條規(guī)定的“但并不要求合格證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提供專業(yè)的應(yīng)急醫(yī)療服務(wù)”均表明了承運人的救治義務(wù)標(biāo)準(zhǔn)相較于醫(yī)務(wù)人員是更低的。對于這一點,各地法院已基本達成共識,如在(2018)京04民終192號民事判決書中,二審法院法官就明確指出“承運人履行救助義務(wù)以‘盡力’為限,承運人只需在自己的能力和條件范圍內(nèi)盡最大努力來救助旅客即可,對承運人履行該項義務(wù)的標(biāo)準(zhǔn)不宜以結(jié)果為導(dǎo)向,不應(yīng)強制要求救助行為必須達到特定結(jié)果”。由此可見,在旅客運輸合同糾紛中,原告以被告未達到專業(yè)醫(yī)務(wù)人員的救治標(biāo)準(zhǔn)為由主張損害賠償?shù)恼埱蟛粦?yīng)得到支持。
基于現(xiàn)有規(guī)定并結(jié)合以上兩點結(jié)論,承運人應(yīng)當(dāng)履行的救助義務(wù)內(nèi)容可被確定如下:發(fā)現(xiàn)乘客突發(fā)疾病后,工作人員應(yīng)當(dāng)立即電話通知患者家屬相關(guān)情況并廣播尋醫(yī)。若乘客中恰好有醫(yī)務(wù)人員,則應(yīng)指派急救培訓(xùn)合格的工作人員積極配合醫(yī)務(wù)人員實施搶救;若現(xiàn)場乘客中沒有醫(yī)務(wù)人員,則由上述工作人員獨立使用藥箱藥品或運用創(chuàng)傷急救、心肺復(fù)蘇等急救技能先行施救。同時,其他工作人員應(yīng)及時向沿線站點的醫(yī)療機構(gòu)求助,就近將病患交與專業(yè)醫(yī)務(wù)人員[12]。
2.2 查驗救助者身份的做法非為正當(dāng)
“高鐵急救”事件的焦點問題即客運公司要求救助者出示醫(yī)師證并出具情況說明的做法是否妥當(dāng)。事實上,此要求不僅不合理,甚至面臨違法的風(fēng)險。理由在于《合同法》、《旅客列車急救藥箱管理辦法》(暫行)等規(guī)范及客運公司與乘客所簽訂的客運合同均未賦予客運公司查驗救助者身份的權(quán)利或義務(wù)。南寧鐵路局的做法于法無據(jù),乘客有權(quán)拒絕配合。此外,一味糾結(jié)救助者是否具有醫(yī)師證的行為也不具有現(xiàn)實意義。因為在現(xiàn)場急救活動中,真正重要的是救治者是否掌握相關(guān)醫(yī)學(xué)知識,而非是否取得執(zhí)業(yè)資格證書。一名醫(yī)學(xué)院學(xué)生甚至一名接受過各類基礎(chǔ)急救培訓(xùn)的普通公民都可能在現(xiàn)場急救中發(fā)揮關(guān)鍵作用。在實踐中,肯定普通乘客參與救助的司法裁判并不少見。如在(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32914號民事判決書中,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法官就認(rèn)為“有乘客自稱有醫(yī)學(xué)知識,并愿意給予幫助,這名乘客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的精神和行為值得褒揚”。由此可見,普通乘客也可成為醫(yī)療救助的主體,客運公司查驗救助者身份的意義即被消解。
上述結(jié)論引申出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普通乘客在救治過程出現(xiàn)了重大偏差,誰應(yīng)當(dāng)為此失誤買單?乘客可基于《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四條免責(zé),客運公司卻不行。此時患者若主張客運公司因用人不慎而未盡“盡力”救助義務(wù),客運公司又將如何自保?解答此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充分理解并運用民法上的合理信賴制度。具體來說,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信賴社會,“幾乎沒有一種關(guān)系是完全建立在對他人的確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象理性證據(jù)或親自觀察一樣,或更為強有力,幾乎一切關(guān)系將不能持久”[13]。為保證交往活動的順利開展,當(dāng)一方當(dāng)事人的某種意思表示及權(quán)利外觀足以引發(fā)善意相對人的合理信賴時,這種信賴便可以得到法律的保護[14]。就普通乘客參與救助問題而言,其真實有效的意思表示(掌握醫(yī)學(xué)知識并愿意救助)足以引起承運人的合理信賴。在該規(guī)則的庇護下,客運公司無過錯,所以即使后期發(fā)生了不利后果,也不得歸責(zé)于客運公司。
除上文所舉案例外,實踐中乘客病患與承運人因緊急救治而對簿公堂的情形更是五花八門。在此背景下,本文所能做的,僅是于理論層面厘清承運人緊急救助義務(wù)相關(guān)問題的法律爭議,至于如何在“高鐵急救”類案件裁判中統(tǒng)一法律適用標(biāo)準(zhǔn)、保證司法統(tǒng)一,仍有賴于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司法解釋及其他有針對性的司法文件,通過解釋相關(guān)法律條文、規(guī)范同類案件的法律適用以回應(yīng)社會關(guān)切、發(fā)揮法律規(guī)范定紛止?fàn)幹πА崿F(xiàn)法與社會的良性互動。
3 社會公眾的緊急救治
急救社會化是急救醫(yī)學(xué)發(fā)展的趨勢[15]。路遇行人突發(fā)疾病,社會公眾應(yīng)當(dāng)成為救助的主力軍。以心臟驟停事件為例,據(jù)國家心血管中心統(tǒng)計,我國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高達54萬,大城市心臟驟停的搶救成功率卻不到3%。深究背后原因,其實是公眾急救出了問題。在4分鐘的黃金搶救時限內(nèi),每1秒鐘都應(yīng)得到充分利用。但在實際搶救活動中,鑒于路程較遠以及交通擁堵,即使是最好的救援醫(yī)療服務(wù)(EMS),往往也無法及時到達救助現(xiàn)場,急患的搶救成功率大大降低。依筆者之見,于公共場所配備急救設(shè)備并通過培訓(xùn)使現(xiàn)場第一目擊者掌握急救技能應(yīng)該成為當(dāng)下提升社會公眾自救互救能力的最佳選擇。為實現(xiàn)此目標(biāo),我們至少需要在以下三方面作出努力。
3.1 教育公眾樹立救助弱者的同理心
鼓勵公眾成為院外緊急救助的主力軍不應(yīng)僅從免責(zé)和獎勵方面出發(fā),更應(yīng)該從根本上改變公眾的救助動機,教育公眾樹立起救助弱者的同理心。當(dāng)前中國社會之所以呈現(xiàn)出冷漠狀態(tài),原因之一就在于國民缺乏換位思考的能力——人處于強勢時,往往不會考慮弱者的困境,并且根本不相信自己也會淪為弱者。但事實上,任何人都可能淪為弱勢群體,如果今天我們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那么終有一天自己也會遭遇同樣孤立無援的境地。換言之,幫助他人就是幫助我們自己。在當(dāng)前社會環(huán)境下,轉(zhuǎn)變公眾的救助動機可謂是任重道遠,但也只有堅定地往這個方向邁進,一個熱忱的社會才有望建成。
3.2 清除AED推廣的制度障礙
我國AED的配置嚴(yán)重不足[16]。即使是在北京,相較于實際需求,現(xiàn)有AED的配置量也是杯水車薪。曾有記者探訪北京地鐵、體育館等25個人流量密集的場所,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僅9個場所配備了AED,地鐵站作為心源性猝死的高發(fā)地區(qū),卻未配有此設(shè)備[17]。事實上,中央或地方政府層面并不乏普及推廣AED的舉措,但收效甚微。早在2016年9月,國家藥監(jiān)局就表示要將AED從第三類醫(yī)療器械分開,單獨予以分類。2017年1月發(fā)布的《體外除顫產(chǎn)品注冊技術(shù)審查指導(dǎo)原則》中卻又明確規(guī)定“體外除顫產(chǎn)品的管理類別為Ⅲ類”,限制了普通公眾使用AED實施急救的可能。原北京市衛(wèi)計委于2018年1月發(fā)布的《北京市公共場所醫(yī)療急救設(shè)施設(shè)備及藥品配置指導(dǎo)目錄(試行)》更是嚴(yán)格遵照國家藥監(jiān)局的分類標(biāo)準(zhǔn),直接將AED界定為僅醫(yī)療專業(yè)人員方可使用的專業(yè)性急救設(shè)施設(shè)備。由此可見,制度障礙是我們接下來必須跨越的一關(guān),也只有在這一障礙被清除后,制定符合本土情況的AED推廣計劃、加大財政資金支持以及鼓勵生產(chǎn)企業(yè)科研創(chuàng)新以降低AED制造成本等后續(xù)工作才能有序開展。
3.3 切實普及急救技能培訓(xùn)
國內(nèi)公眾急救目前遭遇的尷尬境地是:一邊是猝死事件頻發(fā),一邊是大量急救設(shè)備與藥品閑置。“想救卻不會救”、“想用卻不會用”成為阻礙目擊者積極行動的主要因素。以全球公認(rèn)的“救命第一要術(shù)”CPR為例,標(biāo)準(zhǔn)的CPR操作看似簡單,實則步驟要求非常嚴(yán)格。且不論公眾,甚至連專業(yè)的醫(yī)務(wù)工作者也必須在反復(fù)練習(xí)后才能真正掌握按壓姿勢、力度等要點。反觀國內(nèi)現(xiàn)狀,CPR培訓(xùn)活動較少,社區(qū)居民的積極性和掌握度參差不齊,CPR培訓(xùn)的廣度及深度均有待提高。至于AED,雖被歸類為需要嚴(yán)格管控的第三類醫(yī)療器械,但使用方法非常簡便、安全。使用者無需人工識別室顫,只要根據(jù)語音提示實施相應(yīng)救援即可。相關(guān)研究結(jié)果也顯示,在應(yīng)用AED日益普及的歐美國家,如接受4小時學(xué)習(xí)演練,一般非醫(yī)務(wù)人員及市民都能完全掌握[18]。因此,筆者呼吁國家加強對急救技能普及工作的重視,進一步擴大急救知識和技能的普及范圍,將培訓(xùn)對象從學(xué)生擴大到普通社會公眾,逐漸提升我國公眾的自救能力。
4 結(jié)論
“高鐵急救”事件啟示我們:面對急患,醫(yī)務(wù)人員應(yīng)走出所謂的法律風(fēng)險誤區(qū)而勇于救死扶傷;承運人應(yīng)配備基本的醫(yī)療急救設(shè)備并對工作人員進行必要的急救培訓(xùn)以滿足《民法典》所要求的“盡力救助”標(biāo)準(zhǔn);至于社會公眾,則應(yīng)樹立救助弱者的同理心,積極參與急救技能培訓(xùn)以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此外,還應(yīng)適時制定司法解釋、充分發(fā)揮其在爭議類案件中的良好引導(dǎo)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