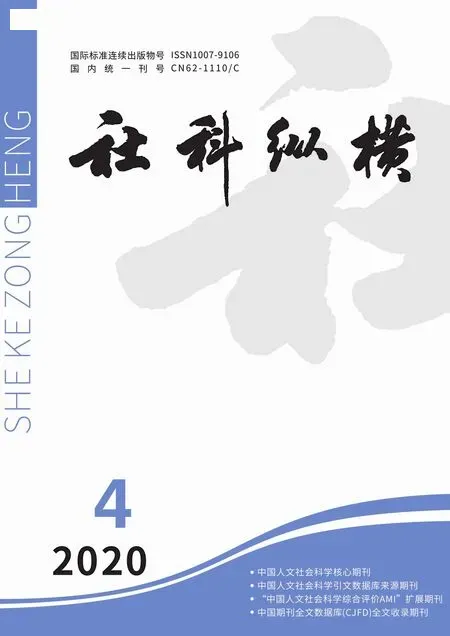立象以盡意
——《懷念狼》中“狼”的文化內涵
白玉紅
(鄭州師范學院 河南 鄭州 450044)
賈平凹2000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懷念狼》是一部意象詭異、意蘊豐厚的作品。整部作品圍繞“狼”而展開:從開始的“狼患”,到“我”跟隨舅舅為狼拍照建檔,再到結尾“我”呼喚狼,狼不僅在這部長篇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是進入到文本的深層、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作品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實質必由之路。
一
在作品《懷念狼》之中,狼代表了原始的野性力量。匪患與狼災把一個縣城毀滅了,在那次大亂中,死了數千人,也就是從那時起,人與狼就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獵人們也由此開始崛起。狼與人搏斗了很多年,獵人們激情四射、雄姿英發,在和狼的搏斗之中成為了英雄,而狼在與獵人的斗爭中僅留下來了少部分的精英。終于,狼漸漸敗下陣來,商州就只剩下15 只狼了。當地政府便開始頒布嚴禁捕狼的規定,甚至讓昔日的獵人傅山擔任起護狼隊的隊長。15 只狼成為瀕危動物接受著保護,獵人們也被收了獵槍。狼患問題雖然解決了,但是人是在和狼的搏斗之中才成為人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沒有了狼的獵人們開始得了一種怪病:他們手無縛雞之力,整天手腳麻木、精神萎靡不振,視力也越來越差。獵人們只有在和獵物的抗衡之中,才能煥發出生命的勃勃生機,如果沒了對立力量,那就只能如大熊貓那樣生命力微弱,連繁殖后代都成了問題。奇怪的是,沒有了獵人的狼也開始得病,甚至有的抱著木樁在河里自殺。高子明作為記者,找到了自己覺得有價值的工作——在舅舅傅山和爛頭的陪同下,為狼拍照建檔。在這個過程中,狼并沒有躲著舅舅,有時候甚至主動出現,逼舅舅殺了它們,而舅舅和爛頭也在無奈殺它們的時候恢復了獵人的健壯和敏捷。從舅舅在保護狼與殺狼掙扎中的瘦骨嶙峋到殺狼后的滿面紅光、手腳剛健的對比,更表現出了獵人的異化。
獵人與狼的體內都有著原始的野性,他們似乎并不甘于平淡地活著,他們好像與新的時代格格不入,滅亡便成了他們唯一的出路。狼最終被殺完了,那與狼密切聯系的雄耳川地區的人們最后都成了人狼。狼在這里不再是簡簡單單的動物了,而是導致現代人的生命力萎縮與人種退化之根源,是小說中現代文明的禁地,是留在懷念中的勃發的生命。
二
狼是維護生態平衡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現代文明中人們所丟失的一部分,狼的消失是商州生態失衡的表現。《懷念狼》中,狼消失了,人類也失去了和它對抗的力量,人類的體內卻逐漸異化出來了狼性。他們殘忍、冷血、野蠻、沒有人性,有的人甚至將自家孩子推到別人的汽車下來騙賠償,絲毫不顧及孩子的生命安全。以至于舅舅認為馬路上跑著的車都是由狼變化的,而車禍就肯定是狼變成了車在吃人。離開了狼的獵人也變得無事可做,漸漸地身體也開始虛弱、萎縮,有的死時萎縮得只有四五歲孩子那么大。與狼有著密切淵源的雄耳川人異化成了人狼,這種奇異的現象無疑是作者為了表現狼的重要性而特意設定的。而之前一直被狼吃的黃羊反倒是變得猖狂了,沒有了狼和黃羊的相互制衡,黃羊開始稱王稱霸,它們喜愛互相打斗,數量也越來越少。黃羊也禍害莊稼,農戶們現在反而希望有狼來把它們吃掉。狼的消失,使商州變了副樣子,好像一切變得凌亂而不正常了。政策又頒布禁止捕狼的條例,可是所有的這些似乎變得不可遏止。此時的狼對政府的保護似乎并不領情,他們老是主動出現在獵人傅山面前,出來挑釁他,最后結果是被完全殺死。人是貪婪的,從開始的大肆捕狼到后來意識到問題后而保護狼,人都是在滿足自己的需求。身為護狼隊長和曾經是捕狼隊長的傅山此時的處境則更為尷尬,他只有無盡地獵殺狼才能在自己的故鄉雄耳川立威。人和狼共存的表象之下有著巨大的悲哀——相互理解、共榮共存的道路上存在著鴻溝。
作品耐人尋味地刻畫了紅巖寺的老道長這個人物形象,他深諳狼性、懂得狼語,為受傷的狼治病,收養小狼崽,而狼病好后銜來金香玉報答他。道長到了彌留之際,還在想著以后狼再來還能去找誰,而道長逝世時,好多狼跑來悼念,有的狼又銜來金香玉作為給老道長的感激,這些描寫說明了狼和人都是自然的一份子,是可以和諧相處的。整體觀之,現代人是不可能在“無狼”的狀態下生存,懷念狼是對自然平衡的懷念,是對破壞生態的控訴,也是對尋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呼喚。
同時,狼還從側面表現出作者對城市生活的厭倦以及對生活在這里的意義的思考。《懷念狼》是賈平凹在受市場經濟影響下創作的一部作品,他以高子明作為一個視角,通過高子明對城市生活的厭倦、無奈、困頓,來表現自己對城市生活的厭惡。作者描繪了城市的生活景象——“西京城里依舊在繁華著,沒有春夏秋冬,沒有二十四節氣,連晝夜也難以分清,各色各樣的人永遠擁擠在大街小巷,你吸著我呼出的氣,我吸著你呼出的氣,會還是沒有頭緒地開,氣也是不打一處來。”突出表現了現代都市里人們精神萎靡、死氣沉沉的生活景象。“而我的生命也從此在西京墜落下去,如一片落葉于冬季的泥地上,眼見著腐爛得只留下一圈再撿也撿不起來的脈網了。”文中多次描寫高子明“沒有胡子”以及高子明因為沒有胡子多次受到大家的嘲笑而羞愧,也寫出了自己對于城市未來的人種可能退化的一種擔憂。總而言之,城市缺少了活力,城市的未來堪憂。狼給了高子明生活以激情,商州作為擁有眾多狼的地方自然而然地被他記起并選中,于是他踏上尋狼之路。然而商州作為農村的代表,卻也是不甚理想。商州太過貧窮落后,為保護大熊貓的一批研究人員而蓋的新的三層小樓與破敗的鄉村格格不入,這里的人們大都吃窩窩頭,部分人家甚至吃不起飯,穿不起一條完整的褲子。同時,人類對于狼的過度捕殺,使得這里出現生態倫理失衡以及人性喪失的現象。商州部分地區的生活方式也太過野蠻,生龍鎮的人們砍掉活著的蛇的頭并生喝蛇血,他們切食活著的牛身上的肉。雖然這里民風淳樸,但是現代文明的影響下,一些現實問題出現在這個地方。高子明在城鄉兩個地方反復游走,他的生命力也在萎縮,卻并未得到救贖,這無疑是一次失望之旅。城市和鄉村生活在這部作品里是難以抉擇的,它們似乎都有著弊端。賈平凹在整體把握上描寫出了商業化時代的人們在價值觀上的惶恐和不安,說出了人們在文化選擇方面矛盾的抉擇。他抨擊了現代文明中存在的“城市病”,也對臆想中的農村美好生活在文明的侵蝕下變得丑陋而感到痛苦與惋惜。
三
賈平凹自言在他創作《懷念狼》時,常常有一種恐懼感,他自己也搞不明白是因為年齡所致還是自己閱讀了太多的戰爭、災荒和高科技成果的新聞報道,他甚至產生為什么生而為人的想法。基于此,也可以認為賈平凹在這部《懷念狼》中所想要表現的是一種人文關懷。“懷念”中有作家尋覓平衡的一種理想與追求,也滲透著一些洞觀事實真相后的焦灼和憂患,甚至是面臨人類危機時的恐懼,有點類似于投放新狼種而引起的驚恐與慌亂。因此,釀就這種“懷念”的原因,也就是當下人類生存處境的影響或者說是所謂“現代文明”的負面刺激的驅使。但是現實就是這樣,誰能阻擋歷史的前進呢?然而“我需要狼”便僅僅是一種聲音的存在,因為“狼”滅絕已經成為了必然——“狼”被毀滅了,“英雄時代”隨之變成了一種古典式記憶。可是人類的生活前景或者人的生存命運又會是什么樣子呢?這只能是一種尷尬,一種無奈,再就是只能等候一個另類的“英雄時代”出現。
《懷念狼》通過“狼”這一意象創造性地寫出了“懷念”與關于“懷念”的情緒,若隱若現地傳達出了一種對于現實社會或者說是所謂的“現代文明”的憂慮與悲情。賈平凹的這種悲天憫人的觀念,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一脈相承。生而為人,應該把萬事萬物同等看待,不做高低貴賤的區分,就像紅巖寺的老道士,深山溝子里收養狼孩的老太太。相互理解、共存共榮才是王道。天、地、人的和諧相處,才是永恒不變的真理。
小說中的狼是一個很豐富的意象鏈,它不只是傳統印象中的狡詐、兇殘的形象,它還知恩圖報。人與狼的關系除了相生相克,還有和諧共處。狼在作品中也承載了重要的象征意蘊。回想狼和人相處的歷史,人們和狼的關系不斷地發生著變化。首先,人們對狼的主要印象還是跟傳統中的一樣是充滿著狡詐與兇殘的,多有貶義意味;其次,人與狼是互相學習、互相作用、互相發展的螺旋式關系;再次,狼文化歷史悠久、深厚,有眾多可供截取的素材,也有前輩們的優秀創作,為狼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了土壤;最后,當然也是最重要的,狼與人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四
賈平凹一直不停地在文學創作之中探索著,他滿懷著對故鄉的熱愛為讀者展現出了商州獨特的民俗人情與粗獷而又靈秀的地輿景觀。他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為我們展現現代文明與傳統文明交融的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種種不能避免的矛盾,他更以一個古城人的驕傲讓我們感受到商州濃郁的文化底蘊與深厚的古都歷史。賈平凹在《懷念狼》中構建了龐大的意象世界,這些意象的建構,讓小說具有多重意義的可讀性,讓小說的內涵更加豐富,更具趣味性,讓小說的精神空間得以拓展,從而讓不同層次的讀者需求得到滿足。文化背景和生活閱歷不同的讀者們能從賈平凹創造的意象世界中得到不同的感悟,而繁多的意象也會讓作品百讀不厭,每讀一遍都會有新的發現。與此同時,賈平凹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繼承以及宗教文化、家鄉獨特地域文化等豐厚的意象資源的基礎上,不但達到了“立象以盡意”的美學效果,而且讓小說呈現出亦幻亦真、虛實相生的獨特感受。這一切都讓賈平凹理所應當地成為了當代文壇之中極具份量的作家。
我們在品味其小說獨特韻味的同時,也慨嘆著他的用心良苦。在人們生活的節奏越來越快、科技日新月異發展的今天,電子書的普及讓人們進入淺閱讀與輕閱讀的新時代,而賈平凹則通過自身的努力,一直堅守著純文學的立場,為中國文壇貢獻著自己的力量。賈平凹在作品中進行的意象世界構建,不僅讓蘊意深厚的主體之情愫得以抒發,也為中國文學的意象世界描畫了濃重而精彩的一筆。
作家們之所以把“狼”當為意象來頻繁使用,不僅僅是因為狼是民間最常見的動物,是兇惡的代表,更主要的是它的形象十分豐富,和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適合于各種隱喻和象征。而賈平凹的長篇小說《懷念狼》中狼的意象更加具有多義性。懷念狼,究竟懷念的是什么?賈平凹自言,“懷念狼是懷念著勃發的生命,懷念英雄,懷念著世界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