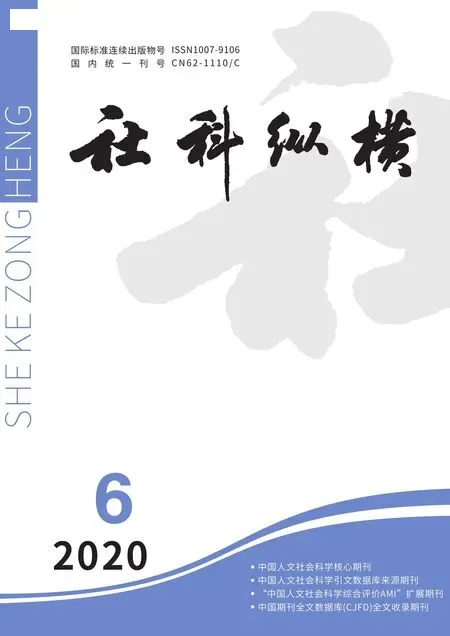《共產黨宣言》中批判精神及其對捍衛和建構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啟示
趙 艷
(安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是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不斷自我批判以及同各種反對勢力及其反動思想理論斗爭過程中的經驗總結,是兩人在革命斗爭和真理探索中勇于批判和敢于接受批判的精神成果,也是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和開拓創新的理論品質,更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保持旺盛生命力和科學創造力的動力源泉。馬克思恩格斯“站在新的時代實踐的高度,在當時德國和歐洲的具體政治環境里,批判地審視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思想……鍛造出為先進階級的實踐所需要的理論武器”[1](P88),也為當今時代我們理解和改造新世界提供了最銳利的武器——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這種批判精神直接或間接地貫穿在馬克思主義眾多經典著作中,《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正是這一精神集中運用的鮮活體現。本文正是通過對《宣言》中這一批判精神的梳理和挖掘,以期為當今時代處于西方話語霸權打壓和圍剿下的中國如何有效地抵制和解構西方話語霸權,以及積極捍衛和建構我國國際話語權提供方法指引和借鑒。
一、《宣言》中批判精神的運用與體現
(一)對資本主義社會及資產階級的批判
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的抽絲剝繭和層層解析,深入批判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和資產階級的貪婪本性。首先,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對立和階級剝削的本質。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脫胎于封建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并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只是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雖然變換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也“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舊的”[2](P32),并沒有改變階級對抗與剝削壓迫的實質。其次,批判了資本邏輯下社會關系的扭曲與異化。資本主義通過肆無忌憚地擴張生產關系,斬斷了封建社會“尊崇有序”宗法倫理關系的根系,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溫情脈脈的面紗,把一切社會關系都異化成純粹的金錢關系,表現在“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2](P33-34)。最后,批判了資產階級對民族文明的破壞和城鄉關系的剝離。隨著資本的無限擴張,資產階級的貪婪本性暴露無遺,加之工業社會下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的迅速改進和發展為資本的無限擴張提供了便利條件,資產階級開拓了世界市場,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2](P35-36)。為此,它還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使農民被迫脫離農村生活,被趕進了城市工廠進而轉變為被資產階級剝削和壓榨的對象。“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2](P36)正是通過這種全球性的資本擴張和野蠻侵略,資產階級快速實現了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與全球化,使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2](P36)。
如果說以上這些正面的直接批判還不能讓資產階級面紅耳赤、無言以對,或者還能讓他們道貌岸然地進行狡辯,叫囂他們創造了所謂的“自由競爭”“獨立個性”和“自由、法律”等先進理念的話。那么,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對此所進行的針鋒相對的回應性批判更可謂是一針見血,讓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自我美化與自我吹噓的謊言不攻自破!如,針對資產階級把消滅財產私有關系說成是消滅個性和自由的謬論,馬克思恩格斯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反擊,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是過去支配現在,在共產主義社會里是現在支配過去。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2](P46),并對準資產階級詭辯言論的要害進行了有力反駁,“我們要消滅私有制,你們就驚慌起來。但是,在你們的現存社會里,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被消滅了;這種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為私有財產對十分之九的成員來說已經不存在”[2](P47)。揭穿了資產階級萬惡的謊言之后,馬克思恩格斯又名正言順地公開聲明:“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2](P47)這種直接劍指資產階級狡辯性言辭要害的回應性批判可謂是一種具有沖擊力的反駁,不僅使資產階級陷入自我打臉的矛盾漩渦,更有助于共產黨人和無產階級透過資產階級唯慌唯恐的虛偽面孔和丑惡嘴臉,認清其竭力辯護私有制的真正意圖和背后實質。
(二)對各種偽科學社會主義思潮和意識形態的批判
面對當時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各種錯誤意識形態和流派,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綜合辯證地運用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針對各類流派一系列冠冕堂皇的思想理論和反動的社會實踐一一進行了深度剖析和有力批判。首先,有力批判反動的社會主義半革命半反動的革命調和性。《宣言》中反動的社會主義包括(甲)封建的社會主義、(乙)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丙)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三種流派,三者都打著“工人階級”或“社會主義”的旗號進行了某種程度上的理論或實踐斗爭,但當革命深入開展涉及到政治本質和階級利益的時候,他們就原形畢露地呈現出階級局限性,暴露出革命的虛偽性和反動性。如,批判(甲)封建的社會主義,“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刺中資產階級的心”[2](P54),但當革命斗爭真正深入的時候,它就毫不掩飾自己批評的反動性了,“在政治實踐中,他們參與對工人階級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違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辭,屈尊拾取金蘋果,不顧信義、仁愛和名譽去做羊毛、甜菜和燒酒的買賣”[2](P55)。批判(乙)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某種程度上“非常透徹地分析了現代生產關系中的矛盾。……它確鑿地證明了機器和分工的破壞作用、資本和地產的積聚、生產過剩、危機、小資產者和小農的必然沒落、無產階級的貧困、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財富分配的極不平均、各民族之間的毀滅性的工業戰爭,以及舊風尚、舊家庭關系和舊民族性的解體”[2](P56-57),但按實際內容來說,它“或者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系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系的框子里去”[2](P57)。批判(丙)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們鼓吹超階級的社會主義,聲稱自己代表人的本質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而實際上這種人不屬于任何階級,也根本不存在于現實界。發展到最后,這種社會主義“就直接反對共產主義的‘野蠻破壞的’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階級斗爭之上的”[2](P60)。其次,猛力批判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半改良半投降的革命妥協性。這類社會主義的資產者希望維持現有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產關系,又想要消除現存社會的一些“弊病”,同時清除那些使這個社會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顯然,這是小資產者階級自我改良的一套把戲。他們試圖用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來使工人階級厭棄一切革命運動,而他們所理解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改變,“絕對不是只有通過革命的途徑才能實現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廢除,而是一些在這種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實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絲毫不會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2](P61)。最后,極力批判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半幻想半實踐的革命空想性。這是早期無產階級的代表,他們已經意識到階級間的對立,但限于當時自身解放的物質條件和自覺意識不高等各種因素,他們又看不到無產階級的歷史主動性,只能通過幻想的條件設計一些社會組織和社會計劃去推行他們想象中的美好社會。相對來說,他們有一定的進步性,敢于抨擊現存社會的全部基礎,提出“消滅城鄉對立、消滅家庭、消滅私人營利、消滅雇傭勞動”等消除階級對立的先進主張,并且進行了一些社會試驗;同時他們也呈現出早期無產階級的歷史局限性和純粹空想性,沒有認識到階級斗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他們拒絕一切政治行動,特別是一切革命行動;他們想通過和平的途徑達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圖通過一些小型的、當然不會成功的試驗,通過示范的力量來為新的社會福音開辟道路”[2](P63)。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深刻指出的,“階級斗爭越發展和越具有確定的形式,這種超乎階級斗爭的幻想,這種反對階級斗爭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實踐意義和任何理論根據”[2](P64)。
通過上述對各種偽科學社會主義流派反動思想理論和偽社會實踐的無情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深入披露了各流派背后所代表的階級本質和利益關系。揭露了“(甲)封建的社會主義代表著封建貴族階級及其利益,(乙)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代表著中世紀的城關市民等級和小農等級所組成的小資產階級及其利益,(丙)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代表著德國小市民階級及其利益;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代表了當時社會中小改良家/小資產者階級及其利益;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代表著早期落后的、傳統的無產階級及其利益”[3]。透過這些表象深入到其背后的政治實質與利益關系,馬克思恩格斯深刻認識到正是由于這些流派所代表階級本身的歷史地位和階級局限性,使得他們只能從本階級利益出發進行某種程度上的革命斗爭或社會改良,因為不能代表受苦最深的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也就不可能進行最徹底的階級革命和政治斗爭。因此,無產階級要實現自身的解放,必須喚起整個無產階級的覺醒,依靠無產階級自身的聯合,并且拿起武器進行最徹底的革命斗爭和政治斗爭,才能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
(三)對自身革命理論的自我批判
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不僅都戰斗在對政敵及其思想理論的無情批判中,還一以貫之地堅持在批判別人的同時也以一種批判的態度審視自己,始終做到自我批判,就是為了確保自己的理論能夠符合不斷發展的社會實踐,避免固步自封和走向教條化。正如他們自己所明確的,“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4](P7)。基于這種大無畏的勇于批判精神,兩人也時刻不忘正視自身理論的不足和局限,敢于并善于從自身理論內部進行自我解剖、自我批判,力爭做到立足于社會現實的基礎上實現批判與自我批判的有機統一。《宣言》更是這一批判精神的集中體現和代表。作為指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理論與實踐綱領的《宣言》,最初出版時只有一篇引言和四章正文,出于國際工人階級聯合斗爭和革命發展的現實需要,先后又以多種譯本在世界各地出版發行。為了更好地指導國際工人運動,馬克思恩格斯更是本著自我反思和自我更新的自我批判精神,結合時代發展變化的特點以及各國特殊國情與歷史條件,前后為不同譯本寫了七篇序言,共同構成了現在所見《宣言》版本的全部內容。在多個版本的序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政治形勢已經完全改變”,由于“《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2](P6/15),因此他們一再在序言中補充強調“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并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兩次聲明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2](P9/14)。這些作為補充內容的序言正是馬克思恩格斯對自身理論自覺進行自我批判的發展成果,更是兩人自始至終堅持唯物主義辯證法的鮮活體現。
二、《宣言》中批判精神的特征與實質
《宣言》中,批判精神是內蘊在馬克思恩格斯對自身理論的反思以及對資產階級與各種偽科學社會主義等反對派的思想理論和偽社會實踐的披露之中的。這種深入全面的批判和深刻徹底的揭露,鮮明地彰顯了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主要特征和內在實質。
(一)批判精神的主要特征
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貫穿于《宣言》整部著作的始終,使其作為整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不僅具有較強的指導性和實踐性,更是同時兼備科學性和價值性、批判性和建構性、開放性和內在規定性有機統一的顯著特征。
1.科學性和價值性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性與價值性的辯證統一,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也同樣彰顯著科學性與價值性兩個最重要特征。科學性本身就是一種符合客觀實際,并能夠反映事物本質和內在規律性的客觀標準。《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對一切反對派所作的批判都是立足于歷史和現實的基礎上,以“是否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歷史規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作為衡量一切理論與實踐的科學標準,并據此客觀地厘清了無產階級不同于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鮮明地劃清了科學社會主義與偽科學社會主義之間的界限鴻溝。價值性體現在價值主體(指馬克思恩格斯和整個無產階級)根據事物的客觀本性和內在規律性有效地改造客體對象,從而使自身的實踐活動和對客體的改造符合價值主體追求的科學真理與價值目標。《宣言》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綱領性文件,貫穿其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立場和實現整個無產階級及全人類解放的終極價值目標,這是引領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出發點和根本方向,也是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價值旨歸。正是對“無產階級自身解放”與“建立自由人聯合體”的這種價值追求,使馬克思恩格斯對一切剝削階級和不平等社會現實的批判突破并超越了以往任何階級的立場和局限,能夠站在價值的制高點上,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指導無產階級對剝削壓迫的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最徹底的革命和改造,并且引發了全世界所有受剝削受壓迫階級的共鳴和響應,以致在整個歐洲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為實現自由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奮斗的工人運動和武裝革命。
2.批判性與建構性的統一
批判即否定、革命和打破,建構即確立、構筑和重鑄,簡而言之就是破和立,兩者是一個矛盾統一體。批判是建構的前提和根基,建構是批判的目的和歸宿。批判往往是為了更好地建構,內蘊在批判之中的建構本身就是最好的批判。“很多時候,正確的科學理論往往正是在破除錯誤和反動思想理論過程中創立和發展的。《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無產階級的奮斗目標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確立,也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各種反動社會思潮基礎上實現和完成的。”[3]馬克思恩格斯力爭在借鑒過去一切階級創造的優秀文化傳統基礎上達致自身理論的縝密完善,又努力在突破過去一切階級局限性基礎上實現自身理論的革故鼎新,不僅讓批判越加深入全面、徹底有力,而且讓建構更加科學完整、客觀公正。可見,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絕不是簡單地一味抨擊和肆意批判各類反動派,更不是純粹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始終堅持有理有據、有破有立、破立結合地全面批判,在揚棄基礎上有否定有繼承地理智理性批判,真正做到批判與建構的有機統一。
3.開放性與內在規定性的統一
開放性是與保守性和封閉性相對立而存在的。開放是創新的前提和內在要求,保守和封閉只會裹足不前并導向教條。開放性本質上就是一種求實的態度,正是對事實的尊重和忠實才讓馬克思恩格斯時刻不忘以發展變化的眼光和寬敞明亮的胸懷,坦誠地面對自己和別人的一切理論成果。《宣言》中,兩人始終以客觀開放的態度審視自身理論及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學說,不僅以自我批判精神不斷更新和修正自身理論,而且適時學習和借鑒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的合理成分以補充修繕自身理論。雖然馬克思恩格斯一直以開放的心態對待各種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但求真更是兩人終其一生所奮斗的目標。“從追隨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到創設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從研習國民經濟學到圖構馬克思的批判政治經濟學,從探究空想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到為社會主義指明科學理路……”[5],馬克思恩格斯一生正是本著對求真的這種虔誠和追求而不懼艱辛奔波、四處樹敵(然而卻沒有一個私敵),卻至始至終堅定不移地堅持事物發展的客觀真理性和內在規定性。所謂內在規定性就是事物發展變化過程中本質的、必然的屬性,也即事物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性。“兩個不可避免”理論的提出,就是兩人對“資產階級必然滅亡,無產階級必然勝利”和“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這一社會發展規律內在必然性的清醒認識和始終抱持。可見,無論是批判還是自我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都始終如一地堅持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開放性和內在規定性的有機統一。
(二)批判精神的內在實質
作為工人運動的革命領袖,馬克思恩格斯無比同情受苦最深的無產階級,也嫉惡如仇地鞭撻不擇手段的資產階級,這種善惡分明的態度不是兩人一時情緒化或情感化的控訴,更不是憑空想象或蒼白無力的惡意指責,而是批判主體(馬克思恩格斯)對批判客體(批判對象)的理性反思和自覺的能動性批判,“包含著批判主體對批判對象的肯定性、否定性或引導性的價值判斷”[6],更是批判主體“在實踐批判與理論批判辯證統一的基礎上,對自身及其理論與現實的關系的反思,對自身局限的揚棄和超越”[7]。所以說,這種批判實質上是一種對象明確、目的明晰、全面到位、徹底有力的綜合性、革命性和超越性的批判。
首先,這種批判是一種既勇于向論敵公開亮劍,又敢于向自己公然開戰的全方位、雙維度和多視角的綜合性批判。它縱向上包括批判和自我批判,橫向上包括理論批判和實踐批判,即對他人的批判與對自我的批判同時進行,對理論的批判與對實踐的批判雙管齊下。“這種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也不怕同現有各種勢力發生沖突”[4](P7),也就是說這種批判不僅包括外在的批判他者和回應他者批判,即批判與回應性批判;而且還包括內在的自我批判,即對自身理論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此外,正是意識到“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8](P9),馬克思恩格斯不但善于運用“批判的武器”,還常常拿起“武器的批判”對準“批判的武器”,不斷完善批判的武器,讓批判由理論指向實踐,更加綜合全面、深刻透徹。其次,這種批判不是簡單的否定,也不是純粹為了否定而否定,而是一種在否定中積極揚棄和構建的革命性批判。《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不只是簡單地對現存的一切進行最徹底無情的批判,而是極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和創造一個新世界。如,通過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深入批判論證了社會發展進程中“兩個不可避免”與“兩個必然”的歷史規律,通過對各種偽科學社會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全面揭露喚起了無產階級的聯合和開展革命斗爭的意識覺醒,通過對自身理論的深刻反思和充實完善使馬克思主義理論走下神壇走向科學。最后,這種批判是一種尊重歷史、立足現實、面向未來的邏輯的、辯證的超越性批判。《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資產階級創造的歷史成就,也犀利地披露了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的不平等社會現實,并基于全世界無產階級和整個人類解放的立場,以超越過去一切剝削階級歷史局限的視野,致力于消滅一切私有制和階級對立的條件,鏟除一切不平等的社會根源,呼吁并力行建立一個“自由人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P53),這種追求被壓迫階級整個階級解放和個體權利實現的社會理想觀,超越了歷史上過往一切剝削階級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總之,馬克思恩格斯這種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辯證思維和高度自覺的批判與自我批判精神,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實現自身理論科學化的方針指南,也是當今時代我們全面認識和分析新形勢新問題的指導方法,更是培育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有力武器。
三、《宣言》中批判精神對捍衛和建構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啟示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短短數十年就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跡,不僅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而且國際影響力也一路攀升。中國的快速崛起引起了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恐懼與不安,加之當時我們主要精力大都致力于國內社會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很少在國際舞臺上主動亮相發聲,這種國際發言權的缺失給了西方國家不斷變換手法丑化、矮化中國國家形象的可乘之機,相繼炮制出“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強國必霸論”等一系列惡意唱衰、抹黑和污蔑中國的國際輿論。這種帶有強烈不軌意圖和目的的棒殺與捧殺,導致我國國際話語權常常處于被動局面。雖然我們一再向世界證明和闡釋我國“不稱霸”的和平發展道路,但限于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國際話語權的把持與壟斷,以及我們自身在話語闡釋和傳播方面還存在各種不足等因素,致使我們在國際舞臺上多數情況下的發言仍局限于針對指責和批判的被動性解釋和回擊,話語“音量”與話語“音效”依然提不高和傳不遠,遠遠不能與我國硬實力的發展相匹配。面對這種困局,被動回擊并不能真正消解西方發達國家的話語霸權,塑造我國的國際話語主導權。因此,“求助于某種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仍然是當務之急,而且將必定是無限期的必要的”[9](P122)。這從《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針對資本主義社會和各種偽社會主義思潮盤根究底式的深度批判,以及對自身理論不斷反思、充實與完善的自我批判精神中同樣可以得到指引和啟發。
(一)通過“批判與自我批判”不斷反思和創新中國話語
無論是批判還是自我批判,我們都要實事求是、有理有據,這樣才能使我們的批判話語更加信服有力。正所謂“以誠立身,方能取信于人”。“真正的‘批判’不是憑空臆想或源于經驗的設想和假想,而是在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有破有立地批駁,進而形成有信服力的批判。”[3]我們在對外傳播自身話語時,第一,要做到從內容到形式、從主體到客體、從“音質”到“音效”等各方面的深度剖析和自我批判,反思我們的話語傳播形式是否過于單一單調和路徑不暢等;抑或作為話語主體的我們在闡釋和傳播自身話語的同時,是否考慮到話語對象(話語客體)的歷史文化和現實環境,以及話語力度的把握是否契合話語對象(話語客體)的情感認同和價值認同等。第二,要在自我反思的基礎上主動創新自身話語內容、改進話語方式、拓展話語平臺,切實提升話語質量和話語效應,真正做到讓自身話語無懈可擊、無隙可乘。話語內容上,要精于提煉具有標識性的和易于為話語對象所理解與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和新表述。話語方式上,要巧于運用生動活潑、幽默風趣、喜聞樂見的詩詞、名言、警句、諺語、俗語等,以及國際上慣用的語義清晰且契合話語對象文化習俗的字詞語句等各種表述形式。話語平臺方面,要在堅守傳統媒體陣地優勢中謀求創新并自覺提升國內主流媒體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更要善于借勢發力,積極利用國際組織、西方媒體、國際學術會議和民間交流等各種平臺和載體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總之,在對外闡釋和傳播中國話語時,不僅要從自身視角積極正視問題和不足,更要從客體角度批判和挑刺自身話語,即擅于在批判與自我批判中主動自覺地進行反思和變革,從而做到推陳出新和開拓創新。此外,還“應有意識地了解對方的社會文化、善用對方的話語表達方式,通過話語融合、文化握手,使自己的思想觀點呈現易于理解、樂于接受的形式,推動思想上的同頻共振,從而有效生成國際話語權”[10]。
(二)通過“回應批判”大力抵制他者對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消解
作為向來主張和平共處、多元共存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一直倡導求同存異的“和合”精神,始終堅持“不稱霸”“不結盟”和“不輸出革命”。但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還存在不均衡和不充分的現實短板,并且又相對缺乏國際輿論場上話語權建構和創新的經驗以及反制西方國家話語霸權的能力,所以一直以來我們很少在國際舞臺上積極主動去爭奪話語主導權,更不會為了搶奪話語權率先挑起矛頭和論爭。正因如此,我們在話語主動權上往往錯失先機,并且受制于人。相反,西方歐美發達國家憑借自身話語優勢長期壟斷話語霸權,不但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的話語規則和話語標準,更是頻頻攻擊和消解中國話語,企圖遏制中國的崛起。表現為:當我國發展遭遇困難和阻礙時,“歷史終結論”“中國崩潰論”繼之而起;當我們發展取得成績時,“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強國必霸論”一哄而上。總之,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被西方發達國家帶著有色眼鏡去解讀,并被貼上各種標簽后推向輿論漩渦。《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針對論敵各種詭辯性言論的回應性批判啟示我們,針對他者帶有不軌圖謀的強詞奪理和栽贓污蔑,除了敢于正視自身不足和勇于自我批判以使自己能夠立得住和站得穩之外,我們不能僅僅停留于或滿足于解釋和說明性的回應性批判,而應毫不畏懼地正面迎擊一切挑刺和潑臟,以積極踴躍的姿態作出有根有據、據理力爭的回擊和批駁,并有力有節地做到“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見招拆招”,最終以“無招勝有招”。同時,還要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分析法和歷史分析法,透過西方話語的表象深挖并揭穿其言辭背后隱藏的真正意圖和實質——認識到話語權之爭其實質就是意識形態之爭,歸根結底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掌握話語權才能掌握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和領導權。當然,話語權歷來都不是天然生成的,也“不是自然而就的,始終是一個有意識的自覺建構的結果”[11],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主動維護和捍衛,并積極爭取、塑造和培育我國的國際話語權。無論話語權的維護和捍衛,還是話語權塑造和培育的過程都是一個不斷與對手相互角逐和實力比拼的過程,更是一種在相互批判和回應批判中斗智斗勇并最終取得話語權優勢的過程。而要在話語權斗爭中取勝,培育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將是強有力武器。既要敢于運用這個武器抵御和回擊對方不懷好意的指責與批判,還要用富于批判的戰斗力正面迎擊西方話語霸權的威脅和挑戰,更要擅于運用批判的精神直擊西方話語霸權的軟肋和硬傷,才能徹底粉碎西方話語霸權對我國國際話語權的消解。
(三)通過“批判西方話語霸權”積極爭奪和建構中國國際話語主導權
縱觀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話語權發展的歷程,隨著國力的增強我國國際話語權逐步提升,目前已轉入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戰略機遇期,但一路走來我們一直處于西方強勢話語的鉗制和打壓之下,并經歷了話語權塑造和培育的艱難爬坡期和曲折成長期。一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愿正視中國的崛起,經常歪曲和過度解讀我國的話語和行為,使我國在國際舞臺上的發聲一度陷入“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尷尬境地。二是因為中國文化基因中向來謙遜恭讓的品格和秉承“以和為貴”的主導思想促使我們總是奉行低調、不當頭的國際處事原則,不善于也不強于在國際舞臺上主動亮相和發聲,因而不利于我國國際話語權的培育和爭奪。然而,歷史和現實已經多次向我們證明,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和沖突不可能使資本主義國家心甘情愿地放棄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圍剿和瓦解,即使被“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分化和西化后改旗易幟的國家也難逃被西方霸權主義欺凌和排擠的命運。最好的例子就是蘇聯解體后繼起的全新政權俄羅斯,曾“一邊倒”地傾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期望與之建立良好關系,非但沒有被接納反而到現在還一直遭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遏制。《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與各種反動勢力斗爭到底、毫不妥協的同時,積極建構工人階級自身科學理論的批判精神也啟示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務必在堅決抵制和徹底消解西方話語霸權的同時,全力爭奪和建構我國的國際話語主導權。不僅要正常有效、光明正大地發出中國聲音,還要“通過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的對外傳播爭奪全球價值標準的定義權,形成我國對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文明、人權、發展等人類共同價值的解釋權和影響力”[12]。為此,中國必須主動扛起批判和解構西方話語霸權的旗幟,攜手各國共同抵制國際霸權主義,徹底消釋“西方中心主義”無理橫行的肆虐,打破“北強南弱”“西強東弱”不平等、不協調的話語規則和國際格局。中國要積極推動國際話語規則進行改革,力爭讓更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話語舞臺中具有發言權,并“通過在國際話語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來推動國際話語規則重構和再塑,為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提升爭取更多有利條件和規則保障”[13]。此外,中國更要切實增強議題設置能力,敢于突破并勇于創新國際話語議題設置,善于并強于設置和引領國際社會普遍關注和共同關心的國際熱點話題和議題。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就是這類議題設置的成功案例,不僅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歡迎和大力支持,在國際舞臺上樹立了中國愿與世界各國“攜手共進、互利共贏”的良好國際形象;西方霸權主義的強盜邏輯和叢林法則不得人心,只有關注人類共同發展的長遠未來,積極回應國際社會共同希冀和期待,才能不斷開拓國際話語空間,真正為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發展創設更加公平正義的良好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