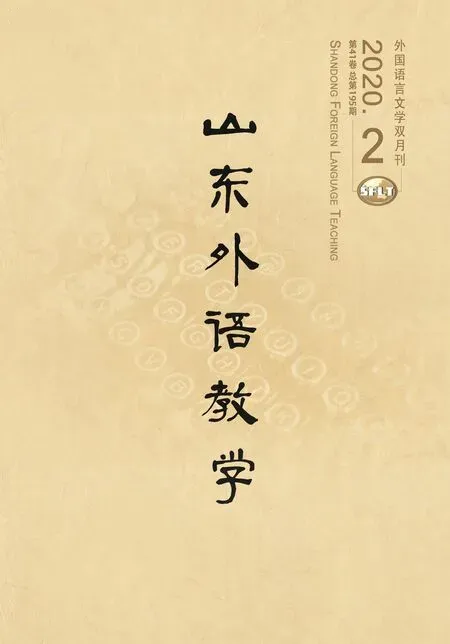微閱讀/微寫作
瑪喬瑞·帕洛夫; 何慶機 (譯)
(1.美國斯坦福大學 英語系,斯坦福 CA 90272,2.浙江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閱讀本身無需借助任何理論,足以改變批評話語。這一轉變對那些將文學教育視作神學教育、倫理學教育、心理學教育或思想史教育的替代品的人來說,具有深刻的顛覆性。(De Man,1986:24)
引述保羅·德·曼上述觀點之后,李圭在文中寫道:“這樣的細讀不是封閉的,它在過去和現在的確拓展了文本空間的新視界,同時以時間拓撲式干預和發明的形式為自己獲取了空間。”接著,李圭以其特有的和藹可親的口吻,退后一步說道,“不過,我的視野更窄、更小,幾乎是一種微哲學詩學,類似于禪宗聚焦。”
在此,我想進一步闡明“微哲學詩學”閱讀實踐——這也越來越成為我自己的閱讀方式。查爾斯·伯恩斯坦在其《細聽:詩歌及表演的世界》提出“細聽”(close listening)一說,毋庸置疑,用它在這個大部分閱讀只是機械式閱讀的時代,對日常假新聞進行回應,是很有必要的。讓-弗朗索瓦·利奧塔所質疑的“宏大敘事”(master narrative)已成為遙遠之事;同樣遙遠的還有二十世紀晚期的觀念——沒有外在的、明確的真理掌控我們的生活,我們必須學會接受與語言的內在不確定性和飄忽不定相伴的復雜性。不過,2019年宏大敘事再次成為風行的詞匯——《紐約時報》會刊印如此的語句“唐納德·特朗普是一個說謊者”,其語氣的權威性似乎與說“唐納德·特朗普身高6英尺1英吋”是一樣的。現在的話語方式,不是批評一個人說了謊,而是指責他(她)本質上是個說謊者。再或者,不是說“某某說了句種族主義傾向的話”,而是說“某某是種族主義者”。誰會相信,在德里達的延異說展示出深刻影響之后,我們會在這個新世紀再次不斷陷入“是”之言說的洪流。
在數字時代,閱讀/寫作行為也因其替代行為而打折扣。在此我自己先認罪。例如,近幾年來我習慣于“聽”而不是閱讀小說或非虛構書。從很棒的Audible.com網站下載一部由朱利亞·史蒂文森(Juliet Stevenson)朗讀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說《金碗》(TheGoldenBowl),在夜深人靜之時傾聽,是再愜意不過的事。聽而非閱讀這部小說,我注意到詹姆斯的句子結構詭異地預示了格特魯德·斯坦因的重復,如在此句中——“他知道她知道他正知道……”。斯坦因常常表達出對詹姆斯的無比崇敬之情,但批評家們往往關注的是她與在哈佛就讀時的老師、亨利的哥哥威廉的關系。再或者,當我聽著杰勒米·諾森(Jeremy Northam)朗讀喬治·奧威爾的小說《致敬嘉泰羅尼亞》(HomagetoCatalonia),小說的主題在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戰爭之無意義以及西班牙內戰時期理想主義革命者的可怕命運。
在洛杉磯,如遇到交通堵塞,我便聽書。交通堵塞越來越常見,而Audible.com使得開車出行不那么難以忍受。不過,我發現這只對我熟悉的書籍有效;艱澀難懂的新小說、批評性文本或T.J.克拉克(T.J.Clark)撰寫的藝術理論論文,并不適合于“公路聽讀”,因為出乎意料的交通狀況會讓我們分心——突然減速、交通事故、紅燈等等。
電郵和社交媒體中的閱讀與寫作也同樣不無令人擔憂。我經常一大早懶洋洋躺在床上用蘋果手機語音輸入;可每次一“輸入”,沮喪便隨之而來。我說的是“期待見到您”(“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轉換成文字很可能就成了“期待著揍你”(“I look forward to beating you” );“阿什貝利”(約翰·阿什貝利,John Ashbery)被轉寫成了“屁眼”(asshole)。我曾經給一位朋友“寫”道,我參觀了一個非常棒的福克納(Faulkner)手稿展,但“福克納”卻成了“fuck her”。如果專家告訴你人工智能將很快取代人類,別相信他們。從我的經驗來看,蘋果手機上的GPS、語音郵件、語音助手Siri等錄音系統,其理解力似乎經常不如一個小孩子。Siri甚至連”too”都拼不對,總是拼成“to”。所以“I am going too”成了“I am going to”,讓讀者摸不著頭腦。
一個字母之差,意義全然不同。讓人頗感矛盾的是,在現在數字技術蓬勃之際,我卻更加渴望李圭所說的“微哲學詩學”閱讀。我的指導原則來自二十世紀偉大藝術家馬塞爾·杜尚。杜尚為我們帶來了影響深刻的新形式,他在《大玻璃》又名《新娘甚至被光棍們剝光了衣服》里提出了“延遲”,尤其是虛薄(infrathin)這一概念。杜尚(1999:21-24)在按編號匯集的《筆記》(Notes)中對這一概念進行了描述(共43個筆記,由保羅·馬蒂斯編輯):
虛薄是什么意思?杜尚曾說該詞無法定義,只能通過例子說明。例如:
1.可能的事是一種虛薄。
4.座椅的溫度(坐的人剛走)是虛薄。
7.在時間上,同樣的物體一秒鐘后并不相同。
8.地鐵的滑門。最后一刻進出的人。
12.(非常近的)槍的引爆聲與靶上顯現的彈孔是虛薄式分離。
15.從未繪畫的一面觀看玻璃繪畫帶來一種虛薄感。
18.以最大(?)精確度衡量,一系列(產自同一模子)物品中兩物之間的(尺寸)差異是一種虛薄。
最后一種“虛薄”尤為重要,因為它呼應了路德維格·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探尋的問題:“不過相同之物(the same)不該至少是相同的嗎?”(2009:215)。至少對詩人和詩人的讀者來說,答案永遠是否定的。格特魯德·斯坦因諳熟此理——同一物在不斷變化之中,不論每次重復中發生的變化有多虛薄。
他們待在那里,在那里開心著;在那里不是非常開心,只是在那里開心著。她們倆都在那里開心著,她們一直在那里工作,她們倆都在那里形成了自己的聲音,她們倆在那里都開心。喬金·皮在那里是開心的;她性情不變,不變地開心,不變地不開心,不變地做這樣一個開心的人——開心的時間不會超過做一個相當開心的人所需要的長度。那時她們倆在那里都開心,那時兩人都在那里工作。(Stein,1999:17)
上述引文選自斯坦因的著名短篇小說《毛小姐與皮小姐》( “Miss Furr and Miss Skeene”)。引文共98個單詞,開心一詞(gay)重復了12次。在斯坦因的時代,“Gay”的字面意思是“高興”(“happy”)、“快樂”(“jolly”)、“愉快”(“good-humored”),不過已經有了“同性戀”(“homosexual”)這一隱含意思。“那里”(“There”)出現了11次,“她們”(“they”)在前三行出現了5次,最后一句出現1次。不過,當讀者以為“她們”(毛小姐和皮小姐)是一樣的時候,“不變”(“regular”)一詞以及它的副詞形式(共用了5次)起到了修正作用。我們得知,與毛小姐相反,皮小姐完全沒有總是開心。她是“這樣一個開心的人——開心的時間不會超過做一個相當開心的人所需要的長度”。虛薄在此起了作用——換句話說,皮小姐與她的愛人并不同步;實際上,在這篇非常短的故事里,兩位女性最終將分手。
斯坦因整個故事都有賴于對幾個詞的審慎操縱:gay、cultivating、working、regular/regularly、there、and then。“那時”到底是何時?這些再普通不過的詞重復的次數越多,我們對這兩個女性的關系了解得越少。讀者只能靠想象,不過在故事結尾海倫·毛(Helen Furr)獨自一人,告訴(新詞)別人如何成為開心的人。但不過相同之物(the same)不該至少是相同的嗎?不,實際上在這個故事里一切都在變。海倫和喬金擁有不同的姓氏(毛和皮),她們相遇,相愛,“在那里生活”,“工作”,“培養說話的方式”,遇到“又黑又笨重的”但后來又“不那么黑,不那么笨重” 男人,然后兩人分開,喬金最終去了別的地方,與別人在一起。
與杜尚一樣,斯坦因是虛薄大師。杜尚(1999:115)在后期筆記中這樣寫道:“復數的桌子不是桌子的復數,過去式的吃與一般現在時態的吃毫無共同之處”。讀者要能捕捉到這些小詞依語境而產生的差異,不管這種差異多么細微。在這里,詞源起到關鍵作用。俄羅斯形式主義批評家尤里奇·圖尼亞諾夫(Jurij Tynjanov)在1924年發表的文章“詩歌中詞語的意義”中指出:“單詞不存在于句子之外。孤立的詞并非在一個非詞組的環境中找到的”(135)。的確,“詞語的色澤取決于其在某個特定語境中的位置”。圖尼亞諾夫以俄語單詞zemlja (意為大地、土壤或地上)為例,說明不同的語境帶來截然不同的意義。
Zemlja and Mars:Earth and Heaven (人間與天堂)
Bury an object in the zemlja (土壤)
It fell on the zemlja (地上)
Native zemlja (國土) (Tynjanov,1971:137)
斯坦因(2014:11)在《軟紐扣》(TenderButtons)中寫道,“差異在散布中”,而語境具有欺騙性。我最喜歡的巴西詩人兼理論家之一,哈羅德·德·坎波斯(Haroldo de Campos)(2007:294)1981年在一篇談論詩歌功能和意符的文章中寫道:“對語言的指稱用途而言,astre (星星)一詞是搭配形容詞désastreux(“災難性的”)還是名詞désastre(“災難”)并沒有任何區別……但對詩人來說,這種‘發現’卻至關重要”。德·坎波斯以馬拉美的詩為例,不過波德萊爾的詩“我的旅行”(“Le Voyage”)中例子也許更合適。
Nous avons vu des astres
Et des flots,nous avons vu des sables aussi;
Et,malgré bien des chocs et d’imprévus désastres
Nous nous sommes souvent ennuyés,comme ici....(Baudelaire,1961:IV,1,124)
我直譯如下:
我們已經看到了星星
還有大海,也看到了沙灘;
盡管不缺驚訝和不可預見災難
我們還是常感乏味,就像現在這里……
在這里押韻的astres (星星)和désastres (災難) 可以互相替代。不論是詩人旅途中的異域美景,還是遭遇的可怕危險,都不能緩解現代生活的枯燥乏味。不過,名詞désastre的構詞是由否定性前綴des或dis與astron(希臘語“星星”)合并而成;也就是說,其指稱是指向星星的負面作用——指向不幸的事(ill-starred)。所以,astres與désastres(Baudelaire,1961:IV,1)這兩個日常話語中無關聯的名詞,實際上的確相互勾連。正如歐內斯特·費諾羅薩(Ernest Fenollosa)(1968:22)在《論漢字》中所說,在詩歌中“關系比相互關聯之物更重要”。
請注意,這種閱讀詩歌的方法絕不等同于新批評的方法,或者通常被稱為形式主義批評的方法。現在我們習慣性地將后者斥之為“純粹的”細讀,“純粹”解釋浮于表面(文本中)的詞語,而忽視了它們的政治、文化或人類學價值。不過,杜尚、斯坦因以及德·坎波斯卻深諳閱讀的本質——他們本人就是藝術家或詩人。他們明白詩人的作用不是去“言說”——任何非虛構作家都能做到這一點;詩人的作用是從語言之河中創造新的結構。
不幸的是,社交媒體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催促我們,時刻去瀏覽,點擊通常完全不是“新聞”的“爆炸新聞”,最終將閱讀簡化為對信息流的吸納,消化之后很快像快餐一樣遺忘殆盡。因此,我們更加需要對虛薄保持敏感,通過李圭所說的反閱讀的方法揭開日常新聞流的面紗。杜尚筆記第35條寫道:
同一個模子(?)制造的兩種形式,由于虛薄式差異而各不相同……
對被認為相同的東西進行大類分組,會帶來一種明顯的既視感。探尋兩個“相同物”之間的虛薄式差異,比不假思索地接受將兩個望遠鏡與兩滴水相比較的概括更有價值。(De Campos,2007:295)
不過,請等等,你也許會問,誰會將望遠鏡比作水滴呢?政客和新聞記者一直如此。在解釋為什么某項立法不起作用時,某參議員說“這又不是靈丹妙藥”。或者想想在沒有任何嚴肅的事情時,說讓我們“開始嚴肅的討論”這句成詞濫調。不過,我最討厭的,是對那些做了不可饒恕之事的人或因政治原因必須棄用的人使用圖形隱喻——應該把他們“扔到車下”。
說得多么輕描淡寫!顯然,是時候以不同的方式閱讀,進行差異性閱讀了。如李圭所說,是集中注意力用虛薄來回應文本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