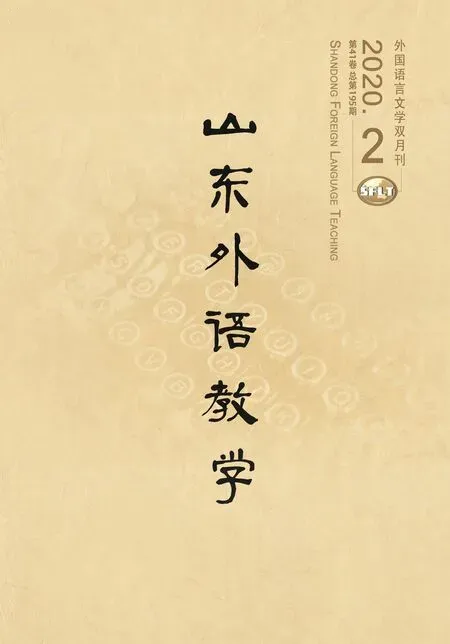科技典籍《天工開物》中修辭格及其風格英譯之譯者行為批評分析
王煙朦 許明武
(華中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1.0 引言
晚明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被李約瑟(Needham,1965:171)譽為“中國技術典籍的扛鼎之作”。而美國技術哲學家唐·伊德強調“技術無論如何都不能擺脫其自身的社會和文化情景”(Ihde,1990:144)。宋應星飽讀儒家經典,投身科舉,卻“五上公車不第”,而且他曾撰寫政論文《野議》,闡發恢復農事和提倡實學等挽救時局的觀點。實際上,《天工開物》記載農業和手工業兩大領域的谷物、染色、造鹽、冶鑄等生產技術是將《野議》的設想落到實處(Sch?fer,2011)。《野議》字里行間表明其諫言對象是皇帝和朝堂之人,而“歷代以文章詞賦桎梏天下人士之思想,遂群注重于文學之一門”(李喬蘋,1940:1),《天工開物》得以廣泛流傳,進而主張被采納必然以此為價值取向,其行文訴諸了多種修辭格,即為提升語言表達效果而有意識地偏離語言和語用常規,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的言語表達結構和模式(王希杰,2004:11),由此構成了原文風格的一部分。
科技典籍承載的科技應用價值對于當今社會十分有限,其中蘊含的偉大文學傳統和藝術張力“在一定程度上比傳達科技信息更有意義”(肖嫻,2019:60)。翻譯也是文體風格轉換的過程(Nida &Taber,1982:12),修辭格正是作者寫作風格的重要體現(周領順,2014a:234)。本文試以1966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籍華裔任以都和先生孫守全的《天工開物》英文全譯本,與1980年我國臺灣中華文化學院出版社推出的化學史家李喬蘋英文全譯本(分別簡稱“任譯本”和“李譯本”)為對象,從譯者行為批評視閾探討修辭格的英譯及相應的風格傳達,以期豐富《天工開物》英譯研究和譯者行為批評研究。
2.0 譯者行為批評與“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
作為翻譯主體和有意志的譯者是文字符號轉換的“語言人”,亦是具有多重身份的“社會人”。加之翻譯是發生在真實語境中的交際活動,語言性和社會性在譯者身上烙下了鮮明的印記(周領順,2014b:64),社會性顯著或曰社會需求占主導則會使其角色行為超出翻譯的基本范疇。以此類推,譯者行為是“社會視閾下譯者的語言性翻譯行為和社會性非譯行為的總和”(同上:25)。為了對譯者行為及行為下的譯文質量進行充分描寫,周領順開創的譯者行為批評研究,即“在社會視域下對譯者行為所作的批評性研究”(同上:26)考慮到譯者的雙重屬性,并兼顧作用于翻譯的語言內外部因素。這一路徑規避了規約式翻譯批評聚焦語言文字的靜態視閾,以及翻譯研究的泛文化傾向,從而提升了翻譯批評的客觀公正和科學性(許鈞,2014:112)。
譯者行為批評的核心概念和分析工具——“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將“求真”和“務實”置于連續統的兩端。“求真”為翻譯之必要,指譯者以原文/作者和務實目標為出發點,而部分或完整地求原語意義之真的行為;“務實”指在全部或部分再現原文承載的意義的基礎上為滿足社會性而采取的態度和方法,因而產生的譯文體現翻譯之用,趨向目標讀者和社會一端(周領順,2014b:76-77)。正如任何翻譯都不是絕對的歸化和異化,即分別向原語文化和譯入語文化靠攏,翻譯內的“求真”和翻譯外的“務實”也并非二元對立。語言性求真確保翻譯之本,而翻譯的社會屬性和譯者的“非譯者”社會角色多少會驅使譯者追求社會性務實,并在兩者之間尋求“合理度”或受制于現實因素偏向某一端(周領順、趙國月,2015;2017)。正因如此,譯者行為的評價標準,即檢驗其行為的合理度便落實在對求真度(譯文和原文)和務實度(譯文和社會)以及對二者之間平衡度的把握(周領順,2014b:106)。鑒于風格也是語言攜帶的信息形式之一(周領順,2019),本文擬借鑒該評價模式分析《天工開物》中修辭格及其風格的翻譯和傳達。
3.0 譯者行為批評視閾下《天工開物》任譯本和李譯本對修辭格及其風格之迻譯
通過文本細讀可以發現《天工開物》運用了引用、明喻、暗喻、擬人、夸張、反問、雙關等修辭格,它們兼具藝術審美和情感表達的雙重訴求,文字蘊含的“形、神、意”風格的傳遞難以用數據衡量(Li,2016),仍有賴于定性對比手段。其中,引用、擬人、明喻三種典型的積極修辭“帶有寫說者的體驗性,而能在看讀者的心里喚起了一定的具體的影像”(陳望道,2008:57)。譯者行為批評研究的第一步是對譯者行為進行盡可能客觀的描寫(周領順,2014b:25),加之篇幅所限,下文嘗試描寫任譯本和李譯本對引用、擬人和明喻以及與之依附風格傳譯的求真抑或務實取向。
3.1 引用及其風格
引用是在“行文中引用他人言論或文獻,以增強語言說服力和感染力,闡明自己的觀點或抒發感情”(譚學純等,2010:273),又細分為引經和用典。引經是引用特定群體認可的著作并從中找出歷史依據,用典是援引歷史典故或事件來含蓄地表達觀點。原文直接或間接引用了典故以及《論語》《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史記》《本草綱目》等古籍。引用能夠有效地引發受眾對被引作品和文字的共鳴,并激發他們思考被引文本和引用文本的關聯。Cullen(1990:298)就指出,宋應星援引先秦經典避免了著作被視為異端和偏離學者的創作方式。因此,引用配合了相關科技主題,也是宋應星的社會改良思想得到認可的重要手段。
例1.凡飴餳,稻、麥、黍、粟皆可為之。《洪范》云:“稼穡作甘。”(p.74)①
任譯本:Maltose can be made from rice,wheat,sorghum,or millet.According to the “Grand Regulations” chapter [in theBookofHistory],“this [i.e.making maltose] is the ultimate development in making sweet condiments out of grains.”(p.130)
李譯本:Malt-sugar can be made from paddy,wheat,millet,sorghum,etc.Thus we understand,why it was stated in the chapter “Hung Fan” 洪范 (or Great Plans) of the “Shu-ching” (orBookofHistory) that sweets could all be made from grain crops.(p.189)
出自《尚書》的《洪范》是箕子向周武王陳述治理之道的政論文,大意為國家的政令法度。原文介紹稻、麥、黍等農作物可制作飴糖,并引用《洪范》的“稼穡作甘”強調甜味可以從谷物中獲取佐證。宋應星“掉書袋”強調統治者重視農業生產并引以為鑒,產生了典雅的閱讀基調。任譯本原汁原味地保留引用,并將現代讀者熟知的“maltose(麥芽糖)”置于括號中避免改寫語體色彩,而且在章末注釋中補充“References to it are found in writings dating from the Chou dynasty (1122-256 B.C.)”(Sung,1966:132)。引用的內涵和形式得以保存,讀者的理解也被兼顧。因此,任譯本在譯者行為連續統上偏向語言性求真,又確保譯以致用,從而協調了語言求真和務實的接受效果,譯者行為合理度較高。李譯本將原文轉換成間接引語的形式,且“Great Plans”的政治色彩弱于任譯“Grand Regulations”。這一做法顯然偏向社會性務實而降低了異域文化帶給英語讀者的陌生感,修辭格韻味和語體特征卻有所不符,文本求真度相對低一些。
例2.年來著書一種,名曰《天工開物》卷。傷哉貧也,欲購奇考證,而乏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贗真,而缺陳思之館。(p.3)
任譯本: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I have written a book entitledT’ien-kungK’ai-wuchüan,orAVolumeontheCreationsofNatureandMan,but it is sadly limited by the author’s lack of wealth.It was my wish to purchase some rare artifacts in order that [statements made in the book] might be objectively verified,yet I lacked the funds;and although I wished to gather a group of colleagues to discuss the general subject of the book and to ascertain the truth of its contents,yet there was no meeting place for such conferences to take place.(p.xiv)
李譯本:Recently I wished to write a book entitled,“TienKungKaiWu”,but alas,I am poor!I desire to purchase rare books and objects,in order to examine and verify them,but I am lacking the funds required for such work.While I wish to induce men of literary ability to discuss with me the true and the spurious of these objects,I lack the means to set out food and lodging for them.(p.v)
“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程顥、程頤出生于洛下(洛陽)。“洛下之資”容易使明代學者自然地聯想到宋代以來討論哲學的學術傳統(Sch?fer,2011:136)。“陳思之館”典出曹植,他數次招集門客共同從事文章創作,作品在明代備受推崇(Cutter,1984:12)。宋應星在此借貧困這一主題聲明道德高潔和抒發經世致用的學術理想,原文蘊含了一定的文學性和深厚的個人情感。任譯本和李譯本均采用意譯法,對原文進行解釋性翻譯,致使典故背后的文化內涵丟失,原本抒情性文風被轉換成直白型表達。需要指出,兩處典故蘊含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原封不動地移入英語語境勢必給不諳中華文化的絕大多數讀者造成閱讀障礙。“求取原文任何的意義之真也是‘求真’”(周領順,2014b:264),兩個譯本傳遞表層含義而疏離了“作者/原文”一端。在部分求取原文之真的基礎上,任譯本和李譯本避開烙有民族性的修辭,譯文的流暢度和可讀性增強,減少和降低了大多數英語讀者的閱讀障礙和理解困難,所以文本的社會務實性較高。
3.2 擬人及其風格
擬人是將無生命的和無意志的事物或者抽象的概念賦予人的思想情感、行為語言、聲音容貌,給人以鮮明、活潑的感覺和印象(譚學純等,2010:5)。《天工開物》不乏此類文字,如“麥以麩為衣”“老蚌猶喜甚”。擬人化的事物寄托了深邃的說理,相關文字也具有文學氣息。例如:
例3.宋子曰:天生五谷以育民,美在其中,有“黃裳”之意焉。(p.36)
任譯本:Master Sung observes that,as Nature creates the five grains to nourish mankind,it places the essential part of the substance inside covers as though wrapping these cereals in yellow robes.(p.81)
李譯本:Nature creates the cereals to nourish the people.The best part of the grain is kept in the center and protected by an outer yellow cover (or clothing,viz:the hull,etc.).(p.117)
自然界生出五谷以供人食用,它們的外殼像黃色的外衣,自然之“天”被賦予了人的行為意識。與此同時,原書中的重要概念“天”字用于代指人世之天和最高統治者皇帝(王煙朦、許明武,2018),“黃裳”(皇上)還借助語音雙關使語言形式具備雙重意義(譚學純等,2010:216)。宋應星在此抒發個人情感,即強調農產品于國家賦稅和恢復社會穩定的意義,使文字流露出文藝氣息。首先,任譯本的“Nature”首字母大寫有擬人化色彩,將之與動詞“place”搭配強化了這一基調;“as though”屬于擬人手段,“robes”則呼應了其先前對“龍袍”的譯法“Dragon Robes”(Sung,1966:59)。由是觀之,任譯本從求真角度直譯修辭之美,并實現了譯文風格與原文風格的一致。而且語境連貫有利于激發閱讀興趣,由此兼顧讀者理解的務實性,譯文的合理度高。李譯本的“Nature”首字母大寫因單詞位于句首,且譯本傾向于意譯,大意為谷物被黃色的外殼包裹。原文的文體色彩發生了變化,故譯文求真度較低。另一方面因為讀者可以快速獲取到信息而具有較強的社會務實性。
例4.后世方土效靈,人工表異,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p.201)
任譯本:In later times,however,ingenious designs began to appear in various localities,human craftsmanship exerted its specialities,and superior ceramic wares were produced,beautiful as a woman endowed with fair complexion and delicate bones.(p.135)
李譯本:Gradually,the use of clay was discovered and the art of pottery making was perfected,to form the best kind of porcelain,with a surface smooth as flesh,and of a consistency similar to jade.(p.195)
陶器取代了商周以降的木質祭祀器具,民居房屋和防御外敵的城垣也離不開陶器。隨著方法改進,陶器衍生出瓷器。這里用“素肌、玉骨”形容瓷器外觀,而“冰肌玉骨”贊美女子皮膚光潔,形體清新脫俗。原文的審美藝術不言而喻。這背后還蘊含了宋應星贊美“巧奪天工”的“人工”。任譯本再次直譯,力求恰如其分地再現原文的意蘊內涵,因此在“求真-務實”連續統上靠近“原文/作者”一端,語義求真度很高。而比擬的事物易為目標讀者理解,“fair complexion and delicate bones”還營造出一種東方審美情調,所以嫻熟地實現了求真性解讀和務實性處理。相反,李譯本踐行了意譯法,“smooth as flesh”和“of a consistency similar to jade”傳遞事實信息卻改寫崇尚美感的漢語文風,因而是在部分求真的基礎上更多地追求閱讀務實性,使譯文接近英語文本總體注重簡潔直白的風格(周領順,2014a:252)。
3.3 明喻及其風格
比喻是借助兩類事物的相似點,用本質不同的一類事物來形容和說明另一類事物,并由本體(被比喻的人、物或事)和喻體(用于打比方的抽象的或具體的事物)構成,二者同時出現或出現一個(譚學純等,2010:5)。本體和喻體被比喻詞連接并共同出現的比喻被稱為明喻。常用的古漢語喻詞“如”“若”“似”“猶”在《天工開物》中頻繁出現。由此可見,宋應星對技術的記敘并非毫無感情的羅列,而是廣泛運用了通俗易懂和舒緩節奏的明喻,避免了枯燥的論述。試看下例:
例5.凡取汁煎糖,并列三鍋如“品”字,先將稠汁聚入一鍋,然后逐加稀汁兩鍋之內。(p.67)
任譯本:In boiling the [clarified] juice for sugar,three cooking pots should be arranged to form a triangle [and used simultaneously].First the thick syrup [that has been obtained after boiling in the other two pots] is transferred into one pot,then more thin [uncooked] juice is gradually added into the two other pots.(p.127)
李譯本:To boil sugar,three pots are provided,which are arranged in such a way that one is on top and two are underneath,in triangular formation.The thick juice is boiled in the upper pot,while the thin juice is boiled in the two pots below.(p.187)
原文談到造紅糖的工序流程:將甘蔗反復壓榨取汁,再加入石灰令妨礙糖分結晶的雜質沉淀,浮在上面的汁便可熬糖。熬糖時將濃度稠的集中在一口鍋內,另外兩口鍋逐步加入稀汁熬制,變濃稠后轉入第一口鍋。宋應星將三口鍋的位置比喻成書面文化“品”字,體現出提升工農業地位的出發點,又顧及受眾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原文的畫面感強,閱讀者可以輕松地汲取實學知識和審美快感。眾所周知,漢字是表意文字,“品”字的多重內涵無法在從屬拼音文字的英文中找到對應或貼切的單詞。恰如“務實的前提是因為‘求真’之無力”(周領順,2014a:30),在無法全部實現原文語義和形式之真的情況下,兩個譯本均以務實為上策,即巧妙地使用大同小異的“form a triangle”和“in triangular formation”仿譯出主要內容,某種程度上彌補了語言形式和風格韻味的流失。顯而易見,調整后的譯文流暢清晰,能夠有效地在目標受眾中實現務實效果。
例6.密布地上,微以土掩之,頭尾相枕,若魚鱗然。(p.63)
任譯本:These are laid on the ground close to each other and lightly covered with earth,the ends of the sections overlapping like fish scales.(p.125)
李譯本:These again are covered with earth,being placed close together,lengthwise,with the end of one superimposed over the end of other,like fishscales.(p.184)
此處描述造白糖和紅糖的甘蔗的種植辦法:確保每段約五六寸長排在地上,上面覆蓋少量的土,并使每段如同魚鱗狀一樣頭尾相疊。宋應星借助明喻,用“若”連接本體(糖蔗的相疊)與喻體(魚鱗)。毋庸置疑,這一修辭格營造的畫面生動形象,明代讀書人可以通過熟知的意象了解實際學問。任譯本和李譯本對“若魚鱗然”的翻譯有異曲同工之處,比喻的事物為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下的讀者所熟知,譯文的社會接受度自然有所保證。兩個譯本均用“like”作喻詞表明它們在原文形式方面講究求真。若進一步探究,任譯本的“overlap”指“to cover something partly by going over its edge”,李譯本所用“superimpose”表示“to put especially a picture,words,etc.on top of something”②。兩相比較,后者可能讓讀者誤以為每段荻蔗上下放置,與魚鱗狀沒有任何關聯。如是,任譯本的文本求真度再次高于李譯本,譯者行為合理度也略勝一籌。
4.0 《天工開物》英譯者行為總結和成因探析
綜上,任譯本完整地迻譯了上述引用、擬人和明喻。語言風格與修辭格相互依存,修辭翻譯與文采和風格傳達效果也成正比。任譯本堅守語言性求真,有助于引導讀者感悟《天工開物》的復合文本特征和多元價值;譯文直譯加注,恰如其分的用詞和語境連貫也確保了交際的有效性。整體而言,任譯本對修辭格及其風格的傳譯在“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上為合理度找到了支點。相比之下,李譯本趨向“讀者/社會”一端,呈現出較高的社會務實度。換言之,譯文簡明易懂,卻淡化了修辭形式以及與之伴隨的語體色彩和文學性。正如描寫和解釋是推動翻譯研究朝縱深方向發展的助推力,“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強調在描寫的基礎上重點解釋譯者行為背后的動因(周領順,2014a:23)。《天工開物》中修辭格及其風格英譯差異的主要原因可以總結如下:
4.1 譯者主觀因素
首先,譯者身份和研究專長不同。任以都③曾就讀西南聯大歷史專業,后因抗戰爆發而負笈美國,直至在哈佛女校獲得博士學位,之后與先生孫守全均執教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治學明清經濟史。這種離開故土但對民族身份保持強烈認同感的華裔飛散譯者身份使她具有良好的雙語文化素養,重視語言的情感和價值觀念,又知悉英語讀者的文化預設和閱讀期待(汪世蓉,2017)。因此可以解釋在大多數情況下,任譯本對原文修辭格及其風格的翻譯和傳達游刃有余,取得了語義求真和可讀性務實的統一。比較之下,李喬蘋專攻化學專業且生平投身于自然科學教學和研究,相對在文史哲領域不見長。這在無形之中會影響他對修辭立意及文學性風格的把握,或將之轉換成偏向社會務實的表述和平實的文風。此外,他的英文自學習得,且長期在國內生活和教學多少會影響外語使用的敏感度和精確度(如例6中的“superimpose”)。其次,譯者的翻譯動機和讀者定位有別。任譯本的譯者序交代譯者因為研究中國經濟史而關注《天工開物》,他們預設的對象包括西方科技史研究人士,更針對美國大學中對亞洲文化感興趣的一般學生(Sung,1966:i;張朋園等,1993)。這種立場很大程度上確保譯文求語言之真,以盡可能客觀地再現與科技“相矛盾”的修辭格和文學性文字。李喬蘋親歷抗日戰爭而發奮弘揚中國古代科技文明,其生平無不致力于此(趙慧芝,1991)。彼時李約瑟等中國科技史研究人士對待科技典籍的態度是選擇繞開與西方科技文本不符的部分(吳國盛,2016),李喬蘋主觀上為滿足西方科技史研究學者的期待,而會不自覺地基于務實目標改寫語體色彩和漢語重古雅的風格,從而影響到文本求真度。
4.2 外部客觀因素
首先,漢語的異質性彰顯譯者意志。盡管漢語修辭格具有普遍的詩學和美學特征以及普世價值,但是與英語不屬相同的語言體系,因此有時無法對等地將之移入英語文化語境。這時求真無力或無解,譯者只能在盡可能忠實“作者/原作”的情況下做出調整,優先選擇交際信息的有效傳遞(如例2和例5)。其次,翻譯發起者對譯文務實性施加了影響。任譯本是純粹的自發行為,外部制約因素少,因而在處理語言性求真和社會性務實的關系方面掌握了主動權。李譯本為我國臺灣的教育部門和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發起,且由臺灣前“教育部”部長張其昀贊助出版,并被列入傳播中華文化外文叢書(Sung,1980:i)。這一“官方”弘揚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出發點下意識地驅使李喬蘋積極地書寫中華民族科技之輝煌,并使與此無直接關聯的修辭格與講究表述客觀和信息直白的英語科技文體適應,以實現打造科技典籍與西方科技經典相媲美的務實目標。
5.0 結語
宋應星疾呼恢復農事,革新科舉和關注實學,而在《天工開物》中系統地記錄了農業和手工業兩大領域的18個部門的生產技術。為了使著作和諫言得到文人階層乃至統治者的認可,他遵循做文章的主流規范,使用增強語言感染力的修辭格。本文從譯者行為批評視角描述和對比了任譯本和李譯本對引用、擬人、明喻的翻譯及相關文學性風格的再現,發現任譯本在“求真-務實”連續統上平衡了“作者/原文”和“讀者/社會”,譯文質量和譯者行為合理度較佳;在部分求取語義和風格之真的前提下,李譯本重視特定專業讀者的接受和閱讀期待。窮根溯源,譯者身份和研究專長、翻譯動機和讀者定位以及英漢語言文化差異和贊助者等因素影響了譯者行為。而通過調查反映譯本接受情況和影響力的學術書評和被引率④,任譯本為不少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的學者關注,李譯本難以望其項背。基于此,本文認為科技典籍英譯既應秉承社會接受的務實理念,也應以包容的姿態傳遞文化要素之真,以深入挖掘作品的多元價值,使之肩負起與文史哲典籍共同實現讓中華文化“走出去”這一宏大目標的重任。
注釋:
① 為了節省篇幅,原文和譯例僅標出頁碼,下同。
② 參見Cambridge Dictionary: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
③ 各種資料均表明任以都是《天工開物》翻譯的主力,其借助理工科出身的孫守全的幫助和身份來增強譯文準確性和譯本權威性。
④ 截止2019年6月1日,任譯本斬獲11篇外文書評,谷歌學術顯示被引142次。比較之下,李譯本的書評闕如,學術引用率屈指可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