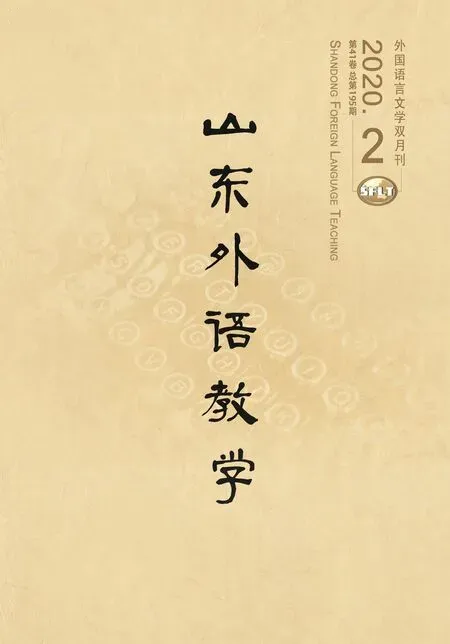夢的再解析:漢英對照版《紅樓夢》的內副文本研究
商瑞芹 劉曌龍
(南開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071)
1.0 引言
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迄今為止,共有三種英文全譯本,分別為邦斯爾神父(Reverend Bramwell Seaton Bonsall)譯本、楊憲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夫婦合譯本、霍克斯(David Hawkes)和閔福德(John Minford)翁婿合譯本。其中邦斯爾神父的譯本RedChamberDream完成于上世紀50年代,但是其電子版直至2004年才由香港大學圖書館以在線瀏覽的形式發布,至今仍未成書出版。楊氏夫婦的全譯本ADreamofRedMansions分三卷,外文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前兩卷,1980年出版第三卷。霍閔二人的五卷全譯本TheStoryoftheStone則由英國企鵝出版集團分別于1973 年、1977 年、1980 年、1982 年和 1986 年出版。其中前三卷為霍克斯翻譯,譯文內容為《紅樓夢》前80回;后兩卷則為閔福德翻譯,譯文內容為《紅樓夢》后40回。有學者曾運用語料庫對這三種英文全譯本進行統計和分析,指出三種譯本不同的譯者風格(劉澤權等,2011)。由于篇幅限制及研究側重點的關系,本文聚焦于霍閔譯本的研究。
在這三個英文全譯本當中,霍閔譯本是第一個譯者均為英國漢學家并正式出版的譯本,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霍閔譯本自問世以來,其充滿魅力的翻譯藝術和對審美要素的創造性處理也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黨爭勝 2012:3),國內學界對此譯本的正文本研究已具備一定規模,蔚然可觀。其中,既有對譯本中所涉及的中華文化內容翻譯的研究,如佛教文化(錢亞旭、紀墨芳,2013)、服飾文化(張慧琴、徐珺,2013)、中醫藥文化(王銀泉、楊樂,2014;王才英、侯國金,2019),飲食文化(黃勤、陳蕾,2015)等,也有對具體語言內容翻譯的研究,如人名(林克難,2000)、稱謂語(潘明霞,2002)、習語(劉澤權、朱虹,2008;劉曉天、孫瑜,2018),以及詩詞曲賦(王宏印,2001)。在翻譯策略和譯者研究方面,有學者對其翻譯策略及技巧進行探討(左飚,2009),還有學者采用實證方法研究其譯者的文體與風格(馮慶華,2008)。可見,該譯本的正文本研究參與者眾多,研究領域廣泛,方法多樣,不一而足。
相比之下,從副文本的角度對該譯本的研究則顯得單薄。目前國內研究中,有學者從霍譯本第一卷的封面和序言兩方面來考察副文本對霍譯本研究的意義(李雪,2016),也有從霍譯本的前三卷的副文本來探討霍譯本的產生、傳播和接受,進而加深讀者對于譯者和譯本的認識(李菁、王煙朦,2015)。最新的研究成果則是通過分析閔譯本的副文本成分來發掘譯者閔福德對中國文學及文化傳統的認知模式,并說明這種認知模式對中國傳統典籍翻譯的影響(楊柳,2018)。譯本的副文本雖已漸成為《紅樓夢》翻譯研究的一個新視角,并日益引起譯學界的重視,可是我們不難發現:當前的研究要么集中探討霍譯本的副文本,要么單獨探討閔譯本的副文本,未能將二者視作一個有機的整體進行審視。而霍閔五卷本譯文是對《紅樓夢》整部小說的完整英譯,閔福德曾是霍克斯的學生,其在《紅樓夢》后40回的翻譯過程中反復推敲學習霍克斯的翻譯,努力使其譯作風格與霍克斯的保持一致,就連霍克斯本人也承認二人的譯作達到了完美的結合(朱振武、閔福德,2017:51)。霍譯本和閔譯本具有時間先后順序和風格上的繼承性。因此,對此譯本副文本的考量也應該將五卷本的內容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而不應該人為地割裂開來。再者,現有的研究集中在通過副文本因素來進一步探討譯本和譯者,而對于副文本所能揭示的其他重要問題,如出版社的意圖、目標讀者的定位、霍閔譯本之間的關系等,其探討程度明顯不足。縱覽當前的相關研究,副文本理論未能充分發揮其在《紅樓夢》翻譯研究領域應有的作用。
因此,本文以熱奈特的副文本理論為依據,對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漢英對照版《紅樓夢》的副文本成分進行分析,以揭示其中蘊含的譯者的翻譯思想、校勘者的目的、出版社的意圖以及對目標讀者的定位等豐富的信息,為翻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視角,并促進《紅樓夢》翻譯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2.0 副文本理論與翻譯研究
“副文本”這一概念由法國當代敘事學家熱奈特 (Gérard Genette)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指的是那些伴隨著正文本一起出現的語言或其他材料,如作者姓名、書名(標題)、前言、插圖等。副文本環繞并擴展了正文本,為了呈現(present)正文本,確保正文本在世界的“在場”(presence),使得其以書的形式得以接受和消費(Genette,1997:1)。這說明副文本具備形式的多樣性,對正文本起到補充、強化和促進其傳播的作用。熱奈特進一步指出,副文本相當于“門檻”,或是“前廳”,讓人要么踏足深入要么轉身離開(Genette,1997:2)。由此可見,副文本的作用是在譯者、譯本和讀者之間起到了橋梁紐帶似的連接作用。熱奈特認為副文本與正文本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共生關系,無論是正文本,還是副文本都不能各自獨立存在(Genette,1997:3)。
熱奈特根據副文本相對于正文本所處的空間位置,將副文本分為內副文本(peritext)和外副文本(epitext)兩大類。內副文本同正文本的位置一樣,都處于書卷的內部,包括封皮、標題頁、作者姓名、前言、序跋、題詞、獻詞、致謝以及注釋等。外副文本是那些位于書卷外部的且與正文本相關的信息,包括訪談、講話、私人日記以及信件等。內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共享了副文本的全部空間,可用如下公式表達:副文本=內副文本+外副文本(Genette,1997:2)。
熱奈特并沒有對翻譯副文本進行闡釋,但其副文本理論與翻譯研究卻具有較大的相關性。因為一個完整的翻譯文本是由譯本的正文本和各種翻譯副文本因素組成的,沒有對翻譯副文本的深入研究,也就沒有完整的翻譯研究。因此,國內外學界對副文本理論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探究其對翻譯研究的意義。國外學界中,兩部文集的出版標志著副文本理論逐漸進入翻譯研究的視野。這兩部文集分別是 《翻譯邊緣:翻譯中的副文本元素》(TranslationPeripheries:ParatextualElementsinTranslation) 和《翻譯中的文本、外文本、元文本和副文本》(Text,Extratext,MetatextandParatextinTranslation)。《翻譯邊緣:翻譯中的副文本元素》在翻譯研究中引入副文本這一新的研究模式,且較為全面地呈現了翻譯副文本研究中的代表性因素(張玲,2013:79-80)。《翻譯中的文本、外文本、元文本和副文本》分別探討了副文本中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動機及其操控、出版商對副文本運用、故事與詩歌中的副文本三個方面,對副文本的文化、政治、意識形態和商業功能加以關注,是翻譯中副文本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黃艷群,2015:21-24)。國內學界對副文本的研究在經歷了“發展初期”“穩步增長期”“快速激增期”三個階段后,其研究發展趨勢呈現出從文學領域轉向語言領域,再延伸至翻譯領域的特點。近五年副文本的研究熱點和前沿漸變為翻譯研究(殷燕、劉軍平,2017:26)。由此可見,在譯學界,副文本研究已漸成為翻譯研究的研究課題,其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為翻譯研究注入了新的發展活力。從副文本的角度對漢英對照版《紅樓夢》進行研究,能洞悉以往研究未能關注到的新問題,進而豐富《紅樓夢》的翻譯研究。
3.0 漢英對照版《紅樓夢》的內副文本
2014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霍克斯、閔福德的《紅樓夢》英譯本,仍為五卷,前三卷為霍譯本,后兩卷為閔譯本。與之前企鵝出版集團版本不同的是,此次外教社采用漢英對照的形式出版。書的正文采用相同的體例,左頁為漢語原文,右頁為英語譯文。
當一本圖書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時候,其封面會給讀者第一視覺沖擊。讀者對書籍進行粗略翻閱,不難發現其中的標題、版權頁、插圖、獻詞、以及序言等副文本成分。在文本閱讀中,副文本發揮著“門檻”的作用,帶領讀者深入文本。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和研究關注重點等原因,本文探討的是漢英對照版《紅樓夢》的內副文本成分,發掘其所蘊藏的豐富涵義。
該漢英對照版《紅樓夢》5卷均為16開本,其內副文本存在于漢英對照正文的不同位置。我們不妨繼續采用熱奈特相對位置的劃分標準,對內副文本加以細分。處于漢英對照正文之前的內副文本有封面、插圖、標題頁、版權頁、獻詞、目錄、拼讀說明、序言、校勘說明等,我們可稱之為“前內副文本”;在正文之后的有附錄和封底,我們稱其為“后內副文本”。在漢英對照正文之中出現的內副文本則為“中內副文本”,如插畫、不同字體顏色以及校勘符號。由于封面、封底和書脊三者共同構成了書的封皮,具有一定的整體性,不宜分開進行討論,因此我們將此三者放在“封皮設計”中進行討論。其余的內副文本成分我們按照前內副文本、中內副文本和后內副文本的順序分別進行探討。
3.1 封皮設計
該套圖書封皮為朱砂紅色,裝幀精美,質感溫馨。每冊封面右上角的菱形圖案內為漢語書名、作者和書卷編號。左上角每卷的書名采用漢英雙語,每卷書的漢語書名均使用漢語四字格進行表述:第壹卷為《枉入紅塵》,第貳卷《海棠詩社》,第叁卷《異兆悲音》,第肆卷《絳珠還淚》,第伍卷《萬境歸空》。封面正中為著名紅樓畫家戴敦邦的插畫,五冊書的插畫內容各不相同,分別對應的是第三回“接外孫賈母惜孤女”、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第七十五回“賞中秋新詞得佳讖”、第八十七回“感秋聲撫琴悲往事”和第一百二十回“甄世隱詳說太虛情,賈雨村歸結紅樓夢”。五幅插畫用筆細膩,采用“白描”技法將人景融合,充滿中國文化元素,與小說內容密切相關,且從時間上將整部小說加以貫穿。插畫試圖構建《紅樓夢》這一中國古典小說的藝術形象,吸引讀者閱讀文本。每冊封面右下角為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中英文名稱、社標及網站。封底正中為一獸面鋪首銜環圖案,呈現一定的立體感。獸面鋪首多為中國古代官府以及縉紳、富戶大門的裝飾物,發揮著辟邪的功能(解玉峰,2018:57)。該圖案和封皮的朱砂底色構成了門的意象,與文本中榮國府的“獸頭大門”相吻合,其正文本內容恰如門內之物,讀者唯有叩開大門方能探尋其中的萬千景象。每卷書脊上的文字均為漢英對照版,從上至下依次為“漢英對照”四字、小說名稱及分冊卷號、分冊書名、出版社名。每卷書的前勒口(封面的延長內折部分)對二位譯者以及校勘者范圣宇做了簡介,均采用雙語形式,譯者和校勘者的位置分明,讓讀者容易辨別。讀者因而會注意到文本校勘者范圣宇的存在。每卷書的后勒口(封底的延長內折部分)列有整本小說以及分卷書名,也采用雙語形式,讀者因而可以對整套圖書的結構和內容有個大概的了解。編輯者和設計者的信息也在分卷書名下出現。
可見,該套圖書的封皮設計突出其漢英對照特色,紅樓插畫以非語言的形式重現該小說經典章節內容,發揮著裝飾書籍和闡釋文本的雙重作用。同時,校勘者、編輯者以及設計者的身份也通過封皮設計得到了彰顯。
3.2 前內副文本
漢英對照版《紅樓夢》的前內副文本包括插圖、書名頁、版權頁、獻詞、回目、拼讀說明、序言以及校勘說明。
每冊書緊隨封面之后為同一張紅樓圖畫,《紅樓夢》的主要人物之一賈寶玉現身其中,該圖采用暗灰顏色勾畫,影影綽綽,人景合一,恍如夢中,契合小說“夢”這一主題。漢語書名和版權頁在同一張書頁上,書名頁采用豎版,包含小說名、分卷名、作者姓名、譯者姓名、校勘者姓名,出版社。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社除了上海外語出版社外還出現了“企鵝出版集團”,版權頁對此進行了說明:“企鵝出版集團授權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在中國境內銷售”。由此可以看出這兩家出版社之間的相互聯系和共同的出版目的。
譯者的獻詞位于英文書名頁的背面。獻詞宣示了作者和某些人或團體之間存在的關系(Genette,1997:135)。五卷書的獻詞對象各不相同:第一卷是Dorothy和Jung-En,即劉程蔭和劉容恩,此夫婦二人本為天津人氏,是霍克斯的朋友,尤其是劉程蔭對霍克斯的譯文提供了極大的幫助(范圣宇,2019)。第二卷是R.C.Z.,即Robert Charles Zaehner教授,此人讀過霍克斯第一卷譯文后,說過“樂見泣涕漣漣,遠勝言笑晏晏”(Hawkes,2014b:7),霍克斯的第二卷就是獻給這位知音讀者Zaehner教授的,表達對其深切的悼念之情。第三卷是Jean,其為霍克斯的妻子。而閔福德的獻詞對象均為其家人。相比之下,霍克斯的獻詞對象更加廣泛多樣,除了家人外,還包含朋友、譯文讀者等。獻詞為我們深入了解兩位譯者的個人生活,研究他們《紅樓夢》的翻譯過程提供了可信的材料。
每卷書的回目同樣采用漢英對照的形式。讀者可以清楚看到漢英回目各自的特點及差異。回目后有一拼讀說明,通過與英語發音進行類比,介紹了漢語拼音聲母和韻母的發音和拼讀規則,并通過小說中人物的名字加以說明。此拼讀說明五卷本中均有,但無漢語譯文,可知該拼讀說明面對的只是西方讀者群。
同企鵝出版集團出版的第一卷相比,漢英對照版第一卷多了閔福德撰寫的漢英對照版《紅樓夢》序言以及范圣宇撰寫的校勘說明。閔福德的此篇序言寫于霍克斯去世之后,其對該套圖書具有重大的意義。首先,作為譯者之一,閔福德具有一定的權威地位,其對漢英對照版的評價無疑會對圖書產生巨大的推介作用。其次,閔福德回顧了霍克斯在譯《紅樓夢》的底本選擇問題,提及研究霍克斯所依據底本的重要參考材料《紅樓夢英譯筆記》,并明確提出霍克斯的版本研究是為其翻譯服務的(Hawkes,2014a:2),這有助于學界正確理解霍克斯的翻譯方法和翻譯理念。再次,閔福德盛贊了范圣宇的校勘工作,回顧了二者之間愉快的合作,這表明譯者和校勘者之間有充分的信任和有效的溝通,這是此版本的《紅樓夢》能順利問世的關鍵原因之一。范圣宇的校勘說明則詳細論述了中英文各自依據的底本和參考材料,并對中文使用的校對符號分三種情況進行了說明。范指出了校勘的目的,即“為讀者提供一個可靠的漢英對照本,同時如實反映出霍克斯先生在翻譯過程中到底做了哪些增刪改動,為翻譯研究者和愛好者提供參考”(Hawkes,2014a:7)。同時,校勘說明中也明確了漢英對照版的讀者對象為“研究漢英翻譯與學習英語的中國讀者”(同上),但是因為該版圖書采用英、漢雙語對照,其實際讀者群不僅僅局限于中國讀者,對中國古典文學、文化感興趣的西方讀者、漢學家們都可囊括在內。而企鵝出版集團上世紀出版的霍、閔譯本僅為英文文本,霍克斯也明確指出企鵝版所面對的讀者群是“英語世界的讀者”(Hawkes,2014a:4)。可見目標讀者群的變化,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發起此套圖書出版活動和邀請范圣宇先生進行校勘工作的重要原因。閔福德的序言和范圣宇的校勘說明與該套圖書密切相關,對譯者研究、霍譯底本研究及校勘工作、漢英對比研究、讀者定位等方面均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可以說是正確打開漢英雙語版《紅樓夢》大門的“金鑰匙”。
霍克斯在第一卷中不吝筆墨,用了21頁的篇幅寫了 “譯者序”(Introduction),該序言內容豐富,包含多方面的內容,列舉了自己的學術參考材料(Hawkes,2014a:40),其翻譯原則和翻譯策略、以及翻譯所依據的底本:為追求一致性,霍譯文的底本主要采用的是高鶚的版本(Hawkes,2014a:20,38),范圣宇的校勘說明對此進行了進一步說明 “中文部分以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豎排版(啟功校注)為底本” (Hawkes,2014a:7),人民文學1964年出版的即是程乙本。根據序言和校勘說明可知,霍閔譯本的主要依據底本就是程乙本。這些內副文本信息為正確解讀霍克斯的譯文底本、評價其譯文提供了依據。霍克斯在第二卷的“preface”(序言)當中,介紹了第二卷的小說情節,指出自己對文本進行的“再創造”,即對原文中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在進行版本考證后,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修改(Hawkes,2014b:5),同時說明了其修改的目的:對于西方讀者的關照(Hawkes,2014b:6)。霍克斯所依據的底本及其創造性的修改工作這兩方面保證了其譯文的和諧一致。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楊憲益、戴乃迭《紅樓夢》譯本第一卷的譯者前言中,楊戴夫婦指出其譯本所采用的底本前八十回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9月影印的上海有正書局1911年前后的石印本,后四十回譯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重印的1792年活字本(Yang Hsien-yi &Gladys Yang,1978:ix)。楊譯本前八十回的底本是戚蓼生的抄本,后四十回的底本是程乙本,這是兩種不同的《紅樓夢》版本。對兩部《紅樓夢》英文全譯本的副文本進行解讀,可知霍閔譯本比楊譯本在底本選擇上更具備統一性和一致性。霍克斯明確承認其對底本進行的適當修改充分體現了其對目標讀者自覺肩負的譯者責任,同時為范圣宇的校勘工作提供了依據和線索。霍克斯在第三卷前言中說明了此卷的兩個特點:次要角色的發展和文本矛盾沖突的增多,并對二者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進行了說明(Hawkes,2014c:10-12),這再次說明霍克斯對底本進行嚴謹的考據,體現了其認真勤勉的翻譯態度。閔福德第四卷的序言記敘了其在北京恭王府的尋夢之旅,對高鶚生平及其編輯后四十回《紅樓夢》的研究(Minford,2014a:4-14)。在第五卷的序言里,閔福德敘述了《紅樓夢》的結局并對《紅樓夢》主題進行了挖掘(Minford,2014b:4-6)。可見,閔福德的序言集中在對小說背景、內容和主題的分析,重點是對文本內涵的闡釋 (楊柳,2018:128)。序言主要功能是保證文本能夠被正確閱讀,即為什么要讀這本書,怎樣閱讀此書(Genette,1997:197),霍閔二人的序言對讀者正確閱讀理解此部小說可謂功不可沒。
前內副文本在漢英對照版《紅樓夢》內副文本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形式最為多樣,也最能揭示各類豐富的信息。插圖的使用給圖書增添了濃厚的藝術氣息,強化了小說主題,有助于吸引讀者。涵蓋多種角色各種信息的書名頁和版權頁,實為譯者、讀者、出版參與者各自利益和目的的交匯之處。獻詞能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譯者的生平和翻譯歷程,豐富對譯者的感性認識。閔福德的第一卷序言和和范圣宇的校勘說明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對正確閱讀漢英對照版《紅樓夢》、明確目標讀者進行了準確的說明。五卷書中的譯者序言從小說的整體和部分兩個層面,輔助和引導讀者正確解讀文本。
3.3 中內副文本
漢英對照版《紅樓夢》的中內副文本包括插圖、校勘符號和不同的字體顏色。這些副文本與漢語原文和英文譯文結合在一起,使得這部小說以更豐富的形象展現于讀者面前。
在每回漢語回目下均有一副戴敦邦的插畫,插畫的內容凝練反映了該回的主要內容。圖文結合,相得益彰,濃厚的中國文化信息撲面而來。插畫繼續發揮其裝飾和輔助文本閱讀的雙重作用。
校勘符號只出現在前三卷的漢語文本之中。根據范圣宇的校勘說明,讀者能夠很容易明白這些校勘符號的含義。校勘符號并非可有可無的附屬物,它們貫穿三卷本的始終,還原底本,為讀者進行漢英比較提供了可靠的參照。例如,在第四十回結尾部分,漢語文本中“只聽外面亂嚷嚷的,不知何事”這句話,用方括號“[ ]”將其括出,表示霍克斯未翻譯此句。因為無論是四十回末尾,還是四十一回開頭都沒有論及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霍克斯選擇不譯此句,這樣其譯文在情節上更趨合理,不會顯得突兀。校勘符號的使用能反映出霍克斯創造性的改寫的具體之處,體現了其對前八十回小說版本的深入研究,同時也有利于讀者進行雙語文本的對比,發現二者之間的特殊的對應關系,從而進一步理解霍克斯的翻譯策略和理念。
漢英文本中,所有的韻文(詩、詞、曲、賦)、俚語、諺語、謎語均采用紅色字體,惹人注目,這突出了這些特殊文體在整部小說中的重要地位,是時代文化精神生活的反映,也是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蔡義江,2007:1-10),讀者可以通過漢英文本感受到各類韻文的不同特點,感受其音、形、意三美,進而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多姿多彩的內容和形式有所了解,同時紅色字體能讓讀者意識到這些特殊的文體形式在整部小說的重要地位,加深對小說情節和主題的理解。
中內副文本輔助呈現正文本內容,與正文本一道成為小說的表現形式,豐富讀者的閱讀體驗,使文本更具形象立體感,突出其中的古典韻味,并還原底本,同時向讀者展示中國古典文學搖曳多姿的文體,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豐富其閱讀體驗。
3.4 后內副文本
漢英對照版《紅樓夢》的后內副文本為每卷書的附錄。
霍譯本的附錄中包含其對紅樓夢曲和紅樓夢判詞的解讀、對中國律詩、骨牌和詩謎的介紹、以及《紅樓夢》相關人物的考證,霍克斯試圖構建小說的文化背景,在這部經典小說和西方讀者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閔譯本的附錄中則包含程本序言對中國文化特有的事物如“八股文”“琴和知音”的介紹。五卷本的最后都附有人物簡介及兩府族譜。可見,后內副文本和前內副文本首尾呼應,共同構建《紅樓夢》的歷史和文化脈絡,豐富讀者的閱讀體驗。這些副文本成分使得霍閔兩位漢學家對《紅樓夢》主題、人物的理解得以彰顯,代表了《紅樓夢》海外研究的重要成果。
與企鵝版相比,漢英對照版的后內副文本都提供了相應的漢語譯文,因而更多的漢語讀者能理解兩位譯者的文化視角,感受到中國文化對異語讀者所產生的獨特吸引力。
漢英對照版《紅樓夢》的后內副文本是對前內副文本內容的補充和擴展,提供了更為詳實的小說歷史文化背景,拉近了讀者與中國文化之間的距離。霍閔二人作為文化協調者,在其對中國文化充分理解認同的基礎上,為進行有效文化溝通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使其譯文具備促進中西文化雙向交流的重要價值。該版《紅樓夢》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可以幫助其研究漢英翻譯和學習英語;對于西方讀者來說,能讓其領略到中國古典文學的魅力及所蘊含的燦爛中華文化,激發其學習漢語的熱情,契合了當前國際上興起的“漢語熱”“中國文化熱”,該圖書的出版為中國文化走出國門提供了一種可供借鑒的模式。
4.0 結語
副文本闡釋并豐富了正文本的含義,同時也揭示出正文本自身所未蘊含的內容。本文以熱奈特的副文本理論為基礎,對漢英對照版《紅樓夢》的內副文本進行分析,發現了其中所蘊含的大量信息。其中較為明顯的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雙語對照且更加注重中國傳統藝術成分的運用,如插畫、封面書法字體的使用,以此凸顯小說的主題的中華文化屬性。第二,出版社的參與及其意圖。霍閔譯本這次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使《紅樓夢》的一個經典的英譯本以新的形式再次呈現。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相關信息在內副文本中多次出現,體現了其市場營銷手段和擴大銷售的目的。第三,校勘者的目的以及讀者定位發生的變化。校勘者及其校勘說明的出現,為讀者進行漢英對照閱讀,或進行底本考據提供了依托,同時明確指出霍閔譯本所依據的主要底本,體現其底本的相對一致性。校勘者對漢英對照版的讀者群進行了明確說明,與上世紀單單面向西方讀者的英文版相比,漢英對照版的讀者群顯然更加多樣廣泛。第四,譯者翻譯思想的繼承性。二位譯者的翻譯思想在內副文本中既相互參照,具備前后歷史繼承性;同時,副文本也體現出兩位譯者對中國文化充分的尊重和深層次的認同感。
《紅樓夢》翻譯研究,既屬于紅學,又屬于翻譯學,是一種交叉性的研究(馮全功,2015:142)。漢英對照版《紅樓夢》的內副文本研究為《紅樓夢》翻譯研究帶來新的研究話題,是對《紅樓夢》及其英譯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視角,拓寬了《紅樓夢》翻譯研究的研究范圍,為其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當然,關于漢英對照版《紅樓夢》的內副文本研究,仍有一系列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根據相關統計,該套圖書出版至今,單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書店這一家實體書店的銷售量已達340套①。那么內副文本對此套圖書的銷售和讀者接受產生了哪些實質性的影響?副文本包括內副文本和外副文本,本文只考查了漢英對照版的內副文本,那么其外副文本有哪些?二者之間又存在怎樣的關系?這些問題的解答都有待于日后更為深入系統的研究。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了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中文系范圣宇博士的幫助,在此表示感謝!)
注釋:
① 該數據為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書店門市部提供,銷售量統計截止日期為2019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