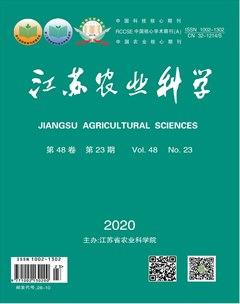旅游扶貧開發之于鄉村空心化:機遇還是挑戰?
褚玉杰 王思雨 周嫚
摘要:鄉村空心化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現實問題。現有研究普遍認為,旅游扶貧開發是改善鄉村空心化的重要機遇。然而,旅游扶貧并非“萬能藥”,在精準扶貧戰略下,旅游扶貧開發對于鄉村空心化的作用不僅需要考慮機遇,更需要具體結合村落的資源稟賦、發展情況等客觀條件來考察其帶來的挑戰。以陜西省西安市藍田縣簸箕掌村為例,通過實地調查,結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的理論框架,對旅游扶貧對于鄉村空心化的作用進行探討。研究發現,在簸箕掌村,旅游扶貧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鄉村空心化,如出現“周末經濟”,但其成效受到旅游地發展階段性困境、旅游業季節性特征以及社會資本流失等諸多限制性因素的影響,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其鄉村空心化的問題,可能是“短暫的機遇”。只有貧困村落旅游發展保持活力才會出現長效的人口回流現象,進而可持續地緩解貧困村落的空心化現象。
關鍵詞:旅游扶貧;鄉村空心化;旅游地生命周期;社會資本;機遇與挑戰
中圖分類號: F323.8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20)23-0013-06
在黨的十九大上,脫貧攻堅被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贏的三大攻堅戰之一,當前扶貧開發已成為貧困地區統攬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點工作。從實際情況來看,大多數貧困地區集中在廣大鄉村,這些地方不僅面臨著貧困問題,同時受到鄉村空心化的嚴峻挑戰。因此,長期貧困現象不僅嚴重制約著鄉村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還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鄉村青壯年人口的大量流失,使貧困鄉村進入“貧困—空心化—貧困”的惡性循環,這種持續存在的貧困和空心化重疊現象,是當前扶貧開發中面臨的主要困難之一[1]。因此,改善和緩解貧困地區的鄉村空心化問題儼然已經成為扶貧工作的關鍵之一。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鄉村旅游成為我國城市居民緩解快節奏生活壓力的重要選擇,這為貧困鄉村地區的空心化治理帶來了全新的機遇。“十三五”規劃中也指出,力爭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帶動建檔立卡貧困村和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致富。已有研究表明,旅游產業可以帶動農村居民在本地就業,主要通過創造新的就業崗位、調整升級產業結構和提升基礎公共服務水平等方式[2]實現。可見,作為一種能夠吸引農民“本地就業”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式,鄉村旅游可有效刺激外出人口回流,進而成為許多貧困鄉村發展社會經濟,推動鄉村城鎮化,最終可持續緩解當地空心化問題的重要途徑[3]。然而,現有研究主要從宏觀層面闡述旅游扶貧開發給鄉村空心化帶來的機遇,卻忽視了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的作用并非是單向的,即旅游扶貧開發究竟是鄉村空心化的機遇還是挑戰尚存在爭議;同時單純從宏觀層面進行研究,難以窺見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施加的實際效應。因此,本研究擬從微觀層面探討旅游扶貧開發在鄉村空心化實踐中的作用,旨在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的切實影響。
1 研究現狀
1.1 鄉村空心化的概念
作為當前農村地區廣泛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鄉村空心化是在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復雜產物。關于鄉村空心化的內涵,研究者們尚未達成一致的觀點。
田新強指出,鄉村空心化表現為社會現象和空間現象的復合,本質上是特定鄉村地域經濟社會功能的整體退化[3]。鄉村空心化指由于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舊,以及城鎮化引起的“人走屋空”導致村莊用地規模擴大,閑置廢棄加劇的一種“外擴內控”的不良演化過程;其主要特征包括村莊內出現大量閑置或廢棄房屋致使村莊“外擴內控”,鄉村人口的城鎮化轉移,土地閑置等[3-4]。
相關學者提出,應綜合多種角度來定義鄉村空心化,劉杰認為,鄉村“空心化”包括5個方面的內涵,即人口、地理、經濟、基層政權和公共性意義上的“空心化”[5]。崔衛國等則表示,鄉村空心化體現在鄉村人口、宅基地、產業和基建4個層面[6]。杜緩緩強調,人口學角度的鄉村空心化概念主要表現集中在人口學方面,如農村人口總量減少、流動人口的爆炸性增加、人口結構以留守老年及兒童為主等[7]。
鄉村空心化研究中人口層面的空心化研究是學者們共同關注的焦點,更是解決空心化問題的重難點。隨著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鄉村勞動力不斷地流向擁有更多就業機會、工資水平更高的城市,導致鄉村區域大量土地被拋荒撂荒,鄉村的基礎公共建設處于停滯不前狀態,留守人口生活困苦和鄉村傳統文化持續衰落等問題日益加劇,最終演變成嚴重的鄉村空心化問題。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鄉村空心化指在城鄉資源分布不均的背景下,鄉村適齡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導致鄉村人口結構以留守人口為主、大量房屋閑置的現象。
1.2 旅游扶貧與鄉村空心化
旅游扶貧概念存在3種觀點,一是有利于貧困人口發展的旅游,核心是貧困人口在該類項目中獲得了多少凈利益;二是減貧的可持續旅游,即有計劃地加強旅游在提高生活水平標準方面的能力,以及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擴大旅游發展[8-9];三是旅游扶貧,即通過在擁有旅游資源的貧困地區發展旅游產業,帶動當地經濟社會進步,促進貧困問題的解決,進而推動當地可持續發展[9]。旅游扶貧不僅是資金、技術、人才等的投入,更表現為貧困人口通過參與旅游業而從中獲益,獲得發展機會并提高收入水平,最終減少貧困[10]。旅游扶貧被認為是“造血式”的發展戰略,成為全球“反貧困”實踐的重要方式之一。考慮到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鄉村空心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不難發現我國鄉村地區貧困與空心化問題的明顯重疊。目前,已有學者在研究中注意到了旅游扶貧開發與鄉村空心化問題的關系,具體如下:
1.2.1 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有正向影響 多數研究認為,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問題具有緩解作用。主要觀點集中于旅游扶貧開發能夠有效改善鄉村人口就業和人口結構,進而推動鄉村空心化問題的改善。“推-拉”理論認為,發展旅游業能夠給鄉村直接帶來就業機會,這會對勞動力產生“拉力”,進而直接且有效地緩解鄉村的空心化狀況;同時,鄉村旅游業提供的就業崗位大多對職業技能要求較低,更適合鄉村人口,因此可為大量留守婦女提供本地就業機會。農村婦女的本地就業不僅直接緩解了農村空心化帶來的“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問題,且借助婚姻和家庭的紐帶關系,對農村男性勞動力也產生了一定的“拉力”,間接減少了他們外出務工的距離和時長[2]。
相關學者指出,旅游扶貧開發之所以能夠緩解鄉村空心化,主要原因是它能夠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孟秋莉通過對湖北省2010—2015年旅游扶貧相關數據的分析指出,旅游扶貧開發背景下,政府的資金投入、旅游企業投資和地方旅游收入的增長,均對貧困人口的人均年收入增加產生了正向影響,其中尤以當地旅游收入增長的影響較明顯[10]。
1.2.2 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有負向影響 當前旅游扶貧對于鄉村空心化的緩解也不盡如人意。作出該判斷的主要原因在于,旅游扶貧在實施的過程中,面臨著諸多挑戰。其中,最突出的挑戰就是旅游產業對就業人群具有一定的素質要求,而貧困人口在知識及技能方面較為匱乏[11],導致他們無法獨立經營高質量的旅游產品與服務,從而無法充分享有旅游發展的收益。這也意味著,旅游扶貧開發不僅需要向貧困村莊提供資金、項目和政策等物質性援助,更應注重提升貧困人口的就業素質,如知識及技術由非貧困區域向貧困區域和人口的轉移。然而,現實中進行旅游開發的鄉村地區普遍存在外來經營者不斷進入,而本地貧困人口逐漸被邊緣化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旅游企業培訓本地員工的動機[12],致使無法有效提高人力資本,從而影響旅游扶貧中的貧困人口獲益、青壯年勞動力回流,最終無法緩解鄉村空心化問題。這種情況使貧困人口長期處于低技術且低收入的基層操作崗位,知識技能提升非常緩慢。從當地人口角度來看,空心化地區青年多趨向于向經濟發達地區轉移,學習相應技能并在外工作。所以,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的負向作用體現在非原住居民的流入所產生的人口置換,導致開發紅利無法真正惠及貧困人口以及原生社會網絡的重建。當開發地區人口結構以外部人為主導時,鄉村空心化雖在人口上得到緩解,但也缺失了深層的社會意義。
綜上所述,旅游扶貧對鄉村空心化影響的研究多從宏觀層面展開,微觀層面的研究不足;且關于旅游扶貧對鄉村空心化究竟是正向作用還是負向作用仍然存在大量爭議,旅游扶貧與鄉村空心化之間的關系并不明朗;國內研究多集中于對理念和原則等問題的探討,未從具體的微觀情境中探究旅游扶貧對于鄉村空心化究竟是機遇還是挑戰,也較少論及旅游扶貧緩解鄉村空心化過程中的風險,因而對實踐的針對性指導作用較弱。
基于此,本研究以陜西省西安市藍田縣簸箕掌村為例,通過對當地村民進行調查,從經驗事實角度探討旅游扶貧對鄉村空心化的作用,并借助旅游地生命周期和社會資本理論來分析二者之間的關系,以期深化對旅游扶貧與鄉村空心化關系的理解,為旅游扶貧開發戰略的實施提供針對性建議。
2 研究設計
2.1 案例村落介紹
簸箕掌村位于陜西省西安市藍田縣城以北,距離滬陜高速2.5 km。這里三面為溝,背靠大山,形似一只倒扣的簸箕,因而得名。簸箕掌村有5 個小組,15 個居住點,301 戶1 071 人,小麥、玉米、核桃等基本農作物是村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截至2012年)。2011 年,該村人均純收入2 500 元,是藍田縣重點貧困村。旅游扶貧開發前,簸箕掌村以第一產業為主,第二、第三產業發展困難,且交通等基礎設施落后,與外界來往不便。在此背景下,簸箕掌村大批適齡勞動人口選擇外出打工以獲取收入,常住村民以老人及留守兒童為主,大量房屋出現閑置現象,據此判斷其存在嚴重的鄉村空心化。
2013 年開始,藍田縣政府主導對簸箕掌村實行整村移民搬遷,并引進外部資金為當地建設旅游扶貧開發項目,形成政府主導、移民遷置、景區帶動、鄰里互助、農旅結合5個方面的綜合發展模式。2014 年底,該村已初步建設成四大休閑板塊:女媧湖休閑度假區、移民新村民俗風情區、溫泉養生度假區、山地運動休閑區;三大片區:珍佰糧行綠色農業基地、珍佰糧休閑農業區、山地運動延展區共10 個項目。面積為6.5 km2的生態旅游景區已初具雛形,并配套娛樂、小吃、住宿及停車場等旅游設施。
至2018年,簸箕掌村基礎設施建設得到極大改善,各大景區模塊建設完成并投入使用,余有幾項景區仍在開發中。簸箕掌村旅游扶貧開發提升了全村經濟水平,創造出許多就業、創業機會,村民通過集體經濟和參與旅游接待的形式在旅游扶貧開發中獲益。簸箕掌村人均年純收入從2011年的 2 500 元增至2018年的12 150元。
2.2 研究方法與數據收集
調研組人員分別于2018年7月、2019年10月對簸箕掌村進行了2次實地調查,收集資料。其中,一手資料來自參與觀察、26人次的半結構訪談(其中9人次為深度訪談,包括3位旅游業經營者、2位游客、2位當地居民以及2位政府工作人員)、影像記錄(影像共收集相片約300張,以記錄簸箕掌村旅游扶貧的情況)。影像記錄反映簸箕掌村旅游開發的客觀特征,訪談反映當地不同年齡層次居民在旅游開發中的參與度情況。另觀察4個游客群體(每個群體3~8人)在簸箕掌村的旅游體驗情況。二手資料包括藍田縣政府統計資料、檔案、文獻及政府門戶網站資料。
3 結果與分析
3.1 簸箕掌村空心化現狀
在調研過程中筆者發現,許多家庭的子女在旅游扶貧開發前都選擇了外出打工,這種情況有些持續到簸箕掌村經濟改善之后。
簸箕掌村于2013年開始旅游扶貧開發,尤以2016—2017年期間當地旅游產業發展形勢最好,村內的小吃一條街、民宿、交通運輸以及景區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工作崗位和增收機會,吸引了一批勞動人口進入簸箕掌村從事旅游業,其中也不乏原簸箕掌村住民及看準商業機會而進入的城市人,在此期間簸箕掌村鄉村空心化有所緩解。根據政府門戶資料,自旅游扶貧開發后,村內常住人口增長了200多人。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簸箕掌村出現了“周末經濟”現象,即旅游扶貧開發背景下,年輕人周末回鄉參與旅游經營活動幫助家庭在旅游中增收,工作日又返回城市謀生的現象。并且,由于其自身并未形成品牌效應,加之周邊同類型民俗文化村落(如袁家村、馬嵬驛)發展競爭激烈,使得近期簸箕掌村旅游發展進入停滯階段,旅游業顯出疲軟的態勢。雖然政府希望通過下一階段的發展吸引更多的勞動人口回流,但從現階段看,旅游扶貧未能從根本上緩解該村的空心化問題。
3.2 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的作用
從簸箕掌村旅游扶貧開發后的空心化現狀來看,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的影響,并非單純的正向或者負向影響,而是正負交織的情況。
3.2.1 正向作用 旅游扶貧開發背景下,簸箕掌村的常住人口數量增加及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簸箕掌村地處陜西省藍田縣,離西安市只有1 h左右的車程。旅游扶貧開發前,大量的適齡勞動力涌向城市就業,導致村內大量人才外流,鄉村空心化嚴重。簸箕掌村通過旅游扶貧開發改善當地基礎設施,發展第二、第三產業,創造就業機會,改善經濟環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鄉間的資源不平衡狀況,使得部分有意愿留在當地發展的適齡勞動力回流,也吸引部分城市人口進入。近年來,隨著簸箕掌村經濟環境的改善,人口有所增加,青年人口占人口比重也有所上升。
簸箕掌村的旅游開發對于鄉村空心化的改善具有周期性的短暫經濟效應,根據實地調查,旅游扶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簸箕掌村的鄉村空心化,在短時間內吸引了一些年輕人回流,出現“周末經濟”等新現象,即旅游扶貧大背景下年輕人在節假日或周末回鄉參與旅游經營活動并獲取經濟利益的一種現象。
參與經營農家樂的村民R1回憶說:“我是我們村小吃街上第1個開農家樂的,這些年旅游發展越來越好,越來越多的游客到訪這里,我的生意越來越紅火。我的子女們平時在西安市打工,現在交通便利了。賺錢的機會也多了,孩子們周末也會回來幫我干活,接待游客。這些年隨著我們村旅游扶貧的發展,家家條件越來越好了,不光是我的孩子,很多年輕人周末都會回來看望父母,順便照顧家里的生意。”周末經濟是旅游扶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鄉村空心化的表現。
綜上所述,旅游扶貧對于鄉村空心化的緩解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通過創造就業機會,改善經濟環境,增加了當地村民的實質性收入,促進了青年的部分回流,流動人口總體上呈下降趨勢,并且由于簸箕掌村在旅游扶貧后交通條件的改善和當地游客的增多,出現了“周末經濟”等新現象,這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鄉村空心化。
3.2.2 負向作用 旅游扶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鄉村空心化問題,但也帶來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一方面體現在各種資源的利用上,簸箕掌村服務業的發展,使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上由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農村家庭資本投資轉移到旅游行業,這造成農業發展受到勞動力與資本的雙重缺失,旅游旺季與農忙在時間上重合,從而導致土地資源浪費,這在調研過程中也得到了印證。村民普遍反映簸箕掌村存在大量閑置的土地,嚴重依靠勞動力的精耕細作而維持的傳統農業受到沖擊。
另一方面體現在旅游扶貧對不同群體影響的差異性上。不同的群體參與鄉村旅游業的程度是不同的,旅游扶貧開發對原住居民家庭的經濟影響依據不同的經濟狀況有不同的效果。筆者所在課題組依據原住居民家庭參與旅游開發經營的經濟狀況將他們分為維持生計型、文化經營型、出租經營型3類。結合簸箕掌村的具體情況,筆者所在課題組發現經濟基礎較好的原住居民家庭通過文化經營,依托村內旅游平臺建設,獲得高于從前的收入,旅游開發對吸引此部分家庭成員回流作用較強。部分原住居民家庭依靠房屋租賃獲得租金收入,以間接形式參與旅游扶貧開發,雖然收入得到改善,但家庭子女依舊在外打工,吸引回流的作用不大。
維持生計型的原住居民家庭不僅在旅游開發中參與不足,而且隨著大量農用土地的征用與建設,這部分村民也無法依靠自給自足的農業維持生活,從而引起生活成本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反而會加劇其貧困狀況,導致對這部分原住民的擠出效應,導致家庭青年繼續流失。雖然在政府進行整村搬遷和安置房建設之后基本實現了村民家家戶戶有所居,但對于部分貧困戶來說,住房是剛性需求,無法用于旅游經營,且由于自身缺乏經營意識和技能,在旅游開發中獲益能力不強。特別是原來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家庭,在旅游扶貧開發土地回收后,失去了經濟來源,其子女不得不向外尋找新的工作機會,而老人則在家留守,變相導致了部分人口的流失。
因此,總體上對于目前的簸箕掌村而言,旅游扶貧開發之于鄉村空心化機遇與挑戰并存,但挑戰很大,也更值得引起當地政府的重視。
4 限制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發揮作用的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盡管旅游扶貧開發通過改善經濟環境創造就業機會途徑吸收人口,緩解了鄉村空心化,但是總體上作用還是十分有限,未從根本上解決鄉村空心化的問題。這種情況的出現與以下限制性因素有關。
4.1 缺乏核心競爭力,外部競爭激烈
簸箕掌村主打鄉村旅游,周邊同類型民俗村落競爭激烈。相對于較早開發的民俗村落,如袁家村、白鹿原影視城等,簸箕掌村的后發優勢不足,且未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袁家村堪稱鄉村旅游的典范,其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分析自身自然稟賦,因地制宜專注關中民俗的旅游主題,旅游項目和產品由村民自主經營,專注于提供優質的餐飲服務,村民充分參與旅游活動,形成了全民致富的氛圍。白鹿原影視基地是以陳忠實長篇小說《白鹿原》為藍本興建而成的仿古建筑群,在影視城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大力宣傳影視文化,形成了兼具觀光旅游、文化娛樂、休閑度假等功能的綜合性旅游區。影視文化使其在鄉村旅游中獨樹一幟,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這些早開發的較鄉村旅游景點具有較為成熟的運營模式,且根據自身稟賦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形成了較強的品牌效應,具有穩定的客源。簸箕掌村的模仿式旅游開發,外包式經營模式,并未根植于自己獨特的要素稟賦和文化基礎,后發優勢明顯不足,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和核心競爭力。
4.2 旅游扶貧項目中貧困人口主體地位不突出,受益有限
貧困人口難以從旅游扶貧中受益的主要原因如下:(1)原有生產資料喪失,傳統農戶邊緣化。貧困戶擁有的大多是傳統的生產資料,簸箕掌村旅游扶貧整體規劃的基礎設施建設,使其失去土地等傳統生產資料,無法維持傳統的經濟來源方式,貧困戶會逐漸被邊緣化,導致旅游扶貧后個人收入減少,從而導致貧困人口的外流。(2)貧困人口資本、技術不足,開發能力有限。由于貧困戶缺乏資本、技術等更高級的生產要素而普遍缺乏利用基礎設施提高收入的能力,基礎設施的改善通常能給貧困村中相對富裕的農戶帶來更多利益,從而緩解該部分人群的外流,但卻加劇了貧困人口外流的可能性。
4.3 旅游業發展的階段困境和季節性特征
根據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旅游地的發展可分為探索、起步、發展、穩固、停滯、衰落和復興7個階段[12-13]。在前3個階段中,隨著旅游產業的發展,旅游扶貧開發地區經濟得到改善,相應的就業機會出現增加,并在穩固階段時達到就業人數的頂峰,在此期間本地人口有所回流。但隨著后期旅游業的停滯和衰落,就業機會開始減少,人口回流動力不足,甚至出現重回城市的現象。由于旅游資源本身特色有限,簸箕掌村在接受大量旅游投資的情況下,本應處于發展階段,卻出現了當前的臨時停滯和衰落期,旅游投資熱潮已過,游客增長有限,使得就業機會有限,這種就業供給量的變化必然會限制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的改善。且簸箕掌村旅游業具有較強的季節性特征:春秋為旺季和冬夏為淡季,這一特征導致了就業機會的季節性變化,即就業機會隨著人流量的季節性變化也呈現出季節性增減,不穩定的就業機會無法充分發揮旅游扶貧開發對流動人口回流的吸引作用。
4.4 鄉村空心化地區的社會資本短缺
布迪厄將社會資本定義為資源的集合體,具有經濟、文化和社會等3種形態。李金成認為,社會資本是一個基于社會關系網絡的復雜多維概念,大體上有2個方面含義:(1)個人或者組織在社會網絡中獲取資源的能力;(2)個人或者組織在社會關系網絡中擁有社會資源的數量和質量。二者的共同要義在于社會網絡的社會資源[14]。隨著市場經濟的沖擊及鄉村貧富差距的加大,鄉村的社會資本存量越來越少,人際關系觀念逐漸淡薄,相互之間的交流減少。特別是在鄉村空心化地區,人口的流失逐漸瓦解了固有的社會資本。鄉村社會資本的流失限制了旅游扶貧對鄉村空心化的積極作用。
社會資本指的是由實際或潛在的與人們有價值的社會關系網絡構成的資本,即社會關系網絡所形成的資本[14]。流入城市的鄉村人,在城市生活和發展一段時間后,逐漸積累起以城市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網絡,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減少了對鄉村社會關系的依賴程度。而存在空心化的鄉村地區,原有社會資本隨著人口的外流逐漸流失。對于鄉村空心化地區外出務工的人而言,他們的鄉村社會網絡呈現較為單一的鄰里、家庭模式,反而在城市中有更加豐富的社會資本。鄉村空心化地區流動人口在不同地區間的社會資本存量對比也影響了他們的回流決策。
在鄉村空心化地區,社會資本的重構也有一定的過程性和時間性。研究表明,農村非農人口的就業與社會關系網絡有關,個人、家庭及村莊的發展情況對非農就業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果耕地不足,農村人口非農就業的概率會顯著提高[15]。而發展旅游扶貧的地區,環境的開發伴隨著耕地面積的下降,在沒有充分就業供給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向外擠出適齡勞動力。在這些社會資本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旅游扶貧開發的作用十分有限。
因此,筆者認為,旅游扶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鄉村空心化,吸引部分青年回流,但并不能從根本上緩解鄉村空心化。要從根本上緩解鄉村空心化,還需要在旅游扶貧開發中聯合政府、旅游企業、村民,從地方資源稟賦出發,因地制宜,全民參與,多角度尋求對策,真正讓鄉村煥發活力。
5 結論
根據鄉村適齡勞動力向外轉移、鄉村房屋閑置和留守人口為主的人口結構的特征定義了鄉村空心化。分析表明,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總體上是一種機遇,但若無法控制多種限制性因素,也可能將機遇轉化為挑戰。
具體而言,旅游扶貧在短期內吸引了部分年輕人回流,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簸箕掌村的鄉村空心化,出現“周末經濟”等新現象。但這種現象缺乏持續性,僅是旅游開發中的階段性現象,旅游扶貧對資源稟賦有限和外部同質化競爭激烈的農村的鄉村空心化而言,只是一個短暫的機遇。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的改善受到鄉村旅游地競爭實力、發展階段、貧困人口參與度、旅游業季節性特征和社會資本流失等因素的限制。因此,旅游扶貧開發對鄉村空心化是機遇與挑戰并存的。
參考文獻:
[1]韓 婷,張守志,賀 旭. 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空心化問題研究及對策[J]. 現代農村科技,2019(11):1-3.
[2]蔣慧云,王興山. 淺析旅游業對農村空心化緩解效應的機理[J]. 中國商論,2017(25):54-55.
[3]田新強. 鄉村旅游開發與農村空心化問題治理[J]. 農業經濟,2017(4):52-54.
[4]劉彥隨,劉 玉,翟榮新. 中國農村空心化的地理學研究與整治實踐[J]. 地理學報,2009,64(10):1193-1202.
[5]劉 杰. 鄉村社會“空心化”:成因、特質及社會風險——以J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為例[J]. 人口學刊,2014,36(3):85-94.
[6]崔衛國,李裕瑞,劉彥隨. 中國重點農區農村空心化的特征、機制與調控——以河南省鄲城縣為例[J]. 資源科學,2011,33(11):2014-2021.
[7]杜緩緩. 如何破解鄉村空心化困局[J]. 吉林農業,2015(9):66-67.
[8]李會琴,侯林春,楊樹旺,等. 國外旅游扶貧研究進展[J]. 人文地理,2015,30(1):26-32.
[9]黃淵基. 貧困、扶貧與旅游扶貧:幾個基本概念厘清[J]. 長沙大學學報,2018,32(1):27-34.
[10]孟秋莉. 貧困人口視角下的旅游扶貧經濟效應研究[J]. 統計與決策,2018,34(14):107-111.
[11]Spenceley A,Meyer D. 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theory and practice in less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ountri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2012,20(3):297-317.
[12]饒 勇. 旅游開發背景下的精英勞動力遷入與本地社區邊緣化——以海南三亞為例[J]. 旅游學刊,2013,28(1):46-53.
[13]余書煒.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綜論——兼與楊森林商榷[J]. 旅游學刊,1997(1):32-37.
[14]李金成. 社會資本視角下鄉村振興動力探析[J]. 農村經濟與科技,2018,29(17):274-276.
[15]陳 瑛,劉寒雁. 社會關系網絡與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基于云南數據的分析[J]. 中共云南省委黨校學報,2012,13(5):106-108.袁 驥,倪羌莉,李 敏. 新型農村社區治理模式研究——以江蘇省為例[J]. 江蘇農業科學,2020,48(23):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