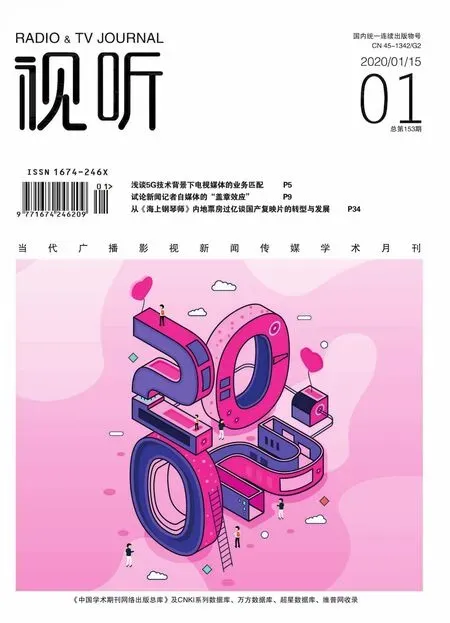從《白蛇:緣起》看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的敘事特征
□ 趙宏博
近年來,隨著國(guó)內(nèi)電影行業(yè)的發(fā)皇張大與電影制作技術(shù)的不斷革新,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也逐漸呈現(xiàn)出遍地開花的態(tài)勢(shì),并且影像內(nèi)容由幼兒化逐漸趨近成人化發(fā)展,動(dòng)畫電影的受眾面也愈加擴(kuò)大。以此為代表的有近幾年涌現(xiàn)出的《大圣歸來》《大護(hù)法》《風(fēng)語(yǔ)咒》和《大魚海棠》等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它們都收獲了較多的好評(píng),至此,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也得以在中國(guó)電影市場(chǎng)上分一杯羹。截至 2019年 2月 26日,電影《白蛇:緣起》累計(jì)總票房4.55 億元,也算是可觀的成績(jī)。動(dòng)畫電影與真人電影相比,鏡頭運(yùn)用與場(chǎng)面調(diào)度更具有自主性和靈活性,因此也給予了動(dòng)畫電影敘事表達(dá)更多的創(chuàng)作空間。本文從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白蛇:緣起》的傳統(tǒng)戲劇式線性結(jié)構(gòu)敘事、跨媒介敘事的表達(dá),以及區(qū)分文本和影視劇的“陌生化”敘事形態(tài)三個(gè)方面來具體剖析《白蛇:緣起》的電影敘事特征。
一、傳統(tǒng)的戲劇式線性結(jié)構(gòu)敘事
電影《白蛇:緣起》講述了已修煉五百年的白蛇始終不能獲得突破,同伴小青將一支碧玉珠釵交還與白蛇,從而開啟了白蛇五百年前的記憶。五百年前有一位掌握邪術(shù)的國(guó)師,他命令天下百姓捕蛇以供自己修煉法術(shù)。為了拯救族群,白蛇冒險(xiǎn)行刺,結(jié)果卻遭遇挫敗,失去了記憶。白蛇在一個(gè)專門捕蛇的村落被救下,救人者是村子里“不務(wù)正業(yè)”、膽小善良的青年許宣。白蛇想要找回自己的記憶,許宣便與白蛇一起踏上了尋找身世的路途,前往永州城。途中兩人經(jīng)歷了國(guó)師爪牙的追殺,蛇族派出的殺手和小青的追蹤,在一路的前行中兩人逐漸產(chǎn)生了情愫,白蛇也恢復(fù)了記憶。為了和白蛇在一起,許宣不惜化人為妖,并與小白、小青一起,與貪婪的蛇母和國(guó)師進(jìn)行了殊死的拼殺,最終取勝,但阿宣也即將形神俱滅,永遠(yuǎn)地消失。白蛇則將阿宣的魂魄封印在碧玉珠釵中,使阿宣能夠投胎轉(zhuǎn)世,但同時(shí)珠釵也封印了自己的記憶。回到五百年后,白蛇決定去尋找轉(zhuǎn)世投胎的許宣。影片最后,兩人在西湖長(zhǎng)堤又以碧玉珠釵為媒再次相見,為以后二人的故事留下伏筆。
整體來看,《白蛇:緣起》并未將故事聚焦于人人傳頌的經(jīng)典故事“白蛇傳”,而是把許仙與白娘子的愛情傳說設(shè)置為“今生”,并將筆墨之重點(diǎn)放在了二人情感的“前世”之上,采取了倒敘的敘事方式和戲劇性線性結(jié)構(gòu)進(jìn)行敘事表達(dá),展現(xiàn)白蛇尋找記憶的經(jīng)過,可以說設(shè)計(jì)十分精妙。
李顯杰曾把影視藝術(shù)的敘事結(jié)構(gòu)分為五大類,分別是戲劇性的線性結(jié)構(gòu)、環(huán)型結(jié)構(gòu)、交織對(duì)照結(jié)構(gòu)、綴合團(tuán)塊結(jié)構(gòu)和幻想結(jié)構(gòu)。線性結(jié)構(gòu)是電影最基本的一種形式,它往往以單一的線性時(shí)間為敘事線索,以事件間的因果關(guān)聯(lián)為敘述動(dòng)力,追求情節(jié)結(jié)構(gòu)上的環(huán)環(huán)相扣和完整圓滿的故事結(jié)局。這也是時(shí)下好萊塢乃至世界電影的主流敘事結(jié)構(gòu)。著名的編劇學(xué)者悉德·菲爾德對(duì)這種結(jié)構(gòu)模式進(jìn)行了深入的分析總結(jié),提出了著名的“三幕劇結(jié)構(gòu)理論”——即建置、對(duì)抗和結(jié)局三幕。建置即電影中的開端部分,對(duì)抗即故事的沖突及發(fā)展,結(jié)局則是高潮與結(jié)局。通常,影像需要有三個(gè)情節(jié)的重大逆轉(zhuǎn)才可以精彩地表現(xiàn)出一個(gè)完整的故事,才能將情感傳達(dá)得既到位又不唐突。以迪士尼系列的動(dòng)畫電影為例,影片往往以童話故事或神話傳說為故事文本,并最終以完美的大團(tuán)圓結(jié)局落幕。有前者之經(jīng)驗(yàn),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往往也參照這種敘事結(jié)構(gòu),營(yíng)造出團(tuán)圓美滿、合家歡等故事結(jié)局。在《白蛇:緣起》中,由開端白蛇的修煉不得果,到回憶五百年前的人與妖、國(guó)師與蛇族的斗爭(zhēng),與許宣的情愫,再進(jìn)入到高潮部分許宣為救白蛇犧牲性命、拯救村民、珠釵記憶找回,到與投胎轉(zhuǎn)世的許宣再次相見的大團(tuán)圓結(jié)局,都遵循了這種傳統(tǒng)的戲劇性線性結(jié)構(gòu)敘事,且較為注重使用和建構(gòu)這種三幕式的結(jié)構(gòu)作為敘事表達(dá)的基本,這也是目前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普遍采用的基本敘事方式。
二、跨媒介敘事的表達(dá)
《白蛇:緣起》既然是以“白蛇傳”為基本范本,就勢(shì)必會(huì)與其他相關(guān)的文本作品及影視作品進(jìn)行比較和對(duì)比,這種跨媒介敘事就使得動(dòng)畫電影《白蛇:緣起》必須進(jìn)行一定的創(chuàng)新和突破,才能不流于形式,落入俗套。
跨媒介敘事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guó)教授亨利·詹金斯提出,指的是一種利用電影、電視、漫畫、小說、游戲、網(wǎng)絡(luò)等多種媒體形式和語(yǔ)言進(jìn)行敘事和營(yíng)銷的策略。他認(rèn)為,雖然跨媒介敘事是利用不同媒介平臺(tái)進(jìn)行播放,但敘事內(nèi)容需要具備一個(gè)統(tǒng)一的世界觀。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中跨媒介敘事現(xiàn)象目前也十分常見,不少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都是取材于民間故事,并且在不同時(shí)代被反復(fù)創(chuàng)作拍攝,每一次重新拍攝都會(huì)使原故事被賦予新的詮釋視角和內(nèi)涵。例如廣受好評(píng)的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大圣歸來》就是運(yùn)用了民間傳說和《西游記》的文本內(nèi)容進(jìn)行再創(chuàng)作。
動(dòng)畫電影中的中國(guó)風(fēng)格和中國(guó)元素不得不提。動(dòng)畫電影能夠呈現(xiàn)出非常豐富的視聽風(fēng)格。以往以“白蛇傳”為范本進(jìn)行的影視作品創(chuàng)作主要有電視劇《新白娘子傳奇》和電影《青蛇》等,這些影視劇對(duì)劇中的人物和情節(jié)也都已經(jīng)進(jìn)行了較為完整的詮釋和塑造。《白蛇:緣起》也運(yùn)用了諸多傳統(tǒng)文化的符號(hào),加入了些許水墨動(dòng)畫藝術(shù)中的“神似性”和“空靈性”,力圖超越簡(jiǎn)練的形象來表達(dá)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情致,努力使畫面達(dá)到情景交融和托物言志的絕妙境界。例如動(dòng)畫中出現(xiàn)的仙鶴、五行八卦等文化元素符號(hào),都彰顯出中國(guó)動(dòng)畫電影的獨(dú)特風(fēng)格。這也是動(dòng)畫電影的獨(dú)特?cái)⑹聝?yōu)勢(shì)。
三、區(qū)分文本和影視劇的“陌生化”敘事形態(tài)
為了完成整個(gè)電影故事的創(chuàng)新,電影《白蛇:緣起》選擇了一種“陌生化”敘事形態(tài)。
俄國(guó)形式主義文學(xué)評(píng)論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過著名的“陌生化”理論。他說:“藝術(shù)的技巧就是使對(duì)象陌生,使形式變得困難,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shí)間的長(zhǎng)度,因?yàn)楦杏X過程本身就是審美目的,必須設(shè)法延長(zhǎng)。”通俗地說,陌生化就是用藝術(shù)的技巧顛覆人們?cè)臼熘某J鲁@恚m然在形式上打破了熟識(shí)的邏輯,但在情感維度符合邏輯,給受眾以感官刺激,達(dá)到新奇的審美感受。
《白蛇:緣起》在敘事中十分注重“陌生化”的敘事形態(tài)。從故事上來分析,《白蛇:緣起》并沒有將故事的主視角集中于傳說中廣為人知的許仙與白素貞人間生活的部分,而是追憶二人的前世情緣。這部分內(nèi)容往往在文本和現(xiàn)有的影視劇中很少被提及。在《新白娘子傳奇》中,白素貞與許仙的結(jié)緣是前世的小牧童許仙從捕蛇人手中救下了白蛇。而《白蛇:緣起》則把故事背景設(shè)定為《捕蛇者說》中的永州城,尊重歷史的同時(shí)也營(yíng)造出真實(shí)性。從字面上看,許宣與小白和許仙與白素貞就能讓受眾第一時(shí)間將其與“白蛇傳”進(jìn)行聯(lián)系。片中小白與許宣撐起飛行的油紙傘,以及保安堂的牌匾和湖中船夫哼唱的曲調(diào),都在反映著故事的內(nèi)核就是“白蛇傳”的傳說,但動(dòng)畫電影中故事的經(jīng)過和整體的構(gòu)建卻已經(jīng)超過受眾普遍認(rèn)知的白蛇故事,給人以新鮮感。
從人物設(shè)定分析來看,童話、民間神話、民間傳說等一直都是動(dòng)畫電影中常見的取材來源。對(duì)于這些熟知故事的改編,傳統(tǒng)的動(dòng)畫電影大都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礎(chǔ)上略加創(chuàng)新,而對(duì)于人物形象,更是完全尊重原著的描述,例如一身白衣的白素貞。但《白蛇:緣起》對(duì)人物性格的塑造卻與原著有所不同。白蛇在影片中被叫做“小白”而不是“白素貞”,有了更多的感性色彩;而許宣的人物設(shè)定則是灑脫率性、向往自由、敢于擔(dān)當(dāng)和承擔(dān)責(zé)任的人物形象,不再是拘泥于傳統(tǒng)故事中有著懦弱性格的文弱書生形象了。人物定位和設(shè)定的“陌生化”更能吊起受眾的胃口。這也從根本上營(yíng)造出了一種區(qū)別于其他相關(guān)題材作品的“陌生化”敘事感。
四、結(jié)語(yǔ)
20世紀(jì)中后期,中國(guó)的《大鬧天宮》《天書奇談》《哪吒鬧海》等多部?jī)?yōu)秀動(dòng)畫作品蜚聲海外,此后一度陷入沉寂,直至21世紀(jì)初才開始逐漸繁榮發(fā)展,其主要的弱勢(shì)便在于敘事方面。因此,在愈發(fā)商業(yè)化、娛樂化的消費(fèi)文化時(shí)代,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在敘事結(jié)構(gòu)、敘事內(nèi)容和敘事符號(hào)上都明顯區(qū)別于20世紀(jì)中后期的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從戲劇式線性結(jié)構(gòu)的大量運(yùn)用、美式經(jīng)典主題的借鑒和強(qiáng)對(duì)立的人物關(guān)系中,都能看出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在敘事上不斷迎合大眾審美。《白蛇:緣起》便是這眾多探索中的一個(gè)。在審美風(fēng)格多變的當(dāng)下,創(chuàng)作者需要有所堅(jiān)持也有所摒棄,要盡量探索跨媒介敘事,將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動(dòng)畫電影用大家喜聞樂見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這樣才能與時(shí)俱進(jìn),開拓創(chuàng)新。《白蛇:緣起》不是近些年來唯一可圈可點(diǎn)的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當(dāng)然也必然不是最后一部,未來國(guó)產(chǎn)動(dòng)畫電影的蛻變與前進(jìn)值得期待。
- 視聽的其它文章
- 淺談馬克·呂布《中國(guó)印象》的攝影技巧與影像價(jià)值
- 高職學(xué)生媒介素養(yǎng)現(xiàn)狀數(shù)據(jù)分析
——以恩施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為例 - “觀摩·參與·實(shí)踐”三位一體理念下廣電教學(xué)模式的探索
——基于“電視紀(jì)錄片”課程的考察 - 動(dòng)畫品牌傳播的理論闡釋與實(shí)踐指導(dǎo)
——評(píng)《動(dòng)畫品牌傳播研究》 - 地市級(jí)新媒體平臺(tái)的廣告運(yùn)營(yíng)現(xiàn)狀分析
——以平頂山微報(bào)為例 - 社會(huì)化媒體傳播環(huán)境中廣告受眾主體性身份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