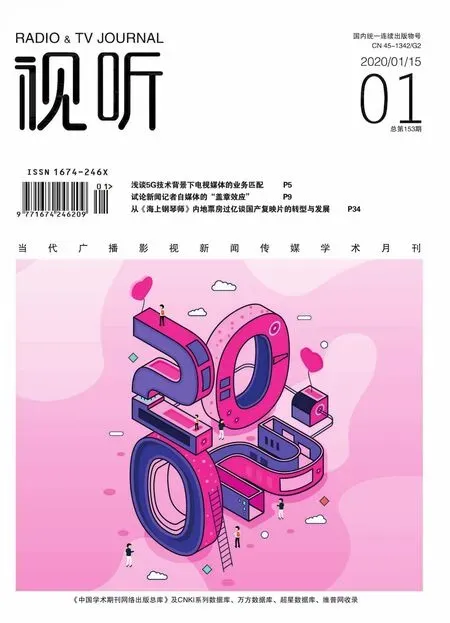《風(fēng)味人間》:東西方飲食文化交融下的中國(guó)表達(dá)
□ 周添舒
美食紀(jì)錄片《風(fēng)味人間》作為一個(gè)飲食文化的傳播載體,創(chuàng)作者在其中貫徹著“平民化”的理念,在東西方飲食文化不斷進(jìn)行融合的背景下,賦予了中國(guó)紀(jì)錄片更加民族化和區(qū)域化的表達(dá)。攝制組將美食的流傳歷史、世界各地的飲食文化習(xí)慣、民族風(fēng)俗影響下的豐富美食作為表現(xiàn)主體,記錄了制作美食的勞動(dòng)者在生活中與美食有關(guān)的點(diǎn)滴片段,傳遞出他們對(duì)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duì)家鄉(xiāng)美食的頌揚(yáng),承載著一份中國(guó)飲食文化的精髓。
一、《風(fēng)味人間》的敘事視角定位
《風(fēng)味人間》對(duì)食物的拍攝采用了飲食文化融合下的平民視角,既貼近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又具有獨(dú)特的民族文化吸引力。拍攝的食材囊括了全球六大洲的二十幾個(gè)國(guó)家和地區(qū),從法國(guó)、西班牙,到摩洛哥、秘魯,甚至埃塞俄比亞、冰島,攝制組在全球范圍內(nèi),尋求著不同食材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表現(xiàn)出各種美食的特色風(fēng)味。其視野的廣大,把中國(guó)美食與世界美食連接在了一起,例如存在于中國(guó)某個(gè)古老小鎮(zhèn)的特色美食,就與數(shù)千里之外異國(guó)他鄉(xiāng)的風(fēng)味有制作工藝上的巧妙聯(lián)系,在文化上也淵源相通。通過(guò)類比敘事手段,使得中國(guó)的美食具備世界性的同時(shí),也讓全世界美食具有一份整體性,用紀(jì)錄片的形式編織出一張美食的“世界之網(wǎng)”。
世界上人口和民族眾多的特點(diǎn)造就了美食文化的多樣性,《風(fēng)味人間》的敘事視角從食材的發(fā)展流變、飲食文化的傳承、中華美食制作理念的全球傳播等多個(gè)角度,將食材作為文化信息紐帶來(lái)連接時(shí)空,傳遞出食者的人生百味。例如在第五集《江湖夜雨》中,講述武漢宵夜的“紅色江湖”,無(wú)論年齡資歷,每個(gè)餐館經(jīng)營(yíng)者都有自己的獨(dú)特生存之道。接著在美國(guó)路易斯安那州,處于龍蝦豐收季,托馬斯正進(jìn)行著帶有粗獷浪漫的南部鄉(xiāng)村氣息的野炊。敘事內(nèi)容上加入了中西方美食的對(duì)比,表明在食物的制作上中國(guó)從來(lái)不是一方孤島。創(chuàng)作者從人們的平凡生活中取材,探索當(dāng)下中國(guó)社會(huì)縮影中普通家庭的生存與追求,傳達(dá)了中國(guó)人因勞動(dòng)而產(chǎn)生的味覺(jué)審美及智慧思考。這一切都使得質(zhì)樸無(wú)華的天然食物具有了濃厚的人情味與生活感。
二、《風(fēng)味人間》的人物形象塑造
除了全球化的敘事視野,《風(fēng)味人間》也在不同的“故事段落”中塑造了飽滿的人物形象,用人物故事引發(fā)觀眾的情感共鳴,達(dá)到紀(jì)錄片真實(shí)感人的藝術(shù)效果。為了進(jìn)一步表達(dá)中華傳統(tǒng)飲食理念,創(chuàng)作者通過(guò)選取各地有代表性的美食勞動(dòng)者,對(duì)其進(jìn)行原生態(tài)生活方式記錄與食物制作過(guò)程記錄,進(jìn)而審視全球美食現(xiàn)狀,成為了片中人物的獨(dú)特建構(gòu)方式。
例如鏢魚(yú)手盧旻易和父親在六七級(jí)的風(fēng)浪中出海,他們?nèi)詡鞒兄鴮?duì)海洋生態(tài)傷害最小的鏢魚(yú)法,其“敬畏自然”的性格自然顯露;中國(guó)廚師劉厚平在國(guó)外將中國(guó)菜與秘魯風(fēng)味融合,其“善于創(chuàng)新”的廚師性格自然呈現(xiàn);還有慶祝孫女滿月準(zhǔn)備“三朝酒”的楊玉清,遠(yuǎn)赴厄瓜多爾的中國(guó)工人李庚,對(duì)仿古菜有著濃厚興趣的董順祥……在這些鮮活的人物群像中,既有職業(yè)性的美食制作者,又有平凡的食材生產(chǎn)勞動(dòng)者;既有堅(jiān)定繼承祖輩飲食習(xí)慣的餐飲店老板,又有大膽融合各地風(fēng)味的新興美食探索家。這些多元共生、以食為本的美食者凸顯了《風(fēng)味人間》的核心主題:飲食交融、求同存異。也正因?yàn)槿绱耍@些將食物視為文化鏈條進(jìn)行傳承的中國(guó)普通大眾和國(guó)外廚師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說(shuō)服力,才能講述飲食文化交融之中以美食為中心的人文故事。
三、《風(fēng)味人間》美食儀式化傳播的實(shí)現(xiàn)
美國(guó)學(xué)者詹姆斯·W·凱瑞在1975年首次提出“傳播儀式觀”,他認(rèn)為“傳播并非僅指訊息在社會(huì)中的擴(kuò)散,更是指訊息在時(shí)間上對(duì)整個(gè)社會(huì)的維系;傳播不是指分享信息的一種行為,而是人們共享信仰的表征”①。在《風(fēng)味人間》中,美食分享的過(guò)程結(jié)合儀式化畫(huà)面組接在某種程度上更體現(xiàn)了美食傳播的社會(huì)建構(gòu)功能。
美食對(duì)于人類而言,其美在于與家人好友共同享有食物時(shí)所形成的親密感,分享是美食的標(biāo)簽。食物古往今來(lái)都是一個(gè)族群自我辨識(shí)、區(qū)分他族和文化傳承的媒介物,它承載著的是人類在歷史發(fā)展進(jìn)程中族群之間的定位價(jià)值,是凝聚族群情感的紐帶。
《風(fēng)味人間》中,創(chuàng)作者用結(jié)構(gòu)化的敘事模式來(lái)提升不同美食作為同一個(gè)社會(huì)維系和信仰表征的意義。例如每一集每一個(gè)故事段落結(jié)尾處,都會(huì)有該段落故事的主人公及其家人們端著食物飽含感激地面對(duì)鏡頭,興致高昂地喊出他們手中最為熟悉的食物名稱:從新疆沙漠深處,阿布都夫婦和孩子們面對(duì)鏡頭表達(dá)出對(duì)自然饋贈(zèng)的巴楚蘑菇的誠(chéng)摯感謝,到伊朗高原上的孩子與大人們毫不吝嗇地表達(dá)對(duì)石子燒馕的贊美;從荷蘭艾瑟爾湖旁西蒙父子舉起自家養(yǎng)殖的大閘蟹十分滿足,到甘肅黃土高原上臨洮人用話語(yǔ)表達(dá)他們對(duì)洋芋攪團(tuán)的熱愛(ài):“若要吃好飯,洋芋砸攪團(tuán)”……這一組結(jié)構(gòu)化的表達(dá)體現(xiàn)了濃濃的儀式感。
除了每個(gè)小故事結(jié)尾處有儀式化的編排,在相同食材故事銜接處也體現(xiàn)了創(chuàng)作者對(duì)美食儀式化傳播意義的思考。例如《落地生根》一集中,日本魚(yú)生制作大師面對(duì)制作完成的魚(yú)生宴席對(duì)著鏡頭虔誠(chéng)地鞠躬“請(qǐng)慢用”,畫(huà)面一轉(zhuǎn)廣東順德魚(yú)生的食客們圍繞大盤魚(yú)生而坐,歡聲笑語(yǔ)間共同用筷子夾起食物,對(duì)鏡頭喊出“撈起撈起,風(fēng)生水起”……這些儀式感極強(qiáng)的畫(huà)面,不斷強(qiáng)化了美食紀(jì)錄片的儀式化傳播的意義。美食儀式化享用過(guò)程通過(guò)紀(jì)錄片傳播,在時(shí)間上完成了對(duì)社會(huì)的情感維系,形成了整個(gè)族群的共享信仰。
四、《風(fēng)味人間》中食物的情感傳達(dá)
在全球視野下觀照中國(guó)風(fēng)味和中外美食多元化烹飪方式,更能夠厘清中國(guó)美食歷史流變,從而在廣袤時(shí)空中思考食物對(duì)本民族族群個(gè)性的塑造。
《風(fēng)味人間》中選取的食物均具有大眾化平民化特點(diǎn)。最為普通的小麥、莜麥、土豆、水稻等主食在不同的地區(qū)因其獨(dú)特的制作方式,成就了世界主食的多元風(fēng)味。而風(fēng)味的形成離不開(kāi)它生長(zhǎng)的那一方水土,比如安徽皖南火腿的制作與它冬季最低溫徘徊在冰點(diǎn)上下以及濕氣彌漫的環(huán)境不可分開(kāi);西班牙窖藏火腿的熟成與來(lái)自大西洋的豐沛水汽受到山脈阻擋形成溫和的獨(dú)特氣候密切相關(guān)。人類因循自然,從食物中獲取能量;竭盡才智,用美味慰藉家人。
味覺(jué)里包含著人情、鄉(xiāng)愁、記憶。因?yàn)槭澄锏奈兜朗巧嗉庾钐籼薜母杏X(jué),由食物在味覺(jué)記憶中延伸出來(lái)的家與親情的味道,能牽引出人對(duì)家鄉(xiāng)的依戀。
人因食物而聚。在片中,臨近新年,身處馬六甲的海南人在同鄉(xiāng)會(huì)館祈福祭祖,過(guò)去海南華僑依靠制作白斬雞和米飯?jiān)隈R六甲發(fā)家致富,而今他們?nèi)匀挥眠@種質(zhì)樸的風(fēng)味凝聚親情,勾連過(guò)往。在南美大陸上從事水利工程的李庚和張杰為了撫慰思鄉(xiāng)的味蕾,大家每月一次進(jìn)行火鍋聚餐都心照不宣,因?yàn)榛疱伩s短了他鄉(xiāng)與故鄉(xiāng)的距離,代表著在外游子對(duì)家鄉(xiāng)的眷戀。
這表明不論是何階層、民族、年齡的人都離不開(kāi)食物的牽引,因此紀(jì)錄片賦予了食物很強(qiáng)的全球共通性,它不需要語(yǔ)言,就可以輕易突破文化、民族的障礙,獲得不同種族的共同認(rèn)可。食物往往擁有最廣泛的受眾基礎(chǔ),它能夠喚起世界各地的人們對(duì)美好生活的向往與期待。
五、結(jié)語(yǔ)
《風(fēng)味人間》以美食為切入點(diǎn),記錄了中國(guó)各民族、各個(gè)地區(qū)人們的生產(chǎn)生活,折射出了當(dāng)代中國(guó)大社會(huì)的整體形象與進(jìn)步。就國(guó)內(nèi)而言,拍攝對(duì)象的選擇具有當(dāng)?shù)靥厣澄锏闹v述中結(jié)合了平凡勞動(dòng)人民的生活,使觀眾加深了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飲食觀念的認(rèn)知。就國(guó)際而言,片中異國(guó)他鄉(xiāng)的食物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國(guó)飲食的影響,展現(xiàn)的異域特色凝聚成了中國(guó)的特色。我國(guó)是頗具特色的飲食大國(guó),國(guó)際社會(huì)于無(wú)形中了解到中華五千年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食物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紐帶,使中國(guó)的飲食文化張力得以完美釋放。借美食探討百味人生,這是中國(guó)人在東西方飲食文化交融碰撞中對(duì)本土美食的一次恰當(dāng)?shù)恼軐W(xué)表達(dá)。
注釋:
①[美]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M].丁未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12.
- 視聽(tīng)的其它文章
- 淺談馬克·呂布《中國(guó)印象》的攝影技巧與影像價(jià)值
- 高職學(xué)生媒介素養(yǎng)現(xiàn)狀數(shù)據(jù)分析
——以恩施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為例 - “觀摩·參與·實(shí)踐”三位一體理念下廣電教學(xué)模式的探索
——基于“電視紀(jì)錄片”課程的考察 - 動(dòng)畫(huà)品牌傳播的理論闡釋與實(shí)踐指導(dǎo)
——評(píng)《動(dòng)畫(huà)品牌傳播研究》 - 地市級(jí)新媒體平臺(tái)的廣告運(yùn)營(yíng)現(xiàn)狀分析
——以平頂山微報(bào)為例 - 社會(huì)化媒體傳播環(huán)境中廣告受眾主體性身份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