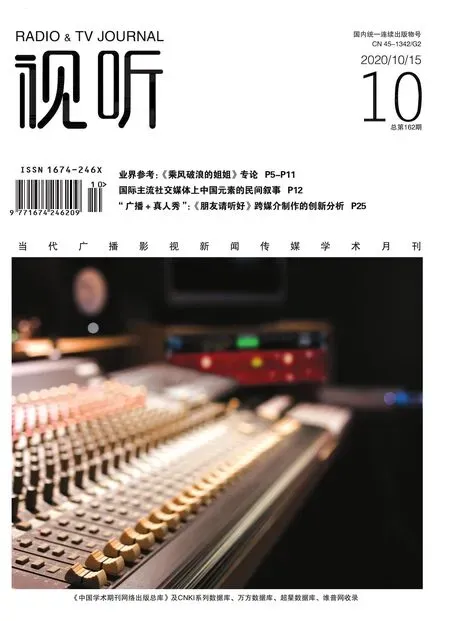淺析聲音在寓言體電影中的連貫作用
——以電影《寄生蟲》為例
□ 臣昕月
《寄生蟲》是一部典型的寓言體電影,講述的是一個生活在地下室的貧窮四口之家以不同的身份潛入富人家庭,在向上欲望的驅使之下,他們愈發渴望“鳩占鵲巢”,最終影片以開放式結局揭露了無法調和的階級固化矛盾。“寓言體電影更加重視主題的展現和意義的升華,這種‘等待戈多’式的劇情斷裂和細節的碎片化處理并不干擾我們對影片內涵的理解,反而做到了情節的極度簡化,以及主題的直接展現。”①寓言體電影通過巧妙的情節設計和敘事策略來表達主題寓意,而情節的完整性與邏輯的嚴密性往往容易會被忽略。邏輯斷層很有可能使得寓意表達不夠清晰,電影聲音的作用則體現在通過渲染人物的情緒,闡釋人物的言行舉止,為情節發展提供更多的信息量,連接起碎片化的敘事線索,減輕情節簡化和邏輯性減弱給觀眾帶來的不適感,起到寓意表達的連貫作用。電影《寄生蟲》的故事模型極具戲劇性,具有鮮明的寓意色彩,部分段落采用快節奏敘事、交叉剪輯、敘事視角轉變等敘事策略,其中電影聲音也起到了獨特的連貫作用。本文從電影《寄生蟲》的敘事角度出發,分析聲音如何在敘事中增加視聽表達的信息量,從而更好地為寓意表達服務。
一、敘事節奏上的連貫性
第二幕上半部分講述了從基澤成為新司機到基澤夫人成為新管家的過程,展現出基宇一家成功地侵入樸社長一家。這一段的電影配樂為《The Belt of Faith》,是一種情緒高昂的古典配樂,輕快燦爛的管弦樂器與沉穩復古的大提琴結合,猶如一場華麗優雅的演奏。在電影情節上窮人們也在這樣的氛圍中完成了一場華麗的表演,營造出基宇一家步步為營的侵入快感和刺激感。在音樂時長上,從樸太太說出“信任鎖鏈”之后,音樂開始響起,并且在女主人走上階梯聽到女管家咳嗽的時候達到高潮,暗示基宇一家走到離成功最近的一步,情緒此刻也達到高潮。最后當女主人真正上當受騙,驚嚇暈倒的時候,音樂在黑場處鄭重地結束,也暗示侵入計劃的圓滿落幕。
這一段落通過快速剪輯將真實時間縮短,聲音使得鏡頭戲劇化,朝著一個目標前進,產生一種期待和急迫感。而且,對白和音樂控制了段落節奏,起到推動劇情發展的作用,人物心理和行為的節奏跟隨著音樂變化,使得影片的內在情緒逐漸加強,戲劇張力逐漸凸顯。
在該片段中,音樂與畫面的組合體現了兩種情緒線索,一是基宇一家人步步為營,順利潛入的一種邪惡的爽感;另一個是富人家庭逐漸陷入所謂的“信任鎖鏈”,對基宇一家的信任和依賴逐漸加深。這種荒誕行為和古典端莊的樂曲之間的對比使得情節更具諷刺意味而充滿了寓意:一方面放大富人階級的極易受騙,表現上層階級的精神空虛;另一方面凸顯下層階級在騙局中獲得前所未有的快感,是一種現實無法給予他們的快樂,對比之下更顯悲涼的意味。同時導演將情節簡化,原本“侵入”過程應該是復雜的,其中的一些細節如富人十分容易上當、各種時機恰到好處等都經不起邏輯上的推敲。但是,通過運用聲畫對位,在原有基宇一家人情緒信息的基礎上,增加了富人一家的情緒信息,強化了諷刺意味,從而掩蓋了邏輯上的不合理,使得主題先于邏輯,情感先于理性,聲音不僅連接了情節邏輯,而且也貫通了寓意主題的表達。
二、交叉剪輯中的連貫性
暴雨之夜片段在第二幕的下半部分,基宇一家雨夜驚險逃出富豪家之后,發現大水淹沒了自己的家,場面十分狼狽不堪。暴雨段落是人物命運的轉折點和電影高潮前的關鍵情節點,在聲音的運用方面也極具特色。
這一段落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逃出富人家,二是回到被淹沒的地下室。在第一部分中,鏡頭以固定鏡頭為主,畫面景別多遠景與全景,聲音以暴雨和打雷的環境音和低頻配樂為主。在畫面中,人物慢慢往下奔跑,暗示著他們回到底層的過程,具有強烈的寓意。第二段,當基澤一家回到自己的家,發現家幾乎被淹沒了,絕望地去尋找家里的東西。此時,在大別墅中的管家夫婦也處于一種絕望的狀態,拼命地向外界放出求救信號,但是樸社長家的小兒子看到之后依然選擇了冷漠。在同一場大雨中,身處不同地點的管家夫婦與基澤三人形成了平行蒙太奇,電影音樂屬于情感共鳴的聲音,將其在情緒和寓意表達上連接了起來。
這一段落的聲音復雜而豐富,在磅礴詭異的配樂中加入了音量較低的暴雨聲,而雨聲凸顯出了一種毀滅性的意味;根據畫面的跳接改變音量大小,體現一種距離感的變化,讓我們感受到來自不同角度的聲音帶來的感受。配樂則為整個段落的聲音場景奠定基礎,使得來自自然的雨聲變化更為順暢。此外,配樂也具有寓意層面的連貫性,敘事邏輯上以聲音渲染的人物情緒為共同基礎,起到了寓意表達的作用。這兩個群體都是處于社會底層,他們在交叉剪輯和聲音渲染的作用下成為一個整體,在這個大雨中絕望地掙扎著而又萌發了新的欲望。
暴雨段落長達6分鐘左右,在敘事上并沒有重點為高潮部分做邏輯上的鋪墊,而是更多地通過電影配樂和暴雨聲的融合創造一種魔幻詭異的聲音情境,并以此為基礎,與畫面相配合,反映人物在暴雨中的不同心境,展現了同一場大雨中窮人的狼狽與富人躺在別墅里的愜意,為主題寓意服務,同時為高潮情節做好人物心理的鋪墊。
三、視角轉變中的連貫性
整部影片在語言上都是以客觀視角進行敘事,但是結尾選擇改變敘事視角,先是基宇的視角以內心獨白的形式進行第一人稱敘述,而后轉為基宇父親的內心獨白,最后又回到基宇的內心獨白。內心獨白可以表露人物的心理感受,從主觀心理視點講述母子倆的艱苦生活以及父親躲在地下室的情節。整段獨白以《Moving》為配樂,該配樂和開頭配樂十分相似,都是溫柔的鋼琴曲。但是,結尾配樂在疊加了弦樂之后具有不同的意味。基宇一家的計劃最后落空,始終無法逃離那個地下室,故事在平靜中展開,經過一番波瀾曲折之后回歸了平靜,只是平靜中又多了一份無奈與悲涼,突出了底層窮人始終無法實現階層跨越的宿命感。
在基宇幻想與父親重聚的時候,音樂停止了,只有微弱的腳步聲和外界環境的鳥叫聲。此處的聲音設計不是為了突出環境特征,而是一種省略音樂的寂靜設計,增加了一種非真實性的信息,暗示了這是幻想中的場景。音樂暫停是一種戲劇性表現非真實情節的方式,然后接上更具節奏感的片尾曲,創造了影片結尾的獨特節奏。寂靜之后,片尾曲《Soju One Glass》響起,揭示前面買下別墅的情節都是基宇的幻想,故事最終回到了那個從半地下室望出去的窗子。畫面與開頭的窗子相呼應,同為鋼琴曲的音樂相互照應,但結尾處的曲子更有節奏感和悵然若失的苦澀情緒,烘托出人物經歷了一系列事情之后的復雜情緒,為電影留下余韻。
寓言體電影的結尾通常起到主題升華和寓意表達的作用。結尾在敘事視角上進行轉變、呼應開頭的音樂以及音樂的停止繼續等聲音設計,一方面從人物心理出發,渲染無奈絕望的情緒,體現美好夢想與骨感現實之間的反差;另一方面,從電影整體敘事結構出發,聲音的呼應中渲染一種循環往復卻一切皆空的宿命感,極具荒誕諷刺意味。所以,電影聲音可以貫通影片整體的敘事結構,使結尾和開頭形成對比,強化主題寓意的表達。
四、結語
寓言作為一種藝術形態折射了人們審美觀念的改變,寓言體電影的發展則體現了現代人對于現實體驗的復雜性與深刻性,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多元化發展途徑。所以在當今時代,以現實意義為內核的寓言體電影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對創作者而言,清晰明確地表達出寓言體電影的寓意內涵也成為了創作中的重點。電影聲音可以使敘事邏輯更為連貫,寓意表達更為清晰,所以聲音對寓言體電影的主題傳達具有重要的作用。電影《寄生蟲》的成功,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充分運用電影聲音,傳達了對階級社會和真實人性的深刻反思,彰顯了電影現實主義的價值內核。
注釋:
①陳睿姣.寓言體電影敘事特征初探[J].電影文學,2020(04):7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