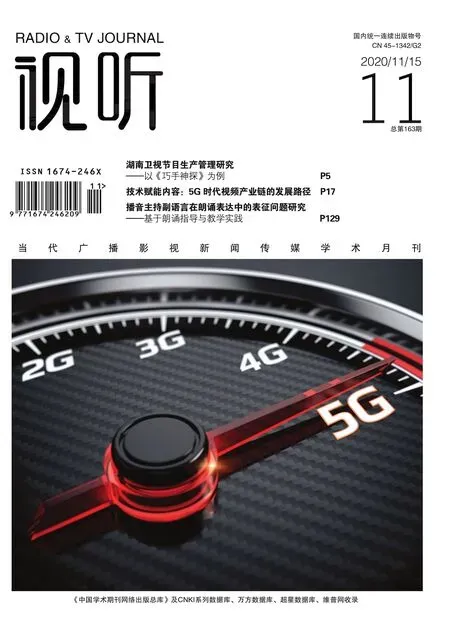試論《金陵十三釵》電影改編之失
□ 章簡寧
由張藝謀執導的《金陵十三釵》改編自嚴歌苓所著的同名小說。電影故事以抗日戰爭時期的南京大屠殺為背景,講述的是1937年被日軍侵占的中國南京,軍人李教官帶領教導隊從日軍手中救出一批教會學校女學生,而李教官等人卻喪失了出城的機會。幸免于難的女學生返回教堂,隨她們一起來到教堂的還有受雇遠道至此收殮神父遺體的美國人約翰·米勒,以及十四名強行進入教堂避難的風塵女子。在日軍要求女學生“赴宴”的逼迫之下,教堂內的人們面臨孰生孰死的抉擇。
中國新浪娛樂網站對張藝謀導演的《金陵十三釵》進行觀影調查,大約有56%的觀眾認為《金陵十三釵》超出期待,非常優秀。但原著小說所表達的女性主義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所塑造的飽滿人物形象也存在扁平化的缺陷。
一、電影和小說的差異
(一)媒介不同
著名傳播學者麥克盧漢依據媒介提供信息的清晰程度、受眾想象力的發揮程度和參與程度,將媒介劃分為熱媒介與冷媒介。所謂“熱媒介”,即傳遞信息明確、受眾無需進行廣泛的聯想就能夠理解與接受的媒介;“冷媒介”則與之相反。電影影像和小說文本恰好分屬兩方。電影是聲、光、色、影的藝術,創作者通過有限的畫幅,運用景別、色彩等畫面語言進行直接具體的表達;小說的核心是刻畫人物,是一種通過完整的情節和環境描寫來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體裁,其表達是抽象的,需要通過文字敘述激發讀者的想象,進行一種間接的構建。張藝謀導演《金陵十三釵》以其獨特的聲畫藝術、嫻熟的運鏡,令人深切體驗秦淮河女子的美艷、日軍的殘忍和南京人民感受的苦難,比文字更具沖擊力和震撼力。
但電影由于時間限制,不得不砍掉許多枝蔓,要求矛盾突出,主題明確。在有限的時間內,復雜的人物性格難以進行完整的表達,故而人物性格刻畫趨向扁平單一;而篇幅對于小說的表達限制較小,細膩的心理、動作、語言、表情描寫可以生動形象地刻畫不同的人物性格,離開善惡二元對立的傳統價值敘事,描寫人性中的灰色地帶,塑造更為貼近現實的人物。小說《金陵十三釵》中的人物飽滿而富有張力,人物的正反兩面表現得淋漓盡致。玉墨在電影中的形象是高貴、冷清、沒有污點的“英國女王”,在小說中卻是和普通“窯姐”一樣勾引有婦之夫、為自己生存謀利、向神父下跪、講葷段子的“五星窯姐”。
同時,電影是集體創作的產物,其本身的投入又要求它不得不以謀利作為目的之一。除了導演、演員、攝影、剪輯會對于同一劇本、同一影像有不同理解,從而進行多次創作以外,行業審查、大眾愛好等都是電影創作過程中需要考慮的問題。故而在《金陵十三釵》電影的創作中,張藝謀舍棄原本女性主義的表達,轉變為一種英雄主義。暴力美學、情愛因素迎合現在的消費市場,從而為票房取得保證。小說的創作則相對個人與私密,與電影相比投入較小,受行業制度干涉有限,對于盈利追求較低,且主創人員有限,能夠較為忠實表達作者本身的思考與探索。在小說《金陵十三釵》中,嚴歌苓想要表達內容之一,即兩種身份的女人之間的和解與解放,對于人性層面、女性主義的探索內容在電影有所缺失。
(二)受眾不同
小說以文學性、隱喻性將受眾劃定為相對較高層次的群體,而電影因其影像化的表達,理解門檻較低,故而成為大眾化的藝術,尤其是院線上映的電影,在前期制作時本身就會考慮受眾群體的問題。
二月河認為,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應該堅持兩個原則,一方面是關照到忠于原作者、忠于原作;另一方面要關照到觀眾的欣賞能力和欣賞層次。
張藝謀在《金陵十三釵》的拍攝紀錄片《張藝謀和他的金陵十三釵》中也表示,他曾為影片結尾設計的鏡頭是風吹起日軍卡車后的帆布,十三釵們著學生裝,高興地唱歌。但最后他舍棄了這一想法,因為“這是去日本人那里,可能觀眾不一定會馬上轉過這個文學性的彎來,可能會誤讀”。
二、電影改編之失
(一)女性主義的缺失
小說是以書娟的初潮作為開端的,女性特征貫穿全程。包括使用相當大的篇幅去刻畫書娟和同學小愚之間的情緒糾葛,描繪每位女性都會經歷的拉攏、背叛、排擠和孤立以表現她們作為女性的成長與欲望;女學生對于地下室“花船”的多次窺視與對于使用身體過活的窯姐又好奇又厭惡的復雜心情……小說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女性群體相互和解的過程,大屠殺在一定程度上退化為背景,嚴歌苓想要敘述的不僅僅在那個時代女性的痛苦,更是女性群體之間的相互原諒、相互救贖和認同內化的過程,是在戰爭背景下女性的生存狀態的問題,是對刻板印象發起的挑戰,是對人性的考量。
在小說中,男性形象是無力的——軍人沒有能力保護女人;神父為了保護女學生們不得不在心里就預設“窯姐的生命是次一等的”,以減輕獻祭她們的心理障礙。玉墨等人作為年長的女性,不僅完成了女孩們對于性別的啟蒙,而且最終完成對于后代的一種保護。在小說中,如果沒有十三釵的出現,教會的女學生認識到自己女性特征和欲望的時刻將會延遲。因為小說中的這些孩子多半是孤兒,生命中女性的痕跡較少,但十三釵的出現激發了女學生對于女性、對于身體、對于男女之愛渴望又復雜的情感。由于戴少校這樣有男子氣概、軍人理想的男人出現,書娟與玉墨之間無可避免地出現了“厄勒克特拉情結”,即“戀父情結”。這一情節與“弒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結”相對。書娟嫉妒玉墨能夠得到戴少校的愛,從而怨恨。此時的書娟已經逐漸剝離女學生的圣潔形象,走下神壇迎接欲望本我。
在超我和本我的拉扯中,女學生們最終完成自我的成長,接納十三釵,接納自我欲望,接納男女之事。故而在小說的結尾中,所謂優雅有教養的女學生身上時常冒出窯姐的習氣,她們的嘴里常常吐出窯姐的臟話,這是兩個群體之間的認同和內化。
而在電影中,十三釵和女學生之間的矛盾被壓縮,刪去了女學生多次窺視、討論哪個窯姐最好看的情節;刪去了女學生夜談時針對窯姐的討論;書娟對于救贖者的愛戀也被玉墨的幾句話輕輕帶過;女學生之間的群體拉扯也失去了痕跡。玉墨等人在決定代替女學生的時候,打的旗號是打破“商女不知亡國恨”的社會偏見,是去做一件“頂天立地”的大事以期洗刷“自古以來的罵名”。但妓女地位低下的社會語境,本身就是男權背景下的話語體系,故而即便在最后,兩個群體也沒有達成真正的心理認同。張藝謀試圖通過女學生叫十三釵“姐姐”,將自己的衣服給十三釵穿來表現兩個群體之間的和解,但是其為打破罵名而進行的前提預設就使得女性主義本身有所缺失。
(二)人物形象的缺陷
在小說中,嚴歌苓將矛盾拘在小小的教堂,著眼于幾個群體內部的沖突,是對戰爭背景下人性的剖析和思考,這種思考甚至不僅僅局限于中國人。由于嚴歌苓的華人身份,以及《金陵十三釵》的靈感來源之一是歷史上南京安全區的負責人之一魏特林女士的日記,故而在小說中還有法比對于夾在中西兩國文化之間的掙扎和糾結。但是在電影中,矛盾主要轉變為中日民族沖突,每個人物身后的故事枝蔓被砍掉。軍人們一改小說中軟弱的形象,英勇無畏,戰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強化了中國軍人的擔當與血性,并且通過小心翼翼地歸還女學生皮鞋,聽到她們唱歌時落淚的細節,凸顯軍人柔情的一面。
嚴歌苓的小說原著中記載了許多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事件——士兵為了出逃扒平民的衣服,將孩子硬拉入伍等與受眾的情感認知相左的歷史事件,并且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力圖將人刻畫為飽滿的正反兩面的結合體。在原著中,玉墨有風塵、軟弱的一面;書娟固執傲氣;士兵身上有兵痞子式的“流里流氣”,在地窖中和窯姐們調情;神父在內心看不起風塵女子;法比也和普通男人一樣對玉墨的風情有所貪戀……面對生命的威脅,每個人都有不可避免的弱點。但是為了迎合受眾的期待,表達一種愛國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宣傳,電影中人性的弱點被崇高遮蔽——士兵英勇無畏,約翰從貪生怕死到奮起反抗,十三釵們有情有義,攜手赴難。這樣的改編確實可以讓人產生一種悲憫崇高的情懷,但從一部影片的人物塑造和真實程度來說,未免有所欠缺。
作為一部商業片,電影《金陵十三釵》無可避免地受到商業化和社會語境的影響。對于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觀眾都十分熟悉,因此好奇有限,悲憤十足。故而大眾對影片的心理期待本身就不是想要獲知歷史的真實面貌,他們對這段歷史的悲憤情緒需要泄口和安撫。張藝謀借用《金陵十三釵》的女性敘事角度,從戰爭中最脆弱的視角入手,塑造出的是小人物身上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而當入殮師約翰從一開始的唯利是圖轉變到出手保護女孩,甚至放棄和同伴離開南京的機會,就完成了一種英雄主義的表述,是典型的好萊塢的英雄主義敘事,但因缺少鋪墊,這一轉折顯得生硬。
三、結語
不可否認,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充分運用電影的音畫表現藝術,塑造了秦淮河女子的美艷形象,方言的使用也使小說原著中的描寫具象化,戰爭場景的加入更顯厚重感。嚴歌苓在《五寫“十三釵”》中表示,她自己都不相信這個生命體和她有什么關系,電影給予了她太大的驚喜。我們當然贊賞電影《金陵十三釵》對于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宣揚,贊賞對于戰爭中小人物的關注,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在新媒體時代,人們更傾向于觀看作為熱媒介的視頻圖畫,而作為冷媒介,天生具有“排斥”特性的小說文本難以得到關注。視覺傳播的地位逐漸上升,碎片化閱讀廣泛,人們很少花時間深入閱讀經典,去了解小說文本之后的哲思。因此,承接文本的責任,視覺傳播藝術責無旁貸。
視覺傳播不應該僅僅著眼于聲畫之美,局限于用藝術手法講好一個簡單的故事。時代要求進步,要求我們面對中國獨特的歷史情況和社會語境拿出自己的“軌”。這是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優秀的畫面語言和改編過程中的缺失給予我們的思考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