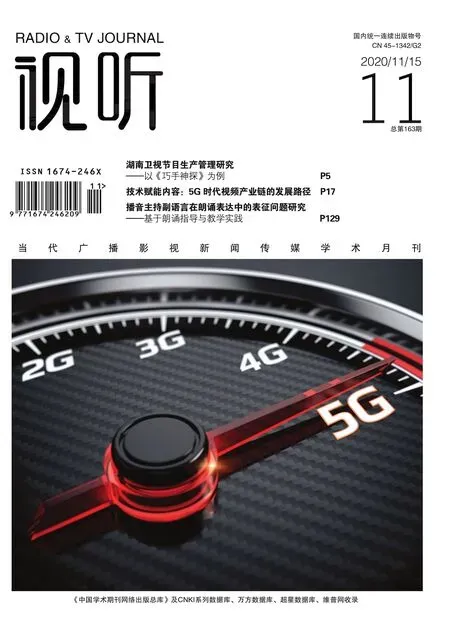從《路邊野餐》看畢贛電影的超現實主義建構
□ 樓俊辰
畢贛是一個十分特別且充滿靈感的導演,他的《路邊野餐》在2015年獲得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這部長篇處女作體現了畢贛的個人風格,體現了其對藝術創新的嘗試和打破傳統敘述結構的表達。本文試圖從超現實主義這個角度對這部電影進行分析。
一、超現實主義元素
超現實主義的表達風格最為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對夢境的構造。“……夢的肉欲性或官能性、夢的絕對自由、夢的綺糜特征以及一種能夠喚起無限和永恒的氛圍”①,這是法國電影評論家德斯諾斯對電影中應當塑造的夢境的一種期盼。然而夢境應當是混沌的,類似于解構主義所提到的“邏格斯中心主義的消解”,夢囈中的言說使得實物的主體性遭到了消解。在《路邊野餐》中,超現實元素的大量使用為主體性的消解提供了實物材料。影片中許多意象反復出現,但是它們都與現實中自己應當承擔的主體功能不符,比如在影片開頭山洞內的電視機、衛衛家客廳與陳升家陽臺上的舞廳鐳射燈、屋內隆隆駛過的火車,它們被迫在場,但是它們失去了自己的主體性,于是失去了言說的能力,由此導演構造出了夢境混沌的特征與一種超現實的美感。
法國的超現實主義作家布列東認為,“關閉的窗戶和門是現實與夢、神秘與未知領域之間的連接點。”②在《路邊野餐》的開頭,老陳開鎖將門打開,既暗示了他過往的身份,也在暗示夢境的開始。而同樣具有超現實的元素還有廣播里的野人以及貫穿整部影片的方言。根本不存在的野人也在廣播中反復播放,許多關于它的周邊新聞也荒誕而不真實,而方言則使敘述更加逼真而親切,由此產生了幻想與現實的錯亂,更加深了夢境的特點與氛圍,同時也是對現實的顛覆與分解,從而使主體的本質直接展示在觀眾面前。這是電影超現實主義風格體現得最為明顯的地方,它深埋于整部電影的隱秘角落,為其奠定了超現實的夢境基調。
二、時間與空間的超現實構建
鐘表是電影中常見的時間的承載物。它在《路邊野餐》中也由于暗示時間的功能而反復出現。例如童年衛衛與在去鎮遠路上遇到的青年衛衛手上共有的手表涂鴉,花和尚“一房間的手表”,以及影片最后列車上時光倒流的鐘等,每一次出場都暗示著時間的不真實性。畢贛讓它在影片中反復出現,目的在于用這個意象使電影的時間產生破碎感。他將原本完整的時間割裂開,用碎片化敘事打破了線性時間的傳統敘事方式。他將現實抽離,從而構造出一個超現實的夢境。而在空間層面上起到同樣作用的還有摩托車這個意象。凱里是個鄉鎮,且位于山區,綿延的盤山公路與鄉間小道使摩托車成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在影片的中前段,采用了大量鏡頭表現陳升在山路上騎摩托車。這部影片所要表達的就是陳升尋找的過程,而在這過程里鏡頭內的山路大多相似,但主體運動卻是持續的,這表現了一種相對靜止的運動狀態,空間感也遭遇了割裂,仿佛永遠無法找尋與到達,營造了空間固定與時間停滯的錯覺。
《路邊野餐》中的時空構建最具代表性的技巧是長鏡頭的使用。在陳升前往鎮遠的路上,影片前段主要使用的組接鏡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長達數十分鐘的長鏡頭。沿途打鬧的小孩、路邊廢棄的磚頭水泥、農田、百無聊賴的人們都出現在了鏡頭內,敘事結構突然變得單一,但這現實的紀錄片似的風格卻讓觀眾沒能回歸現實,反而更加沉浸于陳升的夢境之旅。鏡頭下的每件事都真實地發生著,但是在音樂聲與詩歌的吟誦之中,真實性被消解了,這一切都仿佛是陳升一個人的記憶。鏡頭不再進行主體敘述,它只作為旁觀者在默默觀察著,觀察著凱里這個夢境中的世界。這與阿拉貢的敘述不謀而合,“估量了現實的兩重性經驗——在這種現實中,它毫無歧視地把一切存在的事物混雜起來了……超現實是用心靈把這些概念混合起來的狀態,是宗教、魔術、詩歌、夢想、瘋狂、醉酒、狂喜以及隨風飄動的杜鵑花”③,顯然,當現實和非現實在心中混合后,它們會產生一種超現實的暗示,這是一種“雙重錯覺”。在《路邊野餐》中,畢贛將時間與空間打碎后以一種非線性的邏輯重組,從而構建了一個夢境的凱里,也是屬于凱里的夢境。
三、電影整體的超現實主義建構
在布列東的《娜佳》一書中,有一段關于布列東和娜佳在圣戈爾曼小鎮上的闡述,他把城堡中所有的隱秘之處都比作了內心生活。而《路邊野餐》整部電影所做的就是構造出這座“城堡”,然后帶領觀眾去探索這些隱秘之處。
建構城堡的方式就是前文所提的大量超現實元素的使用與時間空間的錯亂表達,由此產生了系統錯位,而在這時空的非線性表達中影片又實現了分層景深的空間分離感。那么我們是如何探索這座城堡的呢?這需要重新回到電影本身來討論。
傳統的電影敘事大多借用人物的內心獨白或者是某些時刻的特寫來刻畫人物情感,從而使人物形象變得豐滿,也讓觀眾更加了解人物。但是在《路邊野餐》中畢贛打破了這樣的敘事結構。人物不再被單獨刻畫,他們只有在事件發生做出選擇時才能真實地存在。他們不再承擔言說故事的作用,他們就是言說本身。人物不僅僅是劇情和故事的載體,從根源上說,是他們本身在訴說故事。就像影片中陳升說的那句“像夢一樣”,畢贛借助片中人物構建了事件的因果,這也在超現實的錯亂中賦予了邏輯的因果性。
在建構這部超現實的電影過程中,畢贛還開創性地使用了詩歌旁白來推動劇情的發展,并使其渲染了環境氣氛。看似為自由派詩歌的吟誦實際上卻包含了影片主體未言說的諸多線索,讓整部電影蘊含的內容更加豐滿。詩意與故事性填充了這個夢。而它對現實性與主體的消解使得現實與超現實合并,最終構建了這座超現實的城堡。就如同影片中的那句詩所表達的那樣:“手電的光透過掌背/仿佛看見跌入云端的海豚。”海豚無法飛翔,被錯亂放置的意象使得極端對立的現實性被強行合并,超現實的感受由此而來。這可以看作是《路邊野餐》整部電影的縮影,現實與非現實融合,最終一個夢的城堡也就是超現實主義的結構也由此建構。
布列東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對超現實主義下了定義:“純粹的精神無意識活動……它是思想的筆錄,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賴于任何美學或道德的偏見。”所以超現實的表達并不意味著混亂與無序,其更多的是那種現實性與超現實性的雙重結合。正如畢贛在《路邊野餐》中所做的那樣,用超驗性的材料構建超現實的城堡。
四、結語
畢贛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講故事”的導演,他更像是一個詩人,攝影機則是他的筆。他也像是一個夢境的制造者。在《路邊野餐》里,他用超現實的手法構建了一個美麗的夢。而凱里則是這個夢發生的地方。毫無疑問,這是一部杰出的藝術創新與飽含野心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技巧性之外,他還表達了一種鄉土精神以及人文關懷。這在今天的電影界是少見的,也為他的電影提供了更多值得解讀的意味和價值。而如何平衡與發展這種獨特的電影風格,以探索新的電影拍攝范式,也是畢贛電影引領我們去思考的問題。
注釋:
①[法]理查德·阿貝爾.法國電影理論與評論1907-1939[M].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8:396.
②[法]安德烈·布列東.超現實主義宣言[M].袁俊年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12.
③Louis Aragon.Le Libertinage[M].French,19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