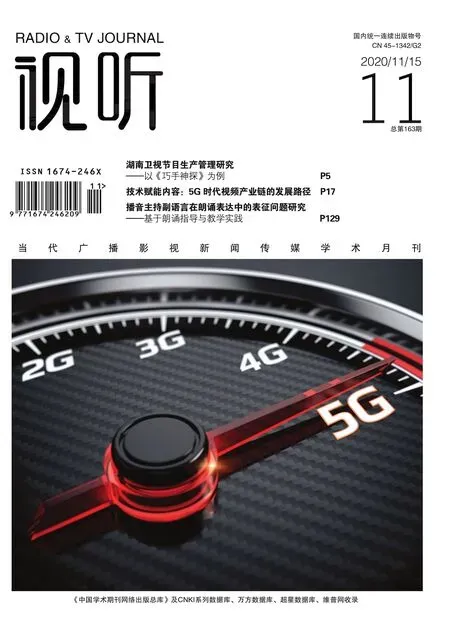畢贛導演超現實主義電影風格研究
□王瑤
2015年,導演畢贛憑借其自編自導的電影《路邊野餐》斬獲多項獎項,2019年又以電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收獲2.8億元的票房,成為當年的現象級文藝片。畢贛的電影充斥著濃郁的個人敘事風格,法國《電影手冊》給出的評價是:“畢贛的出現讓賈樟柯后繼有人,給中國電影注入了一劑強心劑。他的作品創造了一種強有力的新魔幻現實主義,有時令人費解,卻刻刻讓人著迷,并認可了影片在電影美學上的驚人嘗試與成功。”①
畢贛運用“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奇異的構圖和詭譎的運鏡等疏離化技巧”②,將機器與人物調度完美結合,打破了夢境與現實的邊界,讓時空不再統一,編織出一個亦真亦幻的夢境,極具超現實主義風格。本文從影片主題、敘事風格和影片蘊含的哲學式思考來對畢贛導演的超現實主義電影風格進行探究。
一、以“尋找”為母題,尋求與自我的和解
“尋找”是畢贛導演的《路邊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母題,其借尋找他人之路,補償過去的遺憾,與家人和自己和解。
影片《路邊野餐》中,男主人公陳升因入獄9年,未能顧及父親與妻子,心存愧疚,便在“尋找”侄子衛衛的旅程中來彌補曾經的遺憾。陳升在蕩麥遇見了已故的妻子,無論是流著眼淚說著坐牢的種種,還是從不曾唱歌的他為妻子唱了一首《小茉莉》,均表達了對妻子的愧疚,希望得到妻子的原諒。當陳升來到鎮遠,得知花和尚接走衛衛的原因(花和尚是怕衛衛的父親將他賣掉,擔心陳升會像自己曾經失去兒子一樣難受,才接走衛衛的)時,與花和尚和自己達成了和解。
在影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畢贛則用類似的敘事手法讓時空交錯、夢境交織。男主人公羅纮武在尋找情人萬綺雯的旅程中陷入夢境。夢境中,他和幼時好友白貓打了一場乒乓球,幫助母親與情人私奔,并與凱珍在天空中飛起來,也讓他們所在的屋子旋轉起來……這些都是在彌補過去留下的遺憾,為求與他人和自己達成和解。
二、非線性敘事鏡頭展現導演獨特的個人風格
畢贛的電影就如夢一般,缺乏客觀性和邏輯連接。他運用高超的導演技巧將夢境中一切詭譎的、碎片化的、混亂的、非理性的、顛覆常識的場景合理化,把符合蒙太奇敘事邏輯的多個鏡頭統一到一個鏡頭里,然后用機器和人物的調度代替了剪輯點,這是畢贛超現實電影敘事風格的極大特色。
(一)非線性敘事:夢境與現實雜糅
“原樣復制現實并不是藝術。”③畢贛在運用現實主義手法將夢境現實化的同時,并非一味地復制現實,而是有技巧性地選擇與詮釋,并融入了獨具個人特色的“詩性”敘事審美基調,將影片本身打造成一場憂傷且神秘的碎片化夢境。
影片《路邊野餐》分為凱里、蕩麥和鎮遠三個部分。蕩麥其實存在于陳升的夢境之中,陳升在這里遇見了亡故的妻子和成年的衛衛等。導演運用詭譎的移動鏡頭將故事展開,將夢境與現實雜糅,亦真亦幻。影片《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敘事方式亦是如此。
(二)超長鏡頭:顛覆常識的鏡頭運用
畢贛導演的兩部電影均因超長鏡頭引起熱議。《路邊野餐》有一個42分鐘的長鏡頭,《地球最后的夜晚》更是有著一個長達1小時的超長鏡頭,這完全顛覆了常規的電影敘事模式——蒙太奇敘事。畢贛擅長調度機器與人物使空間頻繁轉換,在顛覆蒙太奇敘事的同時,盡可能符合蒙太奇邏輯。這種現實與夢境交織的敘事手法,顛覆了巴贊所認為的長鏡頭可以完整地、真實地復原世界的觀點,而是以長鏡頭編織了一個幻象世界。
《路邊野餐》中,陳升在到達蕩麥(夢境)時開始了一個42分鐘的長鏡頭。但這個長鏡頭以陳升、成年后的衛衛、衛衛心儀的姑娘洋洋,以及病故的妻子的視角豐富地、多層次地展開敘事。《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羅纮武在尋找情人萬綺雯的旅程中陷入夢境,遇見了幼時好友白貓、與萬綺雯極其相似的凱珍,以及拋棄自己與情人私奔的母親,同樣是以多人敘事視角編織出了一個超現實主義時空,如夢似幻。
(三)“莫比烏斯帶”式的移動鏡頭:詮釋生死輪回
1858年,德國數學家莫比烏斯和約翰·李斯丁發現:把一根紙條扭轉180°后,兩頭粘接起來,一只小蟲可以爬遍整個曲面而不必跨過它的邊緣,這種紙帶被稱為“莫比烏斯帶”。畢贛也巧妙地將這種鏡頭敘事手法融入了自己的作品中。例如《路邊野餐》中,陳升坐著成年后的衛衛開的摩托車去尋找吹蘆笙的人,鏡頭如同“莫比烏斯帶”移動著,陳升在另一方向遇見了衛衛,而后陳升遇見衛衛心儀的黃衣女時,鏡頭跟隨她穿過河,與衛衛再次相遇,然后又走過橋回到了河對岸,回到了陳升視角,在理發店與亡妻對話。《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畢贛運用了相似的詭譎的移動鏡頭跟隨著羅纮武,到凱珍,再到羅纮武,將人生的生死輪回詮釋得淋漓盡致。
三、魔鬼寓于細節之中:借物敘事,以物喻人
畢贛擅長于運用細節來隱喻人和事,將意涵寓于各種細節之中,增強了電影的豐富性和可讀性。
(一)借物敘事
《路邊野餐》中,老醫生讓陳升將一件衣服和一盤磁帶帶給自己多年前的情人,這也成了陳升在夢境中與自我和解的重要道具。舊磁帶封頁上有“告別”“旅程”“情婦”“錯誤”等字樣,這已然將整個故事的主題融入其中。
影片《路邊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中都多次出現了“鐘”和“表”。鐘表是時間的象征,在《路邊野餐》中,陳升掛在墻上停滯的時鐘,意味著他的心停留在過去,難以自拔;而后來到鎮遠,花和尚向陳升坦白接走衛衛的原因時,時鐘的走動意味著陳升時間不再停滯,開始流向未來。影片《地球最后的夜晚》開頭,羅纮武的繼母取下墻上壞掉的時鐘,換上羅纮武父親的遺像,意指其父親生命的終止。
鏡子在電影敘事中是非常重要的道具,而在畢贛的電影中,它是模糊現實與虛擬的重要敘事手段。例如《路邊野餐》中,陳升與老醫生交談時,鏡頭中同時出現老醫生與鏡子中的陳升;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夢境中萬綺雯在與羅纮武說到自己懷孕并且流產之時,畫面中出現的是“真實”的萬綺雯以及背景的鏡子中折射出來的羅纮武,暗示著夢中記憶的“真實”與虛假的邊界被模糊,也回應了男主最初的獨白——“記憶分不出真假,它隨時浮現在眼前”。
火車的行駛,象征著時間與空間的流動。在畢贛的電影中,火車的出現特指夢境的開始或結束。《路邊野餐》中陳升和衛衛一起乘坐的小火車,陳升的兄弟將衛衛“賣掉”時出現的火車,以及《地球最后的夜晚》中出現的火車,都意指時空的變換和夢境的開始。
(二)以物喻人
在早年的電影學習生涯中,畢贛對動物有著深厚的情感。《路邊野餐》中,一只狗貫穿于整部影片;而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將精明、常說謊的朋友比作“白貓”,用動物特征來展現人物性格。
四、探討生命的意義
生與死,性與愛,對于這些寓于人類生命意義的哲學式思考,畢贛運用各種技巧將之體現在影片之中,等待觀眾解讀剖析。
(一)生與死
當陳升與老醫生談到花和尚因為被活埋的兒子托夢,開了一家鐘表店,老醫生表示“那我們開診所也是同樣的原因嗎”時,陳升笑了,也即是默認了自己開診所其實是對因入獄未能顧及父親之死、妻子病故的一種代償。又如老醫生說的“病人好了,也還是會生病,我們這些當醫生的人忙來忙去其實沒什么用”,亦是對生與死的討論。在影片《地球最后一個夜晚》中,羅纮武的母親告訴他,“泥石流不可怕,活在記憶里面才可怕”,也揭示了人生的意涵——不應該只停留在記憶之中,而應放下過去,尋求未來。
(二)性與愛
“無論是人類還是動物,對性都有著本能的需求。”④畢贛的兩部影片都對性進行了探討。這在《路邊野餐》中較為隱晦,以手電筒象征男性生殖器。在凱里,老醫生與陳升的談話中出現過手電筒,以及陳升在蕩麥時,握著妻子的手拿著手電筒,都隱含著性的意味。
德國美學家、移情說代表人之一伏爾蓋特認為:“眾所周知,夢在性事方面尤其放縱,本人在夢中可能變得完全無恥,缺乏道德情感和自律。”⑤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性的表達則更為開放,夢境中的羅纮武與萬綺雯在野外、車里和燒焦的屋子里相互表達著對性愛的渴望。
五、超現實主義敘事風格的形成溯源
畢贛的電影均是植根于自己的故鄉貴州凱里。他從小生長在農村,十五六歲時開始讀詩寫詩,塔可夫斯基對畢贛的電影道路有著深刻的影響。畢贛不僅以其詩集名稱《路邊野餐》作為自己影片的片名,更是將詩歌融入電影之中,用詩歌獨白詮釋劇情,以詩性敘事風格描繪電影人生。
畢贛在談話節目《十三邀》中表示:“作品首先要解決自己(的問題),任何一個藝術工作者都是這樣的,一定是自我的訴求為先。”畢贛的父母在其年幼時因性格不合離異,母親外出打工。畢贛在電影中也射了其本人的家庭關系,尤其是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羅纮武的母親在他小時候拋棄了他,與情人私奔,更是側面反映了畢贛對母親的復雜情感。但值得欣慰的是,在影片長達1小時的夢境中,羅纮武最終幫助母親與情人私奔,與母親和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畢贛對過去的釋懷。
六、結語
畢贛的電影充斥著濃郁的個人敘事風格,運用長鏡頭等現實主義手法將現實與夢境完美結合,打造了一個超現實主義世界。然而,對比《路邊野餐》與《地球最后的夜晚》,后者被人詬病為“豪華版《路邊野餐》”,雖在演技和拍攝技術上有一定的提升,但電影敘事風格并未有大的突破。所以,畢贛在今后的電影創作中仍需進行大膽的突破與創新。
注釋:
①貴州日報.黔籍導演畢贛新作成金馬獎開幕影片[EB/OL].人民網,2018-08-03.http://gz.people.com.cn/n2/2018/0803/c370110-31892691.html.
②馬靜嵐.電影《路邊野餐》的審美疏離化分析[J].美與時代(下),2019(12):121-123.
③[法]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 [M].崔君衍 譯.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9:242.
④[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學三論[M].廖玉笛譯.北京:臺海出版社,2018:8.
⑤[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夢的解析[M].姜春香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19.
——以《山河故人》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