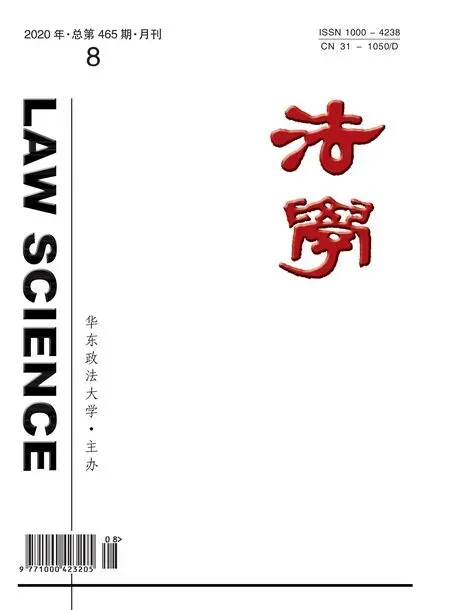《民法典》合伙合同規范的體系基點
朱 虎
《民法典》在典型合同中增設了“合伙合同”一章,替代了《民法通則》關于個人合伙的規范;《民法典》第102 條以下條文規定的非法人組織包含了合伙企業;在《民法典》之外,還有《合伙企業法》對合伙企業進行調整。這些規范的重心和具體內容存在諸多區別,在具體案件中究竟適用何種規范會影響裁判結果。同時,合伙合同中財產的歸屬涉及合伙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以及合伙人與第三人的外部關系,前者的價值重心是實現合伙人之間的公平,后者的價值重心是維護第三人的交易安全以降低交易成本。這兩種不同的價值考量,再疊加上不同規范群預設對象的不同,導致合伙財產歸屬問題變得復雜。雖然合伙合同也是合同的一種,但是,合同作為所有交易的“公分母”,其本身又可以區分為不同類型。《民法典》合同編通則的規則多是以買賣等雙務合同作為原型構建,合伙合同呈現出區別于雙務合同的諸多可能,由此,合伙合同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適用合同編通則規范,就存有諸多疑問。因此,關于合伙的規范,至少涉及《民法典》中的主體規范、物權規范、合同規范以及《合伙企業法》中的規范,如果將這些規范進行組合,就呈現出極為復雜的規范關聯,進而導致具體案件中規范適用的復雜性。考慮到所有類型的合伙都以合伙合同為前提,因此,最為重要的就是以涉及合伙的規范為出發點,確定《民法典》合伙合同一章規范的體系基點,將這些基點作為合伙規范體系聯結的中心,厘清所涉規范的關聯性,進而對法秩序中關于合伙的規范予以體系化整合,并為具體規范的適用和續造確定整體方向。
本文的論證主題是,《民法典》中的合伙合同規范是以未形成組織的合伙為預設對象,進而合伙財產并非屬于合伙組織而是由全體合伙人共同共有,同時合伙合同具有非交換性或者組織性,這些體系基點會影響合伙合同章具體規范的解釋、適用和續造。據此,合伙合同章規范的預設對象、合伙合同中財產的歸屬和合伙合同的非交換性相互連接,共同塑造了《民法典》合伙合同規范的體系基點。
一、合伙合同規范的預設對象
(一)預設對象和規范影響
合伙在實踐中可根據不同的標準區分為不同的類型,合伙規范的首要問題就是以何種類型的合伙為預設對象。類型區分都是目的導向的,區分目的不同導致區分標準不同,進而形成不同的區分結果和合伙類型。以是否存在穩定的營業為標準,合伙區分為民事合伙和商事合伙;以是否頻繁發生對外交往為標準,合伙區分為內部合伙和外部合伙;以是否最終形成組織為標準,合伙區分為未形成組織的合伙(合同型合伙)和形成組織的合伙(組織型合伙);在形成組織的合伙中,以是否登記為標準,又可以區分為登記的合伙和未登記的合伙。民法典合伙合同的規范以何種類型的合伙作為預設對象,不同法域都有不同的預設,《德國民法典》關于合伙的規定側重于合同性,而《德國商法典》關于普通合伙的規定側重于主體性;《意大利民法典》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關于合伙的規定更多地體現主體性;《瑞士債務法》區分規定了單純合伙和普通合伙,前者強調合同性,后者強調主體性。〔1〕更多立法例和學說觀點的具體整理,參見肖海軍、傅利:《合伙契約性與主體性的解構——基于民法典分則“合同法編”的視角》,載《當代法學》2018 年第5 期。
這必須考慮到我國《民法典》編纂的規范前提。其中極為重要的是《合伙企業法》已作為特別法存在,其預設對象是合伙企業,即商事的、外部的、組織型的、登記的合伙,這決定了其具體規范的構建。在此前提下,如《民法典》合伙合同規范純然以上述類型的合伙作為預設對象,就必然與《合伙企業法》規范存在大量重復,且并無實踐價值,故只能調整預設對象,將《合伙企業法》預設的合伙類型中的一個或者多個因素弱化。觀察《民法典》合伙合同的規范,其與《合伙企業法》預設對象的最大區分是未形成組織的合伙和形成組織的合伙。如果合伙經由合伙合同形成了組織,則已逸出單純合同的范疇而進入主體法中,這又會反射到合伙合同的規范內容上。具體而言,合伙是否形成組織會在規范內容與規范適用方面產生如下差異。
首先,會影響合伙財產的歸屬。如果形成組織,則合伙財產應當歸屬于組織,《合伙企業法》第20條和《民法典》第104條都承認了組織的財產;但如果未形成組織,則只能將財產歸屬于全體合伙人。〔2〕具體參見下文第三部分的論述。
其次,會影響合伙債務的承擔。在形成組織的合伙中,債務人就是合伙組織,且合伙財產為合伙組織所有,其與合伙人個人財產的區分較為清晰,合伙債權人不先請求以合伙組織的財產清償而直接請求以合伙人的個人財產清償,合伙人有權據此抗辯,這對債權人不會造成其他損失,故《合伙企業法》第38 條和《民法典》第104 條都規定先以合伙組織的財產清償。但在未形成組織的合伙中,債務人是全體合伙人,且合伙財產屬于全體合伙人共有,與合伙人個人財產的區分較弱,并且經全體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即可分割合伙財產,如果合伙人仍享有上述抗辯,則會使債權人的債權實現成本增加。〔3〕同樣觀點,參見[日]我妻榮:《債權各論》(中卷二),周江洪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 年版,第275、277 頁;李永軍:《民事合伙的組織性質疑——兼評〈民法總則〉及〈民法典各分編(草案)〉相關規定》,載《法商研究》2019 年第2 期。故《民法典》第973 條規定合伙人并非承擔補充連帶責任,而是直接承擔連帶責任,更為清晰地體現出以未形成組織的合伙為其預設對象。同時,《合伙企業法》第39 條規定普通合伙人承擔“無限”連帶責任,這同樣體現了其預設對象是形成組織的合伙,有限責任和無限責任的區分在形成組織且出資財產歸屬于組織時才有意義。
這也會對其他問題產生影響。例如,《民法典》并不要求先以合伙財產清償合伙債務,故合伙出資財產的價值確定對合伙債權人并不重要,而僅在合伙人內部補充性地確定利潤分配、虧損負擔等權利義務。因此,對于貨幣以外的出資,只要全體合伙人一致同意,無論是否評估、采取何種評估標準和方法、誰來評估,均無關緊要,無需依出資標的的客觀價額評估以符合資本充實原則。同時,當合伙財產不足以清償合伙債務時,對形成組織的合伙而言,此時縱使合伙人的出資義務未屆履行期,其亦喪失期限利益,未屆期之合伙人應履行出資義務。〔4〕參見劉春堂:《民法債編各論》(下冊),三民書局2013 年版,第52 頁。《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2019〕254 號)第6 條對公司股東出資也規定了一定情形下的加速到期。但是,《民法典》以未形成組織的合伙為預設對象,并不要求先以合伙財產清償合伙債務,故此等出資義務加速到期規則并無必要。正因為如此,《民法典》合伙合同章未對合伙出資的形式、評估、期限等作出規定。
再次,《民法典》合伙合同章未規定與組織相關的規則。例如,《合伙企業法》規定設立合伙企業的條件包括名稱和生產經營場所(第14 條第4 項),同時規定了登記、組織成立日期、營業執照等事項(第9-11 條),但《民法典》合伙合同章對此均未規定。在形成組織的合伙中,組織的解散和清算極為重要,《合伙企業法》第四章對此設有詳細規定。但在未形成組織的合伙中,只存在合伙合同的終止。對于清算,由于不要求優先以合伙財產清償合伙債務,清算的目的并非保護合伙債權人的利益,而是為了保障合伙人之間的公平,故僅是內部清算。〔5〕同前注〔3〕,李永軍文。因此,即使一些民法典規定了合伙的清算程序,但是,這些程序規范都是任意性規范,可以通過全體合伙人的合意排除適用,例如,為發揮合伙財產的組合效益,約定合伙財產由一個合伙人接收而由其向其他合伙人補償。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309 頁; [德]格茨·懷克、克里斯蒂娜·溫德比西勒:《德國公司法》,殷盛譯,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133 頁。因此,較之《合伙企業法》第四章關于合伙企業清算程序的規定,《民法典》中合伙合同終止后的清算規范更為簡略,更尊重合伙人之間的意思自治,僅在第978 條規定了合伙剩余財產的分配比例。同樣,《合伙企業法》基于合伙人承擔補充連帶責任的規定,其第89 條在清算中確立了“先償債后分配”的原則,以避免債權人利益受損,且理論上將該條解釋為強制性規范。〔6〕參見李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142 頁。但在《民法典》規定的合伙中,第978 條應僅是任意性規范,如果合伙人在支付清算費用和清償合伙債務前進行了合伙財產的分配,分配仍然有效,但對未支付的費用和未清償的合伙債務仍要進行內部分擔。
最后,《民法典》合伙合同章強調合伙人之間更強的信任關系。在形成組織的合伙中,存在組織的信用,能夠以組織信用吸收人的信用;但是,在未形成組織的合伙中,則更為著重合伙人之間的特別信任關系。例如,《民法典》并未對合伙人的變更(即入伙和退伙)作出一般性規定。《合伙企業法》以形成組織的合伙為預設對象,組織內部的人員變動不影響組織本身的同一性,故明確規定了入伙和退伙規則。但是,《民法典》的合伙合同章以未形成組織的合伙為預設對象,無法以組織的信用吸收人的信用,更為著重合伙人之間的特別信任關系,新的合伙人加入或者合伙人退出合伙關系,都可能會破壞此種特別信任關系。因此,在《民法典》的合伙中,默認規則是新合伙人加入或者合伙人退出合伙關系,均會導致原合伙合同的終止,并產生新的合伙合同,且原合伙合同和新合伙合同之間不具有同一性,合伙債務或者合伙債權不當然地發生法定的債務轉移或者債權轉讓。當然,即使這并不會對第三人產生影響,但為避免使合伙人的內部關系過于復雜,以合伙合同另有約定或者合伙人另有決定為前提,仍允許不喪失合伙合同同一性的入伙和退伙。〔7〕《德國民法典》第736、737 條所規定的退伙都是以存在合伙合同的約定為前提,這表明其是以合伙合同全部終止為默認規則,同時未明確規定入伙;《瑞士債務法》第542 條則規定了入伙和合伙人地位的轉讓,但未明確規定退伙;《日本民法典》原僅規定了退伙,之后在債法改訂時增加了入伙的規定;《意大利民法典》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則對入伙和退伙都有明確規定。這同樣取決于不同民法典中合伙預設對象的不同。
同時,《民法典》第977 條規定合伙人死亡、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或者終止的,如合伙人無特別約定或者決定,合伙合同即終止,其規范意旨正在于充分考慮合伙人之間的特別信任關系,一旦某一合伙人無法繼續從事合伙事業,合伙合同賴以存在的信賴關系可能就會破裂,故原則上將導致合伙合同的終止。《合伙企業法》第48 條第1 款第1 項、第3 項以及第2 款后半句中的事由與《民法典》第977條中的事由大致對應,但后者規定的后果是合伙人當然退伙。此處區別對待的理由在于,在形成組織的合伙中著重組織的穩定存在,故某一合伙人的退出原則上不應影響整個合伙的繼續存續。〔8〕《德國民法典》第727 條與我國《民法典》第977 條的規范意旨類似,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687 條第1 項則與《合伙企業法》持相同的價值考量。基于同樣原因,對于未定期限的合伙,《合伙企業法》第46 條規定合伙人僅有權聲明退伙,但《民法典》第976 條第3 款規定合伙人可以隨時解除整個合伙合同。
(二)體系效益
合伙形成組織進而作為主體,當然具有諸多好處,例如,方便對外交往,降低合伙取得權利的成本;財產實現資產分割,更有利于保護債權人的權益;克服合伙成員變更帶來的不便,維持合伙的持續,在不喪失合伙同一性的前提下解決合伙的組織變更;降低監管成本等。但是,這同樣會產生主體法定的僵化成本以及由此所導致的服從成本(例如年度檢驗成本)、政治成本、代理成本等。〔9〕參見李鳳章:《從合伙的主體性到主體化》,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6 年第6 期;劉召成:《德國法上民事合伙部分權利能力理論及其借鑒》,載《政治與法律》2012 年第9 期。因此,不形成主體,僅將合伙作為合同,也可能是符合當事人利益的最佳合約安排。《民法典》以最為純粹的未形成組織的合伙為預設對象,強調合同性而非主體性;與之相對,《合伙企業法》以最為純粹的形成組織的合伙為預設對象。〔10〕民法典編纂過程中類似的觀點,參見前注〔1〕,肖海軍、傅利文;房紹坤、張旭昕:《民法典制定背景下的合伙立法》,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 年第1 期;滕威:《民法典編纂背景下合伙立法的評價及建言》,載《海峽法學》2018 年第3 期;王利明:《論民法典對合伙協議與合伙組織體的規范》,載《甘肅社會科學》2019 年第3 期。
換言之,根據合伙的組織性強弱,在合伙的類型光譜中,一個極點是組織性最弱的合同,即《民法典》合伙合同的預設對象;另一個極點是組織性最強的合伙,即《合伙企業法》的預設對象。《民法典》以組織性最弱的合伙這個極點為預設對象,以此設置任意性規范,復雜的中間形態可以由當事人在這些任意性規范的基礎上作調整。如果《民法典》以合伙類型光譜中的中間形態作為預設對象,首先,中間形態的合伙類型非常廣泛,有千變萬化的形態,立法中很難預設一個典型狀態并以此確定默認規則。其次,組織性最弱的合伙當事人如要減弱主體性,可能是十分困難的。一是交易成本問題,此種合伙往往沒有或者沒有詳細的書面協議,最需要法律上的補充性規范。二是特約的效力問題,例如,如果《民法典》規定了退伙作為默認規則,合伙人試圖排除適用該規則,約定任一合伙人死亡等就可以導致合伙合同終止,但這種約定的效力有可能不被司法實踐認可。目前的規范安排使得這兩個預設極點之間存在廣闊空間,當事人可以根據具體利益需求尋求最佳的合同安排以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形成大量的中間類型的合伙,即其組織性比《民法典》預設的合伙類型要強,但比《合伙企業法》預設的合伙類型要弱。在規范安排上,《民法典》和《合伙企業法》越以最純粹的兩個極點作為預設對象,所能夠包含的合伙類型光譜的范圍越廣,調整的區域越寬。反之,《民法典》和《合伙企業法》的預設對象越趨同,越會妨礙當事人的選擇可能性和規范調整的廣度。
更為重要的是,目前的方式能夠使得規范的適用更為靈活和更為符合當事人的利益安排。這在德國法關于合伙權利能力的發展中體現得極為明顯。在弗盧梅看來,合伙不僅是債權關系,還外溢到物權關系,更進一步延伸至主體法上,合伙在屬性上接近于法人,屬于法律主體范疇,享有部分權利能力。〔11〕參見[德]維爾納·弗盧梅:《合伙與合手》,金晶譯,載王洪亮等主編:《中德私法研究》第14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65 頁以下。萊塞爾進一步從主體法的視角主張合伙可以作為法人予以理解,與法人具有同等地位。〔12〕參見[德]托馬斯·萊塞爾:《新變更法視角下的共同共有與法人》,徐同遠譯,載王洪亮等主編:《中德私法研究》第14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92 頁以下。事實上,合伙存在不同的類型,即使不將成員的有限責任理解為權利能力的構成要素,也并非所有的合伙都可作為法人予以同等理解,認為其必然享有完全的或者部分的權利能力。權利能力真正解決的問題是行為歸屬,即將個人的行為理解為組織的行為,故必須存在相應的行為歸屬機制。這種行為歸屬機制包括行為機關、責任體和身份條件。〔13〕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已經實質性地承認了該理論,參見[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債法分論》,杜景林、盧諶譯,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389-390 頁;也請參見杜景林:《德國最高法院的民事合伙造法及評價》,載《北方法學》2015 年第1 期。法人和非法人組織自然存在此種行為歸屬機制,有一些合伙即使未構成非法人組織,但如果為參與法律交往設置了機關和共同的稱號(例如登記和字號),在合伙財產與合伙人個人財產之間實現了相當程度的資產分割,則已具備了組織的行為歸屬機制。〔14〕托依布納從系統論的角度闡述了理解組織的關鍵為其是具有組織化的行動系統的自我描述,包括組織起來的行動系統,組織身份的自我描述,以及通過歸屬機制所發生的身份與行為的循環聯結。參見[德]貢塔·托依布納:《企業法團主義:新工業政策與法人的“本質”》,仲崇玉譯,載[德]貢塔·托依布納:《魔陣·剝削·異化》,泮偉江、高鴻鈞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212頁以下。組織的這三個要素也可被簡單地理解為具備組織規則,名稱、住址、財產等團體身份的自我描述規則,將作為環境因素的他人行為轉換成組織行為的機關、代表、代理和勞動法等歸屬規則。這意味著只有具備此種歸屬機制的合伙才可以具有部分權利能力,而純粹的對內合伙,即使具備合伙財產,但不對外從事法律行為,也僅僅是一種合同關系,而不能外溢到物權關系和主體關系上。〔15〕參見[德]彼得·烏爾默:《共有制合伙?——一種至今未明的組織形式?》,張懷嶺譯,載王洪亮等主編:《中德私法研究》第14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112 頁以下。擴展言之,遺產繼承人共同體雖然基于共同財產成立,并具有特殊的責任體,但不具備機關和身份條件等這些組織的行為歸屬機制,故不能認為遺產繼承人共同體具備主體法意義上的權利能力。認為無論何種合伙都不能作為主體的觀點,同前注〔3〕,李永軍文。
據此,對居于組織性最弱和最強之間的中間類型合伙,在規范適用時,應避免大一統思路,而應根據具體事項,依照其背后的價值、原理乃至政策目的,以及組織需求和參與者值得保護的利益,個別地考慮在具備何種前提時適用或者類推適用何種規范以及到何種程度。〔16〕具體參見李昊:《我國民法總則非法人團體的制度設計》,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12 期。關于德國法中的組織類型光譜,參見[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184-197 頁。換言之,根據上述組織性的判斷因素,具體類型合伙的組織性越強,越有理由類推適用或者適用《合伙企業法》的規范和《民法典》中非法人組織的規范;組織性越弱,越有理由適用《民法典》中合伙合同的規范。因此,也很難將《民法典》合伙合同的規范簡單地認為是一般性規范,而將《合伙企業法》中關于合伙協議的規范認為是特別規范,〔17〕采取此種觀點的,參見嚴城:《民法典合同編(草案)合伙合同的成功與不足》,載《法治研究》2019 年第1 期;李宇:《民法典分則草案修改建議》,載《法治研究》2019 年第4 期。否則就會出現一般性地適用《民法典》合伙合同規范的結果,喪失前述適用上的靈活性。
較之組織性強弱的類型區分,僅就合伙合同而言,民事合伙和商事合伙的區分反而并非那么重要。合伙未必是以營業作為共同事業目的,《民法典》第967 條所規定的共同事業目的也不限于營業,即使合伙未形成商事的合伙企業也不見得組織性一定就較弱。雖然《民法典》在預設對象的商事性方面有所減弱,例如第971 條規定合伙人原則上不得因執行合伙事務請求支付報酬,第970 條以合伙人共同執行為原則等,〔18〕參見李建偉、帥雅文:《民法典合同編分則“二審稿”民商事規范的區分設置檢討》,載《法律適用》2019 年第21 期。但是,《民法典》和《合伙企業法》預設對象最大的不同仍然是組織性強弱。同樣,在判斷組織性強弱時,登記是考慮因素之一,但不是要件,沒有登記的合伙并非一定不能類推適用《合伙企業法》中的規范。登記確實具有諸多好處,例如,合伙人的登記,能夠充分利用合伙人的信用而擴大合伙本身的信用;通過登記予以公示并發生外部效力,有助于保護交易的安全,進而擴大合伙的對外交往。但是,登記僅是為了獲得與登記對應的各種法律便利和行政管理的便利而采取的手段,是當事人基于自己利益而作出的選擇,但并非當事人的義務。〔19〕同前注〔9〕,李鳳章文。《民法典》第103 條第1 款僅規定非法人組織應當“依照法律的規定登記”,這與第77、88、90、92 條等規定“經依法登記成立”不同,由此,在組織性較強而法律未規定必須登記成立時,規范上至少容納了合伙仍然能夠成為非法人組織,進而適用非法人組織規范和參照適用《合伙企業法》規范的可能性。〔20〕同樣觀點,參見李宇:《民法總則要義:規范釋論與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305 頁。
(三)非組織中的對外事務執行
只要不是單純的內部合伙,合伙就會發生對外關系。《合伙企業法》的預設對象是形成組織的合伙,故第37 條規定了此種對外執行機制,并稱之為對外代表,《民法典》合伙合同章對此未規定,這可能會引起一些批評。〔21〕同前注〔17〕,嚴城文。事實上,《民法典》以未形成組織的合伙作為預設對象,在對外關系上并無“對外代表”的可能,但已規定了對外的執行機制,即通過代理解決合伙人之一作出行為的效果歸屬于全體合伙人的問題,這也與委托和代理的區分形成對應。〔22〕《民法通則》第34 條僅規定“合伙負責人和其他人員的經營活動,由全體合伙人承擔民事責任”,并未解決效果歸屬的法律機制問題。
如果以代理解決行為效果的歸屬,使得執行事務合伙人對外行為的效果歸屬于全體合伙人,依據《民法典》第162 條,執行事務合伙人應當在代理權限內以作為被代理人的全體合伙人名義(起字號的則以合伙名義)實施,這也是代理的顯名要求;如果執行事務合伙人以自己名義實施(尤其在純粹的內部合伙中,按照合伙合同約定,合伙人應當以自己名義實施),行為效果不能歸屬于全體合伙人,而僅能歸屬于該執行事務合伙人,除非符合第925 條的規定,〔23〕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關于個人合伙糾紛法律適用問題的解答(試行)》第6 條規定:“當事人以其個人名義簽訂承包合同,但以合伙方式履行承包合同權利義務的,人民法院在審理承包合同糾紛中應認定承包合同載明的主體為承包人。但當事人有證據證明在簽訂承包合同時雙方均明知承包人為合伙各方,或在履行過程中雙方同意變更為以合伙方式承包的除外。”但在合伙人內部可以按照合伙事務處理。〔24〕《瑞士債務法》第543 條第1、2 款對此有明確規定。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254-259 頁;同前注〔5〕,格茨·懷克、克里斯蒂娜·溫德比西勒書,第102-103 頁;同前注〔13〕,迪特爾·梅迪庫斯書,第392-393 頁。所謂的以全體合伙人名義,在起字號時可以字號或者用某一合伙的管理人等頭銜表明,而沒有必要出示全體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名稱。
對外代理權限的范圍根據合伙協議的約定或者合伙人依法作出的決定確定,可以與對內的執行權限不同,但可以推定具有內部事務執行權者也具有對外代理權限,且權限范圍相同。〔25〕參見《德國民法典》第714 條、《瑞士債務法》第543 條第3 款、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679 條。例如,《民法典》中的合伙事務執行以共同執行為原則,故在外部關系中,對外代理也應當共同行使代理權,根據第166 條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26〕有觀點認為,在合伙企業中,除非另有約定,任一合伙人均有權單獨對外代表合伙企業。參見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第105 頁。但是,即使此種單獨代表權對于合伙企業是恰當的,但在民法典規定的合伙中,在價值上安全要重于效率,與合伙企業仍存在不同。其中一人未經全部合伙人同意而代理作出法律行為的,則超越其代理權限形成無權代理。相應地,保護交易相對人的規則也并非《民法典》第61 條第3 款、第504 條或者《合伙企業法》第37 條所規定的越權代表規則,而是《民法典》第172 條規定的表見代理規則。
代表和代理在實質上存在諸多類似之處,但在規范上應予區分,由此導致一些具體問題的差異。《民法典》第61 條第2 款規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義從事的“民事活動”,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而第161 條僅規定代理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兩相對比,可代表的行為比可代理的行為似乎更為寬泛。但在《民法典》規定的合伙中,內部關系中無涉代表或者代理問題;而在外部關系中,所涉及的行為更多是法律行為,雖然也可能涉及準法律行為、公法上的行為等,但這些行為也可通過類推適用代理解決。至于違約責任和因合同無效、被撤銷、被解除等所產生的責任,只要法律行為的效果歸屬于全體合伙人,則這些責任自然由全體合伙人承擔。對于侵權責任而言,如果全體合伙人共同作出決定實施侵權行為,則按照《民法典》第1168 條關于共同侵權的規定承擔連帶責任即可。
真正產生不同的是執行事務合伙人的行為構成侵權時的責任承擔問題。在代表規則中,依照《民法典》第62 條第1 款,法定代表人因執行職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法人承擔民事責任,這可以參照適用于非法人組織。但在代理中不存在類似規定,依據《民法典》第167 條,只有在被代理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為違法未作反對表示時,被代理人和代理人才應當承擔連帶責任。據此可作反對解釋,即原則上被代理人對代理人的違法行為不承擔責任,而是由代理人自己承擔責任。即使要加強對被侵權人的保護,但《民法典》的合伙以未形成組織的合伙為預設對象,對于其他合伙人而言,并不存在組織化的因而邊際成本較低的監督控制機制,這與普通的代理人和被代理人關系并無區別,而與組織和代表人之間的關系存在顯著不同,故一般而言并無足夠理由將其他合伙人列入責任承擔范圍。因此,一般可以認為,未形成組織的合伙并不具備侵權能力,執行事務合伙人應當自己對被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但在內部關系中可依據合伙合同請求其他合伙人分擔。〔27〕同前注〔13〕,迪特爾·梅迪庫斯書,第394 頁;同前注〔5〕,格茨·懷克、克里斯蒂娜·溫德比西勒書,第108、110 頁。這僅指的是未形成組織的合伙這個極點,如果合伙的組織性較強,則可以考慮類推適用《合伙企業法》規則,這仍與前述區分相關。關于合伙組織性較強時合伙人承擔連帶責任,參見[德]漢斯·布洛克斯、沃爾夫·迪特里希·瓦爾克:《德國民法總論》,張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326 頁;王澤鑒:《民法總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171-172 頁。在其他合伙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執行事務合伙人實施侵權行為但未作反對表示時,可認為其構成主觀上的意思聯絡,致第三人受損,則對第三人而言,應由全體合伙人依據《民法典》第167 條承擔連帶責任。〔28〕關于該條規定的法政策檢討,參見王利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詳解》(下冊),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 年版,第746-747 頁(本部分由朱虎撰寫)。
關于合伙人的訴訟,是合伙對外業務執行的特殊樣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45 條區分了起字號的合伙和未起字號的合伙,其規定在起字號的合伙中,合伙負責人(執行事務合伙人)自動延伸到訴訟領域成為訴訟代表人,但這會產生很大的問題。其一,如果有數名執行事務合伙人,誰為負責人;在他們之間意見不一致時更會使得訴訟程序復雜。其二,無法保障其他合伙人的訴訟權利,其他合伙人無法參加訴訟,但執行事務合伙人的訴訟行為對全體合伙人發生效力。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5〕5 號)第60 條不再區分起字號和未起字號的合伙,僅規定有字號的合伙要在法律文書中注明登記的字號;同時,合伙事務執行人不自動延伸到訴訟領域,全體合伙人可以重新推選訴訟代表人。所有未形成組織的合伙的訴訟地位處理都可據此解決。
二、合伙合同中財產的歸屬與確定
(一)合伙財產的歸屬
關于合伙財產的歸屬,《合伙企業法》第20 條規定合伙財產為合伙企業的財產,合伙企業是獨立的民事主體,享有相對獨立的合伙財產。《民法典》第104 條也承認了“非法人組織的財產”。因此,在合伙企業的情形中,合伙財產歸屬于合伙企業,而非合伙人。〔29〕同前注〔6〕,李飛主編書,第32-33 頁;戴孟勇:《論共同共有的類型及其純化》,載王洪亮等主編:《中德私法研究》第14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49-51 頁。在未形成組織的合伙中,《民法通則》第32 條區分了出資財產和合伙經營積累的財產,后者明確規定為合伙人共有,而對前者僅規定為“由合伙人統一管理和使用”;《民法典》第969 條第1 款則對此未作明確規定。在學說中,對于合伙財產的歸屬也存在很大爭議,〔30〕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9 頁。有觀點認為屬于全體合伙人共同共有;〔31〕參見楊立新:《共有權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67-171 頁;劉家安:《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 頁;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244 頁;周顯志、陸露:《試論我國合伙財產的立法定位》,載《河北法學》2005 年第7 期。采此種觀點的判決,參見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蘇13 民終5045 號民事判決書、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8)津01 民終630 號民事判決書。有觀點認為屬于全體合伙人按份共有;〔32〕參見尹田:《物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313-314 頁;同前注〔29〕,戴孟勇文,第51-52 頁。也有學者否定共同共有的概念,而認為合伙財產是合伙人“調整的按份共有”。參見唐勇:《論共有》,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121 頁。采此種觀點的判決,參見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川05 民終501 號民事判決書、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甬民一終字第237號民事判決書。也有觀點認為根據《民法通則》第32 條區分合伙人出資和合伙運營財產,是混合共有。〔33〕參見崔建遠:《物權:規范與學說》(上冊),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479-480 頁。
合伙財產歸屬的爭論是對既有規則的解釋選擇,無法作為確定合伙財產相關規則的起點,毋寧是對合伙財產相關規則予以總結的終點。〔34〕故有學者認為討論該問題意義不大,參見申衛星:《物權法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236 頁。如果僅著眼于合伙財產歸屬的合同性,這實際上是僅著眼于合伙人之間的內部關系,則無論合伙財產是共有抑或不是共有,事實上均無關緊要,對合伙人之間的權利義務而言,如合伙事務執行、利潤分配、虧損分擔等,合伙人可以在合伙合同中約定,即使無約定,關于合伙合同的任意性規范也可以起到補充性作用。換言之,合伙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這種內部關系,并非取決于合伙財產的歸屬,而是取決于合伙人之間的約定以及關于合伙合同的任意性規范,這與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內部關系的規定無必然關系。例如,《民法典》第968 條第2 款規定,在合伙合同終止前,合伙人不得請求分割合伙財產,這與合伙人之間存在合伙關系這種共同關系而屬于“因人聚物”相對應,符合第303 條規定的共同共有特征。但是,即使認為合伙財產屬于合伙人按份共有,屬于“因物聚人”,但基于合伙合同追求共同事業目的的特征,法律仍可對合伙人不得在合伙合同終止前請求分割作出特殊規定。依據《民法典》第301 條,除共有人另有約定外,處分共有物等重大事項需要全體共同共有人同意,這也與第970 條第1 款相同;但是,即使認為合伙財產屬于按份共有,但法律仍可根據合伙合同的特征作出不同于第301 條的規定。
因此,對合伙財產歸屬的爭論主要涉及物權性,這必然涉及合伙的外部關系。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區別主要是“份額”在分割前是否存在。如果認為合伙財產屬于合伙人按份共有,則合伙人對合伙財產整體和單個合伙財產都享有份額,且可以處分該份額;即使合伙人之間約定不得轉讓份額,但該約定僅在合伙人之間具有債權效力,而不具有物權效力,對作為處分相對人的第三人而言沒有意義,其依然可以取得份額。但是,如果認為合伙財產屬于合伙人共同共有,則合伙人對合伙財產整體和單個合伙財產都不享有份額,也談不上處分份額的問題,此時,第三人自然就無法取得份額。
首先觀察合伙財產整體。《合伙企業法》第22 條和《民法典》第974 條都規定了合伙財產份額的轉讓,似乎承認了合伙財產整體的份額存在。但是,這實際上并不涉及財產(Verm?gensstellung),而是涉及“共手份額”(Gesamthandsbeteiligung)。〔35〕Vgl. MüKoBGB/Sch?fer, 7. Aufl., 2017, § 719 Rn. 4; Flume, Personengesellschaft, Springer, 1977, S. 350 f.共有份額是合伙人地位或者資格的一部分,后者除了財產份額之外,還包括共同執行合伙事務、利潤分配、剩余財產分配等權利,是具有復合性的權利,包括自益和共益的權利以及虧損分擔等義務,類似于公司中的股權或者股份。共有份額作為合伙人地位或者資格的一部分,與后者密不可分而不可單獨處分,〔36〕Vgl. MüKoBGB/Sch?fer, 7. Aufl., 2017, § 719 Rn. 6; 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281-283 頁。這也與共同共有所蘊含的日耳曼團體主義聯系在一起。參見唐勇:《共同共有詞義考》,載王洪亮等主編:《中德私法研究》第14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3 頁以下;同前注〔11〕,維爾納·弗盧梅文,第65 頁以下。對我國民國時期繼受共同共有的考察,參見李啟成:《“誤讀”抑或“創造”——近代中國“公同共有”語詞考》,載《北大法律評論》2012 年第2 輯,第481 頁以下。即使承認合伙人對合伙財產整體的份額,但因其必須與合伙人地位一并處分,故也可以認為無需合伙財產整體份額的處分,而只需要合伙人地位的處分。因此,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683 條將之稱為合伙人“股份”,以表明合伙人對合伙財產和合伙債務所分享或者分擔的一定比例或者權數,實際上也就是合伙人地位或者“合伙份額”。〔37〕參見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28 頁;同前注〔17〕,嚴城文。《德國民法典》第719 條第1 款規定不得處分財產份額,但通說認為第727 條允許合伙人地位的轉讓。同前注〔5〕,格茨·懷克、克里斯蒂娜·溫德比西勒書,第123 頁。《合伙企業法》第22 條和《民法典》第974 條規定的合伙財產份額的轉讓,事實上也就是合伙人地位或者“合伙份額”的轉讓,因此,《合伙企業法》第24 條才會規定:“合伙人以外的人依法受讓合伙人在合伙企業中的財產份額的,經修改合伙協議即成為合伙企業的合伙人,依照本法和修改后的合伙協議享有權利,履行義務。”
其次觀察單個合伙財產。對于單個合伙財產,確實存在合伙人共有的問題,例如,作為出資的房屋所有權登記在全體合伙人名下,全體合伙人對該房屋自然處于共有狀態。但是,合伙人對單個合伙財產在合伙終止前是否享有份額?如果認為享有份額,則依據《民法典》第305 條,該份額可以處分給第三人,即使合伙人之間存在禁止處分的約定,該約定也不能對第三人發生效力,第三人仍然能夠取得份額。此時,在該單個合伙財產屬于合伙主要財產的情況下,由于第三人取得了該單個合伙財產的份額,合伙人要對該財產進行利用,則需要取得第三人的同意,這時,第三人就已取得了介入合伙事務的權利,有違合伙目的的實現和合伙人之間的特別信任關系。據此,更為合理的解釋方案就是,合伙人對單個合伙財產也不享有份額。〔38〕同前注〔35〕,Flume 書,第351 頁;MüKoBGB/Sch?fer, 7. Aufl., 2017, § 719 Rn. 8; 同前注〔29〕,戴孟勇文,第52 頁。不同觀點參見Weber-Grellet, Die Gesamthand - ein Mysterienspiel?, AcP 182 (1982), 316, 331.
退一步而言,即使承認合伙人對合伙財產整體和對單個合伙財產的份額,就處分而言,基于上述合伙共同事業目的的實現和合伙人之間的特別信任關系,就必須弱化處分可能發生的效力。或者如《德國民法典》第719 條第1 款規定不得處分,并且通說認為該規定為強制性規范,不得通過當事人約定而被改變,故轉讓行為不能發生物權效力;〔39〕Vgl. Staudinger/Habermeier, 2003, § 719 Rn. 1; MüKoBGB/Sch?fer, 7. Aufl., 2017, § 719 Rn. 5, 8.或者如《日本民法典》第676 條第1 款那樣規定“合伙人就合伙財產處分其份額時,不得以其處分對抗合伙及與合伙已作出交易之第三人”,此時也僅發生債權效力而不發生物權效力。〔40〕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269-270 頁。《瑞士債務法》第542 條第2 款有類似規定。這樣,雖然存在份額但合伙人對份額的處分不能發生物權效力,這與不承認合伙人對合伙財產整體和單個合伙財產的份額得出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民法典》未作出如德國和日本上述規定的前提下,更好的解釋方案是不承認合伙人的份額存在,無論是對合伙財產整體還是對單個合伙財產的份額。〔41〕弗盧梅即直接認為承認合伙人份額“意義甚微”。同前注〔11〕,維爾納·弗盧梅文,第83 頁。如果合伙人就份額處分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合同雖然有效,但僅僅被解釋為利潤分配請求權和清算時所享有的請求權的轉讓,而不能代位行使合伙人在合同中的權利。〔42〕《德國民法典》第717 條承認這兩種請求權的轉讓,同樣觀點參見Staudinger/Habermeier,2003,§ 719 Rn. 4;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270 頁。同樣,單個合伙人的債權人對合伙財產整體的份額進行強制執行,實質上也僅是對合伙人地位中的利潤分配請求權和強制性退伙時的財產分配請求權的強制執行。《民法典》第975 條和《合伙企業法》第41、42 條對此明確規定,否則,就會出現有違合伙目的的實現和合伙人之間的特別信任關系的結果。
據此,合伙財產應當屬于合伙人共同共有,合伙人對合伙財產整體和單個合伙財產在合伙合同終止前都不享有份額。〔43〕《德國民法典》第718 條第1 款、《瑞士債務法》第544 條第1 款、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668 條對此有明確規定。《日本民法典》第668 條將其規定為“共有”,學說上也多認為屬于“合有”,也可認為是加強版的共同共有。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266-267 頁;日本最高裁判所1958 年7 月22 日判決,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12 巻12 號1805 頁。因此,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關于個人合伙糾紛法律適用問題的解答(試行)》第4 條規定:“合伙人訴請確認合伙份額的,人民法院應進行釋明,要求其明確訴請的是確認出資比例、盈余分配比例或是虧損承擔比例,并依照當事人之間的約定及法律規定予以處理。”另外,按份共有人或者共同共有人也享有管理共有物、分配共有物的收益和表決等權利,但仍僅限于對共有物的權利,而并非如同合伙人那樣享有廣泛的合伙事務執行權,故有很大的不同。當然,這種共同共有不以所有權為限,還包括《民法典》第310 條規定的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的共同共有,也包括其他財產的準共同共有,是最廣義上的共同共有,相關規則都可參照適用以所有權為限的共同共有規則。《民法典》第969 條第1 款并未對合伙財產的歸屬予以明確規定,這有助于回避理論上的爭議,而且如前所述,該理論爭議是對既有規則的解釋選擇,是合伙財產相關規則的終點而非起點。既然如此,僅對合伙財產的相關規則予以規定即可,這恰恰是體現立法與法學區分的妥當方式。同時,這種做法同樣有助于避免可能的誤解,即將《民法典》第974 條規定的合伙財產份額理解為物權中的共有份額,事實上,該份額應理解為合伙人地位或者合伙份額。
但是,這并不妨礙全體合伙人一致同意將合伙財產轉變為按份共有,這實質上屬于全體合伙人合意分割合伙財產的一種方式。《民法典》第969 條第2 款規定的“合伙合同終止前,合伙人不得請求分割合伙財產”是任意性規范。可能有所影響的是合伙債務的債權人的利益,但是債權人仍可以請求合伙人承擔連帶責任,而且即使合伙人將共有份額轉讓給他人使得他人取得份額,導致債權人無法執行該共有份額,但除非符合債權人撤銷權的要件,債權人本來就無法禁止全體合伙人分割處分合伙財產,也無法禁止作為債務人的單個合伙人處分其財產。〔44〕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268 頁。
(二)合伙財產的確定
如果合伙財產的歸屬不僅是為了確定合伙人之間的權利義務而僅具有合同性,而是屬于全體合伙人共同共有故具有物權性,就會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保護,于此應當考慮第三人利益的保護機制。與此直接相關的問題就是合伙財產的確定,即財產在何種情況下才構成合伙財產。如果對此欠缺清晰的規則,則可能會損害第三人的利益。此處的第三人不包括合伙債務的債權人,畢竟合伙人承擔《民法典》第973 條規定的連帶責任而非《合伙企業法》第38、39 條規定的補充連帶責任,該債權人可直接請求合伙人對合伙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故合伙財產對合伙債務的債權人沒有太大意義。但是,合伙財產的取得涉及單個財產的受讓人和單個合伙人的執行債權人、破產管理人(背后是全體債權人)的利益。如果單個財產屬于合伙財產,則對該財產的處分屬于執行合伙事務,未依據《民法典》第970條規定處分該財產的,可能會影響單個財產的受讓人取得該財產;同樣,單個合伙人個人債務的債權人申請強制執行該財產時,其他合伙人有權以該財產屬于合伙財產為由提出執行異議或執行異議之訴;單個合伙人破產的,該財產本身也并不屬于破產財產。因此,合伙財產的確定規則對維護這些第三人的利益非常重要。
依據《民法典》第969 條第1 款,合伙財產包括合伙人的出資、因合伙事務依法取得的收益和其他財產。如果僅著眼于合伙財產確定合伙人之間權利義務的作用這種合同性,而認為合伙出資的財產在合伙合同生效后即屬于合伙人共有,或者因合伙事務依法取得的收益和其他財產即使登記在單個合伙人名下也屬于合伙財產,這就會出現未經公示的權利變動,增加了本來就相互熟悉的合伙人之間串通,將合伙人的個人財產虛假轉變為全體合伙人共同共有的合伙財產的道德風險,進而損害第三人利益。因此,必須基于合伙財產屬于全體合伙人共同共有的這種物權性,對合伙財產的確定予以細致考量。
合伙人的出資是合伙財產的初始來源,即使合伙未形成組織,以非貨幣的財產出資的,作為出資的財產權利也應當轉讓給全體合伙人。這意味著能夠作為出資的權利首先是能夠被轉讓的權利,不能轉讓的權利無法被出資;同時,作為出資的權利的轉讓適用該權利的轉讓規則。具體而言,《合伙企業法》第17 條第2 款規定:“以非貨幣財產出資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辦理財產權轉移手續的,應當依法辦理。”《民法典》規定的合伙合同中同樣如此,區別僅在于不是向合伙企業轉讓而是向全體合伙人轉讓。采取登記生效主義的財產權,應當將該財產權登記在全體合伙人名下;采取登記對抗主義的財產權,不登記在全體合伙人名下,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45〕參見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7)滬02 民終4783 號民事判決書。如果是以交付作為生效要件的動產物權,則需要交付;財產權沒有法定公示方式的,則合伙合同生效時即同時移轉權利,〔46〕同前注〔37〕,邱聰智書,第18 頁。例如,以債權出資的,依據《民法典》第546 條第1 款,在債權轉讓合同生效時債權即移轉,不以通知債務人為生效要件。在出資未按照所涉權利的轉讓規則將權利移轉給全體合伙人的情況下,該權利并不屬于合伙財產,但是,其他合伙人對出資人享有的出資請求權和相應的違約請求權是合伙財產的組成部分。〔47〕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265 頁;同前注〔5〕,格茨·懷克、克里斯蒂娜·溫德比西勒書,第105 頁;王千維:《由合伙組織之四大原則看合伙人之更易》,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版,第2 頁。在實踐中,經常出現出資未移轉于全體合伙人名下的情形,例如,貨幣出資合伙人將資金轉入某個合伙人個人賬戶的情形,但合伙人均認可該款為合伙人出資,則可以認為在合伙人的內部關系中,出資義務已經完成;〔48〕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桂03 民終25 號民事判決書。但是,該財產并非合伙財產,而是持有該賬戶的合伙人所有,其他合伙人有權請求該合伙人轉讓該財產給全體合伙人,該請求權屬于合伙財產。
如果全體合伙人因合伙事業依法取得了收益和其他財產,則此部分財產亦屬于合伙財產。除獲得的收益之外,因合伙事業而取得的其他財產包括用合伙財產所購入的新財產,合伙財產所生的天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以及因合伙財產毀損、滅失等原因而獲得的保險金、賠償金或者補償金等。〔49〕參見黃立主編:《民法債編各論》(下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版,第397 頁。《德國民法典》第718 條第2 款對此有明確規定。在該問題上,這與《合伙企業法》第20 條的規定相同。可能的爭議點是何為“因合伙事務”,《合伙企業法》第20 條使用了“以合伙企業名義”,這是因為合伙企業作為非法人組織是獨立的民事主體。而《民法典》以未形成組織的合伙為預設對象,則此時可認為所謂“因合伙事務”的客觀標準是法定的權利移轉公示方式或者“以全體合伙人名義”(起字號的則以合伙名義)。如果一個合伙人以自己的名義取得財產,或者將該財產登記到自己名下,則該財產應當屬于該合伙人所有,并不屬于合伙財產;但是,其他合伙人在證明該合伙人是執行合伙事務而取得時,有權請求該合伙人轉讓該財產給全體合伙人,該請求權屬于合伙財產。〔50〕同前注〔5〕,格茨·懷克、克里斯蒂娜·溫德比西勒書,第105 頁。
據此,在區分合伙人的個人財產和全體合伙人共同共有的合伙財產時,要考慮到合伙財產的具體組成。如果該單個合伙財產有法定公示方式,要依據一般性的法定公示方式確定合伙財產;如果該單個合伙財產沒有法定公示方式,則是依據合伙合同或者以全體合伙人名義取得,并且由主張屬于合伙財產者承擔舉證責任。這有利于保障第三人的利益。以房屋所有權為例,合伙合同約定某合伙人甲以房屋所有權作為出資,但是,甲并未將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全體合伙人名下,故房屋所有權并非合伙財產,屬于合伙財產的僅是請求甲移轉登記的請求權。由于房屋所有權仍登記在甲名下,對第三人而言,該房屋所有權就屬于甲。如果甲以自己的名義將該房屋所有權處分給乙,就是有權處分,無論乙是善意還是惡意,在辦理了移轉登記后都能取得房屋所有權。同樣,甲個人債務的債權人丙,申請對該房屋予以強制執行,其他合伙人也不能以該房屋屬于合伙財產為由提出執行異議或者執行異議之訴;在甲破產時,該房屋就屬于甲的破產財產,其他合伙人不能行使取回權,僅能作為債權人而與甲的其他債權人平等受償。因此,通過與房屋所有權聯系在一起的登記公示方式,有利于保障上述第三人的利益。
如果以債權出資,在合伙合同生效后,該債權即成為合伙財產。對該債權的債務人的利益通過《民法典》第546 條第1 款足以保障,即未通知債務人的,該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但是,如果出資人之后又以自己的名義將該債權轉讓給第三人的,此時就可以參照適用第768 條保障第三人利益。〔51〕《民法典》第768 條實質上構成了債權多重轉讓的一般性規則,本文因主題限制不予展開。如果出資人之后未經全體合伙人的同意,以全體合伙人的名義將該債權轉讓給第三人,此時出資人構成了無權代理,對第三人利益通過《民法典》第172 條的表見代理予以保障。如果以動產所有權出資,則需要將該動產交付給全體合伙人,全體合伙人可以授權出資人代表全體合伙人占有,此時,交付的公示性非常弱,但出資人將占有的動產所有權以自己的名義轉讓給第三人的,第三人利益可以通過《民法典》第311 條的善意取得予以保障。如果出資人未經全體合伙人同意,以全體合伙人的名義將該動產轉讓給第三人的,對第三人利益同樣通過《民法典》第172 條的表見代理予以保障。
換言之,合伙財產屬于全體合伙人共同共有,這使得合伙財產的歸屬具有物權性,就會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保護,按照前文所述,合伙財產的確定必須考慮單個合伙財產的法定公示方式。由此,首先通過法定的公示方式實現對第三人利益的保護,進而通過其他一般性的相關規則,例如善意取得、表見代理等,進一步保護第三人的利益。對于不存在法定公示方式的單個合伙財產,仍會出現第三人利益保護機制的欠缺,但這已不是合伙財產屬于全體合伙人共同共有所產生的問題,而是因不存在法定公示方式而在所有場域中都會出現的一般性問題,單純在合伙中設計特殊的規則試圖解決這個一般性問題,實際上既是越俎代庖,也會徒勞無功。
更進一步而言,就第三人利益的保護,合伙財產與夫妻共同所有的財產的區別就在于,是否存在出資行為和是否存在以共有人名義取得的可能性。在合伙中,存在出資行為,經由出資將合伙人個人財產轉變為共有財產,這要求適用一般性的權利移轉規則,故有法定公示方式的要采取法定公示方式;但是在婚姻中不存在類似的出資行為,無法作出與合伙中相同的要求。同時,在合伙中,因合伙事務取得的財產成為合伙財產,要求取得財產要以全體合伙人的名義;但是在婚姻中,無法事事要求以夫妻雙方名義作出,故《民法典》第1060 條規定了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對夫妻雙方都發生效力,這已溢出代理的規則而確定了特殊的歸屬規則。〔52〕參見王戰濤:《日常家事代理之批判》,載《法學家》2019 年第3 期;朱虎:《夫妻債務的具體類型和責任承擔》,載《法學評論》2019 年第5 期。因此,較之合伙財產,在夫妻共同所有的財產中,就會出現大量未予公示的隱蔽權利變動,對第三人利益保護的需求就更為強烈,由此可能需要引申出一些特殊的規則設計,包括對夫妻共同所有財產可能采取“潛在共有”的理論,實質上是將夫妻共同所有財產僅作為夫妻內部關系,即共有僅具有債權性,對外仍依據物權公示原則確定權利歸屬。據此,夫妻共有的房屋或者股權僅登記在夫妻一方名下時,對第三人而言,該房屋或者股權就屬于登記的夫妻一方所有,以此實現對第三人的保護。〔53〕具體參見龍俊:《夫妻共同財產的潛在共有》,載《法學研究》2017 年第4 期;賀劍也將此稱為更優的“債權方案”,參見賀劍:《論婚姻法回歸民法的基本思路——以法定夫妻財產制為重點》,載《中外法學》2014 年第6 期。但是,就保護第三人利益的目標而言,合伙財產沒有必要采取此種特殊的債權性共有或者潛在共有方案,而是應選取更符合體系的解釋方案,承認合伙財產共同共有的物權性,通過法定公示方式和全體合伙人名義等一般性規則實現對第三人的保護。
(三)合伙財產共同共有的規則延伸
合伙財產由全體合伙人共同共有,與單個合伙人的個人財產區分,合伙財產成為一個特別財產,因此單個合伙人的債權人僅有權追索債務人的個人財產,而無權追索合伙財產,這有助于實現正向的資產分割(affirmative asset partitioning),〔54〕See Hansmann & Kraakman, The Essential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aw, 110 Yale L. J. 387(2000);張永健:《資產分割理論下的法人與非法人組織——〈民法總則〉欠缺的視角》,載《中外法學》2018 年第1 期。同時,除非有特別規定,《民法典》關于共同共有的規則也同樣應適用于合伙財產,例如合伙財產的管理費用和稅收等其他負擔規則等。
在合伙財產為債權時,該債權本身也屬于全體合伙人共同共有,學說上稱之為“準共同共有債權”“共同債權”或者“協同債權”,〔55〕具體參見李中原:《多數人之債的類型建構》,載《法學研究》2019 年第2 期。《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11.2.1 條、《歐洲合同法原則》第10:201 條和《歐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3-4:202 條都對此種債權予以承認,以區別于按份債權和連帶債權。《民法典》并未規定此種債權,但其關于共同共有的規則也應參照適用于此種債權。這意味著《民法典》第521 條關于連帶債權的規則并不能當然適用于此種債權,〔56〕這涉及債權本身的歸屬,而與《民法典》第307 條所規定的因財產共有的歸屬而產生的債權債務為連帶之債不同。最為重要的是抵銷。按照《民法典》第521 條第3 款結合第520 條第1 款,抵銷具有絕對效力,這隱含著抵銷的可能性。但是,作為合伙財產的債權屬于合伙人的共同債權,共同債權的債務人必須向全體合伙人履行,以保障全體合伙人的利益,基于履行和抵銷的同等效力,自然也不允許共同債權的債務人以其對單個合伙人的債務抵銷該共同債權。據此,《合伙企業法》第41 條規定,合伙人發生與合伙企業無關的債務,相關債權人不得以其債權抵銷其對合伙企業的債務。〔57〕同樣的規定參見《德國民法典》第719 條、《意大利民法典》第2271 條、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682 條第2 款。在《民法典》規定的合伙中,基于債權由全體合伙人共同共有,則同樣不允許共同債權的債務人以其對單個合伙人的債權抵銷該共同債權,主張抵銷的,不發生抵銷效力;而且,作為債務人的單個合伙人也不得以其個人債務抵銷共同債權,〔58〕同前注〔37〕,邱聰智書,第28 頁。這也是由其不得未經其他合伙人授權單獨受領共同債權的債務人作出的給付而自然推導出來的結論。這同樣有助于實現正向的資產分割。〔59〕在該問題上,資產分割并非規則設計的前提,而是規則設計所要實現的目標,雖然資產分割存在強弱程度,但考慮到共同的事業目的,還是要通過規則的設計實現弱的資產分割。
該結論有可能會產生增加道德風險的擔憂,即合伙人之間串通將原是單個合伙人的個人債權轉變為合伙債權,導致該債權的債務人不能以其對該單個合伙人的債權主張其本可主張的抵銷權,這會損害其利益。這種道德風險主要發生于意定債權中,但如前所述,在意定債權中,合伙債權的取得必須有全體合伙人的名義,否則就是個人債權,在作出法律行為時,如果沒有全體合伙人的名義,債務人即可主張該債權為單個合伙人個人的債權,進而以其對該單個合伙人的債權主張抵銷,這已防止了上述道德風險。同時,也有可能出現單個合伙人與其他合伙人串通,虛構該單個合伙人已經以其個人債權對合伙出資的事實,從而使得該債權成為各合伙人的共同債權,同樣有可能使得該債權的債務人不能以其對該單個合伙人的債權主張其本可主張的抵銷權。但是,將個人債權對合伙出資,適用債權轉讓的一般規則,依據《民法典》第549 條,該債權的債務人對該單個合伙人的抵銷權仍然延續,也同樣不會損害該債權的債務人利益。
三、合伙合同的非交換性
(一)交換性和非交換性
《民法典》將合伙合同作為典型合同的一種,這意味著合伙合同中的共同事業目的、合伙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等約定,都對合伙人具有約束力,各個合伙人都應當按照合伙合同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合伙人也基于合伙合同負有義務,任何一個合伙人違反合伙合同對其他合伙人都構成違約。〔60〕具體論述,參見王利明:《論合伙協議與合伙組織體的相互關系》,載《當代法學》2013 年第4 期。合伙合同的合同性強調的是合伙人的意思自治,畢竟合伙合同不同于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尚未取得主體法意義,因此,合伙人仍有其獨立的存在,有關合伙的組成和事務執行,也并未取得獨立于合伙人的意思而客觀存在的地位,仍與合伙人的意思相關,由全體合伙人的意思決定、補充甚至變更,合伙作為合伙人意思一致的效果,通過各合伙人對其他合伙人擁有要求其履行出資義務以及其他事務執行所需要的合作的權利而形成。〔61〕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224、226 頁。這也同時意味著合伙合同僅對合伙人產生約束力,而未如同公司章程那樣對外產生法律效力。
但是,即使如此,合伙合同也是形成合伙這種共同體的協議,合伙人不僅是債權人和債務人,也是合伙共同體的成員,即使該共同體的組織性沒有非法人組織那樣強。為促進共同的事業目的,合伙合同包括最初時合伙人的合意,也包括合伙存續期間合伙人的合意,以為合伙共同體的發展奠定基礎和提供決策機制。這與典型的雙務合同存在明顯區別。在典型的雙務合同中,首先當然要求當事人的給付義務之間存在對價關系(牽連性),在合伙合同中也同樣存在這種特征,例如合伙人出資的給付義務與其他合伙人出資的給付義務之間是相互依賴的。但是,在典型的雙務合同中,當事人之間的給付義務還具有交換性,是為了各自的利益而交換給付,例如在買賣合同中,買方支付價款是為了賣方的交付并轉移所有權。在合伙合同中,合伙人是“為了共同的事業目的”,是以為了全體合伙人的利益而統合給付為目的,不限于一次性的或者具體化的交換,而是針對一個動態程序中的共同目的。〔62〕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224-227 頁;同前注〔5〕,格茨·懷克、克里斯蒂娜·溫德比西勒書,第79-82 頁。據此,合伙合同就并非多組具體的雙方合同之間的簡單疊加,并非對某個合伙人而言,其他的合伙人都是他的“對方當事人”。這就是合伙合同的非交換性,即組織所有合伙人實現共同的事業目的。
《民法通則》第30 條對個人合伙的界定也通過“各自”和“合伙經營、共同勞動”體現了對價性和非交換性這兩個因素。〔63〕《德國民法典》第705 條、《瑞士債務法》第530 條第1 款、《意大利民法典》第2247 條、《日本民法典》第667 條第1 款、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667 條第1 項關于合伙合同的界定規定也都將對價性和組織性結合起來。而《民法典》第967 條關于合伙合同的界定,更為強調合伙合同的非交換性,其中“為了共同的事業目的”“共享利益、共擔風險”都是如此。最為典型的是,其對合伙合同通過“協議”予以界定,并未如同之前關于其他典型合同的界定中那樣使用“合同”,更是強調合伙合同的非交換性,回應了《民法典》第134 條第1 款所規定的雙方法律行為和多方法律行為的區分。〔64〕同樣更為強調合伙合同組織性的界定,參見《俄羅斯民法典》第1041 條、《美國修正統一合伙法》第101 條。
(二)對規范適用的影響
合伙合同是合同,這意味著應當適用關于法律行為和合同的一般規定,尤其是但不限于關于法律行為和合同成立的規則。但是,合同編通則中的規范更多地是以典型的雙務合同為原型而構建的,故無法完全適用于合伙合同。所謂的合伙合同是合同性和非交換性的結合,并未對規則適用提供清晰的指引,因此,關于合伙合同是原則上適用一般規則,但基于其非交換性不應當適用的除外,抑或是原則上不適用一般規則,但基于其合同性應當適用的除外,會產生持久的爭論。《民法典》第967 條對合伙合同非交換性的強調事實上隱含了一個規則適用的結論,即原則上不適用一般規則,只有在基于合伙合同中不同給付義務的關系,產生了與典型雙務合同類似的利益基礎時,才可以適用一般規則。這對合伙合同中關于效力瑕疵、出資義務的履行抗辯權等規則的適用例外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同時也會影響解除、抵銷等一般規則的適用。
1.效力瑕疵
合伙合同作為法律行為的一種,自然也應當適用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瑕疵等法律行為的效力瑕疵規則,但是,基于合伙合同的非交換性,應當在后果方面有所調整。首先是應當以部分無效為默認規則。《民法典》第156 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部分無效,不影響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這隱含了全部無效作為一般規則,理由在于當法律行為部分無效時,推定當事人無意受到不完整的法律行為的約束。〔65〕同前注〔20〕,李宇書,第731-732 頁;《德國民法典》第139 條也采取同樣觀點。而在合伙合同中,基于合伙合同的非交換性,全部無效不利于實現合同追求的共同事業目的,故應以部分無效為原則,使之不影響其他部分效力,再以任意性規范補充。〔66〕同前注〔27〕,漢斯·布洛克斯、沃爾夫·迪特里希·瓦爾克書,第168 頁;同前注〔5〕,格茨·懷克、克里斯蒂娜·溫德比西勒書,第84 頁。主張在所有法律行為中都應當以部分無效為原則的觀點,參見陳甦主編:《民法總則評注》(下冊),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4 頁(本部分由葉金強撰寫)。
其次是對自始無約束力的限制。《民法典》第155 條規定無效的或者被撤銷的民事法律行為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在合伙并未開展合伙事務之前,即合伙合同尚未履行,或者已經出資但尚未與第三人發生法律關系,此時純粹是合伙人之間的內部關系,并無保護外部交易安全和其他第三人利益的必要,于此僅是純粹債法上的意義,對其適用一般規則并無問題,合伙合同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由此應適用《民法典》第157 條,產生實物返還、不能或者沒有必要實物返還時的價值返還和賠償損失責任。〔67〕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230 頁。也有觀點認為,只有在未形成合伙財產時才可如此。同前注〔5〕,格茨·懷克、克里斯蒂娜·溫德比西勒書,第85、157 頁。但是,即使已形成合伙財產,只要未與第三人發生法律關系,仍僅是純粹的合伙人之間的內部關系,適用一般規則似乎并無問題,且在被欺詐出資的情形中尤為必要。
但是,如果已經開展合伙事務,無論是法律行為還是非法律行為,已經與第三人發生法律關系,就存在保護第三人利益的必要性,如果使合伙合同自始無約束力,則意思表示人自始就并非合伙人,可能會損害第三人的利益。〔68〕在公司設立瑕疵中該問題尤為重要,學者多主張公司被撤銷的判決不具有溯及力,僅發生解散公司使公司進入清算狀態的后果,公司解散前實施的行為不因此受到影響。具體參見施天濤:《公司法論》,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93 頁以下。因此,可能更佳的方案如下。其一,在合伙人之間的內部關系中適用自始無約束力規則,例如,合伙人因受欺詐而作出了不利的利潤分配比例約定,該約定撤銷后自始無約束力。其二,在外部關系中,對自始無約束力予以變更,原則上僅使得其向將來發生效力,該合伙人對在此之前的第三人仍要承擔合伙人的責任,此時無需考慮第三人的善意與否問題。〔69〕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231-233 頁;同前注〔5〕,格茨·懷克、克里斯蒂娜·溫德比西勒書,第84 頁,第156 頁以下;同前注〔13〕,迪特爾·梅迪庫斯書,第196 頁以下。當然,在此也要考慮一些特殊的例外情形,例如,基于對欠缺相應行為能力的合伙人的特殊保護需要,不應使其承擔責任;合伙人之一對另外一個合伙人實施欺詐,而欺詐人同時也是交易第三人,此時對交易第三人沒有保護的必要。
當三人以上訂立合伙合同時,其中一人的意思表示具有效力瑕疵而無效、被撤銷或者確定不發生效力,基于合伙合同的特殊信任關系,可以考慮認為合伙合同全部喪失效力,而在其他合伙人之間也不能發生效力,除非可以認為其他合伙人有成立合伙的意思。〔70〕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230 頁。但《日本民法典》第667 條之三作出了不同規定。即使合同效力仍然在其他合伙人之間發生,但其他合伙人可以因該重大事由而解除合伙合同。
2.出資義務的履行抗辯權
合伙人是否能夠行使出資義務的履行抗辯權,基于合伙合同的非交換性,較少持絕對肯定的觀點,但存在否定和限制肯定的不同觀點,即使在限制肯定的觀點中,在何種情況下應予肯定也存在不同。〔71〕否定觀點,參見王洪亮:《〈合同法〉第66 條(同時履行抗辯權)評注》,載《法學家》2017 年第2 期;同前注〔10〕,王利明文;同前注〔3〕,李永軍文;《日本民法典》第667 條之二第1 款采取了否定觀點。在限制肯定觀點中,較多共識是在兩人合伙中適用,但就其他情形有無適用余地則觀點不同。參見史尚寬:《債法各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684-685 頁;同前注〔37〕,邱聰智書,第20-21 頁;同前注〔3〕,我妻榮書,第227-228 頁;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6 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264 頁;同前注〔5〕,格茨·懷克、克里斯蒂娜·溫德比西勒書,第82 頁;同前注〔47〕,王千維書,第4 頁以下;同前注〔4〕,劉春堂書,第45 頁。此時應當根據合伙合同的非交換性中合伙人的具體利益狀態予以判斷。
首先是兩人合伙的情形。舉例言之,甲和乙簽訂合伙合同,并明確約定了與實繳出資比例不同的合伙份額,甲不履行出資義務,請求乙履行出資義務,如果乙不能行使履行抗辯權,在其履行出資義務后,實際上是授信給甲,如果甲資力不足,就會出現甲的合伙份額被執行或者列入破產財產的情形,雖然乙仍享有出資請求權,但僅為普通債權,無法避免損失。這意味著乙的風險因不能行使履行抗辯權而大大增加。如果乙能夠行使履行抗辯權,則可以督促甲履行出資義務,進而實現共同事業目的,同時避免增加自己的風險。雖然乙能夠以甲違約未出資為由解除合同,〔72〕《日本民法典》第667 條之二第2 款規定:“合伙人,不得以其他合伙人不履行基于合伙合同之債務為理由,解除合伙合同。”但這會進一步增加合伙人的上述風險。但解除和履行抗辯權的功能本來就有區分,履行抗辯權至少能給予雙方進一步磋商打破僵局的機會,故不能以乙能夠解除為由否定乙的履行抗辯權。據此可以認為,此時合伙合同具有類似于雙務合同交換性的特征,〔73〕Vgl. MüKoBGB/Sch?fer, 7. Aufl., 2017, § 705 Rn. 169.其非交換性較弱,乙可以在甲未出資的比例范圍內行使履行抗辯權。
其次是三人以上的合伙情形。仍舉例說明,甲、乙、丙三人簽訂合同,此時又會出現兩種情形,即尚無合伙人履行出資義務和已有合伙人履行出資義務。在尚無合伙人履行出資義務的情形中,甲對乙請求,如果乙不能行使履行抗辯權,則乙必須出資,這實質上是對甲和丙同時授信,則在甲或者丙資力不足時,乙的風險就更大,故此時應允許乙行使履行抗辯權。在甲已經出資而乙和丙尚未出資的情形中,當同樣未出資的丙對乙提出履行請求時,兩者處于相同地位,無需在丙和乙之間對丙予以特殊保護,故乙可以對丙行使履行抗辯權。但是,當甲對乙和丙提出履行請求權時,甲已經出資,其已經授信,具有較大的風險,故對甲的利益應當予以更強的保護,故乙和丙不得行使履行抗辯權,否則會增加甲的風險,進而形成競相不出資的局面,妨礙共同事業目的的實現,增加交易成本。但是,如果甲對乙提出全部履行請求,但卻不對丙提出履行請求或者僅請求丙履行較少比例的出資義務,這違反了乙、丙之間合伙人地位的平等性,尤其在甲和丙存在關聯關系時容易增加道德風險,故應承認乙有權在相應范圍內行使履行抗辯權。〔74〕Vgl. MüKoBGB/Sch?fer, 7. Aufl., 2017, § 705 Rn. 168.而所謂的相應范圍就是請求丙履行的出資比例范圍,例如,甲請求乙履行全部出資義務,而僅請求丙履行1/3 的出資義務,則乙有權就其約定出資的2/3 比例行使履行抗辯權。
3.對其他規則適用的影響
合伙人之間的出資義務不存在交換關系,因此,應當認為這不屬于《民法典》第568 條第1 款中“當事人互負債務”的抵銷要件,即使只有兩個合伙人。基于《民法典》第566 條第1 款中的“合同性質”,合伙合同的解除不能產生溯及力;同時,由于合伙合同的非交換性,在判斷是否存在法定解除事由時,合伙的共同事業目的構成了重要的判斷標準。在合伙人履行出資義務不符合約定時,合伙合同所具有的共同事業的目的這種非交換性,會影響對《民法典》第582 條中“合理選擇”的判斷。例如,基于共同事業的目的,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的體現不應當是據此減少其他合伙人的出資,而僅可以考慮對有瑕疵的出資予以重新厘定比例。〔75〕同前注〔5〕,格茨·懷克、克里斯蒂娜·溫德比西勒書,第88 頁。
四、結論
第一,與《合伙企業法》以形成組織的合伙(組織型合伙)為預設對象不同,《民法典》合伙合同一章的規范以未形成組織的合伙(合同型合伙)為預設對象,這決定了《民法典》中合伙合同有關合伙財產的歸屬、合伙債務的承擔、合伙出資的價值確定以及入伙和退伙等方面的諸多具體規范與《合伙企業法》有明顯差異。
第二,《民法典》中合伙合同的預設對象與《合伙企業法》的預設對象分別構成了合伙類型光譜中的兩個極點,大量中間類型的合伙根據其組織性的強弱個別考量適用或者類推適用何種規范,從而使得規范的適用更為靈活和更為符合當事人的利益安排,實現規范的最大體系效益。
第三,與合伙組織通過“代表”解決對外行為的歸屬不同,未形成組織的合伙通過“代理”解決對外行為的歸屬問題,對第三人的保護也相應地適用表見代理的制度。據此可進一步推導出未形成組織的合伙欠缺組織化的監督控制機制而不具有侵權行為能力,全體合伙人對執行事務合伙人的侵權行為原則上對外不承擔連帶責任。
第四,與合伙組織中合伙財產歸屬于組織不同,未形成組織的合伙中合伙財產歸屬于全體合伙人共同共有,合伙人對合伙財產整體和單個合伙財產在合伙合同終止前都不享有份額,所謂的“合伙財產份額”實質上是合伙人地位。此種共同共有的物權性對外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保護,于此將通過法定公示方式和全體合伙人名義等一般性規則得以實現。共同共有中蘊含的資產分割目標通過抵銷限制等規則進一步得以貫徹。
第五,即使《民法典》合伙合同章預設的合伙未形成組織,但基于合伙中共同的事業目的,仍然構成了共同體,故合伙合同具有非交換性而不同于雙務合同,這對《民法典》合同編通則的規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合伙合同會產生重要影響,對于有關效力瑕疵、出資義務的履行抗辯權等規則適用于合伙合同應予以適度調整。
本文并非是對《民法典》合伙合同一章條文的簡單注釋,而是試圖通過對條文的細致梳理,確定這一章條文的整體體系基點,即預設對象是未形成組織的合伙、合伙財產屬于全體合伙人共同共有以及合伙合同具有非交換性。基于這些體系基點,能夠對《民法典》合伙合同這一章的規范意圖和內容作出整全式的體系理解,進而能夠為之后規范的適用確定基本的思考方向,實踐中的諸多問題能夠根據這些基點,結合具體的規則和價值考量而得到更為妥當、靈活以及合體系的處理,實現規范的妥當適用和開放續造。此外,上述三個體系基點分別涉及主體和合同的關系、物權和合同的關系、合同內部的交換性和非交換性的關系,甚至還擴及合伙共同體與婚姻共同體的不同,事實上是以合伙合同為切入點,考量德國法學說中的“權利共同體”理論,探究此種理論在我國《民法典》中的可能性,并以具體的規范內容返觀此種理論的正當性及其限度,分析此種理論對實踐的可能影響。通過立法、司法和法學的生機勃勃的有機互動,《民法典》才可能并非法學的“墳墓”,而是法學進一步發展的基礎。畢竟,《民法典》的整體形象是立法、司法和法學通過持續的交流和協力而共同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