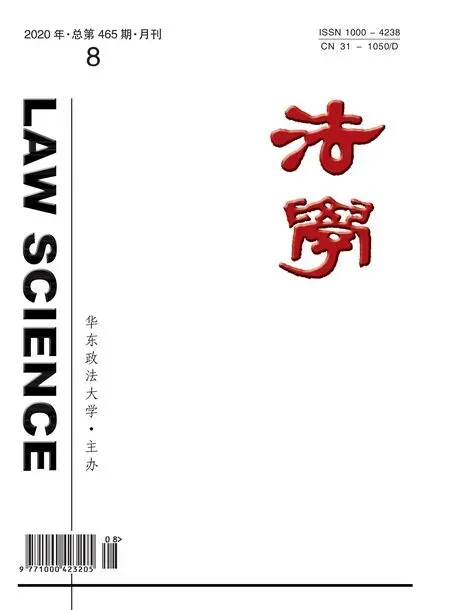認真對待社會規范
——法律社會學的功能分析視角
吳元元
充分挖掘多元治理機制的制度潛能,有效實現協同共治,是國家治理技術現代化轉型的題中應有之義。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良性變遷,隱喻著社會治理欲求的目標應當在以下層面得到全面落實:優化執法資源配置、儉省執法成本、提升執法效率、增強執法認同感。循此邏輯,在執法資源稀缺、執法負荷沉重的雙重約束下,社會治理亟需治理技術和能力的根本性轉型,需要以整體主義的系統性制度觀,全面衡量在特定的經濟生產方式下治理目標所面臨的社會約束條件,選擇與之相匹配的治理機制和附著其上的規范體系。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大命題,經由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 “十三五”時期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十九大進一步闡明至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以及至本世紀中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應當“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上述國家治理的科學邏輯和實踐智慧一脈相承、一以貫之。從治理技術的角度觀察,國家治理的現代性變革和轉型,其核心要義就在于:如何確立“巧治理”(smart governance)〔1〕See Zsuzsanna Tomor, Albert Meijer, Ank Michels, Stan Geertman, Smart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Cities: Findings from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Vol. 26, No. 4, 2019, pp.3-27.的意識自覺和決策視角,有機整合不同的制度資源,深入提煉其中的治理機能,使得各類規范都能因事因地而宜,皆有用武之地。特別地,不少規范都有相應的自我實施機制,當適配的社會約束條件成就之時,自我實施機制隨之浮出地表。若能識別、挖掘、科學運用它們,或者在治理過程中巧妙借力、促成匹配的社會約束條件得以生成,推動自我實施機制的適用,這將極大地減輕國家治理實踐中的制度運行成本,有效回應當下執法資源稀缺、執法負荷沉重的治理難題,由此在具體而微的實踐場域里“實打實”地完成國家治理技術的轉型與良性變遷。
一、從“地方性知識”到社會規范:知識論的考察
社會規范有著自身特有的生發、創立、演化規律和軌跡。所謂社會規范,是國家公權力主體以外的社會主體制定、約定或經由長時段的博弈互動和社會交往演化而成并獲得公共認可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包括不限于村規民約、社規民約、行業章程、行業行規、風俗慣例等。無需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社會規范能夠借助自我實施機制,對社會主體的行為選擇構成制度約束。而從知識論的視角觀之,社會規范的功能在于能夠將特定主體基于所處社會場域的內在運行邏輯而生成的偏好、需求、情感、價值判斷、得失利弊考量等予以匯集提煉,是一種高效的信息聚合—轉化機制。在這個進程中,社群成員的行為條件、行為模式初步顯露雛形,其后在接續而來的反復博弈和社會互動中,可以做什么、應當做什么、禁止做什么以及附著其上的責任后果經由持續的試錯、修正、協調而漸次在人們的認知心理結構中沉淀下來,成為一種集體共識,并固化定型為相應的行為規范,從而足以在社會博弈互動中為相關主體提供行為指引、價值評判,建立主體之間所期待和信賴的穩定預期。
(一)作為“地方性知識”聚合—轉化機制的社會規范
與由國家強制力支持的立法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徑不同,社會規范依循的是自下而上的路線。按照知識的分布狀態,無論是關于具體治理程序、操作的技術知識,還是關于利益、情感、心理的價值知識,都是以離散化形態存在的,都是吉爾茲意義上的“地方性知識”〔2〕參見[美]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事實與法律的比較透視》,載梁治平編:《法律的文化解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年版,第73-94 頁。,不存在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中樞機構,足以將這些星羅棋布、繁多如恒河沙數的離散型的知識集中于自身,〔3〕參見[奧]F. A.馮·哈耶克:《知識在社會中的利用》,載《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賈湛、文躍然等譯,施煒校,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年版,第74-86 頁。并據此能夠像柏拉圖筆下的知識論意義上的“哲學王”一般行事,〔4〕參見蘇力:《波斯納及其他:譯書之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92 頁。做出毫無差池的各類重大決策,包括制定規范體系。因此,作為一種規范生產的群眾路線,社會規范具有出色的知識轉化功能,它對于所涉范圍內彌散化的個體的特有知識都予以尊重,并經由反復的博弈互動和民間自治程序將之轉化為相關主體的行為指引和評價,充分體現了聚合民智的溝通理性追求,促成了多元的智識、價值判斷、利益追求和實踐智慧融貫互通的思想交匯的力量。分殊各異的社會主體是嵌入特定社會—歷史語境下的獨特的“這一個”,是在社會—歷史約束條件下的行動者,他們對于所處場域的體驗、感知、訴求,和所面臨的社會約束條件一起,構成了對于他們難以替代的意義之網。他們欲求的“說法”,他們的基于身體記憶/實踐智慧而“習得”的技術知識和價值知識,只有放置在這張意義之網里方能正確解讀。這些“地方性知識”對于個體是獨一無二的,但它們并不自動具備規范意涵。如果沒有經由社會規范而成為一種規范形態,從而推廣成為場域中群體所分享的“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5〕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28 頁。,沒有被從中凝化、提煉出具有明確指引功能的行為模式—責任后果,那么這些知識就依然停留在“地方性”的狀態,缺乏社會通約層面的交流意義。
盡管相較于立法,社會規范的形成需要經歷更為持久的演化過程,但是,由于它們是在特定主體的反復博弈、試錯中“磨”出來的,這一規范的砥礪過程不同于國家公權力的外部強加,更容易為相關主體接受,并將之內化于自身的認知結構之中。附著于特定主體的“地方性知識”能否成為規范的構成要素,并不存在一個事先的周全構設,這取決于在相關主體的無數次博弈中能否有效協調行動者的彼此預期,能否合理定分止爭,能否提供有效激勵,能否成為科學的信號傳遞機制,能否最終真正提升各相關主體的福利水平。〔6〕參見張維迎:《博弈與社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338-348 頁。如能實現上述制度職能,“地方性知識”才得以具備了通約的價值,才能夠在激烈的規范競爭中順利通過多重博弈場景的嚴格考驗而勝出,最終被作為一種群體認可的慣例得到普遍適用。這一博弈、試錯過程,是“地方性知識”獲得規范形態、向社會規范轉化的必經之路,是社會規范形成的特有程序,其中“那些被證明有助益于人們做出更有效努力的規則存續了下來,而那些被證明只有助于人們做出較為低效努力的規則就被其他的規則取代了或淘汰了”,〔7〕[英]馮·哈耶克:《大衛·休謨的法律哲學和政治哲學》,載鄧正來選編譯:《哈耶克論文集》,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社2001 年版,第491 頁。正是由于這一砥礪、探索程序的展開,具有強烈個性色彩的“地方性知識”得以逐步增強規范所必需的共性,從而有效轉化為更具有普遍意義的行為指引規范。恰恰是經由反復博弈而獲得的普適性優勢,社會規范對法律的形成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很多法律規則就是對社會規范的承認和認可:“當代的合同法、商法等等,很多來自于對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之間、私人之間的交易規則的認可(所以來源于羅馬制定法的大陸民法和來源于地中海商業文明的商法在很多地方存在著不一致),后來逐步變成國家法律;而中國古代的法律很多則是來源于社會習慣和風俗,甚至是儒家的學說,即所謂的‘援禮入法’。”〔8〕同前注〔6〕,張維迎書,第335 頁。
(二)“制度企業家”對于社會規范變遷的知識角色
社會規范的形成過程,也是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各類“制度企業家”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在追求更優水平的社會福利狀態的目標指引下,有力推動誘致性的制度變遷的過程。市場層面的企業家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能看到消費者自己搞不明白的需求,第二類是能滿足市場上已經表現出來的需求,第三類是按訂單生產。第一類企業家也就是創造產業的企業家,如亨利·福特、比爾·蓋茨、斯蒂文·喬布斯這樣的人”;〔9〕同上注,第363 頁。而在制度的意義上,企業家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創造社會上絕大部分人需要但還不明白應該是什么的游戲規則,第二類是創造社會上已經表現出來需要但還沒有生產出來的游戲規則”。〔10〕同前注〔6〕,張維迎書,第363 頁。作為特定社會—歷史語境中的行動者,不同的社會主體皆有自己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地方性知識”,都有可能對新規范的形成做出邊際貢獻。如果對于社會規范的生發留出足夠的制度空間,重視人民群眾在自主創生行為指南上的實踐智慧,借助提供制度設計的“試驗田”,鼓勵他們及時發現現有制度框架之外的潛在收益,清醒認識到現有規則的不足或留白,并且對制度變遷所產生的轉化成本和預期收益進行系統的得失利弊分析。此時,眾多獨具創造力的“制度企業家”勢必應運而生,他們將深度開掘特有的“地方性知識”,提煉通約性要素,積極轉化經驗蘊含的實踐理性,規范創生、演化進程中的群眾路線和集體智慧將得到充分的實現。以國家公權力支持下的強制性的制度變遷為參照,“制度企業家”們自主推動的誘致性的制度變遷更強調對于特定約束語境的敏感,對于反映既定約束條件下的利益、情感、心理以及價值判斷的吸納、整合,注重繁復多元的語境化信息和知識的匯集融貫,因此,它的靈活度更高,更容易契合特定場域內的運行邏輯和身處其中的社會主體的特有的制度需求。這些規范看似瑣屑、平常,往往是“法律中心主義”很難顧及或者力所不逮的所在,個中也很難看出存在復雜深奧的法律制度設計技巧和實施技術,如果僅以知識來源地作區分,這類規范似乎過于“鄉土”,過于“生活化”以至于略顯庸常,〔11〕以著名的“楓橋經驗”為例,位于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的楓源村根據本村的實際情況,針對該村創建“AAA 級”景區旅游村的階段性目標,規定了積極開展五水共治、實施垃圾分類、不在綠化帶種菜和不散養家禽等相當具體而微的行為規范。諸如此類的“微小敘事”在各種類型的社會規范中分布廣泛,極為常見。詳見汪世榮、褚宸舸:《楓橋經驗: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實證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4-125 頁。很難被納入注重宏大敘事的制度分析的視野。然而,對于生于斯、長于斯而又具有制度變遷敏感性的“制度企業家”來說,這些構成了他們嵌入其中的社會網絡,他們的意義世界必須附著其上才得以彰顯,他們能夠從這些瑣屑平常的既定約束條件出發,從而厘清影響自己重要決策的深層次社會因素或“暗物質”。而對于這些日常生活之問的解決和規則因應,更注重的是對于社會網絡的情境化理解,是對于諸多基于實踐智慧的“無言之知”的洞察、自覺和“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巧妙運用。盡管和規范化的法律設計或實施技術屬于不同類別的知識,但是,無論是在認知層面還是治理運作層面,它們都以其對于所處場域的出色的因應性、契合性而得以無可替代。
(三)基于知識優勢的社會規范的治理意義
社會治理能否實現預期的制度目標,取決于行為規范能否有效實施;而任何規范的實施,都與兩個基礎要素息息相關:行為的可觀察性和可檢驗性。所謂可觀察性,是指一項行為可以被當事人之外的包括裁判者在內的其他主體便利地察知;所謂可檢驗性,則是一項行為能夠在外部觀察者面前清晰呈現并得以客觀證實。〔12〕參見張維迎:《信息、信任與法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年版,第196-197 頁。法律是一種典型的第三方實施機制,它的有效運轉必須建立在行為的可觀察性和可檢驗性同時滿足的基礎之上。如果行為的外顯只限于當事人自身或彼此之間,抑或是即便可以從外部察知,但卻缺乏有效手段對之進行證明,以至于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形,甚至導致“百口莫辯”的舉證窘境,那么,法律實施機制的運轉即告失靈。概言之,可觀察性和可檢驗性一同構成了法律制度的信息成本,也決定了法律的有效功能邊界,這是任何制度設計都無從繞過的現實挑戰。〔13〕同上注,第198 頁。
由可觀察性和可檢驗性決定,單一的“法律中心主義”在治理實踐中很可能異化為中看不中用的“屠龍術”,而科學高效的治理制度結構應當是法律、道德自律、社會規范分工合作的協同產物。社會規范是繁多如恒河沙數的“地方性知識”的聚合—轉化機制,它們對于分殊各異的利益訴求、價值判斷、心理預期具備個性化的因應之道,能夠有效改變社會治理主體和治理相對方因為知識不足所導致的信息不對稱;同時,加之對于“地方性知識”相當敏感的“制度企業家”的努力,社會規范的知識優勢極大地降低了社會治理對于行為的可觀察性、可檢驗性的要求。在“地方性知識”作為治理底色的支持下,社會規范可以很好地借助公共輿論、社群交往、聲譽機制等社會資源成就自我實施,形成密如凝脂、繁若秋荼的規訓機制,即便無法同時滿足可觀察性和可檢驗性,自我實施機制仍然可以憑借高速流布的信息之網、長期博弈的交往格局、難以替代的互惠資本,或是及時懲罰社會主體的機會主義與道德風險,或是在事前就對之形成充分威懾,從而有效減少社會治理負荷。
不同的治理場景有著各自迥異的“地方性知識”和“地方性需求”,適應這些知識、需求的規范系統及其運行邏輯也分疏有別。正如民諺體現的實踐智慧所言: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量體裁衣看菜吃飯,如果缺乏知識論的意識自覺,無法挖掘、發揮不同規范體系的知識優勢,治理機制與所指向的社會場域的內在邏輯不相適配,那么將會導致南橘北枳,適得其反,而原本用心良苦的制度理想也會隨之落空。在這個意義上,制度構建是沒有普適主義路線的,也不存在哪一種治理機制能夠無差異地適用于所有語境。科學的做法應當摒棄普適主義的思路——比如源自于科斯的法律中心主義,認為這是社會秩序的唯一來源,代之以充分認知社會規范的知識優勢,以及立基其上的適用條件、比較優勢、制度職能,從而促使特定場景下的場域邏輯和以各種鮮活的“說法”表現出來的“地方性需求”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因應,避免應有的規范缺位,而以公權力推動的正式制度卻又無法植根的尷尬境地。〔14〕參見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 鄉土重建》,商務印書館2011 年版,第61 頁。
二、社會規范自我實施機制的構成與運行
社會規范的有效適用,取決于所適用的社會場域能否構成一個埃里克森意義上的交織緊密的社會網絡,能否同時滿足信息高效率流播、行為主體擁有強力維度,以及主體之間是否具備源源不斷的再次相遇的機會等構成性要件。上述要件的滿足,改變了行為主體之間“原子化”的分布狀態,使之得以被整合進一個息息相關、緊密勾連的意義之網;而這個作為整合機制的社會網絡,促成了主體之間更多的共時狀態,縮短了他們彼此的距離——無論是自然空間還是社會空間。行為的可觀察性與時間和距離高度相關,相處的時間越長、距離越近,顯然行為的可觀察性越高,在一般意義上來說,時間和距離與行為的可觀察性成正比。〔15〕同前注〔12〕,張維迎書,第197 頁。因此,在這個網絡之中,形成了社會功能意義上的“熟人社會”,行為的可觀察性大為增強,人們彼此處于“看”而又同時“被看”的狀態。與此同時,一種規訓和自我規訓的意味彌漫其中,行為主體之間繁密如福柯筆下毛細血管一般的權力機制和有機連帶關系隨之即來,〔16〕參見蘇力:《閱讀秩序》,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0 頁。借助聲譽機制等自治技術,行為的可檢驗性難題被巧妙地克服,由此促成了社會規范的自我實施和社群自治。
(一)高效流播與充分共享的信息基礎
“信息是個人行為受到監督的基礎”,〔17〕張維迎:《產權、政府與信譽》,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版,第6 頁。如果主體的某一行為外顯化程度很高,外部觀察者能夠便利地獲得相關信息,這時可以說信息的流動是高效的,分布狀態是均勻的,關于該行為主體,社群成員有著充分的信息—知識作為認知基礎對其展開社會評價,并據此做出對應的社會交往決策。在傳統的社會學—人類學分析框架中,信息得以快速流傳和充分共享的場域主要是指地理意義上的鄉土社會。費孝通先生的研究指出,鄉土社會中人們比鄰而居、雞犬相聞,結成了彼此相當熟稔的“面對面的社群”(face to face group),甚至不必見面就知道對方是誰,正如歸有光在《項脊軒記》里說,他日常接觸的總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腳步聲來辨別來者是誰。〔18〕同前注〔14〕,費孝通書,第14 頁。無需公權力為中心進行信息集中發布,社群內作為自發演化的公共輿論機制的“閑言碎語”(gossip)即具有突出的信息功能。在這個“信息池”(information pool)里,關于社群成員做了什么、沒有做什么、應該做什么等話語迅速流進又瞬時流出,每一個社群成員都在這個強大的信息流的覆蓋之下,每一個個體在其他人眼里都是“可看的”。
“自滕尼斯以降,社會學中‘關系緊密’的典型一直是某種農村生活,也常常用這種生活與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的所謂無序生活作為對照”;〔19〕[美]羅伯特·C.埃里克森:《無需法律的秩序:相鄰者如何解決糾紛》,蘇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193 頁。然而,切換到現代工商社會,盡管在地理空間維度上人們之間進入陌生化狀態,但是由于互聯網的廣泛普及,各種社交軟件的普遍適用,依托于作為“第三次浪潮”的網絡技術,離散化分布的個體可以在虛擬空間被有機鏈接起來,大大突破地理空間的邊界限制,從而生成“云”意義上的另一種形態的“熟人社會”,結成各種各樣的新型社群。博客、微博、微信等的興起及附著其上的各類群體建立,原本陌生化的個體可以經由興趣、價值訴求,以及其他社會交往等完成各類“圈層化”。圈層中信息分布是高度對稱的,以“共同知識”形態出現的信息相當充分,成員之間擁有評價他人的堅實的認知基礎。而且,與鄉土社會信息的口耳相傳相比,互聯網社群的信息傳播速度、擴散面以及擴散的“漣漪效應”等都不可同日而語,人們行為的透明化程度獲得了極大的增強。相應地,進入大數據時代后,社會治理的數字化網格化程度日益加深,充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建構新型信息機制成為信息流布的新形態。由“互聯網+”的技術推動,信息孤島被迅速打破,數據及時實現共享,經由各類公共信息系統建設——典型的比如平安建設信息系統、信用建設信息系統、“雪亮工程”系統,它們為社會治理接入了人工智能中樞即“城市數據大腦”。〔20〕參見車俊:《透過浙江看中國的社會治理》,外文出版社2019 年版,第127-135 頁,第146-158 頁。對于“云”層面的信息機制而言,它們的信息識別、提取、匯集、分類、編碼、發布功能日益突變,個體行為的動態可視化實現了質的飛躍。可以說,在強大的信息機能支持下,現代工商社會足以成功地復制傳統鄉土社會的自治優勢,推進社群內部自我治理;而在深度強化信息能力的同時,注重借助村規民約、行業章程等社會規范與法律制度的合力,注意個體權利保護和公共信息汲取之間的均衡,在確保個體合法公民權益的基礎上既能重現社群自治的治理優勢,又能避免既往以“閑言碎語”為主要信息機制的偏頗、錯誤、遲滯,以及其他侵犯公民合法權益之弊。
(2)研究還發現,2018年的高考數學試題強化了試題的綜合性,有很多題目綜合考查了學生多個核心素養.但是目前的試題整體過分偏重于對數學運算素養的考查,而對數據分析、數學建模素養的考查相對較少.
(二)以強力維度—長期博弈為核心的自治格局
與法律規范主要依靠國家公權力的強制實施不同,社會規范必須依托于從社群內部演化而成的自治機制,這是它們得以落實的關鍵所在,也是社會規范之所以能夠優化執法資源配置、降低執法成本的重要緣由。基于交織緊密的社群結構形態,個體之間經由各種各樣的利益、情感、心理認同、價值共識等彼此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織就了繁復多元的有機連帶關系,每一個個體都是深嵌其中的社會網絡上的構成性節點。在這個有機連帶的社會網絡之中,個體之間的組織化程度大為增加,相互依賴性也隨之極大強化,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擁有能夠影響、限制,甚至是約束其他社會博弈主體進行行為選擇的強力維度,也都或顯或隱受到其他行為主體所擁有的強力維度的影響、限制和約束,彼此之間產生了互相依賴的緊密關系結構,增強了功能意義上的互惠權力。〔21〕同前注〔19〕,埃里克森書,第193 頁。強力維度并不必定是國家公權力強制的產物,它在法律意義上的平等主體之間同樣可以生成。當某一個體只能從現有的社會交往對象中獲得其必需的資源,或者轉向其他社會交往對象獲取資源的時候成本過高而變得不可行,這時,后者就對之具備了如上所述的強力維度。正如麥克羅伊德所指出,博弈關系持續的長短取決于退出成本的高低,〔22〕Macleod M. Bentley, Equity, Efficiency, and Incentives in Cooperative Teams, in Derek C. Jones and Jan Svejnar, eds., Advances in the Analysis of Participatory and Labor-managed Firms 3, 1988, PP. 5-23.如果主體能夠便利地從他者處獲得替代性資源,那么博弈關系是隨時可以中斷的短期博弈,甚至是一次性博弈;如果這一替代的成本過高,從而導致難以退出現有博弈,則構成了長期博弈格局。在強力維度的支持下,彼此有機連帶的個體之間很難輕易地離開嵌入的既有社會網絡而轉向其他,因此,高昂的退出成本決定了博弈關系的長期性。
1.聲譽機制的行為約束功能
長期博弈格局中,聲譽機制非常重要,是社會規范能否得到有效實施的核心要素所在。某一行為主體的博弈相對方將根據前者在上一輪博弈互動中的表現來決定自己后續的行動策略,即過去的行為深刻影響未來的交往機會。在這里,阿克塞爾羅德的“一報還一報”即針鋒相對策略〔23〕參見[美]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合作的進化》,吳堅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19-36 頁。將構成個體策略選擇的核心邏輯:如果行為主體在上一輪博弈中不予合作,機會主義或道德風險盛行,博弈相對方就會在下一輪相遇中“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或是“用腳投票”中斷社會交往,或是采取相類的機會主義、道德風險予以回擊,行為主體則由此而喪失附著于無數個再次相遇機會之上的、源源不斷的未來收入流,未來社會交往/交易機會與自身過去的行為緊密聯系在一起。〔24〕See David M. Kreps, 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in Jams E. Alt , Kenneth A. Shepsle, eds.,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06-109.這一點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由此,即便沒有國家強制力的“在場”,聲譽對社群內的人們是否遵守社會規范也構成了強有力的制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聲譽機制是一種“弱者的武器”〔25〕See Jam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典型的比如,在費孝通意義上的鄉土社會,當某一鄉民在村社交往中違反社會規范,采取機會主義或其他道德風險行為,一旦傳揚開來——交織緊密的村社結構中有高效的信息機制可以使之很快成為公共信息——其他村民無需訴諸國家強制力,只需要在諸如祭社、廟會、集市等社群活動中對之采取冷落、排斥、譏諷等邊緣化策略,在前者面臨蓋房、紅白喜事、疾病或者其他需要緊急救助的情形之時拒絕施以援手,采取漠然旁觀的態度,那么,由于無法享有群體成員以自治形式提供的公共物品,個體在社群的處境必然日益艱難,甚至日常必需的社會交往也難以為繼。因此,在交織緊密的社會生活中,“人們必定會為自家聲譽操心,因為這些歷史信息能為他人分享。某甲若在上一局與特定對手博弈時背叛過,他就一定擔心其他人知道這一點。許多文化都鼓勵其成員要相信規范執行者一定了解自己的一切言行,以此促進社會控制。”〔26〕同前注〔19〕,埃里克森書,第191 頁。
2.聲譽約束功能的適用場域拓展
這一約束邏輯并不限于鄉土場景,它具有足夠的廣譜性,只要能夠生成社會交往意義上的功能性的緊密網絡,就有它的用武之地。比如,經由行業協會的組織整合,同一行業的企業之間充分落實法團主義,成員企業必須一體化遵循協會章程、行規行約和其他行業規范;作為布勞意義上的互惠式的社會交換,〔27〕參見[美]彼得·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孫非、張黎勤譯,華夏出版社1988 年版,第104-134 頁。它們將獲得協會提供的成員身份認證、優惠產業政策、同行對手合作、行業利潤共享與分割等回報。〔28〕參見余暉:《行業協會組織的制度動力學原理》,載《經濟管理》2001 年第4 期;魯籬:《行業協會經濟自治權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40 頁。這些回報,是功能意義上的社會資本——“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29〕[美]林南:《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張磊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4 頁。,更是行業協會得以吸引成員企業加入的激勵所在,也因此恰恰正是行業協會得以有效約束成員企業的強力維度。當成員企業拒不遵守行業協會的規范指引,或者在協會規范的實施過程中暗行機會主義或道德風險,協會作為組織化的制度載體,將對之采取申誡、財產罰、聲譽罰、資格罰等自治型懲戒,成員企業因成員身份而享有的一系列貨幣資產、文化資產將喪失殆盡。這一剝奪效應,將對成員企業潛在的機會主義或道德風險產生顯著的阻嚇效應,使之有充分的動力以自身的遵守行為落實行業協會的規范實施,精心保持與協會組織之間的長期博弈關系。強力維度以及附著其上的長期博弈關系,對于行為主體遵守社會規范形成了有力的約束機制。任何理性的個體,只要考慮到強力維度之上的長期博弈關系無從回避,自覺遵守社會規范的行為指引而不是相反就必然是他們視角下的最優選擇。
3.遵守社會規范與文化資產積累
聲譽機制的信息傳播、口碑評價、行為指引等功能,依托于長期博弈關系和相互依賴的權力關系,深刻影響行為主體未來的源源不斷的長期收入流,由此在群體之中催生了講求良好口碑、注重累積聲譽——作為一種重要文化資產——的集體心理;而一旦“愛面子”蔚然成風,反過來則有助于增強社會主體的自律,推進社會規范的落實,使之進一步轉向成本更為低廉的自律型實施。所謂文化資產,是有關人、事、物的公共形象,是社會對人、事、物通過足夠的時間長度方能形成的穩定公共評價,是由集體認知、社會口碑、群體分層、身份識別等要素構成的無形資產,在功能上類似于韋伯所言的“社會印章”。社會學和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文化資產是一種非正式的社會控制機制,對其分享者的行為有顯著的約束作用。通常,“缺乏文化資產的人趨于行為少受約束,而文化資產多的人則常常更愛惜自己的羽毛,乃至有時會‘為名聲所累’。日常經驗也趨向于印證這一點;‘不要命怕不要臉的’、‘男不同女斗’、‘光腳不怕穿鞋的’、‘秀才遇到兵’等俗語就說明了這一點;商業社會中也往往是不知名商家假冒知名商家的商品,而非相反;大公司與顧客發生邊際性糾紛時,前者一般更情愿并急于‘私了’而不愿打官司或公諸媒體等;所有這些,都表明文化資產具有自我執行的社會控制功能。”〔30〕蘇力:《“海瑞定理”的經濟學解讀》,載《中國社會科學》2006 年第6 期。
基于文化資產形成的內在規定性,良好聲譽的獲得并非是無代價的,它需要行為主體做出具有相當行動成本的舉措,以此作為信號來證成自身的懿行嘉品,使得其他群體成員對其產生“值得信任”的共同心理,進而形成“好人”的公共輿論評價,“好名聲”才能得以點滴累積。社會規范是一種無需國家強制力而對個體的自由和行為施以約束的規范形態,對行為主體的選擇施加了相應的成本,具有重要的信號傳遞功能。根據信號傳遞理論,具有相應成本的行動才能成為有效的信號,〔31〕參見[美]埃里克·A·波斯納:《法律與社會規范》,沈明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31-35 頁。顯然,遵守社會規范意味著相關主體自愿讓渡一部分個人自由給公共體,所以遵守它才顯示出一個人更愿意與他人合作,是“可以置信的”,而不是機會主義取向的或具有道德風險之虞。否則如果沒有成本,也就沒有信號價值。正是因為有成本,所以才能夠起到篩選和信號傳遞的作用。比如,見義勇為和打抱不平意味著當事人需要冒一定的風險,只有道德水準相當高的人才甘于冒這種風險,才有勇氣承擔這種風險引發的成本,所以可以傳遞信息:這是一個好人,更是一個高尚的人。〔32〕同前注〔6〕,張維迎書,第344-345 頁。因此,在一個講求良好聲譽的社會,在一個“愛面子”文化盛行的群體,聲譽的絕對價值和相對價值日益豐隆,個體將有充分的激勵借助各種足以證成自身品行的渠道來增進聲譽資本的積累,對于社會規范的遵守就水到渠成地成為一種重要的信號顯示器,從而在基于珍視聲譽資本的內心追求上為社會規范營造了科學巧妙的自我實施機制。與此同時,聲譽資本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演化過程,不是一朝一夕即可一蹴而就,而它的失卻則可以發生在旦夕之間。作為重要的文化資產,“好名聲”難得而易失,這就進一步提高了它的稀缺性和附著其上的貨幣收益、符號收益及其他。失卻“好名聲”的主體將遭遇突出的剝奪效應,面臨相當沉重的機會成本和心理成本。依據卡尼曼的行為經濟學分析,人們在決策時往往受到“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的影響,即同一單位的所失相比于所得,人們更看重前者。〔33〕“稟賦效應”這一范疇是行為經濟學的重要研究成果,由卡尼曼等人在心理—行為實驗中發現并提出。它指的是行為人對其擁有的物品(包括有形的實物、無形的權利等)比對不擁有的同樣物品有更高的貨幣評價,人們對損失的評價要高于對收益的評價。詳見魏建:《行為經濟學與行為法經濟學》,載《制度經濟學研究》2003 年第2 輯,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年版;Daniel Kahneman, Jack L. Knetsch , Richard H. Thaler ,Experimental Test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and the Coase Theore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6, 1990, pp. 1325-1348.循此,聲譽資本將借助顯著的剝奪效應,從另一反面路徑為人們不得偏離社會規范的行為指引提供事先阻嚇,并與正面的符號收益等形成雙重合力,將人們的行為穩定在遵守社會規范的納什均衡上。
三、社會規范與法律交互作用的內在機理
社會規范與法律之間存在相當復雜微妙的互動機制和原理。同為提供行為指引、穩定人們的社會交往預期、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規范形態,二者的比較制度能力不同,比較優勢各異,倘若彼此能夠取長補短,互補協力,則可以成就一個分工協作的共治治理結構,最大限度地推進各類規范的自我實施機制運轉。一方面,法律可以借力社會規范的自我實施機制,提升法律運行實效;另一方面,人們可以“以守法為借口”擺脫不合理的社會規范的束縛,〔34〕參見戴昕:《“守法作為借口”:通過社會規范的法律干預》,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7 年第6 期。法律可以將他們從既無效率也不公平的社會次優狀態中解脫出來。同時,社會規范可以填補法律漏洞,而法律則是新生社會規范的重要支持力量。法律更可以借助自身在形成速度、覆蓋廣度、國家強制力度等層面的優勢,在社會規范力所不逮的地方及時展開治理之翼,積極推動現代民族—國家的戰略治理實施。
(一)經由社會規范的法律自我實施
當法律的行為指引與社會規范相一致或彼此兼容時,前者的規范性要求實際上就是后者的義務性所在,雙方是一體同構的。根據哈特對于法律的功能性界定,如果“它的存在意味著特定種類的人類行為不再是任意性的,而是在某種意義上是必須的”,〔35〕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6.即便在沒有公權力強制的場合,行為主體仍然有“不得不為之”的自覺意識和內在驅動,這里就有一種法律存在,一種霍姆斯意義上的“不得不”,并進而生成相應的自我實施。法律與社會規范的一體同構狀態,使得法律得以嫁接社會規范的自我實施機制,實施成本低廉。也就是說,它們可以附著于后者的自我實施機制運行,實現制度之間的“借東風”。具體而言,社會規范是一種共同體執行,是一種彌散化執行,它們產生于無處不在的社會交往和博弈,其中每一個個體既是守法者也是執法者。正是基于共同價值觀和秩序觀,社會規范的執行成為共同體成員的當然義務,成就了多數人對于少數人的執行。〔36〕同前注〔6〕,張維迎書,第336 頁。而多數人對于少數人的監督執行,會極大地提高違反規范行為被發現的程度——依據貝克爾的分析理路,人們是否實施違法違規行為的沖動和數量與被發現程度、懲罰嚴厲程度成反比〔37〕See Gary S. Becker,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6, No. 2, 1968, pp. 169-217.——因此能夠在事先有效地威懾潛在違法者,使之放棄違反規范的做法,并且將對少數人的違反社會規范的行為的監督成本和懲罰成本分攤到多數人身上,是一種成本低廉的社會執行機制。〔38〕同前注〔6〕,張維迎書,第336 頁。法律嫁接于其上,就是法律被置入了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共同體執行或者彌散化的執行之中,深刻影響法律實施效果的可觀察性、可檢驗性等約束得以有效克服,很好地降低了不少場域中囿于可觀察性、可檢驗性無法滿足而導致的法律實施不能,拓展了法律的適用邊界。同時,借助社會規范自我實施機制中的聲譽、長期博弈關系、強力維度等要素,法律變成了行為主體彰顯自律的重要信號系統,人們積極遵守的內在激勵大為增強,國家強制力得以抽離出來,既節省執法資源又巧妙地推動了法律的公眾認可。上述原理對于如何經由改變組織結構,在現代工商社會成功地復制出交織緊密的場域,從而為法律借力社會規范的自我實施機制營造沃土而言,提供了一個可供參酌的切入視角:借助法律積極推動以行業協會為代表的社會團體培植與發展,深入落實法團主義精神,在遵守法治的根本前提下,將不同的個體用內部規范組織起來,讓每一個組織成員在一定程度上對其他成員的行為承擔連帶責任,使得外部治理轉化為內部治理,從而經由法律與社團規范的兼容性建設,憑借后者的信息傳輸和連帶責任促使法律得到高效便利的實施。
(二)“守法作為借口”對于社會規范的改造
社會規范并不總是可欲的,由于規范演化過程的黏滯性、群體利益的局部性、信息/知識缺乏,以及制度轉化成本過高等緣故,總是存在某些既不合理也難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社會規范制約或支配著行為主體的決策。支持社會規范實施的社群制裁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其綿密的懲罰之網使得在不合理的社會規范面前的“不情愿個體”〔39〕同前注〔34〕,戴昕文。也深陷其中,難以除卻它們的干預和影響。行為主體遵循所屬群體的社會規范,這一遵守有著特定的社會意涵:其實質是個體以遵守規范的行為向群體傳遞信號,表明自身是值得信賴、可以合作的理想主體。這一信號傳遞行為,是行為主體對于社會規范的既有涵義的認可和接受,他們是在該既有涵義的行為指引下展開社會交往和博弈互動。而對于不合理的社會規范,則必須要有制裁力更強的上層位階的規范及時介入,改變前者的原有涵義,扭轉它的評價取向和價值引導,才能改變“不情愿個體”的行為窘境。法律作為國家公權力集中供給的制度規范,在強制性、普適性等維度具有顯著的制度比較優勢。當它給出與不合理的社會規范截然相反的行為指引時,社群成員面臨的制度約束就開始發生變化。一方面,他們是深嵌其中作為局部的群體的成員;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國家公權力觀照下的現代社會公民,既享有現代公民法定的基本權利,也必須履行現代公民的法定義務,配合落實現代民族—國家的治理戰略目標。因此,在他們面臨的制度約束集合上,就有一個效力位階排列的問題,有一個約束力高低的比較問題。選擇效力位階更高、規范性約束力更強的法律指引作為自己的決策指南,是對于法定公民義務的履行,是一種容易被理解的“人之常情”。此時,背離原有的不合理的社會規范設定的行為模式,其傳遞的信號將不再被解讀為是對于社群及其他社群成員的“不合作”或“不值得信任”,而是為了守法而不得不為之的“不得已”,自然也就不再是社群懲罰的規制指向對象,從而形成了“守法作為借口”的特殊現象。〔40〕同前注〔34〕,戴昕文。
“守法作為借口”為改變不合理的社會規范提供了契機。恒常性是社會規范的內在特性,也是它得以作為群體行為指南的緣由所在。恒常性意味著社會規范的形成必須經由一個持續展開的記憶過程,借助規范的不間斷的遵守,從而在群體成員的認知框架和意識結構中沉淀并層層累積下來,凝化為一種福柯所說的附著于“馴順的肉體”的一種身體記憶,〔41〕參見[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年版,第153-190 頁。一種“隨心所欲不逾矩”。而正是由于這一特性,社會規范的集體記憶機制隱含著被瓦解的風險。當某些“不情愿個體”以守法為理由,繞開、回避甚或對抗不合理的社會規范時,實際上就在后者之中打入了一個楔子。基于這個制度楔子,背離原有的社會規范不再被解釋成機會主義或道德風險,違反規范的成本大為降低,而相應的收益卻相當可觀:包括但不限于更多的自由,更有效率的決策選擇,更少無意義的社交或禮儀,諸如此類。當背離社會規范在“守法”的支持下越來越能夠為社群成員所理解和接受,這種共情理解彌漫開來,將會造就現有社會規范之外頗為豐厚的潛在收益。外部潛在收益和獲利機會是促使規范變遷的重要驅動,是誘致性的制度變遷的關鍵,〔42〕參見林毅夫:《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載[美]羅納德·H.科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經濟學派譯文集》,劉守英等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260-276 頁。基于有待實現的可觀潛在利益的激勵,“不情愿個體”以守法為借口的策略就會具有強烈的示范效應,越來越多的群體成員必定仿而效之,日益脫離不合理的社會規范的束縛。當這一脫離努力達到了臨界點,社會規范的集體記憶機制宣告瓦解,社會規范的恒常性隨之難以為繼,其作為一種規范形態也因而被推向了變革的十字路口。
(三)社會規范對于法律漏洞的填補功能
法律并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完備的封閉體系。在法學發展史上,一直不乏對于法律作為一個邏輯自洽、無所不包、自為自在的“物自體”想象,認為法律可以完美地自我運行,在此基礎上形成純粹邏輯演繹的法律科學,即便實踐中出現法律運轉失靈,那也是暫時的偶在的現象,依靠法律內部機制如法律解釋、法律推理、類推適用等足以解決,從而恢復法律體系圓融自洽。然而,正如制度經濟學研究所指出的那樣,法律是不完備的,本質是一種不完備的契約,〔43〕See Katharina Pistor, Chenggang Xu, Incomplete Law: A Conceptu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Market Regulation. Columbia Law School the Center for Law and Economic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204, pp.1-79.其間必然充斥著相當的空白、罅隙和漏洞,僅僅依靠法律解釋等內部機制無法有效回應法律的不完備性所提出的制度挑戰,勢必要求有與之相匹配的外部機制予以有效填補,在此基礎上進行法律的發現,甚至是法律的續造。〔44〕參見[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 年版,第286 頁。
法律的不完備性主要源于以下緣由:首先,法律的制定是一個依靠語言文字的編碼化的過程,而語言文字本身就是非全涉性的,它有著自身力所不逮的區域,即《老子》中所言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此,法律,尤其是制定法,不可能借助語言文字的編碼化對于各類社會關系都給出明晰準確的行為模式—責任后果,正如一份商事契約無法就標的之數量、成色、價格、交貨時間、地點、不可抗力導致的風險分配以及其他所有事項都在事先約定巨細無遺的條款。其次,法律體系是由概念、規則、標準、原則所構成的系統,其中按照明確性標準排序,則是概念/規則、標準、原則依次遞減。法律體系是一個開放的結構,它本身具有哈特所意指的規范的雙重性:一方面具備“確定的核心”,另一方面又有“疑問的半影”……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法律會形成某種適當開放性的結構,在開闔之間會產生裁量的余地。〔45〕參見季衛東等:《中國的司法改革: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與頂層設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68 頁。概念/規則屬于上述“確定的核心”的范圍,而更具有彈性的標準、原則是落在“疑問的半影”的邊界內,因此這個“疑問的半影”內生性地具有相當的罅隙、漏洞,既需要法律解釋、法律推理等內部機制予以補缺,也需要包括但不限于習慣、慣例、行規等社會規范作為外部機制進行填充。最后,在新事物、新現象層出不窮的轉型社會,諸多社會關系尚處于變動—演化的進程之中,距離定型為時尚遠,其間存在著大量的不確定性、隨機性因素。由法律的穩定性特質所決定,它所調整的對象必須是定型化的社會關系,倘若時機尚未成熟而法律貿然介入,則很可能對調整對象內含的因果機制及其作用機理認知錯誤,設定的行為模式—責任后果產生了既不公平也無效率的利益再分配效應,從而引發調整對象的集體抵觸或規避,法律的預期目標落空。在這類情況下,法律采取適度的謙抑主義,有意保持部分空白留待其他形態的規范來履行調整職能,是立法中的明智之舉。
社會規范,是國家公權力主體以外的社會主體制定、約定,或經由長時段的博弈互動和社會交往演化而成并獲得公共認可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包括但不限于村規民約、社規民約、行業章程、行業行規、風俗慣例等。首先,社會規范主要是在繁復多樣的社會博弈中砥礪而成,無需國家強制力“在場”,它們依靠社群交往、公共輿論、聲譽約束可以成就出色的自我實施。而這類自實施機制不必同時滿足法律實施所必需的可觀察性與可檢驗性,只要有社會博弈的地方,就有它們的用武之地,形成福柯筆下繁密如毛細血管的規訓之網,對于因為無法訴諸語言文字的編碼化而導致的法律罅隙或漏洞,是及時且高效的補缺因應。其次,社會規范的外延極其豐富,包括但不限于村規民約、社規民約、行業章程、行業行規、風俗慣例等,可謂包羅甚廣,無微不至。其中,根據不同的調整對象和適用場域,立基于彼此分殊的運行邏輯,形成了形態各異的規范形式。規范細分的優勢在于靈活性、針對性、適應性強,能夠根據調整對象的局部特征和需求做出契合的因應。由于種類繁多,適配性突出,社會規范對于落在“疑問的半影”的法律標準、法律原則,足以針對它們強弱不等的不確定性給出一一映射的補缺方案,幫助法官在查漏補缺的自由裁量過程中有據可循,高效地完成法律發現和法律續造。最后,由于社會規范匯聚了大量適合于特定場域的“地方性知識”,是一個有效的信息—知識集成機制,可以有針對性地反映各類“地方性情境”之下不同社會主體的利益需求、價值判斷、心理期待,并能夠借助多元的規范資源對之做出個性化的回應。社會規范以自身的知識優勢,很好地彌補了法律基于有所不知而產生的信息盲點,對于制定法由于社會關系尚未穩定,因而對調整對象認知不足導致的法律漏洞有突出的填充意義。
(四)法律對于新生社會規范的支持作用
社會規范的生發是一個頗費時日的演進過程,需要相關社會主體之間經由反復博弈漸次砥礪而成。如此一來,當“制度企業家”們敏銳地注意到現有制度體系之外的潛在收益,意欲借助社會規范的變革來推動制度良性變遷之際,規范的創新努力很有可能遭遇不理解,繼而無法感知潛在的制度收益的其余社會主體的抵觸,抑或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從而大大延緩制度變遷的進程,甚至是導致制度變革失敗于萌芽之中。因此,如果片面地強調社會規范的自發演化,過于注重它們的內生性成長力量,就可能忽視社會規范的“阿喀琉斯之踵”:過于緩慢,無法適應急劇變革的社會情勢的需求;以及當尚未定型為普適性的行為指引時,它們很容易在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博弈中夭折。
法律是國家依據法定程序制定或認可的、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和保障的行為規范體系,它的比較優勢在于,當遇到阻礙其實施的反向作用力時,能夠迅速逆轉力量對比,改變原有的博弈格局。一方面,當法律有序介入社會規范的創新之時,經由法定程序,制定良好的法律以及附著其上的國家強制力能夠及時改變社會主體之間關于什么是可為、什么是必為、什么是禁為的信息分布,改變他們的社會認知,以明晰準確的信號向社會主體提供行為指引,減少因為認知分歧導致的對于社會規范創新的延宕和阻滯。另一方面,當不同的利益集團因為局部的得失利弊而進行沒有效率的競爭,彼此膠著而僵持不下,可欲的社會規范創新陷入停滯,良法和其背面的國家強制力能夠快速協調相關主體的預期,為多元談判格局設定一個必要的軸心點。由于法律往往是公意的體現,相比于其他替代性的談判中軸,制定良好的法律是社會認知中的“最大公約數”,是多數方認可的“共同知識”。以此為軸心展開社會博弈,各方主體則有了一個比較公平的參照系,能夠較為科學、客觀地測度自己的得失利弊,衡量預期收益和機會成本。在此基礎上,相關的各方利益主體能夠在一個共享的溝通平臺上提出各自的構設方案,各自的利益訴求、價值判斷等能夠圍繞“最大公約數”進行理性、客觀、平等的對話,而不是無的放矢陷入無謂的語詞之爭,抑或是拘泥于眼前/短期利益而不知進退,從而推進溝通理性的實現。因此,對處于制度創新狀態的新生社會規范而言,它們并不是在一個純粹自發演化的進程中成為普適性的行為指引,相反,法律是它們生發過程中的內在構成性力量,能夠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左右社會規范形成的速度、方向、軌跡,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內生性變量。而目光深遠的“制度企業家”就會高明地借助法律的力量減少社會規范創新中分歧,盡可能迅速地統一預期,加速社會規范的生發進程,增強制度創新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規范演化論”與“法律建構論”的截然二分是既不科學也不符合客觀實踐的,因為,法律是新生社會規范的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持。
四、構設法律與社會規范的良性互動格局
應當高度重視社群內部“地方性知識”及其對于制度建設的功能意涵,為社會規范預留足夠的發展空間。信息是決策的基礎,“地方性知識”是獨屬于社群內部的、無可替代的信息,充分反映了群體成員作為獨特的“這一個”的利益訴求、情感心理、價值判斷。忽視了“地方性知識”對于基層社會治理的構成性作用,所選取的制度治理技術往往難以做到有的放矢,因時因地制宜。社會規范是群體成員實現社群共治和自治的重要制度載體,他們的“地方性知識”需經由這一規范的建設渠道,方能轉化為有約束力的行為模式—責任后果,才能對包括自身在內的眾多群體成員產生約束效力,由此影響、決定甚至是塑造了群體的博弈格局和社會交往結構。由此可見,倘若過多地“送法下鄉”或“送法上街”,過度地以國家法律強制替代社會規范自治,實際上是放逐了“地方性知識”,進而將會導致基層治理缺乏有針對性的實踐信息,治理決策嚴重缺乏信息基礎。欲為社會規范培育良好的生長空間,使之在基層治理中充分發揮行為指引、預期穩定、價值評價的制度職能,實現法律與社會規范協同共治的善治理想,有必要從以下維度入手進行制度構設:
(一)社會規范應主要針對“地方性問題”進行設計,突出社群個性
社會規范不得與國家法律、法規相抵觸,不得侵犯群體成員的人身自由、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們是后者的翻版或復本。任何社群都是一種社會組織形態,而從組織社會學的視角看,作為組織規章制度的社會規范——典型的比如村規民約、社規民約、行業章程等等——的個性之所以不可或缺,蓋在于它的如下功能:“第一,組織規章制度決定了(組織體)注意力分配——不同的決策程序和過程影響了注意力的分配和決策的頻率;第二,規章制度決定了利益分配——什么人參加決策的過程;第三,規章制度決定了信息——不同的部門結構導致不同的信息加工、解釋的過程和結果”。〔46〕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版,第171 頁。當前,囿于“法律中心主義”的慣有思維,不少社會規范在相當程度上仍然重復國家法律體系的規范性內容和結構,沒有對自身社群面臨的治理場域及其挑戰做出語境化的理解,沒有做出有針對性的制度因應,難以成為所屬社群的制度資源。以村規民約為例,諸如村集體經濟收益分配、分家析產、遺產繼承、土地及建房管理、婚喪紅白喜事、糾紛預防與調解、家庭與鄰里關系、村莊治安消防等,與村民的日常生活須臾不可分,具有突出的地方特性;〔47〕同前注〔11〕,汪世榮、褚宸舸書,第122-142 頁。而其余形態的社會規范也與之相類,所涉及的多為高度語境化的問題,具有強烈的“地方性知識”的底色,在操作性層面的行為模式—責任后果設計上,往往正是國家法律鞭長莫及、力所不逮之處,勢必會有不少留白。因此,相應的規范設計必須樹立治理功能互補的意識自覺,緊扣相關的“地方性知識”,重視有地方個性色彩的鄉俗民風,尊重各類社會團體的內在規定性,在落實法律基本原則要求、遵守法律強制性規定的前提下,將法律的一般性要求與“地方性知識”的個性有機融貫整合,確保規范構設的針對性和回應性,使之成為切實針對社群治理實踐而展開的有效制度資源。經由這一注重實際、重視實踐的制度地方化治理探索,社情民意得以充分吸收,基層治理經驗得以有效沉淀積累,法治、自治、德治協同建設獲得了共治機制的支持,為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尚不平衡的大國治理提供了寶貴的制度試驗田。
(二)法律應當適時吸收社會規范的有益成分,增強自身的可適用性
比較而言,以國家公權力為中心的立法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模式,如果立法者遠離地方性場域,對于各類繁復多樣的“地方性知識”相對疏離,不可避免地就會導致相應的制度設計疏闊迂遠,更多地著眼于抽象而對于眾多具象針對性不足、回應性較弱,從而導致所設置的行為模式在制度實踐中容易被規避或違反,本應配套的法律后果也未能適時跟上,無法發揮應有的激勵—威懾效應,不能證成法定行為模式的可置信性和必須遵守性。結構科學、功能良好的社會規范為立法者識別合理、有效的行為模式和責任后果配置提供了必要的通道,從知識論的意義上看,社會規范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立法的“知識不能”,即對于“地方性知識”的認知和吸納弱勢。如前所述,信息是決策的基礎,立法的知識論上的實質則在于對繁復多元的信息是否能夠充分識別、吸納與整合,立法者的知與不知,即信息能力極大地決定著立法的實效,對于非己所長的信息——陌生的“地方性知識”——立法者應當借助相應的補強機制來補己之短,最大限度地填補信息鴻溝,避免在信息不完備或不準確的情形下展開立法決策,導致立法干預失靈。
原生態的“地方性知識”難以被有效對外傳遞,原因蓋在于其中蘊含了不少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無言之知”或實踐智慧,必須經由場域中人借助長期的砥礪、磨煉“習得”這類知識,并與群體其他成員在長期博弈和密集社會交往中形成默契和共同認知,從而在共同體內部的“立規矩”時將之予以有效的編碼化,凝化為社會規范的形式,才能成為一種能夠為外部主體所便利觀察、閱讀、理解和吸收的知識。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規范是一種巧妙的知識轉化機制,它們把原本眾多的只是附著于特定交織緊密的社會場域的“無言之知”或實踐智慧予以編碼,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些原本交流起來不經濟或不便利的知識〔48〕參見汪丁丁:《知識的經濟學性質》,載《讀書》1995 年第12 期。的可讀性和可傳遞性,使之能夠以相當低廉的信息成本被包括,但不限于立法者在內的眾多外部主體所閱讀、理解,成為能夠被共知和共感的“共同知識”。經由這一轉化,即便遠離眾多“地方性場景”,立法者同樣可以識別:在對社會行為進行調整的過程中人們追求什么、回避什么,他們作為語境化的行為主體,在面臨不同的社會約束條件下會出現何種行為模式和選擇趨勢,什么是他們的激勵因素和威懾效應所在。雖然從表現形式上看,社會規范承載的“地方性知識”多如恒河沙數,但是,經由社會規范的功能性轉化,其中必定具備一般性意義的存在,必定能夠提煉、升華出社會交往和博弈互動的“最大公約數”,進而得以探知人們最基本的行動—決策規律。法律規范在對相關主體的行為調整中出現“失靈”,進而無法實現行為指引、預期穩定、價值評判等功能,究其根源,是一種特別形態的“知識失靈”:正是由于沒有獲得充分的源自實踐場域的行為知識,法律規范設計沒有很好地與人們的行動—決策規律相貼合,出現各種法律規避或違法現象則在所難免。倘若能及時吸收社會規范的有益成分,借此對于立法的“地方性知識”短板予以糾偏補弊,可適用性自然隨之有效增強。
(三)充分發揮互補效應,實現法治與自治、德治的協同共治
法律與社會規范的生成機制不同,實施機制不同,對應的社會約束條件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比較優勢。在認真對待社會規范之時,同樣應當對于法律的比較制度能力形成科學的認知,充分認識法律的“能”對于社會規范的“不能”所具有的結構性意義,以前者之長補后者之短,積極推進基層治理的制度技術創新。
社會規范具有自我實施機制,這個機制無需借助國家公權力的外部強制即可自我運行,其關鍵就在于它有效滿足了非正式社會控制系統所必需的要素:“人們的關系必須持續,擁有關于對方昔日行為的可靠信息,以及各方有效的抗衡力。”〔49〕同前注〔19〕,埃里克森書,第302 頁。但是,這個機制并非自為自在的,法律系統作為它走不出的制度底色,可以影響上述信息、強力、博弈長度等結構要素,從而深刻決定了能否在社會功能的意義上結成交織緊密的共同體,能否促進社會規范自我實施機制的順利運轉。典型的比如,土地租賃的基本法律規則既可以大大影響土地糾紛中涉及的當事人數量,更可能大大影響這些當事人相遇的頻率——土地的再分割會令當事人進入重復關系中,如近鄰一般,因此可能強化他們的合作;一些根本性法律則會延長人們對于時間跨度的理解,比如法律授權親屬繼承、依據遺囑處置財產以及永久享有土地利益,都會促使人們在配置自己資產時,感知到生活博弈似乎永無盡頭,這將激勵他們采用有利于長期規劃的合作型的行為模式來為子孫后代節省資源。而恰恰是長期博弈關系的建立,將激勵人們更傾向于遵守社會規范的行為指引,以此證成自己合作型的公共形象。法律規則也影響人們為獲取非正式社會控制所必需的信息的難易程度,晚近在數據處理上的發展令人們更容易存取公開記錄的關于某人先前是否可靠、是否合作的相關信息,更容易為社會規范的實施形成強大的公共輿論基礎。并且,有助于權力/強力更廣泛平等分配的法律規則也會支持社會規范的自我實施機制,比如,當立法者在諸如房主房客之間及夫妻之間的關系成功平權之際,就會使得涉入這些關系的當事人更容易借助社會規范來非正式地解決糾紛。〔50〕同上注,第302-303 頁。概言之,社會規范無法脫離法律框架,它們常常是在“法律的樹蔭影子”〔51〕See Robert H. Mnookin, Lewis Kornhauser, 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Law: The Case of Divorce,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88, No. 5, 1979, pp. 950-997.下展開生發演化、自我實施的過程。因此,法律應當注意自身得以影響信息、強力、博弈長度等結構性要素的機制原理,注意這一過程展開的內在規律、演化路徑和作用模式,借助對于以上三個結構性要素的回應性制度設計,促成更多交織緊密的共同體,從而使得社會規范的自我實施獲得強大的制度—組織根基。
同時,盡管法律的實施機制面臨的信息成本較高,但是,它以國家強制力為依托,在無法成就一個個交織緊密的共同體,進而社會規范缺乏實施基礎之際,法律可以及時介入,以國家強制力的強大整合能力、動員能力和規范能力,確保社會秩序的重建和維護。社會規范的實施是一種條件依存型的實施模式,即在信息、強力、博弈長度三個結構性要素上都必須同時得到滿足,否則,規范的自我實施就只能宣告失敗,而法律社會學家們津津樂道的“無需法律的秩序”也只能是舌尖上的話語而已,無法成為協同共治機制中的有機構成。一旦關于行為主體的往昔信息流通不暢,人們之間處于高度信息不對稱狀態,或者是無法借助轉向其他的社會場域以便獲得替代性的必需資源,嚴重缺乏懲罰博弈對手采取機會主義行為的強力維度,甚或是博弈對手退出現有博弈關系的行動成本很低,無法與之建立長期博弈,這時,場域的社會結構性條件發生了根本變化,實施機制缺乏組織基礎,因社會規范“失靈”導致的社會“失序”勢必呼喚法律的權威結構。法律的權威結構以它強大的強制能力、整合能力、動員能力和約束能力,能夠及時矯正“搭便車”現象,克服自發演化社會中常見的集體行動困境;也能有效制止“以鄰為壑”,防止因缺乏權力中心而經常出現的“公地的悲劇”。特別地,當社會出現緊急狀態或重大突發事件,原有的社會規范不敷使用而新的社會規范供給不及——考慮到社會規范以演化為主導的生成模式,人們無法通過協商、討論、試錯等來進行制度實驗,無法以漸進化來規范彼此行為、協調預期、達成集體共識,法律作為國家集中供給的公共物品,具有迅速、及時、強制遵循度高、對緊急情勢因應性強等特點,足以在相當緊迫的時間界限內為人們的決策提供行為指引,穩定彼此預期,推動人們行為有序化,成為強有力的秩序重建者。因此,在克服單一的“法律中心主義”的同時,也必須深刻理解法律在現代民族—國家建設中無以繞過的制度意義,注意防止“法律虛無主義”,防止社會規范對于法律的不當或過度替代。
五、結語
社會規范是多元治理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國家治理技術的現代化轉型具有顯著的制度意義。社會規范擁有知識論意義上的比較優勢,能夠對“地方性問題”給出具有充分針對性的因應方案。在這個創造性轉化的過程中,“制度企業家”的知識角色使之足以推進良性的制度變遷。聲譽機制和長期博弈關系成就了社會規范的自我實施機制,由此促使基層社會治理得以平滑順暢展開。法律與社會規范的一體同構狀態,使得法律可以經由社會規范而實現自我實施,有效提升法律實施效率;而法律對于社會規范的改造同樣具有積極的意義,“以守法為借口”能夠幫助社會主體勇于打破某些不合理的社會規范造成的制度僵局。社會規范可以填補法律漏洞,而法律則是新生社會規范的重要支持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有必要從現代民族—國家的現代化戰略建設的歷史宏觀視角來重新審視法律與社會規范,樹立系統性的觀念自覺,充分認知、把握法律與社會規范的適用條件、適用場域、治理功能,深度挖掘各自的比較制度職能,從而成就一個彼此呼應、優勢互補的協同共治格局,充分實現國家—社會治理能力和技術的現代性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