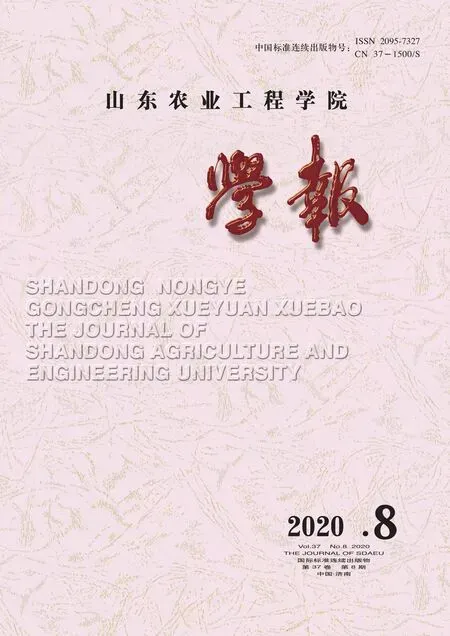論《金瓶梅》的“戲謔”藝術
(淮南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安徽 淮南 232038)
明代“四大奇書”中,《金瓶梅》完全顛覆了《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游記》的累積型創作模式,開啟了中國小說史上的第一場“真人秀”表演,它以核磁共振的方式全方位掃描現實生活,再現了明代后期的社會現實,至今雖然毀譽參半,甚至不能完整出版,但在當下的閱讀視野中行情看漲。潘知常認為,《金瓶梅》描寫的是“裸體的中國”,“裸體的民族”,“是中國文學史的第一次回歸生活的本來面目”[1]。
戲謔,“作為現代美學的一個范疇”,原指用詼諧有趣的話開玩笑,與嘲諷、調侃、搞笑親近,本來與古代小說批評無涉,倒是十分疑似戲曲表演中的“插科打諢”,但“如果戲謔有可能允許被進入美學殿堂的話,那么,我就請它到丑學的祭臺上去供奉遙遠迷茫的阿芙洛狄武女神。”[2]若以戲謔作為審美范疇,考察《金瓶梅》的文本描寫倒也十分妥貼。本文無意于對小說的思想藝術作全方位評判,僅就戲謔藝術的的作用和手法做些瑣碎的探討,求教于各位同人。
一、戲謔的對象
《金瓶梅》洋洋百回,人物800余,根據人物性格刻畫的完整和豐富程度以及出場次數的多寡,為下文論述之便,我們暫且把《金瓶梅》的人物分為三類,即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和過場人物。
1.對主要人物的嘲諷
《金瓶梅》命名直接關聯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幾個主要人物,但一號人物還是西門慶。以79回為界,西門慶的人生可以分為兩個時段。
生前的西門慶,是王婆眼中的 “鉆石王老五”,一個“潘驢鄧小閑”的五全人物;而熟悉西門慶的蔣竹山,看法恰恰相反,但更接近實際,說“此人專在縣中包攬說事,廣放私債,販賣人口,家中丫頭不算,大小五六個老婆,著緊打倘棍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作者眼中的西門慶:“專一飄風戲月,調占良人婦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賣了。一個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余遍,人多不敢惹他。”(詞話本第2回,人民文學出版社,)今人孟超概括為“包括了地主、官僚、商人、惡霸、市儈、流氓,額外再加上少不了的色鬼欲魔”,[3]
死后的西門慶,水秀才的祭文故意惡搞。有意為男性陽具畫像,倒也與活著的西門慶十分般配。
“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濟人以點水,恒助人以精光。囊篋頗厚,氣概軒昂。逢樂而舉,遇陰伏降。錦襠隊中居住,齊腰庫里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撓摑,逢虱蟣而騷癢難當。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隨幫。也曾在章臺而宿柳,也曾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撐頭活腦,久戰熬場,胡為罹一疾不起之殃?見今你便長伸著腳子去了,丟下小子輩,如班鳩跌腳,倚靠何方?難上他煙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墻。再不得同席而儇軟玉,再不得并馬而傍溫香。撇的人垂頭落腳,閃的人牢溫郎當。今特奠茲白濁,次獻寸觴。靈其不昧,來格來歆。尚享。”
2.對次要人物的戲弄
西門慶的交際網中,妓女和幫閑是最基本的兩類人群,前者有李家妓院麗春院的李桂姐、鄭家妓院的鄭愛月,后者有西門九友。
《金瓶梅》洋洋灑灑八十萬字,主要人物西門慶、潘金蓮之外,應伯爵的戲份最多。僅小說回目中,就有八處立題直接涉及應伯爵。西門慶的日常生活中幾乎天天可以見到應伯爵的身影,他是西門慶的座上客和開心果,兩人關系十分 “融洽”,“熟得狗也不咬”。應伯爵如影隨行跟著主子幫嫖、吃酒、解悶。
擁有了金錢和權勢的西門慶,女人和幫閑是必不可少的交往對象,前者供其調情縱欲,后者助其消磨業余時光。前者屬于西門慶的私有財產,基于家庭地位的不對稱,她們在西門慶面前為衣食之欲和錢物之利,只能俯首帖耳,是完全的性奴隸。她們與以應伯爵為代表的那些狼狽為奸、低眉趨利的幫閑人物一起成為作家戲弄調侃的對象。
第六十八回寫應伯爵在鄭愛月兒家置酒宴飲,席間,他要粉頭們吃酒。“愛月兒道:‘你跪著月姨兒,教我打個嘴巴兒,我才吃。”黃四也道:“二爺,你不跪,顯的不是趣人。”伯爵“于是奈何不過,真個直撅兒跪在地下……這愛月兒一連打了兩個嘴巴,方才吃那杯酒。”他善于裝瘋賣傻、嬉皮笑臉,打情罵俏,丑態百出,可謂無恥之極。對他來說,這些常人難以忍受的屈辱竟然成了他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只要這種“閑情逸趣”不觸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能博得西門慶一笑,即使喪失人格,他也會心甘情愿。目的就是滿足衣食之欲,錢物之利。幫閑需要智慧,需要口才,更要有犧牲精神,那就是面子、臉皮,說得文乎一點:尊嚴!
他給被西門慶趕走的樂工李銘傳授秘訣說:“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嗔拳不打笑面。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拿著大本錢做買賣,還帶三分和氣。你若撐硬船兒,誰理你!全要隨機應變,似水兒活,才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墻,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4]這是他自己的經驗總結和生存之道,甘做幫閑的應伯爵早已做好了心理準備。
《金瓶梅》是市井小說,其中的人物以清和縣城為中心。決定其人物從廳局級的州府官員,下至各色人等。在小說的人物圖譜中,以西門慶為中心主要刻畫了兩類不同的形象,一是位高權重的大吏,如親家楊提督、太師蔡京、狀元、御史、巡按、提刑,他們貪污受賄,巧賣祿奉,為西門慶帶來滾滾財源,成為西門慶的政治靠山和經濟后盾,作品用了很小的篇目寫他們,不是作者主要的關注對象。而在西門慶的日常生活中,接觸更多的是普通的飲食男女和市井百姓。
好色的西門慶“一個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余遍”,媒婆自然成了西門慶“飄風戲月”的交接對象。職業媒婆薛嫂子就是帶著七言八句的出場詩登臺亮相的。
“我做媒人實自能,全憑兩腿走殷勤。唇槍慣把鰥男配,舌劍能調烈女心。利市花常頭上帶,喜筵餅錠袖中撐。只有一件不堪處,半是成人半敗人。”(第7回)
媒婆和庸醫自古以來就是民間文學和宋元話本取消調侃的對象,《金瓶梅》的作者繼承了傳統的題材,在小說中依然作為插科打諢的最佳選擇。作者借鑒戲曲上場亮相自我介紹的方式,讓那些邊緣搞笑人物現身說法。
小說第六十一回,寫趙太醫給李瓶兒看病。趙太醫居然這樣介紹自己:
“我做太醫姓趙,門前常有人叫。只會賣杖搖鈴,那有真材實料。行醫不按良方,看脈全憑嘴調。撮藥治病無能,下手取積兒妙。頭疼須用繩箍,害眼全憑艾醮。心疼定敢刀剜,耳聾宜將針套,得錢一味胡醫,圖利不圖見效。尋我的少吉多兇,到人家有哭無笑。”(第61回)
醫生不比媒婆,那是一種救死扶傷的職業,需要的是技術和經驗,人命關天,絲毫馬虎不得。即使岐黃不濟,醫術有限,通常也不至于自毀聲譽,砸了生計的飯碗。而趙太醫竟然說找他看病就“少吉多兇”、“有哭無笑”。這不是自己炒自己的魷魚嗎?他開了一味藥,連八十一歲的何老人都不以為然,倒是與其 “趙搗鬼”的外號相得益彰了。讀到此處,人們自然想起《竇娥冤》的賽盧醫,他那“行醫有斟酌,下藥依《本草》,死的醫不活,活的醫死了。”的自我表白就有了異曲同工之妙了。趙太醫的確很像《竇娥冤》中賽盧醫的復制、重生。
3.過場人物的插科打諢
插科打諢,是中國戲曲普遍使用,制造滑稽效果的一種表現手法。“科”指滑稽動作;“諢”是指滑稽語言。插科打諢在戲曲中的作用是制造滑稽,逗樂觀眾,成為喜劇性的穿插;插科打諢也發揮著一些戲劇功能,是戲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具有獨特的藝術特色和美學旨趣。從參軍戲到元雜劇皆有插科打諢的詼諧調侃和笑料打趣。李漁《閑情偶寄·詞曲部》專列“科諢第五”章予以討論,認為插科打諢“乃看戲之人參湯也,養精益神,使人不倦”[5]。
作為一種古老的藝術樣式,比起小說來,戲曲是地地道道的民間娛樂方式。要求在限定的時間和空間演繹人物的悲歡離合,出于對觀眾和讀者的關切,減少聽戲的瞌睡和閱讀的疲勞,劇作家們送上一碗碗插科打諢的“人參湯”。《金瓶梅》的作者精心借鑒俗文學的表現手法和宋元雜劇插科打諢的養料,在小說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插科打諢風格。
所謂“過場人物”,可以有姓但無名,其出場多曇花一現,一次露臉便完成使命,自行告退。這些人物出場時,作家甚至連完整的姓名和字號都吝于施舍,只省略為一個代號。接生婆蔡老娘、牛皮街陶扒灰、丫環玉簪兒即屬此類。
西門慶家庭成員中女性眾多,雖然主人開著藥鋪,但似乎不通醫術,并不能保障家庭成員的健康,卓二姐、吳月娥、李瓶兒一向身體不好,平時需要經常看醫生,臨清有名的醫生在李瓶兒病危期間仿佛都集中到了西門大宅。與經常路面的醫生這類次要人物相比,接生婆的出現倒是屈指可數,原因在于西門慶的女人們肚子不爭氣。西門慶生前唯一的一次接生過程中,就出現搞笑的接生婆蔡老娘形象。
小說第三十回,李瓶兒生孩子,家里請來接生的蔡老娘。這位蔡老娘居然如此介紹自己的接生技術:
“橫生就用刀割,難產須將拳揣。不管臍帶包衣,著忙用手撕壞。活時來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
這是接生嗎?與其說是接生,簡直是催命!
作品第三十三回寫西門慶的伙計韓道國妻王氏與小叔韓二偷情,被好事者游街示眾的描寫: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廂鋪里,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個來問,那一個來瞧,內中一老者見男婦二人拴做一處,便問左右看的人:“此是為什么事的?”旁邊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奸嫂子的。”那老都點了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奸,兩個都是絞罪。”那旁邊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連娶三個媳婦,都吃他扒了,因此插口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相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卻論什么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著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看到這段描寫,令人油然想起《紅樓夢》第七回借賈府老門人焦大醉后詈罵的情景。比起陶扒灰的赧然知恥,寧國府賈珍之流更覺道貌岸然。
小說第九十一回,在李衙內、孟玉樓之間安排一個吃醋使性的丫環玉簪兒。這個丫環用這樣的口氣對她的主子說話!
先是命令男主人:“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使乏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睡瞌睡,起來吃茶! ”
再是抱怨女主人:“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齋時才起來。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蜜攪酥油一般打熱。房中事,那些兒不打我手里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
這是低眉順眼的丫環做派嗎,即使李衙內、孟玉樓再如何高風亮節,這樣的丫環也很難置身李府。
二、戲謔的手段
1.講笑話
李家妓院李桂姐答應西門慶包月后又私自接客王三官,西門慶大鬧麗春院,關系緊張。應伯爵牽線搭橋,從中斡旋。為疏解尷尬氣氛,應伯爵開始表演其拿手絕活。
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雞結為兄弟,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螃蟹說:‘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捩的恁樣了!’”桂姐兩個聽了,一齊趕著打,把西門慶笑的要不的。(第21回)
小說第五十四回,應伯爵、常峙節在郊外的內相花園宴請西門慶,作家一連讓應伯爵說了四個笑話,“江心賊”、“生礬”、“銅錢牛”和“品屁”,是應伯爵說笑話最多的一次。“江心賊”與“生礬”暗示西門慶的富貴有劫色劫財的強盜賊人之嫌;“生礬”旨在調笑妓女金釧兒。經常峙節提醒,西門慶領悟后,應伯爵自覺,馬上罰酒兩杯,為彌補過失,照顧主子的尊嚴,趕緊說了第四個笑話“品屁”。這個笑話顯然是為幫閑畫像,所以常峙節奉承道,“你自得罪哥哥,怎的把我的本色頁說出來。”
2.漫畫式掃描
圣人不諱言“飲食男女”,何況蕓蕓眾生。一百回的《金瓶梅》中,寫到應伯爵的有六十多回,而其中寫到應伯爵跟隨西門慶混吃溜喝的就達五十回之多。可以說,在應伯爵與西門慶的交往中,能夠貫穿始終的就是一個“吃”字。
小說第一回應伯爵第二次出場就寫到了吃早飯的問題。西門慶熱結十兄弟不久,應伯爵借口傳播武松打虎事大清早便來西門慶家蹭飯了。
西門慶故意問道:“你吃了飯不曾?”伯爵不好說不曾吃,因說道:“哥,你試猜。”西門慶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這等猜不著。”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不吃便說不曾吃,有這等張致的!”一面叫小廝:“看飯來,咱與二叔吃。”伯爵笑道:“不然咱也吃了來了,咱聽得一件稀罕的事兒,來與哥說,要同哥去瞧瞧。”(第一回)
兩人早餐,飲食的內容和過程一般比較簡單,何況又不是蔡狀元那樣的貴客,小說就此省略。至于集體宴飲,則需多費筆墨了。小說第十二回寫西門十友在麗春院聚餐,那吃相真如饕餮盛宴,作家一夸張性的漫畫手法為讀者精彩奉獻:
“人人動嘴,個個低頭。遮天映日,猶如蝗蚋一齊來;擠眼掇肩,好似餓牢才打出。這個搶風膀臂,如經年未見酒和肴;那個連三筷子,成歲不筵與席。一個汗流滿面,卻似與雞骨禿有冤仇;一個油抹唇邊,把豬毛皮連唾咽。吃片時,杯盤狼藉;啖頃刻,箸子縱橫。這個稱為食王元帥,那個號作凈盤將軍。酒壺番曬又重斟,盤饌已無還去探。
當下眾人吃得個凈光王佛。西門慶與桂姐吃不上兩鍾酒,揀了些菜蔬,又被這伙人吃去了。那日把席上椅子坐折了兩張,前邊跟馬的小廝,不得上來掉嘴吃,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便剌了一泡屯谷都的熱屎。臨出門來,孫寡嘴把李家明間內供養的鍍金銅佛,塞在褲腰里;應伯爵推斗桂姐親嘴,把頭上金琢針兒戲了;謝希大把西門慶川扇兒藏了;祝實念走到桂卿房里照面,溜了他一面水銀鏡子。常峙節借的西門慶一錢銀子,競是寫在嫖賬上了。”(第12回)
3.諧音提示
崇禎本第一回《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就描寫一群人格卑微并非大奸大惡的市井人物。小說仿照《三國演義》的桃園結義寫到了西門慶的九個結義兄弟,他們的姓名,結合張竹波的評注[6],使人自然而生諧音聯想:
應伯爵:硬白嚼,字光侯,光喉也;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云理守:云里守;字非去,飛去也。
常峙節:常時借,有借無還。
祝實念:逐日粘,抑或住十年。
孫天化:天話;字伯修,不羞也。
吳典恩:無點恩。
卜志道:不知道。
白賚光:白借光,
謝希大:攜帶也。
……
古代中國人格外看重名、字、號,姓氏屬先天血緣決定,除偶爾皇帝賞賜,無法更改。起名一般由父親或祖父完成,字由德高望重的前輩賞賜,號則多為主人自己完成。名和字多在出生后不久形成,號多在中年后自我進行,而綽號更多地帶有社會的色彩。中國小說創作中人物綽號的命名與《三國演義》同步完成,多以人物的容貌關聯,如美髯公關羽。《水滸傳》一百單八將都有一個綽號,這些綽號的意義正如伊恩·P·瓦特所說,“它所應象征的是,人物被看成了一個特殊的人,而不是一個類型。”[7]賦予人物一個綽號,使之成為這個人的象征,凸顯其主要的性格特點,成為小說作者塑造陪襯人物的重要手段,金陵笑笑生借鑒施耐庵、羅貫中的做法,對西門慶的十兄弟逐個貼上標簽,所不同的是,《水滸傳》的人物綽號多以武功的專擅、器械的使用為考察標準,《金瓶梅》的人物綽號則與人物性格的刻畫直接關聯。
4.直接戲謔
古代小說大多運用全知視角描寫人物,并經常從道德層面對人物進行評判,以表明作家的情感態度。《金瓶梅》的評語,又多從戲謔的角度入手,以調侃語言出之。
小說伊始,王婆第一次出場時作者就直接出面進行調侃: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隋何。只憑說六國唇槍,全仗話三齊舌劍。只鸞孤鳳,霎時間交仗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搬說擺對。解使三里門內女,遮莫九皈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臂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略施奸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才用機關,交李天王摟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合,女似麻姑須亂性。藏頭露尾,攛掇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調弄嫦娥偷漢子。”(第2回)
西門慶死后不久,李嬌兒先是渾水摸魚,盜取幾百兩元寶,然后迫不及待的歸來麗春院,其薄義寡情連作家都看不下去了,直接出面嘲諷:
“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為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辰張風流,晚夕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后門接兒子;棄舊憐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活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后嚷鬧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第80回)
妓院出身的李嬌兒無情,一向蒙主子惠顧的幫閑更是無義。西門慶尸骨未寒,應伯爵立馬改換門庭投到張二官麾下,繼續他的幫閑生涯,作者給予無情嘲諷。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閑子弟,極是勢利小人。”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第80回)
5.惡搞
俗話說“謔而不虐”,意即開玩笑不宜過分,不令人難堪。如同“怨而不怒”抒情傳統一樣,強調節制,含蓄。戲謔也應該 “戒淫褻”“忌俗惡”“貴自然”,做到“雅俗同歡,智愚共賞”[8]。可惜的是,《金瓶梅》的戲謔運用,偶爾流于油滑和惡搞。小說第五十二回和第五十四回里就有兩處對妓女的惡謔性描寫。
應伯爵發現西門慶與李桂姐離席很久,就悄悄跟蹤尋找,終于發現二人在藏春塢里茍合。常人唯恐避之不及,這個下流無恥的家伙不僅沒有回避,先是在門縫外“只顧聽覷”,然后“猛然大叫一聲,推開門進來”,要“抽個頭兒”,硬是按著李桂姐“親個嘴”,在妓女身上揩完油方才罷手。(第52回)
“伯爵一面叫擺上添換來,轉眼卻不見了韓金釧兒。伯爵四下看時,只見他走到山子那邊薔薇架兒底下,正打沙窩兒溺尿。伯爵看見了,連忙折了一枝花枝兒,輕輕走去,蹲在他后面,伸手去挑弄他的花心。韓金釧兒吃了一驚,尿也不曾溺完就立起身來,連褲腰都濕了。不防常峙節從背后又影來,猛力把伯爵一推,撲的向前倒了一交,險些兒不曾濺了一臉子的尿。伯爵爬起來,笑罵著趕了打,西門慶立在那邊松陰下看了,笑的要不的。”(第54回)
三、戲謔是小說藝術的審美需求
蘇涵說,“在中國小說美學中,趣味追求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一種同樣富于文化意味和審美意味的現象,我們甚至可以把它視作中國小說審美理想的先導。今天的古代小說批評,很少涉及小說趣味問題,實在是學術上的一個疏漏;今天的小說創作,回避小說趣味,也實在是文學與小說的遺憾。”[9]
“趣味”是小說與生俱來的審美訴求,宋元以降,伴隨城市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擴大,審美趣味的易變成為歷史的必然。誠如潘知常所言,“伴隨著明中葉審美理想、審美趣味的變化,對于藝術美的要求,也就從‘意境’轉向了‘趣味’。”“明中葉,最先以趣味作為審美范疇的,是李贄。”[10]
李贄在《水滸傳》第五十三回的評語中發出了“天下文章當以趣為第一”的審美呼喚,在《西游記評》中更有47處 論“趣”之語,深刻影響小說的創作和批評。比起《西游記》作者對佛道人世的調侃,蘭陵笑笑生小說對社會、人性的批判力度更深,手法更豐富。
明代中葉以后,整個社會物欲、人欲橫流,道德滑坡。“既然現實是如此荒唐滑稽,那么作為藝術形式的戲謔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文藝作品表現出來,這既是藝術家的必然選擇,也是現實的必然選擇。”[11]這或許就是《金瓶梅》的主要創作動因和審美追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