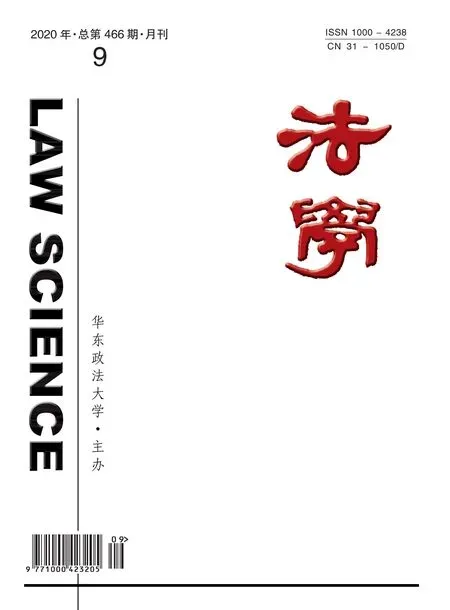論軍事活動規制國際法的碎片化與開放性
——從“烏克蘭艦船扣押案”切入
江 河
自蘇聯解體后,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國在領土歸屬與海洋劃界問題上一直存在嚴重的對立與分歧。盡管兩國就刻赤海峽水域的法律地位及其劃界已進行過多輪談判,但雙方仍未能有效解決其爭端,而2014 年初發生的“克里米亞公投事件”更是進一步加劇了兩國關系的惡化。2018 年11 月25 日,三艘烏克蘭軍艦從黑海的烏克蘭敖德薩港出發前往亞速海的烏克蘭別爾江斯克港,在途徑刻赤海峽時遭遇到俄羅斯海岸警衛隊的攔截、追捕和扣押,隨后俄羅斯以非法跨越國境罪起訴了船上的24 名烏克蘭海軍官兵。2019 年4 月16 日,烏克蘭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290 條第5 款之規定,聲稱俄羅斯非法行使了管轄權,請求國際海洋法法庭發布臨時措施。作為回應,俄羅斯辯稱,其行為涉及軍事活動,并已依《公約》第298 條作出了軍事活動強制管轄排除聲明,否認法庭對案件的管轄權,并缺席了法庭有關臨時措施的審理。研讀案件基本事實和雙方主張,不難發現該案的焦點主要聚集在此類爭端是否屬于軍事活動的范圍上,而法庭是否具有管轄權則取決于對《公約》第298 條第1 款軍事活動例外的解釋及適用。根據相關事實和證據,法庭一方認定《公約》第298 條的例外條款不適用于此案,而烏俄雙方對爭端是否涉及軍事活動或適用《公約》第298 條則是各執己見。梳理剖析此案,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國際司法實踐中軍事活動的法律界定及其司法管轄的現實困境,而如何解讀軍事活動規制國際法的碎片化與開放性有助于我們認識和解決這一困境。
一、“軍事活動”規制法律體系的碎片化
作為國際法的一個分支,戰爭法的歷史頗為悠久。在國際關系中,國家被視為國際法的原始主體。在原始的“自然狀態”中,戰爭被視為國家的天賦權利。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國家的戰爭行為逐漸為國際人道法所規范,軍事活動也日益成為國際法的規制對象。然而,國際法的碎片化狀態使其無法對軍事活動展開有效規制,《公約》爭端解決機制的相關程序規則也導致軍事活動在強制管轄權上的不確定性。這種實體與程序管轄的雙重困境在“烏克蘭艦船扣押案”〔1〕Se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www.itlos.org/cases/list-of-cases/case-no-26/, last visit on November 6, 2019.(以下簡稱“扣押案”)中得到了充分印證。
(一)“扣押案”中“軍事活動”界定之爭議
“扣押案”管轄權爭議的特殊性表現在國際海洋法法庭對于爭端的管轄取決于對《公約》第298條“軍事活動”的解釋與適用,這歸因于俄羅斯與烏克蘭就艦船扣押行為是否屬于“軍事活動”擁有截然相反的主張。根據俄烏雙方向法庭提交的相關證據,被扣押的烏克蘭艦船包括兩艘軍艦及一艘輔助性拖船,俄羅斯聲稱,烏克蘭艦船于2018 年11 月25 日通行刻赤海峽的行為違反了俄方2015 年10 月制定的國內法《刻赤海港強制條例》(Mandatory Regulations for the Seaport of Kerch),在對烏克蘭艦船進行封鎖并要求停航無效后,俄羅斯海軍和海岸警衛隊對烏克蘭艦船進行了追捕、發射警告并隨之開火,造成烏方一艘軍艦受損和3 名海軍士兵受傷。隨后,俄羅斯扣押了烏克蘭三艘艦船和24名海軍官兵,并依其國內法以“非法穿越俄羅斯國家邊境罪”對所有官兵提起了刑事訴訟。在此行動過程中,俄羅斯國防部的一架戰斗直升機也參與了攔截,其黑海艦隊的軍艦亦承擔了對烏克蘭海軍行動的監測任務。
《公約》第十五部分是對國際海洋法法庭管轄爭端的解釋或適用。作為強制爭端解決程序的任擇性例外,第298 條規定了締約國可通過書面聲明排除特定法院或法庭管轄的爭端類型和相關程序。〔2〕《公約》第298 條第1 款規定的各締約國可書面聲明排除強制管轄的爭端主要包括關于劃定海洋邊界及涉及歷史性海灣或所有權的爭端、關于軍事活動的爭端,以及關于安理會履行其職能的爭端等三類。根據俄羅斯與烏克蘭批準《公約》時所發表的聲明,兩國都不接受《公約》對有關“軍事活動”爭端進行強制管轄。〔3〕俄羅斯于1997 年3 月12 日、烏克蘭于1999 年7 月26 日批準《公約》時均發表了聲明,根據《公約》第298 條,對該條款中的特定事項不接受《公約》第十五部分第二節規定的強制程序。See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III.aspx?src=TREATY&mtdsg_no=XXI-6&chapter=21&Temp=mtdsg3&clang=_en#EndDec, last visit on March 8, 2020.所以,《公約》第298 條第1 款b 項中規定的軍事活動例外便成了本案各方爭論的焦點。在2019 年4 月30 日遞交的照會中,俄羅斯駐德大使館主張,爭端涉及軍事活動,法庭沒有管轄權;烏克蘭則聲稱,該爭端源于執法活動,雙方聲明并未排除對此類活動的管轄權,法庭應該享有管轄權。造成管轄權認識分歧的原因顯然是基于兩國對“軍事活動”的不同解讀。
法庭雖最終認定此案不適用《公約》第298 條第1 款b 項的規定,排除了軍事活動例外條款的適用,但在所發布的臨時措施中并未對軍事活動及其具體判斷標準給予明確之界定。對此,目前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盡管《公約》和相關國際司法實踐對“軍事活動”缺乏準確定義,但基于軍事活動的高度政治性,對其作相對廣義的解釋更容易為各國所接受,也就是說,它不應僅局限于軍艦和軍用航空器或從事非商業服務的政府船舶和航空器進行的活動。〔4〕See Stefan Talmo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Is There a Case to Answer? in Stefan Talmon and Bing Bing Jia(eds.),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Hart Publishing, 2014, p.57-58. 美國在審議《公約》的批準事項時曾經主張,根據《公約》第298 條第1 款b 項,締約國享有確定其活動是否屬于軍事活動的專屬權利,并將其作為加入《公約》的前置條件,可見軍事活動的高度政治性。Se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olution of Ratification: Senate Consideration of Treaty Document 103-39, https://www.congress.gov/treaty-document/103rd-congress/39/resolution-text, last visit on March 11, 2020.然而,應該看到,廣義的解釋在客觀上容易導致軍事活動行為主體的模糊化,無法根本解決“軍事活動”的界定難題。事實上,傳統的觀點多將行為主體作為軍事活動的唯一界定標準,強調行為主體必須具有“軍事”性質。〔5〕See Wol☆ Heintschel von Heinegg,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 Belgi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47, No.1, 2014, p. 45-64.比如,在《專屬經濟區航行與飛越指南》中,“21 世紀專屬經濟區小組”將軍事活動界定為軍艦、軍用航空器和其他軍事設備的行動,包括情報搜集、演習、試驗、訓練和武器演練等,〔6〕該指南以《公約》、國家實踐與軟法為法理基礎,盡管在性質上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它為專屬經濟區內軍事活動的界定提供了基本原理,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際社會的共識。See EEZ Group 21, Guidelines for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https://www.spf.org/en/_opri_media/publication/pdf/200509_20051205_e.pdf, last visit on November 7, 2019.這種主體性界定將海岸警衛隊、海關、漁政等政府船舶及航空器的行動絕對排除于軍事活動之外。又如,美國學者特里·吉爾和迪特爾·弗萊克將“軍事活動”界定為由武裝部隊從事的具有明確目的的協同行動。〔7〕See Terry D. Gill and Dieter Fleck(eds.), The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Military Operations,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681.不同的定義顯然也不能完全適應不同情形下“軍事活動”的界定要求。其實,除了行為主體的類別外,行為本身的客觀表現形式及其主觀目的也會對行為性質的界定產生實質影響。例如,非軍事行為體出于軍事目的而使用武力或特定武器的,往往也會被認為具有軍事活動的性質。而類似活動的性質爭議在于,軍艦和軍用航空器有可能基于非軍事目的而從事執法行為或經濟活動。〔8〕如有學者認為,軍事主體所從事的活動,既可能涉及武裝沖突,也可能涉及執法行動。同上注,第31、63 頁。為此,瑞典學者賽義德·馬哈茂迪結合行為主體與目的,將“軍事活動”界定為由軍艦、軍用航空器或從事非商業服務的政府船舶和航空器進行的以提高一國戰備狀態為目的的活動。〔9〕See Said Mahmoudi, Foreig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Swedish Economic Zon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11, 1996, p. 375.
所以說,就“軍事活動”的界定標準而言,行為主體、方式及其主觀目的等多重考量因素使得各國難以就其概念界定達成一致意見。而針對和平時期的海上維權活動,各國執法船只開始配備準軍事力量裝備,也日漸模糊了傳統軍事主體與行政執法主體之間的界限。同時,軍事主體與非軍事主體海上協同維權模式應用的逐漸增多也讓行為主體難以成為軍事活動的唯一或主要的界定標準。若僅從行為目的出發,則缺乏客觀標準的主觀判斷可能對軍事活動作出擴大解釋,模糊其與一般意義上的海上安全行動之間的界限;若將戰爭相關的武力或武器之使用作為軍事活動的構成要素,則更加不合理,因為其排除了其他出于軍事目的而以非武力手段從事的諸如軍事科研之類的活動。
由是可見,僅單一考量行為主體、方式或目的,皆不足以對“軍事活動”進行準確的界定。筆者以為,何為“軍事活動”的判斷應當結合特定案件的具體情勢和相關事實,從行為主體、方式和目的等方面進行綜合考量,海上軍事活動的外延應當涵蓋由海上武裝力量出于軍事目的所進行的系列行動,包括一國軍艦、軍用航空器或其他軍事設備,或者以其為主并有其他海上力量參與的,出于維護本國主權、國民及其財產安全等軍事目的,所從事的海上軍事演習、軍事偵察及測量、武器演練等武力或非武力行為。
(二)國際法的碎片化與“軍事活動”的規制困境
“冷戰”結束后,全球和區域層面在各領域的相互依存逐漸深化,然而國際法規則在數量上的劇增并未能使其在性質上形成統一的法律秩序。現有國際法中不同規則和結構的局部體系構成了一種“無組織體系”,〔10〕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the Work of Its Fifty-second Session, Annex, A/55/10.導致各種國際法規則之間存在相互沖突之可能。國際法的碎片化就是對這種國際法規范不成體系性的描述。〔11〕在不同程度的法律一體化中,各國締結的普遍的、區域的甚至是雙邊的體系、小體系和小小體系充斥著國際法體系。不同體系內部的各種規范和制度之間缺乏結構上的有機聯系,“它們相互沖突、彼此矛盾,就像堆積在一起的‘玻璃碎片’。”參見古祖雪:《現代國際法的多樣化、碎片化與有序化》,載《法學研究》2007 年第1 期,第139 頁。“扣押案”對“軍事活動”的界定及管轄困境正是源于國際法的碎片化。
國際社會的平權結構是造成國際法碎片化的首要原因,缺乏統一的中央立法機構使得具有不同結構的國際法規范難以被協調一致地適用。在國際法語境下,作為國際法基礎規范〔12〕凱爾森認為,法律秩序是一個規范體系,不能從一個更高規范中得來自己效力的規范被稱為基礎規范(basic norm)。可以從同一個基礎規范中追溯自己效力的所有規范,組成一個規范體系,或一個秩序。參見[奧]漢斯·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版,第124-126 頁。的條約必須遵守只有形式之邏輯建構,而無實體之價值規范,導致國際法的不同部門法或條約規則缺乏宏觀上的體系性及效力位階,也沒有為微觀規范沖突的解決確立優先性原則。相較而言,國內法的基礎規范體系,既具有效力等級的位階,〔13〕在國內法體系中,不同的部門法存在不同的基礎規范,在整個體系中,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和法治的結合點,因此,憲法的基礎規范在整個國內法中具有最高的效力位階。也具有實體權利義務之含義。在實質上,法律位階是立法機構立法權限及其位階的體現,因為公民政治的缺乏,國際社會不存在超國家的統一立法機構,國際法自然也就缺乏憲法性基礎規范所具有的效力位階整合功能。
于軍事活動相關的國際法規范而言,這些規則的內在沖突是其碎片化的具體表現。作為最重要的造法性公約和國際法價值的權威表達,《聯合國憲章》第1 條規定的3 項實質性宗旨〔14〕《聯合國憲章》第1 條規定:“聯合國之宗旨為:一、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并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于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二、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系,并采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三、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于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并激勵對于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十分清晰明確地界定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首要價值。在此基礎上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則體現為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而侵害一國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盡管這類規范并未禁止軍事活動,甚至未出現軍事活動的表述,但客觀上它對軍事活動的主要形式,即武力之使用或威脅進行了限制。此外,包括海上武裝沖突法、習慣國際人道法等在內的戰時國際法,肯定了交戰權之合法行使,但平時國際法規范體系,尤以《公約》為例,卻排除了對軍事活動爭端的強制管轄,從而給予了反向規制。在碎片化的國際法律秩序中,由于不同的國際法規范對軍事活動進行了直接或間接的規制,所以厘清各類規范的效力位階,對法律沖突的解決尤其重要。
從國際法本體論出發進行審視,〔15〕一般而言,以國際法的淵源來指代其本體。國際法的本體論實際上是借由國內法意義上本體論的邏輯,與國際法基本范疇的必然發展規律,闡釋實證法意義下的法律規范對國際法原則具體外延的確定,以及自然法意義下的法律價值對法律原則內涵的塑造和法律規范制定的指引。參見江河:《國際法的基本范疇與中國的實踐傳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16-20 頁。國際法價值是指引主體建構國際法體系的正當性基礎與環境資源,國際法基本原則以其價值傾向和普遍性主導著具體規則的創設和適用;反之,國際法規則也體現了基本原則。在國際法具體規則的集合中,盡管不存在類似于國內憲法的“基礎規范”,但基于聯合國的主導地位和重要職責,《聯合國憲章》在各種國際法規則中具有優先適用性,〔16〕《聯合國憲章》第103 條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依任何其他國際協定所負之義務有沖突時,在本憲章之義務應居優先。”第2 條第6 款規定:“本組織在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范圍內,應保證非聯合國會員國遵行上述原則。”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內涵揭示了其具有普遍適用性。〔17〕國際法基本原則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適用于一切國際法領域的、構成國際法基礎的法律原則。參見梁西主編:《國際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40-41 頁。于一些特定領域或特定情形下適用的國際法規則而言,無論其是否具有自足性,都應當按照一般國際法進行一致性解釋。〔18〕See Jan B. Mus, Conflicts Between Trea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45, 1998.只是這類規則之間的效力等級只能通過規則本身的規定加以判定。
國際法的碎片化必然會導致法律適用中的規則沖突,而國際司法裁決在這種沖突中發揮著一定的體系整合作用。盡管基于裁判本身的司法屬性,其法律拘束力因僅限于特定事項和當事國而不具普遍性,〔19〕國際司法機構的裁決及國際仲裁機構的裁決對當事國具有拘束力,被認為是一項普遍承認的國際法原則。(參見許光建主編:《聯合國憲章詮釋》,陜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602 頁。)《國際法院規約》第59 條也規定:“法院之裁判除對于當事國及本案外,無拘束力。”但包括國際法院在內的國際司法機構經常援引前例,對國際法原則、規則進行解釋或論證。通過國際司法實踐,國際法規范的實質內容得以界定和解釋,沖突規范之間的優先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決。作為國際法淵源的權威性說明,〔20〕See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8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340.《國際法院規約》第38 條第1 款將司法判例作為確定國際法規則的輔助方法,表明司法判例在確定國際法規則時構成了國際法的輔助性淵源,而抽象意義上的司法裁決則成為國際法淵源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者作為國際軟法而存在。事實上,國際司法裁決所具有的這種法律作用促進了國際法的發展,就國際法規則的闡明和適用而言,它是國際法體系性得以增強的重要路徑。
需要注意的是,國際司法裁決還可能對特定國際習慣的形成和條約規則的解釋產生積極或消極的作用,其法律整合作用也會受到大國政治的影響。在解決國際爭端的司法實踐中,有關爭端依托的國際政治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法官或仲裁員對特定事項的法律判斷。通常情況下,具備較強國際實力的大國可能會通過程序霸權影響審判過程,抑或是事實上不執行裁決,損害國際司法裁決的公正與實效。
二、國際法的開放性與軍事活動的可規范性
國際法的發展離不開其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歐洲30 年戰爭之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促成了近代國際法的形成;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成為推動現代國際法發展的歷史契機;21 世紀的全球化則在相互依賴中促進了國內法與國際法的融合及國際關系的法治化。國際法的社會基礎和基本特性決定了其法理具有雙重性,即功能性合作領域的自然法精神與軍事等敏感領域的權力政治。其中,前者代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后者與大國政治和小國政治的外交博弈相關,兩者的互動有賴于國際民主對國際法治的主導性整合。
戰爭法與國際人權法的歷史發展揭示了軍事活動不斷被禁止或限制的規范化進程。在國際關系中,“高政治”和“低政治”分別對應著國際法雙重法理的理論語境,國家主權的雙重屬性在呼應了雙重法理的同時也造就了國際法的開放性。也就是說,國際法的體系性和專業性都是隨著“高政治”領域的軍事活動被不斷規范而增強的,這一切皆源于單個國家的脆弱性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價值追求。
(一)軍事活動法律規制的歷史邏輯
在社會契約論的自然狀態下,國家及其法律規制的缺乏,使人們本能地訴諸于暴力以滿足自身追求安全、利益或名譽的天性,此際便導致了“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21〕參見[英]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2009 年版,第94-95 頁。在早期的國家關系中,戰爭被認為是無政府狀態下一種原始的軍事活動。換言之,在無序的國際社會中,國家通過戰爭保障安全,訴諸武力以解決爭端,是合乎邏輯的自然行為。因此,戰爭可被視為國家的一種天賦權利,抑或是國際行為規范的正當性基礎。而國家主權觀念的形成和近代國際法的發展,則進一步使戰爭權具有了法律上的意義。
盡管使用武力乃至訴諸戰爭的權利構成了傳統國家主權的一部分,〔22〕有觀點認為,一國主權特別體現在戰爭中,而限制國家訴諸戰爭的權利是與該國主權不相容的。參見[奧]漢斯·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商務印書館2017 年版,第470 頁。但戰爭權的濫用不僅無益于保障個人安全,而且也會破壞國際社會的基本秩序。戰爭的殘酷與災難推動了國際人道法的發展,以軍事活動為主要形式的戰爭或武裝沖突逐漸為國際法所禁止。通過國際習慣的編纂和條約造法,以“日內瓦體系”和“海牙體系”為主要內容的國際人道法日益限制了戰爭和武裝沖突,以保護受害者。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經兩次海牙和平國際會議簽署及修訂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構成了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的歷史淵源。隨后,《國際聯盟盟約》以“冷卻制度”限制了訴諸戰爭的時間與條件,雖然它未禁止以戰爭作為國際爭端解決的手段,但至少讓會員國承擔了一定的戰爭節制義務。〔23〕《國際聯盟盟約》第12 條第1 款規定:“聯盟會員國約定,倘聯盟會員國間發生爭議,勢將決裂者,當將此事提交仲裁或依司法解決,或交行政院審查。聯盟會員國并約定無論如何,非俟仲裁員裁決或法庭判決或行政院報告后三個月屆滿以前,不得從事戰爭。”1928 年《巴黎非戰公約》首次正式宣布廢棄推行戰爭的外交政策,并強調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但該公約依舊未明文禁止在國際關系中使用武力。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通過的《聯合國憲章》第2 條中明確規定了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而侵害他國領土主權或政治獨立,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以安理會為核心的集體安全制度,這一法律制度加強了對軍事活動的規制。
一方面,出于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考慮,國家的原始性軍事活動日益受到國際法的限制;另一方面,國際法的例外規則又以自保權名義賦予主權國家以軍事活動的自由。自保權可以分為自衛權和國防權。自衛權是國家在遭遇外敵入侵的特殊情況下享有的權利,而國防權是國家制定國防政策,進行國防建設,以防備外來侵犯的權利。〔24〕參見周鯁生:《國際法》(上),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167 頁。在國際法中,國家軍事活動的外延是由剩余原則決定的,即國際法上沒有限制的軍事行為都屬于國家的軍事活動自由。廣義的戰爭法可分為訴諸于戰爭權的法律(jus ad bellum)與戰爭狀態下的作戰法(jus in bello),后者可視為狹義的戰爭法,它主要分為規范作戰方法的海牙公約體系與保護戰爭受難者的日內瓦公約體系。然而,國內的公民安全和外在的國家安全是國家高政治活動的基本目標,軍事活動是國家最為核心的高政治活動。因此,就實證國際法而言,國家的軍事活動并未被完全禁止,主權國家不但在其領土范圍具有較為寬泛的軍事活動自由,而且在國家管轄范圍外的國際區域也具有一定的軍事活動自由。
(二)軍事安全的“高政治”性與國際法的開放性
國際關系中的“高政治”,是指從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的角度對民族國家的生存至關重要的問題,如軍事、外交、執法等領域的事務;“低政治”則涵蓋了對國家生存并非絕對重要的問題,如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領域的事務。〔25〕See Cecilie Brein, Does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High’ and ‘Low’ Politics Mark the Limit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Justice and Home A☆airs,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February 2008.現實主義學者認為,“高政治”,如軍事安全問題,總是支配著“低政治”,如經濟和社會事務等。〔26〕See Robert O. Keohane and Jr.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4th ed., Pearson, 2012, p. 19.從國際法的關聯論出發,國際政治是國際法社會基礎的重要維度,〔27〕國際法規則的創設和適用與國際政治、全球市場和民族文化融合存在密切聯系,其中國際政治發揮著關鍵作用,而這種關聯性也使原始的國際法向其社會基礎開放。同前注〔15〕,江河書,第26 頁。也是導致國際法開放性的關鍵因素。政治是法律的基礎,前者構成后者的合法性淵源。而國內法中政治與法律的關聯性為認識國際政治與國際法的相互關系提供了理論邏輯。國際法以國際關系為主要調整對象,其社會基礎也必然隨國際關系或國際政治的演進而發生變化。在此基礎上,國際法開放于國際政治,這種開放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依次體現為對霸權政治、大國政治和公民政治的開放。任何法律的發展史皆為其主體的發展史,國際法的開放性亦體現在其主體與國際關系主體的關聯性之上。國家主權的相對性和國際人權的發展,使得國際法主體的外延發生了變化,國際組織和國際人權保護領域內的個人都在一定程度或范圍上具有了國際法律人格。基于主體論對價值論的決定作用,國際法的價值也因此顯示出特定的發展趨勢:和平價值的基本內涵由國家間無戰爭的消極狀態演進到對人類基本人權的尊重和保護,這種發展體現了“天賦人權”在國際社會的邏輯延伸。
基于國際政治和國際法的邏輯互動,國際法的開放性存在雙向解讀。一方面,國際政治對國際法的開放使其受到國際法的積極規范;另一方面,國際法也因這種開放性而遭到權力政治的消極削弱。前者對應于法治導向的自然國際法,后者體現為權力主導的實證國際法。作為國際政治的重要因素,對外的軍事活動在人類文明進步的過程中不斷為國際法所規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自然國際法為戰爭類罪行的懲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礎。同時,國際法的創設、適用與實效,包括國際爭端的司法解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國政治的影響。與霸權政治不同的是,大國政治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對國際法價值的實現具有積極作用。國際聯盟與聯合國不同的決策制度及其實踐皆表明,大國政治的決策機制比小國政治的全體一致更為有效地維護了國際和平與安全。〔28〕See Russell S. Sobel, The League of Nations Covenan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 Analysis of Two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s,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5, 1994.
由于軍事安全是主權國家“高政治”中的核心內容,所以國際法對軍事活動的規制也逐步向國際政治因素開放。國際關系和世界秩序的發展史表明,霸權政治對國際法的發展具有抑制作用,而大國政治與小國政治則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促進了國際實體法和程序法的發展,兩者之間的博弈也體現于軍事活動的國際法規制及其司法管轄上。在國際爭端的解決實踐中,大國基于自身實力更易控制國際制度的政治規范,因而傾向于以政治方法獲取利益,而小國則更多訴諸于體現國家主權平等的國際法機制。〔29〕參見江河:《南海爭端的和平解決:大國政治和小國政治的互動》,載《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2 期。例如,在前文述及的俄羅斯與烏克蘭領土爭端中,烏克蘭是俄羅斯地緣政治上的重要安全屏障,位于烏克蘭之南和俄羅斯之西的克里米亞半島具有較高的軍事戰略地位,也是兩國領土爭端的主要客體。蘇聯解體后,行政上受烏克蘭管轄的克里米亞繼續劃歸其所有,在克里米亞公投之后,實力強大的俄羅斯事實上接管并從軍事上控制了該地區。〔30〕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軍事實力對比大致為:現役軍事人員數量76.6 萬:16 萬,坦克裝甲戰車總數43107 輛:10543 輛,4 代與4代半戰機數量630 架:116 架,作戰飛機與直升機總數4055 架:493 架,海軍艦只總數352 艘:25 艘。參見《圖解:俄羅斯與烏克蘭經濟軍事實力對比》,載鳳凰網2014 年3 月3 日,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wukelanshiwei/content-3/detail_2014_03/03/34344196_0.shtml。針對涉及兩國海上劃界問題的“扣押案”,俄羅斯否認法庭管轄權并缺席有關臨時措施的審理,對不符合其訴求的司法裁決也能在事實上不遵守和不執行,這些均深刻地體現了國際爭端解決中的大國政治因素。與俄羅斯相比,烏克蘭在國際關系的影響力和政治風險規避能力明顯處于劣勢。因此,在兩國領土與海洋劃界爭端中,烏克蘭傾向于運用小國政治來抗衡大國政治,這種策略在“扣押案”中則體現為將雙邊爭端訴諸于強制性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在克里米亞爭端中則以主權國家的立法來否定公投效力。雖然烏克蘭與俄羅斯在文化上同源,但兩國的綜合實力差異巨大。在小國與大國的對立博弈中,小國政治的優先選擇是訴諸于有效的國際機制,包括政治機制和法律機制,而次優的選擇是與大國或大國集團結盟。在克里米亞爭端中,烏克蘭的本能選擇是“脫俄入歐”,并加入北約以對抗大國俄羅斯,此舉與歐美向東擴張勢力以遏制俄羅斯的目標相一致,如此做法無疑導致了地區爭端的復雜化和國際化。
由是可見,國際爭端司法解決的有效性顯然受到了大國政治的影響,軍事安全的高政治性與國際法的開放性則是國際司法管轄及裁決執行困境的根因。以國際海洋法為例,《公約》第十五部分規定了爭端的強制解決程序,此司法解決路徑比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的外交談判方法更進了一步,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際關系中主權國家的平等性。但是,在《公約》第298 條列舉的任擇性例外中,有關軍事活動的爭端作為例外而免于強制管轄的規定,又顯示出國際法對國家主權和高政治敏感問題的妥協,客觀上為大國政治的實踐提供了外交空間,從事實上削弱了國家之間的實質平等。
除此之外,集體安全制度也是傳統國際法向現代國際法發展的標志之一,〔31〕參見梁西:《梁著國際組織法》,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181 頁。盡管聯合國集體安全制度表明了大國政治對維護國際秩序具有積極作用,但國家之間的實質平等才符合國際關系的發展規律。實踐中,追求平等權利的小國政治與大國政治的博弈,以及小國政治對大國政治的漸進式超越,皆預示了國際法的發展趨勢是國際組織或國際機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
(三)國際和平價值與“軍事活動”管轄例外的沖突
國際法語境中的和平是指國家間無戰爭的狀態。〔32〕[法]雷蒙·阿隆:《和平與戰爭:國際關系理論》,朱孔彥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 年版,第158 頁。就法律價值而言,國際和平對應著國內法語境中的秩序。秩序的核心是安全,盡管安全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但在社會關系的穩定性上,秩序與安全具有同質的基本內涵。
在現代國際法的價值體系中,國際和平與安全為首要價值。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對國際正義的不同認知,使得國際正義的終極價值難以實現。作為國際法基本價值的權威解讀,《聯合國憲章》第1 條的內在邏輯凸顯了國際和平價值的優先性。由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到發展國家間的友好關系,再到對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各項實質性宗旨的排序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國際法的基本價值將會沿著消極和平到積極和平再到永久和平的邏輯軌跡發展。〔33〕《聯合國憲章》第1 條第1 款中的“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等措辭,顯示出這種和平價值取向的消極面向;而第2 款中國家間的“友好關系”則表明這種和平狀態具有持久性與積極性,預示著從消極和平向積極和平過渡的歷史軌跡;第3 款中對全體人類之人權的普遍尊重和保護則使國際和平之價值的內涵進一步豐富,這種普遍的友好關系為世界公民權利及永久和平提供了基礎。參見[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2009 年版,第118 頁;參見江河:《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南海安全合作——以國際法價值觀的變革為視角》,載《法商研究》2018 年第3 期。
在某種程度上,國際法淵源于無政府狀態下的戰爭規制,傳統國際法的發展史也是一部戰爭法的歷史。“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構成了社會契約的邏輯前提,人類對和平與秩序的欲望,為法律的形成提供了內在動因。〔34〕參見[美]E·博登海默:《博登海默法理學》,潘漢典譯,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179 頁。在早期的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以其天賦的戰爭權利解決爭端或獲取利益都被視為是一種本能行為。國際法語境中“一切國家對一切國家的戰爭”狀態也同樣要求通過國家間的“社會契約”來保障國際安全。承前所述,歐洲30 年戰爭和威斯特伐利亞和會促進了近代國際法的形成,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也客觀上推動了現代國際法的迅速發展,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及其主導的國際法律制度得以形成。盡管仍不存在一個“超國家”的世界政府,但國際關系的發展史已經表明,國際法的價值取決于它對戰爭的禁止,在和平時期,則依賴于對軍事活動的規制。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尤其是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與現代武器的結合,將使人類面臨戰爭帶來的毀滅性災難。經濟全球化的負外部性正在不斷蔓延至國際社會的各個領域,氣候變化、國際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日趨嚴重,國家的脆弱性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的全球風險社會中日益凸顯。〔35〕相對于傳統安全而言的非傳統安全則可界定為:一切免于由非軍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脅的自由。簡而言之,非傳統安全是“非軍事武力的安全”,如經濟安全、恐怖主義、環境污染、人口爆炸、毒品走私、跨國犯罪、艾滋病傳播等。參見余瀟楓、王江麗:《非傳統安全維護的“邊界”“語境”與“范式”》,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 年第11 期。在某種意義上,人類的生存將取決于高科技戰爭與國際法規制的競賽。在國家領土之外的管轄海域、爭議海域及國際公域,國際和平與安全顯然比國家的軍事活動自由更具有價值層級上的優先性。然而,《公約》第298 條關于軍事活動的任擇性例外,事實上鼓勵了爭端國將相關執法活動升級為威脅和平的武力行為,如此可通過軍事活動的例外來規避國際司法機構的強制管轄。依此可以推斷,具有強大軍事實力的大國,可能會沿著這種現實主義的邏輯,假以國際法之名,罔顧國際和平而追求單方利益,這無疑將威脅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也與國際法治和人類文明的發展相違背。
三、海上軍事活動的司法實踐與我國的海洋維權
沿海國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和海洋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了新一輪的“藍色圈地”運動,各種海洋爭端日益尖銳,其中不乏武力之使用或軍事活動的重要案例。“扣押案”和“南海仲裁案”均說明,海上軍事活動的司法實踐具有不確定性,特別是管轄權的確定和對相關規則的解釋。基于司法裁決本身對爭端方海洋權益的實質影響和對國際法規則形成及發展的重要作用,海上軍事活動與執法活動的概念界定及比較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同時,它還有助于我國對內完善海洋執法體制,對外有效進行海洋維權。
(一)國際司法裁決的不確定性及其法律意涵
國際司法裁決的不確定性源于國際法實體規則的碎片化及國際司法機構管轄權和爭端可受理性的不確定性。就海上軍事活動相關的司法實踐而言,軍事活動的法律界定與行為規制都處于國際法的灰色區域,相關原則或規范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在這種狀態所導致的法律“空隙結構”中,大國政治通過司法能動主義削弱了國際法的實效,小國政治則通過國家主權來維護其國家利益。大國政治與國際法治在全球治理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動。〔36〕參見江河:《國家主權的雙重屬性和大國海權的強化》,載《政法論壇》2017 年第1 期。國際司法裁決作為一種較為公正和獨立的國際法實踐,其在條約規則的解釋和國際習慣的證成中都具有重要作用,還能通過國際軟實力和國際軟法來間接規范大國政治。
無論是《國際法院規則》,還是《公約》附件七設立的仲裁法庭議事規則,管轄權和可受理性均被視為爭端方初步反對的依據。在國際實踐中,爭端方的書面陳述和司法裁決均未對管轄權和可受理性問題予以權威性界分。若以國際司法機構的司法權力為視角,管轄權規則旨在界定法院在爭端解決中是否享有司法權力,而可受理性規則旨在界定法院行使這種司法權力的能力范圍,〔37〕See Yuval Shany, Questions of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Before International Cour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這表明普遍意義上的管轄權之確立是判斷可受理性問題的前提,兩者的權能內容有所不同。
由于國際法的碎片化和自行決定管轄權的爭端解決機制,所以隨著國際司法機構的擴散,它們決定具體國際爭端的管轄權及其可受理性問題的規則也存在差異。海洋法客體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決定了其法律屬性,〔38〕參見江河:《海洋法的特性演變與中國的海洋權益——以海洋基本屬性為框架的研究與建議》,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 年第23 期。如《公約》中大陸架法律制度是以地理意義上的大陸架為法理基礎的。與陸上爭端客體不同的是,海洋具有特殊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導致法律權利與規則創設更為復雜。海洋爭端(特別是混合型海洋爭端)定性的模糊化也使得司法過程中的自由裁量權過大,而具體行為界定的不確定性,則進一步增強了管轄權和可受理性的不確定性。
對《公約》第298 條第1 款的解釋將影響司法機構的管轄權,而對軍事活動的外延界定又是決定管轄權依據的關鍵問題。相關司法實踐已經表明,軍事活動外延的界定具有不確定性,甚至其實體規則處于未定狀態。以“扣押案”為例,法庭的管轄權完全建立在對軍事活動條款的解釋上。盡管如此,法庭仍未能明確軍事活動外延的具體標準,僅主張其行動性質的界定應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不能僅依據行動的軍事或執法性質,抑或爭端各方的主觀描述進行判斷。〔39〕See 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case_no_26/C26_Order_25.05.pdf, last visit on December 1, 2019.然而,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認為,相關行動的準軍事力量可與附近的軍艦組合而構成一種軍事情勢,從而排除了對菲方有關仁愛礁若干訴求的管轄權(盡管該軍艦并未直接參與行動)。〔40〕針對菲方訴求14(a)至(c),仲裁庭主張,盡管中國阻止菲方軍艦補給和輪換的船舶為非軍事船舶,但中國軍艦在附近游弋,這使中國軍事和準軍事力量組合與菲方軍事力量形成一種軍事情勢,因而中國在仁愛礁及其附近的行動構成軍事活動例外。同時仲裁庭認為沒有必要探討軍事活動的具體外延。See https://pcacases.com/web/sendAttach/2086, last visit on December 1, 2019.此外,仲裁庭在論證涉案行動是否具有軍事性質時,還多次援引了中國高層領導人或新聞發言人對有關行動目的的發言及立場,這也充分說明仲裁庭有關“軍事活動”解釋的司法實踐存在前后不一的問題。由于《公約》本身并未能明確界定軍事活動的外延,仲裁庭對其的解釋又具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這都為司法能動主義提供了可能性。只是這種司法能動主義能否成為現實并發揮積極作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具體案件中的大國政治及其軟實力,因為爭端雙方的條約解釋能力和外交軟實力都會影響到國際司法機構的自由裁量。
基于世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法律文化對法律價值的塑造作用,國際法官或仲裁員的法律意識在客觀上易受到各自所屬法律文化的支配。除了應具備的必要才能外,法官全體應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系。〔41〕參見《國際常設法院規約》第9 條、《國際法院規約》第9 條、《國際海洋法法庭規約》第2 條、《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第36 條。以聯合國國際法院為例,具有不同法律文化背景的法官對特定法律問題的意見可能不同,并通過反對意見或補充意見的形式在裁決中體現出來。法官的構成等程序規范是司法公正與實體正義得以實現的基本前提,而法官的自由裁量,抑或說適度的司法能動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世界法律文化融合于國際法實踐之中,尤其是國際爭端的司法解決。但是,全球范圍內若不能體現法律文化的代表性,特別是爭端當事國的法律文化,則域外大國便可能會借機推動司法能動主義的實踐,而過度的司法能動主義無疑將會削弱國際法的實效,進而抑制國際法治的區域性發展。
按照“行動中的法”的觀點,〔42〕法理學家羅斯科·龐德提出了“書本上的法”與“行動中的法”的概念,主張法律的生命在于法律的實施,強調法的社會實效。書本上的法,是指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具有強制力的行為規范;行動中的法,是指法律規范在現實社會中的運作,特別體現在法官的司法審判活動中。正如霍姆斯所言:“法律是對法院事實上將做什么的預測。”See Roscoe Pound, Law in Books and Law in Actions, reprinted from the American Law Review, Vol.44, 1910;Roscoe Pound, The Scope and Purposes of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 Harvard Law Review, Vol.25, 1912.國際爭端的司法解決構成了國際法運行的重要環節。同時,司法判例對國際法本體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的法律作用。《國際法院規約》第38 條構成國際法淵源的權威界定,司法判例在確定國際法規則時發揮了輔助性功能。詳言之,司法判例不僅可視為對國家實踐一致性和連續性的權威確認,而且也有可能構成這種實踐的法律確信,進而證明相關國際習慣的存在。相較于國內法院的司法判例,國際司法判例往往具有更強的證明力和影響力。此外,盡管國際司法機構并不是當然的條約解釋機關,但條約自身設立的爭端解決機構一般構成合法的解釋主體,因為司法裁決及其法律論證本身可被視為條約解釋上的司法實踐。除了有助于國際習慣的證成和國際條約的解釋外,司法判例還能進一步發展和補充國際法的淵源體系。〔43〕See Andre da Rocha Ferreira, Formation and Evidence of Custom International Law, UFRGS Model United Nations Journal, Vol.1, 2013.因此,有關海上軍事活動管轄的司法實踐,不僅事關爭端方的海洋權益,其不確定性在特定情勢下也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當域外大國推動司法能動主義時,其裁判有可能激化爭端,而過度司法能動主義與大國政治的交互影響會造成無法預料的后果。但在另一方面,以軟實力為基礎,司法判例的研究與借鑒也為各國參與國際規則的建構和海洋權益的維護提供了一定的啟示意義。
(二)海上軍事活動司法裁決的經驗借鑒與中國海洋維權
在國際海洋爭端解決實踐中,海上軍事活動與執法活動的界分困境導致了相關司法裁決的不確定性,這給沿海國海洋維權執法活動帶來了嚴峻挑戰。于此情形,我國新近的海洋執法體制改革所引起的執法主體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會導致國際海洋維權困境。基于此,借鑒海上軍事活動相關司法裁決經驗,將有利于我國制定海洋維權的外交路線圖。
領土是國家行使執法權與司法權的空間范圍。在一國領土范圍內,正常的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一般被排除在國際司法機構的管轄之外,盡管兩者的區別對外不會產生重要的法律后果,然而,在一些非領土性質的各種海域,特別是爭端海域,海上軍事活動與執法活動的界定對于管轄權的確立和實質判決具有不同的法律意涵。如前所述,《公約》第298 條第1 款并未明確軍事活動的概念和其與執法活動的區別,這在適用依據上便會導致國際司法實踐的不確定性,特別是軍事活動的外延變化。
就海上軍事活動的語義而言,具有軍事性質是其被認定為軍事活動的決定性要素。它因涉及對外使用武力而威脅沿海國的安全,但單以行為主體、行為方式及行為目的等不同標準來判斷其軍事性質,則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專門機關依法定職權和程序實施法律的行為是執法活動的基本內涵。例如,在“極地曙光號”仲裁案中,國際海洋法法庭首次論及執法活動的解釋和適用的限定前提,即《公約》第297條第2款及3款。〔44〕See PCA Case N 2014-02, The Arctic Sunrise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v. Russia), Award on Jurisdiction, https://pcacases.com/web/sendAttach/1325, last visit on December 1, 2019.盡管《公約》例外的執法活動限定于科學研究和與漁業相關的執法活動,但軍事活動與執法活動在概念的界定上并非完全排斥,尤其是在其行為涉及使用武力時。基于海洋爭端本身的復雜性及地緣政治或域外大國因素的影響,在沿海國對非領土水域管轄權不明確的情況下,軍事活動主體和執法行為主體的協同維權,就會使得海上軍事活動與執法活動的界限變得更加模糊。從“扣押案”的裁決看,對兩者的區分需要結合特定爭端的具體情況,綜合考量行動主體、行為本身的特征及行為目的等因素才能作出最終決定。
我國海洋執法體制的改革,特別是海洋執法機構的整合,在主體層面對認定海洋維權行動的執法或軍事屬性造成了影響,“扣押案”和“南海仲裁案”等國際司法實踐無疑可為我國海洋維權行動提供一定的鏡鑒與啟示。2013 年國家海洋局重組,將原中國海監、公安部邊防海警、農業部漁業漁政管理局、海關總署海上緝私警察的隊伍予以整合,由國土資源部管理,并以中國海警局的名義開展海上維權執法活動,接受公安部業務指導,說明整合后的國家海洋局并未被直接授予法定的警察權,其海上維權執法應屬委托執法,國家海洋局在性質上仍為海洋行政主管部門。2018 年7 月1 日,國家海洋局領導管理的海警隊伍正式轉隸武警部隊,并成立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海警總隊,稱中國海警局,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盡管這并未改變海警職能的屬性,但轉隸至武警部隊則意味著中國海警局具有了“準軍事”性質,其執法權限可能由行政擴展到軍事領域。
海洋執法機構的整合及其職能改革增強了我國海上維權執法的能力,但也應看到,當相關海洋爭端進入司法程序后,尤其是涉及武力使用時,新的執法主體所造成的法律影響便呈現出兩面性。“扣押案”的法庭認為,不應僅據參與行動的是軍艦還是執法船只來界定行動的性質;“南海仲裁案”的裁決結果顯示,出現于現場而未行動的軍艦和實際參與行動的準軍事力量,都可因主體依據而被認定為軍事情勢的存在。在我國海洋執法體制改革后,海警局經常推行綜合執法模式,部分海警船采用軍艦船型建造,或者由海軍退役軍艦改造而成,這便表明對中國海警局海上維權行動的性質界定不應該只限于其使用的艦船性質,而應更多地依據具體情形下的行動目的與行為特征加以界定,也就是說,需要以是否使用武力及其方式和程度進行權衡及考量。
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是我國參與全球海洋秩序構建的基本前提。基于國際法的開放性,國際法的形成、運行及其實效深受大國政治的影響,兩者間的良性互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際法治的發展。不妨以此為基礎、以國際軟實力為路徑,在戰略層面運用大國政治,在戰術層面積極參與國際法規則的創制,實現戰略與戰術的互動。可以說,政治與法律的結合,將有利于我國制定有效的海洋維權路線圖。具體而言,在海洋執法體制的改革中,應先明確海上執法主體及其主要權責。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關于中國海警局行使海上維權執法職權的決定》,〔45〕中國海警局履行海上維權的執法職責包括執行打擊海上違法犯罪活動、維護海上治安和安全保衛、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海洋漁業管理、海上緝私等方面的執法任務,以及協調指導地方海上執法工作。參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國海警局行使海上維權執法職權的決定》,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8 年6 月23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6/23/content_5300665.htm。盡管中國海警局屬于海上武裝力量,但其性質不屬于軍隊。海警局行使法律規定的公安機關與相關行政機關的執法職權,這再次強調了其執法權能。就海上維權行動而言,由于相關規則本身及其司法裁決的不確定性,行動性質的界定依賴于法院或仲裁庭針對爭端的相關事實和具體情勢的認定與考量,而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司法能動主義及爭端當事國外交軟實力的影響。換言之,一國可通過外交軟實力和國際機制的控制能力影響國際爭端的司法解決,甚至通過議題設置的話語權及國際組織的主導能力推動國際法規則的形成。因此,通過外交軟實力與國際軟法推動國際法淵源體系的發展,將有助于提高我國的海洋維權能力,同時也將促進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
四、結語
國際法的碎片化與開放性及其關聯性對國際爭端司法解決產生了重要影響。“扣押案”說明海上軍事活動管轄問題的本質是不同國際法規范之間的內在沖突。《公約》有關軍事活動管轄的排除條款揭示出國際法對國家“高政治”事項的開放性,而世界文化的多元導致了法律文化多元與法律價值沖突,這決定了國際法本體的碎片化與國際法適用的司法抑制主義。
同時,國際法也向大國政治開放。在一般國際法與國際海洋法的價值沖突中,通過《公約》的法律空隙,大國的外交軟實力與軟法的創設能力都會促成司法能動主義在國際爭端解決中的實踐。以新自由主義和霸權政治為動機,西方大國推動的司法能動主義是其干涉主義和例外主義的體現。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我國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導下,促進各國民族文化的融合,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增強國際法的體系性。同時,在國際海洋法領域,通過海洋命運共同體的共建來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有效地維護國家的海洋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