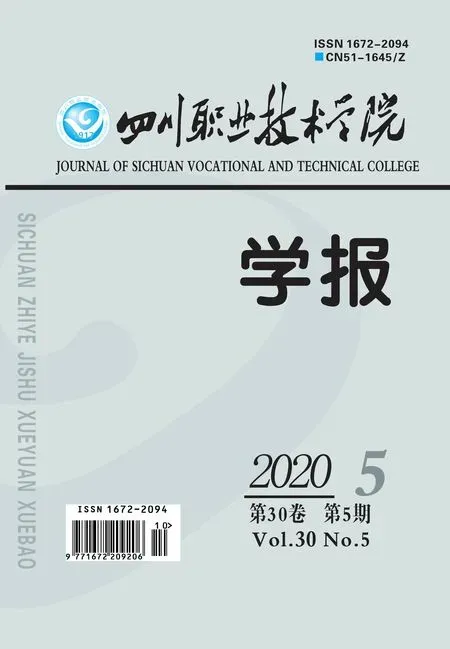牛首山故事中的江南書寫與權(quán)力話語
韓明亮
(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南京 210097)
牛首山作為金陵佛教名山被歷代文人題詠。經(jīng)統(tǒng)計,《牛首山詩詞》一書有495 篇詩詞,筆者利用當下的數(shù)據(jù)庫資源又輯出171 首詩詞作品。細讀這些詩詞作品,我們會發(fā)現(xiàn)牛首山與文人心中的江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
牛首山在金陵的西南。今天的地理測繪圖顯示,牛首山海拔400 多米,長江位于牛首山的西邊,海拔20 多米,站在牛首山頂,向西俯視,長江如一條玉帶蜿蜒而過。這一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讓牛首山成為歷代文人喜愛登臨的景點。
在這些詩文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江”有兩種含義。第一是作為眼前的長江。如宋代詩人吳龍翰的《牛首山觀揚子江》所言:“固知長江當城壁,立此界限分南北。東南王氣無窮年,此江未必成桑田。”[1]13宋代蘇頌也說:“亂山次阡陌,長江繞提封。蕭條舊井邑,茂盛新杉松。攬物思浩然,懷古心颙颙。念昔全盛時,茲山眾之宗。天都對雙闕,霸業(yè)基盤龍。六朝遞興廢,百祀居要沖。人情屢改易,世事紛交攻。當時佳麗地,一旦空遺蹤。惟有出岫云,古今無變?nèi)荨!盵1]11其他的詩詞還有:
江分楚水淮流遠,地擁鐘山王氣騰[1]63。
牛首之山緲何在?大江東畔王畿內(nèi)[1]31。
千峰忽避江流出,雙闕遙分曙色開[1]66。
山束江流縈作帶,樹迷僧寺爛成霞[1]72。
共尋虎穴攀蘿蹬,天末長江一線明[1]97。
云中孤塔亭亭立,天際長江滾滾來[1]27。
“江”的第二種含義是江左或江東。蘇頌在《暮春與諸同僚登鐘山望牛首》中說:“清明天氣和,江南春色濃。”[1]10明代楊守阯在《牛山宴別分韻得嶺字》中也說:“龍蟠虎踞江東境,牛首昂然兩峰并。”[1]26如果說第一種含義是因為長江與牛首山的特殊地理位置,那么第二種含義便決定著牛首山參與到了文人心中江南江北分界線的構(gòu)建。筆者將通過追溯牛首山在幾個特殊歷史時期參與到的歷史事件,以及歷代文人對此的題詠,來關(guān)照牛首山與江南心理范圍的關(guān)系。
一、天闕之名的爭議
當政局變動的時候,倉皇逃奔的統(tǒng)治者依然在文化宣傳上不能失去話語權(quán),至少要通過對于新事物的解釋來給新政權(quán)的落地以合理的依據(jù)。牛首山的別名——天闕山就作為一種別樣的宣傳,被刻在歷史的榮辱柱上。《文選》收錄陸倕的一篇宏文《石闕銘》,其中有:“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jīng)舊典,寂寥無記,鴻規(guī)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于牛頭,托遠圖于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2]2420這里的“假天闕于牛頭”講述了晉氏南遷中的一段歷史。山謙之《丹陽記》曰:
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彧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后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峰,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2]2420。
這個故事大意是說,晉室南遷之后,皇帝和大臣紛紛建議應(yīng)該把漢代許彧墓前的雙闕搬到皇家,以樹立威儀,王導不愿意,正巧看到建康西南方的牛頭山(即牛首山),因為它雙峰似闕,便對皇帝說,牛頭山就是天賜的石闕,又何必再勞民傷財建立石闕呢?就這樣,王導成功阻止了晉室建造石闕。
《南史·何胤傳》記載了這樣的版本:
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3]50。
這里兩個版本的不同主要在于和王導辯論的對象。前文說是議者,后文說是晉室,不過從《丹陽記》的故事末尾記載“帝從之”,可見,建立石闕也是皇帝的訴求。
在《丹陽記》中,議者和王導雖然觀點不同,但是他們都忽略了一個本質(zhì)問題。議者認為石闕“高壯”,足以顯示威風,而王導反對的意見是認為建立石闕動用民力物力,是勞民傷財之事。這雖然反映了王導管理政局的厚生和簡政思想,但也暴露出王導忽視了石闕作為禮制的象征意義。這一點,主張建立石闕的議者也沒有關(guān)注到。這也更加佐證了陸倕所說的“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jīng)舊典,寂寥無記”的狀態(tài)。
下面我們來具體論述石闕在禮制上的象征意義。
《文選》的《石闕銘》記載:“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shè)舊章之教,《經(jīng)禮》垂布憲之文,《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之制,銅雀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化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2]2419-2420這里追溯了象闕的歷史,也全面闡明了象闕的功用,即體現(xiàn)國家的禮制與威儀。
《南史·何胤傳》也記載了石闕對于頒布禮制法令的意義。其文曰:“闕者謂之象魏,懸法于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涂而高大貌也。”[3]50象魏是天子、諸侯宮門外的一對建筑,亦名“闕”或“觀”,是國家頒示教令的地方。《周禮·天官·太宰》記載:“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玄注引鄭司農(nóng)曰:“象魏,闕也。”[1]13
可見,象闕是一種頒布禮制的建筑物,以天闕山為雙闕便讓闕失去了禮的功用,也便沒有了闕的意義。這里陸倕和何胤都以此來批評王導不識禮制。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那些主張建立石闕的“議者”無非是看到了闕的高壯,同樣也是不懂禮制的表現(xiàn)。
何胤作為隱居的名士向剛剛即位的梁武帝提出三條意見,其第三條是“樹雙闕[3]50”。后來梁武帝果然這樣做了。
劉璠《梁典》曰:“天監(jiān)七年正月戊戍,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筑,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wù)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鐫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2]2421
而陸倕的《石闕銘》就是為此而寫。考察這兩位評論者的處境和主張,我們更能夠明白何陸二人為何反對王導的厚生簡政的舉措。
王導把牛首山稱作天闕,這一故事的解讀遠遠不是禮制那么簡單。當晉室倉皇南渡,來到建康,它面對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給百姓解釋南渡,如何確立自身的穩(wěn)定性和權(quán)威性。在《世說新語》中也的確記載了元帝面對的尷尬處境,其文曰:“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qū)υ唬骸悸勍跽咭蕴煜聻榧遥且怨ⅰ①駸o定處,九鼎遷洛邑,愿陛下勿以遷都為念。’”[4]
同時,晉室還要在事務(wù)上盡可能不讓原住民有太大的干擾,當然,這一點幾乎無法做到。但王導命名天闕山無疑有著這方面的考量。同時,天闕給晉室一個絕好的理由,即天命所歸。晉室的國都定在建康,這本是迫不得已的倉皇之舉,但是王導指出牛首山就是晉室的象闕,而且是天造地設(shè)的象闕,可見晉室定都建康乃是天命所歸,順天之舉。王導的這一命名無形中把牛首山拉入到了政治體系之中。同時,牛首山也成為人民心頭江南江北的分界線。奇妙的是,牛首山位于建康都城的西南方,它本身是絕不可能作為一種分界線來看待的。但是,當牛首山被解讀為天闕的時候,牛首山便不再是一座山,而成為了一種象征,象征著帝都,象征著國家的權(quán)力和威儀。這種強大的象征意義又因為天闕之名而變得不可撼動,因為這種象征不是憑空構(gòu)建,而是天造地設(shè)。
二、千秋功罪的天闕山
但是,歷史終究洞穿了這一構(gòu)建的天闕謊言。王導的命名固然起到了穩(wěn)定人心和建立國家向心力的功效,但這只是一時的效果。僅僅到了齊代,何胤就指出了這一構(gòu)建無法掩蓋的缺點,即喪失了禮制的意義。只是齊統(tǒng)治者沒有采用何胤的觀點,直到梁武帝才在何胤的建議下大力建造了宏偉無比的石闕。
然而,天闕之名卻并沒有因為東晉的滅亡而風流云散。“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5]對于這件事,歷史上的題詠出現(xiàn)了三種態(tài)度:一是貶低王導之舉而達到暗諷時政的目的,二是贊揚王導的努力和不易,三是對于此舉的理解之同情。
南唐的朱存在《天闕山》中寫道:“牛頭天際碧凝嵐,王導無稽亦妄談。若指遠山為上闕,長安應(yīng)合指終南。”[1]5《十國春秋》記載:“朱存,金陵人。保大時,常取吳大帝及六朝興亡成敗之跡作覽古詩二百章,章四句。地志家多援以為證。”[6]從這二百章的覽古詩中,我們可以推測身處南唐的朱存有著怎樣的興亡感受。而對于王導的批評亦可理解為對于一個長安盛世的呼喚。
南宋馬之純在《天闕山》中說:“不知象魏欲何邊,布政頒條總在茲。凡有往來須仰視,庶幾眾庶可周知。后來江左當新造,好向城隅踵舊規(guī)。卻指牛頭作天闕,此言多少被人嗤。”[1]12馬之純在這里把天闕的禮制意義解釋得非常清楚,在這種視角之下,王導的“卻指牛頭作天闕”的舉措難免被人嗤笑。馬之純著有《周禮隨解》,以禮制視角來看待歷史也是不足為奇的了。懷有此種視角的還有民國張通之。他的《牛首白云》說:“王導曾名為天闕,天闕牛首那能同。豈因兩峰若牛首,將欲執(zhí)此以稱難。”[1]184
這種禮制視角和何胤、陸倕的觀點是一致的。這種視角我們應(yīng)該如何看待?在禮制派看來,王導的做法是“有欺耳目,無補憲章[2]2420”。他們所期待的是一個禮樂興隆的盛世,在否定王導做法的同時,也是在表達對當時執(zhí)政者的勸諫。孔子就說:“必也正名乎[7]143”。他認為執(zhí)政者最大的權(quán)力是名,國家能夠賦予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7]143”。名是不能夠亂用和濫用的。因為如果名不正,執(zhí)政者的合法性就會受到質(zhì)疑,那么無論什么事情都不會做成。所以孔子嘆息“爾愛其羊,我愛其禮[7]66”。修建石闕的人力物力就是“羊”,“闕”的象征意義就是禮,依照孔子的想法,即使損耗民力也要建立禮的權(quán)威性和合法性。這也是后世無數(shù)文人的立場。這種立場的背后含義是期待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一個禮樂興隆、政通人和的社會。這種呼聲往往在南唐、南宋、民國這種動亂的年代里被一次次喚起。
第二種觀點是贊揚王導的努力。不當家不知柴米貴。能夠感同身受地理解王導之不易的是乾隆皇帝。他的《題文伯仁金陵十八景·牛首山》記載:
石闕誠如天闕披,但司馬未足當之。峣峰對峙青云表,詄蕩銘辭緬陸倕。(其一)[1]146
欲因立闕指牛頭,卓識由來自不侔。桓彝渡江期管仲,斯人豈祇尚風流。(其二)[1]146
第一首詩歌首先交代牛首的確有天闕之形,不過晉室配不上天闕,潛臺詞就是“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后面兩句是否定了陸倕的《石闕銘》,認為其“詄蕩”,縱觀歷史,縱使梁代建立了宏偉絕倫的石闕,不還是走了東晉的老路,難免衰亡的敗局。明白這一點,陸倕的禮制觀念和《石闕銘》中的皇皇之論都變成了一時風光,轉(zhuǎn)瞬即逝。而動用民力也變成了勞民傷財,禮制不在于建立一個建筑物,而應(yīng)深扎于統(tǒng)治者的內(nèi)心。
這首《牛首山·其二》很耐人尋味。前兩句直接評價王導命名天闕的舉措是“卓識”。這種“卓識”當理解為利用天闕加以穩(wěn)定民心和增強國家的向心力,具體如上文所述。千載之下,惟有乾隆看出了王導的苦心。后兩句“期管仲”指的是《世說新語·言語》中的典故: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jié),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歡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fù)何憂!”[4]94
當時,朝野沉浸在離別故土的悲痛之中,惟有王導奮然向上,維持大局。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fù)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4]88
乾隆對于王導的評價和其委曲的挖掘正是其自身深切地明白治國之不易。這種評價的確比一心期待禮樂昌盛的文人所作的評價顯得更加真切和深刻。
第三種是冷靜地站在歷史的帷幕背后,明白各家委曲卻也只是“讀書人,一聲長嘆!”[8]
最顯著的要算清代的屈大均,他的《秣陵》上說:“牛首開天闕,龍崗抱帝宮。六朝春草里,萬井落花中。訪舊鳥衣少,聽歌玉樹空。如何亡國恨,盡在大江東!”[1]152-153作者面對六朝的興替感到恍惚,質(zhì)問這冥冥中的造物:為何讓金陵承擔這么多的傷痛和無奈?這種質(zhì)問,也顯示出作者懷古生發(fā)的一種無力感。
最是眼光獨到要數(shù)孫星衍。其《牛首山》曰:“巋然天闕作南門,渡馬人知帝子尊。似此家居撞亦壞,千秋名讓謝公墩。”[1]174孫星衍要算文人中唯一一個看到了王導命名天闕的苦心,即渡馬人知帝子尊。說到底,是為了確立皇權(quán)的正當性和合法性,那么,最強有力的理由就是天命所歸,而天闕就是天命的彰顯。但是孫星衍不止于此。他不僅能洞穿歷史橫切面的種種委曲,他還能縱觀整個歷史,發(fā)出高妙的感概:似此家居撞亦壞,千秋名讓謝公墩。天闕山也無非是一個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擺設(shè)。面對六朝種種的興衰,命名天闕山也不過是一家一姓的一個瞬間。天闕山對于當時的東晉政權(quán)有著近乎封禪的意義,然而,孫星衍認為,千載之下,天闕山比不過謝公墩的高名。這里的典故同樣出自《世說新語·言語》: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費務(wù),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4]126
謝公墩象征著一種高士精神,“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沉浸清言,忘懷得失。從治理國家來看,王導的舉措自然是有其衷心,而從一個千載之下看慣興衰的文人孫星衍來看,王導這一番苦心也是徒然,六朝已經(jīng)遠去,而唯有《世說新語》里保存下來的“高世之志”,讓我們悠然遠想,神往不已。
三、南宋政局下的牛首山記憶
宋室南渡前后也有兩段記憶發(fā)生在牛首山。一是岳飛大戰(zhàn)金兀術(shù),一是眼香娘娘治療目疾。這兩段故事承載了我們民族一段非官方的話語,也可以說是民間記憶保存下的真實歷史。
《宋史》記載:“兀術(shù)趨建康,飛設(shè)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術(shù)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術(shù)奔淮西,遂復(fù)建康。飛奏:‘建康為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9]岳飛在牛首山打敗金兀術(shù)的事跡被歷代傳頌。在《故宮博物館藏清宮南府升平署戲本》里有一出戲,講的就是岳飛大戰(zhàn)金兀術(shù)的故事,名字就叫《牛頭山》[10]。民國程晉燾在《金陵雜詠》里說:“庸臣誤國實堪嗟,南渡偏安一念差。牛首山前留戰(zhàn)跡,至今爭說岳爺爺。”[1]201岳飛在牛首山大敗金兀術(shù),收復(fù)建康的壯舉被載入史冊,同時,也被后世文人爭相書寫。這一方面是對這種愛國壯舉的贊揚,另一方面也是對庸臣誤國、君主偏安以至國家衰落的悲嘆。
眼香娘娘的故事同樣被牛首山銘記著。清代周寶偀的《牛首山眼香祠》記載:
在牛首山旁。宋高宗南渡,有妃留建業(yè),善治目疾,歿而祠之,甚有靈異,俗稱為眼香娘娘。
靈旗風卷暮潮低,宛宛瑤篸映翠笄。此日巫歌陳玉單,當年俗障掃金鎞。要知五馬應(yīng)隨渡,卻怪孤鸞只別棲。回首故宮秋草遍,巋然碧瓦照清溪[1]181。
這首詩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是眼香娘娘的身份。當宋室倉皇南渡,眼香娘娘卻不知為何留在了建業(yè),正如詩中所說,“卻怪孤鸞只別棲”,至今讀來,依然感到奇怪。不過,重要的不在于此,而是眼香娘娘留在牛首山為百姓治療眼疾,造福一方。這種行為和宋室南渡,偏安一隅的行徑比起來要高尚的多。歷史的對比多么具有諷刺意義。一個是皇皇朝野,一個是亂世妃子,一個依然在正史里耀武揚威,一個卻在百姓心頭,在牛首山頭被膜拜、被歌詠。哪一個才是我們應(yīng)該去景仰、去銘記的歷史呢?抑或者,面對正史和牛首山上的歌詠,我們應(yīng)該銘記怎樣的歷史?
再有一點就是周寶偀的歷史觀。詩中說“要知五馬應(yīng)隨渡”,可見作者在寫宋室南渡的同時,也聯(lián)想到了晉室南渡,不過這一次是更南一些。這里讓我們想到了杜牧《阿房宮賦》中的那句名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fù)哀后人也。”[11]作者顯然也是為了凸顯這種懷古的傷情,所以最后感嘆:“回首故宮秋草遍,巋然碧瓦照清溪。”[1]181當一切的繁華因為國家的衰弱而煙消云散之后,唯有眼香祠的碧瓦倒影在清溪之中,在歲月的長河里,牛首山保存下這樣一份默默奉獻、造福一方的民族精神。它永遠在訴說著亂世里依然有人在堅守,有人在奉獻。
周寶偀的另一首《眼香廟》表達了另一種情感。其詩曰:
在牛首山旁,宋高宗南渡,有妃留建業(yè),善治目疾。歿,立廟祀之,呼為“眼香娘娘”。琉璃窯亦有小廟。
上池神水療昏盲,怎不官家試此方。當日若教明四目,早應(yīng)奸佞識咸陽[1]182。
這首詩和上文歌詠岳飛的詩歌情感相似。都是在為因奸佞而衰落的國家感到悲憤,也是在毫不保留地批評朝廷。直言朝廷昏蔽,不辨忠奸。可見,對于同樣一份記憶,在題詠之中又有著不同的情感。這種情感和記憶是我們民族最珍貴的遺產(chǎn),它不應(yīng)該被冷落乃至遺忘。
四、牛首山與江南的變與不變
上文我講述并評論了兩個歷史時期發(fā)生的三件事。這一部分,我將統(tǒng)攝這三個事件以研究牛首山與江南的關(guān)系。為了表述完備,我將從心態(tài)史和權(quán)力話語這兩個角度展開。
(一)歷史事件與心態(tài)史
種種的內(nèi)部與外部的因素導致一個歷史事件的發(fā)生。這就像牛首山被王導稱作天闕山一樣,從外部來說,如果王導沒有這種厚生和簡政思想,沒有聯(lián)系到東晉皇權(quán)的確立,抑或者,皇帝堅持建立象闕,這種種的外部原因都會導致歷史上沒有天闕山;從內(nèi)部來說,如果牛首山不在建康,抑或牛首山在外形上不似石闕,都會導致牛首山無法擁有天闕之名。同樣,岳飛大戰(zhàn)金兀術(shù)的愛國故事也與岳飛從小被父親的教育①與其卓越的軍事才能還有宋金兩國的戰(zhàn)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眼香娘娘的故事所受到的影響因素就更多了。歷史事件的發(fā)生有著內(nèi)部和外部的因素,而歷史事件被一次次的回憶也同樣有著現(xiàn)實考量和懷古心緒的雙重原因。
如果歷史事件不被歷代回憶,那么其生命從其誕生便已然夭折。也就是說,歷史事件的意義存在于被不斷的追憶當中。一千五百年前的一件事可能有著一千五百年的記憶史,而且這種記憶是累積的,多變的。從王導命名天闕山這一事件的后世褒貶之中,我們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也就是說,每一個歷史事件都擁有屬于它的一部心態(tài)史,牛首山就是這樣。牛首山上的遺跡和建筑本身就是歷史事件的見證者,牛首山的歷代文學題詠就凝結(jié)著對這些歷史事件的文人心態(tài)。
這個心態(tài)是什么呢?歸納起來,我們可以看到是一種官方意識與民間意識的交織心態(tài)史,甚至可以說是一部話語的斗爭史。這一問題我將在權(quán)力話語這一節(jié)展開。我在這里要從內(nèi)容分析牛首山的這三件歷史事件所凝結(jié)的江南內(nèi)涵。
首先,我們先要明白江南的內(nèi)涵流變。
有學者指出:“魏晉南朝時代,‘江南’表征著以建康所在的吳越地區(qū)為主的長江中下游地區(qū)……宋代由于江南東路、江南西路的行政區(qū)域劃分,所以‘江南’仍指代著具體的行政區(qū)域。但就狹義而言,仍然指代著吳越之地。”[12]王導命名天闕山建立了一個江南江北的心理分界線。在盛世,江南被視作是一個最終回歸的故鄉(xiāng)。它是和朝堂相對的心靈歸宿。在亂世中,江南往往是統(tǒng)治者的現(xiàn)實歸宿,無論是晉室南遷還是宋室南渡,都證實了這一點。統(tǒng)治者不能向單個文人一般,在江南煙雨里做一個寒江獨釣者,他們在這種倉皇遷都中還要建構(gòu)一個新的話語,來給天下一個交代。王導不得不以天闕來取信于民,從而給南遷的晉室構(gòu)建一個統(tǒng)治合法性。同時,這個舉措的成功也標志著牛首山成為了江南江北的心理分界線,也是兩個國家的心理分界線。如上文所說,江南在魏晉南朝時代包含建康,牛首山在地理上形成了對建康的拱衛(wèi),在民眾心理上,因為有了天闕山的解讀而成為了江南江北的分水嶺。
如果說前一個事件是官方的構(gòu)建,那么后兩個事件就是民間的記憶。岳飛大戰(zhàn)金兀術(shù)的愛國故事被歷代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傳唱,牛首山發(fā)生過漢政權(quán)和金政權(quán)的斗爭,作為同屬于漢民族的歷代文人,書寫這一件事就意味著加深這種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這種記憶也讓牛首山在那個戰(zhàn)爭年代成為了兩個國家對峙的戰(zhàn)場,也可以說,在那一刻,牛首山是兩個國家的分界線。同時,在整個歷史之中,因為有了這一事件和后世不斷的追憶,牛首山擁有了一種永不磨滅的愛國精神。
宋代時,狹義的江南指代吳越地區(qū)。我們不談這種文化區(qū)分形成的原因,只談在這種區(qū)分之下,眼香娘娘留守建業(yè)意味著什么。這個時候建業(yè)已經(jīng)不屬于江南了,而朝廷已經(jīng)偏安江南。那么,眼香娘娘就不僅與宋室有著地理上的隔膜,更有著身份認同上的隔膜。后者的隔膜更是天壤之別。同時,這種對比也在另一個角度展開。在那個動亂年代,作為一個流落人間的留守女子為建業(yè)百姓治療眼疾,于此同時,皇皇宋室偏安江南,歌舞升平,只把杭州作汴州,全然不顧還在期待著和平統(tǒng)一的中原百姓。民眾給眼香娘娘建造祠堂,后世文人對她贊不絕口,這里一方面是對這樣一位默默奉獻的女子的紀念,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對于宋室的批評和諷刺。眼香娘娘為牛首山注入一種個人的奉獻精神,同時也構(gòu)建了一種奇妙的關(guān)系,即官方與邊緣,偏安與奉獻,江南與金陵,朝堂與江湖,滿朝文武與柔弱妃子。這種民間記憶把宋室永遠地放逐于眼香娘娘塑像的陰影下,這也是別樣的真實歷史,永遠不會被寫入正史的歷史。
(二)權(quán)力話語:官方與民間
《福柯說權(quán)力與話語》這本書中說:“傳統(tǒng)歷史觀著眼于遙遠、高貴的事物,將目光投向崇高的時代;而譜系學則要朝向身體,投向社會的底層,恢復(fù)歷史的本來面目,而不是統(tǒng)治者對其的粉飾和偽裝。”[13]這里福柯解釋了兩種歷史觀和話語體系。一種是傳統(tǒng)歷史觀,它構(gòu)建了官方的話語,一種是福柯的歷史觀,他關(guān)注底層話語。我們可以借鑒這一思路來考察這三個歷史事件。
王導命名天闕山指的是官方話語,他給民眾建構(gòu)了一個堂而皇之的天闕,從而給南遷的晉室賦予了先天的統(tǒng)治合法性。這一高明手段讓后世的乾隆皇帝贊不絕口。而陸倕、何胤的批評也是站在官方立場,何胤是給梁武帝建言獻策,陸倕是對梁武帝建立石闕大加阿諛。不過陸、何二人是站在官方立場批評同樣站在官方立場的王導。歷史成了“權(quán)力斗爭的空間”②。不同歷史時期,官方之間會形成話語的斗爭。同樣,對于岳飛的書寫也是如此。南宋當局的書寫和《宋史》的書寫以及歷代史書的回憶都會有著截然不同的立場。又如對于錢謙益等降清的明朝士大夫,官方話語在清朝剛建立和乾隆時期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也反映了這種話語的角逐[14]。
對于話語的構(gòu)建,不僅不同時期的官方之間會形成角逐,整個歷史當中的民間記憶也會形成一個強大的話語體系,和官方話語一較高下。眼香娘娘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證明。在眼香娘娘被宋室拋出權(quán)力體系之后,她以高明的醫(yī)術(shù)默默為一方百姓奉獻,最終被人們永遠地紀念,建造祠堂、寫詩題詠無不是在努力地形成一種官方話語之外的民間話語。這種民間話語豐富且強大,足以沖擊乃至顛覆官方話語。
上文我們說過,每一個歷史事件都有一部心態(tài)史。這部心態(tài)史存在于歷代的題詠和祠堂等遺跡之中。其實,這部心態(tài)史就是一個民間話語和官方話語的場域,不管是哪一方占優(yōu)勢,書寫本身就是在歷史長河當中把這一事件不斷地推出水面,回憶本身就在強化,就在抵抗遺忘,就在書寫歷史。當然,這種書寫本身也變成了歷史。正如陳寅恪為紀念王國維所寫的碑文,陳寅恪的書寫固然強化了王國維在文化史上的記憶,但是,換個角度思考,王國維的死對于陳寅恪主張的學者的“獨立精神”何嘗不是最好的宣傳場所?也就是說,書寫本身在成為歷史,它成了今人借助古人走進歷史的一種獨特方式。
歸納起來,對于歷史事件的書寫,權(quán)力與話語的運作機制是這樣的。一個歷史事件有一個官方的書寫,這是當時的官方話語。而縱觀整個歷史,對于這個事件有著一部心態(tài)史。這部心態(tài)史包含后世的官方話語和民間話語。這兩種勢力沖擊著最初的官方話語,在其內(nèi)部也進行著撕扯。這種撕扯和沖擊的原因是古為今用的書寫態(tài)度,有著對當下的現(xiàn)實考量。正是這種現(xiàn)實考量,讓歷史書寫變成了一種自我觀念的建構(gòu),從而大大減弱了話語的權(quán)威性,于是又會產(chǎn)生另一種建構(gòu)自我思想式的書寫,最終形成了這樣一部奇特的心態(tài)史。
注釋:
①《宋史》卷三百六十五記載:“(岳飛)少負氣節(jié),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shù),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shè)祭于其冢。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徇國死義乎。’”
②“權(quán)力斗爭的空間”在福柯的語境中指的是在譜系學倡導的“歷史感性”的關(guān)照下,歷史成了一種反記憶的歷史,不再是連續(xù)的,而是各種權(quán)力斗爭的空間。本文對此句屬于化用,說的是不同時期官方話語之間存在權(quán)力斗爭,并非福柯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