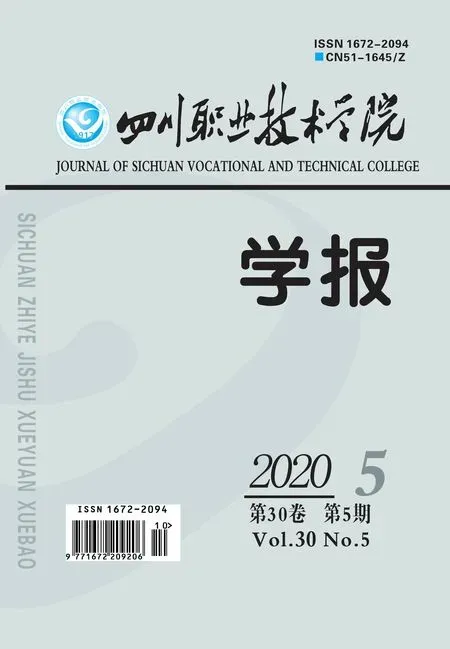論《云中記》中嗅覺書寫的敘事功能
魏夢茹
(安徽大學 文學院,合肥 230031)
繼2008 年完成故鄉回憶系列長篇小說《空山》的創作以后,《云中記》是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阿來醞釀十年精心打磨的又一部長篇作品。故事以2008 年汶川大地震為題材,主要講述了遭遇地震災難后一個祭師的消失和一個小村落的消亡。作品中阿來用文學話語寫出了對生命的敬畏,對人性的尊重,筆端觸及人們內心深處共有的災難記憶和時代創傷,呈現出廣闊的現實圖景。阿來懷著對自然的虔誠之心和對人類生命的崇高敬意,寫出了一部獻給地震中死難者的安魂曲,不僅撫慰了逝去的人的亡魂,也從不同程度上修復了地震存活下來的人們的心理缺口,給了生者直面那場巨大災難的勇氣。在作品中,讀者能明顯注意到文本中出現頻率極高的各種各樣的氣味描寫,嗅覺書寫是阿來結構小說的重要策略之一,他對氣味的描寫不單純停留在感官表面,而是將身體反應融入整個文本的敘事框架里。從嗅覺書寫的角度來看《云中記》,或許能發現這部作品不一樣的價值蘊涵。
一、嗅覺書寫在文本中的呈現
嗅覺相比于視覺、聽覺等感官功能而言,更有一種霸道的主宰意味。呼吸與生命同在,當我們不能拒絕呼吸時,氣味便從各種通道、入口甚至狹小的縫隙爭先恐后地進入我們的身體,透著一股強權的氣息,不論你接受與否,氣味都將留下印記,成為自身身體記憶的一部分。不僅如此,嗅覺的記憶能力也天賦異稟,曾經接觸過的氣味再次相遇時很大程度上將喚醒你的感官去搜尋以往的經驗并牽動腦部神經判定其產生的時間、地點,最終蔓延至節點式的個人經歷。當與一種熟悉的氣味相碰撞時,人們會回想到與其相關的種種事件,感受也不再單純停留在嗅覺層面,而進入氣味背后所隱喻的記憶符碼。嗅覺誘發心理活動、觸發回憶不可以刻意為之,它是一種直覺的特性與本能。
目前學界針對小說《云中記》中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故事的主旨內涵、深層思想意蘊,挖掘其背后閃爍的草木之心與人性光芒,并未涉及嗅覺書寫的探討,嗅覺書寫雖不是文本的重要內容,卻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意義。在《云中記》中,嗅覺本能主要通過各種不同氣味的顯現來反映,人的感官接觸到這些氣味的出場并表達出來。氣味在小說中的出場次數并不多,屈指可數,并且其中大部分氣味的識別都來自主人公阿巴,伴著返鄉路途的進發變換身邊的景象,周遭的氣味也隨著紛紜復雜。例如開篇第一天阿巴在山道上攀爬,“弓著腰向上的阿巴跟在兩匹馬后面,鼻梁高聳,寬大的鼻翼掀動,他聞到了牲口汗水腥膻的味道。”[1]2阿巴回到云中村曬樹皮與枯葉,“樹皮和枯葉在陽光下散發著濃烈的柏香”[1]7。云丹牽來的兩匹馬還在院子里便“散發著熱騰騰的腥膻氣息”[1]14。云中村人用動物油脂自制頭油,散發出來的氣味在村民們看來也是好聞的。馬的腥膻味、樹葉的柏香、動物油脂的芳香,阿巴和村民們感知到的氣味幾乎都來自動、植物,這是自然界與人類和諧共生的符號。在這和諧相處的另外一極,人類自我意識的強化和創造潛能的不斷挖掘,包括動、植物在內的客體世界都成為被征服的對象,他們渴望用武力征服自然并獲取駕馭自然的自信,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關系劍拔弩張。山上久違地出現了鹿群,阿巴本身沒有惡意,并強調其“身上也沒有火藥和鉛彈的味道”[1]143,因為這種氣味在過去是動物瀕臨危險、命懸一線的信號,這種氣味也不是渾然天成的,它是人類強大意志的反映。小說最后,當阿巴與云中村一同消失之時,“仁欽聞到了空氣中充滿了破裂翻滾的巖石互相碰撞而散發出的硝石味道。”[1]386山體崩塌、巖石翻滾的畫面撲面而來。
《云中記》的敘事文本中,嗅覺書寫所占篇幅并不多,但其存在卻貫穿小說始終,是不可忽視的一個文本寫作現象,氣味在故事的各個章節、片段悄然出現,游走在各式各樣的地點、人物之間,與小說的整體敘事緊密貼合。
二、嗅覺書寫的敘事功能
除了從一般常見的聽覺、視覺等角度對觀察對象進行描敘以外,阿來在這部小說中還采用了以嗅覺為重要方式的一種敘事策略。阿來為何花費筆墨、如此細致地描寫人類的嗅覺本能及其表現形式呢?采用這種敘事角度有什么樣的敘事功能?這都是我們在閱讀作品時會思考的問題,也是值得挖掘探討的關注點。
(一)以氣味作為行文線索,推動故事情節發展
阿來運用嗅覺作為小說敘事的一種角度和方式,除了讓讀者感受到人類嗅覺本能的獨特魅力之外,還有效地提高了敘事效果,使故事的行文結構更加連貫,形成一個有機整體。
這部小說主要講述的內容以主人公阿巴回鄉為起點,云中村的最終消失為終點,其間穿插著阿巴關于云中村地震前的一些片段性的回憶,讀者通過小說看到的不僅是一個祭師履行職責的故事,還包括一個傳統村落在地震后的消亡史。在阿來的筆下,云中村被描寫成一個氣味豐盈又具體可感的村莊,生活在其間的村民們能敏感地捕捉到這些氣味并為這些氣味的顯現感到自豪。在村民們的眼中,這些氣味是云中村獨有的,芳香的頭油從動物身上的油脂提取而成,是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生的表征,村民們用這些氣味的存在判定自身的身份——云中村人,離開云中村以后,這些氣味都逐漸消失了,村民們也失去了評判身份的依憑,成了無根的漂泊者,村民與云中村之間依靠嗅覺建立的情感紐帶出現長達三年的斷裂。祭師身份所賦予的使命——祭祀神靈和安撫鬼魂,這是祭師應盡的責任義務,也是主人公阿巴在云中村的職責所在。阿巴在移民村的家具廠工作了四年,做著本不屬于自己做的事,內心有著洶涌澎湃的回鄉想法。阿巴的回村之路若從嗅覺的角度來說就是一場尋“味”之旅,而這個味道為云中村所獨有,離開意味著失去,而回歸代表著對這種味道的尋找。肢體對環境的感知能力經常先于大腦的神經思維,當意識無法確定周遭的安全性時,身體反映往往預先提供答案。阿巴還在返回云中村的路上,嗅覺感知便提前到達了這次路途的終點站,用身體反應告知他就要回家了。阿巴回到云中村以后,他的周圍便充盈著各種氣味,這些氣味在阿巴心里都是云中村的味道。廢墟上的云中村并沒有死去,到處都是生命綻放的痕跡,各種紛紜復雜的氣味是云中村鮮活的生活圖景在嗅覺層面的表現,當這些氣味纏繞著他,他便從心里產生了身份認同。包括祭師阿巴在內的所有云中村人在三年前因為這場毀滅性的災難被迫離開了生活已久的故鄉云中村,這是故事發展的開端,移民村的生活缺少了曾經熟識的氣味,這雖然不是阿巴回鄉的主要原因,卻是啟程的導火線,最終他重返云中村并與云中村同眠,像是選擇了祭祀的方式將自己奉獻給云中村以及村里殘存的鬼魂,祭師是唯一也是最后的祭品。氣味是這些線索發展變化的重要節點,它將幾個主要情節貫穿起來,從起點到終點有機融合成一個整體。故事的整體情節脈絡如果從嗅覺的角度來進行勾勒,便是“遠離云中村的氣味——踏上尋找氣味的路途——到達目的地、回到氣味產生的原點”,那么從這種文本表層結構來看,嗅覺書寫便有著推動情節發展,連接上下,貫通全文的作用。
(二)誘發心理活動,塑造人物形象
人物的形象不僅可以通過人物本身的動作、行為、心理活動以及神態等描寫直接達到精細刻畫的目的,還可以通過環境、背景或者其他次要的表現因素來側面烘托、間接塑造人物。在《云中記》中,嗅覺似乎只是角色一種條件反射的行為,與嗅覺相關的書寫看似與主題內容的表達不存在什么必要的關聯,但實際上很多情境下的嗅覺書寫都引發了人物心理活動,自然而然地起到了塑造形象的作用。
小說開端主人公阿巴便說到自己遠離云中村的味道已經三年了,云中村的氣味殘存在村民們的感官記憶中,一旦再度回到同樣的環境,這種與氣味之間的熟稔之感便會自然而然地生發出來。啟程對阿巴來說是一次義無反顧的嘗試,態度十分堅決,抱著必死的心態,在安撫鬼魂的道路上與這些廢墟上的鬼魂一同去往大化之途。阿巴第一次見到云丹安排的兩匹馬時,靈敏的嗅覺讓他在一定距離以外便聞到了這種氣息,靈敏源于對這種氣味多年接觸所培養下來的熟識。在回鄉的路上阿巴與兩匹馬相依相伴,濃烈的牲口汗腥味包裹著他,這種闊別已久的氣味再次襲來,無意識中便迅捷地誘發了心理活動,觸發個人內心回憶:阿巴回想到地震前的日子里,他總是在這種氣味營造的環境中生活。災難來臨,這令人安心的味道也離人遠去,但這種氣味卻并不是虛無縹緲、來去無痕,在過去那么多年里阿巴與它互相觸碰,身體與氣味結合,嗅感經驗像烙印一般深深鐫刻在他的內心世界里,如同旁人無從理解的暗語。當周圍的生活背景一點點接近過去的面目,內心的回憶在眼前也逐漸清晰。氣味憑借似曾相識的嗅感經驗最先牽引他回到三年前的村莊,阿巴明白那個魂牽夢縈的地方就快要抵達,那些曾經有過的經歷也會再度發生。回到云中村不久,阿巴的嗅覺反應本能地表現出他對故鄉的貼近與親昵,熏香的氣味、祭師行頭的氣味、就連塵土也是云中村的氣味,本能的嗅覺力量實際上是阿巴內心想法的披露,這股遠離了三年之久的氣味終于再度回歸。嗅覺是世間萬物的本能特質,對人類而言,嗅覺本能包含著強烈的原始欲望與感官記憶,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直覺特性。阿巴選擇留在云中村,安撫鬼魂的同時也在陪伴著這個隨時被判處死刑的村落,或許理性思維警示過他這種行為的冒險和可能產生的代價,但嗅覺引起的身體反應又在潛意識中指引著他。嗅覺能夠體現人物的心理活動,阿巴的嗅覺本能實際上反映了他內心的欲望,以嗅覺為契機產生的記憶追溯便是在腦海中對目標味道的搜索。嗅覺在阿巴的潛意識中產生了引導作用,帶領他在自身真實欲望的指引下完成心靈的救贖與皈依。阿巴選擇與云中村、與云中村的鬼魂同眠,不單是為了安撫鬼魂,如果針對個人來說,這種自我犧牲的行為讓他完成了精神上的救贖,此處安心是吾鄉,在云中村,心靈也得以皈依,生命于此時產生了永恒的價值。阿來著眼于嗅覺這個層面,表現的不單單是人類的本能感官反映,還包含了這種感官反映下真實的內心想法與心理欲望,嗅覺不僅是一種敘事角度,同時也是主人公行為的線索軌跡與內里誘因,這些相關的嗅覺書寫不僅生動地將阿巴在各種情景下的心理活動展現出來,也起到了側面烘托人物形象、使其更加飽滿立體的效果。
(三)隱形的二元對立結構
嗅覺書寫在文本中具有強烈的隱喻性,傳統鄉土生活與現代文明的激烈沖突通過嗅覺反映在其隱形層面,同樣也采用這種方式暗喻了本地居民與云中村人之間的隔膜,于是在表層文本下便形成兩個方面的二元對立結構。
1.人際交往的隔膜
云中村是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村莊,村民們相信在一千多年前,他們的祖先帶領他們的前輩來到這里并在這里生根發芽。對村民們來說,云中村便是他們的家鄉,他們在這里世世代代生存下來,生活溫馨,精神幸福。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地震不僅奪走了許多村人的生命,也摧毀了他們的家園。鑒于地質危害的潛在因素,幸存下來的村民們不得不搬離云中村,離開雪山,在移民村重新生存。在新的環境中生活并非易事,他們與本土居民之間總會存在人際交往的縫隙,無法做到真正的親密無間。云中村的居民來到移民村和當地的人們之間也產生了隔膜,阿來從嗅覺的角度表達了這種間隙。村民們習慣并喜歡自己身上的氣味,同樣的氣味當地居民卻不喜歡,在他們看來這是“山上蠻子”的特有屬性,同一種氣味在不同人眼中出現了兩種完全相反的特性。由這股氣味產生的不同反應表明當地居民潛意識中并不把自己當老鄉,言語間的關愛掩蓋不了內在的隔膜。對村民們來說,他們的體味是在云中村時特有的,當他們離開云中村,這股氣味伴隨著時間、距離的拉長也逐漸消失了,身份特征的唯一確證不復存在,他們感覺自己不像是云中村人了。在內心他們都想要回到云中村,這個曾經的家園,村民們心中永恒不變的故鄉,但他們不得不考慮現實條件,只能在這種隔膜中生活下去,它不是狹窄的縫隙,實際上是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阿來在文中并未赤裸裸地將這種矛盾展露并剖析,而是從敘事者的層面將其通過冷靜客觀的陳述來處理,反映事實,表現村民們內心的本真想法。雖然作者采取的是冷處理的方式,但通過嗅覺敘事來刻畫這種間隙是十分尖銳并深刻的,嗅覺屬于人類器官的本能,好壞、優劣的評價背后隱含的情感態度是最真實、不經掩蓋加工的,本地居民無意識的感受更強烈地刺痛人心,這種對立來源于人際交往中的隔膜,也是一些現實的、傳統的心理習慣使然。
2.傳統與現代文明的對峙
如果說人際間的矛盾尚不尖銳甚至經過時間的洗刷能夠磨平其棱角,那么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的沖突則會在歷史的作用下得到凸顯并且是無法圓滿解決的。20 世紀后半葉萌生的信息革命帶領人類進入到全新的電子智能時代,機器解放了人們的雙手,催生了很多全新的產業和社會領域,同時,也有不少曾經輝煌的傳統逐漸破敗甚至消失。雖然阿來在小說中主要講述的時間點與地震以前和地震之后相關聯,但他通過阿巴的回憶讓讀者見證了云中村接受現代科技文明洗禮的整個啟蒙過程,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云中村通上電一直延伸至21 世紀的現在。一大波新概念、新事物向云中村涌來,這都是村民們的認知里從未有過的,這種沖突很明顯地體現在語言里,他們發現自己的語言好像沒有辦法描述出整個世界了。新東西的進入極大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但人們對這種技術文明并沒有全盤接受,技術可以帶來物質上的便利,卻不能撫慰精神上的空缺,他們沒有辦法像過去那樣一邊勞作一邊悠悠歌唱了。現代世界涌入傳統王國,首先就是要摧毀最古老的那一部分歷史與經驗[2]。封建迷信的祭祀行為被明令禁止,與牛、馬等動物之間的情感維系也消弭了,這些牲畜的作用因為機器的到來被代替,阿巴準備馬匹上山之前也發現云中村已經有很多年不將馬作為交通工具了。搬到移民村以后,人們的謀生方式也出現很大變化,許多村民變成了具有針對性工作的職業人員,傳統農業成了商業性質的觀光農業。阿來沒有從生產、生活方式上的改變表現這種沖突、將其直接挑明,但從嗅覺敘事的角度也暗指了傳統世界與現代文明的對峙。村民們用感官親身體驗兩種文明的差異,移民村沒有馬的腥膻味,也沒有柏樹葉的馨香,所代替的是工廠里厚重的油漆味,穿著一身工裝在家具廠工作的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也沒有云中村的味道了,取而代之的是科技符碼的現代氣息。
傳統與現代文明的對峙、移民村村民與云中村人的間隙是小說在人際交往和文化傳統兩個維度的二元對立結構,這種對立模式間接成為敘事的強大動力,正是這些異質因素的存在打破了生活本真的穩定狀態,使主人公靈魂與肉體分崩離析,不得不踏上尋求生存本質意義的征途。
(四)營造靜謐的敘事空間
與嗅覺敘事相比,小說創作中聽覺敘事運用的頻率往往更多,在很多作品中會用較多體量的對話、語言、聲音描寫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背景的介紹以及故事情節的展開,作家用聽覺敘事構建了一系列聲音景觀。文學作品中,聲音的先行出場不僅僅是定調子,還提供了時間、節令、主體所處位置、周邊環境以及人物的精神狀態、心情心境等相關信息[3]。在這類小說中聲音作為一種媒介,讀者通過對聲音的捕捉將其轉化為相對應的人、物意象,從而發現原始的文字編碼空間。例如阿來之前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就是一個典型的聲音文本,里面充斥了各種各樣的聲音信息,宏大熱鬧,錯落有致,讀者通過聽覺拓展對應的想象空間,整個場面可能是十分喧囂的。嗅覺與聽覺、視覺相比有自身不同的特征,嗅覺是一種遠距離的感覺,但雙方之間的內在感知是緊密的。傳統創作中對審美對象的觀照、主觀審美感受的傳達往往采用視覺描寫的方式直接表現,這種敘事手段的確能讓讀者展開廣闊豐富的想象空間,卻沒有完全深入客體的內里部分,停留在表層的描敘對讀者的想象產生了一定的阻斷。嗅覺相對于視覺、聽覺、觸覺、味覺而言,因缺少限制,因與呼吸同在,更能直達個體生命[4]。與單純的視覺、聽覺經驗相比,用嗅覺探索自然的行為更加親密,兩者間的氣味相互交織,雙方達到了一種零距離的接觸。嗅覺的表現形式是各種不同的氣味,氣味無形卻又十分立體,對嗅覺主體來說,氣味是一種強烈的氛圍充盈在周圍環境中,即便距離尚遠但是已經親密貼合,在還沒有目睹之前,嗅覺能夠提前預知,這種短暫的過渡可以讓讀者更好理解接觸對象的內在蘊涵,通過嗅覺敘事創造出的灰空間去設想這種氣味的來源以及它背后的面目。在這部小說中,聲音出現的頻率降低,人物對話的比重也減少了,對物、環境的描寫占據很大篇幅。阿來側重運用嗅覺書寫將文本塑造成了一個靜謐的敘事空間,這個故事不僅是寫給地震死難者的安魂曲,也是給讀者心靈上的一劑湯藥。在小說中,聲音的話語權被氣味代替,沉默的文本空間更有利于讀者在閱讀時體會種種氣味背后的具體意蘊與復雜內涵,理解語言文字背后的言外之意和韻外之旨,并將這種閱讀體驗在寂靜中升華,從而引發對生命、自然的思考,這是阿來創作的目的也是這部作品的意義所在。正如阿來自己所言:“《云中記》這本書,在表現人與靈魂,人與大地關系時,必須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現象,必須把眼光投向于人對自身情感與靈魂的自省。”[5]他用冷靜客觀的文字直書災難,疏解經歷者們的傷痛,從絕望中生發出希望,通過個體的消失和一個村落的消亡達到對整個人類群體命運和精神的觀照。阿巴的肉體雖死,精神永存,這個鮮活飽滿的人物形象不僅撫慰了小說里的鬼魂,也震撼了現實中的讀者,啟迪他們尋找物欲橫流時代剪影下自身迷失已久的靈魂。
三、結語
對于人類而言,嗅覺與味覺、視覺等本領都是人們普遍存在的原始本能,正常情況下幾乎所有人都具有這些能力,集體共有的經驗特質不僅對群體日常生活有益,作家們還可以利用這個集體本能進行文學創作,因為文學作品的受眾也是這個廣闊的群體空間。阿來用《云中記》創造出一個生動豐富的嗅覺世界,以嗅覺書寫作為小說敘事的獨特視角與表現方式,凸顯了嗅覺書寫強大的敘事功能,呈現出全新的藝術體驗,打破了已有的審美期待,有意讓讀者感受到人類嗅覺本能的強大魅力和嗅覺敘事的獨特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