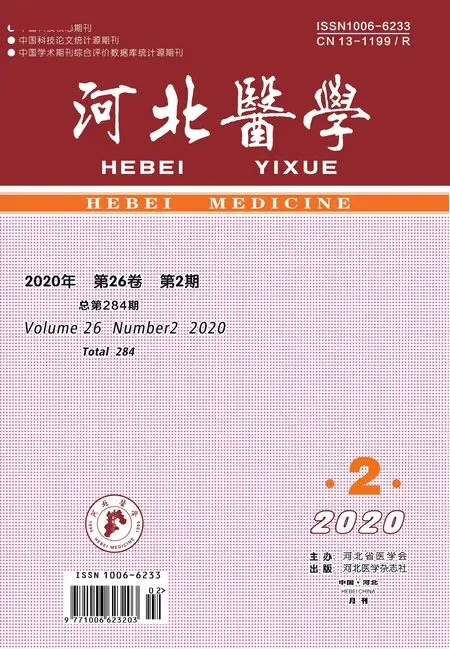影響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支架植入術后冠脈支架再狹窄相關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盧曉操, 王曉琳
(遼寧省丹東市中心醫院, 遼寧 丹東 118000)
隨著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和加重,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CHD)的發病率在近年來呈現逐年增高的趨勢,該病已是臨床常見的一類心血管疾病,具有高發病率和高死亡率的特點,對人類生命健康造成極大的威脅[1,2]。冠狀動脈支架植入術安全性較高,手術創傷較小,可促進患者術后恢復,可取得良好的的治療效果,因此在CHD的臨床應用中起到重要作用[3]。有研究表明,CHD患者支架植入術后容易出現冠狀動脈支架內再狹窄(in-stent restenosis,ISR),其發生率為5%~30%,對患者的治療效果及預后狀況造成極大的影響。直至目前,有關支架植入術后冠狀動脈ISR的具體發生機制仍未完全明確。為此,本研究通過收集本院收治的105例行支架植入術的CHD患者的臨床資料,開展回顧性研究,探究影響患者術后冠狀動脈ISR的相關因素,旨在為臨床及時預防和處理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回顧性分析本院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105例行支架植入術的CHD患者的臨床資料,納入標準:①冠狀動脈造影提示存在明確冠狀動脈病變,具備支架植入術的適應證;②存在心絞痛的明確表現,伴或不伴心電圖T波改變或ST段壓低;③具備完整的臨床資料。排除標準:①伴有嚴重血液系統疾病、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惡性腫瘤或精神性疾病等;②伴有嚴重肝腎功能不全、腦梗死、消化道出血或腦出血等;③近期伴有活動出血等。
1.2方法:收集105例CHD患者的臨床資料,記錄患者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是否伴有CHD家族史、糖尿病史、高血壓史、吸煙史、飲酒史、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濃度、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是否停用阿司匹林、應用他汀類藥物劑量情況等信息。記錄患者冠狀動脈造影檢查和介入結果,包括支架植入數、支架長度、支架直徑、是否伴有串聯支架等。
1.3判定標準:冠狀動脈ISR定義為冠狀動脈支架植入術后行冠狀動脈造影檢查可見支架兩邊緣5mm或支架內血管內徑狹窄≥50%管腔面積[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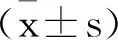
2 結 果
2.1支架植入術后冠狀動脈ISR的發生情況:105例CHD患者中,19例術后發生ISR,發生率為18.10%。根據術后是否發生ISR進行分組,結果顯示,ISR組與無ISR組臨床基線資料的比較,并無明顯差異(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臨床基線資料比較
2.2支架植入術后冠狀動脈ISR發生的單因素分析:經單因素分析結果發現,伴有CHD家族史、糖尿病史、高血壓史、吸煙史、支架≥3枚、支架長度≥30mm、支架直徑<3.00mm、伴有串聯支架、LDL-C≥3.37mmoL/L、常規劑量應用他汀類藥物、停用阿司匹林者ISR發生率較無CHD家族史、無糖尿病史、無高血壓史、無吸煙史、支架<3枚、支架長度<30mm、支架直徑≥3.00mm、無串聯支架、LDL-C<3.37mmoL/L、大劑量應用他汀類藥物、未停用阿司匹林者明顯增高(P<0.05),而飲酒史、支架植入部位及LVEF在ISR組與無ISR組中的比較,并無明顯差異(P>0.05),見表2。

表2 支架植入術后冠狀動脈ISR發生的單因素分析n(%)
注:與無ISR組比較,*P<0.05
2.3支架植入術后冠狀動脈ISR發生的多因素分析:設定自變量為單因素分析結果中P<0.05的變量,經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發現,伴有CHD家族史、糖尿病史、高血壓史、吸煙史、支架≥3枚、支架長度≥30mm、支架直徑<3.00mm、伴有串聯支架、LDL-C≥3.37mmoL/L、常規劑量應用他汀類藥物、停用阿司匹林是CHD患者支架植入術后發生冠狀動脈ISR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見表3、表4。

表3 變量賦值

表4 支架植入術后冠狀動脈ISR發生的多因素分析
3 討 論
支架植入術后ISR的發生是一個復雜的病理過程,且已有研究表明,支架植入術后冠狀動脈ISR的發生與多方面有關,如炎癥反應、血管重塑、血管彈性回縮、平滑肌細胞增生和遷移、血栓形成、細胞外基質聚集等[5]。此外,有研究認為,冠狀動脈ISR的發生并不會導致嚴重后果,患者的臨床表現較穩定,且經二次冠狀動脈介入治療后,可取得良好的臨床療效;但隨著近年來冠狀動脈介入在臨床中的進一步發展,行支架植入術的病例數逐年增多,而術后ISR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或猝死事件亦隨之增多,因此應引起臨床工作者的關注和重視[6]。此外,相比裸金屬支架,藥物洗脫支架可有效減少ISR的發生,但藥物洗脫支架仍存在5%~20%的ISR發生率,且可能存在晚期支架內血栓形成等后果。
本研究發現,105例CHD患者中19例術后發生ISR,發生率為18.10%。ISR的發生可能會引起嚴重心血管事件,因此應引起臨床工作者的足夠重視,以盡可能減少冠狀動脈ISR的發生。有研究表明,代謝因素(伴糖尿病等)、遺傳因素、不良生活習慣(伴吸煙史等)、支架相關因素(支架植入數、長度、直徑等)等均是ISR發生的主要影響因素[7]。本研究經單因素分析結果發現,伴有CHD家族史、糖尿病史、高血壓史、吸煙史、支架≥3枚、支架長度≥30mm、支架直徑<3.00mm、伴有串聯支架、LDL-C≥3.37mmoL/L、常規劑量應用他汀類藥物、停用阿司匹林者ISR發生率較無CHD家族史、無糖尿病史、無高血壓史、無吸煙史、支架<3枚、支架長度<30mm、支架直徑≥3.00mm、無串聯支架、LDL-C<3.37mmoL/L、大劑量應用他汀類藥物、未停用阿司匹林者明顯增高。此外,本研究進一步經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發現:伴有CHD家族史、糖尿病史、高血壓史、吸煙史、支架≥3枚、支架長度≥30mm、支架直徑<3.00mm、伴有串聯支架、LDL-C≥3.37mmoL/L、常規劑量應用他汀類藥物、停用阿司匹林是CHD患者支架植入術后發生冠狀動脈ISR的獨立危險因素。
其中,①CHD家族史:伴有CHD家族史的患者出現血栓形成的幾率高于無CHD家族史的患者,究其原因可能與免疫因素、遺傳因素有關[8]。因此,臨床上對伴有CHD家族史的患者更應警惕血栓形成的風險性,及時、合理應用藥物進行干預。②糖尿病史:機體代謝異常是引起冠狀動脈血管內皮損傷的一種主要因素。伴有糖尿病史的CHD患者容易發生ISR的原因可能與胰島素平滑肌細胞增殖和遷移的作用密切相關,并且凝血系統與抗凝血系統失衡,機體內皮細胞舒張和收縮功能減弱等,均可能導致患者支架植入術后發生ISR。③高血壓史:高血壓的發生可導致冠狀動脈內皮損傷進一步加重,在收縮壓每升高10mmHg時,發生ISR的幾率可升高約20%,部分行支架植入術的CHD患者伴有高血壓史,而相比血壓正常者,高血壓者出現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的幾率升高2~5倍。④吸煙史:有研究報道,伴有吸煙史的人群患CHD和支架植入術后發生ISR的幾率較無吸煙史者高出1~2倍[9],吸煙既可引起冠狀動脈痙攣,亦會引起血管內皮細胞損傷,導致動脈粥樣硬化,促使血小板粘附,導致纖維蛋白原水平增高,可進一步導致血栓形成,使得CHD患者遠期病死的風險性增高[10]。⑤支架≥3枚、支架長度≥30mm、支架直徑<3.00mm、伴有串聯支架:本研究結果表明,支架植入數、支架長度≥、支架直徑及是否伴有串聯支架等有關支架植入的情況是CHD患者支架植入術后ISR發生的可預測因素。支架植入患者體內均可導致不同程度的炎癥反應,誘導內皮增生,因此臨床中在保證解決冠狀動脈主要狹窄處的情況下,盡可能選用長度小、直徑大的支架,且盡可能不串聯支架。⑥LDL-C≥3.37mmoL/L:LDL-C對動脈內皮具有較強的破壞性,若血清LDL-C濃度過度增高,則容易使之附著于動脈內皮下,進而破壞動脈內皮結構及其功能。此外,LDL-C過度增高可加重內皮的炎癥反應,而后者是引起動脈粥樣硬化的主要影響因素。⑦常規劑量應用他汀類藥物:他汀類藥物既能有效降低LDL-C濃度,亦能穩定斑塊、有效逆轉斑塊形成、改善炎癥反應,因此對改善CHD患者的預后狀況具有重要的作用。有選擇性地應用大劑量的他汀類藥物可促使血藥濃度增加,對減少ISR的發生具有重要意義。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臨床中大劑量服用他汀類藥物時,應時刻警惕其可能引起的肝功能損害、肌肉疼痛等不良反應。⑧停用阿司匹林:已有研究表明,相比無ISR發生的患者,ISR患者停用阿司匹林或不規律服藥的比例較高。及時、有效的抗栓治療對CHD患者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伴有缺血風險的患者,應適當增加抗栓時間以盡可能降低術后ISR的發生。
綜上所述,臨床上存在著多種影響CHD患者支架植入術后ISR發生的影響因素,因此臨床中應合理評估各項影響因素,并結合患者基礎疾病和冠狀動脈造影結果,及時、重點對因處理可能出現ISR的患者,必要時應用CHD二級預防藥物進行強化治療以盡最大程度改善患者的預后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