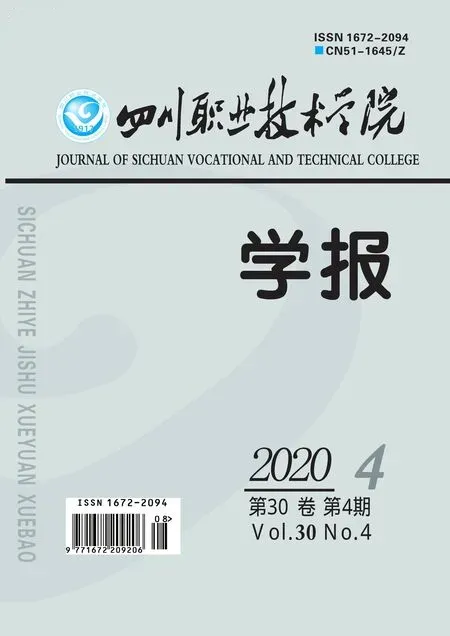譯者主體性視角下《賣炭翁》英譯本的比較研究
郭航樂
(貴州城市職業(yè)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貴陽 550025)
一、引言
唐朝中晚期出現了專門為皇家采購服務的“宮市”,宮廷所需日用品由遍布各街市的太監(jiān)及其爪牙向百姓搜刮,他們無憑無據,隨意付給貨主極為低廉的收購價并要求其送到宮內,該弊政對城市商人和近郊農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難。白居易對宮市有十分的了解,對百姓又有深切的同情,故而創(chuàng)作出了感人至深的《賣炭翁》。詩人通過對賣炭翁悲慘遭遇的描寫,揭開了“宮市”的虛偽面紗,深刻剖析了晚唐腐朽的社會現實,抨擊了統(tǒng)治階級的殘酷剝削,表達了對被壓迫人民的深切同情。
二、譯者主體性的概念
在詩歌翻譯中,語言與文化的轉換者——譯者可以根據源語和目的語的語言、文化特征甚至讀者的接受能力來選擇特定的翻譯策略。我國學者查明建和田雨曾將譯者主體性定義為“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chuàng)造性”[1]。換句話說,譯者主體性貫穿于翻譯活動的全過程,它不僅體現在譯者對作品的理解、闡釋和語言層面上的藝術再創(chuàng)造,也體現在對翻譯文體的選擇、翻譯的文化目的、翻譯策略等方面[1]。
三、譯者主體性在《賣炭翁》英譯本中的體現
作為翻譯的主體,譯者在詩歌翻譯過程中一定會受到文化、生活背景、自身審美以及讀者接受能力等內外因素的影響,從而導致每個譯本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譯者身份”的烙印。本文選取《賣炭翁》三個英譯本——許淵沖譯本[2]、Arthur Waley譯本[3]以及楊憲益、戴乃迭合譯本[4]為研究對象,從譯者主體性的視角下對三個英譯本的語言和文化翻譯策略進行比較與研究,探討譯者主體性在譯詩中的發(fā)揮,以期為中國古詩英譯提供一些借鑒和思考。
(一)譯者主體性與許淵沖譯本
許淵沖是我國著名翻譯家,翻譯作品數不勝數,他通過幾十年的文學翻譯實踐歸納提煉出“音、形、意三美”翻譯理論,為我國的翻譯領域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領域都做出了極大的貢獻。這得益于他的成長環(huán)境:他的母親受過教育,擅長繪畫,賦予了他愛好文學和追求美的天性;他還深諳中國古典文化知識,亦曾有留洋經歷。他的譯本十分尊崇原詩的音韻美和形式美:仿照原詩全詩押尾韻,開篇2行和結尾3行譯詩用的韻腳形式是“aabbccdd”,體現在“fare”和“ware”,“away”和“say”,“red”和“head”的押韻上;中間15行譯詩基本采用“ababcdcd”的押韻形式,表現在“dust”和“just”,“black”和“back”,“price”和“ice”,“he”和“be”等詞的押韻上,全詩一韻到底,讀起來朗朗上口,有一種回環(huán)的樂感美,這體現了許淵沖在審美方面的譯者主體性。
將一個句子的內涵擴充譯為兩個句子,此為一句雙譯。其作用一為充分展現原詩意境,二是達到押韻的目的。例如:許淵沖將“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譯為兩個句子:“What does the old man fare?He cuts the wood in southern hill and fires his ware.”[2]。譯文采用提問方式引出賣炭翁的身份,可以吸引讀者的好奇心,使得讀者想要深入閱讀一探究竟。句中,“fare”和“ware”形成尾韻,符合原詩尾韻的修辭特點。再如:許淵沖將“宮使驅將惜不得”擴展譯為 兩 句 :“Theydrivethecartaway.What dare the old man say?”[2],體現了他主張意譯的翻譯策略——“What dare the old man say?”是對“(賣炭翁)惜不得”的意譯。一句雙譯既區(qū)分了原詩中連續(xù)謂語“驅將”和“惜不得”的不同主語,又通過“away”與“say”押尾韻來滿足音步和韻腳的需求。這些都是許淵沖在譯詩時譯者主體性的體現。
許淵沖為了通過押韻實現“音美”可謂煞費苦心,但也有處理不得當的地方,如將“牛困人饑日已高”譯為“The sun is high,the ox tired out and hungry he.”[2]。為了和“Who can they be?”[2]句中的“be”一詞形成隔行尾韻,將“人饑”譯成“牛又累又餓”,且“he”在句子結構上明顯多余。此處倒裝使得句子結構混亂、語法錯誤,為了“音美”而犧牲“意美”就有點得不償失了。再如:為了和“Outsidethesoutherngatein snow and slush they rest.”句中的“rest”一詞形成隔行尾韻,許淵沖將“黃衣使者白衫兒”譯為“Two palace heralds in the yellow jackets dressed.”[2]。根據唐朝歷史可知,此處的“黃衣使者”指的是在宮廷聽差或侍奉皇帝及后宮妃嬪的太監(jiān),但“白衫兒”卻另有其義,他與“黃衣使者”因為制服顏色的不同而有著身份地位的差別,一般指太監(jiān)手下幫助搶購貨物的隨從。許淵沖將二者一并譯為“兩個身穿黃色宮廷制服的人”顯然會誤導讀者。此處漏譯失去了原詩顏色意象產生的視覺效果,許淵沖在譯詩時一味追求“音美”反而限制了其譯者主體性的發(fā)揮。
(二)譯者主體性與Arthur Waley譯本
Arthur Waley(亞瑟·威利)是英國著名漢學家、文學翻譯家,他所翻譯的中國古詩深受西方讀者喜愛,增進了西方世界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理解,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為Arthur Waley的預期讀者是西方普通讀者,考慮到其不太了解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和習俗,所以在譯詩時他更多采取了歸化的翻譯策略,使《賣炭翁》中很多文化意象本土化,讓讀者聯想到自己熟悉的事物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譯詩,增強譯詩的可讀性和欣賞性,這體現了他的譯者主體性。例如:Arthur Waley將“炭車”譯為“char-coal wagon”[3]。牛津詞典對“wagon”一詞的定義為:“a four-wheeled trailer for agricultural use or a light horse-drawn vehicle,especially a covered one”,而《賣炭翁》中的炭車應該是用牛拉的兩輪車,譯者將其譯成西方交通工具——農用四輪拖車或輕便有篷馬車,這是典型的歸化處理。
但Arthur Waley畢竟生長在西方國家,沒有中國生活背景的他對漢語文化的理解與把握還是不夠精準。比如:他將“使者”一詞譯為“public official[3]”(公職人員),這是由于 Arthur Waley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將中國古詩中的形象重塑為西方形象,這雖然有助于目標讀者理解,但卻歪曲了“使者”在原詩中的太監(jiān)形象。再如:原詩中的“白衫兒”指代太監(jiān)的隨從,譯者將其譯為“a boy in a white shirt[3]”(穿白色襯衫的男孩),因為英國缺失這樣的文化意象,譯者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卻并不恰當,容易誤導讀者。此外,他將“黃衣使者”譯為“public official in a yellow coat”[3]。在中國歷史文化中,“黃衣使者”指的是太監(jiān),而太監(jiān)所穿的“黃衣”是短上衣而非長大衣,故此處是明顯誤譯,應改為“a yellow jacket”。
從目標語讀者的接受能力和翻譯目的考慮,譯者采取了歸化的翻譯策略,這體現了他的譯者主體性;但對于中國讀者來說,這些又是制約其譯者主體性發(fā)揮的表現。因此,對于譯詩質量的評判是一件見仁見智的事,沒有絕對的標準。
(三)譯者主體性與楊憲益、戴乃迭合譯本
楊憲益成長于一個家境顯赫優(yōu)渥的環(huán)境中,其父是當時杰出的金融家,曾任天津中國銀行的行長。楊憲益曾在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學成歸國后被推選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由于家風嚴肅、為人處事方式謹慎,使得他的譯風也十分嚴謹,因此他在譯詩時竭力保留原詩文化意象,努力讓中國文化走出國門。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合譯本語言準確,亮點頗多,他們并未拘泥于原詩的韻律和形式,閱讀他們的散文體譯詩也可以帶來美的享受。從以下分析中可以看到楊憲益、戴乃迭夫婦譯者主體性的發(fā)揮:
例如:白居易通過三個形容詞“煙火色”、“蒼蒼”和“黑”分別對賣炭翁的面孔、鬢發(fā)和手指進行了細膩、傳神的描寫,使年邁體衰、辛苦勞作的賣炭翁形象躍然紙上,讓讀者深切體會到賣炭翁生活之艱辛。若將這三個形容詞簡單譯為“smoke”、“gray”和“black”就顯得平淡刻板,不夠立體,難以再現原詩中的賣炭翁形象。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將詩句“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譯為“His face streaked with dust and ashes,grimed with smoke,/His temples grizzled, his ten fingers blackened.”[4]。該句中,三個由動詞變化而來的特殊形容詞“grimed”、“grizzled”及“blackened”頓時增添了一種動態(tài)效果,給詩句增色不少,從而使得艱難困苦的賣炭翁形象在譯詩中栩栩如生、躍然紙上。
再如:“手把文書口稱赦,回車叱牛牽向北。”一句中,白居易連用了五個動詞——“手把文書”的“把”、“口稱敕”的“稱”、“回車”的“回”、“叱牛”的“叱”、“牽向北”的“牽”。宮使急迫連貫的五個動作使賣炭翁沒有反抗的余地,從而揭露了宮使兇殘掠奪的真面目。楊憲益、戴乃迭嚴謹地將此句譯為“They wave a decree, shout that these are imperial orders;/Then turn the cart,hoot at the ox and drag it north.”[4],也同樣巧妙地連用了“wave”、“shout”、“turn”、“hoot at”和“drag”五個動詞,尤其是“drag it north”傳神地再現了賣炭翁雖然極不情愿,他的炭車卻還是被宮使強拉硬拽著拖去皇宮的畫面,堪稱精彩!
四、結語
從《賣炭翁》三個英譯本的對比研究可以看出:譯者的文化背景、語言及審美特色、翻譯策略的選擇以及目標讀者的差異等主客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制約著譯者主體性的發(fā)揮,但正是因為這些影響才使得不同語言文化背景下譯者的譯詩大放光彩,也促使多種高質量譯本的出現,從而帶給讀者多重的藝術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