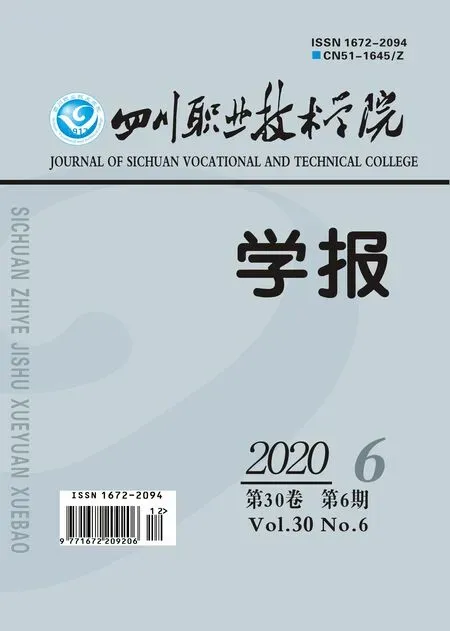抒情與諷刺:論蕭紅小說中的擬兒童語言
曾春葙
(大連外國語大學 漢學院,遼寧 大連 116044)
擬兒童語言是蕭紅將沉重的故事娓娓道來的一種特別方式。擬兒童語言常常運用于兒童文學中,以語言的淺顯、直白、趣味為基本要點,讓兒童在閱讀時更容易接受理解。但蕭紅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兒童文學作家,她只是擅長從兒童視角出發進行創作。蕭紅以兒童視角創作的作品,如《牛車上》《小城三月》《呼蘭河傳》等,其中以長篇小說《呼蘭河傳》最具代表性。由于這三部作品中的兒童視角實際上是兒童敘述者與隱含作者兩種敘述聲音交錯共存,在這種復調敘事的策略下,擬兒童語言的書寫便使得兒童敘述者與隱含作者之間的對話關系更加有張力——在天真爛漫的兒童話語中抒發成年人的人生感嘆;在幼稚無邪的兒童話語中暗諷悲涼的世間;在單純質樸的兒童話語中道出蕭紅最真摯的情感訴求。
一、擬兒童語言的界定
先行學者們對于蕭紅作品的研究視角多樣,新觀點層出不窮。但鮮有學者關注到蕭紅作品的擬兒童語言方面,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對于兒童視角與擬兒童語言之間的界限存在些許爭議。為了使得擬兒童語言的概念更加清晰,筆者嘗試將擬兒童語言界定為:基于兒童視角出發,作家模仿兒童的語言方式,由此創造出的表達兒童思維的文學語言。這樣的界定便于進一步理清兒童視角與擬兒童語言的關系:兒童視角側重敘事的角度,注重還原兒童所遇到的人與事,再現事件發生的場景;而擬兒童語言更側重表述的語言,注重還原兒童對于所遇到之人與事的評價,再現兒童心理活動的狀況。作者以擬兒童語言搭建起兒童視角的敘述,不同的作家都可以創作出以兒童視角為敘述視角的作品,但構建起兒童視角的擬兒童語言卻大有不同。
作家在創造擬兒童語言時,不僅是記述兒童使用的語言,也是對兒童的一種模仿。作家通過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根據自身文本的需要,選擇性模仿兒童的話語方式,創造出適合文本需求的兒童語言,在文本中還原真實的兒童心理。但正因為是模仿,再加上不同年齡階段以及不同生活環境的兒童所呈現的語言特點也有所不同,這對作家的寫作功力確實是一種考驗。假若對于兒童的語言組織把握不到位,那么創造出的擬兒童語言可能會顯得過分矯揉造作,或是缺少童真之感;假若作家在模仿創造兒童語言時,沒有考慮兒童心理學的規律及特點,作家所模仿創造出的兒童語言則偏離了作家以孩童之心觀照成人世界的創作意圖。
正因兒童語言的復雜性,這就更要求我們在對文學作品中的擬兒童語言進行研究時,需要更加深入地剖析其擬兒童語言的真假性。對于《牛車上》《小城三月》《呼蘭河傳》等這樣非兒童本位的作品,作者借助擬兒童語言深化其內涵,其藝術價值與敘述秘密耐人深思。
二、擬兒童語言的抒情方式:童言中的人生感嘆
蕭紅利用擬兒童語言,將成人理性思考下抑制住的情感在擬兒童語言中一一流露。蕭紅以不同的抒情方式抒發內心最深層的情感,在作品中注入了她對生死的認知、自由的向往、離家的鄉愁。
首先,蕭紅作品的詩意之感夾雜在各種景物的描寫性語言之中,以描寫兒童眼中的環境來抒發內心情感,是文本最大的抒情方式之一。在《呼蘭河傳》中,蕭紅賦予了后花園中的動植物生命感,將它們擬人化、自由化。在這里,“黃瓜愿意開一個黃花,就開一個黃花,愿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管。”[1]180這段書寫是兒童“萬物有靈”的早期心理特點的語言體現,抒發了蕭紅對自由世界的向往。《呼蘭河傳》中祖母死后表哥領著我去到了南河沿,“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那里有黃土坑、南大營、小洋房、柳條林以及“我”第一次見到的河水,這比起后花園來說,是十分新奇的體驗。小小的“我”開始期待大大的世界:“是不是我將來也可以一個人走得很遠?”[1]261雖然這是擬兒童語言的描寫,刻畫一個年幼孩童對未來的好奇和懵懂,但其中的深意,不禁喚起每個人對人生的追問。隨著“兒童眼中的環境”一步一步地擴寬,離故鄉越來越遠的蕭紅對黑土地的想念,對童年自由時光的懷念,漸漸地加深為了對人生的感慨和思考。
其次,蕭紅筆下擬兒童語言獨具匠心之處,集中體現在通過兒童不停的追問抒情。
蕭紅以“我”之口追問離鄉,抒發了蕭紅思故鄉念故人的情感。《呼蘭河傳》中蕭紅以“少小離家老大回”的詩句引出“我”對離鄉的追問,“我” 問祖父:“我也要離家的嗎?”[1]203當“我”第一次走出后花園,看到了更大的世界的“我”也不禁發出追問:“ 是不是我將來一個人也可以走得很遠?”[1]261——文中多次重復了這個追問,反映新世界對“我”帶來了非常新鮮的認識體驗,同時也隱含了作者復雜的心理活動——此時蟄居于香港的蕭紅,顛沛流離。她真的一個人走得很遠,十八歲出逃黑土地,從此她與后花園的距離越來越遠。除此之外,蕭紅以“我”之口追問生死,表現了蕭紅對自我人生的思考。在《呼蘭河傳》中,祖母的離世是“我”第一次感知到死亡,但“我”對死亡的認知僅限于祖母從床上躺到了長板上。“我”甚至認為祖母的死使“我”變得聰明了,這樣不合常理的想法確實也是孩童心理天馬行空的體現。《呼蘭河傳》中的“我”第二次直面死亡是團圓媳婦的死,文中沒有過多刻畫“我”對于團圓媳婦的死心情如何,但卻隱含著“我”對死亡的進一步認知。當“我”不斷追問老廚子和有二伯關于團圓媳婦的埋葬過程,卻得不到回答時,對生命的唏噓之感更加深化。整本《呼蘭河傳》呈現了“我”對生死認知的層層遞進,祖父問“我”:“等你老了,還有爺爺嗎?”[1]184那時候的“我”心生恐懼,但在文中尾聲處,蕭紅卻平淡地寫道;“呼蘭河這小城里面,以前住著我的祖父,現在埋著我的祖父。”[1]313蕭紅以“住”和“埋”兩個字展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生命狀態,原先“我”十分恐懼的事情,現在也坦然接受。《牛車上》的“我”追問五云嫂:“五云哥陣亡的時候,你哭嗎?”[2]102五云嫂沒有回答,“我”的追問得不到答案,就如以“哭泣”無法回答“死亡”,面對生死沒有一個正確的處理答案。
生死在蕭紅筆下顯得無關輕重,擬兒童語言追問之下展現的生死淡然,可能是源于孩童對生死的認知有限,正如“參禪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人生境界,孩童對于死亡的認知僅停留在生理層面,似乎并未意識到死亡的社會意義。但非擬兒童語言刻畫的“任由生長”的生死觀更加淡然,仿佛蕭紅筆下的成人們已步入“禪中徹悟,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人生階段,將社會賦予生命的意義拋擲腦后。蕭紅筆下似乎從未沒有出現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之人,人生的第二境界在蕭紅筆下的消失,是蕭紅對于生死本質的闡釋——人生的無力感從始至終,社會所賦予人的所有意義與束縛都將在自然的輪回中消解。在“我”對生死的追問中,不僅展現了蕭紅淡然處世的生死觀,同時也在追問的層層遞進中,展現了一個小女孩成長的心理過程。
三、擬兒童語言的諷刺方式:童言中的反抗意味
雖然蕭紅筆下的擬兒童語言的諷刺方式相比非擬兒童語言的諷刺方式來說,較為遜色,但通過擬兒童語言來進行諷刺,是一個較有挑戰性的文本建構,具有其特殊的諷刺力量和美學張力。
無論是《呼蘭河傳》中三歲懵懂的“我”,還是《牛車上》頑皮的“我”,或是《小城三月》中已經漸漸讀懂少女心事的“我”,“我”在文本中都擔任著一個重要的角色——說出真話,成為一面鏡子,照出世間的善惡美丑。這種童言無忌的諷刺首先體現在《牛車上》“我”對當兵人的評價上。村里的孩子都害怕當過兵的車夫,但車夫在聽了五云嫂的故事后居然拿手巾安慰五云嫂,“我”的反應是:“當兵的人,怎么會替人拿手巾?我知道的當兵的人就會打仗,就會打女人,就會捏孩子們的耳朵。”[2]102當兵的人在孩童的眼中呈現出“力氣大、厲害”等鮮明特點,這樣的特點沒有使得孩童對于當兵的人產生崇拜感,而是恐懼。“我”的反應結合五云嫂的經歷充分反映出時代的混亂帶給人的壓迫,不僅是一種強權的壓迫,更是一種男權的壓迫。蕭紅借助車夫這一舉動,諷刺了強權的男性勢力對于女性造成的傷害。
其次,童言無忌的諷刺還表現在團圓媳婦到來的這件事情上。在團圓媳婦正式登場之前,文本大肆渲染了周邊的人對團圓媳婦的關心程度,所有人都跑去看她,而“我”也因此產生了對團圓媳婦的強烈好奇,通過見團圓媳婦前,“我”對自己的不斷反問,與見到了團圓媳婦后的反應形成一個強烈的反差,團圓媳婦在“我”看來,只是一個小姑娘,但呼蘭河城的人們都湊熱鬧,大家對這件事表現出來的關心程度早已遠遠超過了這件事本身的價值和意義。在老胡家準備給團圓媳婦作法洗澡時,所有人都給團圓媳婦“診治”,卻只有“我”說“她沒有病,她好好的”。可“我”的力量終究太小,無意識違背了“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團圓媳婦終于死了,有意識地反抗著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的蕭紅則只能以含淚的微笑回憶這寂寞的小城。作者只能以“我”的口,說出真話,諷刺這些被封建舊俗迷惑的愚昧又可憐的人。
此外,《小城三月》中的“我”又與《呼蘭河傳》和《牛車上》的“我”有所不同。童言無忌的諷刺在《小城三月》中顯得柔和一些。《小城三月》中的“我”比起《呼蘭河傳》和《牛車上》的“我”來說更年長幾歲,“我”已可以琢磨到翠姨的少女心事,但“我”卻也只是小心翼翼地談起翠姨和堂哥兩人似乎戀愛的事。“我”不敢直接地幫助翠姨追求她喜愛的東西,只敢“默默的祝福翠姨快快買到可愛的絨繩鞋,我從心里愿意她得救”[3]。蕭紅以“我”無力的話語表現,從而對于壓抑女性欲望的封建社會發出無聲的吶喊。蕭紅筆下塑造的少年的“我”不再像年幼時的“我”一般率真直接,成長的變化揭露了封建舊社會對于一個童真靈魂的改變,孩童表達的欲望逐漸被社會壓制,最終孩童也成長為大人。
孩童以別樣的方式質問世界,但世界卻無法給孩童一個正確答案。蕭紅終其一生尋找答案,她的筆下寫出詩,寫出血,寫出淚,最終還是以孩童之口道出真心,諷刺這個讓她遍體鱗傷的社會。在蕭紅的語言組織下,稚嫩的擬兒童語言中也隱隱透露著反抗的意味。蕭紅借“我”之口,反抗著封建壓迫,反抗著愚昧的傳統,以世間最單純的孩童目光直視黑暗。
四、結語
蕭紅的擬兒童語言創造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成功的,我們不能否認它的藝術價值。
蕭紅擬兒童語言創造的成功首先在于,成功塑造了一個立體的“我”。在《兒童語言的發展》一書中,李宇明對于歐文— 特里普(S.Erivin-Tripp)、科薩羅(W.Corsaro)、格利森(J.B Gleason)、謝茲(M.Shatz)、格爾曼(R.Gelman)、張璟光等人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得出結論:兒童可以根據角色間的權勢關系,來選擇不同的語碼①[4]。蕭紅筆下不管是處于任何年齡階段的孩童也符合這一結論,他們都可以根據角色間的詮釋關系,來選擇不同的語碼。無論是在《呼蘭河傳》中,或是《牛車上》,還是《小城三月》里,蕭紅所塑造的“我”都具有鮮明的性格特點:《呼蘭河傳》的“我”天真且淘氣,《牛車上》的“我”頑皮又單純,《小城三月》的“我”懵懂又心思細膩。文本中的“我”對不同的人說話風格都有所不同,這凸顯了蕭紅語言創作能力的過人之處。
蕭紅擬兒童語言創造的成功還在于,成功還原了一個孩童的心理世界,并且在孩童的心理世界中注入成人對世界的思考。在孩童的懵懂中觀照成人世界的愛恨,以孩童之眼直觀黑暗背后最純真的世界;在孩童對世界的疑惑與追問中抒發人生感嘆,以孩童之口試探人生本質;在孩童天馬行空的想象與思考中暗諷被束縛的人世間,以孩童之心找尋世間真理。
除此之外,從語言學層面來看,蕭紅通過語言的變形或詞語的超常搭配,更好地塑造了一個源于兒童口中的世界,讓讀者更能感受到童真、童趣,凸顯了擬兒童語言的魅力。曾有沈云佳在其研究成果中指出《呼蘭河傳》的色彩詞語使用十分豐富,ABB 式詞語最為突出[5]。這非常符合擬兒童語言的形式,正如王金禾在《兒童歌謠疊音藝術研究》中所提到的:音節復疊使得語言透露出童真自然的味道,給人一種嬌小、可愛的感覺[6]。在這基礎上,渠亞楠繼續深入從語音層面指出了文本語言在于擬聲變異、狀物變異上的語言變形[7]。出其不意的語言變形,童趣滿滿的詞語搭配,擬兒童語言的藝術效果一涌而出。
但擬兒童語言還是存在著它的局限性,童言無法完全轉達作者的內心態度。擬兒童語言在抒情上可以充分發揮作用,因為成人在抒發感情時可能會受到很多理性的限制,但兒童不一樣,他們可以愛憎分明,他們單純可愛,因此擬兒童語言可以更好地直接或間接地表達情感。但擬兒童語言在諷刺效果上存在局限性,兒童的語言簡單直白,很難把復雜的諷刺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反映作者內心。比起蕭紅筆下非擬兒童語言的諷刺,擬兒童語言的諷刺還是顯得有些力不從心。蕭紅非擬兒童語言在全知第三人稱視角下,不同于使用擬兒童語言時小心翼翼、委婉曲折地表達自己內心最真實的吶喊,她尖銳無情地把那些打著傳統稱號的封建外衣直接撕開,諷刺抨擊之感十分強烈。
注釋:
①語碼:社會語言學的術語,指的是具有不同的語用價值的詞語、句子、篇章及其他一些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