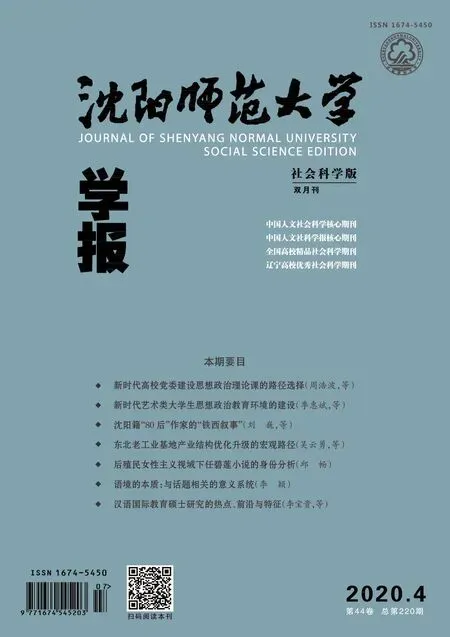后殖民女性主義視域下任碧蓮小說的身份分析
邱 暢
(遼寧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遼寧 沈陽 110036)
20世紀(jì)60年代,美國文壇呈現(xiàn)出全新的氣象,華裔女作家的作品頗受讀者歡迎,十分暢銷,華裔女作家也因此開始在美國文壇占有一席之地。目前國內(nèi)對(duì)任碧蓮小說的研究日趨成熟,研究深度和廣度均有所突破,整體研究初具規(guī)模。盡管如此,現(xiàn)有研究仍然具有一定局限性,研究視角沿襲傳統(tǒng)的種族、文化等視角,理論基礎(chǔ)尚未形成成熟體系。從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視角研究任碧蓮的小說可以突破現(xiàn)有局限,開創(chuàng)全新的研究視角。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的有機(jī)結(jié)合不僅能夠彌補(bǔ)單維理論造成的單一視角的不足,而且能夠?qū)⒎N族與文化有機(jī)融合,使研究視角更加立體,研究內(nèi)容進(jìn)一步升華,凸顯小說的精神實(shí)質(zhì)和文化內(nèi)涵。
一、后殖民女性主義
后殖民女性主義是20世紀(jì)末期興起的新興理論,按照理論歸屬來劃定,屬于后殖民主義范疇[1]。后殖民女性主義衍生于殖民主義理論,既關(guān)注后殖民主義的焦點(diǎn),又關(guān)注女性主義的焦點(diǎn),在此基礎(chǔ)上,將二者的理論觀點(diǎn)有機(jī)融合,將矛頭直指第三世界女性。從理論的關(guān)注焦點(diǎn)來看,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存在差異,前者關(guān)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男性,后者關(guān)注受到父權(quán)壓迫的女性,兩種理論的結(jié)合使理論的焦點(diǎn)直指在異質(zhì)文化和父權(quán)文化中被雙重邊緣化的女性,以及女性在打破異質(zhì)文化和父權(quán)文化的統(tǒng)治地位過程中的抗?fàn)帯:笾趁衽灾髁x不僅批判針對(duì)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殖民統(tǒng)治,而且批判父權(quán)文化對(duì)女性的壓迫和束縛,集中關(guān)注異質(zhì)文化與父權(quán)文化雙重壓迫下第三世界女性身份和地位的嚴(yán)重缺失。后殖民女性主義跳脫性別與身份的局限,主張?jiān)谖幕蟊尘跋绿骄康谌澜缗缘纳矸輪栴}、地位問題甚至生存問題,充分考慮民族、階級(jí)等影響因素。后殖民女性主義有效彌補(bǔ)了原有單維理論的局限性,揭示西方女性主義的單一視角,主張關(guān)注第三世界女性的生存狀態(tài),闡明性別差異對(duì)第三世界女性的影響,突顯文化語境與性別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
在后殖民女性主義興起之前,尚未有理論直接關(guān)注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地位和生存狀態(tài)[2]。作為生存在社會(huì)中的人,個(gè)體不再是自然人,而是社會(huì)人,第三世界女性成長和生活的社會(huì)和文化因素與西方女性截然不同,因此西方女性主義對(duì)第三世界女性并不適用,缺乏理論的支撐使第三世界女性長期處于被忽視的狀態(tài)。后殖民女性主義大膽突破原有理論框架,將種族、階級(jí)等概念與性別概念相融合,構(gòu)建多層次的理論體系。后殖民女性主義不僅將第三世界女性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多元化,而且多層次、多角度地關(guān)注第三世界女性所遭受的壓迫,將女性的身份和地位置于歷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下進(jìn)行分析,辨別差異的同時(shí),分析產(chǎn)生差異的原因,其目的在于消除壓迫,打破種族和性別的限制,改善第三世界女性的生存狀況,提升第三世界女性的社會(huì)地位。
二、華裔女性的身份缺失
威廉·布魯姆認(rèn)為,身份是一個(gè)相當(dāng)復(fù)雜的概念,個(gè)體的身份并不局限于對(duì)個(gè)體本身的認(rèn)知,個(gè)體所處社會(huì)環(huán)境中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因素都應(yīng)該考慮在內(nèi)。身份確認(rèn)既是個(gè)體的內(nèi)在需求,也是個(gè)體一種無意識(shí)的行為要求[3]。個(gè)體的身份能否得到確認(rèn)直接關(guān)乎該個(gè)體的身體和心理能否正常發(fā)展,其中對(duì)心理的影響尤為突出。身份確認(rèn)對(duì)個(gè)體的心理安全感至關(guān)重要,如果個(gè)體的身份能夠得到確認(rèn),那么個(gè)體就會(huì)產(chǎn)生心理安全感。個(gè)體的心理安全感與其身份得到確認(rèn)的程度正相關(guān),隨著個(gè)體的身份得到確認(rèn)并且這種確認(rèn)能夠不斷鞏固和維護(hù),那么心理安全感也會(huì)隨著身份的維護(hù)和鞏固而得到某種程度的鞏固和加強(qiáng)。反之,則對(duì)個(gè)體產(chǎn)生消極影響。一旦個(gè)體的身份無法得到確認(rèn),個(gè)體將陷入薩義德提出的“中間狀態(tài)”[4],即指生活在異質(zhì)文化中的個(gè)體既無法擺脫舊環(huán)境,又無法適應(yīng)新環(huán)境,只能徘徊于兩種文化之間,在文化的夾縫中生存,導(dǎo)致心理上形成嚴(yán)重的孤獨(dú)感和心理安全感缺失,并最終造成身份缺失。
(一)身份危機(jī)
任碧蓮小說中的華裔女性均陷入身份危機(jī)之中,雙重邊緣化的生活不僅使她們飽受來自異質(zhì)文化和父權(quán)文化的壓迫,而且使她們的心理嚴(yán)重缺乏安全感。在異質(zhì)文化下,華裔女性是主流文化的“他者”;在父權(quán)文化下,華裔女性是男性的“他者”。雙重邊緣化導(dǎo)致華裔女性的身份無法得到確認(rèn),更無法實(shí)現(xiàn)身份的鞏固和維護(hù),陷入身份危機(jī)。
主流文化具有絕對(duì)的壓倒優(yōu)勢(shì),華裔文化只能處于主流文化的邊緣,永遠(yuǎn)無法融入主流文化,華裔作為華裔文化的代表孤獨(dú)地漂泊在主流文化的邊緣。在主流文化的大環(huán)境下,華裔文化屬于弱勢(shì)文化,華裔群體屬于弱勢(shì)群體。雖然華裔置身于異質(zhì)文化之中,并且絕大多數(shù)華裔一直通過各種途徑努力融入主流文化,但是華裔的種種努力均以失敗告終,最終的結(jié)局往往是徘徊在主流文化的邊緣,成為主流文化的“他者”。在父權(quán)文化中,男性是社會(huì)的主體,始終占據(jù)主宰和支配地位,性別的優(yōu)勢(shì)使男性自然凌駕于女性之上,在社會(huì)中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占據(jù)較大的生存空間。與此相反,性別的差異使女性完全喪失爭取權(quán)利的資格和能力,只能從屬和順從于男性。父權(quán)文化的內(nèi)涵剝奪女性的權(quán)力,限定女性的社會(huì)角色,制約女性的社會(huì)發(fā)展,華裔女性在從屬和順從中逐漸淪為父權(quán)文化的“他者”。
在《夢(mèng)娜在希望之鄉(xiāng)》中,夢(mèng)娜所經(jīng)歷的身份危機(jī)正是許多第二代華裔的真實(shí)寫照。夢(mèng)娜出生于美國,成長于美國的文化環(huán)境,從未到過中國,也未接觸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夢(mèng)娜看來,她是一個(gè)完全意義上的美國人,自然融入美國主流文化。事實(shí)卻恰恰相反,夢(mèng)娜仍然被排斥在美國主流文化之外,成為主流文化的“他者”,因身份無法得到確認(rèn)而造成身份缺失。縱觀夢(mèng)娜的生活背景和經(jīng)歷,夢(mèng)娜生活在多種文化形成的夾縫中。夢(mèng)娜的父母希望夢(mèng)娜能夠延續(xù)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中國傳統(tǒng)價(jià)值觀為行為準(zhǔn)則,完成中國傳統(tǒng)價(jià)值觀的代際傳承。夢(mèng)娜在學(xué)校接受的是美式教育,完全浸潤在美國文化中,美國社會(huì)的大環(huán)境促使置身其中的夢(mèng)娜接受西方價(jià)值觀。面對(duì)兩種截然不同的價(jià)值觀,夢(mèng)娜無從選擇,她無法形成清晰的價(jià)值觀,更無法在兩種文化間做出選擇與取舍。隨著夢(mèng)娜搬到猶太人社區(qū)居住,夢(mèng)娜的生活中又出現(xiàn)了猶太文化。夢(mèng)娜在三種文化間均處于邊緣地位,三種文化的雜糅和拉扯徹底阻礙夢(mèng)娜的身份確認(rèn),導(dǎo)致夢(mèng)娜在多種文化的夾縫中逐漸迷失自我身份。無法選擇的夢(mèng)娜決定自己開辟全新的道路,全然拋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美國文化,轉(zhuǎn)而投入猶太文化的懷抱,希望融入猶太文化并且使身份得到確認(rèn)。這只是夢(mèng)娜的美好愿望,她的生存環(huán)境和文化背景導(dǎo)致她仍然無法融入猶太文化,因?yàn)樗裏o法褪去美國文化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給她留下的烙印,帶有兩種文化烙印的夢(mèng)娜根本無法融入第三種文化,無法使自己的身份在新的文化中得到確認(rèn),依然陷入身份危機(jī)的結(jié)局。
《誰是愛爾蘭人》中的老祖母也是陷入身份危機(jī)的典型形象。與夢(mèng)娜不同,老祖母并不是出生在美國,而是在美國居住多年,對(duì)美國的社會(huì)與文化環(huán)境十分熟悉。多年的美國生活經(jīng)歷使這部分華裔群體想當(dāng)然地認(rèn)為自己可以融入美國主流文化,然而事實(shí)并非如此。無論華裔在美國生活多少年,依然游走于美國主流文化的邊緣,成為異質(zhì)文化的“他者”,沒有歸屬感,也無法在美國文化中確認(rèn)自己的身份。由于無法實(shí)現(xiàn)身份確認(rèn),華裔群體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在彷徨無奈中產(chǎn)生各種身份危機(jī)。老祖母的身份意識(shí)在美國主流文化與老祖母所秉持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間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這道屏障將老祖母不僅與美國主流文化隔絕,而且與美國社會(huì)中其他文化群體隔絕,嚴(yán)重阻礙老祖母融入美國社會(huì)。即便以老祖母為代表的華裔在美國生活多年,從根本上說,華裔仍然生活在自己構(gòu)筑的文化環(huán)境中,不斷受到中國文化的浸潤,與美國文化基本隔絕。兩種文化環(huán)境的并立必然造成某種程度上的文化沖突,在文化沖突下華裔由無法確認(rèn)身份到逐漸迷失自我。盡管華裔多年生存于美國主流文化之中,卻依然遺憾地淪為異質(zhì)文化的“他者”,陷入無法自拔的身份危機(jī)。任碧蓮精準(zhǔn)地刻畫了陷入身份危機(jī)的女性形象,通過描寫華裔女性的人生經(jīng)歷和心路歷程,向讀者展現(xiàn)身份缺失對(duì)女性身心造成的影響,以鮮明的筆觸反映雙重壓迫下華裔女性所遭遇的身份缺失,表達(dá)對(duì)華裔女性不幸遭遇和無助的同情。
(二)失語
斯皮瓦克認(rèn)為,第三世界女性普遍失去話語權(quán)[5]。第三世界女性普遍受到異質(zhì)文化與父權(quán)文化的雙重壓迫,因此而導(dǎo)致的雙重邊緣化使第三世界女性無法確認(rèn)自己的身份,造成身份缺失。結(jié)合海德格爾的“沉默的他者”的理論,斯皮瓦克指出,身份缺失會(huì)造成個(gè)體的自我表達(dá)受到阻礙。當(dāng)個(gè)體的身份無法得到確認(rèn)時(shí),會(huì)造成個(gè)體身份缺失,缺乏身份的支撐,言語表達(dá)便失去必要的依托,個(gè)人表達(dá)便失去途徑和指向。話語權(quán)與第三世界女性的身份密切相關(guān),身份與話語權(quán)相互作用,身份缺失必然造成話語權(quán)喪失,話語權(quán)喪失也必然造成身份缺失。一旦失去話語權(quán),第三世界女性會(huì)在沉默中逐漸失去自我意識(shí),自我意識(shí)缺失與身份缺失的共同作用徹底將第三世界女性推向雙重邊緣,在夾縫中無法言說,第三世界女性只有奪回話語權(quán)才能夠?qū)崿F(xiàn)身份建構(gòu)。
任碧蓮以犀利的筆觸刻畫華裔女性的失語及失語后所表現(xiàn)出來的心理狀態(tài)和行為狀態(tài)。在《典型的美國佬》中,任碧蓮刻畫了非常經(jīng)典的華裔女性失語形象。拉爾夫的母親是固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女性,面對(duì)來自異質(zhì)文化和父權(quán)文化的種種壓迫和折磨,拉爾夫的母親理所當(dāng)然地自愿承受,在沉默中喪失身份和地位。拉爾夫的父親在家中占據(jù)絕對(duì)的統(tǒng)治地位,掌管家中事務(wù)的決策權(quán)和選擇權(quán),母親在家中處于完全被忽略的狀態(tài),甚至最基本的發(fā)言權(quán)也被父親無情地剝奪。在兒子面前,拉爾夫的母親也失去話語權(quán),甚至失去作為母親的身份和地位。拉爾夫是出生在美國的新一代移民,從小浸潤在西方教育中,已經(jīng)形成比較完備的西方價(jià)值觀,對(duì)中國傳統(tǒng)文化知之甚少。拉爾夫的母親是老一代移民,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價(jià)值觀在母親的頭腦中根深蒂固。盡管母親極力傳承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其價(jià)值觀,但生長于西方文化環(huán)境下的拉爾夫缺乏對(duì)中國傳統(tǒng)觀念的基本認(rèn)知,對(duì)于中國傳統(tǒng)的價(jià)值觀無法接受,與執(zhí)著于中國傳統(tǒng)觀念的母親格格不入,觀念的差異在母子之間構(gòu)筑起一道溝通的障礙。為了擺脫中國傳統(tǒng)文化,拉爾夫拒絕采納母親的任何建議,母親與拉爾夫的溝通存在巨大障礙。當(dāng)母親意識(shí)到無法與拉爾夫溝通時(shí),逆來順受的母親并沒有試圖跨越這道溝通的屏障,而是選擇逃避,放棄與兒子溝通。家庭中的溝通屏障使拉爾夫的母親完全失去話語權(quán),順從和沉默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使順從和沉默的人進(jìn)一步被剝奪應(yīng)有的權(quán)利和地位,陷入更加深重的身份危機(jī)。
縱觀華裔女性生活的社會(huì)和文化背景,華裔女性注定游走于兩種文化及其價(jià)值觀的邊緣。任碧蓮筆下的華裔女性以第二代華裔為主,第二代華裔普遍出生在美國,對(duì)中國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知之甚少。第二代華裔完全接受美國的西方教育,思維方式和價(jià)值觀念已經(jīng)完全西方化,并且將自己視為真正意義上的美國人。盡管如此,第二代華裔女性往往忽略了家庭中的文化氛圍。作為第一代華裔的父輩們,他們?nèi)匀粓?jiān)守從上一代人繼承而來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傳統(tǒng)觀念,并且以此來教育自己的兒女。因此,第二代華裔所生活的家庭環(huán)境相當(dāng)于一個(gè)微縮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環(huán)境。對(duì)于華裔女性而言,她們?cè)诩彝ヒ酝饨邮艿氖俏鞣轿幕诩彝?nèi)部接受的則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華裔女性無法融入任何一種文化,只能游走于兩種文化的邊緣。
三、華裔女性的身份建構(gòu)
福柯指出,權(quán)力的實(shí)施與知識(shí)的創(chuàng)造密切相關(guān),權(quán)力的實(shí)施能夠創(chuàng)造知識(shí),反之知識(shí)又能夠創(chuàng)造權(quán)力,權(quán)力由話語權(quán)組成,因此說話也是一種權(quán)利[6]。敘事學(xué)家蘭瑟提出,對(duì)于因壓抑而無法言說的個(gè)人或群體而言,話語也代表該個(gè)人或群體的身份和權(quán)利[7]。根據(jù)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華裔女性所遭受的壓迫最為深重,不僅要遭受來自異質(zhì)文化的壓迫,還要遭受來自父權(quán)文化的壓迫,長期處于被忽略的狀態(tài)。除了客觀因素之外,華裔女性的主觀因素也是導(dǎo)致其遭遇不幸的主要原因。華裔女性的逆來順受不僅助長了白人和男性的囂張氣焰,而且將自己推向更加無法自拔的深淵,在失去話語權(quán)的同時(shí),喪失自己應(yīng)有的身份和地位,導(dǎo)致身份缺失。華裔女性只有喚醒自我意識(shí),重新控制話語權(quán),為自己的訴求找到恰當(dāng)?shù)某隹冢侠戆l(fā)聲,才能夠找回已經(jīng)喪失的身份和地位,實(shí)現(xiàn)身份建構(gòu)。
(一)自我意識(shí)覺醒
來自異質(zhì)文化和父權(quán)文化的雙重壓迫使華裔女性的生活陷入沒有出路的困境,在壓迫中順從沉默[8]。在自我意識(shí)沒有覺醒之前,華裔女性的順從思想已經(jīng)根深蒂固,并未意識(shí)到自身缺乏自我意識(shí),也沒有意識(shí)到身份缺失。在異質(zhì)文化的熏陶和影響下,華裔女性的自我意識(shí)逐漸覺醒,對(duì)平等自由的生活形成某種模糊的渴望,開始有意識(shí)地改變自身的現(xiàn)狀,以此擺脫身份困境。自我意識(shí)的覺醒對(duì)于長期處于雙重壓迫下的華裔女性而言是一個(gè)至關(guān)重要的轉(zhuǎn)變,自我意識(shí)覺醒之后,華裔女性不再心甘情愿地淪為異質(zhì)文化和父權(quán)文化的從屬物和附屬品,而是意識(shí)到爭取自身在社會(huì)中應(yīng)有地位和權(quán)利的重要性,并且將思想轉(zhuǎn)化為行動(dòng),勇于為爭取自由和權(quán)利打破現(xiàn)狀,爭取全新的生活。對(duì)于華裔女性而言,身份建構(gòu)需要經(jīng)歷一個(gè)由順從到抗?fàn)幍穆L過程,自我意識(shí)覺醒是整個(gè)過程的前提條件。自我意識(shí)覺醒撬動(dòng)整個(gè)進(jìn)程之后,華裔女性重拾話語權(quán),言說情感,表達(dá)訴求,進(jìn)而重新建構(gòu)身份。只有自我意識(shí)覺醒,華裔女性才能真正踏上身份建構(gòu)的路程。
在任碧蓮的小說中,自我意識(shí)覺醒在華裔女性身份構(gòu)建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發(fā)揮作用。華裔女性的身份建構(gòu)通常要經(jīng)歷誤讀、迷茫、覺醒三個(gè)階段才能夠完成身份建構(gòu)。在誤讀階段,華裔女性由于缺乏對(duì)自身身份的基本認(rèn)知而對(duì)自身身份產(chǎn)生錯(cuò)誤的印象,當(dāng)華裔女性在現(xiàn)實(shí)中逐漸意識(shí)到自己對(duì)身份的誤讀,她們便開始進(jìn)入迷茫階段。迷茫之后,華裔女性會(huì)對(duì)自身身份產(chǎn)生更加清楚的認(rèn)知,并且做出艱難的選擇,這便是覺醒階段。在誤讀階段,夢(mèng)娜對(duì)于自身身份的認(rèn)知只是模糊的概念,關(guān)于自身身份的信息均來自父母的言說。由于缺乏自身經(jīng)驗(yàn),夢(mèng)娜對(duì)自身身份產(chǎn)生誤讀。在夢(mèng)娜隨父母搬到猶太社區(qū)之后,由于猶太社區(qū)比較推崇中國文化,夢(mèng)娜的華裔身份使她在猶太社區(qū)享受著優(yōu)越的生活,這種暫時(shí)的優(yōu)越感使夢(mèng)娜對(duì)自身身份產(chǎn)生某種誤讀。隨著夢(mèng)娜逐漸接受美式教育并且不斷接觸美國文化,夢(mèng)娜開始意識(shí)到華裔與美國人之間的差距,她越來越向往美國文化中的自由與獨(dú)立,越來越厭惡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繁文縟節(jié)及其對(duì)人造成的種種壓抑和束縛,甚至開始厭惡自己的華裔身份。此時(shí)的夢(mèng)娜開始意識(shí)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美國文化的差異并且為此迷茫不堪,她身處兩種文化,卻在兩種文化中均無法找到歸屬感,更無法在兩種文化之間做出取舍,此時(shí)的夢(mèng)娜進(jìn)入迷茫階段。由于夢(mèng)娜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美國文化之間無法取舍,她索性放棄兩種文化,轉(zhuǎn)而在第三種文化中尋求身份確認(rèn)。盡管身處兩種文化的夢(mèng)娜在猶太文化中依然無法得到身份確認(rèn),但是此時(shí)的夢(mèng)娜通過對(duì)多種文化的認(rèn)知,對(duì)各種文化形成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并且逐漸意識(shí)到華裔身份對(duì)自身的重要性,努力追尋自身的華裔身份,在經(jīng)歷誤讀、迷茫、覺醒三個(gè)階段之后,夢(mèng)娜的自我意識(shí)開始覺醒,促動(dòng)身份確認(rèn)的抗?fàn)帲瑢?shí)現(xiàn)身份建構(gòu)。
(二)文化皈依
華裔女性身處異質(zhì)文化與父權(quán)文化的邊緣,既無法融入美國社會(huì)的主流文化,也無法在父權(quán)社會(huì)中獲得自己應(yīng)有的地位和權(quán)利。由于兩種文化的雙重邊緣化,華裔女性無法在任何一種文化中確認(rèn)自己的身份,加之華裔女性失去話語權(quán),自我意識(shí)沒有覺醒,導(dǎo)致華裔女性在兩種文化中身份缺失。從這個(gè)角度看,華裔女性身份建構(gòu)的過程從根本上說是文化皈依的過程。華裔女性只有在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歸屬和定位,才能真正找到自己身份的印記,實(shí)現(xiàn)身份建構(gòu)。在自我意識(shí)覺醒之后,華裔女性開始通過抗?fàn)幹厥霸捳Z權(quán),努力發(fā)聲,建構(gòu)身份。縱觀整個(gè)過程,從實(shí)質(zhì)上說,身份建構(gòu)的過程正是文化皈依的過程;反之,如果無法實(shí)現(xiàn)文化皈依,身份建構(gòu)也無法實(shí)現(xiàn)。
任碧蓮小說中遭遇身份危機(jī)的華裔女性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生存,身份無法得到確認(rèn)。由于身份缺失,華裔女性的心理和行為在不同程度上出現(xiàn)了扭曲現(xiàn)象。無論在異質(zhì)文化里,還是在父權(quán)文化里,華裔女性都無法擺脫邊緣化的困局。在異質(zhì)文化里,華裔女性被白人文化邊緣化;在父權(quán)文化里,華裔女性被男性邊緣化,導(dǎo)致華裔女性在社會(huì)和家庭中都缺乏身份和地位,沒有話語權(quán),在逆來順受中可悲地沉默。如果華裔女性試圖擺脫雙重身份困境,她們必須適應(yīng)文化環(huán)境的轉(zhuǎn)換,換言之,華裔女性必須以明確的身份出現(xiàn)在每種文化環(huán)境中,否則依然無法擺脫雙重邊緣化帶來的身份缺失。霍米巴巴指出,文化身份與“他者”不同,“他者”身份一旦形成便無法更改,而文化身份具有流變性,通過與“他者”的協(xié)商與轉(zhuǎn)換,文化身份可以重新構(gòu)建,因此文化身份并不是單一的本質(zhì)性特征,而是多向度的混雜性特征[9]。當(dāng)華裔女性不再執(zhí)著于“他者”身份,轉(zhuǎn)而采取全新視角認(rèn)知自己的身份,表明華裔女性的文化身份開始轉(zhuǎn)換,在主動(dòng)調(diào)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美國文化沖突的過程中,華裔女性的身份逐漸建構(gòu),文化皈依的過程得以實(shí)現(xiàn)。
在《典型的美國佬》中,拉爾夫家的女性是通過文化皈依實(shí)現(xiàn)身份建構(gòu)的典型形象。拉爾夫家是典型的傳統(tǒng)中國家庭,父權(quán)文化十分強(qiáng)勢(shì),拉爾夫的母親和妻子都是在沉默中逆來順受的女性,她們徹底被家中的男性邊緣化。由于拉爾夫家固守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他們完全無法融入美國文化,無法在社會(huì)中確認(rèn)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只能徘徊在美國文化的邊緣。文化身份具有流動(dòng)性[10],然而文化身份的流動(dòng)往往需要催化劑的作用,格羅弗便是拉爾夫家文化身份轉(zhuǎn)變的催化劑。在格羅弗的勸誘下,拉爾夫家天真地認(rèn)為只要拋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束縛,就可以輕松融入美國文化,結(jié)果適得其反,他們不僅沒有融入美國文化,反而因拋棄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喪失了原本的身份和地位。拉爾夫家的男性來到美國追尋美國夢(mèng),想通過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追求自我發(fā)展的機(jī)會(huì)。男人追尋美國夢(mèng)的虛假美好使拉爾夫家女性的文化身份開始流變,她們?cè)噲D融入美國文化,在美國文化中確認(rèn)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然而此時(shí)她們并沒有對(duì)美國文化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形成正確的認(rèn)知,不僅無法建構(gòu)身份,反而導(dǎo)致更加嚴(yán)重的身份缺失。只有擺脫美國夢(mèng)的桎梏,對(duì)文化和身份都形成正確的認(rèn)識(shí),才能夠開啟身份建構(gòu)的過程。華裔女性實(shí)現(xiàn)身份建構(gòu)的過程正是文化皈依的過程,在這個(gè)過程中華裔女性由對(duì)美國文化傾慕,再到對(duì)美國文化適應(yīng),進(jìn)而使原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逐漸演化為一種象征符號(hào),促進(jìn)身份建構(gòu)過程的完成,文化皈依與身份建構(gòu)并行不悖。
四、結(jié)語
任碧蓮小說中展現(xiàn)了形形色色的華裔女性形象,通過描寫不同性格女性的人生軌跡,小說凸顯華裔女性在異質(zhì)文化與父權(quán)文化的雙重壓迫下身心備受折磨的悲慘境遇。華裔女性在雙重排斥和壓制的過程中日益被雙重邊緣化,不僅在異質(zhì)文化中被主流文化邊緣化,而且在父權(quán)文化中被男性邊緣化。雙重邊緣化導(dǎo)致華裔女性逐漸失去話語權(quán),自我意識(shí)逐漸模糊甚至喪失,最終陷入身份危機(jī)。華裔女性的身份重構(gòu)必須以自我意識(shí)覺醒為前提條件,并且在痛苦中經(jīng)歷從無意識(shí)的順從到有意識(shí)的抗?fàn)幍哪鶚劊拍苤匦芦@得話語權(quán),逐步恢復(fù)和確立自我意識(shí),進(jìn)而走出身份危機(jī),實(shí)現(xiàn)身份建構(gò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