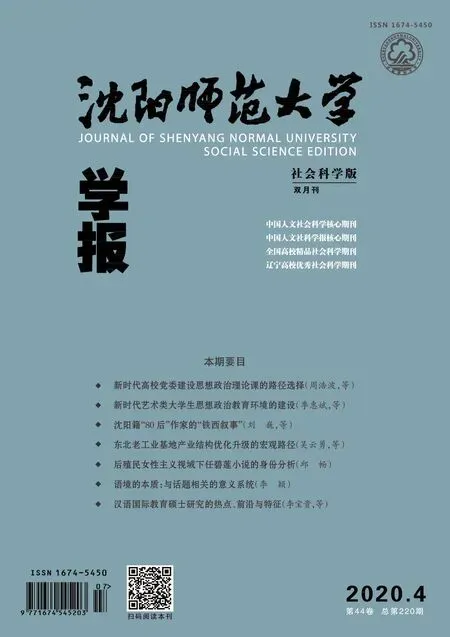從“個人體驗”中透視“人類共相”
——論福克納和大江健三郎創作的契合與差異
姜文莉
(沈陽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遼寧沈陽110034;吉林大學文學院,吉林長春130012)
當代美國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評論家、杜克大學比較文學教授詹姆遜曾坦言:“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似乎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人因獎而榮,另一類是獎因人而榮。那么有些被歸于第一類的,最終卻證明他們一直都是第二類。比如,‘《圣殿》(Sanctuary) 那部骯臟小說的作者’不出所料被證明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小說家。無獨有偶,我認為大江健三郎也是如此。”[1]福克納與大江健三郎作為來自東西方異質文化的兩位諾獎作家,都在充斥著歷史的記憶與個人體驗的創作中,透視人類共同面臨的困境與危機,表現出對人類命運的關注。同時,他們以寄希望于未來的作品探尋治愈人類心靈的良方。
威廉·福克納作為美國現代主義小說的經典作家,一直是許多小說家學習的榜樣,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爾克斯、莫言和大江健三郎都坦言自己的創作受到他的啟發和影響。大江從1966年春開始,為創作長篇小說而系統閱讀福克納的作品,并因此克服了“因創作長篇小說而形成的憂郁癥”[2],于1981年7月在《文學界》發表題為《閱讀作為作家的福克納》一文。可見,福克納的文學作品不僅屬于美國,而且屬于世界。福克納的經典作品至今仍有當代價值,源于他對人類命運的思索。如著名翻譯家李文俊先生所言:“倘若全面綜覽20世紀世界文學,可以認為,他的作品既有現實主義具象的逼真性,也不乏現代主義的想象力、穿透力……若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他總的思想傾向,歸根結底,他是可以毫不遲疑地被列入擁護寬容創新、主張人與人之間享有平等的權利、贊成全人類相互理解與合作這樣一股人文主義大潮流中去的。”[3]而東方的日本先鋒作家大江健三郎,亦扎根于世界版圖邊緣的家鄉,在作品中融合了西方的異質文化,在其試圖“拯救日本、亞洲乃至世界的明天”的創作中[4],逐漸形成了表現人類普遍性內容的獨特文體。
兩位作家的創作都源自故鄉的想象,他們的多部帶有濃重自傳色彩的作品,都充斥著各自民族的歷史記憶與時代精神,并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從人類的希望和恐懼的角度把握人類狀況的自覺”[5]。福克納百科全書式的創作,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南方近現代歷史與現實;另一方面,又從總體上刻畫出西方現代人的困惑與苦惱,對他們的異化感、孤獨感表現出深切的關懷[3]3。在批判和反思家族與南方新舊交替的歷史中、在反種族主義的呼聲中,構建其約克納帕塔法的神話王國,不斷探索拯救人類靈魂的路徑;而大江則在與殘疾兒共生的個人體驗中,開始了對生命價值的拷問,表現出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擔憂,并由此確立了自己的文學主題與創作方向,從而走上尋求救贖自我與同時代人心靈與道德困境的文學之路。
因此,通過比較兩位諾獎作家的經典作品及其背后所隱含的創作意識,探尋其中的契合與差異,從而挖掘世界文學經典的本質,對了解世界文學的總體創作傾向有著深遠的意義,對我國的現當代文學也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一、聚焦時代、社會與人類的共同命運
福克納與大江的創作都因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而被更多的批評家與讀者所關注,從而使他們的“邊緣文學”逐漸步入世界文學舞臺的中心。兩位作家的創作,都在家族與歷史傳說的書寫中反映出他們對各自所處的時代、社會及人類命運的關注,而由此引發的危機感與責任感也成為他們創作的靈感之源。
福克納所處的南方,相對于南北內戰中勝利的北方,無論在地形學意義上,還是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都處于美國的邊緣。盡管如此,他的創作卻不僅有其南方性,而且具有更為廣泛的意蘊。雖然表面上看他的寫作主題仍然是有關南部的,但他卻具有世界主義的眼光,他最忠誠的對象是他的讀者,無論他們身處何時何地[6]。在他筆下,對像《在我彌留之際》中本德倫一家的窮白人、《八月之光》中的克里斯·默斯和《墳墓的闖入者》中的路喀斯·布香那樣受到種族歧視的黑人混血兒及像《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中的愛米麗、《八月之光》中的喬安娜和《押沙龍、押沙龍》中的羅莎那樣,遭受清教和父權思想迫害的南方白人婦女構成的邊緣群體表現出深切的關注,對其中人物的刻畫與拯救,體現了福克納的責任感與憐憫之心。他曾在隨筆《致日本青年》中指出:“我相信,主要是戰爭與災難在提醒人類,他需要保留一份有關自身的耐力與堅強的記錄。”[7]也正如他所言,福克納的整個創作生涯所做的筆耕不輟的努力,都在倡導人類的自由、平等、尊嚴與希望。他主張:“人類的希望存在于人類的自由,而作家所言的普遍真理的基礎,正是讓人類保有希望,這是一種權利與責任,只有在人類有資格、配得上得到它,愿意為得到它付出勇氣與犧牲并作出努力,然后又決心永遠保衛它的情況下,人類才能擁有自由。”[7]84而“那種自由必須是對全人類都適用的完全自由;我們現在不是得在膚色與膚色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之間作出選擇……僅在每類人之間選擇一小部分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7]84。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逐步擴大,席卷美國。黑人要求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的訴求導致黑白人之間摩擦不斷,尤其是福克納所在的南方,種族矛盾不斷激化。而身為作家的福克納以聚焦時代的眼光和極富同情的筆觸,寫就了如《去吧,摩西》《墳墓的闖入者》等一系列作品來警醒世人:任何人都有爭取自由與平等的權利,無關財富多寡,無關種族出身。對人類命運的思索與責任感使福克納的作品“超越時空的界限,而成為人類的共同財產”[8],從而成為世界文學中的重要一環。正如莫言在談及世界文學的本質時所指出的:
真正意義上的文學還是人類的文學,所描寫的是人類所共通的、普遍性的內容。因此,真正的文學,應當是超越民族、國家的……文學作品的寫作技巧、內容、語言,可以是某一國家、民族的,但是在更深的層次上,在思想、哲學層面上,應該是超國家、民族,甚至是超階級的,應該面向全人類共通的課題[9]。
這一點不僅突顯在福克納的文學作品中,大江也在創作中不斷思索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從邊緣出發,超越國家與民族,從整體上把握時代、表現時代,從人類的總體命運觀照未來。在《小說的方法》中,大江坦言:“在這樣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把握現代危機本質的方法就是必須站在邊緣上,不能以中心為導向。這一整體性的表現,必須從邊緣、從隱性結構方面來入手。”[10]薩義德也對大江深表認同:“離開中心,位于邊緣才是有創作性的。位于中心就永遠無法提出邊緣的問題。只有在個人選取的位置或脫離中心的位置才能做到。只有這樣,世界上具有相同經驗的人才有相互接觸的可能。”[4]431大江20世紀60年代的作品《廣島札記》就是通過記錄自己數訪廣島的所見、所思,表現出其“從邊緣出發的指向”,從中透視現代社會乃至現代文明,探索人類的未來命運[11]。而獲諾貝爾文學獎后的大江,依然保持對時代精神與時代危機的敏感度,始終將其創作聚焦于時代與社會的突發事件與危機。他最長的一部小說,也是他晚年非常重要的一部小說《空翻》,就是由當時奧姆真理教事件引發的思考。他在自己的隨筆中反思其創作緣起時寫道:“如果在今天的日本出現救世主式的領導人,而且他也棄了教的話,那么他的信徒們會怎樣生存下去呢?與奧姆真理教事件并行考慮的時候,小說的構成就開始在我心里有了雛形。”[4]49從對“救世主”的期待中可見,大江對日本社會和國家的深切關注與擔憂,他的作家責任感使他超越了國家與民族,在后期的創作中與日本日趨活躍的國家主義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大江“晚年的工作”長篇小說系列的最新作品《晚年樣式集》,也是在“3·11”東日本大地震及福島核電泄漏事件之后,因他對日本政府的反應失望至極所創作的。這是時隔半個世紀,在繼《個人體驗》和《廣島札記》的創作后,大江晚年在新世紀背景下再一次在作品中重申自己的反核立場。小說中的“我”通過參加反核游行與演說來抗議日本政府繼續啟動核電站和將日本核電出口外國的決議,從中也表現出大江對日本“3·11”核泄漏事件給人類生存帶來的潛在威脅表示深切的擔憂。
由此可見,對時代與社會的關注乃至對人類未來的危機意識是大江創作出其獨特文體的根本動力。而大江不同于其他日本的傳統私小說家之處在于,他將對自我痛苦體驗的關注轉化為對所處的社會與時代、人類的苦難與危機的擔憂與思考。而這種危機意識來源于他的責任意識,即對自己、對他人、對世界的責任[12]。
二、從個人體驗中透視人類的困境與危機
雖然福克納與大江都身處邊緣:福克納置身美國的“邊遠南地”,大江根植于世界版圖邊緣的日本,但兩位作家都在各自所處的社會轉型時期,在新舊歷史交疊的書寫中,從個人的體驗出發,透視人類的共相,揭示出當下人類普遍的生存困境與危機。
福克納認為,他真實的自我,多變、朦朧而又明確地體現于他的小說中。“福克納在作品中從現代主義者的立場,發現了他個人和地區的根基的藝術價值,學會運用弗洛伊德的理論來剖析他自己和南方地區在文化上的弊端,第一次認真地把有關南方的歷史和文化問題當作自己的創作題材。”[13]從福克納的整個創作生涯中,都依稀可見他的家人和家族歷史的影子。他將自己目睹的南方社會與文化的巨變、國家、種族與傳統的沖突都融入自己的創作中,而這一切又促使他考慮歷史、分析當前世界可怕的混亂,并且展望人類的未來[13]65。被福克納自稱為“最輝煌的失敗”的小說《喧嘩與騷動》似乎也取材于他的童年時代,是他創作生涯中最為鐘愛的一部,因為據此他發現了“組合成了世界的種種偶然——愛情、生存、死亡、性愛與憂傷,以完美比例糅雜在一起構成了一種恢弘的永恒之美”[14]。他自己也承認:“我就是《喧嘩與騷動》中的昆丁。”[15]而在這部作品中,昆丁似乎代表著福克納矛盾的自我,同時也代表著南方處于戰敗與轉型時期的青年絕望與惶惑的精神困境。他們迷茫、缺乏自我身份認同,沉迷于歷史的記憶與榮耀中無法自拔,對現實中的巨變充滿了排斥與恐懼,遭受著痛苦的精神危機。然而,福克納筆下人物所面臨的精神困境:自我懷疑、心靈的扭曲與異化、戰爭的創傷、家族毀滅性的影響也并非美國的南方所特有,而是至今人類仍共同面臨的心靈困境。
福克納也在對黑人和白人故事的書寫中,洞察到種族危機給人類帶來的矛盾與不安,是人類陷入互相傷害與詛咒的根源。他的晚期作品中,不僅敘述手法和敘述角度有所變化,其主題也與以往有著巨大的差異。直到1942年,福克納不再沉浸在對南方歷史、傳奇與神話的浪漫想象之中,而深切地意識到不得不放棄從前的價值觀[16]。從《去吧,摩西》(1942)到《墳墓的闖入者》(1948)等作品中,都投射出他對白人與黑人的種族矛盾和黑人群體的關注,而這至今仍為引發美國乃至世界政治爭端的癥結所在。他的第十三篇長篇小說《去吧,摩西》被稱為黑人的“人權宣言”,也被稱為“福克納的最誠實、個人身份暴露最多的小說”。桑奎斯特這樣評述道:
《去吧,摩西》以兩個有力和生動的例子——艾薩克·麥卡斯林和路喀斯·布香——說明了這一點,對這兩個人物,福克納似乎殫精竭慮,將他們處理成兩個既不同,又有著密切相關并失敗的形象。艾薩克對遺產的放棄,很像作者福克納自己的情況,因為在想象那種繼承的負擔時,他的藝術力量不再起作用……而再現于具有表現力的尊嚴,他在路喀斯身上很快發現了這種尊嚴[16]14。
在福克納眼中,無論是黑人還是白人,都應該具有選擇權及自由平等的權利,擁有作為“人類”所應有的尊嚴。《去吧,摩西》中的艾薩克深刻地意識到了自己所屬的麥卡斯林家族的腐朽,而選擇放棄繼承與生俱來的家族產業:“他沒有任何財產,也從未渴望擁有,因為土地并不屬于某個人而是屬于所有人,就跟陽光、空氣和氣候一樣。”[17]由此,亦反映出作家福克納呼吁作為類存在的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思想。此外,在看待種族危機的問題上,他提出:無論任何膚色、任何種族都應具備“正直、尊嚴、道德和社會責任”[7]110。在《墳墓的闖入者》中,白人文森·高里被殺,而黑人路喀斯僅僅因為其皮膚是黑色而被捕,并面臨私刑的懲罰。福克納通過白人男孩契克對他的拯救,以白人律師史蒂文斯為自己的發言人,提出化解種族危機的一己之見。正如他自己在提及《墳墓的闖入者》這部作品的主題和創作意圖時所言:“它的主題是關于黑人白人之間要有親密關系……前提是南方的白人,比北方、比政府、比任何人都虧欠黑人更多,因此必須對黑人負責。”[14]213而隨著他對種族危機認識的深入,他也進一步指出:“我不相信人應該向上帝祈求人類正義與種族解放。我相信他可以使上帝確信,不朽的個人尊嚴遠比不公正更持久,在個人尊嚴的面前,家庭、家族、部落談到自己時,應該以人類種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面目出現。”[7]110-111
如果說在福克納個人與家族歷史的記憶中透射出其對人類的精神危機與種族危機的關注,那么無獨有偶,大江也有意識地把自我和包括殘疾長子光在內的家人寫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安藤始曾對此評論道:“大江的文學,出發的基點是反私小說的。但現實中……大江的小說是在他自己及周圍發生的事情的基礎之上,發揮其想象力書寫而成的。”[18]大江在創作中融歷史與現實、想象與真實于一體,突顯出他作為日本“新時代文學旗手”的歷史使命感。與福克納大相徑庭的是,大江在對個人體驗的書寫中,透視和反映個人、時代、社會、國家乃至人類所面臨的殘疾危機與核危機。與殘疾兒共生的體驗“使大江健三郎的文學在想象力的推動下,突破了‘核時代’的現實,進入了與‘弱者’共生的新的作品世界”[12]320。大江不同時期的作品,如20世紀60年代的《個人的體驗》、90年代的《靜靜的生活》及“最后的小說”《晚年樣式集》都深刻地印證了這一點。
《個人的體驗》是大江獲得諾獎的代表作之一,是大江成為先天頭蓋骨缺損的殘疾嬰兒的父親之后,以自身的體驗寫就的一部自傳性很強的作品。從主人公鳥的身上可見,大江如何從最初試圖逃避焦慮、不安的痛苦,到決心與殘疾兒共生的心路歷程。而大江并未將作品的立意局限于私小說層面,而是提升到人類共同面臨的困境來思索。如主人公鳥所言:“即使是在個人的體驗里面,只要一個人漸漸深入那體驗的洞穴,最終也一定會走到看得到人類普遍真實的近路上。”[19]大江甚至由新生嬰兒的頭部畸形聯想到了人類所面臨的冷戰與核危機。小說的第十章中,大江有意提及赫魯曉夫重新開始核試驗的消息。大江借由主人公鳥表達了自己對核危機的關切:“核武器的問題我一直很關心的,我和朋友們的斯拉夫語研究會唯一的政治活動,就是參加呼吁廢止核武器。”[19]221他還將在日比谷公園參加廢止核試驗的集會人員稱為“能把地球的命運放在自己肩上的家伙”[19]232。由此可見,大江對人類所面臨的潛在核危機的擔憂。
而大江創作于90年代的長篇小說《靜靜的生活》則是對從60年代創作的《個人的體驗》和80年代創作的《新人啊,醒來吧》《人生的親戚》等一系列品的延續,是他與殘疾兒共生的又一人生階段的真實寫照,也是他嘗試以女性視角寫作的一部意味深長的作品。然而,在這部作品中,大江進一步表現了對人類普遍存在的殘疾危機的關注與拯救意識。大江曾這樣介紹這部作品的創作緣起:
總之,我們的家庭確實從同時代里掙扎著維持了下來。直截了當地說:有著智障兒子的這個家庭,在社會里是易于受到傷害的……長子往來于護理學校高年級那段時期,聽說住宅附近好像有少女遭到粗暴襲擊,我們便感到不寒而栗,被不安所攫取,盡管沒有任何根據,卻擔心兒子這個一直被我們認為非常純潔的少年還有另一個側面,該不是在什么地方襲擊了那少女吧。如果這是真的,我們家庭便會處于與社會完全對立的境地。我還想到在那之后的、社會和個人生活的關系將會出現的不安定因素以及我們面臨的危險。不久后,長子的妹妹,發現了實際干下那事的犯罪者,是一個溜到我們這個街區來的壞家伙。于是我感到心情舒暢,在家庭里與長子之間的關系,也沐浴著新的光輝。而以此為原型寫出的小說,就是《靜靜的生活》[20]。
這部作品講述的是父親應邀去美國加州大學做駐校作家,而生活與創作中的雙重困境,使父親陷入抑郁的狀態,因此需要母親陪同前往。家中的妹妹小球,毅然承擔起照顧有智力障礙的哥哥的責任。大江在作品中通過女兒小球的視角,透視了殘疾兒父母這一邊緣群體的痛苦和困境。在小球所參加的為殘疾者舉辦的各種聚會中,不同家庭背景、性格迥異的殘疾兒的父母們,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母親大多“沉郁但非常堅毅”,而父親們卻“看起來怯懦而陰暗”,與殘疾兒共生的經歷使這個群體在“人格特質上留下了陰影”[21]。而身臨其境的小球,心中卻有一個聲音反復回響:“即使前景黯淡,不更應該提起精神突破障礙嗎?”[21]51大江通過小球發自內心的吶喊,反映了這個群體雖身處困境,卻勇于直面的勇氣。而小球以帶哥哥小鳥回四國峽谷山村參加大伯父葬禮為契機,解開了長久以來心中對父親和哥哥的困惑。她通過祖母和伯母對父親兒時山谷生活的記憶,進一步了解到,父親一直以來將四國的森林峽谷作為祈禱人類靈魂得到救濟的場所;而通過祖母與哥哥的交談,意外地發現,哥哥所做的以《棄兒》為主題的曲子并非為憐惜自身的處境而作,而是有著“拯救棄兒”的深刻寓意。如大江在這一章結尾所寫的那樣:“如果這個行星的人都是棄兒的話,小鳥作曲所表現的精神,是何等的偉大啊!”[21]85這突顯出了大江希望通過創作來拯救人類心靈的愿望。正如他在《曖昧的日本的我》①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用英文作題為“Japan,The Ambiguous and Myself”(可直譯為“日本,曖昧與我”)的演講,日譯版題為:『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曖昧的日本的我”)與1968年川端康成獲獎時,所作題為『美しい日本の私』(“美麗的日本的我”)形成鮮明的對比。的演講詞中所言:“作為立足邊緣,遠離中心的存在,我愿不斷探尋……希望能為人類的治愈與和解作出自己的貢獻。”[22]
薩特曾在與本尼·萊維的對話錄《今天的希望》中指出:“希望是人的一部分;人類的行動是超越的……在行動的方式中始終有希望在。”[23]也就是說,希望是改變未來的支配力量,它賦予人類走出困境、自我拯救的可能,而福克納和大江在創作中也都意識到了希望之中所蘊藏的力量。無論是福克納的《押沙龍,押沙龍!》,還是大江的《個人的體驗》《靜靜的生活》及《晚年樣式集》,兩位作家都在令人近乎絕望的困境中看見希望:福克納在《押沙龍,押沙龍!》中,通過昆丁這一人物見證了舊南方的歷史,表達了自己對新南方的認同與期待:“你看,我寫下希望,而不是思索。因此,就讓它是希望吧——那就是讓理應受到譴責的人無法逃脫,讓其他人不再缺少憐憫。”[24]由此,體現出福克納對人類所應具有的責任感與憐憫之心的渴望,期待以他的作品引領人們走出精神困境。而大江在《個人的體驗》中,似乎也通過鳥的國際友人戴爾契夫在字典上寫下的“希望”二字,找到解除人類共通的精神與道德困境的答案;在《靜靜的生活》中表達了與殘疾兒共生,希望猶存的心境;在他晚年“最后的小說”《晚年樣式集》中,亦“揭示了被災難和煩惱陰影所覆蓋的人類的希望”[25]。這也是大江與福克納文學創作的契合之處:他們都放眼未來,通過充滿希望的作品,給絕望中的人類以面對困境、繼續生存的精神支柱和勇氣,進而探尋人類的自我救贖之路。
三、異質文化文本中折射出的和平意識
在福克納和大江的創作中,都有著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傾向。同時,他們各自根植于東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現代書寫中,亦突顯出他們的和平意識,引領人們走出戰爭危機帶來的陰霾。
如果說《去吧,摩西》《墳墓的闖入者》體現了福克納對種族危機的關注,那么他歷時10年創作完成的鴻篇巨制《寓言》,則充分體現了他的和平意識。這部作品將背景設置于現代戰爭這樣一個高度濃縮了人類現代危機的社會權力場域,其反戰意圖昭然若揭,可謂福克納畢生至高、至理、至純的一份人本主義宣言[26],也是他為反對人類的戰爭、倡導世界和平所做的最大的一次冒險。骨子里,福克納是地方性極強的作家,然而在這部作品中,他卻選擇離開自己所熟悉的密西西比,而選擇美國以外的法國作為故事背景,以他親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題材,使故事的背景擴展至整個歐洲和北美,甚至借特定的歷史將目光投射于遙遠的非洲,體現出福克納打破身份疆界、超越南方地域主義的國際視野和恢弘氣勢[26]24,映射出他探索復雜的人性和人類自身困境的決心。他將全人類視為和平的共同體,在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聲中,在善與惡的抗衡、權利與道德的較量中,堅信人類信仰與堅韌的可貴,體現出他對人類生命的尊嚴與價值的珍視。這一點深刻的映射于其作品的立意中,突顯出他對人類未來和平的希望與夢想。在《關于〈寓言〉的一點說明》中,福克納指出:
若要結束戰爭,人類就必須找到或是發明某種比戰爭、比人的好戰性、比人的不顧一切追逐權力的欲望更有力的東西……應該教會所謂的權利聯盟去憎惡戰爭,不是為了道德或經濟上的理由,也不是單純為榮辱的問題,而是因為他們懼怕戰爭,不敢冒險發動戰爭,因為他們知道在戰爭中的自己——不是作為國家、政府或是意識形態,而是僅僅作為簡簡單單易于死傷的人類——會首先被消滅[7]270-271。
福克納在《寓言》這部作品中,表達出對消滅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期望,對深不可測的人性與極端復雜的人類境遇的深入思考。在他看來,戰爭是“迄今為止人類發明的最為昂貴、最為致命的罪惡”[26]320。他試圖通過這部作品,提出化解戰爭危機的途徑:即克服人類普遍存在的好勝心與權力欲,同時銘記戰爭中國家與個人需要付出的慘痛代價,永遠對戰爭懷有厭惡與恐懼之心,珍視人類生命的價值。正是這部將人類自身視為和平基點的《寓言》,使福克納的創作最終完成了“從南方到世界中心的跳躍”[27]。
而在東方的日本,作為反戰先鋒的大江,其隨筆《廣島札記》亦表現出對戰爭的憎惡,試圖書寫對人類和平的構想。廣島也是他個人體驗之外的又一創作源頭,成為他“最有分量的、最具影響的存在”[28]。《廣島札記》創作于大江的殘疾兒誕生不久,而畸形兒的誕生與原子彈爆炸在大江創作中被他視為同樣的課題:它們都是大江對人類在無法抗拒的災難面前,對人的存在方式與自我救贖方式的思索。他兩次訪問廣島,在個人面臨與畸形兒共生的人生抉擇和友人自殺等人生困境中,寫就的反映廣島人堅強意志、倡導反戰反核思想的調查記錄,體現出他對人性的關注;從廣島人經受的災難中,反思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倡導人類走向和平。
在《廣島札記》中,大江隨重藤院長深入了解了原子彈受害者的體驗和感慨,在對未得到國家救助的死亡病例的追訪中,對廣島人身上所具有的“勇氣、希望、誠實”等人類共同的品質有了更深的體會。通過對其中一位因廣島原子彈爆炸而患白血病的青年的死,進行了從個人到國家乃至人類危機的深刻反思,提出對日本政府發起戰爭的錯誤選擇的質疑。一位經歷了原子彈爆炸的青年,在接近20歲生日的時候發現自己患上白血病。他并未像其他癌癥患者一樣,在痛苦中等待死神的降臨,而是樂觀的生活和工作。而最終,這個青年還是在受盡一切病痛的折磨后死去了。大江在作品中,表現出了對這個青年之死的惋惜與憤慨。他寫道:“死去的青年在遭到轟炸時,只有4歲……就是這個幼兒在20年后,以他自己的肉體為國家承擔了責任。也許他盡管是一個幼兒,只是因為他是這個國家的一員,就不得不被卷入到這個國家最壞的選擇中去。難道作為一個國家的國民竟然如此悲慘!”[11]116而大江所謂的“國家最壞的選擇”指向的正是日本政府發起侵略戰爭的選擇,而最終政府所應承擔的責任,卻由像死去的青年這樣的廣島人來承擔。可見,與當時日本政府對戰后責任曖昧的態度正相反,大江對此有清醒認識,并以反省的姿態面對史實。繼而,他在反思國家戰爭責任的同時,又將目光投向人類的未來。
而隨著創作的深入,大江在其70年代創作的《洪水涌上我靈魂》(1973)、80年代的隨筆《生的定義》(1985)、90年代的隨筆《廣島的“生命之樹”》(1991)及新世紀初出版的《定義集》(2012)等作品中越來越明顯地投射出了大江反戰反核的和平意識,體現出他對現在和未來的和平的期盼。在寫給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信中,他表達了對自己民族的反思:“我們這樣的國家,經歷了戲劇性的激蕩曲折的現代化,留下了各種各樣的深刻創傷,這個世紀的前半期,給亞洲各國人民造成了傷害,導致了世界上首次由于核武器而遭受的災難,是自身內部造成的,這是關系到未來的一種創傷。”[4]304他認為,在未來日本決不能實施核武裝,必須創造性地提出獨立面向亞洲和世界的長久和平構想。這是有關人類的構想,也是對能夠延續到未來的人性的思考。他希望:“通過我們這流通范圍不大的語言,去構想我們自己的未來人性,并向亞洲、東西歐、南北美發出積極的倡導,我夢想著這一天的到來,并為此做好了準備。”[4]307
據此可見,身處不同時代和文化背景的福克納與大江,在各自的創作中似乎都突顯了一種“倡導和平、寄希望于未來”的文學品格,從而“呼喚全人類的愛與良知,倡導人類擁有同情、犧牲與忍耐的靈魂,承擔起應有的道義和責任”[29]。他們都發出了有別于同時代本土文化圈的其他作家的吶喊聲,引領人類找到通向自我救贖與美好未來的道路。
四、結語
在源遠流長的歷史歲月中,無數思想家不折不撓地綿延著一個輝煌的理想:建設一個讓所有的人、所有的群體、所有的民族共享和平和繁榮,不再恐懼、仇恨,不再殺戮,不再有戰爭的和諧幸福的美好家園[30]。西方的福克納與東方的大江在各自的創作中,都繼承和突破了各自民族的文學傳統,從歷史與現實的神話般的想象中,探討人類內心的沖突與精神危機,思考人類共同面臨的困境,探索拯救人類心靈的良方。福克納和大江因對人類命運的關注所產生的危機感、責任感、和平意識及對人類未來的信心,也使他們充滿希望的作品兼具了理想主義與治愈性,超越了時代,體現了當代世界文學話語的共性與傾向,對我國現當代文學有一定的啟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