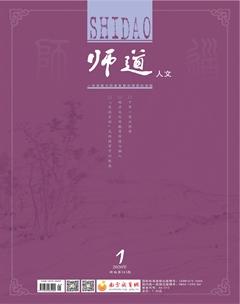任務驅動下的整本書閱讀不可替代廣泛的課外閱讀
楊先武
近兩年,隨著《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版)》的推出,語文教壇正興起一股整本書閱讀的熱潮,并產生了一些值得推廣的經驗。必須肯定的是,整本書閱讀對于改變學生閱讀面十分狹窄的狀況和培養學生的語文核心素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筆者以為,單靠把整本書閱讀列入“學習任務群”并將其納入語文課堂教學的范疇,所產生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對于當前方興未艾的整本書閱讀,需要進行冷靜的分析,不可將其意義拔得太高。因為即便把教材規定的“整本書”讀得再深再透,對于知識貧乏和精神“缺鈣”的學生來說,也不過是杯水車薪。只有在整本書閱讀的過程中,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在課外讀更多的好書,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部編本”語文教材的總主編溫儒敏先生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談到:“語文課怎樣才算成功?一定要延伸到課外閱讀,讓學生養成讀書的生活方式。”語文課程標準也明確指出:“要重視培養學生廣泛的閱讀興趣,擴大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高閱讀品位。提倡少做題,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讀整本的書。關注學生通過多種媒介的閱讀,鼓勵學生自主選擇優秀的閱讀材料。”顯然,課標不只是強調“讀整本的書”,還要求“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如果沒有把語文課“延伸到課外閱讀”的意識,并讓學生享有“自主選擇”的權力,即便將整本書閱讀列為學習任務,也很難解決學生的閱讀面過于狹窄的問題。
關于讀書,古人有太多精辟的論述,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腹有詩書氣自華”“立身以立學為先,立學以讀書為本”“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等,無不說明讀書的重要性。然而,我們的教育(尤其是語文教育)似乎忘記了這個簡單的道理,對于擴大學生的閱讀面,將課內閱讀向課外閱讀延伸,至今未予足夠的重視。在整本書閱讀被列入“學習任務群”后,許多教師也只是把它當作一項“任務”來完成,而不是以此來帶動學生去閱讀更多的“整本書”。還有的教師甚至禁止學生在課外閱讀不屬于指定范圍的書,其理由是影響“正常的”學習。這種現象是極不正常的。要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必須開啟課外閱讀的大門。只有通過大量的可以“自主選擇”的閱讀,才能積累豐富的語文知識,提高語言運用的能力,并從書籍中吸收優秀文化的乳汁,促進學生的健康成長。
筆者從教近40年,對課外閱讀的作用深有體會。上世紀80年代初,筆者剛走上教學崗位,挑起了高中語文教學的大梁。那時正值我國當代文學創作的高峰期,一大批優秀作品相繼問世。作為一名語文教師,我覺得應該讓學生分享這些收獲。于是,每當看到十分感人的作品,我就會向學生介紹。我曾連續利用兩個星期的讀報時間給學生朗讀中篇小說《高山下的花環》。由于農村中學沒有圖書館,很難讀到中外名著,我便把自己的藏書借給他們閱讀。我還組織學生分別訂閱了不同的文學刊物,如《人民文學》《上海文學》《作品》《長江文藝》《雨花》《延河》……每到一期,我都先睹為快,然后向學生推介其中的優秀作品。那時候,還沒有十分激烈的高考競爭,也沒有多如牛毛的復習資料,這使我的語文教學得以與課外閱讀緊密結合在一起。在我的引導下,學生們對課外閱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僅在課堂上學得很輕松,而且在課外盡情享受閱讀的樂趣。后來,我從農村中學調到縣重點中學任教,更是大膽地堅持了這種做法。
語文的涵蓋面最為廣泛,“語文學習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因此,語文教學必須盡可能地拓展學生的閱讀空間。這便要求教師減輕學生的負擔,為他們創造課外閱讀的條件。基于這一認識,我在語文教學中堅持“三不”:不加班加點,不搞題海戰術,不布置與課文內容或與考試相關的課外作業(語文練習在課內完成)。我對學生的要求除了寫日記或隨筆(不限字數),就是每天抽出一定的時間閱讀課外書籍。為了得到家長們的支持,我還印發了“致家長的一封信”。為了避免學生漫無目的地閱讀,我給他們推薦了一些閱讀書目,但不做硬性規定。在以文學名著為主的前提下,只要是內容健康并具有一定文采的書,就允許學生自由閱讀。無論是執教高中還是初中,我都堅持開展課外閱讀,甚至不惜每周拿出一節正課讓學生閱讀課外書籍,每當輪到上語文晚自習,我總會留出一半時間讓學生讀課外書。這種做法即便在中、高考復習階段也從未間斷。
廣泛的課外閱讀并未像某些人擔心的那樣影響學生的考試成績,而是提高了他們的語文水平,并在高考、中考中喜獲豐收。而學生們在寫作上的進步則更為明顯,經常有學生的習作見諸語文報刊,先后有數十位同學在市級以上作文競賽中獲獎(其中一人在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中獲獎)。這些獲獎作文大都與課外閱讀有著密切的關系,請看下面的一例。
恐 悒 之 門
——讀卡夫卡
楊 朗
鄭重其事地談論弗朗茨·卡夫卡是相當困難的事,有些自譽為kafkaian的人常常不著邊際地大發議論,實乃不懂裝懂。我之論卡夫卡,也只能算是胡侃。
讀卡夫卡的作品,總有一種無法驅逐的感受,他的書中有如拉奧孔的蛇一般密實地纏繞著的郁悒與恐懼。讀者一旦不經意地推開了卡夫卡這扇大門,等待他的是無底的地洞與無邊的城堡,于是,讀者們跑呀跑,他們試圖逃出此地,但卡夫卡卻設置了更多的陷阱。他們感到空虛與恐怖,好像一只無頭的蒼蠅亂竄。在跑完一段后,讀者們歇了下來,可令人心悸的是,他們又回到了原地,就在準備歇斯底里狂嚎時,他們發現,卡夫卡又送他們出來了。
這是為什么呢?
當我們把這個問題帶給格里高爾·薩姆沙時,他無奈地說:“沒辦法,我成了一只甲蟲,不能上班工作了。”讀者們可能會出于憐憫薩姆沙而扇卡夫卡一耳光,為什么把這個可憐的人變成甲蟲?卡夫卡怏怏地說:“為什么?我就是他!”所以,讀者們再一次陷入了沉默。是啊,卡夫卡真值得憐憫。那你為什么不抗爭?從某個方面講,卡夫卡是在用筆與命運抗爭,然而,這所謂的resist既非葉甫蓋尼·奧涅金式的,也非牛虻式的,他是對自己這場抗爭感到前景淼然的,即他所謂的“無力改變這個世界”。他帶給人們的是無盡的恐悒,這恐悒是如此強大,以至于它產生的向心力把人向遠方甩去,最終甩到了卡夫卡世界的核心。人們此刻仰頭望到的已不是城堡了,而是羅斯曼、薩姆沙、K合體的卡夫卡了。卡夫卡已藉此表明其作品的自喻性,K的困頓惘然即是他的觖望。原本的卡夫卡無非是想借筆宣泄一下,哪知,揮筆消愁愁更愁。現在,讓我們再顧眄一下吧:弗朗茨·卡夫卡三度訂婚三度離婚,他在當時默默無聞,性格孤僻。由此,你想讓卡夫卡成為蕭伯納,倒不如叫斯特恩變成薩克雷,低凹的溝谷是不會造就高聳的峻峰的。
實際上,卡夫卡是有可能走到現實主義道路上的(從他早期的作品看得出來),但是他在創作《美國》時擱筆了。因為他感覺這是“對狄更斯的直接模仿”,而他并不想做大師們的盲從者、傳統的衛道士,所以,他改變了風格。長期的郁悶使他扭曲了世界,夸大了事物。就連卡夫卡也驚訝的是,他成功地把這種事物觀帶進了創作,一躍而成為表現主義作家。所以,他藝術的內核和外殼,分別是嚴肅和荒誕的。他不寫人物是坐著挨了槍彈,爬著掉進溝里,抑或是站著被砍了頭。讀者所見到的只是忙碌無所終的人們,他們有一個通性,就是無端的恐懼,這個“無端”是對初識卡夫卡的人講的。但即便是熟識,看了卡夫卡的書后也是心有余悸。
讀卡夫卡的作品,須逾越兩個界限:一是手法,二是含義。實際上,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薩特的《禁閉》以及與那些自以為是的未來主義者們相比,卡夫卡是通俗的。他只是走上了一條在當時看來極其怪異的道路,由于這條道路滿是崔嵬奇石,異枝怪草,卡夫卡也遲疑不前了。他也許開始對自己的道路有點沒信心了,不可預料下面有什么情況。所以,在彌留之際,他瘋狂地要求銷毀自己的作品,幸虧好友勃羅德違背了他的遺愿,卡夫卡的文章才得以傳世。這兒有一個不被批評家注意的問題,就是在其恐悒的陰云籠罩下的諸多角色似乎缺少鮮明的個性。一個K也就是約瑟夫·K,一個約瑟夫·K也就是格里高爾·薩姆沙,不僅是《變形記》里的薩姆沙變了形,其他的人亦如是,整個世界亦如是。這樣,《卡夫卡全集》更像一個人的悲慘世界。
卡夫卡由于種種原因,不幸而又有幸地走上了文學道路。他努力使自己不同流合污,茫然地揭示了污濁之世。哦,抗爭的孤獨者,這是否就是你的抗爭?正直的猶太人,這是否就是你的正直?
這是楊朗同學2001年在《光明日報》《教育時報》《中學生閱讀》聯合舉辦的全國中學生讀書征文大賽中的獲獎之作。從文中不難看出,作者讀過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文章所提到的外國作家和文學名著中的人物(如蕭伯納、斯特恩、薩克雷、喬伊斯、拉奧孔、葉甫蓋尼·奧涅金、牛虻等),對于很多人來說都會感到陌生。而作者對卡夫卡的了解更是十分全面,他對卡夫卡的作品并不是一味地贊譽,或只是重復批評家們的觀點,而是有著自己的看法:“這兒有一個不被批評家注意的問題,就是在其恐悒的陰云籠罩下的諸多角色似乎缺少鮮明的個性。一個K也就是約瑟夫·K,一個約瑟夫·K也就是格里高爾·薩姆沙,不僅是《變形記》里的薩姆沙變了形,其他的人亦如是,整個世界亦如是。這樣,《卡夫卡全集》更像一個人的悲慘世界。”無論這種見解是否正確,其個性化的解讀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作為一名高一年級的學生,能寫出如此文質兼美的佳作,與其愛好讀書是分不開的。
實踐證明,多讀多寫乃學好語文的不二法門。沒有大量的閱讀,學生的積累不可能很豐富,語文水平也不可能很高,充其量只能成為應試高手。誠然,語文課堂教學是培養學生語文能力的主陣地,語文教師必須在課堂教學上多下功夫,提高效率。但課內閱讀的范圍畢竟是十分有限的,無論課堂教學多么高效,也只能局促于狹小的天地。雖然近幾年整本書閱讀已越來越受到重視,但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并未給學生以太大的自由。由于整本書閱讀是在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因此不一定能讓學生產生濃厚的興趣,倘若處理不當(如過于“課程化”并與考試掛鉤),反倒會使整本書閱讀成為他們的一種負擔而產生排斥心理。只有激發學生的興趣,使閱讀成為他們的愛好,在課外讀大量的好書,并按課標的要求,讓學生“自主選擇優秀的閱讀材料”,才能真正收到成效。既然課堂教學應該讓學生享有自主權,為什么課外閱讀不能讓他們享有自主權?竊以為,這種享有自主權的課外閱讀,遠遠勝過任務型的“整本書閱讀”。當然,教師對課外閱讀應進行必要的引導,不應放任自流。但這種引導只能是宏觀把控,而不能嚴加限制。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說:“讀名著也好,讀當代文學作品也好,或者讀數學、生物,要允許學生自由安排,允許多樣化,通過自由閱讀使每個人發現自己的興趣與特長,通過自由選擇造就富有個性差異的人才。”(見《中國教育報》2004年5月13日《自由閱讀才能享受讀書的趣味》)
總之,忽視廣泛的課外閱讀,僅把整本書閱讀當作“任務”來完成,是難以收到明顯效果的。筆者并不否定整本書閱讀的必要性,而是主張既要重視列為課程任務的整本書閱讀,更要重視學生享有自主權的課外閱讀(即便達不到溫儒敏先生所說的“海量”,也應達到一定的數量)。雖然整本書閱讀開闊了學生的視野,有利于克服閱讀的盲目性和掌握正確的閱讀方法,但其局限性十分明顯,無法替代廣泛的課外閱讀。只有當整本書閱讀不再被“任務”驅動,而成為學生的良好習慣和自覺行為,才算真正實現了這一課程目標。語文教學必須打開由課內向課外延伸的通道,實現課內和課外雙翼齊飛。否則,整本書閱讀就難免走過場和流于形式。
(作者單位:湖北荊州市實驗中學)
責任編輯 ??黃佳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