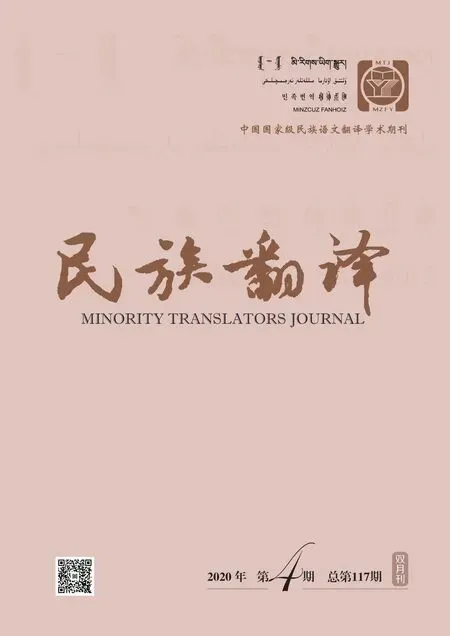李正栓《倉央嘉措詩集》英譯本的譯者行為批評分析
⊙ 高 博
(南開大學濱海學院公共外語教研室,天津 300270)
一、引言
倉央嘉措詩歌既是藏民族文學史上的瑰寶,也是中華民族文學史上的奇珍。自清朝康熙年間以降,倉央嘉措詩歌流傳至今已有三百余年的歷史。“這些詩歌先是在藏地流傳,后來又在漢地傳唱,再后來更是走出國門,漸次蜚聲海外”。[1]1就其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而言,倉央嘉措詩歌最早的英文譯本出現在20世紀初期,一些帶有殖民背景的學者型官員在自己介紹西藏歷史文化性質的著作中提及了一些,然而只是蜻蜓點水,掛一漏萬。直至1930年,我國著名藏學專家于道泉教授翻譯的倉央嘉措詩歌譯本問世,是為海內外第一個正式刊行的藏、漢、英三語對照譯本。此后,又有藏族學者W·泰森英譯的倉央嘉措詩歌74首。2015年初,李正栓和王密卿兩位教授共同翻譯了倉央嘉措詩歌,即《漢英對照倉央嘉措詩集》(以下簡稱為《詩集》),這個譯本為國內第三個英譯版本。然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詩集》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包括英譯倉央嘉措詩歌66首,這是學術界比較認同的數量和內容,其譯者是李正栓教授;第二部分的英譯工作由王密卿教授完成,該部分涉及5首托名于倉央嘉措的詩歌作品。這些作品并非一定為倉央嘉措本人所作,但卻流傳深遠,影響廣泛。本文旨在對李正栓教授的譯者行為進行具體詳實的考察,因此,在文本材料的選擇分析上僅以《詩集》的第一部分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二、譯者行為批評理論及“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
翻譯批評包括許多途徑,而“對譯者進行批評”是其中比較重要的研究視角之一。在譯者批評中,以譯者行為作為批評焦點的“譯者行為批評(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顯然是對傳統譯者批評內容的豐富和補充,也是對傳統譯者批評途徑的突破。[2]具體而言,“譯者行為”是一個基于社會視域下的概念。它主要是指“社會視域下譯者的語言性翻譯行為和社會性非翻譯行為的總和。”[2]91以譯者為切入點并以社會視域為批評維度而對譯者行為所做的批評性研究,構成了譯者行為批評的主要內容。譯者行為視域下的文本批評主要關涉的是譯者對原文和譯文的支配關系,評價譯者行為,探討的是意志體譯者行為的合理性,其行為越有理性,就越能被社會理解,而理性行為下譯文的接受程度也就越高。[3]簡言之,譯者行為視域下的翻譯批評是將“文本批評”與“譯者批評”有機地融為一體,在這其中,譯者的語言人和社會人角色均被納入到考察譯本的理性范圍之內。
譯者行為批評理論構建了穩定的評價模式,即“求真—務實”連續統(Truth-seeking and Utility-attaining continuum)評價模式。在這里,“求真”指的是譯者為了實現讀者/社會的目標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的行為;“務實”則是指譯者在對原文語言所負載意義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礎上為滿足務實性需求所采取的態度和方法。[4]“求真”和“務實”是一體的,它們處在一個漸變的連續統上,二者既相互區別又融為一體。具體來講,“求真”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原文的意義;而“務實”則更多關注的是讀者的需求。兩者的關系表現為,“求真”是“務實”之本,“務實”是“求真”之用。然而,具體到現實的翻譯實踐當中,譯者為了讓譯作順利地進入目標語社會的流通領域,往往會在“求真”的基礎上更多地考慮到譯文的“務實”情況,亦即將“務實”作為更高的目標。據此,一般來說,“以求真為本,以務實為上”就構成了譯者在翻譯活動中通常遵循的行為準則。以下,筆者擬利用“譯者行為批評理論”作為研究框架,并從翻譯內和翻譯外兩個層次對李正栓所譯的《詩集》進行具體剖析,以期在此基礎上對其譯者行為做出客觀且公允的評價。
三、《詩集》譯者李正栓的譯者行為批評分析
(一)譯內行為分析
譯者的“譯內行為”主要涉及“語言文字的轉換和意義的再現等翻譯本身的因素”[6]115,其中包括:詞語運用、句法結構和修辭手段等多個方面。本文即從這三個方面對李正栓的譯內行為進行探究。
1.詞語翻譯
在對原文詞語進行翻譯時,李正栓大多是按照漢文的原初釋義對其做出解讀。這樣解讀出來的結果往往會導致“求真”有余而意蘊欠豐。由此,譯詩不免會在一定程度上為讀者留下缺乏靈動感,生硬刻板的印象。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以于道泉的英譯本為例對比分析。如下例所示:
例1:
漢語原文:草頭上嚴霜的任務,
是作寒風的使者。[1]16
李正栓譯:The task of the severe frost on the grass,
Is to act as the envoy of the cold wind.[1]17
于道泉譯:The business of the Hoar-frost on the grass,
(Is to be)the messenger of the North-wind.[7]22
觀察例1中的兩個譯文不難發現,李正栓對原詩詞語采取了高度“求真”的翻譯策略。具體來說,他將“嚴霜”和“寒風”直接譯作“severe frost”與“cold wind”。該譯不僅在語義上與原詩詞語保持一致,而且在組詞結構上(偏正結構)也與原詞不差毫厘。再來看于道泉的翻譯,先從結構上看,于譯將原詩的名詞詞組處理為合成名詞,改變了原詩語詞的組構方式;再從語義上看,于道泉并未嚴格按照原詩涵義進行翻譯,而是將“嚴”和“寒”分別改譯為“灰白色的(hoar)”和“來自北方的(north)”。筆者認為,于道泉之所以這樣翻譯,其目的有二:一是為了豐富譯詩的詩歌意蘊,具體而言,譯者用“hoar”一詞便于與“grass”構成鮮明的色彩對比,籍此來增添譯詩的抒情張力;二是為了拉近與西方讀者的文化距離,使用“North-wind”來翻譯“寒風”,其詞形更加容易使西方讀者聯想到英國著名詩人雪萊(P.B.Shelley)創作的《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從而在心理上形成“文化互文”,促進讀者接受。由以上對比分析可見,從“求真”的角度來講,李正栓在詞語翻譯的操作上竭力忠實于原詩;但從“務實”的角度來講,李譯詩歌在詞語意境的營造方面有時似乎趨于平淡。
2.句法翻譯
相較于詞語翻譯,李正栓在對句法的處理方面采用了更為靈活的變通手段。從總體上看,譯者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詩語言的句法結構,即仍然使用以“求真”為主的翻譯策略。然而,考慮到詩歌體裁特殊的審美需求,譯者在翻譯時又盡量彰顯“譯詩為詩”的美學效果。以下,我們再以于道泉的譯本作為參照來做詳細分析。
例2:
漢語原文:因為心中熱烈的愛慕,
問伊是否愿作我親密的伴侶。
伊說:若非死別,
絕不生離。[1]46
李正栓譯:With passinate love at heart,
I ask if she’d like to be my wife.
She said:“We’ll never part
So long as I am alive”.[1]47
于道泉譯:Because(I)desperately fell in love with(her),
(I)asked whether(she)would come to bacome(my)intimate companion.
“Unless we are separated by death,
We should never part alive”was(her)answer.[7]88
例2詩歌描繪的是一對戀人之間生不分離,死不相棄的忠貞愛情。原詩情感真摯,詩意濃郁。這兩個譯文中,李正栓的譯詩基本上與原詩語句對應,為了使譯詩在整體上更好地展現出詩歌的形式之美,對原詩語句進行了調整。具體來說:首先,他用“with”引導的伴隨狀語結構對譯原詩首行的原因狀語小句,以此來凝練詩句并濃縮詩意;其次,他在翻譯中積極運用縮略語形式(she’d;We’ll),其目的在于盡量貼近英詩傳統中的指征標記;三是李譯改變了原詩的自由詩體,譯詩以格律體呈現(韻律為abab),增強了詩歌的韻律感和節奏感。與此相反,于道泉的譯詩在用句方面帶有明顯的“散文化”傾向。他在翻譯的過程中更加看重的是清晰地展示出原詩的含義,如通過增譯主語及頻繁地使用從句,旨在將原詩中隱含的信息與邏輯關系加以明示,以易于讀者理解。這樣的翻譯勢必會導致詩句的拖沓冗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損害詩歌的美學價值。
3.修辭翻譯
“明喻(simile)”是《倉央嘉措詩集》中最常出現的修辭手法之一。在對這一修辭手法進行迻譯時,李正栓依然秉持以“求真”為本的翻譯理念,將原詩中的明喻結構據實譯出。例如:
例3:
漢語原文:(1)猶如從大海底中,
得到一件珍寶。[1]6
(2)就如同高樹的尖兒,
有一個熟透的果兒。[1]10
(3)猶如拾了一塊白光的松石,
卻又隨手拋棄了。[1]8
李正栓譯:(1)This is like a pearl,
Recovered from the deep ocean.[1]7
(2)Is like a fruit ripe and mellow
On the top of a tree tall and high.[1]11
(3)Carelessly thrown away
Like a rammel white and clean.[1]9
通過例3中的三組譯文可以看出,李正栓對原詩中比喻的修辭方法基本采用了直譯。原詩中“猶如”和“如同”是明喻的標示詞,譯詩也相應地翻譯為“like”,兩者達到了較好的平衡。然而,值得注意是,除了直接翻譯原詩中的明喻之外,在某些譯詩當中,譯者還會借用比喻的修辭方式,對原詩中一些富有特殊文化內涵的專項詞匯進行闡釋。如例4所示:
例4:
漢語原文:情人藝桌拉茉,
雖是被我獵人捉住的。
卻被大力的長官
訥桑嘉魯奪去了。[1]60
李正栓譯:My love was like an enchanting fairy,
Caught by the hunter in me, thereby,
But was too soon grabbed away
By an officer more powerful than I.[1]61
例4中的“藝桌拉茉”是詩中的女主人公,亦是詩歌敘述的主要對象。于道泉在其英譯本中,將它直接音譯作“Yid-hphrog-lha-mo”,如此翻譯勢必會為西方讀者帶來一定理解上的困惑;相較之下,李正栓采取了更為“務實”的翻譯策略,他利用比喻的修辭格方式,將該詞意譯為“奪人心神的仙女(My love was like an enchanting fairy)”。譯者通過這樣的“創造性叛逆”,一方面維持了詩歌的美感;另一方面也化解了中西文化間的隔膜,繼而提高了譯文的可接受性。
通過以上分析來看,李正栓在翻譯倉央嘉措詩歌時綜合考慮了原詩意義、譯詩效果,并摻雜了譯者自身的主觀意愿。總的來說,李譯倉詩與其在詞語翻譯層面的合理程度相比,其在句法翻譯與修辭翻譯上的合理程度被證實較高。根據譯者行為批評理論,現將李正栓的譯內行為規律標示如下:
(二)譯外行為分析
所謂“譯外行為”指的是,涵蓋“一些關涉翻譯活動之外的超出翻譯本身的因素”。[6]117例如,譯者素養、譯本選擇、翻譯原則、翻譯目的、翻譯媒介和讀者意識等。下文將撮取譯者素養、翻譯原則以及讀者意識三個維度加以詳述。
1.譯者素養
李正栓教授目前就職于河北師范大學,擔任外國語學院院長。他的研究興趣主要涉及英美詩歌與典籍翻譯。[8]李正栓長期致力于英美文學教學與詩歌譯介活動,具有豐富的翻譯實踐經驗。“他先后翻譯出版過《智慧之仗》《樂府詩選》和《藏族格言詩》等多部經典譯著,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9]憑借上述譯者所具備的學識素養,李正栓在著手翻譯倉央嘉措詩歌之前,亦對原詩作者及其作品進行了深入考究,挖掘作者的生平、時代背景、思想風潮和當時的詩學規范,并試圖從歷史的角度彌補譯者與作者之間的距離。王宏印和榮立宇兩位學者在《漢英對照倉央嘉措詩集》的序言中評論道:“正栓教授是以詩人的視角切入詩歌,以學者的嚴謹從事翻譯,以敬業的精神邀請兩位英國教授對譯文進行潤色修訂,這些無疑都是該譯本質量的有力保證”。[1]4但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李正栓在從事倉詩英譯時并不通曉藏文,他的譯文選擇了在我國學界比較權威的于道泉漢語譯本作為翻譯底本。顯然,這種通過“轉譯”而來的文本會在“先天條件”上不可避免地喪失一些源語文化的特質,但退而求其次,其譯詩也算是間接地忠實于藏語源文。
2.翻譯原則
力求“忠實對等”是李正栓在從事漢詩英譯時始終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在他看來,在翻譯的過程中,“對原文的理解、對風格的再現、對音韻的追求以及對文化的遷移都應該講究一個對等”。[10]36詳細來說,首先,李正栓指出,對于詩歌翻譯而言,正確理解原詩是翻譯詩歌的前提,即在理解方面,譯者需要具有與作者最為接近、基本對等的理解。[10]他對倉央嘉措原詩的整體把握忠實可靠,做到了理解上的對等;其次,李正栓強調譯詩應當爭取保留并移植原作的風格。[10]“倉央嘉措詩歌以其質樸的語言表達,多樣化的創作技巧以及細膩的抒情描寫在藏族詩壇獨具一格”。[11]李譯盡量照顧到原詩多元藝術創作手法的運用,并且譯詩所用語言清新、簡潔,與原詩的風格不謀而合。再次,李正栓極力提倡翻譯詩歌要用韻。對此,他曾多次引用汪榕培教授的觀點,“用韻固然可能因聲損義,但不用韻則一定因聲損義。用韻損義的程度反比不用韻小”。[12]具體到倉詩英譯當中,李譯主要采用押尾韻的方式再現原詩藏族“諧體”民歌的節奏。最后,李正栓強調不同文化之間應盡可能維持本來面貌,從而達到平等對話,相互借鑒的目的。據此,他贊成異化歸化兼用的方法,以盡可能讓西方讀者通過閱讀有異國情調的譯文而了解那個未知的世界。[9]總之,“無論采取什么方法,都應以最佳的表達和再現源語文化信息為己任,以功能基本對等為翻譯目標”。[10]39
3.讀者意識
所謂“讀者意識”就是要對讀者負責,“它主要體現在譯者對于譯文質量的把控上”。[13]具體到李譯倉詩,譯者采取了如下措施以保證譯文的質量:第一,謹慎選擇底本。底本的選擇對于翻譯來說,至關重要。善本的選取更是成為翻譯質量的有力保障。李正栓以于道泉漢譯的《倉央嘉措詩歌》作為底本,在此基礎上從事英譯工作。于道泉是我國著名的藏學專家,他的倉詩漢譯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藏族源語的文化因子,加之注釋詳盡,因此通常被視作學界權威。李譯詩歌由于氏漢譯本轉譯而來,從而在“預先規范(preliminary norms)”的準備上保障了譯文的地道純正。第二,中西學者合作。為了擴展讀者效應,獲得更為廣泛的傳播效果,達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目的,譯者在英譯完成之后,特意邀請威爾遜(A.B.Wilson)和墨菲(D.Murphy)兩位英國教授對其進行審讀、品評和潤色,以提高譯詩的可讀性和可欣賞性。第三,增添“英譯者注”。出于對讀者的關照,除了直接添加詩注之外,李正栓還為每首詩歌特意撰寫了“英譯者注”。“英譯者注”在此亦可被視作譯詩的“副文本”,其功能主要是為目標語讀者提供豐富的文化背景信息,以便于他們更快地構建起閱讀視域,并能更加深刻地體味到原詩的潛在意義。下面,我們以李譯倉央嘉措詩歌中的第33首為例進行具體說明:
例5:
漢語原文:彼女不是母親生的,
是桃樹上長的罷!
伊對一人的愛情,
比桃花凋謝的還快呢![1]70
英譯者注:把女子比作桃樹所生,此乃奇想怪喻。不談桃花之美,卻談桃花之落。花開花謝乃常事,但女子變心比花落還快。這是男怨詩。但責任僅由女子承擔嗎?詩人只顧想著愛情,卻忘了他的活佛身份和禁欲主義清規。誰敢愛他嫁給他?他在怨女子還是在怨宗教?[1]70
李正栓譯:That girl was not born by her mother,
She must have grown on a peach tree!
The love she gave to a man faded faster
Than the faded blossoms falling free.[1]71
English Translator’s Note:It is a conceit to compare the girl to a child of a peach tree.The poet did not talk about the beauty of the peach blossoms but the falling of the petals.It is quite normal that flowers bloom and fade.But the girl changed faster than the fading of the blossoms.This is male-complaint poetry.But was only the girl responsible for the change? The poet thought only of love,but forgot his indentity as a rinpoche(living Buddha)and the strict regulation of asceticism.Who dare to love him and marry him? Was he resenting the girl or the religion?[1]71
由例5可見,李正栓在原詩和譯詩后面均增補了詳細的注釋。該注釋一方面直接點明了詩旨,以便于讀者從總體上清晰地把握詩歌主題;另一方面,通過設問的方式,譯者旨在調動讀者積極參與詩歌內容的重新構建,以期能夠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原詩的內在意味。具體來說,李正栓在注釋中首先言明原詩是一首“男怨詩”。此外,通過追問“但責任僅由女子承擔嗎?”“誰敢愛他嫁給他?”“他在怨女子還是在怨宗教?”試圖引導讀者作出自己的思考,繼而走進對詩歌意義的多重闡釋和深入解讀。
四、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作為《詩集》譯者的李正栓在翻譯時,他的譯者行為偏向于“求真”但同時兼顧“務實”,合理程度較高,符合譯者以“求真為本,務實為用”的一般性行為規律。就其譯介效果而言,李譯倉詩一方面生動地再現出原詩作者的情感意蘊,另一方面也照顧到了譯文讀者的閱讀需求,做到了忠實性與可讀性之間的彼此平衡。[14]概言之,李譯《詩集》較好地完成了民族典籍英譯的目標,即讓異域文化的人們增進了對中華文明的了解,與此同時,譯詩也促進了藏族文化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