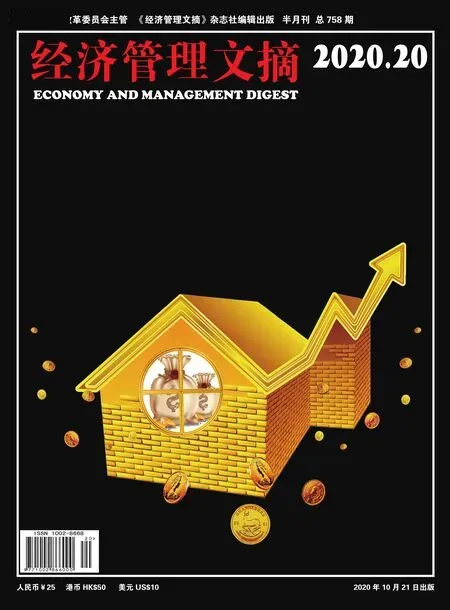治理能力現代化視角下地理標志的保護
■梁飛云
(梧州職業學院)
引 言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條列舉了知識產權權利人享有專有權利的客體,該條款奠定了知識產權在民法保護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宣告了“地理標志”享有的是“專有權利”,確認了地理標志的私權屬性。地理標志注冊為地理標志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后,受《民法典》《商標法》作為高位階法律進行保護,對于提高知識產權治理能力和實現治理體系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1 地理標志商標概述
在我國,《商標法》在基本法層面保護地理標志集體商標或證明商標。因其法律位階高、適用面廣、司法可直接援引等優勢,從而比其他保護模式更具有指導性、權威性和影響力,更容易為公眾認知和接受。地理標志商標法保護模式,既發揮了地理標志優勢資源的公共效益,又符合國際慣用商標法實現地理標志的有效保護。
1.1 地理標志集體商標
集體商標,是表明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為某一集體組織成員的標記,如著名的“五常大米”、“沐川烏骨黑雞”等。集體商標的注冊主體一般是協會或者其他團體組織等,該主體內部所有生產者和經營者均可以在商業貿易中共同使用該集體商標,而不僅僅局限于某個生產經營者,這也是集體商標“共有”或“共用”的法律特征的體現。但是,集體商標也屬于商標,也具有商標本身所具有的專用屬性,即該集體商標的使用權只屬于該特定團體、協會或其他組織內部成員。所以,鑒于使用主體“封閉性”,經工商部門核準注冊的集體商標一般情況下不能進行轉讓。集體商標有效地將特定生產經營者“個體利益”與“共有權益”統一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特定行業的共同發展。因此,集體商標因其特有屬性也得到了國際上將其作為商標進行法律或協議保護,并且在選擇采用商標法對地理標志進行保護的國家中扮演及其重要的角色。其中,《巴黎公約》第七條第二款就有相關的規定,要求其所有合約國家承認并保護其中某一合約國家受理的某一社團提出注冊的集體商標。
1.2 地理標志證明商標
證明商標,是指某一商品或服務的原產地等方面的認證標志,所有權歸屬于具有某一商品或服務監控能力的組織,除該組織外,其他合法主體對該商標有使用權。地理標志證明商標是一種特殊的證明商標,是表明商品原產地或服務來源地的標記,如著名的“龍泉青瓷”、“庫爾勒香梨”。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的使用對象可以是該商標持有者之外的主體。例如,只要第三方的商品或服務也能達到了該證明商標所有求的條件,那么該第三方就可以依照《商標法》,向商標持有人提出使用該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的主張。如果其他合法主體具有該商標注冊主體的必要條件,原來的商標持有人可依法轉讓該已注冊商標。
將作為特殊商標的地理標志納入《商標法》保護系,有效地解決了地理標志在缺乏普通商標所要求具有的顯著性特征的前提下,依然可以獲得基本法的法律保障。用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這兩種方式,依法對地理標志進行注冊,減少了因不同部門對不同主體的合法認定而導致的權利之爭,適應了我國地理標志保護的現實需要,符合特定生產經營者和特定地理區域間的權利專屬和利益共享。
2 地理標志商標保護的現實困境
2.1 地理標志權與商標權存在沖突
國家機構調整提高了地理標志的管理能力,但是我國地理標志保護還存在法律短板,地理標志保護制度并未統一于同一法律體系內[1]。地理標志商標所有權仍然歸屬于特定地理區域內的符合條件的不同主體。根據《商標法》,如果地理標志集體商標的持有人有權將其商標轉讓給該地理標志地域范圍之外的其他生產經營者,那么就可能會造成公眾對該地理標志產品真實產地混淆。如果地理標志集體商標被轉讓給該地理標志區域外的其他合法主體,那么該產品是否在地理標志保護范圍。
2.2 《商標法》中地理標志相關條款不完善
《商標法》關于地理標志概念內涵及構成條件混亂。當地理標志商標中的地理標志申請了原產地域名稱保護并標有標識時,公眾難以區分地理標志產品和地理標志商品[2]。《商標法》還規定某一含有地理標志的商品,雖然并不是來源于該地理標志所在地區,并且還使公眾產生誤解的,如果該申請人取得該商標沒有主觀惡意,可以證明是善意取得的,那么該含有地理標志的商標繼續有效,并且受到法律保護,而這“在先權利”在實踐中往往是商標權利人用來撤銷或異議被搶注商標依據之一。
2.3 地理標志商標注冊缺乏實質審查制度
當前,我國對地理標志商標實質審查的程序和具體內容還不夠明確[3],對地理標志商標實質審查只能根據《商標法》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對商標本身以及申請必需材料進行審查,并未形成專門為地理標志商標實質審查設立的條款。
3 《商標法》模式下完善地理標志相關立法的建議
現行《商標法》作為基本法,對地理標志保護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這從其法律位階就可以看出。因此,將地理標志納入商標法保護,為提高知識產權治理能力,我國要完善《商標法》體系內關于地理標志的具體相關立法,進一步明確地理標志的概念、法律地位、審查內容、權利沖突解決機制等具體條款,從而使司法機關有法可依。
3.1 明確地理標志商標的概念
根據《商標法》第十六條第二款,我們可以看到,規定中只是借鑒TRIPS協議中的描述,并沒有具體指出地理標志要求具備的必要條件。那么根據此款規定,如果某地理標志產品不符合地域或者特征要求,那么工商部門就有權拒絕某主體對于該地理標志提出的商標注冊申請。
如果某一主體在違反第十六條第二款的情況下,對已經屬于集體商標或集體商標進行地理標志商標注冊的,那么依據第三十條規定,工商部門應當不予核準該主體的申請[4]。這樣有利于阻止部分惡意的其他人將那些雖有一定名氣,但是并不符合地理標志的標志,登記為集體或證明商標。這樣的規定是非常有發展性考慮的。所以,本文建議,設地理標志專章明確其概念,防止其商標的泛化。
3.2 明確注冊的主體
地理標志是特定區域產品品質和聲譽的標志,標明該產品與該地域的自然、人文等條件有著必然聯系,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可形成。因此,地理標志本身不是一項創造,而是一件事實。對于可以注冊成為集體商標或證明商標的地理標志,申請的主體不應該是單個民事主體,其所有權和使用權都屬于特定區域內,所有符合條件的全體生產經營者。所以,法律應當明確地理標志的公有屬性。這樣就使工商部門在受理地理標志注冊申請時有法可依,從而不讓本屬于集體的地理標志被個人占有。通過確定地理標志產權歸屬,減少其與商標的沖突。
因為我國對地理標志保護起點比較遲,加上部分地區公眾的法律意識不強。即使某一地理標志已經形成了,但是他們也沒有向相關部門提出注冊申請。《商標法》應承認該地理標志區域內的合法主體對該地理標志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也就是說,該地理標志權人可以申請撤銷某個主體對其地理標志進行商標注冊的行為,從而防止已經形成但卻未經合法認定的地理標志權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
3.3 規范審查的程序
《商標法》應明確規定地理標志集體商標或證明商標申請注冊進行實質審查的程序及內容。要規范審查商品是否具有特定品質、審查地理標志產品與所標示地區的聯系。法律應該規定行使審查權的機關,使其依法對地理標志所有求自然、人文等屬性進行嚴格審查,商品必須具體單一,不能為某一種類的總稱,僅由單一的純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決定特定品質的商品不能注冊地理標志。要規范對申請人是否具有相應主體資格的審查。應該明確的是,地理標志的申請主體必須是具有法人資格,必須是能夠獨立行使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并且該組織還不允許公開或者私下生產該地理標志產品。另外,還要規范政府授權、監督管理能力、申請材料、商品內容等方面的審查。
3.4 明確地名“正當使用”的規定
由《商標法》第十六條以及第五十九條可知,法律允許他人正當使用商標內容本身含有地名的商標。當某個商標本身內容里就包含有地名的,法律要判斷其商標的使用是否屬于“正當使用”時,應該從使用地名的客觀表現形式、使用地名的動機和主觀心理兩種進行判定,《商標法》要明確地名“正當使用”的各種情形,從而避免地理標志商標與其他商標產生沖突。
3.5 明確地理標志商標的地位
在商標法保護模式下,對已注冊為集體商標或證明商標的地理標志,應禁止其他部門再進行地理標志認定。商標法還應明確屬于特殊形式的地理標志證明商標或集體商標與其他普通商標的法律地位,明確禁止具有地理來源的標志注冊為其他商標,并完善地理標志商標的準入與退出的相關條款。
誠如張玉敏教授所提議,我國應該將地理標志列入《商標法》保護體系內部進行保護,這樣有利于協調多部門管理導致的地理標志權與商標權沖突矛盾,保障地理標志權人與商標權人合法權益,提高知識產權治理能力。因此,完善《商標法》中地理標志相關條款內容,為地理標志商標保護的司法實踐提供法律依據,提高知識產權治理能力,更好地發揮地理標志商標在精準扶貧和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