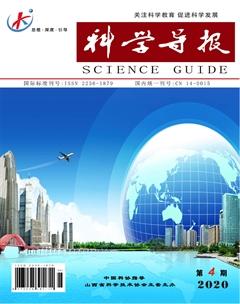“兇宅”買賣合同糾紛法律適用研究
摘? 要:“兇宅”外延上的模糊性造成了此類買賣合同糾紛裁判結果的異化,應堅持客觀標準,限定于曾發生自殺、他殺或意外致死等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房屋。以此類房屋為標的所簽訂的買賣合同有效,并不因違背公序良俗原則而無效。買受人可依據《合同法》第94條第1款第4項,基于“兇宅”這一情況屬于房屋瑕疵而解除合同,或以出賣人違反“兇宅”信息披露義務構成欺詐為由撤銷合同并主張賠償損失等權利。
關鍵詞:兇宅;合同糾紛;解除權;撤銷權
近些年的房屋交易市場中出現了一部分如南京別墅“兇宅”138輪競拍賣到800萬的激烈情況,也出現了逐年增加的以“兇宅”為標的的合同糾紛案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兇宅”應當如何定義,出賣人是否具有法定的信息披露義務,此類房屋買賣合同是否因違背公序良俗原則而自始無效目前均無統一結論。法院對于買受方要求解除合同或撤銷合同的主張態度上出現了“完全支持訴訟請求”和“駁回訴訟請求”兩種截然不同的裁判結果[1],同案不同判的情況屢見不鮮。其合同解除與撤銷的請求權基礎為何,主張獲得支持的構成要件如何理解等問題均值得深入分析論證。
一、“兇宅”概念的法律界定
確定“兇宅”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是解決相關交易糾紛的前提和基礎。“兇宅”不屬于法律概念,只因作為房屋交易市場的常用名詞而進入人們視野,根據目前的中國法律,其定義尚不明確。對此概念在解釋上的差異導致了實踐上的判斷異化[2]。綜合相關司法實踐,法官在認定涉案房屋是否屬于“兇宅”時一般會考慮以下三方面:死因因素、空間因素與時間因素[3]。僅就死因因素一點,其中就包括多種情況,理論和實踐界已基本達成共識將發生謀殺和自殺的房屋確定為“兇宅”。[4]而對發生自殺,但死亡地點在房屋之外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意外死亡事件或因生老病死規律而發生的自然死亡事件的房屋是否屬于“兇宅”各方意見不一[5]。就空間因素,也存在兩種做法,一是嚴格要求事件必須發生在房屋內,二是結合具體案情,分析事件所造成的主觀與客觀影響靈活判斷[6]。時間因素上,法院在部分案件中支持了被告方觀點,即“兇宅”信息對房屋交易活動的影響會隨著時間流逝逐漸淡化,但以“何時”為標準,并未明確[7]。
我們認為,法律上的“兇宅”應當首先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在滿足客觀要求時再適當結合個體主觀感受來調整。曾發生自殺、他殺或意外致死等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房屋為可供參考的死因因素,對于空間因素與時間因素需要司法實踐總結典型情況,為“兇宅”定性提供一般性標準,配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適用,合理確定案件所涉房屋的性質。
二、“兇宅”買賣合同效力分析
在“兇宅”買賣合同糾紛中,部分司法實踐在合同效力判斷這一階段就否認了“兇宅”買賣合同的生效,直接排除了買受人的請求權,但本文認為不能因此否認合同的效力。依據我國法律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有效的構成要件有三點,一為民事行為能力之具備;二為真實意思表示;三為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且不違背公序良俗。
“兇宅”買賣案件中,合同締約雙方一般都具備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且意思表示真實。兇宅的買賣行為,目前沒有強制性規定對此作出禁止,對于是否違背公序良俗這一點,學界爭議頗多[8],主要分歧集中于對公序良俗的理解上。公序良俗,從字面意思理解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的簡稱[9]。公序良俗已成為支配整個法秩序的價值理念與規范原則,是私法自治的界限[6]。草率地將“兇宅”買賣認定為違反善良風俗的行為并不合理[10]。“兇宅”房屋的買賣與社會的公共利益沒有實質性的關系。即使這是民間習俗,也沒有必要在公共秩序和良好風俗或社會公共利益的層面上進行規制,買受人完全可以通過將“兇宅”買賣合同確定為可撤銷合同來保護其利益[11]。目前“兇宅”買賣市場十分火熱,出賣方與買受方均對房屋信息知情,其締結合同的目的就是進行交易,滿足個人締約目的,若法律直接以公序良俗原則否認了合同效力,將置行為人的意思自由于不顧,何談合同法的合同自由原則?因此,肯定趨吉避兇作為善良風俗的一種并無不妥,但是不應當依據《合同法》第52條的公序良俗原則否認該合同的效力。買賣兇宅的行為不屬于違背公序良俗,即便屬于“兇宅”,依舊可以成為房產買賣或租賃市場交易的客體。
三、“兇宅”糾紛的法律適用
在“兇宅”買賣合同糾紛中,買受人通常要求行使合同解除權或是撤銷權,部分案件中買受人僅以出賣人違約為由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事實上,根據請求權基礎分析方法,除以上三種路徑之外,權利人也可以對方違反了忠實的先合同義務主張締約過失責任。在以上請求權中,合同解除權與撤銷權的行使頻率較高[12],但是在行使過程中對于構成要件的認識爭議頗多,其中爭議需要進行深入討論。
(一)基于“合同目的不能實現”解除合同
根據我國《合同法》94條第1款第4項,解除合同請求權成立需要滿足兩點:一為相對方有違約行為;二為違約行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實現。
首先,判斷出賣方是否存在違約行為。出賣人未能交付買受人符合一般大眾期待的正常房屋是否屬于違約行為,“兇宅”是否構成法律意義上的瑕疵?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清楚識別缺陷的標準。依據我國《合同法》,標的是否存在缺陷可按照以下順序依次判斷:第一,標的必須符合當事人的一致約定;其次,如果沒有協議或協議未知,則可以通過協議補充或交易習慣來確定;最后,如果不能滿足上述條件,則可以參考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如果沒有此類標準,則將根據通用標準和合同目的確定[2]。關于識別事物缺陷,《合同法》分為主客觀缺陷。主觀缺陷的識別標準優于客觀缺陷的識別標準,也就是說,標的必須首先達到雙方商定的質量。僅在沒有主觀約定的情況下才考慮客觀標準[13]。在討論兇宅是否屬于物的瑕疵時,如果雙方當事人事前對此有約定,從其約定,無約定時,兇宅屬于標的物瑕疵[14]。雖然發生過慘案的房屋可以居住,但是若對于買受人來說,其訂立合同時所期待的預定效用價值是沒有得到滿足的,即屬瑕疵[15]。因此,在滿足以上前提的情況下,交付“兇宅”本身已經構成了違約行為。
其次,需要分析的是相對方的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此處的合同目的究竟指的是什么?根據學者的觀點,合同目的可以分為主觀目的和客觀目的[16],在大多數情況下當事人明確告知對方訂立合同的動機、依據或者條件后,該動機應被視為合同的目的;或雖然當事人沒有明確告知當事人簽訂合同時指定的動機,但是客觀上有足夠證據證明動機是合同成立的基礎,此類也動機可被視為合同目的[18]。因此,在任何買賣合同中,只要買方沒有表示更具體的動機或目的,則義務的原因始終是買賣的所有權。上述觀點應予贊同,即在此處顯然不能運用抽象目的說來論證,而應該運用主觀目的即動機考量交易目的,在此目的不能實現時,符合《合同法》第94條的構成要件。在滿足解除合同請求權成立的兩點要求時,買受人即可以出賣人交付“兇宅”的行為致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實現而解除合同,獲得賠償。
(二)以出賣方構成欺詐為由撤銷合同
根據我國《合同法》第54條第2款,若要以欺詐為由撤銷合同,其構成要件有三:其一,須有欺詐行為。通常,故意向對方提供虛假信息的積極行為是欺詐。根據學界說法,只有在根據法律、誠實信用原則或交易習慣特別要求進行告知的情況下,才能建立對不告知真實情況的消極評價機制[19]。那么在“兇宅”買賣案件中,出賣人是否負有告知義務?
我們認為,對于影響房屋交換價值或使用價值的重要信息,賣方有向買方披露的告知義務。房屋曾發生過種種事件使之成為“兇宅”的事實屬于重要信息,重大到足以影響對房屋的價值衡量。房屋,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一般會與一家人的一生相伴,不僅屬于個體所有的獨立空間,更重要的是作為生活的必要載體,承載著諸多情感上的因素,因此選擇一個未曾發生過自殺、兇殺等意外事件的房屋是基本需求,對于這樣的愿望不僅法律、行政法規不能予以否定,社會一般評價也無法指摘。基于誠實信用原則和對傳統習俗的尊重,出賣人應當負有異常死亡如實披露的義務,若違反該告知義務則屬于欺詐行為。
其二,被欺詐人須因受欺詐而陷入錯誤,并基于該錯誤判斷而為意思表示。房屋出賣人未告知買受人房屋屬于“兇宅”,屬于消極緘默行為,致使買受人產生了涉案房屋屬于正常房屋的錯誤認識,買受人基于涉案房屋屬于正常房屋的錯誤認識,而向房屋出賣人作出了其愿意購買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從而合同有效成立,而該合同的有效成立并非基于買受人的內心真實意思表示,滿足此條構成要件。
其三,須有欺詐的故意。如果買受人曾要求出賣人提供“兇宅”信息,而出賣人為虛假的回答,這種故意毋庸置疑[20];在買受人沒有主動要求出賣人提供信息的情況下,出賣人也沒有告知情況,有兩種處理。首先,賣方知道“兇宅”為非常重要的住房交易信息,故意隱瞞該信息希望買方陷入錯誤的理解,這種情況應該認定為欺詐;其次,出賣人知道其房屋是屬于“兇宅”,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沒有告知買方。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確認賣家有欺騙買受人的意圖。若同時滿足以上三點要求的,買受人可依據《合同法》第54條第2款主張撤銷合同,要求返還財產、賠償損失。
四、結語
法律上所討論的“兇宅”屬于一種客觀事實,應當優先采用客觀標準,同時輔以個體主觀標準。在對其進行定義時可以考慮死因因素、空間因素、時間因素等綜合判斷。買賣兇宅的行為并不違背公序良俗原則,即便房屋屬于“兇宅”,依舊可以成為房產買賣或租賃市場交易的客體,合同不因此無效。“兇宅”本身屬于合同法概念內的“瑕疵”,交付“兇宅”屬違約行為,可主張違約責任,在違約行為同時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實現時,買受人享有解除權解除合同并主張損害賠償。房屋出賣人負有對“兇宅”信息的告知義務,違反告知義務使買受人陷入錯誤認識從而簽訂的合同可以撤銷。
參考文獻
[1]? 陳枝輝.房屋買賣合同糾紛疑難案件裁判要點與依據[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83.
[2]? 張瀞文.論兇宅之定義以及其與物之瑕疵間之必然性[J].軍法專刊,2016(3):122-142.
[3]? 尚連杰.兇宅買賣的效果構造[J].南京大學學報,2017(5):40-50.
[4]? 吳從周.兇宅、物之瑕疵擔保與侵權行為:以兩種法院判決案型之探討為中心[J].臺北:月旦裁判時報,2011(12):117.
[5]? 朱金東,王紫旋.“兇宅”糾紛的實證分析與法理透視[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0(06):562-569+647.
[6]? 李永.論“兇宅”貶值損害賠償糾紛處理的法律適用[J].法律適用,2019(10):91-100.
[7]? 石記偉.兇宅損害的法律認定[J].天府新論,2019(06):110-120.
[8]? 陳耀東,張瑾.“兇宅”的法律限定及其交易糾紛的法律適用[J].河北法學,2007(10):91-94.
[9]? 王道發.公序良俗原則在侵權法上的展開[J].法學評論,2019,37(02):99-112.
[10]? 劉娥.論“兇宅”糾紛處理的法律適用[J].長沙大學學報,2009,23(06):43-45.
[11]? 肖鵬飛.兇宅買賣下理論分析和救濟[J].沈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9(03):308-312.
[12]? 韋志明.“兇宅”類案件中的法律論證評析[J].法學評論,2015,33(03):33-39.
[13]? 郭明瑞.論物之受侵的侵權責任[J].河南社會科學,2017,25(08):25-29.
[14]? 林誠二.債法總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下)[M].臺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社,2013(1):129.
[15]? 鄭冠宇.民法總論[M].臺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社,2014:320.
[16]? 黃茂榮.買賣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206.
[17]? 本德·呂特斯,阿斯特麗德·施塔德勒.德國民法總論[M].于鑫淼,張姝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87.
[18]? 劉俊媛,姚志華.純粹經濟損失的救濟路徑[J].北方經貿,2019(05):83-84.
[19]? 郭潔.純粹經濟損失概念中的可預見性規則研究[J].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8,17(03):81-84+88.
[20]? 陶鑫明.論“兇宅”所致房屋貶值——從既有案例出發[J].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9,39(06):51-57.
作者簡介:王若珂(1996—),女,陜西渭南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