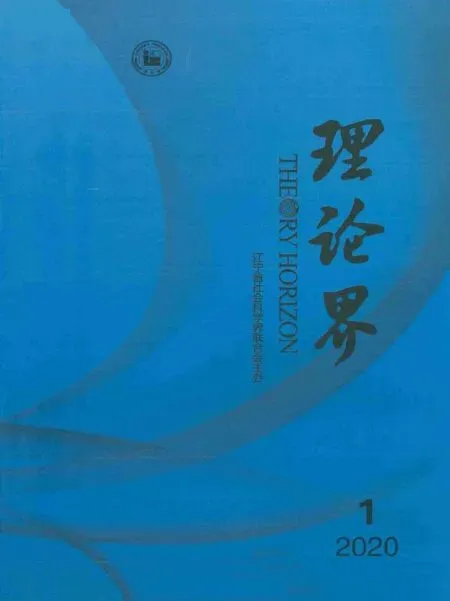農村“漂媽”進城生活困境及對策研究
姚 蓉 張偉豪
由于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及流動政策的放寬,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轉向一、二線城市生活、工作,經過艱苦奮斗后定居在了陌生城市。但是由于城市生活節奏快,工作壓力大,找到穩定工作、結婚生子后的年輕人由于時間和成本問題無暇顧及家庭、照料自己年幼的孩子,因此,本該退出勞動力市場,在老家安享晚年的老人們不得不背上行囊,離開自己生活多年的場所來到子女生活的他鄉,幫助其照料家庭。他們也有一個專門的稱呼,被媒體及學術界形象地稱為“老漂族”。從熟悉的地方來到陌生的城市,老年人的生活習慣、人際交往、語言文化等都與之前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年老精力消退、休閑時間被占據、艱難的社會網絡重構等問題,都使老人在幫助子女承擔家庭養育的過程中承受著身體和心理上的雙重壓力。
“老漂族”的基數不斷增大,其群體的差異性和特殊性也日益突出。一方面,基于現實原因,相對原本就在城市生活的“老漂”,農村“老漂”的不適感更加強烈。在進入城市生活以前,農村“老漂”大都以務農為主,有著穩定的人際關系圈以及帶有農村特色的娛樂方式,但是迫不得已來到了之前從未生活過的城市,跟隨子女住進了封閉的高樓大廈,生活習慣改變、陌生感來襲、生活圈子狹隘、經濟無保障、醫療福利享受不到等問題相繼出現,因此,較之于城市“老漂”,農村“老漂”來到城市生活后身體及心理上表現出了更多的困境和壓力。另一方面,調查發現相比于男性“老漂”,女性“老漂”在照料孫輩后會出現更多負向效用,“女主內男主外”的分工給老年女性帶來了積累終生的社會和經濟劣勢,加重女性老人的照料負擔,給她們的身心帶來不利影響。因此,雙重弱勢身份的加持,產生了“老漂族”群體當中更特殊的一個群體,即來自農村的女性老漂族,我們習慣上稱之為農村“漂媽”。
一、農村“漂媽”的城市生活困境
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稱,2015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了2.471億;其中60歲及以上的流動人口約1800萬人,占總流動人口的7.2%,占我國老年總人口的8.4%,其中為照顧孫輩而流動的老人為43%,而當中來自農村的流動老人約占59%。再根據調查發現,按照傳統的家庭生活倫理及女性善于操持家事等特性,來城市幫子女料理家務、照顧孫輩的主力軍多為女性“老漂”,龐大的農村“漂媽”群體足夠引起學界和政府的重視。農村“漂媽”城市生活的困境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空間“困守”問題
環境不適是農村“漂媽”進入城市生活后所要面對的首個困境。居住空間的局限和出行的不便,讓廚房、幼兒園、社區公共娛樂場地成為了她們主要的活動空間。農村“漂媽”進城之前住在敞亮的平房大院里,熱鬧的街坊鄰居和道路暢通的鄉間小路都給予其較大的自由空間。來到城市后,空間密閉的高層建筑、錯綜復雜的城市道路在給城市帶來活力的同時卻給她們的生活帶來了不便。居住空間變小、樓層阻隔經常使她們感到壓抑和不適應,鄰里無法有效交流、環境封閉使她們不愿意呆在高樓里;但是擁擠的公共交通、道路的錯綜復雜又使她們不愿外出活動,出門搞不清方向、迷路的問題常常出現。大部分的農村老年流動人口僅受過最低等的教育,其中老年女性更是占到了79%,當這些農村老年婦女來到城市外出迷路時常常會因為語言和不識字的問題而更加增長了她們出行的困難。因此,空間和交通的不便把她們的出行范圍固定在了子女生活的小區里,環境在塑造心理健康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空間“困守”很容易使農村“漂媽”在精神上出現孤獨、排斥、焦慮等消極情緒,產生自我隔離和社區隔離。
2.文化適應問題
文化震驚是指生活在某一種文化中的人初次進入到另一種文化模式時所產生的思想上的混亂與心理上的壓力。農村“漂媽”在鄉村生活多年,當來到陌生城市后,許多原有的生活方式因年老以及身心不適應而很難改變過來,從而產生了一系列的“水土不服”,造成“文化震驚”。在進入城市生活以前她們大多以種地為生,鄉下生活依舊會遵循類似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時間安排,生活安靜且簡單;來到城市照顧孫輩以后,嘈雜的小區環境,兒孫輩上下班、上下學時間都使她們原有的生活作息被打破,引起身體的不適。
另外,正所謂“胃知鄉愁”,飲食方面的習慣改變對于農村“漂媽”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一方面,子女較早地來到城市求學,飲食習慣和時間與其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南北飲食差異大,從南到北或從北到南的隨遷也不可避免地使她們面臨著飲食的極大改變,老年女性的身體適應情況遠不如同輩男性,當飲食習慣不同時,不僅引起農村“漂媽”身體的不適,也加深了其對家鄉的思念和眷戀。
所以不僅是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城市氣候、風俗的不同都使農村“漂媽”把在鄉村生活了很久的習慣抽離出來,導致她們產生強烈的不適應感。此外,多數農村“漂媽”文化水平低,學習能力有限,平日里需要花大量時間學習新知識,由此帶來的挫敗感也對其心理造成壓力。
3.家庭關系問題
在中國社會關系的差序格局中,作為獲取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血緣關系依舊是最重要和值得信賴的。但是由于現實原因,農村“漂媽”進入城市后也遇到了與老伴兒、子女之間的困境:
俗話說少來夫妻老來伴兒,由于生活成本的壓力,農村“漂媽”往往獨自來到城市照顧孫輩,老伴兒留守在農村料理莊稼。在即將步入老年享受生活時,夫妻卻要面臨兩地分居的情況,這無疑給她們的精神和情感上帶來了雙重打擊。一方面,農村“漂媽”擔心農村老伴兒的生活狀況,日思夜想。另一方面,當她們在城市遇到種種不適與摩擦想要與自己多年生活的老伴兒傾訴時,卻苦于不在身邊,只好將所有的不快憋到心里,長時間勢必會影響其身心健康。
“農村漂媽”義不容辭地來到城市承擔起隔代照料的任務,也盡最大努力減輕子女的經濟壓力和育幼負擔。但是由于兩代人生活環境和思想觀念的差別,與子女的沖突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她們在城市生活中所要面臨的問題。她們來到子女的“小家庭”生活,傳統的權威感和話語權自然會逐漸瓦解;子女因為忙于事業,也無暇顧及對陌生環境并不適應的母親,久而久之會使其在心理上產生很強的寄居感,形成主觀上的無能和自卑。婆媳沖突也是家庭關系中亙古不變的話題。農村婆婆與城市兒媳朝夕相處,難免會因為生活瑣事和育兒觀念產生沖突。據調查,當與兒媳產生矛盾時,大多數農村“漂媽”會因為家庭和諧選擇隱忍,盡量避免與兒媳發生正面沖突,生活的不適應及情感的無法宣泄勢必會加深其在城市中的孤獨感。
4.社會融入問題
一方面,社會融入體現在農村“漂媽”對社區及社會關系的歸屬感上,社會關系不強,歸屬感低會導致其在城市生活中出現持續邊緣化的困境。在農村,“漂媽”有較多密切的左鄰右舍和親朋好友,非正式照顧資源較多,但進入城市之后,原有的社會支持網絡跟隨距離的移動而瀕臨斷裂,陌生的“公共空間”使農村“漂媽”的生活變得拘謹,城市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紐帶脆弱,因此,在建構新的關系時,往往會變得慎重和保守,久而久之使她們對城市產生了疏離感和冷漠感。另一方面,人的社會融入可以從人們對于正式的社會組織的參與中表現出來。但是農村“漂媽”不被包括到居住地的社會制度中,也不曾擁有城市社區完整的居民身份。無論是文娛活動抑或是福利政策,農村“漂媽”更多的是接收不到其所在社區的服務信息。受自身生活環境、文化程度和閱歷等限制,大部分農村“漂媽”也因害羞、自卑等不愿參與社區活動。新的環境、陌生人群、社區的排斥以及自我否定,都使她們陷入情緒糾葛和生活困境之中。
5.社會保障問題
外來移民和當地居民都是城市的納稅人,他們的父母也應當享受城市的社會福利,但由于政策不到位等原因,其依舊站在了均等社會福利的門檻外。一方面,農村“漂媽”享受不到當地居民擁有的服務政策。另一方面,城鄉分割也使她們在農村的保障制度斷裂。我國現有的服務政策與社會保障制度具有明顯的戶籍分割特征,特別是在醫療保障方面,并未真正實現跨區域聯網互通。而家務勞動是一項時間、精力、體力絲毫不亞于產生經濟價值的生產勞動,長時間的勞作經常讓年齡漸長和水土不服的農村“漂媽”感到疼痛纏身,生病也時有發生。因此,當農村“漂媽”進入城市之后卻因為戶籍的限制,既享受不到“利隨人走”的動態性保障,也不能享受城市福利的公共性,導致她們陷入一種公共性斷裂與失衡的雙重困境。據調查,部分農村“漂媽”因為高昂的醫療費用和“兩不靠”的醫療保障困境使得她們放棄治療,長此以往對身體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二、農村“漂媽”城市生活困境的解決路徑
農村“漂媽”的形成及其發展壯大,折射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市場、社會、文化與國家多種結構性力量對于流動的農村女性老人的裹挾與形塑,社會、不斷涌入城市的流動家庭、農村“漂媽”都應該采取積極態度應對城市生活面臨的挑戰,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農村“漂媽”要學會自我調節
首先,入鄉隨俗,主動適應城市環境。一方面,主動提高繼續社會化的能力,學習在城市生活必備的知識和技能,減少對新環境的排斥。另一方面,放棄舊觀念,調整生活習慣。進入城市后,農村“漂媽”要改變在農村老家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主動適應和調整飲食和時間安排,增強體能,提高自己的城市適應能力。
其次,提高主體意識,防止“邊緣化”。一方面,農村“漂媽”來到城市幫助子女照料孫輩時也不要忘記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面對進入城市后無法自我排遣的壓力,要善于發現和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如跳“廣場舞”、學習上網等,充實休閑生活,消除焦慮。另一方面,尋求各種渠道打破“自我邊緣化”,積極向城市靠攏,如盡量多地向子女敞開心扉、積極參與社區舉辦的文體活動、尋求老年伙伴兒,以便加強與子女、新伙伴兒之間的交流,排解不良情緒,消除精神困擾。
2.子女要給予老人更多關懷
孝敬父母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作為子女應明白母親從家鄉來到陌生城市照顧孫輩的不易。因此,在忙于事業的同時也要了解農村“漂媽”身心的需求。一方面,盡可能多地在生活上關心和照料,如主動提供經濟資助、多抽時間帶母親去熟悉城市;定期帶她們去醫院進行體檢,知曉其身體狀況等。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也要給予關懷,給農村“漂媽”精神上的安慰。第一,與她們分享自己生活和工作當中的趣事和喜悅,增強她們在子女“小家庭”中的存在感;第二,要調整好“漂媽”與女婿或兒媳的關系,充當真正的調解員,而不是一味遷就或不顧及;第三,多與獨自在老家生活的父親打電話和交流,做到讓農村“漂媽”安心,家里父親放心。
另外,農村“漂媽”和子女應加強彼此之間的溝通,坦誠交流。農村“漂媽”要主動向子女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子女也要盡力了解母親的困難,作出恰當的回應和關懷。當身體出現不適時,及時告知子女而不是刻意隱瞞導致延誤;對子女考慮不周或做得不好的地方,相互理解和包容,以恰當的方式讓子女知曉,子女也要積極改正自己的不當之處,切忌憋在心里或獨自生悶氣,從而減輕“漂媽”的身心壓力,促進家庭和諧。
3.社會層面要進行幫扶接納
社區和政府要意識到農村“漂媽”這一群體的到來不僅幫助年輕人解決了后顧之憂,促進了家庭幸福,還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的穩定,有利于城市的發展。因此,社區和政府層面的幫扶也是必不可少的:
社區及居民應該改變對農村“漂媽”的偏見和誤解,將其納入社區大家庭中。一方面,社區應當多給予其物質和精神上的關愛,提供生活、娛樂及交往的支持和機會。另一方面,本地居民應主動與她們交流,不僅要從心理上接納農村“漂媽”,而且要從行動上關愛她們,在日常生活中給予必要的支持和幫助。
政府應加大對農村“漂媽”群體的重視程度,努力優化老年流動的頂層設計,提高社會保障。首先,逐步降低福利保障門檻,深化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如提高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合作醫療保險的統籌水平,建立養老和醫療保險報銷的全國聯網制度,從而解決農村養老金微薄且異地無法領取、住院看病需來回奔波的問題。其次,積極籌辦各種社會組織多為其提供專業服務,提高農村“漂媽”對城市的歸屬感,安心為家庭和社會服務。
三、結語
農村“漂媽”是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特有的產物,也是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可忽視的一個群體。在城市中“漂”的狀態,不僅給“農村漂媽”的身體帶來了很多的“不適感”,也導致了她們心理上的“漂泊感”。空間環境的“困守”、文化差異的不適、缺失的親情關心、孤獨的社會交往、未到位的社會保障等,都直接反映了農村“漂媽”的在城生活狀況,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城市對流動人口的包容感和支持度。因此,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全面二孩政策的放開、城市家庭對子女撫育需求的進一步增加,只要構造農村“漂媽”的各種結構性力量沒有消失,她們的規模就會進一步發展壯大。所以為了能夠促進農村“漂媽”及家庭的生活幸福,促進社會穩定,如何解決其城市生活困境成為了不可小覷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