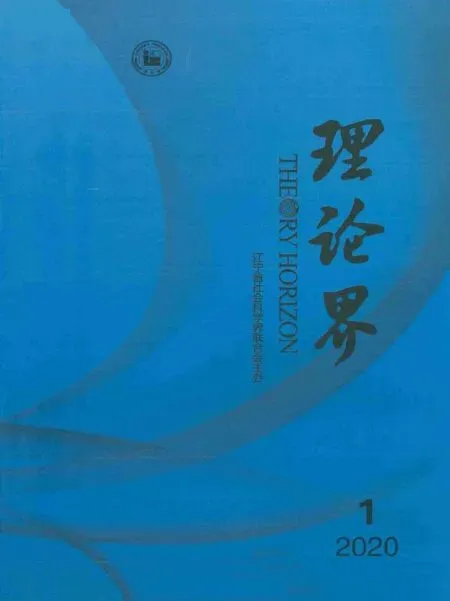精神空間與自我探求:中國古代女性文人室名堂號解析
朱路遙 雷環捷
歷代文人往往有使用室名堂號的傳統。室名堂號可歸為自號的一類,一部分與使用者所實際居住的處所有實際關聯,另一部分則與名或字互相滲透,界限較為模糊。室名堂號多由使用者自行命名,被應用于非正式或者與文學關系較為密切的場合,例如為個人詩文集命名。室名堂號的結構形式較為自由,發揮空間大,自我闡述的目的性強,凝練性高,往往能夠以小見大地反映出使用者的個人志趣。
女性文人使用室名堂號可追溯至唐宋時期。如唐代薛濤晚年建樓名為“吟詩”;又如宋代何師韞因居室外有“懶愚樹”而“榜其室曰懶愚”;〔1〕宋代黃由之妻胡氏自號“惠齋居士”,〔2〕均已見雛形。至明清時期,隨著女性創作和商品印刷的發展,女性文人對室名堂號的使用進入高峰階段,尤以清代為最。其原因之一是室名堂號的使用日趨普遍,之二是相關史料和典籍保存較多,之三是女性創作被社會接受程度有所提升。目前可見的較多以女性文人作品集名的形式保留,其中大部分為女性為自號,小部分為刊刻者在出版時所取。整體而言,女性文人在使用室名堂號時,與以男性審美為主流的文壇風尚有所區別,呈現出較顯著的群體性別特征。
一方面,以往的研究已對中國古代女性的被命名與自命名行為有所關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當時女性的生活和創作情況,但往往僅將女性視為被壓迫者進行考察。另一方面,高彥頤 (Dorothy Ko)、白馥蘭 (Francesca Bray)、〔3〕伊沛霞 (Patricia Ebrey)、曼素恩(Susan Mann)等學者通過對宋代及以后的婦女史研究普遍認為應采取女性中心和動態演變的視角。得益于前人的基礎和啟發,對女性文人室名堂號的研究可循著整體性的路徑,綜合且全面地梳理室名堂號的基本內容與重要主題,深入分析在其背后產生影響的代表性觀念,并進行審視與反思。
一、自然意象與“香草美人”
借助自然意象營造意境是室名堂號的主要命名方式。使用者以短短數字勾勒出文學性意境,彰顯個人的審美情趣與文學意趣。最常被使用的意象或為云、霞、月、山等自然景物,或為蘭、梅、竹、松、桂等植物,都是文學傳統中受文人青睞的物象。雖然文學傳統中對風云月露之風的批判已是長久共識,但部分文人在室名堂號命名時卻未刻意對此規避,依然選用此類意象。文人們擇一物而盡發其意趣,取其閑適自然風雅之意,亦不流于綺麗浮靡。有些文人取與居室或書房有關的實物實景入其室名堂號,以紀實性加強室名堂號與使用者之間的關聯,突出其獨屬特性。
社會容納女性文學創作活動,但同時也存在成見和限制。社會對男性和女性創作在風格和層次上做了區分,并將對女性貞靜嫻美的規范擴大到文學中,樹立了風格的理想模范,許多女性文人在創作詩文和擬定室名堂號時因此趨近婉約清麗的風格。家庭對于女性的命名帶有慣性,淑、貞、婉、嫻等閨范標準,蘭、蘩、芝、蓮等植物意象,以及珠、翠、玉、琴等閨閣物象都是十分普遍的女性命名常用字。這一慣性也可能由女性帶入到對自我的再命名過程,出現于室名堂號與文集名稱中。
在女性室名堂號中被使用最多的自然意象與楚辭“香草美人”意象體系有關,同時也有所改造。檢閱《歷代婦女著作考》可知,以室名堂號作為作品集名的女性文人共有2357位,其中以“香”為構成部分者即達263位。以“蘭”為名者有108位,為字號者有69位,為室名堂號構成部分者有76位,可見“蘭”稱得上是女性名、字號、室名堂號中最常見的意象。元代薛蘭英、薛蕙英姐妹所居樓為“蘭蕙聯芳之樓”,合著詩集名為《聯芳集》,她們對蘭、蕙、芳的強調具有一定代表性。此外,其他女性文人所用“藝蘭室”“友蘭閣”“猗蘭室”等名,也直接指向“蘭”意象。楚辭“香草美人”之典原本虛指君臣之義,在女性文人室名堂號使用中產生了寓意的遷移,轉為實指女性之美及高潔情操,體現了歷代女性文人群體中具有延續性的精神追求。
清代毛國姬自號素蘭女史,其所編《湖南女士詩鈔所見初集》弁言云:“詩三百篇,大抵婦人之作,自楚風不錄于經,而湖外歌謠傳自閨闥者,益不少概見,將澧蘭沅芷之馨香,分得于翡翠筆床者,固獨寥寥與?抑奇葩異藻吐秀于南國美人者,隨序榮落,既無人焉為之采擷,以相餉遺,斯通都大邑儒林詞伯,莫由一頌其芳烈耳。”〔4〕所謂“澧蘭沅芷之馨香”成為女性文學創作的代名詞,其中雖有毛氏本人的湖湘籍貫之影響,但更多的是對女性文學創作特征的描摹——蘭心蕙質、馨香芳烈,從而對創作者及其作品都進行定義。從男性文人視角來看,他們亦重視女性文學作品中的性別特質,并將其作為一個重要的審美切入點。男性對女性文人的評價亦常見“蕙心紈質”“澹秀天然”〔5〕等語,“香草美人”的搭配在女性創作評價體系中已基本形成共識。除蘭以外,竹、梅、松、桂等植物也被賦予類似內涵,共同構成一個更為廣泛的“美人香草”意象體系。
室名堂號是女性文人自我形象的勾勒,是其創作行為的縮影。以“香草美人”為代表、使用自然意象構成的女性室名堂號多表現出幽閑貞靜的特點,并與其自身創作風格相呼應。其中表現出女性在文學創作行為中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認知,即她們沒有刻意抹去性別特征以趨同于文學主流,而是將之保留下來成為特色。一部分女性作者囿于家庭環境和所受教育的限制,只能在社會對閨閣文學早已框定的風格空間內進行創作。但她們仍能夠在有限空間內竭盡所能地錘煉作品,真實地抒發內心情感。另一部分創作水平和自由度較高的女性則對閨閣之學有所反思,她們或突破社會刻板印象限制,豪言壯語不遜須眉;或發揮女性細膩敏銳的長處,將性別特征轉化為創作優勢,在男性主導的文壇中獨樹一幟。
二、家庭生活與親緣關系
家庭生活與親緣關系亦是女性文人室名堂號的主題之一,按照所面向的不同對象可分為同輩、配偶、父母輩和祖輩等四類。
其一是與姐妹、兄弟等同輩親屬間的聯系。除前文提及薛氏姐妹的“蘭蕙聯芳之樓”外,明清兩代亦有許多事例。一類是姐妹間室名堂號互相呼應,如清代王迺德“竹凈軒”,其妹王迺容室名“浣桐閣”。〔6〕另一類是匯編家族中同輩女性詩文時取一概括性的室名為作品集冠名,該行為可能出自作者本身,也可能是匯編者或刊刻者所為。浙江海寧朱淑均、朱淑儀姐妹“幼相倡和,比長,同歸查氏為妯娌。刻有《分繡聯吟閣稿》。妾織霞女史鬘云之詩附焉”。〔7〕閣名記錄三人各自獨立的家庭生活以及聯合性的文學創作活動。安徽桐城張瑞芝、張玉芝、張愛芝姐妹“皆能詩。卒后其弟鵠哀三人之作,名曰《三芝軒詩存》,并為作序”。〔8〕“三芝軒”之名將三位姐妹的詩文囊括起來,在她們身后依然維持其社會性聯系,加上其弟張鵠發揮作用,使同一個家庭中姐妹、姐弟間的親情聯系凝聚在“三芝軒”室名中。浙江海鹽吳慎室名“琴媵軒”,《國朝杭郡詩三輯》記載:“所居曰‘琴媵軒’,意取于歸時,其兄榕園取琴以贈,且戲之曰‘以是為媵’,故名。”〔9〕這是居室主人以室名記錄婚前與婚后生活間的交匯點,可憶往昔在室趣事,同時明確當下已為人婦的婚姻狀態。
其二是與配偶間的情感狀態。清代穆竹村妻金云裳室名“倚竹樓”;〔10〕姚畹真字“芙初”,其夫張蓉靜字“芙川”,“故稱雙芙以名其閣”;〔11〕蕭恒貞字“月樓”,其《月樓琴語》附于其夫周天麟《倚月樓詞》后。〔12〕夫婦間在室名堂號的運用中進行情感的互動和交流,情侶之間亦是如此。明代舊院妓楊琰與閩縣林景清交好,“后林歸閩,楊潔身以待,題‘一清’自名其軒”。〔13〕室名堂號成為含蓄又堅定地表明心志的載體。在丈夫去世后,妻子們也通過室名堂號追懷故人。明代顧若璞自題其集為《臥月軒稿》,并在自序中言:“臥月軒者,夫子所嘗憩息志思也。”〔14〕以“臥月軒”之名表達對亡夫的思念。清代杭溫如室名“息存室”,李元春在其《息存室吟正續集》序中解讀:“室名息存,取朱子一息尚存之語,即未亡人之義也。”〔15〕亦是通過室名標注其未亡人的身份,表達不渝之志。
其三是與父母親間的聯系。一類是表達思親之情。明代仲云鸞借《詩經》中《蓼莪》之典,取名“匪莪堂”,以示追思。〔16〕郭芬“取狄梁公望云思親之義,名所居曰望云閣”。〔17〕另一類是表示對父母親文學成就的繼承。清代王玉芬之父王鳳生有“江聲帆影閣”,故王玉芬自號“江聲帆影閣主人”,為自己的詩集取名為《江聲帆影閣詩》;〔18〕傅范淑“小紅余籀室”源自其母李端臨“紅余籀室”;〔19〕陳蕓《小黛軒論詩詩》附于其母《黛韻樓詩詞集》后,并有自序云:“少時得承母教,微聞聲韻之學”;〔20〕簡貞女有《嗣得到梅花館詩》,原因是“父松培有得到梅花館詩鈔,故云嗣也”。〔21〕
其四是與祖輩之間的聯系。清代李杜有《墨顛閨詠》,“曾大父廉訪王 額所居曰墨顛,因以自號”。〔22〕錢與齡“少承曾祖母南樓老人家學,嘗署所居曰仰南樓”。〔23〕室名使用者追憶童年時在長輩膝下所受的教育,表達對長輩的懷念,并顯示家學的傳承。
雖然不少男性文人也使用與家庭親屬有關的室名堂號,但此種情形對于女性文人而言意義更為特殊。男性可以在家庭和公共場所間自由穿梭,大部分女性的生活空間則被局限在家庭中。家庭、親屬是女性日常生活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女性情感豐富且細膩的特質也使其更容易珍視親情。出嫁后離開原生家庭進入男方家庭,歸屬集體和身份的轉換也常能激發女性對于舊日閨中生活及其親屬的回憶,將對原生家庭的思念注入到室名堂號中,作為自己的符號和標志,使內心有所依靠。通過室名與丈夫互動則是女性融入新家庭的表現,她們以此表明自己和丈夫感情融洽,并將丈夫視作可以文學唱和的精神伴侶。女性文學多以家庭、家族為單位,不論是生在這個家庭中,還是以婚姻的方式加入新家庭,家族內的女性間由此形成紐帶,往來唱和使家庭內形成一個文學創作的小集體,并激發小集體內部各成員的創作活力。
三、閨閣中的順從與反叛
室名堂號記錄著閨閣女性生活的一角,也寄托著她們在閨閣之中的順從與反叛,各自構建閨閣文人的鮮明形象。在女性室名堂號中,展現出社會主流觀念對女性的認知和期望。她們修習琴藝,并將房屋命名為“頌琴樓”“停琴佇月樓”“友琴齋”等;同時也精研女紅,“繡香閣”“繡垂館”“學繡樓”等室名堂號具有強烈的閨閣特色;宗教信仰也是閨閣生活中的重要方面,明清時期女性群體中佛教流行,于是出現了“羼提閣”“繡佛齋”“雙修慧業樓”“芬陀利居”等與佛教有關的室名;婦德也在室名中體現,明代朱有燉室夏云英“嘗取女誡端操清凈之義以名其居曰‘端清閣’”。〔24〕“靜怡山房”“靜好樓”“靜婉齋”等室名也被廣泛使用,是女德在女性群體中的被接受和投射。她們以此自勉,同時也希望藉此證明自身已符合社會所要求的淑女標準。
“弄文舞字,非婦人所便”的觀念由來已久,〔25〕雖然朝代更迭,女性作家頻出,但傳統社會中無論男女的主流觀念都認為文學非婦人應為之事。這使進行文學創作的女性要么從正面回應,嘗試建構女性文學活動的合理性,要么從反面掙脫,直接選擇反叛社會主流觀念。當然,前者比后者更為常見,且實際情形往往并非僅屬一端,而是更為復雜。清代查昌鹓《學繡樓名媛詩選》序:“余自垂髫,承母氏命,從伯兄介庵先生受業。初授《毛詩》 《女孝經》及《內則》 《女訓》,訖于小學四子書,略皆成誦;復授唐詩數百篇,徒伸呫嗶,未遑講解。甫及笄,遂輟誦讀,從事女紅。刺繡余閑,取向所成誦者,私自研求,略曉大義。時就巖門諸兄質其所疑。至聲韻之學,往往見獵心喜。然不敏未嘗能作,且以非女子事,輒不敢為。偶有小詠,即焚棄之,不復存稿。”〔26〕她在序中記錄,婚后與丈夫一起賞奇析疑,重拾詩文。但后來丈夫去世,米鹽瑣碎,不復吟詠,直到含飴弄孫時才稍有閑暇編詩選。從童年到婚后,再到弄孫之時,查昌鹓記錄了自己學習與創作的波折歷程,其中有多次中斷和接續。這也是古代女性文人受業修習情況的普遍寫照。她們早年間女德與詩文同修,在具有一定文化基礎之后則終止詩文的學習,專攻婦德婦功。家庭讓她們學習詩文的主要目的只是為了讓她們獲得粗淺的知識儲備,避免目不識丁的情況。能夠真正將女性納入家學傳承體系,與男性成員一視同仁地進行教育的家族少之又少。在這種普遍背景下,女性作者要想出類拔萃、比肩男性文人創作水平的難度也因此倍增。清代沈善寶《名媛詩話》自序:“蓋文士自由即肄習經史旁及詩賦,有父兄教誨,師友討論;閨秀則無文士之師承,又不能專習詩文,故非聰慧絕倫者,萬不能詩。”〔27〕她陳述男女自小所受教育內容和環境的顯著區別,也闡明女性文人進行創作的艱難程度。
女性只能在社會觀念夾縫中的狹小空間內進行活動,尋求傳統與創新、順從與反叛之間的平衡,同時也是對自身聲名、品格與文學作品的保護。清代惲珠《閨秀正始集》序:“昔孔子刪詩,不廢閨房之作。后世鄉先生每謂婦人女子職司酒漿縫紉而已,不知《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之下,繼以婦言,言固非辭章之謂,要不離乎辭章者近是,則女子學詩,庸何傷乎?”〔28〕嘗試發出迥異于傳統觀念的聲音,為女子學詩爭取合理性。但她又言“是集所選,以性情貞淑、音律和雅為最,風格之高尚其余事”,〔29〕依然對傳統有所妥協,顯示出折中態度。陳蕓《小黛軒論詩詩》序云:“方今世異,有識者咸言興女學。夫女學之尚,蠶績針黹,井臼烹飪諸藝,是為婦功。皆為婦女應有之事。”〔30〕對女性的教育日益獲得重視,但教育內容與目的依然未能突破既有范疇。室名常用“琴余”“繡余”“繡墨”之語,并為作品集冠名,表明雖從事采藻但未忘本分。當然其中也有先后輕重之分,文學終究只是女紅琴藝之余的消遣。部分女性使用“吟秋閣”“藕香吟館”等將詩文創作活動嵌入其中的室名堂號,表明文學活動與個人生活之密切聯系,但同時也用具有女性用語色彩的詞語進行修飾,以求中和。清代左淑芬“度金針室”、徐蕙貞“度針樓”則有雙關之義,既可指女紅活動,亦可解讀為用元好問《論詩》中“度金針”之典指代文學創作活動。雖然多種室名表達方式不一,但其共同點在于女性通過室名堂號表明自身的價值觀念,試圖達成順從與反叛之間的平衡。
另外一小部分女性選擇直接反叛。如明代鄒賽貞號“士齋”,《名媛詩歸》記載云:“博雅好吟,每有奇句,見者以為無愧能言之士,因號曰士齋。”〔31〕“士齋”一名突破了女性室名堂號應有之意和應有之貌的限制,但同時也表明文壇仍存在嚴格區分性別的文學評價體系,即以男性評價體系評價女性作者,暴露出時代觀念的局限。王詩齡的“谷應山房”、李端臨的“紅余籀室”則走得更遠,雖是女性室名堂號,卻也在它們的主人從事印刷出版行業時作為書坊的名稱。〔32〕閨閣名號突破了圍墻的限制,成為市場流通中的商業符號。女性文人既有對傳統觀念的反叛、對文學事業和自由的爭取,也有對時代和觀念的無奈受限。總之仍值得肯定,她們對于女性文學地位的提升和女性文學創作自由空間的擴大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結語
本質上,室名堂號所搭建的虛擬空間是在實體建筑之上主體意志的增添,是一種以想象方式所描繪的建筑景觀。虛擬空間與實體建筑間的關系既可能是實指,即為主人居住的實體房屋;也可能是虛指,是主人基于自身需求而重構的精神空間;還有可能是虛與實的相互交錯,是主人對實體房屋的部分修飾。男性可自由穿梭于家庭與社會之間,女性則居處于內,個體與房屋空間的結合更為緊密,并呈現出更為生活化、非事務性的聯系。與此同時,社會對女性的隔離禁閉并非與外界的絕對隔絕,其界限并非固定,亦非不可滲透,女性仍能通過某些方式穿過隔離進入社會,但大部分時間里,女性都居于家中。“等級秩序試圖用禁閉來控制婦女,卻在這個過程中制造出了抵制這一控制的私人空間。”〔33〕書房代表教養和優雅男性氣質,女性則更多地歸屬于臥室,她們處于公共領域之外,但又通過婚姻合法地成為家中權威。女性對這片私人空間擁有充分權力,包括為其命名的自由及承載其上的情志和喜好。同時,這片空間又成為她們的一方天地,在實體或虛擬空間中,她們皆享有較充分的創作自由。由室名堂號劃出的精神空間實際上是對女性文學創作行為的承認和庇護。
女性同男性一樣進入文學創作領域,亦使用室名堂號為作品集命名,社會性別的界限在這一行為上有所模糊,但她們所使用的室名堂號內容往往又帶有強烈的女性特征。與印刷業發展和女性文學創作增長同時的是女性名字注定被父系和夫系姓氏掩蓋的時代背景。女性作者通過室名堂號達成的對自我的認知、彰顯和再命名,是她們對自身話語權的強調,是女性生存狀態的側面之一。明清時期,“女性的自我意識逐步蘇醒,滋生較為強烈的才名焦慮,并在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獨特的價值判斷體系和自我評價”。〔34〕女性帶著她們自己的話語內容及其評判標準主動進行社會意識的建構,可見中國古代女性并非完全遮蔽于父權和夫權之下,而是文化形態與社會秩序的積極參與者。“雖然無可否認婦女才華沒有被儒家傳統正式認可,但我認為,用‘壓迫’和‘受害’去形容她們的處境是不恰當的。因為無論‘壓迫’或‘受害’這種被動式,只能通用于身處儒家文化之外的異類。但無論是閨秀也好,名妓也罷,她們本身就是儒家社會的一份子,也是儒家文化的產物。她們是在體制之內,靈活運用既有的資源,去為自己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35〕女性文人以“香草美人”的室名建構自我形象,以將家庭和親緣關系加工為室名的方式標注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以室名堂號表明對社會觀念的認同或反抗,其要旨都在于女性如何在受限制的生活空間中對自我的探求和落定,即明確自我的取向與抒發自我的情志。她們不僅以清晰的自我定位獲得內心安定,而且構建出一個面向女性群體、面向文壇乃至整個社會的主體形象,創造出象征其豐富精神世界的文化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