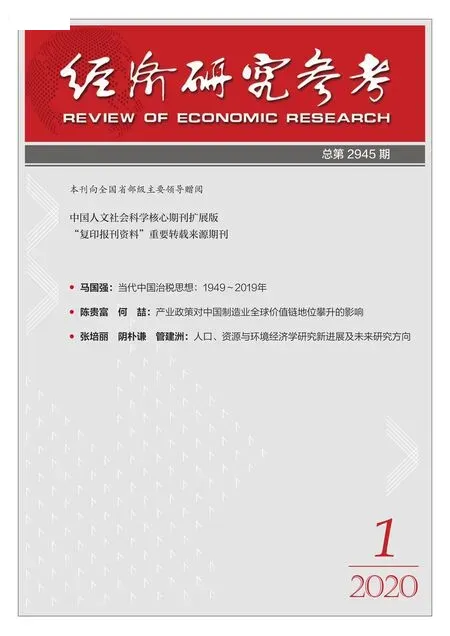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研究新進展及未來研究方向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
張培麗 陰樸謙 管建洲
2018年,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研究仍然表現出三大分支學科相對獨立的突出特征,在關注傳統研究重點的基礎上,三大分支學科也分別針對各自領域出現的新問題、新政策進行了研究和評估,取得了新的研究進展。
一、人口經濟學
2018年,人口經濟學的研究在繼續關注勞動力流動、人口結構和人口政策的同時,重點對戶籍制度改革績效進行了評價。
(一)戶籍制度改革績效評價
2014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出臺以后,各地在戶籍制度改革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的新舉措,這些政策效果究竟如何,學者們對新一輪戶籍制度改革中的不同政策措施進行了評價研究,基本都得出了戶籍制度改革效果有限的結論。評價的主要政策有以下幾個方面。
1.戶籍制度改革路徑。
長期以來,我國戶籍制度改革主要遵循利益剝離和利益擴散兩條路徑,利益剝離路徑的理論邏輯在于,由于戶籍制度被不合理地強加了利益分配功能,因此戶籍制度改革就是要把掛靠在戶口上的一系列特殊福利和公共服務與戶口類型剝離。利益擴散路徑就是制度受益者范圍不斷擴大,新進入者獲得預期利益的過程,很多戶籍制度改革采用的藍印戶口、購房落戶、積分落戶等都是采取的這種路徑。鄒一南(2018)指出,新一輪戶籍制度改革采取差別化落戶和居住證制度并行的二元路徑,延續了戶籍改革的利益擴散和利益剝離模式。利益擴散模式和利益剝離模式均著眼于單個城市,其成功的前提是戶籍利益差異主要在城鄉之間。在戶籍利益的主要差異轉變為不同規模城市之間的情況下,兩種改革路徑都陷入誤區:作為利益擴散式改革的積分落戶演變為大城市“搶人(才)”大戰,而改革原本的目標受益對象農民工被排除在外,造成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在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失衡配置,加劇城市發展差距;作為利益剝離式改革的居住證制度,使城市非戶籍利益和戶籍利益差距縮小,客觀上提高了大城市的吸引力,促使流動人口進一步向大城市非戶籍遷移,增加了改革難度。
2.城市積分落戶政策。
積分落戶政策為超大城市戶籍改革的重要政策,其目標在于大城市人口調控。李競博等(2018)指出,積分落戶政策的實施表面上對流動人口落戶超大城市提供了可能和途徑,但實質上仍是選擇性落戶政策,只是為流動人口設定了新的落戶限制條件,僅僅放開了高層次流動人口落戶超大城市的條件,卻依然在擠出低層次流動人口。他們以天津市為例考察發現,具有相對優勢的城—城流動人口雖然仍是永久遷移人群的主體,但是其遷移比例正在下降,而鄉—城流動人口并沒有因積分落戶制的門檻設定而回流戶籍地或是遷出大城市,他們是事實性的永久移民。積分落戶制依然是城鎮化和戶籍制度改革的權宜之計,是不徹底的戶籍改革政策。
3.戶籍門檻制度。
城市戶籍門檻仍然在新一輪的戶籍制度改革中存在,一些大城市甚至設立了更高的“門檻”,侯新爍(2018)以地級市“市轄區”為樣本,構建空間異質分析模型研究戶籍門檻設置與人口城市化之間的聯系發現,人為設置的戶籍門檻對城市化產生抑制,而這一負向影響有多渠道效應:一是人力資本渠道。戶籍門檻高雖然對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有篩選作用,但也會抑制潛在人力資本積累而抑制城市化。二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戶籍門檻有利于吸引人力資本從而有利于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提升。三是產業結構。高戶籍門檻促進了產業結構變化,但同時抑制投資的城市化。此外,戶籍門檻的作用具有空間梯度性,高戶籍門檻在東部地區對城市化有更明顯的抑制作用。
(二)人口流動
學者們繼續深化了人口遷移、人口集聚等人口流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拓展了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研究,并關注了高學歷人才流動的新現象。
1.人口流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關于人口遷移、人口集聚等人口流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學者們從不同層面進行了研究。
第一,區域經濟層面。楊東亮等(2018)區分了人口集聚和人口遷移的差異,利用2000~2015年31個省份的常住人口數據計算人口密度指標,證實我國人口集聚程度按照東—中—西依次降低且集聚程度不斷提高,大部分城市仍有很充足的人口集聚空間。人口集聚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其中對西部地區經濟的影響最大。此外,人口集聚對提高集聚地區的城鎮化率、人力資本水平和降低地區人口撫養比也有正向作用。
第二,勞動力配置效率層面。史桂芬等(2018)在內生人口增長模型框架下,將勞動力結構和人口遷移因素內生化,采用中國31個省份2001~2015年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發現,人口遷移促進不同地區的不同層次的勞動力不斷流動,技術工人向經濟發達地區集聚,使勞動力結構與勞動力需求結構相匹配,人口遷移通過優化地區間勞動力配置效率促進了經濟增長。
第三,定量層面。周天勇(2018)將沒有體制限制的經濟增長各方面應有水平和實有狀況間的差距界定為人口流動受阻導致的損失,測算認為,2016年遷移受阻造成的損失占當年全國居民總收入的11.29%,造成消費需求損失占當年居民消費總額的18.52%,勞動力被迫窩積于農村產生勞動力產業錯配,造成的損失占當年GDP的12.13%。
第四,城市創業活躍度層面。葉文平等(2018)拓展了創業研究的經濟地理和制度分析,從流動人口的視角揭示了不同地區之間創業活躍度的差異之謎。他們將異質性社會個體與企業家創業的職業選擇假設引入垂直聯系的自由企業家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 with vertical linkage,FEVL)中,并采用我國56個城市2010~2014年面板數據實證考察發現,流動人口比例會提高城市創業活躍度,城市流動人口規模越大,創業活躍度越高。其中,較大的市場規模、較強的知識溢出效應與較低的中間品價格是城市吸引流動人口,特別是創業型個體的重要因素,這類流動人口對城市創業活躍度的提高發揮主要作用,同時,流動人口對城市創業活躍度影響還受到城市的市場化程度和互聯網水平的正向影響。
2.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
學者們在繼續關注子女教育政策等影響人口流動的傳統因素的同時,也將更多新興因素納入研究框架,進一步豐富了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研究。
第一,隨遷子女教育政策。李超等(2018)利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隨遷子女教育政策改革、升學限制門檻低對流動人口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且對農民工家庭的遷移距離有正向作用,其中異地高考試點對農民工流向影響最為明顯,證實了教育供給水平高的沿海發達地區面臨更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壓力。
第二,房價、子女教育和空氣質量。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流動人口開始越來越多地將教育資源、居住條件和環境污染程度等因素作為遷移的考慮因素,李國正等(2018)在關注子女教育問題的同時,發現房價和空氣質量也在影響人口流動。他們采用2012~2015年國家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結果,通過面板數據隨機效應模型研究發現,房價提高、空氣質量惡化都對居留意愿有顯著負向影響,流動人口不僅關注房價,也越來越重視生活環境和身體健康;而高等教育水平提高有利于提升流動人口居留意愿,顯示了流動人口越來越注重隨遷子女的教育質量。
第三,市場規模、地理距離、市場機會和工資。余運江等(2018)從人口流動的省際流動和省內流動兩個維度分別研究人口流動的影響因素,發現市場規模對省際、省內流動都有顯著影響,且這一影響作用隨時間不斷增強,其中第三產業市場規模對省際流動的影響持續增強,但對省內流動的影響則在減弱。市場潛能是省際流動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地理距離和就業機會也對省際流動具有顯著影響,而影響省內流動最主要的因素是工資。
3.高學歷人口流動。
作為人口紅利最主要的載體——高學歷人口流動開始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學者們主要從高學歷的區域流動方面進行了研究。例如,童玉芬等(2018)基于“中心—外圍”理論構建空間滯后模型測度京津冀高學歷人口的空間集聚形成機制,發現以北京、天津為中心,河北為外圍的高學歷人口空間集聚格局已經形成,北京和天津不僅具有“虹吸效應”吸引高學歷人口,同時也具有“溢出效應”促進河北相鄰地區提高人口集聚力。張劍宇等(2018)利用吉林大學2013~2017年畢業生就業數據和地區經濟數據實證研究發現,男性高學歷人才流失明顯高于女性,東北生源畢業生留在東北工作的意愿明顯高于外地生源畢業生,本科生和碩士生相比于博士生更傾向于在畢業后離開東北,自然科學專業的畢業生在畢業后相比于社會科學畢業生也更不愿意留在東北工作,而想進入國有單位的畢業生大多選擇留在東北。畢業生去經濟發達地區就業的傾向在本科生和碩士生中更為強烈,東北地區較低的房價是吸引畢業生留下的重要因素。
(三)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人口結構對經濟影響的研究一直是近年來學界研究的重點,2018年學者們繼續重點從人口老齡化角度深化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各方面影響的研究。
第一,對整體經濟增長的影響。圍繞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學者們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但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齊紅倩等(2018)指出,之所以存在比較多的分歧,理論上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口老齡化因素和經濟增長要素的多元性,使得人口老齡化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是復雜的、路徑是多維的;實證上的原因主要在于,大多學者采用一些線性模型,且衡量指標選擇不統一。為此,他們使用面板平滑轉移回歸模型(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PSTR)在非線性框架內進行實證檢驗,發現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非線性的,且存在顯著的門檻特征,在我國當前階段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是正向和積極的,表現為倒“V”型曲線關系。此外,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嚴重的區域不平衡性和滯后效應。
第二,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部分學者認為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升級存在負面影響。如趙春燕(2018)運用門檻回歸模型,利用1998~2015年30個省份的省級面板數據實證研究發現,總體上我國人口老齡化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存在負向影響,且存在顯著門檻效應。在跨越人口城市化率、平均人力資本積累和高學歷人力資本積累的門檻值后,老齡化對產業結構升級有正向作用,但我國僅有北京、上海等四個省份“跨過門檻”,說明我國仍處于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影響的初級階段,老齡化阻礙了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然而,也有部分學者認為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升級存在正向影響。如逯進等(2018)考慮人口遷移與老齡化的交互作用,利用1993~2015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存在正向影響且影響強度隨著人口遷移逐漸增強。隨著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人口遷移對產業結構的邊際作用由負轉正且正效應逐漸增強,其內在機理在于:人口老齡化促進了人力資本積累,倒逼企業提升技術和人力資本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同時也通過降低勞動生產率、增加社會保障負擔和擠出科教支出等途徑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負向影響。
第三,對儲蓄率的影響。李超等(2018)指出,根據生命周期消費理論,老齡化會導致負儲蓄增大,儲蓄率下降,而根據第二次人口紅利理論,老齡化將由于預防動機而使儲蓄率上升,他們利用2010~2014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面板數據實證研究發現,老齡化顯著提高了中國微觀家庭儲蓄率,且這一正向影響在收入水平較低的家庭和農村、中西部地區更為顯著,證明預防動機對儲蓄率的正效應大于生命周期消費模式的負效應,中國收獲了第二次人口紅利。此外,老齡化對儲蓄選擇和儲蓄規模都有顯著正向作用。王樹等(2018)通過引入雙向代際因子對四期戴蒙德模型進行動態演化分析,利用1997~2015年省級動態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二次人口紅利理論在我國適用,少兒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作用,而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有正向影響。隨著收入增長,少兒撫養比對儲蓄率的負效應持續減弱,老年撫養比的正效應則不斷增加。
第四,對宏觀政策調控有效性的影響。李建強等(2018)在標準新凱恩斯理論框架內引入年齡異質性行為人主體,保留財富分配轉移常用的跨期迭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OLG)實證研究發現,人口老齡化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下降。財政政策方面,人口老齡化除了加重財政養老負擔外,更損害財政刺激效果和財政績效質量,壓縮財政政策發揮空間。貨幣政策方面,老人主導的社會對通貨膨脹率的容忍度下降而使得利率調整更易逼近下限,加大貨幣政策操作難度,被迫提高非常規貨幣政策使用頻率。
第五,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葉小青等(2018)針對不同地區的異質性,通過構建交互效應動態面板分析模型,利用1999~2016年31個省級數據的實證檢驗發現,老年撫養比與房地產價格的關系在東部地區呈負相關關系,在中部地區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在西部地區不具備統計上的影響。原因在于東部地區財富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體手中,而中部地區老年群體擁有的財富占主要地位。總體來看,我國房地產市場尚未出現明顯泡沫,但泡沫風險仍然存在,其中東部地區風險最大,此外房地產政策可以有效抑制過熱房地產且存在地區異質性。
(四)“二孩”政策效果評估與預測
“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的“二孩”政策目前基本具備了評估政策效果的條件,為此學者們對新的人口政策實施效果進行了評估和預測。
1.新人口政策效果評估。
第一,“二孩”政策對未來人口數量的影響。學者們對“二孩”政策實施效果的實證研究大部分都得出了政策“遇冷”的結論,主要表現為家庭生育意愿不高。例如,靳衛東等(2018)建立了關于城鄉家庭生育政策的成本收益模型,基于家庭微觀調查數據發現,農村家庭生育成本迅速增加對其生育意愿產生明顯負向影響,城鎮家庭的生育成本壓力緩慢下降,“二孩”生育意愿小幅增長,從城鄉兩方面因素綜合來看,總體意愿生育水平呈下降趨勢。付文(2018)選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數據對“二孩”意愿偏低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二孩”政策“遇冷”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生育成本增長、生育觀念轉向重質而不是重量、無人照看、政策尚不健全、教育水平升高和城市化。然而,石人炳等(2018)在對生育政策“遇冷”的含義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利用2013~2017年湖北、湖南兩省的總和生育率數據調查發現,生育政策調整的近期效果明顯,但生育政策調整的中長期效果不能適應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要求,不改變現有政策的情況下中國將進入人口總量快速縮小、人口結構老化嚴重的社會。
第二,“二孩”政策對未來經濟增長的影響。王浩名(2018)研究發現,0~9歲出生人口增加經過大約15年后會對經濟產生促進作用,也使儲蓄、個人工作時間、利率和通貨膨脹出現明顯變化,有利于促進投資的快速提高。“二孩”政策保證20~29歲年齡組有充足數量的人口以促進經濟長期增長,30~39歲、40~49歲和50~59歲年齡組人口結構轉變則在中期(15年左右)促進經濟增長,從長期(20年左右)來看這三組人口結構轉變不利于經濟發展。
2.“二孩”政策對未來人口結構的影響預測。
王浩名(2018)根據2015年《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和2010~2014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以及中國家庭幸福感熱點問題調查等相關數據,估算“二孩”政策下潛在受益育齡婦女人數和生育意愿,從而預測了2016~2036年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研究發現,由于“二孩”政策的激勵,0~9歲出生人口在2016~2020年增長較快,該年齡組人口比重提高較快,2020年后增速有所下降,但總體仍然表現為上升趨勢;主要年齡組人口比重出現波浪式變化,其中20~29歲年齡組人口比重波浪式上升,30~39歲和40~49歲年齡組人口比重波浪式下降;60~69歲高年齡人口組波浪式上升;70歲及以上年齡組人口比重波浪式變化,但基本穩定。
茆長寶等(2018)通過對0~14歲少兒人口和65歲以上老年人口在“二孩”政策下的變化進行場景模擬分析,2018~2050年少兒人口經歷增長、迅速減少、緩慢減少三個階段,整體呈現明顯下降趨勢,而老年人口整體上經歷增長、短暫平穩、增長、平穩四個階段,中國未來將不可避免地進入超少子化和超高齡化狀態。前者約出現在2030年前后,而后者將于2037年前后出現,中國將在2028年前后進入少子老齡化社會,并將在2050年前進入超少子化、超高齡化并存的人口年齡結構狀態。
二、資源經濟學
能源、水資源和礦產資源仍然是資源經濟學關注的重點,同時,學界對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研究更加深化和系統化。
(一)能源
關于能源問題的討論,仍然主要集中在能源需求和能源效率兩個方面,但研究的具體內容和重點發生了明顯變化。
1. 能源需求。
關于能源需求的研究,從過去單純測算未來能源需求變動,轉向通過更加客觀地分析判斷未來能源需求變動方向,以提高能源政策的合理性。為此,學者們將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行業的能源回彈效應、金融因素納入能源需求研究模型,完善了能源需求研究的分析框架。
第一,將當前所處階段納入能源需求研究分析框架。2012年以后,我國煤炭需求增長與經濟增長出現背離,對該現象給出合理解釋就能夠更準確地預測未來對煤炭的需求,從而對未來的能源和環境政策有很強的指導意義。林伯強等(2018)以投入產出方法建立經濟增長的結構變動與能源需求相關聯的模型,研究發現,煤炭需求增長在2012年后慢于經濟增速,主要是因為受經濟周期影響大的固定資本形成減少造成的。如果中國經濟維持中高速發展,煤炭需求可能仍需要保持較高增速。產業結構變動以及非化石能源對電煤的替代都會導致煤炭需求的變化,更快的低碳轉型將可能以一定程度的“去工業化”為代價。因此,不同情景的資本形成增長存在很大差異,會對長期經濟增長造成影響。因此在制定能源與環境政策時,需要考慮到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注意能源、經濟和環境之間的平衡。要避免過快地“去煤化”,煤炭“去產能”需要考慮未來煤炭需求,避免大量產能永久性退出可能造成的“矯枉過正”。
第二,將不同行業能源回彈效應納入能源需求分析框架。能源回彈效應,即由于能源效率提高而促進經濟增長所增加的能源需求與理論節能量之比。馮烽(2018)考慮到行業間經濟聯系和結構變動對能源效率的影響,通過編制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價值型能源投入產出可比較序列表,發現1997~2012年整體經濟能源回彈效應并不強,能源消費量增長主要是由于經濟規模的快速擴張,提高能源效率仍將是未來很長時間重要的節能降耗手段。由于能源回彈效應具有明顯的行業異質性,節能減排政策的制定應當根據綜合能耗和能源回彈效應的行業異質性,從整體經濟結構的角度對不同行業采取不同的節能減排政策。
第三,將金融發展水平納入能源需求分析框架。陳志剛等(2018)利用1997~2015年我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將金融發展水平分為信貸規模、證券市場融資規模、金融業競爭程度和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規模四個維度,通過門檻回歸模型實證分析金融發展對能源消費的影響和渠道,發現隨著經濟增長水平上升,信貸規模和金融業競爭程度對能源消費影響呈倒“U”型,證券市場融資規模對能源消費存在負向影響,FDI規模對能源消費影響則保持正向關系。從影響渠道來看,經濟增長渠道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技術創新渠道沒有充分發揮作用。
2.能源效率。
對能源效率的研究不再主要集中于影響因素,而是對能源效率的測度方法和相關產業的能源效率進行分析,以使研究結果更加科學合理,從而對節能降耗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議。
第一,改進能源效率測度方法。李雙杰等(2018)認為,當前測算能源效率存在大量使用單要素指標和選取的投入產出指標存在遺漏或重復兩大問題,他們將投入要素間的組合、替代納入分析框架,并調整了選取指標,選擇投入導向的DEA模型對全要素能源效率測度方法進行了修正,構建了一套新的能源效率測算指標體系。他們利用中國30個省份2005~2015年面板數據對修正方法進行實證檢驗發現,修正后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測算方法得到的結果與單要素指標體系測算結果存在較大差異,2005~2015年大部分省份的工業全要素能源效率逐步上升,證明能源利用效率的廣泛提高。為此,他們指出,在涉及工業的節能政策中不宜過分強調能源生產率或能源強度等單要素指標,應當使用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標,注重產業結構升級的節能效果和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的節能效果,并依靠全社會整體節能。
第二,國際貿易細分行業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響。劉葉(2018)也運用能源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標,將國際貿易細分為中間產品進口、中間產品出口、非中間產品進出口等分別驗證了其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響,發現行業國際貿易總量、出口總量和進口總量與能源效率之間均不具有顯著相關關系,但是中間產品進口總量和中間產品出口總量與能源效率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前者呈正相關關系,后者呈負相關關系。意味著我國中間產品出口落入“污染天堂假說”陷阱,而中間產品進口卻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
(二)水資源
關于水資源問題的研究,學者們主要集中在繼續從不同角度深化水資源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和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區域收斂性研究上。
1.水資源對經濟增長的約束。
第一,對城鎮化的約束。隨著城鎮化的不斷發展,水資源逐漸成為約束城鎮化進程的因素之一。秦騰等(2018)以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為研究對象,選取1998~2015年的面板數據對城鎮化進程中水資源約束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在水資源充沛的沿長江地區,水資源對城鎮化的約束依舊存在,年均城鎮化發展速度由于水資源約束降低了0.6%。在11個樣本省市中,上海和浙江城鎮化未受到水資源的約束,江蘇、重慶和云南表現出較強的約束特征,可能是由于水資源利用效率低和無序城鎮化,安徽、貴州等省份表現出較弱的水資源約束,受約束地區分布表現出明顯的空間集聚效應。
第二,工業活動相對性缺水。武萍等(2018)將人均水資源豐富的青海作為研究對象,界定了生態水資源基尼系數的概念和計算方法,測算出2015年青海水資源與農業產值、工業產值、人口的生態水資源基尼系數分別為0.6763、0.7956、0.7421,反映出水資源與各行政區的農業產值、工業產值和人口匹配極不平衡,表現出相對性缺水。不同行政區的水資源分配與其人口規模不匹配,而工業活動是導致水資源空間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2.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區域收斂性。
大量的研究都認為不同地區的水資源利用效率存在明顯差異,如丁緒輝等(2018)估算了2003~2015年各省份水資源利用效率后發現,水資源利用效率總體上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發展趨勢,研究時限內絕大多數省份水資源利用效率均有大幅度提升,但東、中、西部水資源利用效率存在顯著差異,京津滬等省份水資源利用效率最高,西北省份效率最低。但是關于不同地區間水資源利用效率是否具有收斂趨勢,學者們的研究存在明顯分歧。
有的學者認為,區域間水資源利用效率差異呈現不斷收斂的趨勢(丁緒輝等,2018)。例如,周迪等(2018)選用2003~2015年我國31個省份的用水量和GDP數據研究證明,我國區域水資源利用效率表現出明顯的俱樂部趨同現象,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四類不同俱樂部間流動性較低,水資源利用效率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即鄰近地區較高的水資源利用效率對本地區用水效率提高有正向影響,鄰近地區用水效率較低則有負向影響。
然而,也有學者認為,區域間的水資源利用效率不存在收斂特征。例如,劉鋼等(2018)以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2013年的截面數據為例,用水足跡強度反映省市的水資源利用效率。研究發現,長江經濟帶各省市水足跡強度具有顯著的空間分異特征,上游地區除云南外,水足跡強度從西到東呈遞減格局,中游從西到東呈平緩格局,下游水足跡強度波動劇烈。長江經濟帶各省市水資源足跡強度差異較大,不具有顯著的集聚特征,這種空間分異特征主要來源于區域內差異。馬劍鋒等(2018)從區域農業用水效率空間溢出效應影響因素的角度,一定程度上為區域間的水資源利用效率不存在收斂特征提供了一種解釋。研究發現,在東部地區,其他省份的技術進步對本省份農業用水效率有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但其他省份的效率趕超對本省份有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在中部地區,其他省份的技術進步通過地理距離臨近模式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在西部地區其他省份的技術進步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并且溢出效應隨經濟發展水平的接近而增強,在中西部地區其他省份效率追趕的溢出效應均不顯著。
(三)礦產資源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越來越多的礦產資源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2018年學者們對鉻礦和相關稀有礦產資源需求進行了預測。
1.鉻礦需求預測。
鉻礦是一種重要的戰略性礦產資源,然而當前我國鉻礦的國內供給遠小于國內需求,因而對于鉻礦的相關研究相當重要。鄭明貴等(2018)基于1997~2016年的統計數據,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對我國鉻礦需求影響因素進行選擇研究,發現不銹鋼產量、經濟增長率、工業化率和人民幣匯率是影響我國鉻礦需求的主要驅動變量,我國2020~2030年的鉻礦需求量將逐年遞增,2030年將達到4174萬噸。
2.不同種類礦產資源需求預測。
成金華等(2018)分別構建了26個國家鐵礦石消耗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面板門限回歸模型和中國鐵、鋁、銅、鉛、錫、鋅六種金屬礦產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門限模型,發現產業結構變化與礦產資源需求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多重作用機制,隨著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礦產資源需求的品種正在逐漸增多,需求量也在不斷增加,礦產資源需求由傳統大宗礦產資源逐漸轉向稀有礦產金屬資源。在產業演進過程中,不同礦產資源先后出現拐點,大宗金屬鐵、鋁、銅與第二產業的拐點先到達,并且鋁與銅出現了第二次拐點,此后鉛、錫等金屬的拐點也先后到達,目前鋅與高技術產業之間的門檻效應尚未到來。
(四)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
2018年學界對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進行了大量研究。杜文鵬等(2018)對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中國知網”收錄的圍繞“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為研究核心的295篇文章進行綜合分析后指出,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技術體系的基礎框架已經形成,但編制的方法論及框架體系還處于探討期。圍繞著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編制方法,學者們以水資源、森林資源和土地資源等為例進行了深入探討。
1.自然資源資產和負債的內涵。
石薇等(2018)對自然資源資產和自然資源負債進行界定,認為只有進入經濟體系、參與經濟過程的自然資源才具有相應的自然資源負債,自然資源負債是由于經濟主體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而導致的一種現時義務。
陶建格等(2018)指出,自然資源具有生態功能和經濟功能,其所有者權益主體應該包括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因此自然權益包括生態權益和經濟權益。自然資源負債的產生是由于資源過度損耗、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既有人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是經濟社會為了補償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而需要付出的經濟代價。
閆慧敏等(2018)將自然資源資產負債定義為:在過去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過程中,因自然資源過度消耗和生態環境破壞形成的核算主體的現時義務。自然資源資產負債應該包括資源負債和環境負債兩個部分。
2.自然資源資產負債的界定標準。
關于自然資源資產負債的界定標準,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第一,從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來界定。閆慧敏等(2018)認為,應該從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自然屬性界限和國家政策紅線兩個方面來確定自然資源資產負債核算的方法。陶建格等(2018)也指出,資源環境承載力、相關資源功能規劃和生態約束紅線可以作為自然資源權益與負債的界定標準,自然資源資產首先滿足資源生態權益要求,其次滿足資源經濟權益。當自然資源資產低于界定標準時,產生自然資源負債。自然資源負債無法由自然資源償付,自然資源負債是經濟社會系統中需要進行資源保護和資源修復的活動,需要經濟利益流出來償付。
第二,從可持續發展和非經濟效益的最大可開采量方面來界定。石薇等(2018)指出,不同自然資源的負債臨界值確認方法不同,他們以林木資源為例,認為其負債臨界值應為兼顧林木可持續發展以及非經濟效益的最大可開采量,將超過最大可開采量的消耗量確認為自然資源負債。根據自然資源資產客觀存在和參與經濟過程的兩種形式,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也具有兩種形式,并且兩者之間存在鉤稽關系。
第三,從環境成本核算角度來界定。吳瓊等(2018)從環境成本核算角度出發,提出了基于虛擬治理成本和污染扣減指數的環境負債核算體系,并利用浙江省湖州市2010~2015年的數據進行了核算驗證。2010~2015年湖州市污染治理實際投入大于治理欠賬,污染扣減指數呈下降趨勢,環境負債為45.67億元。
第四,從資源承載能力角度來界定。薛智超等(2018)以土地資源承載能力為標尺,通過新增建設用地的人口承載效率和新增建設用地的GDP承載效率兩個指標,衡量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城市的當前承載狀態、多數城市的平均承載狀態和由少數城市體現的潛在承載能力,并以多數城市的平均承載狀態指標值作為判斷建設用地擴張合理性的依據,進而界定土地資源過耗的核算閾值,建立起土地資源承載力與負債表之間的有機連接,建構了以土地資源承載力為標尺、具有地域針對性和發展階段針對性的負債核算技術。
三、環境經濟學
2018年,環境經濟學在繼續深化環境污染和碳排放的影響因素基礎上,對習近平新時代綠色發展理論、綠色發展水平,以及環境規制政策效果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綠色經濟發展水平
在綠色發展的大背景下,學者們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對綠色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評估,并實證研究了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因素。
1.綠色經濟發展水平評估。
第一,區域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王勇等(2018)基于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統計局、原環境保護部、中央組織部發布的《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對中國大陸除西藏以外的30個省份2013~2016年的綠色發展狀況進行評價,發現我國整體綠色發展水平呈上升趨勢,中國省域綠色發展存在較為明顯的地域性差異,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沿海省份和生態稟賦較好的西南省份綠色發展指數較高。在空間分布層面,綠色發展呈現“俱樂部”收斂特征,主要是源于增長質量的空間集聚以及生態保護的地域性差別。東部和中部省份的綠色發展提升趨勢要快于西部省份。邢貞成等(2018)將生態足跡指標納入全要素分析框架實證分析2000~2014年中國區域的全要素生態效率發現,中國及其中部的全要素生態效率呈現“先下降,后波動”的變化趨勢,東部的生態效率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變化趨勢,西部的生態效率在整個研究期內基本都呈現下降趨勢。中國全要素生態效率的地區分布大體呈現由西北向東南逐步提升的態勢,河北、河南、山東等省份由于區域間的污染排放轉移而出現生態效率塌陷現象。龔新蜀等(2018)運用Super-SBM模型測算中國省域生態效率水平發現,中國區域生態效率在樣本期內呈不斷惡化的趨勢,并表現出較強的空間依賴和空間分異,總體呈東—中—西梯度遞減的空間分布格局。可見,學者們對不同區域的綠色發展水平以及變動趨勢仍然存在不同意見。
第二,工業綠色發展效率。陳瑤(2018)將研發R&D引入環境方向性距離函數(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DDF)模型中,評估國內不同區域工業綠色發展效率,發現相較于傳統要素,我國工業綠色發展的創新要素利用效率更高,但波動程度較大。東部地區的工業綠色發展創新效率均值達到0.91,遠高于其他經濟區域。
2.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
第一,技術進步。胡安軍等(2018)以2005~2015年中國30個省份為樣本,運用系統廣義矩方法(SGMM)識別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發現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兩者之間存在“U”型關系,目前中國處于“U”形曲線拐點的右側階段。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對綠色純技術效率與綠色經濟效率的作用機制一致,但對綠色規模效率僅具有線性作用關系。多樣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顯著為正,而專業化集聚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顯著為負。陳瑤(2018)從工業綠色全要素增長率角度實證研究也發現,技術進步在2009~2013年期間對工業綠色全要素增長率提升作用顯著,2013年以后技術效率的貢獻作用更大。全國及中東部地區的R&D投入強度對工業綠色發展效率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而R&D投入規模以及R&D成果轉化因素則產生負向影響。劉鉆擴等(2018)測評“一帶一路”沿線重點省域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也發現,“一帶一路”沿線中國重點省域GTFP發展現狀總體較好,技術進步是主要動力。“一帶一路”建設對沿線重點省域的GTFP和技術進步均起到了顯著促進作用,影響凈效應分別達0.138和0.156,但研發投入對沿線重點省域的GTFP和技術進步主要表現出抑制作用,但不顯著。
第二,市場分割。孫博文(2018)等利用長江經濟帶2003~2014年的城市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商品及要素層面的市場分割對綠色增長效率存在非線性的影響關系。商品市場分割存在影響綠色增長效率的倒“U”型關系,97%的樣本表現為市場分割對綠色效率的抑制作用。勞動力市場分割與資本市場分割均存在影響綠色增長效率的“U”型關系,分別有100%樣本及87%的樣本表現為對綠色增長效率提升的抑制作用。龔新蜀等(2018)也指出,地方保護主義引致的市場分割導致資源扭曲錯配,技術進步緩慢,不利于生態效率的提升。
第三,外國直接投資。龔新蜀等(2018)實證考察發現,外國直接投資(FDI)對生態效率的直接效應為負,間接效應為正,表明FDI對本地區生態效率的效應為負,但對鄰近地區具有較強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然而,隨著市場分割程度的提高,限制內資企業獲取FDI技術效應的能力與動力,抑制FDI對生態效率的正向溢出效應。邢貞成等(2018)則認為,外資規模對全要素生態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第四,金融發展。葛鵬飛等(2018)使用“一帶一路”的跨國面板數據實證研究表明,金融發展與GTFP負相關,基礎創新能夠緩解金融規模對綠色發展的負作用,基礎創新和應用創新雖能有效弱化金融發展對GTFP的抑制作用,但會加劇金融深化的不利影響。
第五,環境規制、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和貿易等。邢貞成等(2018)研究發現,全要素生態效率與環境規制呈“U”型關系,加強環境規制在長遠上有利于生態效率提升,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均對全要素生態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劉鉆擴等(2018)對“一帶一路”沿線省域的研究發現,經濟發展與GTFP表現為“U”型關系,沿線重點省域的經濟發展水平與GTFP表現為負相關,沿線重點省域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貿易對沿線重點省域的GTFP當前主要表現為負效應,原因是受限于沿線重點省域不合理的貿易結構和研發與經濟水平的掣肘作用。
(二)環境污染
環境污染仍然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學者們主要圍繞環境污染的影響因素尤其是空氣污染的影響因素展開研究。
1.收入差距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占華(2018)將收入差距因素引入環境污染影響因素研究,利用1997~2014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重新研究了引入收入差距因素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假說的適用性。結果發現,考慮收入分配效應后中國的EKC假說依舊成立,長期內污染排放隨人均收入增加而下降的趨勢較為明顯,收入差距與環境污染間存在穩健的倒“N”型非線性關系。總體上收入差距增加不利于環境質量的改善,收入差距的環境效應有著顯著的區域異質性。一方面,東部地區呈倒“N”型關系,西部地區為單調線性關系;另一方面,低收入差距地區的收入差距與污染排放也呈倒“N”型關系,高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擴大反而有利于環境質量改善。人均收入與環境管制是收入差距對環境發揮影響的可能途徑。
2.空氣污染的影響因素。
第一,重點行業。刁貝娣等(2018)以2000~2014年省域PM2.5濃度及相關重點行業為研究對象,實證分析行業驅動因素的時空異質性,發現不同行業PM2.5的影響系數演化趨勢特征鮮明。從時間上看,火力發電行業與鋼鐵行業前期變化顯著,后期逐漸趨于穩定,水泥、建筑行業的系數則在不斷增加后趨于穩定,采礦行業的影響系數不斷減小,供暖行業先減小后增加。從空間上看,不同區域的各產業擬合系數存在空間異質性和空間集聚效應,并表現出與產業重心相應的空間分布格局。火力發電行業較多的影響東部各省,鋼鐵行業則顯著影響著中西部主要的產業轉移接收地,水泥行業對各省域的影響系數有正有負,而余下的建筑業、供暖業和采礦行業的影響則表現出區域特色。
第二,產業協同集聚、貿易開放。蔡海亞等(2018)基于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的研究視角,構建空間計量模型和面板門檻模型,實證考察產業協同集聚、貿易開放與霧霾污染的內在聯系,發現協同集聚對霧霾污染存在明顯的改善作用,在剔除了加工貿易進行修正后,貿易開放對改善霧霾污染發生實質性的轉變。協同集聚與貿易開放交叉項對霧霾污染存在負向影響。貿易開放與協同集聚隨著時間的推移作用從不顯著變得顯著。貿易開放與協同集聚對霧霾污染的作用因兩者發展的不匹配而存在門檻效應。
第三,軌道交通、快速公交系統(Bus Rapid Transit,BRT)。高明等(2018)利用斷點回歸方法,實證考察2014~2016年全國新開通的40條軌道交通線路與24條BRT線路對空氣質量指數(AQI)的影響,發現軌道交通、BRT的開通對空氣質量具有顯著且穩健的改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大小隨城市異質性、交通規模與模式特點的變化而變化。
(三)碳排放
1.碳排放的影響因素。
第一,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孫攀等(2018)基于1999~2014年中國30個省域的面板數據考察發現,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均能促進碳排放減少,特別是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碳排放減少的影響更為強大。由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引致的碳排放空間溢出效應較為顯著。張琳杰等(2018)利用1997~2016年長江中游城市群3省31個城市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長江中游城市群的產業結構高級化相較于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碳減排的效果更好。
第二,國際垂直分工。王敏杰等(2018)采用45個國家(地區)1998~2013年的數據研究表明,國際垂直分工對于碳排放的影響是非常復雜的,直接效應系數為0.1313,一國(地區)直接參與國際垂直分工程度的提高會增加本國(地區)的碳排放。而間接效應的系數為-0.3474,顯著為負,即鄰國(地區)參與國際垂直分工會減少本國(地區)的碳排放。而從世界總體情況看,國際垂直分工會減少世界總體的碳排放。
第三,對外貿易模式。余麗麗等(2018)利用GTAP數據庫實證分析貿易模式效應對中國碳排放凈轉移的影響程度,研究表明,2004~2011年中國對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始終是“污染避難所”決定的污染密集型出口模式,中國與發展中國家貿易的碳排放轉移效應并不顯著,貿易模式效應對中國對外貿易碳排放順差的影響逐漸削弱。
第四,要素市場扭曲和外國直接投資(FDI)。張琳杰等(2018)以長江中游城市群為對象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會導致該區域碳排放量的增加,存在“污染避難所”效應。劉海云等(2018)利用中國2004~2015年30個省份的數據,實證檢驗要素市場扭曲背景下雙向FDI影響碳排放的規模效應也發現,外商直接投資(IFDI)會通過規模效應顯著促進地區碳排放的增加,且要素市場扭曲和對外直接投資(OFDI)會通過促進IFDI的增加而加劇這一正向影響。但是,OFDI會通過規模效應顯著抑制地區碳排放的增加,對于全樣本和低經濟發展水平組,要素市場扭曲對OFDI的影響不顯著,但卻會顯著促進高經濟發展水平組的OFDI,說明要素市場扭曲會通過促進OFDI而抑制地區碳排放;從全樣本和低經濟發展水平組的估計結果來看,IFDI也會通過促進OFDI而加強其對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但在高經濟發展水平組,IFDI的增加則會顯著抑制OFDI。
第五,財政分權、地方政府競爭。田建國等(2018)通過空間溢出效應理論實證分析財政分權和地方政府競爭同碳排放的關系,發現財政分權同碳排放總量水平正相關,財政分權的空間溢出效應為正;地方政府競爭在碳排放問題上存在“趨良效應”;財政分權和地方政府競爭的空間溢出效應具有相似性。財政分權和地方政府競爭都是主要通過空間溢出效應來影響碳排放總量水平。
第六,銀行信貸。吳姍姍(2018)基于增長模型證明銀行信貸通過兩種途徑影響碳排放:一是作用于經濟增長影響碳排放規模;二是作用于技術進步影響碳排放強度。她利用2000~2014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銀行信貸促進人均GDP增長,對碳排放產生規模效應,同時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顯著為負,產生技術效應。工業貸款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卻顯著為正,其技術效應不明顯,規模效應主導碳排放變化,但是當信貸量達到一定規模時,技術效應的減排效果異常顯著。
2.碳減排路徑。
2018年,學者們從新角度提出了減少碳排放的新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優化碳排放責任和額度分配。張同斌等(2018)重新測度15個代表性經濟體的碳排放共同責任后發現,發達國家的共同責任碳排放量高于其生產端責任碳排放量且低于其消費端責任碳排放量,而部分金磚國家共同責任碳排放量則低于生產端責任排放量并高于消費端責任排放量。對責任分擔系數優化后的數據表明,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責任有所上升,土耳其、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碳排放責任維持穩定,而中國和俄羅斯等金磚國家的碳排放責任明顯下降。因此,在共同責任測度優化的基礎上,應根據各國發展的階段特征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完善碳排放的責任核算體系。
第二,多渠道提高能源效率。鐘超等(2018)研究發現,提高潛在能源效率對于實現減排目標的貢獻度最大,且僅通過調整能源結構、經濟結構、人力資本、資本存量或潛在能源效率的單一減排路徑難以實現我國碳強度減排目標,中國若要實現減排目標,必須從能源結構、經濟結構、人力資本、資本存量和潛在能源效率來優化減排路徑。何建坤(2018)也指出,要走上“發展”和“減碳”雙贏的綠色低碳發展路徑,其核心指標是大幅度降低單位GDP的二氧化碳強度。一方面要大力節能,提高能源轉換和利用效率,同時轉變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減少終端能源需求;另一方面是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結構的低碳化,降低單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強度。
第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李小勝等(2018)指出,中國各地區碳排放效率存在較大差距,以考慮效率最大化為目標,各省份二氧化碳重新分配后效率明顯提高。從分配的結果看,發達省份基本都是實際碳排放少于重新分配后的數量,效率低和經濟不發達省份多數處在超排狀態。對于效率低下和碳排放超標的省份,應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否則一旦建立統一的碳排放市場,按照效率分配的原則實施初始額度分配,這些地方的排放額度不足,需要從市場上進行購買,就會加重其經濟負擔,導致其陷入“貧窮的陷阱”。
第四,征收碳稅。碳稅是國際公認的實現碳減排的有效經濟手段。王丹舟等(2018)選取芬蘭、丹麥、瑞典、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日本五個代表性國家(地區)為例研究發現,碳稅征收在實現二氧化碳減排方面具有積極效用,我國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地區)的經驗,通過完善碳稅征收制度來減少碳排放。
(四)環境規制政策效果評估
學者們從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兩個方面評估了環境規制政策的實施效果,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1.環境規制政策的直接效應。
環境規制政策的直接效應主要表現為對環境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大部分研究基本都得出了環境規制政策有利于環境改善的結論。例如,王倩等(2018)采用2007~2015年省際面板數據研究發現,碳交易試點政策促進了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脫鉤,助力中國擺脫“碳陷阱”。但是,在不同區域、不同主體和不同時期,環境規制政策效果存在差異。
第一,環境規制政策直接效應的區域差異。王曉紅等(2018)實證研究指出,省域循環經濟績效對周圍(相近)省域存在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環境規制對循環經濟績效呈現先促進、后抑制的作用。與中西部樣本相比,東部樣本的空間溢出效應較為顯著,不同區域之間存在明顯的空間異質性,節能型與減排型環境規制在促進循環經濟績效提升方面存在互補效應。
第二,環境規制政策直接效應的主體差異。周源等(2018)以浙江省湖州市2011年實施紡織印染行業環境專項規劃為研究對象實證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制定、實施行業性環境政策,顯著降低了相關企業的廢水排放強度,但是并沒有降低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綠色治理政策顯著降低了內資企業、大中型企業的廢水排放強度,而對于外資企業的廢水排放強度影響不明顯。
第三,環境規制政策直接效應的時期差異。黃慶華等(2018)測算2003~2015年中國36個工業行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發現,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與污染減排成本互為格蘭杰因果,但與污染排放強度僅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短期內,近期的環境政策確實能夠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長期來看,不僅不能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增長,還會誘發企業提高污染型經濟產出。
2.環境規制政策的間接效應。
學者們從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和經濟發展水平等角度評估了環境規制政策的間接效應。
第一,環境規制政策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張海玲等(2018)選取2007~2015年CSMAR數據庫收錄的9038個企業樣本實證研究發現,企業基于前沿的技術距離越近,環境治理越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對于臨近前沿型企業,環境治理分別通過自主創新機制和模仿追趕機制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于中間型企業,環境治理主要通過模仿追趕機制提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而對于遠離技術前沿的企業,環境治理未能通過任何一種機制“倒逼”企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第二,環境規制政策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宋德勇等(2018)采用中國35個工業行業2005~2015年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環境規制與勞動生產率之間存在倒“U”型非線性關系,且當前中國正處于倒“U”型的左端,環境規制能夠有效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但兩者相互關系受到行業污染密集程度的影響。資本深化在環境規制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中介效應顯著,且中介效應顯著為正,行業資本深化水平的加深有利于環境規制對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高資本密集行業中資本深化在環境規制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中介作用明顯低于低資本密集行業。
第三,環境規制政策對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王倩等(2018)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碳試點政策的提出與實施,未顯著影響試點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
四、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未來研究方向
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研究針對三大分支學科各自的重點問題不斷深化研究,面對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科存在的融合不足,以及各領域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該學科未來有必要從以下方面加強研究。
第一,加強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學科體系研究。雖然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是理論經濟學下的獨立二級學科,但教育部調整本科專業目錄時,卻設立了“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專業。因此到目前為止,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常常處于割裂狀態,整個學科“研究對象不明確、研究內容和研究體系不嚴謹、缺乏特有的理論概念,體系結構不完整”(童玉芬等,2018)。為加快該學科發展,未來有必要對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學科定位、研究對象、學科體系等進行深入研究,以凝聚共識,提升學科發展水平。
第二,加強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化的內在機制研究。目前,關于人口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大量集中在流動人口和人口老齡化等問題上,但關于當前新的人口政策對未來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影響的內在機制缺乏深入研究,從而導致對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評估以及對未來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化的預測缺乏理論支撐,以至于使得未來勞動力供給難以準確預估,影響了潛在增長率的測算。這就要求加大適齡人口生育意愿調查,深入分析影響生育意愿的各相關因素,準確評估人口出生率,為未來人口政策和經濟政策提供依據。
第三,加強經濟增長中的資源安全問題研究。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和高質量發展的需求,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資源種類不斷拓展,尤其是突破一些關鍵性、基礎性原材料和零部件時所需要的特殊礦產資源,日益成為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經濟安全的重要內容。然而,當前對于特種資源的關注遠沒有置于創新驅動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高度給予應有的關注,如稀土資源、石墨烯資源等。這就要求學界提高支撐經濟增長的資源安全意識,未雨綢繆,增加資源安全和資源戰略布局的前瞻性研究。
第四,加強綠色發展水平評估指標體系和評估方法研究。雖然目前已有部分研究對綠色發展水平指標體系和評估方法進行了探索,但指標體系和評估方法各有不同,從而導致對同一地區的評估結果存在明顯分歧。這說明,在綠色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和方法上學界尚未形成共識,仍然處于百家爭鳴的階段,在當前綠色發展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的新時代,有必要加快推進和完善綠色發展水平評估指標體系與評估方法研究,形成被廣泛接受的、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以明確方向,更好地引導綠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