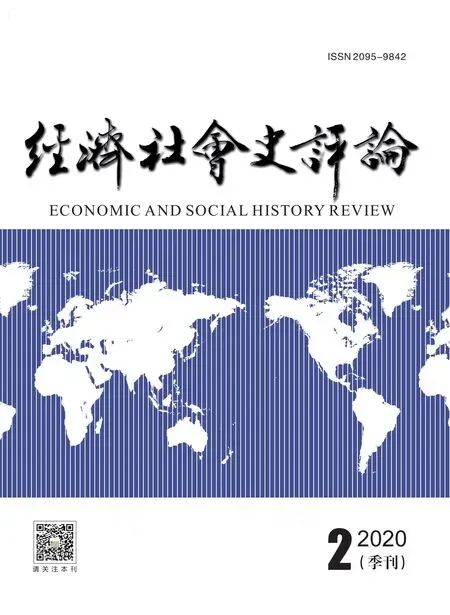中世紀英格蘭官方語言的變遷*
張尚蓮
1066年諾曼征服后,諾曼貴族成為英格蘭新的統(tǒng)治階層,法語和拉丁語也替代古英語成為新的官方語言。這種局面導致英格蘭社會三種語言共用:教會主要使用拉丁語、王室及政府機構使用法語和拉丁語、社會民眾使用英語。三種語言分別由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場合使用。這種現(xiàn)象在1204年諾曼貴族失去諾曼底之前比較明顯,之后由于社會語境發(fā)生變化,三語之間尤其是英語和法語的關系也發(fā)生了顯著變化。這種語言地位此消彼長的變化一直持續(xù)到16世紀。
一、諾曼征服前后英格蘭的語言與社會語境
早期英格蘭社會三語并存的現(xiàn)象,與當時社會語境和具體使用人群的特征密切相關。
中世紀早期,英格蘭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結構屬于典型的莊園經濟。莊園是西歐封建社會的基本單位,如伯爾曼所言,是自治的社會共同體。①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tǒng)的形成》,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第129頁。無論是莊園主,還是莊園里的農民,彼此相互依賴。“等級和依附性是中世紀西歐社會兩個重要的特征。”②王亞平:《西歐中世紀社會等級的演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頁。莊園的管理以及莊園生活的運轉不是依靠王室的強權和行政命令,而是依靠莊園法律。莊園法律決定莊園內一切大小事務,規(guī)定人們能夠做什么,不能夠做什么。廣大民眾與王室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被統(tǒng)治關系,農民日常接觸的是莊園里的成員,莊園生活與王室的聯(lián)系非常松散,因此,即便王室想在語言政策上有所動作,其推行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中世紀英格蘭農民的識字率很低,這種狀態(tài)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原因。在中世紀中期以前,與寫字、拉丁語和基督教這些少數(shù)人的文化并行的,是一個由異教徒民間傳統(tǒng)和英雄詩歌組成的本土大眾文化。③陳宇:《中世紀英格蘭民眾文化狀況研究》,《歷史教學》2006年第11期,第24—27頁。這種本土文化以口頭傳承為主要形式,讀和寫與農民的生活距離太遠。教士和社會上層壟斷教育,“任何針對普通人的有關初等教育的證據(jù)都非常罕見”。④M.T.Clanc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6.大多數(shù)民眾處于文盲狀態(tài),推行官方語言缺乏必需的社會基礎。在諾曼征服后的百年間,諾曼貴族無暇顧及英格蘭事務,而諾曼出身的人口僅占英格蘭總人口的5%—10%,推行法語也缺乏實際的動力和需求。因此,在英格蘭的諾曼貴族采取了相對溫和的態(tài)度,三語現(xiàn)象從一開始就有一個相對寬松的社會語境。
在西歐中世紀,拉丁語一直是正式文本用語,英格蘭也不例外。英格蘭王室或政府頒布令狀多用拉丁語,尤其是特許狀,拉丁語是不二選擇。更為突出的是教會使用拉丁語。從6世紀末開始,基督教逐漸傳播到整個英格蘭。⑤比德:《英吉利教會史》,陳維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67頁。在大部分英格蘭民眾不識字情形下,具有讀寫能力的教士自然成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在傳播和解釋教義過程中具有絕對的權威。他們的拉丁語成為高高在上的宗教語言,是教士壟斷知識的重要工具。諾曼征服后陸續(xù)到達的諾曼教士,除了母語法語一般也都接受過拉丁語訓練,他們大部分也具備英語能力,但是拉丁語作為宗教正式用語的地位并沒有發(fā)生變化。羅馬教會曾一度極力反對將《圣經》翻譯成英語,并對譯者進行人身迫害。拉丁語和法語的壟斷直至黑死病之后,大量通曉拉丁語或法語的教士死亡,教會才不得不補充新的只會講英語的教士。
諾曼征服后,英格蘭官方使用的語言是諾曼法語(Norman French),與巴黎地區(qū)的法語有很大差別。諾曼貴族蜂擁而至,英格蘭原有貴族階層幾乎被滌蕩一空。1072年,英格蘭12個伯爵中只有一人是英格蘭貴族,這個英格蘭貴族在4年后被殺。幾乎所有英格蘭上層社會的重要職位和大型莊園均被諾曼貴族占據(jù)。兩個大主教均為諾曼人,各地修道院院長一旦出現(xiàn)空缺,往往被外國人填補。1075年,21個修道院院長中有13個英格蘭人,12年后,英格蘭人只剩下3個。①Albert C.Baugh & Thomas Cable,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1993, p.102.其他基層教會機構的情況基本類似。很多法國僧侶到英格蘭謀取機會,英格蘭教會的諾曼化已不可避免。留駐英格蘭的普通諾曼人,多為保護諾曼貴族和諾曼教士的士兵。
除了諾曼貴族外,跟隨貴族而來的御用文人以及后來受過良好法語教育的英格蘭本土御用文人,也使用法語。威廉一世的女兒(Adela)就是眾多詩人的庇護人(patron),他的兒子亨利一世先后娶的兩個王后(Matilda和Adelaide of Louvain)也對許多詩人進行庇護。這些御用文人在王室的資助下,寫了大量的詩歌、編年史和傳奇文學,以迎合諾曼貴族的口味和實際需要。②Dialogus de Scaccario (1177), Stubbs, Select Charters (4th ed., 1881), p.168.這樣,英格蘭在12世紀出現(xiàn)了許多法語文學作品,堪稱奇觀。另外,來自歐洲大陸的商人和手工業(yè)者也相應形成了法國人聚居區(qū),至今一些地點仍然存在。③K.J.Holzknecht, Literary Patronage in the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George Banta, 1923, p.12.
在英格蘭的諾曼人,貴族和處于底層的諾曼民眾,使用英語和法語的動力有所不同。諾曼貴族對英語可以用“無暇顧及”來描述。威廉一世43歲時曾經打算學習英語,但是由于國事繁忙,最終沒有投入多少精力,因此沒有取得實質上的進步。威廉之后的200年間,諾曼貴族學習英語的動力不大,法語依然是上層社會主要的交流工具。這種現(xiàn)象的實質原因在于,英格蘭的諾曼統(tǒng)治階層與歐洲大陸的聯(lián)系一直非常緊密,他們對歐洲大陸事務的關注遠遠超過對英格蘭事務的關心。國王威廉死后不僅葬在諾曼底,而且把他認為最重要的諾曼底分給了自己的長子,把英格蘭分給次子。亨利二世時期,英格蘭在法國的領地繼續(xù)得以擴張。亨利二世同時還是安茹伯爵,他從父親那里繼承了安茹地區(qū)和曼恩地區(qū)。亨利二世與阿基坦的埃莉諾(Eleanor of Aquitaine)結婚,又獲得了法國南部大片地區(qū)。從這個意義上說,亨利二世作為英格蘭國王,還占有2/3的法國領土。因此,英格蘭國王往往把大量精力投入法國事務。威廉一世(1066—1087)和威廉二世(1087—1100)在任期間都有一半時間駐留在法國。亨利一世(1100—1135)35年的任期內,在英格蘭只待了6年。亨利二世(1154—1189)在位34年有21年在大陸度過。查理一世(1189—1199)在位10年間,在英格蘭本土只待了6個月,創(chuàng)下全世界君主在自己國家本土駐留時間最短的記錄。斯蒂芬(1135—1154)雖然在任期內留住英格蘭,但他與從不講英語的親戚為爭奪王位連年征戰(zhàn)。不僅國王如此,英格蘭的諾曼貴族同樣在法國擁有大量土地或產業(yè),加之大量的跨海婚姻,英格蘭貴族處理大陸各種事務的時間和精力,也大大超過其在英格蘭本土所花的時間和精力。這種狀況持續(xù)到約翰失去在法國的領地才得以改變。
由此可見,英格蘭上層社會保持使用法語的語境,存在于處理諾曼底乃至整個歐洲大陸的事務當中。諾曼貴族在1200年失去大量歐洲大陸地產之前,對英語的學習和使用尚未提到議事日程。
然而中下層諾曼人在講諾曼法語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學會了說英語,從而具備了雙語或準雙語能力。因為無論是莊園的管家、護院的兵丁,還是牟利的商人或手工業(yè)者,他們都必須與當?shù)氐挠⒏裉m本族人打交道。這個語言使用環(huán)境與諾曼貴族的語言使用環(huán)境一樣都是剛性的,只不過諾曼貴族的語境是法語,中下層諾曼人的語境是英語。與此同時,廣大英格蘭本族人,尤其是與諾曼人有較多業(yè)務往來的群體,也不可避免地接觸到法語,從而具備了一定的法語能力。英吉利人和諾曼人長期混居、互相通婚,加快了彼此雙語能力的形成與提高。在亨利二世統(tǒng)治年代(1189—1199),人們已經很難辨別誰是諾曼出身、誰是英格蘭出身了。①李賦寧:《英語民族標準語的形成與發(fā)展》,《西方語文》1958年第1期,第37頁。13世紀末的一位詩人說,“100個普通人當中不懂法語的也就是鳳毛麟角”。法語在中下層諾曼和英格蘭民眾中也有一定規(guī)模的使用。
諾曼征服后,官方用語和文學用語轉向拉丁語和法語,但是,廣大英格蘭民眾仍然以英語為口語。作為口語的英語不僅沒有死亡,而且生機勃勃地繼續(xù)發(fā)展著。沒有證據(jù)表明英語成為皮欽語(pidgin)②指由不同種語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語。從純粹語言學的觀點看,皮欽語只是語言發(fā)展的一個階段,指在沒有共同語言而又急于進行交流的人群中間產生的一種混合語言,屬于不同語言人群的聯(lián)系語言,往往沒有文法、只是具備非常簡單的溝通功能。或克里奧爾語(creole)③新一代混居人群母語、相對規(guī)范、有一定文法的皮欽語。。90%的英格蘭兒童沒有在法語出現(xiàn)后放棄學習英語,英格蘭人也沒有故意使英語效仿法語的文法。④Manfred G?rlach, “Middle English—a Creole?” in D.Kastovsky and A.Szwedek eds., Linguistics acros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2 vol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amp; Co., 1986), I, pp.337, 338.英語的命運之所以區(qū)別于法語在海地的命運(法語在海地最終成為非洲黑奴所使用的皮欽語和他們后代所使用的克里奧爾語),原因可能在于說兩種語言人群之間的關系。諾曼征服之后,英格蘭人和諾曼人都是英格蘭臣民,民族融合的趨勢遠遠大于民族對立。中下層的諾曼人與英格蘭人,地位日益趨同,生活每天往來,只言片語的皮欽語顯然不能滿足復雜的交際溝通功能。這完全不同于在海地的法國殖民者與非洲黑奴之間,命令與服從之間的簡單溝通關系。
在英格蘭社會,英語的使用除了官方和文學領域外仍然比較活躍。一些英格蘭人努力學習法語,一些諾曼人也在積極學習英語。一些教士除了講拉丁語、法語外,英語水平也相當高。⑤Albert C.Baugh and Thomas Cable,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104.1204年,約翰失去諾曼底之后,英語迎來了快速上升的社會語境。
二、英王約翰失去法國領地后社會語境的變化
1204年,諾曼底被法國國王菲利普沒收,英格蘭的諾曼貴族被迫重新考慮在英法兩地的產業(yè)孰重孰輕。在失去諾曼底之前,許多英格蘭貴族在英法兩地均持有地產,很多情況下很難說清楚自己是英格蘭人還是法蘭西人。諾曼底的喪失標志著英國對抗法國的開始,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兩國貴族陣營的分裂和財產重組。1204至1205年,法國國王宣布沒收在英格蘭持有房產的幾大貴族的田產,這個舉動令所有在兩國均有產業(yè)的法國貴族被迫做出決定,是放棄在英格蘭的產業(yè),還是放棄在法國的產業(yè)。一些大貴族由于在英格蘭的產業(yè)規(guī)模較大而宣布放棄在法國的產業(yè)。①Manfred G?rlach, “Middle English—a Creole?” in D.Kastovsky and A.Szwedek eds., Linguistics acros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I, pp.337-338.英格蘭國王約翰作為報復,也采取了類似政策。一些貴族在兩方壓力下,將海峽兩岸的產業(yè)互相置換,以求減少損失。但是這樣的置換僅限于家族內部,到1250年,雙方懲罰性的田產沒收政策結束后,兩邊的貴族基本站隊完畢。此后,英格蘭諾曼貴族不再看重族源,而把自己看作英格蘭本土居民,法語賴以依存在的使用語境逐漸消失,②Albert C.Baugh and Thomas Cable,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119.英格蘭諾曼貴族自身民族意識開始發(fā)軔。
此外,對大量由法國南部進入英格蘭的法國人的排斥和反感,也是推動英語地位上升的重要誘因。這類法國人被英格蘭本地人稱為外國人(foreigner),他們沒有英格蘭國籍,在英格蘭本地人包括諾曼出身的英格蘭人看來,他們純粹為投機和攫取財富而來。稱他們?yōu)椤巴鈬恕北旧砭头从吵鲐撁嬖u價。從約翰時期,這種法國人開始涌入英格蘭。因為約翰的王后來自法國的普圖瓦地區(qū),一位來自普圖瓦地區(qū)的教士憑借王后的提攜當上了溫徹斯特主教,后來竟升任大法官(Chancellor)和英格蘭最高司法官(Justiciar of England)。一個外國人的發(fā)跡帶來一大群親信隨從,英格蘭人與外國人的對立情緒開始產生。到亨利三世時期,這種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受母親的法國背景影響,亨利的個人品味、愛好以及社會關系也高度法國化。1236年,亨利三世通過與普羅旺斯伯爵家族的婚姻關系,使自己成為法國國王路易九世的連襟。不僅如此,兩個人還分別促成了各自的弟弟與自己的妻妹成親,從而把英法兩國關系從劍拔弩張急轉成密切聯(lián)系。這種密切聯(lián)系又造成新的大規(guī)模的法國人“入侵”英格蘭。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來英格蘭享受榮華富貴。一份年鑒寫道:“我們的英格蘭國王用大量的土地、財產和金錢養(yǎng)肥了王后的親戚們。這樁婚姻與其說是給他帶來財富,還不如說是把他消耗一空。”③Albert C.Baugh and Thomas Cable,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122.
13世紀法國人的蜂擁而至影響了英格蘭上層社會使用英語的進程。但是,對那些已經在英格蘭經營了一代或幾代的諾曼出身的英格蘭人來說,這些新來的法國人使他們更加認識到自己與他們不同。這個不同之處的標志就是這些法國人并不會講英語。這從一個側面印證了英格蘭諾曼人已經產生了英格蘭民族情結,英語使用的本土社會語境進一步得以拓寬。
三、百年戰(zhàn)爭中英格蘭民族意識的形成及英語的使用
英法百年戰(zhàn)爭從1337年開始到1453年結束耗時117年,是英國從屬西歐大陸走向自我發(fā)展的重要歷史階段。百年戰(zhàn)爭雖然以英國勢力全部被趕出法國而結束,但是戰(zhàn)爭期間卻大大促進了英語的使用。
百年戰(zhàn)爭期間,“黑死病”反復發(fā)作,奪去了歐洲大約1/3的人口,許多歐洲學者失去生命。歐洲大陸30 所大學關閉了5所。英國劍橋大學的40位教授死了16位,牛津大學的學生人數(shù)從3萬降到6千人。大學對拉丁語的學習和研究十分嚴格,由于懂拉丁語的教師大量減少,也來不及培訓新教師,因此許多大學只得放棄拉丁語教學。①李荷:《災難中的轉變:黑死病對歐洲文化的影響》,《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第154頁。神職人員也無法逃脫黑死病,修道院長的空缺只得讓只會英語不懂拉丁語及法語的人來接任。②羅伯特·麥克拉姆等:《英語的故事》,秦秀白等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86頁。這種情況雖然導致拉丁語教育的衰落,卻在客觀上有利于整個歐洲教育體制的變化。它促使教育變得更實用、更世俗化,向方言轉化更快。這些變化既包括歐洲普遍從拉丁語轉向方言,也包括英國官方語言從法語向英語的轉化。有人描繪說:“我想,沒有人說拉丁語了,但受過教育的人仍懂拉丁文;有些人會法語,但不說拉丁語,他們多在宮廷供職并在那里生活。有些人偶爾使用拉丁文,卻不懂其寫作技巧。不懂拉丁文和法文的人,卻都通曉英語。不論是平民還是受過教育的人,也不論是年輕人還是老人,大家都通曉英文。”③羅伯特·麥克拉姆等:《英語的故事》,秦秀白等譯,第86頁。
百年戰(zhàn)爭后,英國不再無謂地征服法國。以前在法國有大片領地的英國貴族不能再重回大陸,英國成了他們真正的家。百年戰(zhàn)爭大大提高了英格蘭人的民族認同感,逐漸形成了強烈的民族意識。越來越多的人排斥法國文化,不愿講法語,英語被逐漸用于社會各個領域。1356年,倫敦市長宣布法庭訴訟使用英語;1362年,英國大法官兼上議院議長用英語宣布議會開幕;1362年,愛德華三世在召開議會時首次用英語致辭,以便讓平民院的議員聽懂。應平民院的請求,愛德華頒布了關于法庭審訊必須用英語的法令。1362年10月,為了恢復英語作為英格蘭語言的統(tǒng)治地位,議會采取了一項重要的措施,頒布了《辯護法令》,并在1363年1月底生效。其大致含義是:“……因為高級神職者,公爵,伯爵,男爵,和所有的平民經常向國王陳述發(fā)生在國內的種種事端,法律,習俗,王國的法案在同一個王國內并不是被普遍熟知;他們用法語辯護、訴訟、裁決,這在該王國并不為普通民眾所熟知;以至于人們不起訴,也不反擊控告,無論是在國王法庭還是其他法庭,他們不理解也聽不懂律師及其他控告者是贊成還是反對他們;所以有必要讓大眾了解和理解這些法律和習俗,更好地理解該王國的語言,這樣一來,每個公民就能夠在不觸犯法律的基礎上自我管理,更好地保管和捍衛(wèi)他們繼承的遺產和財產;在好幾個國家和地區(qū),國王、貴族和國內的其他人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務,每個人都知曉自己擁有的權利,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法律和習俗是以該國語言擬定的。國王,希望國民安順,服從管理,因此要打擊和避免危害和隱患當時政局的行為。無論什么法庭,什么場合,都必須用英語訴訟、辯護、裁決,然后才能用拉丁語記錄入冊。”①其英文原文為”……Because it is often shewed to the king by the prelates, dukes, earls, barons, and all the commonalty, of the great mischiefs which have happened to divers of the realm, because the laws, customs, and statutes of this realm be not commonly known in the same realm; for that they be pleaded, shewed, and judged in the French tongue, which is much unknown in the said realm; so that the people which do implead, or be impleaded,in the king’s court, and in the courts of others, have no knowledge nor understanding of that which is said for them or against them by their serjeants and other pleaders; and that reasonably the said laws and customs shall be most quickly learned and known, and better understood in the tongue used in the said realm, and by so much every man of the said realm may the better govern himself without offending of the law, and the better keep, save, and defend his heritage and possessions; and in divers regions and countries, where the king, the nobles, and others of the said realm have been, good governance and full right is done to every person, because that their laws and customs be learned and used in the tongue of the country: the king, desiring the good governance and tranquillity of his people, and to put out and eschew the harms and mischiefs which do or may happen in this behalf by the occasions aforesaid, hath ordained and established by the assent aforesaid, that all pleas which shall be pleaded in his courts whatsoever, before any of his justices whatsoever, or in his other places, or before any of his other ministers whatsoever, or in the courts and places of any other lords whatsoever within the realm, shall be pleaded, shewed, defended, answered, debated,and judged in the English tongue, and that they be entered and enrolled in Latin” (Statutes of the Realm, I, 375-376).更多內容參見Albert C.Baugh and Thomas Cable,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123.
總之一句話:從此,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要用英語書寫。法令中提到的采用英語的理由是“法語在該王國不被熟知”,指的是英格蘭中下層人聽不懂法語。然而,消除二百多年使用法語的習俗也很難,該法令并沒有立即完全執(zhí)行,但它確實在英語被官方認可的進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1381年,瓦特泰勒(Watt Tyler)領導農民起義,國王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不得不用英語與農民對話。當時“肯特和埃塞克斯的農民的冤情(就我們所知)是口頭陳述給理查德二世的,叛亂期間與國王通訊聯(lián)絡似乎也都是用口傳方式,理查德在倫敦塔中只得要求外面的造反者,把大聲嚷嚷的冤情寫下來交他考慮”。②肯尼思·O.摩根主編:《牛津英國通史》,王覺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第 229頁。1450年,肯特和東南部凱德領導的農民起義,一開始便把他們的要求以英語書面形式呈交上去,而且還出了副本供人們傳閱。這一文件很長,但議論全面連貫。③肯尼思·O.摩根主編:《牛津英國通史》,王覺非譯,第230頁。兩次不同時期的農民起義都使用英語與國王交涉,說明底層民眾的英語讀寫水平已大大提高。1399年,理查德二世被廢黜的訴訟用英語進行;理查德二世被迫讓位于亨利四世的文件也是用英語。國王亨利四世首開蘭開斯特王朝,先用英語發(fā)表演說要求繼承王位,后在登基時使用的語言也是英語。④羅伯特·麥克拉姆等:《英語的故事》,秦秀白等譯,第85頁。更為徹底的語言轉向是1385年英格蘭所有文法學校都把英語列為教學正式用語。倫敦、牛津、劍橋等文化中心在百年戰(zhàn)爭之后逐漸使用英語。
四、中世紀晚期倫敦英語主導地位的形成
倫敦一直是全國的政治與經濟中心,王室與最高司法機構的所在地,還是全國學術活動的中心。倫敦的經濟地位在英語標準化進程中起到最關鍵的作用。倫敦是全國經濟信息交流的引擎,吸引著來自四面八方的人。他們相聚于此,帶來各自方言,與倫敦方言交融,等到他們離開倫敦時,帶走的是經倫敦當?shù)卣Z言改造后的英語。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是互惠的,倫敦英語在改變其他方言的同時,自身也受到影響,由最初有南方方言的特點演化為中部地區(qū)方言。因此,倫敦英語是一個南方方言、東南部方言和東中部方言的“語言混合體”(dialectal franca)。1362年,議會開始接納英語,喬叟和高厄開始用英語寫作,并在皇家法院和法學院當眾吟誦,英語已經成為大多數(shù)人的第一語言。H·C·懷德在《現(xiàn)代英語口語的歷史》一書中說:“如果我們審視過去關于我們的語言的記錄,從13世紀起大量在倫敦產生的作品顯然是用首都的方言寫成。這些文檔多種多樣,包括公告、章程、遺囑、議會記錄、詩歌和論著。我們大多推崇喬叟的作品。這些倫敦作品所使用的語言形式比用于中世紀英語文件的其他英語表達方式是更為適合的一種獨特的英語文字表達形式,因為它存在于14世紀,倫敦英語,或其中一類,是我們現(xiàn)在所使用的標準英語的先祖。”①Henry Cecil Wyld, History of Modern Colloquial English, London: T.Fisher Unwin, 1920, pp.4-5.倫敦英語在這一時期已經被廣泛應用。可以這樣說:倫敦英語的發(fā)展史就是標準英語的發(fā)展史;英語標準化的歷史幾乎就是倫敦英語的發(fā)展史。
行會使用英語的情況也是如此。14世紀后期,英格蘭各地行會數(shù)量激增。1388年議會閉會后不久,各地治安官統(tǒng)一發(fā)布公告:各行會的所有者以及負責人需向大法庭核實相關信息,包括建會信息、組織管理形式、集會情況、會內宗旨、土地不動產和動產;如若持有特許經營執(zhí)照或專利證,需攜帶相關證件前往大法庭予以核實;相關人員需在3個月內(1389年2月初之前)攜帶相關證件前往指定地點。
一般來說,14世紀凡是嚴謹精細的證明材料應該采用拉丁文,然而在商業(yè)最發(fā)達的倫敦及諾福克上交的材料中卻發(fā)現(xiàn)了英文材料。梵·格利周(Jan Grechow)的研究解釋了這種現(xiàn)象。1388年,國內很多非正式行會都沒有自己的書面行規(guī),因此他們不得不輾轉到倫敦大法庭,通過口頭敘述的方式向工作人員提供信息,之后工作人員又通過當時的拉丁文模板記錄整理,用當時工作通用的拉丁文書寫下來。這樣一來很多行會的自身特點就被抹殺掉了,造成很多證明材料的書寫模式極其類似。那些成熟的、資金雄厚、經營妥當?shù)男袝凶约簝炔坑⑽陌嫘幸?guī),他們把這些材料送到大法庭。因此,一些發(fā)達城市的行會材料是用英文,而相對偏遠的農村行會則用拉丁文。②J.Grechow, “Gilds and fourteenth Century Bureaucracy: the Case of 1388/89”,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1996,pp.109-148.這些現(xiàn)存資料表明,當時倫敦諸多行會都有自己的行規(guī)或誓詞,并且大多數(shù)人可以看懂。③Laura Wright, “The London Middle English Guild Certificates of 1388-9”,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1995, pp.108-145.由此可見,到14世紀30年代,倫敦一些行會已經使用英語書寫了。
在15世紀后半葉,倫敦標準語至少在書面語中被全國大部分人接受,其普遍性在文學作品里可見一斑。寫于中世紀晚期的劇本集《湯尼里劇本》(Towneley Plays)其中有個情節(jié),偷羊賊邁德(Mad)偽裝成上層人士企圖欺騙約克郡的牧羊人,但他的南方口音很快就暴露了身份,這說明當時國內仍有諸多地方方言。在1450年之后,除了一些來自北方的獨特的文學作品,要想根據(jù)文章語用風格推斷出作品的來源地已經不大可能。在地方的文獻記錄以及人們日常通信中,人們使用的語言越來越和倫敦標準語趨于一致。這種源于倫敦語言的影響在英國大法院文書寫的各種官方文件中得到了印證。到15世紀中期,書面英語無論在單詞拼寫還是語法規(guī)則上都具有了相對統(tǒng)一的模式,倫敦英語作為官方用語勢必影響其他有類似情況的地區(qū)。①John H.Fisher, “Chancery and the Emergence of Standard Written English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Speculum, (52),1977, pp.870-99.1476年印刷術的引進對于倫敦英語的傳播具有重大意義。從一開始倫敦便成為了英國的出版中心,英國第一位印刷師卡克斯頓以及其諸多后繼者都在他們出版的譯作與書籍中使用倫敦英語,這對倫敦英語在各地被迅速接納起到重大推動作用。到了16世紀,倫敦英語不再只是英格蘭語言統(tǒng)一的一種概念,而成為了真正的實踐用語。
五、官方開始確立使用英語
14、15世紀,在英格蘭與歐洲大陸貿易往來中,商人使用英語交流也促使英語向標準化發(fā)展。這一時期官方使用哪種語言來頒布公告、憲章及做議會記錄等則起到更重要的導向作用。盡管法語和拉丁語仍是官方主要用語,但王室法庭和議會開始使用英語發(fā)布議會文件和王室敕令,這標志著官方使用英語的開始。在15世紀早期及中期,王室重視使用英語。1399年,亨利四世登上王位用英語發(fā)表演講,亨利五世時期是法語、拉丁語向英語的轉折期。1415年,亨利五世在阿金庫爾(Agincourt)用英語寫急件(dispatches),打破了350年以來用拉丁語或法語書寫的皇家傳統(tǒng)。②參見Evolving English-How One Language Became Many, http://www.culturevoyage.co.uk/568, 2019-12-12.1417年12月17日,亨利五世寫給貝德福德公爵的加印文書③引自Gwilym Dodd文章附錄(TNA, C 81/1542/9; No.816 in Kirby, Signet Letters),更多內容參見G.Dodd,“Trilingualism in the Medieval English Bureaucracy: The Use and Disuse of Languag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rivy Seal Offic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51, No.2 (April, 2012), p.280.是又一個使用英文的典型例證:國王寫給公爵的信件正文全部使用了英文,僅對公爵的稱謂及玉璽管理處所附意見使用法語④其法文稱謂為 “A nostre treschier et tresame frere le duc de Bedford, Gardein en nostre Roiaulme d’Engleterre”;玉璽管理處所附法文部分意見:Fait aremembre qe par vertue de ceste lettre et aussi d’une autre lettre desouz le signet du Roy directe a l’onurable pere en dieu l’evesque de duresme chanceller d’engleterre…;部分信件英文正文:Right trusty and welbeloved brother.We grete yow often tymes wel.And for as moche as we have understande that maistre Johan Chaundeler that was deen of Salesbury is chosen Bisshop of the same chirche.Wher of we hald us wel agreed and therto we yeve oure assent Roial and we wol wel that after the consecracion of the said Elit he have liveree of his temporaltees.And the holy gost have yow in his kepyng.Yeven under our signet in oure hoost afor Faloise the xvij day of Decembre.更多內容參見 G.Dodd, “Trilingualism in the Medieval English Bureaucracy:The Use and Disuse of Languag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rivy Seal Offic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51,No.2 (April, 2012), p.280.。
此后,無論是與王室法庭、與議會還是與平民交流,亨利五世都堅持用英語。亨利六世更重視官方英語的使用。這種語言變化的背后有著極其復雜的因素,僅就重要文書請愿書為例,可見一斑。
在英格蘭中世紀晚期,請愿機制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表達手段。請愿書呈遞發(fā)生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農民向他們的領主呈遞請愿書,鄉(xiāng)紳向貴族呈遞請愿書,商人向市鎮(zhèn)委員會呈遞請愿書,下層教士向主教呈遞請愿書,訴訟者向法官呈遞請愿書,市民向國王及國王的大臣們呈遞請愿書。由于請愿書在英格蘭中世紀生活中普遍存在,其書寫規(guī)范也因此成為一項重要文墨之技。①格威利姆·多德(Gwilym Dodd):《民眾之聲:中世紀晚期英格蘭的訴狀和議會》,《經濟社會史評論》2017年第2期,第 45頁。更多內容參見Wendy Scase, Literature and Complaint in England 1272-155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一直到14世紀末15世紀初,請愿書一般都用法語書寫。法語的表達方式非常符合法律程序的嚴格要求,法語一直被認為是撰寫請愿書的最佳語言,早就享有“技術性語言”的贊譽。②G.Dodd, “The Rise of English, the Decline of French: Supplications to the English Crown, c.1420-50”, Speculum,86(1), 2011, pp.117-150.這也反映出建立請愿體系的法律傳統(tǒng)。在國王的普通法院里,法官和其他法律從業(yè)人員都用法語進行口頭辯護。15世紀上半葉,寫給國王、大臣、上議院和下議院的請愿書所使用的語言卻發(fā)生了根定性的轉變:英語開始逐漸被人們使用。15世紀30年代后期,特別是在1435年至1437年這幾年,人們開始明顯傾向于使用英語。③格威利姆·多德(Gwilym Dodd):《15世紀英格蘭議會請愿書及法律文書中英文的始用》,《經濟社會史評論》2019年第4期,第 26頁。到15世紀下半葉,那些受雇撰寫請愿書的文書(包括為國王服務的秘書、無固定服務對象的專業(yè)代寫人以及律師),抵制使用方言的保守主義開始動搖。從現(xiàn)存的英國國家檔案館保存的三大主要系列請愿書中,④格威利姆·多德(Gwilym Dodd):《15世紀英格蘭議會請愿書及法律文書中英文的始用》,《經濟社會史評論》2019年第4期,第 27頁。可清楚地看到法語的使用開始減少,英語逐漸向主導地位發(fā)展的變化趨勢。
結 語
英語的發(fā)展史是英格蘭歷史文化發(fā)展的一面鏡子。早期的盎格魯ˉ撒克遜方言是英語的最初母體,接著凱爾特語、拉丁語、法語等外來語的涌入,大大豐富了英語的內涵和表達能力,奠定了英語作為英格蘭官方語言的結構基礎。隨著諾曼征服、約翰王失地、英法百年戰(zhàn)爭等一系列重大政治、經濟、文化事件,英格蘭民族意識逐漸形成,而民族意識的形成過程又極大地影響了英語地位的沉浮。即使是英語被排斥于官方語言地位之外,它依然是英國下層社會廣泛使用的大眾語言,為其日后復興奠定了雄厚的群眾基礎。總體看來,盡管中世紀時期,英語上升到官方語言地位并非一帆風順。到中世紀晚期,英語也已經相對成熟,為早期現(xiàn)代英語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預示著現(xiàn)代英語的發(fā)展將迎來一頁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