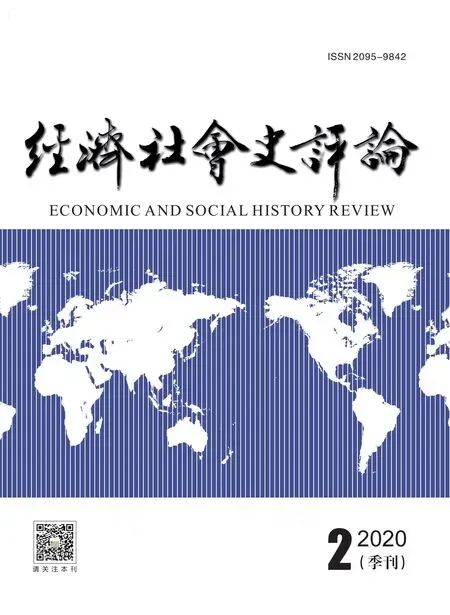1930年代上海勞工識字教育運動*
朱東北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宣布進入“訓政時期”。孫中山認為,人民長期處于做奴隸的狀態,對民主制度和當家作主很陌生,必須用強迫的手段教他們練習做主人。依據孫中山的訓政思想,國民黨積極推動了不同層面的社會變革運動。當時,中國人口80%以上是文盲,不識字很難識理,更不能負起國民的責任。國民黨逐漸認識到,建國程序千頭萬緒,有輕重緩急之分,尤應以識字教育為“第一項工作”。正如蔣介石所言:民權主義是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四權的行使,一定要國民先能識字”。①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專著》第3卷,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年,第228頁。上海作為全國社會運動的示范區,迅速成為國民識字教育運動的首善之地。
識字教育運動的主要對象是城市勞工群體。勞工識字不僅是國家競存的根基,也是提升國民素質、傳播公民常識的必要環節。目前學界已經注意到國民識字運動與民眾自治、公民意識和民族意識的深層次關系,然而有關研究仍偏重于新中國掃盲運動,對民國時期識字運動所論不多。②相關研究有潘祥輝:《“送字下鄉”——晚清及民國時期掃盲運動的傳播社會學考察》,《浙江學刊》2017年第5期;徐秀麗:《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掃盲運動的歷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趙偉:《1931—1937年民國鐵路職工識字教育述論》,《民國檔案》2014年第3期;楊可:《勞工宿舍的另一種可能——作為現代文明教化空間的民國模范勞工宿舍》,《社會》2016年第2期;李忠:《近代中國勞工教育的歷史變遷》,《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0年第5期;(美)魏裴德:《上海警察(1927—1937)》,章紅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本文以上海識字教育運動中的勞工問題為中心,以期豐富我們對那個時期的認識。
一、識字教育的多重起因
勞工識字教育起源于英國,后流行于世界各先進國家,主要是“使勞工能讀、能寫、能算”。①陳振鷺編:《勞工教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0頁。勞工教育在我國興起后,主要作為一種公益性的救濟運動,既可消除工與學的鴻溝,又破除勞心與勞力的傳統分野,因此得到工商政學各界的共同參與。1931年秋,上海市當局曾組成勞工教育委員會,舉辦勞工學校16所,學生有1 600余名。在市政府的倡導下,上海市總工會、各區分會以及《申報》《新聞報》各大報館等,先后自行創辦了職工教育補習學校。②潘公展:《滬市工人教育之過去與現狀》,《教育與民眾》1934年第5卷第3、4期合刊,第594頁。1934年1月12日,識字教育開始納入政府施政規劃。上海市社會局、教育局出臺《勞工教育實施辦法》規定:工廠、公司、商店應普遍籌設勞工學校,盡力向工人、職員提供免費教育。
1934年,蔣介石發起的新生活運動進入滬上,一切民眾自愿識字讀寫被視為延伸國家訓政的基礎。如上海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宣傳組草擬的公約規定:“每日必思如何方能自覺覺人,自新新民,自救救國,自愛愛群。”③晨報社編輯部:《新生活專刊》,上海:晨報社營業部,1934年,第90頁。然而,自覺自愿,過于隨意,收效不大。為實現從底層“革新生活”的目標,上海在具體舉措上一方面提出生活生產化目標,欲以“良好道德的國民共同努力生產”④劉維熾:《如何能使新生活運動成功》,《新生路月刊》1937年第1卷第4期,第21頁。,另一方面又必須利用工作間隙“舉辦勞工補習教育”⑤朱元懋編:《新生活運動章則》(上冊),南京:中正書局,1935年,第70頁。。
1935年初,為建成“世界模范市”,上海市將其確定為社會建設年。這不僅與上海市當局的施政計劃相一致,勞工識字教育也與蔣介石的政治意圖相吻合。1935年2月1日,蔣介石致電各剿共區,應以普遍教育為民族復興要務,至于實行識字教育問題,“若能使成人教兒童,識字者教不是識字者,知識高者教導知識低淺者,各以義務與互助精神,謀民智之提高,民德之增進”。如此種識字教育形成一定聲勢后,“更須以勞動與服務兩項,為學校教育與民眾教育之中心”,“務使一學生及國民,均能認識以勞動為本、以服務為天職……奮勉為健全之國民”。⑥高明芳編注:《1935年2月1日記事》,《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9(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至二月)》,臺北“國史館”2007年印行,第 247—248頁。2月18日,蔣又在南昌勵志分社訓話強調“勞動是做人與做事的基本”,“第一就是要以身作則,提倡勞動;第二就是要各盡所能,為社會、國家服務”。⑦黃埔出版社編:《總裁建國言論選輯》(下卷),黃埔出版社,1940年,第222—223頁。只有養成現代勞動觀念,才能成為現代國民。大家務必“注重社會(民眾)的生存,增進公共道德,養成勞動的習慣,發揚服務的精神!”⑧黃埔出版社編:《總裁建國言論選輯》(下卷),第224—225頁。在蔣看來,養成勞動習慣、倡導服務精神、組成“勞動服務團”,不失為推進新生活運動的“主要辦法”。①黃埔出版社編:《總裁建國言論選輯》(下卷),第228頁。
在此整體布局中,蔣介石將上海視為全新勞工運動的模范區。3月4日,中央意圖轉至上海,上海市長吳鐵城即刻召集各相關黨政部門,商討中央所定民眾教育問題。考慮到上海市財力拮據,擬“先舉辦識字教育,奠定民眾教育的基礎”②陶百川:《上海市識字教育計劃綱要及進行概況》,《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8號(上海市推行識字教育專號),第83頁。。4月2日,中央、地方認識趨向一致后,出于統籌各部共進、事權統一目的,上海市政府正式成立識字教育委員會,專司其事,統一支配20萬專項經費。在這個委員會里,吳鐵城、吳醒亞、吳開先、潘公展、陶百川、蔣建白等13人擔任委員,陶百川任總干事。該委員會下設辦事處,分設總務、管理、調查3股。每股設主任干事1人,干事、書記若干人,由市政府、市黨部各局職員調充之。此后,各區辦事處共22個,內設主任1人,干事2人。③潘公展:《上海市識字教育委員會之緣起與組織》,《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8號(上海市推行識字教育專號),第19—20頁。
為確保新生活運動向各業勞工推廣,1935年4月25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第169次常會決議,組成識字教育協進會,由市執行委員會理事5人組成,下設總務、黨運、工運、商運、社運、農運、婦運7組,并選派各區督促專員,全權辦理一切事務,必要時指導全市識字教育學校工作。④童行白:《上海市識字教育協進會工作概況》,《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8號(上海市推行識字教育專號),第81頁。在成立之初,上海識字教育協進委員會期望多種社會運動形成合力,在提倡“最短期內達到全市工人均能享受八小時之教育機會”⑤《全市工會開會紀念勞動節》,《晨報》(上海版)1934年5月1日,第4版。同時,倡導“以‘新生活公約’為公民教訓練之標準,凡[識字]學生之起居、飲食、穿衣、行動、禮貌、生活各方面,概照公約,切實指導,照約實行”。⑥童行白:《上海市識字教育協進會工作概況》,《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8號(上海市推行識字教育專號),第83頁。
如此,從一開始上海的識字教育運動就與底層生活改良緊密相聯,各業工人的識字教育被推到首位。有鑒于上海勞工居全國之最,居全市人口的1/5,推行識字教育運動自有絕佳增量價值。如時任上海市教育局長潘公展即講道:本市應注重以勞工為主體,應逐步推進文字教育、公民教育、生計教育與休閑教育,最終可以實現“學校教育擴張到勞工社會教育,(由)少數勞工獨享,普施到勞工群眾均沾”。⑦潘公展:《勞工教育與勞工問題》,《民生》1934年第2卷第20期,第5—6頁。
由于“個人身體健康之訓練、家庭衛生之改良,民族意識之充實,均須賴此次識字教育”⑧陳公素:《識字教育之中心使命》,《晨報》(上海版)1935年5月4日,第9版。,因此,上海市之識字教育“尚有常識指導及公民訓練”內容⑨《上海市識字教育委員會推行識字教育宣傳大綱》,《上海市教育局教育周報》1935年第292期,第6頁。。誠如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醒亞所言:在此期間,必以“文字教育在先,常識指導及公民訓練在后”。這個先后次序,沒有輕重之分①吳醒亞:《識字教育的目的在哪里》,《新聞報》1935年5月4日,第18版。。至此,中央新生活運動深入地方后,日益走向物質與精神生活共進軌道。待上海市當局的實施架構基本形成后,一場社會運動的推進仍然有賴于精密的統籌安排,切實解決具體行業面臨的困難,確保其實現目標。
二、分級分區推進與實施
教人識字也是社會革命。縝密的規劃、底層勞工動員與充分的經費保障,無疑是一場大規模識字教育運動的必備要素。上海市當局對于識字教育,并沒有草草應付。例如,上海識字教育委員會作為黨政部門聯席會議,對高效推進識字教育有重要作用。陶百川致力于以黨政學界為中心,聯絡軍警工商各界,分區分級推進勞工識字教育運動,從而大致形成了擴大宣傳、實地調查、編輯課本、設立試驗區、考訓師資、組織識字服務團等要點,以促使識字教育深入民間。
1935年5月,上海市識字教育委員會擴大全市宣傳,以鏟除障礙,減少阻力。自五一勞動節起,該委員會特意推出首次城市識字宣傳周。5月1日至7日為識字宣傳周,面向全市各界。以5月1日為工界宣傳日,由總工會召集各工會各工廠工友舉行宣傳。5月2日為電臺宣傳日,5月3日為商界宣傳日,5月4日為游藝界宣傳日,5月5日為電影宣傳日,5月6日為學界宣傳日,5月7日為農界宣傳日。在上海市長吳鐵城的授意下,工界宣傳日主會場設在新市政中心,且懸掛多種宣傳標語。②《識字運動周今日開幕》,《申報》1935年5月1日,第12版。
上海是“五方雜處的大都市”,除宣傳周活動外,也須“周密而深入的宣傳”。考慮到“居處密度甚高”,“散布面積甚廣”,“職業五花八門”,上海市識字教育委員會期望經由全市公私立學校、社會教育機關、社會團體、大小報紙、娛樂場所等等發動學生、藝員,協助識字教育宣傳。此項宣傳方式有二:(一)直接宣傳,即口頭宣傳,利用游藝、電播、宣講等各種方式直接灌輸給失學民眾;(二)間接宣傳,即文字宣傳,利用報刊、標語、圖畫,通過全市各界知識分子間接傳達給失學民眾。涉及范圍涵蓋有,深入民間的大小報紙百數十種;公立和私立的各級學校及社教機關一千幾百所;集中大量市民的游藝場7所;規模宏大的舞臺4座;無線電臺四十余座和星羅棋布的收音機;說書場大小七八十座;電影院四十余所;其他雜色游藝場百數十所;游藝團體10個;游藝人員約兩萬余人等。③呂海瀾:《上海市識字教育宣傳報告》,《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8號(上海市推行識字教育專號),第59頁。
上海市總工會作為重要協辦者,也積極派遣大批工友分赴各工廠、商店,散發告同胞書及標語、圖畫。主要是利用華商電車與閘北公共汽車,散發標語多種:(一)用手又用腦,才是大老好;(二)有眼不識字,好比是瞎子;(三)識字是權利,人人莫放棄;(四)求人不如求己,快些識字讀書;(五)人人讀書做好人;(六)識字的工人,不為人所欺;(七)莫嫌年紀老,讀書還是早;(八)今日再不讀,以后就不及;(九)實行三八制,先要認識字;(十)識字的工人,大家起來教不識字的工人;(十一)勞動的人要識字,識字的人要勞動;(十二)一天識一個,十天識十個,一年可識三百多。①《本市識字教育委員會識字宣傳周今日開始》,《新聞報》1935年5月1日,第13版。
此后,上海市識字教育委員會選定江灣、南市為特別試驗區,預計開辦識字學校220個,共1 320個識字班。各類識字學校設立同時,再組全市教育服務團,下設分團300個。在上述識字教育架構基本形成后,該委員會借助于市政府、市黨部之力量,開展了頗為龐大的調查工作。“所有的地保、戶籍警察、識字學校考取的教員,以及各區公私立學校年長學生”悉數參與,以充分調查實況。②陶百川:《本會工作之回顧與展望》,《晨報》(上海版)1935年5月4日,第9版。調查具體步驟為:“調查時,以識字測量表——六百字表,逐一令民眾試讀,如連讀一二行而不感覺困難者即為識字,否則為不識字;如調查時而被調查之民眾不在家,即向其家族或附近民眾舉行間接調查,若被問民眾答說識字,則請書面證明,以備他日調查。”③覺非:《上海市強迫識字教育的鳥瞰》,《河南民眾教育》1936年第1卷第7、8期合刊,第40頁。
經排查,上海市當局掌握了不識字者的職業、籍貫與性別分布,由此形成了“勞工教育為改進生活之工具”的基調。④《吳醒亞談勞工識字教育》,《申報》1935年8月29日,第11版。1935年6月,上海市政府先期制頒了《上海市勞工識字教育實施辦法》即規定,務必以工廠、公司、商店的工人、職員作為主要教育對象,避免識字教育本末倒置、緣木求魚。為實現此目標,上海市政府明文規定:“凡本市區域內不識字之工人年在七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均須一律受識字教育。”⑤《上海市社會局識字教育委員會關于限期各工廠商店設立勞工識字學校普及識字教育事至上川交通公司的文函》,1935年,Q409-1-219-1,上海市檔案館藏。“商店工廠之經理及家庭之主人,應令其于工作之暇入識字學校,或不便入校,商店工廠可擇職員中之優秀者任識字教育服務團團員,于適當時間教授之。”⑥馬崇淦:《識字教育之中心使命》,《晨報》(上海版)1935年5月4日,第9版。尤其是“工廠方面,應該由工會和工廠,雙方合力辦理以收協作之效”。⑦陳公素:《提倡識教之雇主責任》,《晨報》(上海版)1935年5月4日,第9版。
廠、司、店分類辦理識教后,無固定雇主之工人流動性最大,逐漸成為識字運動的最大滯礙。為此,上海市識字教育委員會選定在碼頭、車所等人口聚集區域推廣識字教育。為配合此項辦法實施,上海市政府特意遴選“人力車業同業公會、碼頭業務所、營造廠業同業公會、各區水木業職業工會、輪船木業職業工會、雇用流動工人的公營機關,以及其他流動工人之勞資雙方團體”,擔負職責,接納有關教授任務。盡管如此,考慮到具體的辦學能力,凡“設立校數與能容納之學生人數等”,應“與識字教育委員會協定之”⑧《上海市識字教育委員會識字學校入學辦法》,《上海市政府公報》1935年第159期,第194頁。,以實現官民聯動。
為消減民間顧慮,1935年6月23日起,上海市政府又頒行《上海市識字教育委員會識字學校入學辦法》《上海市各廠場公司商店等設立勞工識字學校須知》,深入推進強制識字教育。兩者對商店與工廠雇主責任予以明確規定,勞工識字教育經費應由各廠場、公司、商店負擔,“在辦理勞工識字學校時,經費應為適當的支配,且應有確定的預算”①陳振鷺編:《勞工教育》,第23頁。。由此基本確立了官方監督、資方辦理的推進方式。
遵循此種原則,對于家庭雇工及商店職工,“應由雇主予以上課之便利,不得任意留難”。②《上海市勞工識字教育實施辦法》,《上海市政府公報》1935年第158期,第196頁。對于工廠工人,“凡每日工作時間在十小時以內者,上課時間可在工作時間以外,超過十小時者,上課時間應在工作時間之內”。③《上海市社會局識字教育委員會關于限期各工廠商店設立勞工識字學校普及識字教育市至上川交通公司的文函》,1935年,Q409-1-219-1,上海市檔案館藏。此外,各公司、商店應呈報識字與不識字工人名冊,“限于本月三十日以前,呈送本會各區辦事處候核。倘有工人逾期不報,即以不識字論,概須強迫受識字教育。如各工廠、商店逾限不報,一經查實,即科以二十元以下之罰金”。逾期未辦理,或者未按時開課,甚至學徒未入學,如果是雇主留難,“處以一百元以下之罰金外,令其限期遵辦”。④《上海市社會局識字教育委員會關于限期各工廠商店設立勞工識字學校普及識字教育市至上川交通公司的文函》,1935年,Q409-1-219-1,上海市檔案館藏。
經過前期籌備,1935年7月1日上海市識字教育運動正式開始,為期一年。除陸行、高行、真如三鄉區外,“其余十九區,分別依照各該區情形,設立學校,自二所至三十所不等,共計二百二十所”⑤《上海識委會推行勞工識字教育》,《民眾教育通訊》1935年第5卷第4、5期合刊,第100頁。。上海市長吳鐵城說道:“許多百廢待興,艱巨重大的工作,卻不能不分緩急,不能不辨本末。所以,本黨所規定對七項救國運動,其第一項便是識字運動。從這一點看,識字教育的實施,實在是新中國建設的起點,也是今日負實際訓政責任者,最初應該完成的基本工作……上海是我國文化經濟中樞,這次識字教育運動的成敗,或成效的優劣,實在還可以影響全國人民的觀感,并且可做今后中國救國運動能否徹底成功的測驗。”⑥《弁言》,《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8號(上海市推行識字教育專號),第17—18頁。
識字教育運動鋪開后,各業勞工決定著全市識字教育的成敗。據統計,如以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劃分,全市工業工人有36 739 1人,商業工人有41 464人,交通運輸工人有30 001 9人。⑦王剛:《上海市勞工教育之回顧與前瞻》,《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8號(上海市推行識字教育專號),第32頁。可見,集中推進勞工識字教育十分必要。上海市勞工識字教育負責人王剛就再次重申:各業勞工“是構成全市文盲的最大成分,所以掃除勞工文盲,是這次識字教育中的最重要的工作”。⑧王剛:《上海市勞工教育之回顧與前瞻》,第35頁。
在識字教育運動中,識字課本仍是主要的推廣工具。此前,實業部與教育部即明確要求勞工教育科目:“(一)三民主義千字課;(二)常識;(三)珠算或筆算;(四)樂歌;(五)歷史、地理、自然及其他淺近讀物。”⑨陳振鷺編:《勞工教育》,第25頁。此后,為適應識字教育的實際情形,識字教育委員會又專門編定《短期小學課本》,專門以職業為中心分類推進。如第三課即講“讀書與做工關系”,“做工的要讀書,讀書的要做工,大家要讀書,大家要做工”。①《上海市社會局有關勞工識字教育通告》,1935年,Q253-3-571,上海市檔案館藏。與此同時,“編制上海工人讀、農民讀、婦女讀、小販讀……等課本,切合個人的情境,自可收‘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之效”。②尤蔚祖:《上海市強迫識字教育之理論與實施的我見》,《大上海教育》1935年第2卷第7期,第79頁。
最為尖銳的矛盾是,如何在可能的時間內激發勞工識字熱情,不至流于形式。上海華商水泥廠即具有代表性。由于該廠運營,對技術工人要求頗高,一旦短缺,“工務方面,行將大受影響”③《華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關于四川、中國水泥廠在本廠挖雇技術職工等問題的文書》,1936年,Q414-1-481,上海市檔案館藏。,“工人不識字者居多,欲求其技術進步,不免時感困難”。④《華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1934—1937年舉辦工人識字教育的有關各項文件資料》,1934年,Q414-1-69,上海市檔案館藏。為此,該廠已經在1934年撥付經費1 000元,指派潘玉書、錢興亞二人辦理工人識字教育事宜。具體做法是“各部分工作時間以內,就每班工人中,抽出若干人令至指定處所教之識字,每次教授時間以十五分鐘為度”。全體職工均須入學,由工務主任指定學員,“學習工友因公缺課辦法,屆時由管理員用書面通知識字教育班備查”⑤《華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1934—1937年舉辦工人識字教育的有關各項文件資料》,1934年,Q414-1-69,上海市檔案館藏。。
華商水泥廠的做法堪稱上海市識教運動的“典范”。參加識字教育的工友,按照編定時間表輪流聽講。廠務會議決定抽調時間,“以每日開始上工及將屆散工之時間,如已在工作,即不便抽調”。待散工后,先后確定日班組“下午五時半至六時”,夜班組“下午六時另五分至六時三十五分”。經過這些嘗試,華商水泥公司采用間日教學辦法,“依成績之優劣,參酌工作情形,將日、夜班工友分兩種程度之甲、乙兩組”,“成績優良者,集為甲組,余者為乙組”。⑥《華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1934—1937年舉辦工人識字教育的有關各項文件資料》,1934年,Q414-1-69,上海市檔案館藏。其成功得益于遵循工人作息習慣,調整教學進度,解決了勞動與識字時間的矛盾。
其間,疲勞是勞工識字持續推進面臨的另一個困難。正如上海市勞工識字教育負責人王剛所言:在激烈市場競爭下,“一般工廠的每日工作時間都在十小時以上,甚至有工作十四小時者,一個工人經過這許多時間勞動以后,已覺精疲力倦,在工人本身無法再行振作精神,聽講讀書,強迫聽講讀書,不獨收效微細,并且近乎殘忍。所以,工作時間過久,是實施勞工教育最大的障礙”⑦王剛:《上海市勞工教育之回顧與前瞻》,《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8號(上海市推行識字教育專號),第31頁。。對于此種擔憂,浦東電氣公司的解決辦法具有代表性。該公司定于8月12日開學,“學生七十六人,分為兩班,第一班上課時間為上午七時至八時,第二班上課時間為下午七時至八時”。⑧《浦東電氣公司關于開辦員工識字學校報告表、辦法、規則及上海市社會局布告》,1935年,Q576-1-564,上海市檔案館藏。
另外,識字教育也會遇到方言、年齡與心態等個體差異問題。1935年8月,“為教學便利計,以國語為主,而以上海方音為輔,以免辯正字音而多耗時間”。不同年齡工人,收效不盡相同。“年齡較長者,世故已深,希望較少,不若青年人之富有朝氣,較易引起興趣。但亦有因技藝較高或工作不過繁重者,則其年齡雖較其他工友略高,亦能鼓其勇氣,努力求學”。最終,甲組已完成“約五百字左右”,乙組“尚須略予展期,方能讀完。”①《華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1934—1937年舉辦工人識字教育的有關各項文件資料》,1935年,上海市檔案館藏,Q414-1-69。
鑒于識字教育進度各不相同、效果參差不齊,1935年8月2日,上海市總工會一方面積極自辦勞工學校71所,委托代辦1所,共計72所。②童行白:《上海市識字教育協進會工作概況》,《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8號(上海市推行識字教育專號),第82頁。另一方面通令各分會:務必“調查所屬會員中不識字人數,勸令從速依限入學,不得故事推諉,自甘放棄,同時督促并協助廠方籌辦學校”③《總工會通告各工會推進勞工識字教育》,《申報》1935年8月2日,第12版。。對于此種情形,上海市長吳鐵城也坦言,“原限各廠于八月三十一日以前開辦,惟因特殊關系,多未能如期舉辦”,響應者寥寥無幾,“已舉辦者,計一百五十二校,其已在籌備及已辦理而尚未及報告者,當不下三百余家,均在分別指導督促中”。④吳鐵城:《上海市首屆識字學校辦理情形》,《上海黨聲》1935年第1卷第38期,第756頁。吳醒亞則感慨道:“意存觀望、希圖延擱者,尚居多數。”⑤《吳醒亞談勞工識字教育》,《申報》1935年8月29日,第3張第11版。正因為如此,上海市當局決議采取強制辦法,以保障識字教育高效推進。
三、“懲戒”與“規訓”
面對勞工普遍的消極應付,上海市當局也不斷總結得失,適當調整各部門職能。其中,上海市黨部調查江灣區結果顯示,“在開學二星期左右,出席人數尚多,每校平均有二百余人。以后便逐漸減少,每日缺課,平均約占百分之三十,有時且超過之”。對于識字教育出現種種難題,上海市政府“不得不借用警察的力量,拘罰數人,以示懲儆,當時人數,雖稍有增加,但過了數日,又依舊如故”。⑥《上海市識字運動調查》,《中華郵工》1936年第2卷第5、6期合刊,第94頁。為禁絕此類情況,上海市政府要求公安局在調查戶口時,將不識字的人登記在案,識字教育委員會將通知其入學,“若有不盡責任的,我們就要督促他,務使他盡到責任。一次督促不聽,再次,再次不聽,三次,總要求到識字教育的工作,依照規定的計劃,以達最后之目的為止。若果真是冥頑不靈的,不可救藥的,我們就要很不客氣的,公布其姓名,俾眾周知”。⑦蔡勁軍:《識字教育運動與警察》,《晨報》(上海版)1935年5月4日,第9版。
1935年11月11日,社會局長吳醒亞專門視察各廠,基層問題逐漸顯露。例如光中染織布廠所設勞工識字學校,(一)該校應添置簡單桌椅;(二)缺課太多,應即遵照市府規定辦法制止。再如振泰紗廠所設勞工識字學校,(一)缺課學生太多,應設法制止;(二)該廠每班間日上課,兼之做夜工,則不上課,因之每月每班上課時間,不過六小時,殊有不合,應令廠方每班每星期上課六小時;(三)夜工則在晚間上課,一曝十寒,不易守效;(四)工人常逾十分或五分鐘,方入教室,應由該廠通知各工場職員協助,務使工人準時入教室;(五)該廠應指定職員協助教員,管理工人缺課、遲到等事項,以期識教順利進行。①《上海市社會局有關勞工識字教育通告》,1935年,Q253-3-571,上海市檔案館藏。最為奇葩的是,1935年12月,上海福新面粉廠“于期終考試時,竟發現不識字之工人,請人包代應考情事”。②《福新三廠關于勞工識字教育、檢查工廠通知、填報產銷開工狀況、旱災募捐等件》,1935年,Q466-1-10,上海市檔案館藏。
在識字教育日益形式化背景下,上海市政府雇工成為輿論焦點。作為政府管轄工人識字學校,理應工人自行入校,模范運行,以是提倡。然而,12月21日,該區識字教育委員會辦事處主任呂海瀾報告:“多數工役均借故規避,不肯入校,而各局亦未能充分協助,從嚴督促,致發生困難。”③《上海市政府舉辦識字教育文書》,1935年,Q215-1-6154,上海市檔案館藏。對于此類不識字工人,市政府屢次下達通知書,請工人“從陽歷十二月廿三日起,每天在下午四點鐘,親到該校去讀書一點鐘。兩個月畢業,學費不收,書籍奉送。你若到了那天,不去讀書,那我們就請公安局傳送你去罰款或拘役”。④《上海市政府舉辦識字教育文書》,1935年,Q215-1-6154,上海市檔案館藏。
在萬般無奈之下,上海市政府提出征繳強制性罰款。凡“遷延不入學與無故曠課的,由公安局傳問,強制入學。不遵傳問,罰大洋二角到五元”。⑤《工人不識字,雇主要負責》,《立報》1935年9月27日,第4版。不服或無力繳納時,將處以勞役。推進到1936年1月,有鑒于絲廠為工人集中區域,特別規定“絲廠每車應負擔勞工識字教育經費,國幣五角正,不論營業時間長短,均須一次繳付,并以一次為限”。至于征收方式,“無論是否絲廠同業公會會員,均由絲廠同業公會征收之,由同業公會負擔其他一切會計上之責任,每月收支由同業公會按期呈報社會局”。⑥《上海市絲廠業勞工識字教育辦法》,《上海市政府公報》1936年第165期,第98—99頁。
耐人尋味的是,識字懲戒并不會突破國民黨的規訓底線。勞工與雇主素來是社會秩序是否有序的重要群體。這促使上海市當局既借用警力推進施政,也要規范勞工行為,維持社會良俗。在“重教不重誅”的理念作用下,上海市政府并不希望過度濫用警力,以免事態惡化、得不償失。如上海市政府即指出:“罰金及勞役均不應照最高數科罰,初次只應科以二角罰金,或二小時勞役,如對于罰金不服或無力繳納時,亦只能改易勞役,不得易科拘留。”⑦《為指令關于識字學校入學辦法所定罰金另制收據專案辦理對于處罰應從最少數處罰如不服或無力繳納時應改以勞役仰遵辦由》,《上海市政府公報》1935年第160期,第134頁。由此可見,上海市的此類懲罰舉措意在督促施政推動識字教育。
與市政府的依法施政不同,上海市總工會則更為強調勞工教育權的維護。然而,在無力自辦識字學校的條件下,其做法更多的是指責雇主拖延。1936年5月1日上午9時,上海市總工會在南市梅家弄召集各工會舉行工界宣傳大會。大會議決:“各工廠公司商店等,其雇用工人中有應受識字教育滿三十人以上者,至少須設立勞工識字學校一所。本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各工廠公司商店至少須設立一班。至明年(1936年)六月三十一日前,全部勞工識字教育辦理完竣。”①《上海市識字運動調查》,《中華郵工》1936年第2卷第5、6期合刊,第60頁。“不滿三十人時,其識字教育由市立識字學校辦理之。”②《上海市識字運動調查》,《中華郵工》1936年第2卷第5、6期合刊,第87頁。
在此種強制措施下,直到1936年7月,上海市“已辦有勞校五百余所,入學工人約四萬余,畢業工人約二萬余”③《上海市社會局為籌辦勞工識字教育、撥發經費事與市政府及教育部往來文書》,1936年,Q6-18-139-68,上海市檔案館藏。。其中,上海市政府“設立二十五校,二十七班,入學人數達一八〇八八”④《上海市政府二十五年七月份工作報告》,《上海市政府公報》1936年第175期,第180頁。,其中,總工會“設立勞工補習夜校四所,入學工人達五百余人”⑤復農:《上海市工人運動概況》,《上海黨聲》1935年第1卷第3期,第55頁。,勞工教育負責人王剛呈請市政府重視勞工識字的成績,請求給予撥付經費。8月3日,上海市社會局呈請市政府,撥付經費,“今后若不繼續辦理,非特四十余萬不識字工人,無受識字教育之機會,且過去一年之宣傳與實驗均將消滅于無形。此無論在整個識教計劃上言,或勞工識教計劃上言,殊可惋惜”⑥《上海市社會局為籌辦勞工識字教育、撥發經費事與市政府及教育部往來文書》,1936年,Q6-18-139-68,上海市檔案館藏。。基層識字運動漸趨淡化,也面臨運動本身的重構與轉變。
四、行業識字教育經費問題
經費與時間是保障勞工教育的關鍵。如在運動中擔任教員的王炤回憶道:“大約過了一個多月,我所教的一本識字運動第一冊,已經交完了。而公安局還沒有來抽考”,“熱風徐徐的向南國吹去,把‘識字運動’這個口號也帶了過去。”⑦王炤:《識字運動之回憶》,《民立旬刊》1937年第18、19期合刊,第28—29頁。如此,采取新手段維系識教運行,早已成為此種國家教化延續的不二法門,先后“有班級教學、流動教學、循環教學、傳遞教學、小先生制等等,教師原有定處,現在變成如同走方郎中,沿門挨戶,用盡種種方法”⑧心:《民眾識字要靠大眾努力》,《上海民友》1934年第77期,第5頁。。
為籌集充足經費,上海市社會局遂轉向雇主贊助。由于工商界對于辦理勞工識字教育頗多延誤,所以又進度各異,消極推諉。為此,上海市社會局嘗試從普遍實施轉為重點推進。由于交通運輸業不僅有健全工商團體,作為全市民生活不可缺少的服務行業,成效必不可小噓。如該事業負責人謝承懷即慨言:“本局所需要者,不過為考試、視察、獎勵、印刷等項經費兩萬元。以此區區之經費,而能使本市之勞工識字教育繼續進行,此在行政效能上言,可謂推行政令之經濟辦法。”①《上海市社會局為籌辦勞工識字教育、撥發經費事與市政府及教育部往來文書》,1936年,Q6-18-139-68,上海市檔案館藏。
早在1935年1月8日,在上海市府擴大紀念周上,上海市長吳鐵城講到的上海人力車夫計劃,“第一步,先在市區內,試辦人力車夫合作社,最初以車為政府所有,將來逐漸成為政府與黃包車夫所共有,再進一步,使為黃包車夫所有,以達到‘車夫有其車’”。②吳鐵城:《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市政設施之方針——二十四年一月八日在上海市府擴大紀念周演講》,《中央周刊》1935年第348期,第3頁。繼續辦理識字教育也有顧及輿論觀瞻的意圖,“勞工識教不過為勞工教育之初步基礎,若此初步基礎不能完成,勢必影響勞工教育之整個計劃”。③《上海市社會局為籌辦勞工識字教育、撥發經費事與市政府及教育部往來文書》,1936年,Q6-18-139-68,上海市檔案館藏。
事實上,自1935年5月起,上海市社會局提出人力車行業的救濟計劃,涵蓋了“建筑新村、舉辦合作、教育、衛生、保嬰、保險等福利事業,與公營人力車”④《上海市公用局關于人力車夫請交涉取締人力車互助會》,1935年,Q5-2-1113,上海市檔案館藏。。由于上海識字教育為全國觀瞻,不僅立意深遠且包攬全市勞工,因此,人力車夫識字教育自然變成為了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全市識字教育相繼完成的背景下,1937年2月1日,人力車夫教育計劃成為了延續識字教育運動的重點行業。按照社會局的規劃,此項事業需經常費62 400元,開辦費4 420元,臨時費982元4角,共計67 802.4元,期望設立人力車夫學校65所。
為人力車夫識字教育推進,車商須負擔“每月每車教育費三角”。為防止車主拖延,社會局不得不沿用代捐方式征收經費。之所以車商反應激烈,不僅限于教育費,也在于車照捐與公會會費“捆綁”。對近年來新增車輛而言,更是有失公允。人力車主陳榮懷即上呈:“榮懷營業多年,對上海市人力車業同業公會所有權利,絲毫未曾享受”,而征收捐照費時,須繳納同業公會會費,“繳納會費后,方準繳捐”,“對此無權利之義務,特殊無應盡之理”。⑤《上海市財政局公告取消人力車保捐代捐制度及人力車公會呈請協助捐發車照時檢驗會費收據等》,1936年,Q432-1-555,上海市檔案館藏。此種經費安置,固然公會可確保會費繳納,也受到各方質疑。在上海市政府看來,也有公會壓迫車商、抗衡官廳,乃至私自劃定經營區域之弊。如上海公用局即認為,車商杌隉不安,“間接影響及于車夫生計”⑥《上海市公用局改善營業人力車代、保捐制度》,1935年,Q5-2-1401,上海市檔案館藏。,何談救濟民眾。1935年12月1日,市政府明令,所有保捐、代捐制度“著即取消”⑦《上海市公用局改善營業人力車代、保捐制度》,1935年,Q5-2-1403,上海市檔案館藏。。
直到1937年5月底,“除特區五月份未繳外,其余均已照繳”,僅籌得8 674.4元。⑧《上海市就人力車夫識字教育問題的討論會紀錄》,1937年,Q6-18-263-42,上海市檔案館藏。在兩難之下,人力車業公會方面也提出,應由主管官署派員“分別監導,以便有所遵循而免同業誤會”①《上海市公用局關于人力車夫識字教育事項》,1937年,Q5-2-1119,1937,上海市檔案館藏。。為妥善處置起見,1937年6月1日,上海市社會局、財政局、公用局商議人力車夫識字教育推進事宜。財政局代表馮治直言,“實行以來,手續繁重,且多糾紛,稽征處辦理,極感困難”。公用局代表程鵬展也表示,“恐有人借此操縱把持,形成一種保捐代捐制度之變相”。②《上海市就人力車夫識字教育問題的討論會紀錄》,1937年,Q6-18-263-42,上海市檔案館藏。至此,人力車夫識字教育因征收經費“有欠允當”,無法獲得政、商協助。隨著經費成為泡影后,識字教育運動終于無法延展。
結 語
1930年代,上海識字教育運動是推向基層的廣泛的現代變革運動之一。該運動基本覆蓋了全市各行各業,積累了寶貴的城市社運經驗,對此后社會變革具有特殊的借鑒意義。從此次運動推進看,上海勞工的抵制是識字教育走向失敗的重要根源。對社會而言,盡管底層勞工在政治上已日益走向覺醒,但由于忙于生計勞動,仍不可能認識到識字的民族責任,無法自動自覺;對國家而言,為將底層勞工納入國民黨設定的政治過程,唯有兩種方法:一是法制,二是運動。在制度尚未展開時,嘗試運動方式推進識字教育成為了必然選擇。對于普遍的消極抵制情形,由國家主導的宣傳與組織運動機制并不是可有可無的。為彌補運動能力的不足,上海市當局一度動用警察力量以確保實效,但畢竟有轉向專制之嫌。在這種得不償失的兩難境地中,上海識字教育經費只能重歸于工商政民利益的協調,最終無可避免地成為了低效的強制運動。
需要指出的是,識字教育運動也是長時段深層社會變革的起步。從這個意義上看,識字之本并非讀寫文字,而在于普及現代觀念。欲提升教化廣度、改造力度與文明厚度,遍布全國的社會動員至關重要。一場深刻的現代變革不僅取決于本身的推進技術,也必須與刷新民眾觀念、打破社會等級,乃至重建國家息息相關。在20世紀30年代,依賴國民黨訓政體制,推行以勞工為“主體”的文字普及并不困難。然而,由于識字教育運動不可能脫離國民黨建置的規訓框架,所以,無法高效動員勞工參與,更不能從根本上養成勞工群體的現代意識。與之相比,只有新中國推動了徹底的群眾動員,將提高工人文化水平視為新國家的政治模范,順應了勞工打破社會等級、要求解放的心聲,逐步重建了以工人為中心的國家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