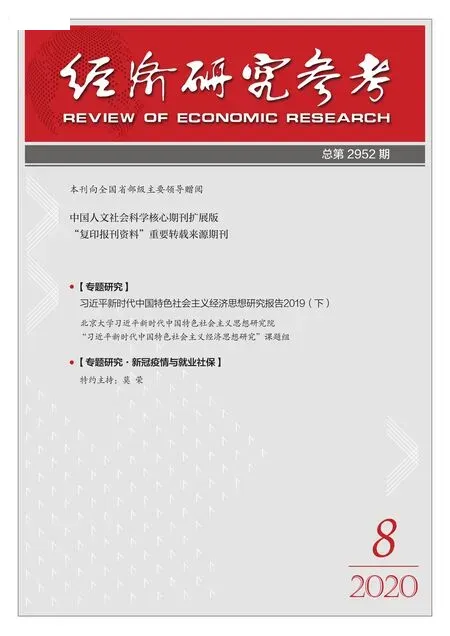我國制造業稅收負擔及相關政策的優化*
席衛群
一、我國制造業發展形勢嚴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發展迅速,實現了歷史性轉變,按不變價GDP計算口徑統計的制造業增加值由1978年的1659.5億元(人民幣計價)增加到2017年的266798.1億元,增加了近160倍,我國已成為重要的制造業大國。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制造業增加值比重持續上升,由1995年的不到5%、2000年的8.5%上升到2010年的18.23%、2017年的27.02%。相比之下,美國、日本和德國在全球制造業的比重分別由2000年的25.23%、17.95%和6.58%,下降到2017年的16.50%、7.65%和5.91%。
隨著制造業的快速發展,我國參與全球貿易的程度不斷提升,貨物進出口貿易總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從1978年的0.8%增長到2017年的11.5%,其中出口額的比重由1978年的0.8%提高到2017年的12.8%。
盡管制造業發展迅速,但是隨著全球競爭的加劇,我國制造業發展的形勢不容樂觀。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制造業總體產出效率不高,無論是質量水平、關鍵技術、優質品牌、研發投入等都與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存在較大差異。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中國工程院、原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在2013~2014年聯合組織開展了“制造強國戰略研究”重大咨詢研究項目,該研究項目構建了由規模發展、質量效益、結構優化、持續發展等4項一級指標、18項二級指標構成的制造業評價體系,將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分為三大陣營。根據研究結果,2012年美國的綜合指數是156,日本和德國分別是121和111,我國是81(根據研究項目跟蹤結果顯示,2016年我國提高到近90)。在世界制造業排名中,我國處于第三陣營,與第二陣營有較大差距。近年來,我國制造業增加值率僅為21.5%,遠低于工業發達國家35%的平均值,在全球產業鏈條中處于相對較低的分工地位。
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力、土地、能源等成本的上升,我國制造業成本逐年上升,低成本優勢逐漸喪失,不僅難以抗衡部分東南亞國家,而且與發達國家的制造成本差距也日益縮小。根據美國波士頓咨詢集團(BCG)2014年發表的《全球制造業的經濟大挪移》報告,如果以美國的制造成本為基準指數100,則我國的制造成本指數高達96。由于制造成本不再具有優勢,制造業產業外遷現象日益嚴重。我國與美國存在競爭關系的產品,如工業制成品、高新技術產品等出口也受到阻礙。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公布的數據,美國商品貿易額2016年達到37060億美元,超越我國位居世界首位,而同期我國商品貿易總額為36850億美元。2016年美國進出口額同比減少3%,而我國的出口額同比減少8%,進口額同比減少5%。
二、我國制造業稅負狀況分析
近年來,為了扶持和促進制造業的發展,我國出臺了不少稅收優惠政策來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筆者通過對2013~2017年的數據分析研究后認為,我國制造業稅負狀況仍不容樂觀。
(一)我國制造業稅負高于全國宏觀稅負
筆者主要使用宏觀稅負、稅收彈性、稅收協調系數等指標反映我國制造業稅負狀況。自2012年開始,我國在上海試點營改增,2016年在全國全面推行營改增試點。為了反映營改增對制造業稅負的影響,筆者選取2013~2017年的數據進行分析,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稅務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其中2017年制造業增加值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宏觀稅負為每年稅收總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其中某產業的宏觀稅負為該產業的年度稅收收入占該產業GDP的比重;稅收彈性為稅收增加額占GDP增加額的比重;稅收協調系數為產業稅收比重除以產業增加值GDP比重。如果稅收協調系數大于1,稅收貢獻偏高;如果小于1,稅收貢獻偏低。
1.制造業稅負高于全國宏觀稅負。2013~2017年全國制造業宏觀稅負水平分別為21.78%、21.96%、21.0%、20.98%和21.53%,略呈下降趨勢。同期全國宏觀稅負分別為18.57%、18.51%、18.13%、17.53%和17.45%,制造業的宏觀稅負高于全國宏觀稅負約3個百分點。
需要說明的是,制造業稅負是根據《中國稅務年鑒》中的年度制造業稅收總收入除以當年的制造業增加值得出,這里的制造業稅收是稅務部門負責征收的稅收,不包括海關征收的關稅、船舶噸稅等稅種收入;全國宏觀稅負是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年度稅收總收入除以GDP得出,這里的稅收收入包括關稅和船舶噸稅收入。因此,如果考慮關稅和船舶噸稅,制造業稅負與全國宏觀稅負的差異可能還要大。
2.制造業的稅收貢獻總體偏高。評價制造業的稅收貢獻主要通過稅收彈性和稅收協調系數兩個指標反映。通過計算2013~2017年的稅收彈性,筆者發現制造業稅收彈性變化幅度極大,2013年為7.70%,2014年為38.62%,而2015年則降為-35.39%,2016年回升到2.10%,2017年為26.00%,與同期制造業稅負變化相比,差異較大。為了進一步分析制造業稅收彈性的效果,筆者進一步計算了全國總體(包括全部產業)稅收彈性。2013~2017年全國總體稅收彈性分別為19.33%、15.9%、13.8%、9.97%、17.35%,呈V形態勢。這表明營改增對全國整體經濟和制造業的減稅效應確實存在,但2017年后效果就不明顯了。此外,制造業的稅收協調系數在2012~2017年均大于1,說明制造業的稅收貢獻偏高,雖然在營改增推進的過程中,稅收協調系數略有降低,制造業的稅收貢獻略有下降,但到2016年又基本回到營改增前的水平,這進一步表明營改增效應存在時間性。
(二)國際稅收政策變化對我國制造業的影響
近年來,為了吸引資本、減少資金和技術的外流,不少國家競相對稅收政策進行調整,進一步加劇了國際稅收競爭程度,對我國制造業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李敬等(2018)利用構建的產業競爭性、資本異質性和赤字約束的多條件稅收競爭模型進行情景模擬,發現美國公司所得稅稅率由35%降至21%后,將導致我國GDP下降0.6%,可分別提升我國食品加工業、紡織及制衣業、電子設備業、機械設備業產出的0.01%、0.15%、0.72%、0.32%,但降低交通電信業、汽車業產出分別為0.03%和0.23%;與此同時,對我國食品加工業、紡織及制衣業、交通電信業的出口有負面影響,出口值分別下降0.18%、0.19%和0.43%,但電子設備業、機械設備業和汽車業的出口值將分別增加0.53%、1.38%、0.29%。從總體看,美國公司所得稅稅率的下調對我國產業結構產生低端鎖定效應。(1)李敬,雷俐,林黎,等.特朗普稅改的世界影響及我國對策[J].管理世界,2018(2):59-79.
與此同時,美國為了減少對華貿易逆差,自2018年7月6日起,對我國部分商品加征關稅。我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增速呈現下滑趨勢。根據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2018年我國出口總值164176.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1%,貿易順差3949.9億元,其中對美國出口31602.7億元,同比增長8.6%;而2017年我國對美國的出口額為29103億元,同比增長14.5%。與2017年相比,雖然對美國出口額有所增長,但出口增速下降了5.9個百分點。進入2019年后,我國對美國出口增速加速下滑。2019年1~8月,我國出口額109518.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1%,貿易順差17743.5億元,其中對美國出口18782億元,同比增長-3.7%,出口萎縮力度明顯增強。
三、進一步完善我國制造業相關稅收政策的建議
近年來我國積極調整稅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業的營商環境,但制造業總體稅收負擔仍不容樂觀。因此,還需進一步完善稅制,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不斷提高企業的創新研發能力,提高我國制造業的競爭力。
(一)遵循的原則
1.統籌規劃。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涉及到多個稅種,其中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對制造業企業的影響較大。因此,稅收政策的調整應統籌規劃,在根據各稅種的特點進行調整的同時,提高政策間的協調,形成政策效應最大化。
2.保持政策的穩定性。稅收政策頻繁調整會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企業的投資和決策預期,加大企業掌握政策的難度,不利于稅收政策作用的發揮。因此,我國應適時優化有優惠期限和優惠標準的稅收政策,減少不必要的調整,提高企業的預期。
3.實行區別對待。戴翔利用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提供的世界投入產出表研究發現,我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擁有較強的出口競爭能力;資本密集型制造業雖然還沒有顯著的比較優勢,但已突破了“弱比較劣勢”臨界水平而向“中性比較優勢”階段發展;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目前比較劣勢還十分顯著,沒有跡象表明具有改善的趨勢,與發達經濟體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2)戴翔.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基于貿易附加值的測算[J].中國工業經濟研究,2015(1):78-88.因此,我國稅收政策的調整應區別對待,著力于鼓勵高科技制造企業、鼓勵企業研發,提高我國高端制造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優化有利于制造業發展的稅收制度
基于上述原則,筆者認為我國的稅收政策可以在以下方面進一步優化。
1.繼續深化增值稅制度改革。在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增值稅稅率。2019年3月,我國將16%的增值稅稅率降至13%,將10%的稅率將至9%,保持6%一檔的稅率不變,增值稅稅率有了明顯降低,但與亞太經合組織成員水平相比,調整后的增值稅稅率還處于偏上水平。因此,結合我國稅制結構的特點,建議未來可將增值稅進一步合并為兩檔,標準稅率由13%降低到12%,9%和6%兩檔稅率合并為6%,條件成熟后再調整為5%,同時保持簡易計稅的3%征收率。與此同時,擴大增值稅實際稅率超過3%部分即征即退范圍,將半導體、信息傳輸、信息技術等納入優惠范圍,引導資金更多地投向高科技產品和先進技術,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2.進一步完善企業所得稅政策。適當下調企業所得稅名義稅率,擴大15%低稅率的適用范圍并統一有關企業的資格認定標準;統一小微企業口徑,采用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統計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2011年下發的《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界定企業所得稅中有關小微企業的標準,并將小微企業的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降低至10%,小微企業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100萬元減按50%計算,保持政策的穩定性;適當提高利息費用扣除標準,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進一步提高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或適當擴大加計扣除75%比例的范圍;進一步加大制造業資本費用化處理的力度,鼓勵企業投資;對取得創新性成果的企業,可適當給予減計收入優惠,提高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對軟件、信息、科學研究等行業的職工教育經費支出允許據實扣除,鼓勵企業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適當考慮對企業取得的境外股息給予免稅政策。
3.改革其他稅種。適當降低城市維護建設稅的稅率;進一步完善企業資產重組中的印花稅、契稅等相關稅種的優惠政策;適當降低城鎮土地使用稅適用稅額標準;在提高費用扣除標準和增加專項附加扣除的基礎上,完善股票期權個人所得稅政策,加大對高端制造業人才的個人所得稅激勵。
(三)通過政策組合拳降低企業綜合成本
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除了稅收成本之外,制度性成本、收費成本、財務成本、社會保障成本、電力成本、物流成本等都極大地影響著企業的經營效益。應繼續清理和規范審批、資格認定、檢測測試等環節收費項目和收費標準,簡化行政審批程序;健全中小企業融資機制,降低融資成本;適當降低“五險一金”繳費率,降低企業用工成本;進一步降低電力價格和物流成本。通過多方努力,降低企業的綜合成本,增強企業的活力,提高制造業企業的競爭能力。
(四)優化納稅服務環境
納稅人對稅收營商環境的關注焦點除了稅收負擔以外,還包括獲取稅收政策難易度、辦稅時間及辦稅成本。因此,在國稅地稅機構合并工作完成后,應著力提高依法治稅水平,規范稅務部門的工作流程,不斷優化納稅服務環境。一方面,應全面深化稅務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優化審批流程、減少申報資料、縮短審批時限,改進稅收優惠備案方式,實行涉稅資料清單管理,推動涉稅資料電子化報送;另一方面,應減少稅收優惠政策落實偏差,稅務部門要及時掌握和了解制造業的動態稅負情況,創新政策傳導形式,加強和其他政府部門的協調溝通,明確辦稅流程,減少稅收優惠政策認定程序煩瑣現象。與此同時,要建立統一、規范、高效的電子稅務局,提供便捷的網上辦稅服務廳,減少納稅成本。